








”你爱我,我也看到你
心灵的美丽和明亮
然而我还是我,渴望
迷失,像光和光的汇合”
机械制造出的波涛拍打着大理石的边岸,如同近在咫尺的,海洋的心跳。苍白的月光映于水波,用亘古的寂静吞没着生的喧嚣。
血的味道在宽阔的水域中弥散开来,像是一场宴席的序幕与终结。
庞大的水流中,再怎么鲜艳的红色都只是昙花一现,如同自己逐渐斑白的头发,在所有的时间中那样。
逐渐苍白的尸体在水底终被水藻缠绕,小小的鱼儿凑近了静默的脸,一点一点,啃食着曾经的主人。衰老的人鱼轻吟着诗句,游曳到尸体的上方。
她俯视着他,但并不像是那个流传甚广的童话。
她轻吻了他布满皱纹的额头,将他带到水池的最深处。水草,岩石,沉没的财富目送着着一切。她亲吻他的嘴唇,单薄,苍白,如同枯萎的叶片。洁白的细沙被捧起,于水中缓缓落下,刺伤涣散的瞳孔。苍白的脸上已不会再有痛苦,所有的怨憎所有的恐惧都已被温暖的水流带走。
衰老的人鱼拥抱了死亡,拥抱了这具尸体,她带着他升上水面,又在最高处将他放开,与他一起自然地下坠。
人鱼开始唱歌,悠长的,如同鲸吟。
”爱情带着一把利刃而来,
而非一个羞答答的问题”
沉没于沙中的一只财宝被撷起,黄金与宝石的手柄依旧华贵而美丽,但铁铸的刀刃早已失去了它的锋利,时间与海洋使它腐朽,但依旧让它美丽。歌声逐渐嘹亮,热烈,如她发末的红色。
”爱情,是一个疯子,
执行着他疯狂的计划,撕扯着衣服,
在山中奔跑,喝着毒药,
现在,安静地选择寂灭”
锈蚀的刀刃将布料割裂,属于社会的皮毛褪下,便只剩最原初的,人。
”大地,大地,海洋,
海洋。
海洋臣服于巨轮,
承受降临于她的一切。
告诉我,海洋会不会
因这样的臣服而变得更糟?”
她牵起他的手,两只发皱的手,终于在水中交握。尚未褪下的布条如同轻幔,环绕着水中的舞者。
”知音,我的知音,
人类,从来都是窃贼。
窃取光阴,名声,爱,自由,与魂灵的共鸣。”
”你的心脏如同鸟儿,
突破肋骨血肉的樊笼,
向我飞来。”
”我的胸膛中
也永远
为你留下一根枝条。
当月光被海浪吞没,当船锚没入流沙,当礁石开出野花。
当我吻你,当你爱我。”
————————————————————————
蒸汽的机车嗡嗡作响,工厂为着新一轮的订单开足马力,商人们谈论着最近流行的趋势与歌剧,海浪拍打着整齐的堤岸,船只拔起铁锚,海洋于此宽阔又狭小。因人鱼贸易而繁荣的都市,从不会缺少故事。
玻璃厂抛光的砂轮配上纺织工的丝绒,街头流行的朴素小吃配上薄薄的金箔,远航的勇士得到邪恶海妖的青睐,财富与爱情中掺杂进仇恨与阴谋。远在天边又唾手可得,冲突但又和谐,人们总会喜欢这样的故事。
罗纳德·哈珀,今天也在为这样的故事而奔波。高尚的行业标杆记者总是为真相,道义奉献自己的努力,鞋子,腰准键盘与手腕。但大多数的人类终究只是普通人,作为一个普通人,为了自己的钱包与生活而努力,是再正确不过的事情了。
早早地乘上尚不算拥挤的有轨电车,让疲劳的双脚稍稍歇息,哈珀开始梳理同事们在前期调查中获得的已知信息。
阿尔瓦罗·科伦坡,著名的印象派画家,收藏家,艺术评论家,几日前被发现溺毙于饲养人鱼的水池中。遗作将于四日后参与拍卖,应拍卖行的邀约,罗纳德所在的杂志社将对这名艺术家的死亡进行报道,为这场拍卖超热气氛,关注此事的人越多,这副遗作越是能被炒出高昂的价格。毕竟最昂贵的画家总是死去的画家。为此,杂志社,以及作为主要跑腿人员的哈珀将会获得不菲的佣金。佣金是拍卖金按比例分成。虽然绝对不及画家家属及拍卖行获利的十分之一,但如果像老板画饼时所说的那些,自己至少能够少奋斗小半年。
所以在这件事上,真相或许并非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笔下写出的东西,变得精彩,有趣,吸引人们的眼球。
与这位画家的家人联系后,最终将采访的地点定为画家于海边的一处别墅。到电车能够到达的最远端,还要走上不少的距离。红砖的小路虽然美丽但略显崎岖,未经过良好维护的海滩散发着些许水腥气,茂盛的植被中藏着大量的蚊虫,让人不得不挥手去驱赶。
而终于走进了那间被白栏杆与藤蔓的别墅,未经休息哈珀便继续向下,走人了别墅的地下走廊。那是约定好的,与家属商谈,并且瞻仰遗作的地方。那也是这位画家陈列收藏品,饲养人鱼的地方。
踩上柔软的波斯地毯,脚步声被绒毛吸收,拍打在玻璃上的单调浪声与心跳的节拍重合。地下走廊的一侧是巨大的水池,即使是在白日里,有阳光滤过幽深的水底,幽蓝色的暗光依旧会让人感到压抑。
而走廊的另一侧是不适感最大的来源。
为了让人们的目光集中于艺术品上,一些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环境光通常较暗,只在艺术品上留下足够的光源。这里也是如此。有着优雅暗红色的墙壁上悬挂展示着各种艺术品。不同艺术家的画作、雕塑、来自不同文明的古物,一一陈列在这面墙上——以一种可以称得上是狂乱的方式。
或是侧置,或是倒悬,天国与地狱颠倒,盖布在努特之上,鸟儿坠落向天空。正确地直立在地面上的瓷瓶在这里反倒算得上是异类。
一些小的艺术品或许还不会给人留下过深的印象,位于这段走廊的中央的巨幅岩彩画则以它的庞大与鲜艳吸引着每一位过路者的目光。
这依旧是一幅倒悬的画,整体黑暗的氛围中绘制着巨浪当中的船只。与一般此种主题中,船只总是在巨浪中破风航行,表达着水手们勇气与决心的形式不同,这幅画中所描绘的,是纯粹的绝望与死亡。船只被巨浪撕裂,桅杆折断船帆尽毁,水手们或被海浪吞没或被断裂的木板刺穿,伤口中涌出的血液是此副画作中唯一的亮色——浓郁的,不符合常理的色彩刺穿了整幅画作,像是最新鲜的血,或是最明亮的火,勾魂摄魄的色彩,也抓住每一位过路者的心。
轻盈的歌声响起,如同海妖诱惑人的低吟,是坠入海中水手唯一的救赎,也是最深最黑暗的绝望。死亡必定到来,那么死前所听到的一切,究竟是绝望中最后的安慰,还是更深沉痛苦的前兆?
但,为何会有歌声?
意识到这一点的哈珀猛然回头,看到了一束枯萎的火。
衰老的人鱼倒悬在水中,静静地凝望着画中的风暴。褪色的红发在水中散开,灰绿发浊的目光顺着波涛流淌而来。
她开口,歌唱
”当我的肉体静止、灵魂孤寂的时候,我身上为什么绽开这朵荒唐的玫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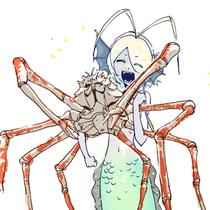
得到身体后不久兰伯特·邓肯意识到上个主人留给自己的不只是身体,名字和在人类社会活下去的方法。
“什么?”他愣了一下
“您可以通过这张苏西·马什签发的支票兑换的金额一共是十万元,我想问您需不需要偿还贷款,您这里的记录显示您的还款期快到了,如果逾期不还我们将会没收您的抵押物,您的抵押物是一处住房。”银行营业员用甜美的嗓音说出了一个让他感到恶寒的消息。
还有数不清的债务。
最后他干脆把这件事丢到了脑后任由银行收走了那套房子,他可不想被银行绑着还款。
但很快他又被其他催债的找上门来,这十万元又成了飞走的烤鸭,银行的贷款只是债务的冰山一角,他仍然欠着他的债主不少钱,那是几个十万都不够算的巨额数字。
“兰伯特·邓肯的人鱼死了,那也是你的债务水涨船高的原因,”他本想撇开头掩饰心虚的目光却被对方用手杖推着脸把头转了回来,那双同样晕染着美丽蓝色的双眼仿佛能看穿这具身躯的伪装,“或许你有什么头绪吗?”
“我有什么头绪?”
似乎是被他装傻的样子逗笑了,总之他的债主不再紧皱着眉头,“你杀过人吧。”他说。
从此兰伯特·邓肯从诗人摇身一变成了用人命还债的杀人犯,但至少他不必只为债主工作,只需要随叫随到。
这次也是一样。
“你在逗我吗,”记者满脸写着对他的话的不信任,这是个聪明人,听话地跟着兰伯特到了他的雇主的房子,兰伯特也懒得绑他,“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把那个人……杀了?”
“我要知道什么,”兰伯特一脸无辜,“知道他得死还不够吗?”
说起来也怪他,他搞错了这个男的的住址。他跟着男人来到这间房子,摁下门铃后他被客客气气地请进了屋,那个男的想先解决掉他但是被他先一步割断了喉咙,为了掩饰伤口他用厨房里的斩骨刀砍断了他的脖子。
他以为这里就是他平常住的地方就离开了,没想到他的住址并不是这里,这只是他租出去的一套房子。但等他意识到并去纠正这个错误时尸体已经被这个房子的租户发现,而警察则把那里围的像监狱一样。当然,他有自信不被发现马脚,却挡不住事情可能会被媒体添油加醋的风险,这是他和他的雇主都不想看到的。
结果这个倒霉的记者自己撞上了枪口。还是早就被他预定要见一面的那个。
“那你把我……”记者停顿了一下,“带过来是想干什么?我可不是那种没良心的记者,我不会乱写的。”
“这可不是你说的算的,你那个时候在和谁打电话?”
“拜托,写报道的是我,谁给我打电话很重要吗?”
“很重要吧,你是不是叫——温德尔?我看你的记者证上是这么写的。”实际上他已经把他那个箱子里的东西翻了个遍,很难找不到能证明记者身份的东西。
“……那又怎样?”
“那个男的还活着的时候说过些你的事,你采访过他?”
温德尔的脸色变得煞白,他张了张嘴又闭上嘴用舌尖舔了舔嘴唇,“你的雇主想和我的资助人谈谈?”
“你好聪明啊!真省事,我就喜欢你这种人。”
记者显然没有因为这句话高兴起来。
——————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杰森·哈顿将手放在听筒上等了一会儿,直到第五声响起才接起来,“喂,我是杰森·哈顿。”
“啊,那就对了,很抱歉之前打扰了你和温德尔的谈话。”
是个男人的声音,语气措辞听起来不像是贵族或者什么上流社会的人,杰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他没事吗?”
“那就要看你了,具体的你可以到米德雷大街十九号和我的雇主详谈。”
电话挂断了。他缓缓放下听筒将它放回电话机上,看来他要去的是另外一个地方,他有且只有和对方达成合作这一个选择,从那通电话被挂断这点就已注定。
或许今早不应该答应温德尔再去找那个男人。温德尔曾以人鱼饲养相关的理由采访过那个男人,他通过私人租赁的方式得到了一条人鱼,因为虐待人鱼的传闻而被温德尔注意到。
他唤来佣人帮自己更衣准备出门。
一开始男人并不愿意接受采访,他是个破产了的工厂主,大概是觉得丢人吧。但是温德尔以自己有上层的人脉为条件让他敞开了大门,在里面记者看到了那奄奄一息的同胞。他不知道温德尔是怎么控制住自己的,总之那场采访还是顺利地结束了。
当他走出房子的大门,马车早已在门口等候,他抓住车厢上的把手跨上马车坐到靠近车夫那边的座位上,佣人帮他关上车门,他敲敲身后的车窗,“米德雷大街十九号。”车厢颤动了一下而后开始移动。
在筹备一番后他们本计划昨晚开始行动去解救那条人鱼,但是却得到了男人今晚没有回到这个住处的消息,而人鱼也早已被他转手卖给了不知什么人,好在他们至少拿到了他另一处房产的地址。
最后马车在指定的地址缓缓停下,这是被漂亮的二层建筑装满的一条街道,杰森·哈顿的父亲曾打算投资这里,但那都是以前的事了。车夫为他打开车门,他走下马车站在铁栅栏的大门前按下门铃。
——————
伊沃·基尔南并非没有听说过温德尔这个记者,倒不如说是这个名字出现在他的回执报告里太多次,好几次这个记者都会在他的人对被租借的人鱼进行回收时“恰好”或者“提前”出现在那里,也因此让兰伯特把他绑过来本是预定之中的事,只不过这次他自投罗网却是出人意料,而且还给了他一个能直接和他的资助人谈话的机会。
一个记者哪里来的那么大的能量做那些事,有资助人是肯定的,那个已经死了的家伙也坐实了他的猜想,现在那个记者变得无关紧要,直接从源头控制他才是根本。
而现在他的资助人——杰森·哈顿正坐在伊沃的面前。
“没想到现任的哈顿侯爵原来这么年轻,”伊沃将所剩不多的烟蒂在烟灰缸里摁灭,“对于那起不幸我深表遗憾。”
“寒暄就免了吧,”年轻的侯爵看起来没有什么耐心,他只想一心救出自己的同伴,伊沃看得一清二楚,“你想要什么。”
“首先,从这件事放手,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写一篇别的文章转移视线。”
“可以。”
“第二,以后不许再来干扰我的生意,”他抬起手阻止已经张开嘴打算讨价还价的杰森,“你的小老鼠出现太多次了,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件事我可能一个人做不了决定,”杰森说,他皱紧眉头语速极快,“我需要见到温德尔。”
“你可以,哈顿侯爵,这没什么不可以的。还是说在你们的革命游戏里他才是那个领袖?”
这次杰森更加坐不住了。
“只有你点头了我才会告诉你他在哪,你明白了吗?我不是在建议或者询问你,我们之间没有条件可谈。”
“……所以你已经知道那条人鱼被转卖给谁了?”
“不然我为什么要杀了他?”
杰森的手从眼镜下面伸过捂住了脸,尽管看不到他的脸但伊沃感觉可以看到他的大脑在如何权衡各种利弊,他决定再激他一把,“如果你无法决定我也并不介意,革命总是免不了要流血。”
这次杰森抬起了头。
“他在哪?”
——————
一周后,题名“马戏团知名女演员竟惨遇杀人事件”的新闻登上了报纸头条,伊沃扫了眼标题,合上报纸将它卷成一个圆筒摁下打火机开关让火苗爬上灰色的纸张,在火焰的包裹下这张白纸黑字的易燃物掉进火盆变黑卷曲解体最后成了容器里无法分辨的一片灰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