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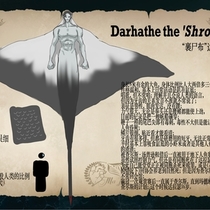


人鱼协会的清洁工从来都是那么有效率,有效率到让道林觉得没必要,好在这间屋子大变样之前道林抢救出了些许有用的东西。
“中央银行年贷,伯利辛根借贷,基尔南私人人鱼转租……”他把桌面上的借据和合同一张张捋过,终于确认了一件事——这个名为兰伯特·邓肯的家伙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和疯子,几十万的债务,就为了一条人鱼。
现在这个数字恐怕还要翻个番。
“你该不会以为把自己的房子变成那样儿的人还能有什么理智吧?”芙蕾雅看着道林最后把这些加起来抵得上普通工薪家庭好几十年开销的纸片子小心折好收进外套内兜,他们现在在道林的事务所里,她坐在道林的对面,背光的侦探更显消瘦,这让他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一些。
而迎着光的记者已经摘掉了她的帽子,比起道林她年轻的皮肤白皙细腻,淡淡的香味从她身上散发出来,他觉得那应该是一种他叫不上名字的香水,“那你怎么看?”
“现在是你采访我?”
“集思广益。”道林做了个请的手势。
“嗯……或许他是为了逃债。”
“怎么说?”
“很简单,这个疯子失手杀了他的人鱼,于是他就要面临协会——或者那个转租人的巨额债务。是我我就会逃。”
“可你也说了他是疯子,他怎么会判断出需要逃跑呢?”
芙蕾雅的眼睛微微睁大,她下意识地挪开自己的视线看向别处,“好吧,”她稍微调整了一下坐姿,“你问倒我了,那我就不知道了。或许这种精神疾病会间歇发作?”
实际上这个问题甚至把道林自己都问倒了,死掉的人鱼,消失的主人……他隐约觉得这和一年前的那起事件之间有什么关联,却无论如何都抓不住那条连接它们的线。
他在迷茫中送走了芙蕾雅。
“等你的好消息,先生。记得不要把这个独家头条透给别人。”
那么现在他要先按顺序一个个地寻找线索,比如给兰伯特·邓肯发了这些纸片子的家伙们。
——————
毫无疑问贝尼迪克特·伯利辛根是个头脑灵活的商业奇才,他对市场走势有着敏锐的嗅觉,而他也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这也是他决定在人鱼行业一掷千金的原因。现在他就在享受他的回报,人鱼协会荣誉副会长的办公室如此宽敞明亮,光是坐在这个房间里他都能捞到不知比起他交的入会钱多多少倍的油水,以至于他有时候都忘了自己名下还挂着一个金融公司这件事。
提醒了他这件事的是一个身材瘦削的男人,他两颊凹陷但并不病弱,而那双紫色的双眸时常以一种观察似的目光扫过他和这个房间的摆设。贝尼迪克特有一个称不上是特异功能的能力,那就是他总能看出谁能让他捞一笔而谁是来找麻烦的,这个男人显然是后者。
“嗯,你说的没错,”他点点头打了个响指,房间里的女秘书为他们端上茶水,而后在胡契克的眼神暗示下离开了房间,“我确实有一个借贷的业务,专门为那些想要拥有——或暂时拥有一尾人鱼的人提供些许帮助。”
“所以你也给这个人借过钱吧,”男人从外套的内兜里拿出一沓皱巴巴的纸从里面抽出一张展平放在桌子上转过来推给他,“这是贵司开具的贷款合同。”
贝尼迪克特挑了挑眉,他将那张纸拿起看了眼最后的落款,上面明明白白地签着他和另一个人的名字,“对,他想要租一尾刚刚分化性别的亚熟期人鱼,我记得这个男人,兰伯特·邓肯。”
“他长什么样?”
现在男人的眼神里又写满了赤裸裸的探究欲,贝尼迪克特耸耸肩,“有没有人告诉过你最好不要去打牌?”
“什么?”
“当你身体前倾,微微侧头将耳朵靠近对方时通常都代表你迫切地希望从对方那里得到信息,”当男人猛地坐直身体为时已晚,贝尼迪克特摊开双手吹了声口哨又合上手掌,“情况变了,道林先生,该我询问你了。兰伯特·邓肯怎么了?”
“我正在找他。”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说一些心虚话的时候应该看着对方的眼睛说?”
道林一拳砸在桌子上,他受够了这个男人的戏弄,“你这人到底什么毛病!你该不会是情报安全局的审讯员之类的吧?!”
“小玩笑而已嘛!冒犯了您我很抱歉,”他无所谓地耸耸肩,身体后仰靠在椅背上,看起来不太像很抱歉,“所以继续刚才的话题,邓肯怎么了。”
“他失踪了。”刚大吼完的的道林的声音听起来闷声闷气,满是不愉快。
“哇哦,那真是太遗憾了。”
“他是失踪了,不是死了。”
“我知道,我只是例行公事地感叹而已,那他的人鱼呢?”
“人鱼死了。”
“那真是太遗憾了。”这次贝尼迪克特的语气听起来认真了一些。
“……听起来你更在意人鱼一些。”
“毕竟那可是协会的重要财产,可是租赁人们总是不懂得爱惜,”他一边摇头一边啧啧做声,“不过我刚看到那个男人的时候就知道他养不久那条人鱼,毕竟他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
“你知道他很穷?”
“资产评估是一家合格的借贷公司应该做到的基础,他的一套房子已经抵押给了中央银行,我们没法动,所以他只能用人身劳动来抵债,如果逾期不还他就会成为我的——”
奴隶。道林在心里帮贝尼迪克特说出了那个碍于对方文明人身份没有说出来的词汇。
“当然,这一过程并不着急,如您所见我不缺那点钱,但是要是他本人跑了我还是很头痛的,”他抬了抬下巴,“先生,茶快凉了。”
当道林被滚烫的茶水烫了舌头时贝尼迪克特哈哈大笑。
——————
贝尼迪克特·伯利辛根的捉弄让道林的舌头又痛又麻,于是他婉拒了伊沃·基尔南的咖啡。
“好吧,”伊沃摆了摆手,他的助理带着咖啡壶离开了这个房间,“所以你是到我这里来找人的?”
尽管伊沃·基尔南不像伯利辛根那样不着调但看起来也绝不是好相处的那一类,不过道林更喜欢和这种人打交道。尤其是他在被当成猴儿耍了之后。
“你见过他吗?”
“签完转租合同之后吗,”伊沃摇了摇头,“没有,我连他的人鱼现在什么样都不知道。”
“那条人鱼死了。”
不苟言笑的商人怔了一瞬,但马上露出了然的神情,道林不知道他究竟清楚些什么,“所以您的意思是邓肯先杀死了我的人鱼又畏罪潜逃了是吗?”
这次轮到道林摇头,“不,他只是失踪了,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要自欺欺人了,先生。事情变成这个样子你我都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是说你道听途说了什么有意思的传闻?”
“只是一般的实事求是,我倒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笃定邓肯逃跑了。”
“下手没轻没重的家伙的惯用伎俩,”自打道林见到伊沃到现在这个商人终于嘴角微微上翘,他轻笑一声,这让道林感觉有些不舒服,“我总是能在各种奇妙的地方逮到他们,为了逃债他们真是开动了所有的脑筋,至于之后的故事……你应该不会想知道。”
“……追回人鱼的工作是您负责吗?”
“对。”
“这是协会默许的吗?”
“你指什么?”
“你全部的这些生意,或者说——业务。”
当伊沃那双蔚蓝的双眸直勾勾地望向道林像是要从他身上挖出些什么的时候,道林忽然明白了伯利辛根为什么总是能看穿他,他无意中也曾不加掩饰地流露出了这种刨根问底。
“为什么你会觉得乌奈还有那个伯利辛根什么都不知道,”伊沃调整了一下坐姿,他直视道林的眼睛,“侦探,我知道你的工作就是寻找真相,但是你要知道有的真相是会消失的,只因人们默许如此。”
——————
之后的好几天道林都一无所获,他从银行职员那里知道了邓肯大致的长相,金棕色的头发,和他相似的瘦削的脸颊,刮得乱七八糟的胡子,蓝色的眼睛。但是就算知道这些也毫无用处,捏着这些特征在这座城市简直就是大海捞针,更糟糕的是另一边芙蕾雅已经开始催促他,她的头版头条早已等候多时。
这个什么活都没干的女人居然还敢像赶驴一样威胁他,又是无功而返的道林从邓肯居住过的公寓出来,这里已经被清洁工们打扫得干干净净,楼下的报案人也已经搬走了,他得到了一笔举报酬金,足以让他脱离这栋破旧的小公寓,但是道林的噩梦还没有结束,他还得想一套说辞去应付芙蕾雅·怀特。
他就这么心不在焉地走在街上,忽的他的肩膀撞上一个和他的身高相差无几的男人,“喂!”他的肩膀被撞得生疼。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下巴上贴着创可贴的男人朝他挥了挥手大声道歉后便立刻转身加快脚步离开了这里。
道林一边拍着衣服上的褶皱一边习惯性地因为这起倒霉事皱起眉头,这种冒冒失失的男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少一些,他甚至连胡子都没刮好……这时银行职员的描述让他立刻抬起头望向男人离开的方向,但他的身后只有人来人往的街道,那头金发再也无法寻觅。他将手插回口袋,口袋里细腻的纸制品哗啦作响。
——————
过了一会儿那个令他难以应付的女声响了起来,“您好,芙蕾雅·怀特,哪位?”
“是我,道林,非常遗憾地通知您,怀特小姐,我们的合作要结束了。”
“……你说什么?!”
“就是字面意思,结、束,这段被您使唤的日子我过得非常不愉快,希望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见面,再!见!”
“那我的头条怎——”
听筒落到电话机上的声音截断了女人的声音,即使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道林仿佛也能听到芙蕾雅·怀特歇斯底里的愤怒叫喊,一种报复和脱离苦海的快感让他感到浑身舒畅,他踢踏着舞步到衣架前摘下帽子戴在头顶,或许去喝点小酒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他的桌子上躺着一张像是刚学会写字的家伙写出来的纸条,或许有的真相就是那么简单。
——————
这就是真相,你好,先生。
兰伯特·邓肯敬上

阅读警告TAG:R18,精神分裂,微克,非人车……我还漏了什么吗?哦,对,祝费尔南迪·乔纳森父亲节快乐!
————————————————————————
一八八七年和其他年份有何不同?世界在此之前以及之后都不断的产生变化,历史大事接连发生,周围吵闹不休,但费尔南迪的一部分被冻结在此地。
一八八七年的冬季,他成了鳏夫,他的老婆给他留下了三个孩子之后撒手人寰。
而在那之后,他偶尔还是会收到请柬,来自他无礼的客户,要求他“携夫人一同前往”。
他想:这些该死的人是否故意耍弄他?难道他们没有见过公报上的讣告?没有参加过他老婆的葬礼?可怜的莉莉娅已经死了!被埋在地底下!而他们要他和她一同赴宴!
他甚至知道他老婆会说:哦,费尔南迪别生气,他们有可能不知道啊,那些无知的外国人根本没有看本地报纸的习惯,打起精神来,亲爱的你需要他们……需要他们的钱呢。
她说到这就会笑起来,红色的头发会随着笑声颤动,然后她会拍拍他安慰道:去吧,拿上你的帽子和手杖,等我去换一件裙子我们就出发,事情总会好起来的。
但是,她错了,事情不会好起来了。
一八八七年冬天她就大错特错。
在那之前,他们不知道她已经重病,如今,他们不知道她已经死了。
他想到,在他母亲死后,他的父亲总是不停打开家里房间的门查看,这个可怜的人,不管在做什么事,总是突然定住,微微偏头,他一定是听某些声音,随后他就跳起来去拉开门,喊道:快来啊费尔南迪!你妈妈在那呢,她真的在那呢。
他就得放下手上的工作,去把那些门一扇又一扇,一遍又一遍地关上。
在他父亲的想象里他的亡妻在门后生活如常,四下走动,整理床单,打毛线衣,读报纸。那他当然要去找她啊!
医生告诉费尔南迪这只是臆症,但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一次他父亲打开了家里所有的门仍然一无所获,于是他拉开大门茫然地走上街头,去找他死去的爱人。
而那时费尔南迪忙着和玻璃发明人扯皮,官司一场接着一场,手头拮据到请不起居家女佣,他试过劝说,上锁,请邻居或报童帮忙照看,但父亲仍然能找到办法逃走。到他第四次走失,好不容易找回之后,费尔南迪不得不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直到一八七七年,那时费尔南迪的事业逐步走上了正轨,不过他仍然忙着搂钱,顾不上把父亲接回来,那时他也还没有结婚,天哪,如果那时莉莉娅在就好了!
但——不可能了,因为莉莉娅是在一八七九年认识他的,而*那件事*发生在一八七七年的冬季,*坏消息总在冬天来*,他收到一个盒子与信件:尊敬的乔纳森先生,十分抱歉地通知您,您父亲病情日益严重,我们尝试加重剂量,但并没有好转。本月二十一日不知怎的他设法逃脱了病护的看管,躲开了守卫,然后步行了两英里,通过重重阻碍,打开了地下焚化炉的大门……您知晓他的病情,我们由衷地感到抱歉,并会退回您在本院缴纳的所有费用,请您务必节哀。
他拿着那个盒子,来回翻看,里面的东西沙沙作响。他心想,这下*事情不会好起来*了,不知怎的,他把耳朵贴上了盒子光滑的木质面,因为在外面放太久它通体冰凉,冻得他打了一个寒颤,但里面什么声音也没有。没有他母亲搁下茶杯的声响,也没有他父亲开门招呼妻子的呼唤。那是臆症,他紧接着想,医生说的,那是臆症,不是精神病,而我是正常人,不可能听到什么。
他把父母合葬在教堂的坟地里,现在莉莉娅也在那里了,挨在他们旁边,墓碑极其简单,只刻着她的名字以及四个字:长眠于此。
他不需要那些华丽的致辞。
等到他死之后,他就躺进去,然后在那四个字之前加上一句,“携丈夫”。
莉莉娅携丈夫长眠于此。
……
一八九五年,费尔南迪已经习惯了寂寂无声的妻子。医生说,那只是在他心底的幻影,没有关系,每个人都会有经历悲伤的过程,人们会拒绝相信爱人已经离开。
费尔南迪点点头,他视线落在医生身后的窗户边,*莉莉娅*正在站在那里往窗外眺望,脸上带着困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晚了街上还有那么多马车。
医生对此毫无察觉,还在继续说:之后他们会愤怒,会埋怨为什么只有自己如此不走运,这些情感会持续很长时间,消耗大量精力,不过在我来看,最终人们会接受现实。
他身体往前靠,盯着费尔南迪:最近您有听到任何声音吗?
费尔南迪摇摇头,他的妻子一向安静:我只是想,如果是莉莉娅恐怕会劝我对孩子们宽容一些。
医生:那很好啊,乔纳森先生,这只是您思念妻子的缘故。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不过,您看起来需要好好睡一觉,我给你开一些安神的药吧。
他拿起笔在本子上一通乱画:您或许应当养一只陪伴宠物,有充分的研究表明它们有利于缓解压力。
*莉莉娅*站在门边,等他为她开门,听见医生的建议她欣然点头,于是费尔南迪站起身道:也好,*她一向喜欢这些*……我是说,我想她也会建议我这么做的。
他摸到了门把手,为她拉开门,门开了一条缝,他屏住呼吸但什么也没听见。
门外,秘书正坐在办公桌后拿着小镜子涂口红,看到他出来,她“啪”地合上镜子露出职业性的微笑,一边按下桌面呼叫器,通知候诊室下一位预约病人可以入内,一边递给他一份账单。
费尔南迪签支票时想,我需要他,我需要有人告诉我,这是正常的,老天,我只是思念过度。
人鱼馆。
*莉莉娅*停在那只人鱼前。
他发现那只人鱼简直和她一模一样,确切地说,是和一八七九年的少女莉莉娅一模一样。她们都有同样的红发,微笑,和白皙美丽的*奶子*。他和莉莉娅都很满意这只昂贵的陪伴动物。
它虽然有人类的容貌,但它毕竟是*动物*,费尔南迪很清楚地明白人鱼和人类的不同,虽然听过下流又古怪的传闻,它们惊人的美貌会让人忘记一切,但当它从他手上接过生鱼肉咀嚼,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动物的感觉就更为明显。
它是一只住在缸子里随心所欲过日子的鱼,潮湿,冰冷,带着咸味。
他完全能够区分两者的不同!
只是——
看哪,莉莉娅,你在一八七九年还多么青涩,像是夏季刚成熟的葡萄。看看它的脸,看看它隔着玻璃冲我笑呐,那让我想起咱们在炎热日光下度过的快活时光。
比起定格过去的黑白照片,它是多么鲜活生动,仿佛一切昨日重现?
他越来越频繁地打开那扇门,那扇通往人鱼房间的门,只要想到长着莉莉娅的脸的人鱼就在那里,*莉莉娅*就在那里,他就无法控制自己。
医生:您已经完全摆脱了失眠的困扰……您没有在我开的药之外再吃别的药吧?没有?那很好,看来陪伴动物起到了作用。
是的,我感觉好一些了。费尔南迪点头赞同,我的孩子们也很喜欢莉娅。
他们当然喜欢,他们见过莉莉娅的照片,那只鱼就是他们怀念母亲的情感寄托,他们分不清照片和活着的幻影的区别。
但我又何必告诉医生此事呢,他只以为我养了只狗,养只狗就会使人振作起来,事业蒸蒸日上,就让他这么以为好了,总不会有什么坏处,再说或许养狗的确会对下一个病人有益,费尔南迪冷静地想。
他告辞时,医生与他握手:我从报纸上看到您连续收购了数家公司,足以证明您精力充沛,能胜任繁杂的工作了。事情会好起来的,会越来越好的,祝你走运,乔纳森先生。
他拉开门,门外还是那个秘书和一张支票。
一切如常,医生再一次给了他支撑下去的信心,*暂时地*,但他的人生已经岌岌可危,在他心底的某处隐隐知道,*事情不会好起来了*,事情永远不会好起来。
因为莉莉娅开始在门外叫他。
他听见一阵古怪的韵律,一种从没有听过的发音方式,既像是动物发出的嚎叫,又像是歌剧演员的歌声,从门后传来。
他打开那扇门,在黑暗之中,缸中之物散发着奇特的魅力。
*上去,亲爱的,你在这里可够不到它,*莉莉娅说。他听从她的吩咐爬了上去,那只鱼湿淋淋地从水中冒出头,一头红发紧紧贴在她脸的两侧,黑暗使他只能看到一个人类的轮廓。
他伸手把她拖出水面,搂进怀里,冰冷的水浇透了他的睡袍,两只白生生的胳膊圈住他的脖子,她的奶子压在他滚烫的胸上,他皮肉下的心脏在疯狂跳动,而她在他手里逐渐发烫,*好了,今天,你应该搞一搞她下面,奶子我们已经玩够了*,莉莉娅的声音仿佛贴在他耳后发出来的,*她多美啊是不是*?
是的,她很美,一八七九年底的盛夏,有一天中午,他们规规矩矩地会面,会客室只得他们两个,然而——莉莉娅翻身骑到他身上来,他硬得像是上了膛的手枪,她绷紧的大腿肌肉夹住他,抱紧他的头,那是一件裙摆极长又暴露胸部的裙子,她差点让他窒息。
他们度过了极其快乐的午休时间,当女仆推开门问他们是否需要下午茶,他坐在背对门的靠背椅上,莉莉娅听见脚步声,早已从他身上溜下来,站在他身侧,裙子落在地上完美地遮住了她赤裸的屁股和脚,即使精液正顺着她腿根往下淌,她也照样稳稳地回答她:不了,茜茜,我们正在讨论弥尔顿的小说,可顾不上喝茶呢费尔南迪你说是吗?
她弯腰作出询问的姿势,但手却按在他那个地方,他一把抓住她手腕咬牙道:是的,弥尔顿说得好呀,“与其在天堂里做奴隶,倒不如在地狱里称王”。
她低声窃笑:哦我的乔纳森是真的读过好些书。她又抬头对女仆道:去干你的活儿吧茜茜我们这儿不需要什么。
他听到女仆鞠躬、退出去并关上门的声音,然后莉莉娅摸到他的脖子上,她刚刚摸过他的性器,还带着一点潮湿的腥气,纤细的手指从他的脖子滑下胸膛,抬起他的下巴,弯腰亲吻他,拉起他的手去摸她翘起来的屁股,淫邪地道:乖乖,你应该搞一搞下边儿,看看我有多湿,奶子我们已经玩够了是不是。他感到全身血液往一个地方奔涌而去,他跳动的心脏只能发出一个喊声——
*莉莉娅!莉莉娅!莉莉娅!*
他顺从地伸手去摸她的下身——
他没有如预期般摸到那个带给他极乐的炙热、潮湿的深谷,而是一整片滑腻又坚硬的肌肉,覆盖着冰凉细密的鱼鳞!
那鳞片边缘无比锐利,像一把刀子猛地割开他的手!鲜血立刻涌了出来!
他猛地把那条鱼推下水,发出巨大的声响,那只鱼翻出水花,一头扎进水里去了!
炎热夏日如潮水般退去,他呼吸急促,瞳孔因为惊恐而放大,手上剧痛无比、血流如注,站在玻璃平台上不住发抖。
黑暗和一股挥之不去的腥味袭击了他,*怪物*!
那漆黑的水面再度荡开一层层的波纹,水面之下则更为幽深,*怪物怪物怪物怪物水里的怪物*!
这个词在他脑子里横冲直撞,他手脚发软地抓着楼梯往下爬,他看见——
透过那些铁制的横栏,隔着玻璃,他看见那里面幽闭、漆黑的冰冷海水,一只从地狱里来的比海水更黑、更深的影子在里面飞快的游动!
它一次又一次地撞击到坚硬的透明墙上!
发出沉闷的响声!
咚!
咚!
咚!
突然!它撞在他面前的玻璃上!她的脸清晰地出现在他眼前!
是*莉莉娅*!
惨白的*莉莉娅*!
他吓得从梯子上摔了下去!他倒在地上,仰面看她,她皮肤白得吓人,红色头发张牙舞爪地飘散在水中!她咧开嘴,露出尖锐的犬齿!
那分明是一个疯狂的狞笑!
这恐怖的一幕很快隐去了,她咯咯笑着在水里翻了个倒仰,迅速弹开!后退!然后又是咚地一声!她再次撞到玻璃上!
他翻身连滚带爬逃回了卧室,把那怪物关在了门后。他跪在地上,血浸透了地毯,颤抖地轻声问:莉莉娅,你在吗?你在这里吗莉莉娅?
没人回答他,不知道何时,那萦绕四周的歌声已经停止了,只剩下连绵不绝的撞击声沉闷地穿透木板,钻进他耳朵和脑子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如同报丧人在夜里疯狂地砸门:开门!乔纳森!开门!
他不敢再去看医生,因为他知道医生会有什么建议:乔纳森先生,恐怕这次您只有把自己送进精神病院了。
他还有三个孩子!假如他去了,那么有一天——这一天不会太远,或许就在这个冬天——三个可怜的孩子会收到那只盒子。杰弗里还没有接触过经营上的事,他的学业甚至还没有结束。永不省心的布雷迪嚷嚷着要给俄亥俄的莱特兄弟投钱造幻想中的钢铁飞鸟。他最小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她还只有十岁,她都分不清*妈妈*和人鱼!
他试过把那只人鱼送走,他向协会写了退回申请,保证就算没有到租赁期限,他也不会要他们退钱,只要他们愿意把这东西接走,他就万分感谢。
但他等了又等,协会没有任何回复,他终于忍不住去询问协会,协会工作人员找出了他的档案袋:是的,我们收到过,可是您当天晚上就给我们发了撤回申请的通知。工作人员疑惑地把两份手写文书递给这个古怪的客人。
撤回通知上的确是他的笔迹,他的印章和他常用的信纸。*她不肯走,她要留在他家里*,他无话可说。
他们终于发展到最后一步,莉娅把他按在玻璃平台上,她爬到他的身上,用带蹼的手握住他的下身,撸动,满是咸味的嘴亲吻他,他们在黑暗里互相爱抚,她让他坚硬的地方插进了她的泄殖腔,那个畸形的穴口隐藏在她柔软的腹下,被坚固锐利的鳞片掩盖,如果他想硬来,恐怕那玩意儿会被割成碎片。
她的腔体收缩是那么有力,可怕的想象伴随着极度的快感,他低声喊叫着扭动胯部,她不让他后退,她按住他的胸,摆动尾部,他疯狂跳动的心脏就在她的蹼下,撞击她的掌心,这只有美丽人脸的鱼学会了很多事,包括如何折磨一个男人,更多的血液涌向他硬挺的阴茎,他含混地求她,她又一次俯身咬住他的下唇,她的奶子顶在他身上揉搓,奶头硬邦邦的,他猛地握住她的腰,*滑腻但劲瘦*,水生生物的力量超乎常人,她在水里也常常如此摆动腰肢,他猛地下压!
阴茎像刀子一样刺入她深处,锐利的快感使他们同时发出喘息,莉娅癫狂地骑他,他灼热的棒状物使得那个湿冷的巢穴升温,性欲如带电的鞭子抽打他的神经,一阵阵从脊柱钻进他脑子深处,他沉闷地哼出声,与她疯狂交媾,她体内涌出微凉的粘液,从两人的连接处被挤出来,她满面潮红,掐他的脖子,鹦鹉学舌般喊他:费、费尔南迪。
她不住吸气,只会叫这个名字。
他拉低她亲吻,堵住了她的嘴,但即使她不说话,他也清楚,她不是莉莉娅,不是人类,她只是一条人鱼。她不但吃他的身体,也吃他的回忆,他是用自己在填满这个怪物的胃口,*尽管他乐在其中*。
只要他和她做爱,歌声就消失了,莉莉娅的声音也消失了,他就可以重获宁静。
不过他心里有数,不管他是不是有商务要谈,有合同要签,不管他的孩子是否长大成人,不管他们有多需要他。
歌声和莉莉娅都在呼唤他,她们会在门后叫他过去,声音不会停止,而他无法抗拒,如今他在门前徘徊,但总有一天他会打开门走出去。因为他知道,穿过那扇门,它就在尽头。
他闭上眼,在强烈的窒息感中射了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