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哥儿。”
“仇哥儿,你看那边。”
仇止命难耐地闭上了眼,嘴角拉扯出的弧度怎么看都像是讽刺。竟会因为微不足道的头痛,而产生幻觉——那名为“过去”的魑魅魍魉。
那道声音似乎有着足够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始终追随着男人,随着心情起起伏伏。
够了。那些曾经,不该堂而皇之地出现,纵然是留有温情的画面,在此刻也足以化作锋利的刀刃,划开那些从未愈合的思念。
他的面容在愤怒下显得扭曲,疼痛的加持更是雪上加霜。
“仇哥?”
仇止命睁开眼。
有一双手从他身边探出,少女的指尖堪堪穿过前方深绿色的长发。少女不信邪地握紧了拳头,却仍是只抓到一把空气。随后她像是发现新大陆般地盯住那三道背影,她举起手,伸出一对拇指与食指,将那对拉拉扯扯的身影框在其中。
“鲨鲨,你能录像吗?”
“在他们出现的时候我就开启了录像功能。”
“干得漂亮。”
“不要做多余的事情!”
“据我所知那个年代并没有任何仪器可以记录这些珍贵的画面。”
“不需要。”
那些记忆从不褪色。
而这些电子设备构筑起的数据世界,又有几分真实。
他闻到一股焦味。
烟熏般的气息纠缠着器灵,木头崩裂的声音如雷贯耳。仇止命提起一口气环顾四周,这是一个狭窄的老旧楼梯间,踏在木质楼梯上还能听见嘎吱作响的年代感,所见之处毫无一丝火光,更别提什么难闻的焦臭味。除了前方少年少女的谈话声,这栋老房安静得异常。
仿佛那一瞬的难耐,只是器灵的又一个来自时间戏弄的噩梦。
仇止命偏头,目光在那红色的发顶之上盘旋,而那有着少年人面庞的灵心有所感地仰起头。望着百琅递来的询问眼神,仇止命扯了扯嘴角,那些躁动毫不意外地平息了下去,重新缩回暗无天日的牢笼,只待下一次露头的机会。
“这地方真让人感觉不舒服。”男人话语里的嫌弃意味十足,要他来说鬼屋探险之类的,是在浪费生命。更别提最先提出建议的人,根本就是动机不纯。想起季旌“无意中”在电脑搜索页面看到的资讯,仇止命内里的邪火又有冒头的趋势。
掌心忽然有了一抹冰凉的触感。
“有什么东西在。”常年与风相伴的风铃总能从风中探听出点什么,随风绵延而出的感知触到了某种不可知,百琅疑心陡起,他与仇止命交换了一个眼神后,又将话题扯回这趟旅程的始作俑者身上,“他也在寻找。”
一如过往的我们。
仇止命自然明白百琅后半句话的意味。当然是不止这栋鬼屋,在欧洲游荡的美洲豹神,以梦境为食的猎梦者等等,种种怪奇的都市传说经常无端出现在无人操作的电脑里。
“我知道,但这不妨碍他欠揍。”
熟悉的电流声滋过男人的耳畔,让他牙酸了一阵。
季裟在寻找。
仇止命当然知道,是他将那层伪装戳破,才得以窥见那道意识所隐藏的真相中的一角。如今他依旧不喜欢没有形态的东西,他也觉得整日对着一台破机器拌嘴很让人恼火。
——我就在这里。
这声呐喊太过空洞,回荡在电子元件之内,碰撞出闷声回响。
连本人都不得而知的求救声又能传递到哪里。
起码有人听见了。
仇止命将目光放远,位于落点的女孩正走过一个转角。也许这是每一个姓季之人的魔力吧,仇止命带着百琅追随季旌的脚步。
一路走过转角,欢声笑语全被摒弃在后,刀灵拉下了嘴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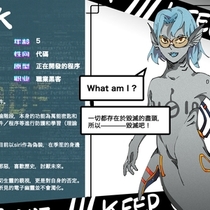

死线战士又来了
没有灵感又没有逻辑
(懒得数字数了x)
小少爷ooc都属于我——
“豹神啊,请祝福我们……”
带着美好祈愿的祝词逐渐消失在薄暮下,西沉日光将云霞染成金红色泽,暮色灿烂之下原始仪式也即将抵达顶峰高潮。
当最后一丝阳光被黑夜吸入,一阵呼喊陡然拔高音量,随之而来的便是投入篝火架子的火把尽情燃烧,冲天而起的火光照亮围拢在篝火边的人们。洋溢在部落子民脸上的笑容似乎能与这火比肩,或者说——更为热烈。
男男女女们正在起舞。
手与手,身体与身体,心与心。在这一刻,彼此贴近的身躯,让爱侣间的心灵更为贴合。
人们仿佛有意将一对夫妻拱在中心,女子那一头淡金色的长发看起来与这里的原住民格格不入,却无人在意,反倒是总有调皮的孩童会挤入她与男子的中间,拉着她的手在火光边打转。
每当这时,男子无奈地眨眨眼,在旁边观望了片刻,便伸手揽住她的肩头,抢人的那一方甚至还低下头冲着那孩子咧嘴一笑,那股得意洋洋的劲儿压都压不下去。一揽一放之间,带着人跳起更火热的舞步。
女子对他偶尔顽童似的行为也早已习惯,冰蓝色的那对眸子里早已是入了春,笑意盈盈间盛满了柔情。
共舞时刻悄然迎来最后的落幕,祭祀也即将结束。一直在圈外冷眼旁观火热场景的野性女子终于迈开了第一步,手与脚化为爪;第二步,人们纷纷舞动着让开一条道路,直通篝火;第三步,一头美洲豹沿着路疾跑。
她昂起头,环视一圈,这些人的脸早就记熟在心里。接着,豹子开口了。
“愿阳光永远照耀你们的梦境。”
“今晚会有个好梦。”
她以神的口吻降下祝福,那么她是神吗?
“豹子姐姐是神吗?”
梅兹里靠着树干揉了揉眼睛,在高空晃荡着的双腿昭示着刚醒来的精灵心情十分不错,随即她微微地张大了双眼,手指卷了卷垂下的发尾,“咦,不对不对,刚刚那个……是梦?”
“一定是梦吧,哥?伊查纳——,是吧是吧是吧!”
“哇,我都不知道我还能做梦耶,除了上次——”小姑娘皱了皱鼻子,似乎是想起什么不好的回忆,立马就另寻了个话题重新开始,也不管被她喊到名字的人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女巫姐姐看起来很快乐呀,明明都已经背井离乡了。啊,真好。”
为什么会知道这种事?
“很奇怪耶,我记不住豹子姐姐的脸了。所以果然是神明吧?”
只是,这回的沉默持续得也太久了点。
“哥。”女孩忽然吐出了单音节,神神秘秘地压低了嗓音,晃动双腿的频率也低了下来,一副有大事要说的样子,“但我觉得她是你喜欢的类型。”
她的耳边响起一声叹气。
“我的月神。”
“你一定很喜欢她。”
“梅兹里。”
“我们去找她好不好?”
“那是……梦。”
那是梦。伊查纳低语着。
他说,豹神的祭祀早在百年前就失传了;他说,我们也曾被误认为神,而我们不过是被女巫唤醒的造物。
他说,这个世界上根本,
——没有神。
“等你梦见她,你就知道了啦。你会喜欢她。”
“等下,不行不行,你的梦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又不好吃——那算了,你不准梦见豹子姐姐。”
“嗯,不会梦见。”
得到保证的梅兹里从树枝上跃下,轻快地跑过一条条小巷,七拐八绕地重新撞进到处都是人类的街道。
她在街边驻足,人流从她身边经过又远去,总有目光落在她身上,黏连不断。不甚在意地四处张望,宛如在确定方向,又仿佛在寻找某个迫切想要找到的人。
“戴安娜不在——赛丝安塔最近又好忙——好无聊喔。”梅兹里踢着脚边的石子,脚尖一勾,飞起的石子被她一把抓在手心,改踢为抛地独自玩着石头。
人声鼎沸,一切与她擦肩而过,那些带着迷恋的眼神也会消失在街道的尽头,被拐角吞没。
笼罩着城市的日光好似根本没有温度,不冷也不热,它只是照射下来罢了。那日梦里头的阳光,都比此刻来得真实。
“我不喜欢这里。”
充斥着人类的地方有太多的欲望,那些丑恶的,阴暗的,不能见人的欲望会化作深夜徘徊不去的噩梦。
瞧,这一个,那一个。
都要被自己的噩梦吓死啦。
“我不喜欢纽约。”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梅兹里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在驱使着伊查纳,不是因为噩梦的甘美——他品不出那些令人沉迷的味道,她只知道他为了那些不值得拯救的人类,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坠入噩梦编织的深渊。
她也从来不问。
她明白,他只会回答——
我为此而生,我的月神。
“伊查纳不准去,今天不行。”
只有在梦见她的清晨,不可以。
梅兹里跑开了,从人类的世界里。
耶特被突然窜进来的印第安少女吓了一跳。
这本该是个悠闲的周末,透过玻璃窗的阳光正好,提供足够的光线的同时也晒得人暖洋洋。起码一分钟前是这样,耶特盯着直冲冲将脸伸到展示柜前的少女,缓缓地放下打磨到一半的宝石。
她就像一阵风,不带任何警示地闯进来,东看看西看看,还想动手摸。这倒也不是重点,重点是——耶特捂着脸,刚刚有一瞬带起的风太大,眼角似乎瞥见不该看到的……。
鲜艳的色泽慢慢爬上耳廓,青年猛地扭过脖子,手忙脚乱地扯下挂在椅背上的外套。
“喂——!”
“哎呀!”
大衣不偏不倚地糊在梅兹里的脸上。
梅兹里看看耶特,又看看捧在怀里的大衣。那上头混合着阳光的热度和人的体温。
还挺暖和。
梅兹里收紧了手臂。
“你倒是给我穿上!”
“诶?为什么?”
耶特现在开始怀疑眼前这个小姑娘脑袋是不是不太灵光,还是个衣衫不整的印第安小姑娘。
太可怜了。
青年一瞬间就在脑内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记,看向梅兹里的眼神也柔和了几分,耶特把大衣从她的怀里拯救出来,撑开衣服把人整个都裹了进去。
有那么个几秒,耶特以为自己听到了一声低笑,还是个男声。他左右看了看,晚上没睡好还能导致幻听,看来今天要早点歇。
随手将梅兹里一直盯着看的小坠子挂在她的羽毛链上,在她不想穿衣服的声讨上,耶特把人带上了阁楼。
“你在这里躲好,躲个……一两个小时?他们应该就走了吧。”耶特说得很没底气,毕竟他才没有被人追杀的经验。
“那我能不能下楼——”领会了青年天马行空的想象,梅兹里乐得捉弄一下这位看起来就很糊弄的人类。
至少这里很温暖。
“那怎么可以!万一有人进店,下面可没地方让你藏。”耶特就快要说出你很扎眼了。
“闪闪亮亮的我很喜欢。”
“对吧,我也觉得很好。避了风头,再让你好好欣赏我的宝贝。”
“约好了哦。”
“骗人的是小狗。”
本该是很清闲的来着。
自从不速之客到访,这家开在巷子深处的小店客人三三两两地来,欢声笑语地离去。做成了几笔单子,接了个小活,最让店主人上心的却还是金屋藏娇的“娇”。
送走最后一位客人,瞅着临近傍晚,再大的危机也该过了失效,耶特踩着嘎吱作响的楼梯爬上阁楼。
所谓的“娇”,果然不会是真的娇。
不知为何,对着人去楼空的阁楼耶特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只不过,这里可是两楼。
耶特对女孩跳窗逃跑的事实痛心疾首。
桌上多出一块小石子。
下面压着一根羽毛和一张便条。
愿太阳神照耀你的梦境。
今晚会有个好梦。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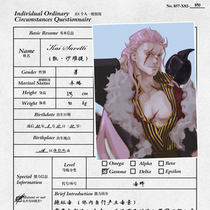
真的只是来狗的旧粮
就只有这么一点啦——————
一轮圆月挂在无星的夜空。
比夜色还浓的漆黑翅膀盖住高大的躯体,偌大的房间里只有屋主缓慢的呼吸清晰可闻。
窗外的月被乌云掩去瑕光,没多久,雨滴便叮叮咚咚地敲击着屋檐,顺着外壁淌进地面,积起一个个小水洼。雨夜奏响的小夜曲唤醒假眠者,黑色羽尖不安分地舒展开来。
金色的眼在黑暗中熠熠生辉,仿佛除了那光亮,倒映不出它物。随后一双锋利的、状似鸟爪的脚踩在地板上发出一阵吱呀声,尖端深深地嵌进脆弱的木头里,想必会留下几道难看的爪印吧,宇贺神伊墨却完全不在意,他只是静静地伫立在卧室,凝视着窗外。
雨仍旧在下。淅淅沥沥。
闪电划亮天空,雷声回响。
只有心跳声应和着震耳欲聋的春雷。
宇贺神迈开脚步,一步、一步又一步地远离原地,拥有良好夜视能力的天狗将整个屋子都看得清清楚楚,连一只蛾子都没有。
推开门,迎接他的是空荡的长廊。
早知道就不买那么大的房子了。宇贺神不知多少次叹气,但始终都没有将这一栋他嫌弃空旷的大屋卖了换够一人住的小屋。
再空也没关系——
越是空旷,哪怕是做一些小事,也会有细微的回音。而天狗的听力同他的夜视一样灵光。
楼下传来千寻的脚步声。
想来这会儿自家女佣是准备就寝了吧,宇贺神随手拉上卧室门,嵌在墙壁上的油灯中燃起簇簇火焰,点亮通往楼梯的道路。天狗火随着主人的惬意心情摇曳。
他站在楼梯口,将头探了出去,“千寻,睡了没,我们来吃夜宵吧。”
收拾妥当的千寻浑身一僵,突兀的乌鸦声线落在夜里着实吓人,千寻结结实实地被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少女按着胸口,仰起脸瞪他,“您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哎呀,我饿了嘛,就满足我一下——?”
宇贺神仿佛没骨头似的瘫在楼梯扶手上,懒得挪动步子向下走两步,背后橙色的微弱火光竟将那身向来如墨的身影衬出些暖色来。像是被妖邪蛊惑,千寻应了声好。
就在下一秒,少女的手就被牵住,被拉着往厨房走了一会儿千寻才惊醒,立刻就逃离温热的源头,猛地抽回手。这只臭妖怪!刚刚还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同情他真是瞎了眼,千寻愤愤地揉着手。
“不好好握着会摔跤喔。”
这就得寸进尺起来了,老爷果然还是老爷。千寻深吸一口气,说出来的话怎么听还有有点咬牙切齿的味道,“点上您得意的火不就行了,天狗大人。”
顿时,几团火焰环绕着少女翻飞,甚至有一团绕着她的手臂转着圈嬉戏。千寻没去搭理宇贺神玩性大起的炫技,忍耐着翻白眼的冲动,快步上前走在了他的前头。
“如您所愿。”后头悠悠地传来宇贺神的声音。
戏弄自己就这么好玩?这家伙如此高兴的样子确实少见。千寻咬咬牙,步子不由地又加快了几分,这下宇贺神是彻底被甩在了脑后。
但他的确是听见了他的小女佣说还有些油炸豆腐,那可是他的最爱之一,淡淡的笑意浮现在金色眼底。轻轻一扇翅膀,转瞬就贴近女孩的妖怪低声在她的耳边说着什么,激起女孩更多的恼怒之情。
再空也无妨。
这里有南云千寻。


又是滑铲打卡x
不好意思我这回连官方剧情都没跟只是个回忆杀(靠
终于能写到琅琅了!(捧脸)
日月真的好难选?!
风在吹。
百琅首次见识到所谓鬼之物,只见其额上生双角,饶是唇角抿成一线,仿若刚吸食过人血的犬齿仍是突出唇外。在那樱花盛开之地无缘见之,原以为不过是民间怪谈传说,没想到竟在隔海相望的地方目睹奇谈中的身姿。看来那些个口舌相传的怪事也不全是夸大其词嘛。
若隐若现的黑色雾气宛如丝绸缠绕在那头短发上,随着男人低头的动作向四处逸散。
狂百之器足下踏着一名酒气熏熏的男子,隔了大老远百琅都能嗅到烈酒味儿,可想而知这人醉得有多不识人与物。那人儿被浊化的器灵踩得胸口疼得紧,这样都不知惧,手臂因醉意打着颤举起,堪堪指着器灵的鼻尖,骂道:“我告你啊,你以为我谁?谁、谁会怕你个倭寇伙夫,趁早赔礼道歉!不然我就让你——吃、吃不了兜兜着走!”
“愚昧。”不愿搅进麻烦事的铃之灵被随风而来的怒声劝住脚步,夹杂着大阪腔咒骂的声音断断续续,“睁大你半瞎的眼珠子看看清楚!”百琅下意识地将视线落在男人一张一合的唇上,以他的眼力轻而易举地瞥见从獠牙上滑落的暗红色被男人用舌头卷走舔进嘴里,男人兀地皱了皱眉,重新摆上一张怒火中烧的面具,仿若先前的邪气只是不符合场景的拙劣演技,被人喊了卡之后消失得一干二净。
“人也好,器也好,哪来那么多高低贵贱。你是谁,我又是谁,重要吗?”倒提的短刀耍了个刀花,寒光闪闪,直指咽喉,“在这块土地上我连个名字都没有,但是这重要吗?天照来了我都照砍不误。”
“我高兴罢了。”
这哪是高兴脸?讨债脸还差不多。
避开横在脚下的断枝,百琅悄悄靠近对峙的一人一器。月光映照在葱葱绿色的发上,倒是衬得他不像鬼神,如果撇开他手中的凶器不看的话。
突然不想撇下无名之器不管。就此放任的话,必是要见血。也许这家伙费了这么多口舌,是想让脚下人憋出些什么话来,不过他也太高估那人的酒量了,百琅若有所思地盯着毫不见动摇的手臂。
一串风铃出现在百琅手中。
会有用吗?
哪怕是这样的我。
浑浊的音还能够……?
我希望能够帮助「他」。
夜风送上铃的问候,轻柔地抚过他的脸颊,在他的耳边缠绵。
铃声渐止。
深林中只剩断了胸骨的醉汉,两名器灵早已不知去向。
——铃声真的消失了吗?
只有伙夫,狂百器,无名器,牙,仇止命,随便怎么称之都行。
只有「他」才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