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http://elfartworld.com/works/74660/
因为是自由角色所以擅自借用了陈瑜大哥!OOC请揍我!
=========================================================
话说南宋年间,临安府招贤坊中有一夫子鳏居;夫子姓胡,自号薄谷先生,平日在私塾讲学,以束修度日,闲时便反复研读程李之学,倒也清闲自在。唯有一事烦恼,便是私塾顽童将夫子雅号讹了去,起个诨名唤作胡不古,想夫子饱读经书,尊古崇贤,蒙此污名自是气结,却又奈何顽童不得,只好横眉拂袖怨一声“人心不古”……此应是夫子诨名之所以。
一日胡夫子行于朝天门外清河坊街中,忽见三五个地痞样打扮的大汉围作一堆,定神一看中间却是一个年方及笄的少女。看那少女:身着素罗衫,青丝作双鬟,未识傅脂粉,更无钗钏繁;那眉眼间神气倒尚称得上机灵可爱,虽五官格局隐隐不似中原人氏,但想来也是良家之女。只听得那几个地痞言辞粗鄙,分明是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人,无奈这清河坊素来人如潮涌,三教九流皆聚于此,路上行人竟也无人敢于妄管闲事,何况手无缚鸡之力的胡夫子?夫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只得暗暗道一句“人心不古……”
再看那少女,被莽汉团团围住却不见一丝惧意,只那一双杏眼滴溜溜乱转,待几人纠缠半晌,少女才终于笑盈盈开了口。
“诸位大哥莫要见怪,阿秀听不懂汉文!”
倒真是带着几分西夏口音。
地痞们初是一愣,当中一人随即换上一副野卑笑脸,作势便要把少女往无人的胡同里带。那少女也不见抵抗,想是未曾识得人心险恶,附近小贩行人及夫子在内是再不忍看,就在这当儿,却是地痞之一惨叫了一声。
“这位大哥,咱们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不知何时从何处出现的男人面上赔笑,拧住地痞两手的力道可是一点没放松。这男人身材高大,脸上大刺刺一条刀疤,只是两眼无甚精光,一手随意插在怀里,形容懒散,自把那一股凶蛮之气去了九分,看起来倒也不至于叫人心生畏惧。这时他把那地痞的手腕捏得格格作响,却还在一迭连声地朝地痞们谢道:“实在对不住,我家小妹年幼顽皮,不知甚么地方礼数不周得罪了几位大哥,还请各位看在陈某几分薄面上宽恕则个……”地痞们被他兜兜绕绕地说得心烦,正待发难,忽然噫的一声,那被抓住的已经昏了过去。其它地痞看他面色惨白,手腕肿胀如棒,心下各知今个惹错了人,只是嘴上还不肯认输,七手八脚扶起了同伴,仍是骂骂咧咧地去了。原地只剩下男人和那被纠缠的少女,若是男人就此也去了,倒不失为一件行侠仗义的美事,只那男人又上下打量了少女两眼,便躬下身笑瞇瞇地道:“小娘子长得好生可爱,何不赏个光跟陈某去那边茶楼一坐?”少女还以一笑,又要开口说那句“阿秀听不懂……”男人像是早有防备,急忙补道:“前面那茶楼的黄金糕可是临安一绝,陈某斗胆给小娘子做个东,小娘子总不会这么不给陈某面子罢?”少女一听黄金糕三字,双眼一亮,脆生生欢叫一声“谢谢陈大哥!”就跟陈姓男子走了去,看起来再无一丝防备。这横生变故又是谁都没曾想到,愣是把行人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胡夫子回过神来,义愤填膺,直拍着砖墙喊道:“人心不古,人心不古啊!”
话说两头,男子将少女带进茶楼,先抢步上去拉了张椅子恭恭敬敬地道:“小姐姐,您坐。”元来这男子名唤陈瑜,乃是闻尘楼门下的传递,少女姓秦名秀,是闻尘楼总堂中一名厨子,论辈分却还比陈瑜高出一些;更不论陈瑜早听说闻尘楼总堂便是厨子买办也个个身怀绝技,自是不敢怠慢。是故陈瑜对着这还没活到自己一半岁数的女娃娃也要称一声“小姐姐”,女娃娃倒是客气,一碟黄金糕就能哄得她千谢万谢,引得跑堂在一旁吃吃窃笑,许是把两人认作亲戚了罢。秦秀一小口一小口吃得高兴,两人东拉西扯些闲话,不多时聊到自己来临安所为何事,陈瑜随口问起:“说到万贤山庄广发英雄帖,听闻贴上有个叫做游月宫的奇珍,不知小姐姐听没听过?”秦秀还在埋头吃黄金糕,听得此言才终于停了下来,边擦嘴边盯着陈瑜笑了起来。
“陈大哥,阿秀只是厨子,这不是阿秀能明白的事情呀。”秦秀笑吟吟地抱过茶壶给两人杯中续上,玉色的细线倾流而下,煞是好看。
“也不是低等传递该明白的事情吧?”
只见杯中的茶水满得堪堪越过杯沿,气泡从杯底慢慢悠悠升上水面,咕嘟破了,水花的声音只比女娃娃最后那一句话略大些儿。
陈瑜哈哈一笑接过茶杯道了谢,顺口又提起临安城里的大小流言,像什么映柳轩中秋被神秘人物订了一大桌酒席,城门外不久前死了个行脚的商人,最近街头巷尾传说着城里出了个采花大盗,这不,那高府的小姐才被盯上了,高家使用人正四处贴告示呢——陈瑜本性风流,说到此种消息总是忍不住多说两句,秦秀也是个最恨恃强凌弱的性子,自然只有这采花贼的话题两人是越说越起劲。正到兴头时,秦秀突然闭了口,只顾看着杯里倒影,却不再搭理陈瑜。过了半晌,秦秀才又小声开口问道:“……陈大哥,您说的高府可是那户高墙大院人家?”
“那是自然,高府再怎么也是大户人家呀。”
听得此言,女娃娃小脸刷白,包住茶杯的手似也有些颤抖。这边陈瑜一开始仍是云里雾里,随即低呼一声探出了半个身子。
“我的小姐姐,该不会那是您……”
“好像,可能,是我……”
“我的小姑奶奶您还有这癖好?”
话音未落就被女娃娃猛抬起头来狠狠剜了一眼,陈瑜自是识趣地不再作声,静待女娃娃自己开口。原来秦秀自幼醉心厨艺,又是少年心性,若是听说哪里有什么珍贵食材或者时令新菜,那是非要去瞧上一眼才肯甘心的。两天前她照例出门散步,无意中听见高家丫鬟跟人闲聊,说自家小姐的远亲姨妈来家里暂住,今晚要施展手艺做一道“龙吟凤鸣羹”,须知临安乃是帝王之都,城中之人大都喜附风雅,秦秀又不懂得太深汉文,只听名字竟完全猜不出是什么用料、何种菜色,当下坐立难安,循着那说话的丫鬟认了高家的门,好容易捱到夜里,原路摸过去三两下无声无息上了墙,待到屋顶上站定却来寻思:“他家院子好大,我又不知道路,怎么找得到后厨?对了,饭菜做好了肯定是要端上来给人吃的,我从最大的屋子一定没错。”心念甫定,忽然听见白日里那丫鬟敲着一间房的门叫道:“小姐,姨娘夫人担心您身子,特地给您单留了一碗龙吟凤鸣羹,您就在房间里吃罢!”又听房里一个年轻女子轻轻柔柔地应了一声,心里欢喜,知道这下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找也不用找啦,这就足尖发力,再跃过二重三重屋顶,小小身子已经到了那小姐房上。彼时院中来去巡逻的家丁护院虽多,却又有谁能看得见她?她急着要看那龙吟凤鸣羹长什么模样,到了屋顶上也不看周围就想伸手揭瓦,不想突然听得一声女子轻呼:“哎哟,么子卵?”
声音是从秦秀脚下不远传来,这一下把秦秀吓得不轻,心想这位千金大小姐怎的内力如此深厚,不仅一瞬之间就发现自己所在,念起咒来还直透梁瓦?再一想不对,这声音和先前听到的似乎不甚相似,一抬头便看到一个黑影跳将起来,月光一映也是个少女身形。那发声的陌生少女神情比秦秀更为惊惶,指着秦秀又念了些“恩是啥人?”“你要哦改咯?”之类的咒语,秦秀听得咒文知道对方是出家人,但借着月光看少女衣着不似道人,她本就没有语言天资,打小跟旁人学些汉文已感吃力,又听不出是哪派真言,胡乱说话又恐触了法家禁忌,把个秦秀急得舌短气结,只说了一句“我只是想看看……”就再也说不下去,她心急起来西夏口音又重,故是对方似乎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两人比划之间那神秘女子脚下又坐起两个黑影,一个看起来像少年,一个却是只猴儿。两人看对方均感奇怪,又不敢先行背转身离开,僵持之下只听房里的小姐颤声叫道:“春雨,你去……你去看看窗子底下屋子顶上,是不是有……”春雨想是丫鬟的名字,亏那丫鬟答应极快,快步走出门来点了灯笼四处乱照,两人这才想起自己还在别人家屋上,若是被发现了纵有千张口也未必说得清,当下心随念动,齐齐往外抢出一步,那猴倒是跑得比人还快,只剩那少年还在原地略略一愣,两人如何等得他?一人一边挟了起来就往墙边飞奔,原来这神秘少女轻功却不在秦秀之下,只是拖着一个人,步子不免粗重,翻过外墙时才不慎碰落了一片瓦,这是悬赏榜上高家护院所说那飞贼毁瓦的由来。秦秀边逃边想:这位道姑怎么也半夜上人墙头,难道是跟我一样来看龙吟凤鸣羹的?心知不可能,却是慌乱之下怎么也想不出答案。待到逃至街上,秦秀终于回过神来,指着少女轻喝:“你,你难道是去偷人家东西?”少女似乎本想说些什么,听了她这一句既惊且怒,念道:“果夺路吾一不晓嗲!”便领着少年和猴儿扭头急冲冲地走了,秦秀虽听不懂,但想中原出家人总不至于就下毒咒的,在路上呆站了一会儿,无法可想,只得回了客栈。
秦秀说完了这一段缘由,气忿道:“虽然女子当不了采花贼,不过既然三番五次去骚扰人家小姐,那位道姑果然是不安好心,想来也不是什么名门正教,我要去抓她起来,不然小姐太可怜了!”陈瑜听她说了,总觉有什么不对,但一时又想不出来,正自想着,随口问道:“小姐姐仗义助人是好事,抓那女子起来之后又要做什么?”这一问像是难住了秦秀,只见她沉吟半晌,小声问道:“陈大哥,饺子您喜欢荠菜馅儿的还是白菜馅儿的呀?”他一口茶险些喷在桌上,定了定神才回答“……只要不是剁了我做肉馅,小姐姐做的我都喜欢。”话音未落,秦秀已经翻身往门外出去,他急忙招呼跑堂结了帐追出去叫:“小姐姐,您这就去追那女子么?临安城恁样大,您从何找起?”女娃娃停也不停,只回答:“他们一男一女一猴稀奇得很,我用心找找总能找得到。不过现在要紧的可不是去追他们。”说着,女娃娃在大太阳底下颤抖了一下才又道:“要是被师傅知道此事,我可要变成滚刀肉了,先把悬赏榜撕下来才是要紧!”说完催动身形疾奔而去,留下陈瑜在原地发呆。
正是:
堂前本自无风波,波风自起惊春阁。
不虞新燕衔枝去,却恼寻芳是谁何。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嗨,冷静地听我讲。我本来在愉快地唱歌种地打怪兽,突然有人按我门铃,我打开门然后就被奇怪的卷心菜教信徒推销了据说可以边睡觉边自动打印文言小说的机器。虽然我是个有常识并不会碰奇怪机器的人但做人没有科学探究心跟咸鱼还有什么区别呢于是我打开机器调到南宋档然后就昏迷了,醒来之后发现机器自己停在了明清白话小说档而且发出一阵焦臭味内部自爆掉了。总之之后悬赏榜就被撕了。有没有真去追我也不知道。湖南教真言咒的部分感谢百度,讨论剧情的时候我跟花心小姐中之人讲人家在吟風舞月弄劍帛我們在上房揭瓦翻墻頭是不是画风不太对会不会被拖到墙角打死啊我好方。对方说没事我们跑得快。所以我就跑了。因为以上原因所以下回分解是骗人的。没有下回分解。我的回合结束了。谢谢观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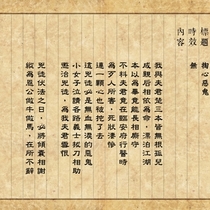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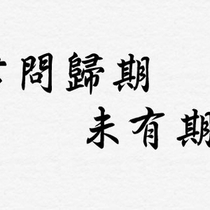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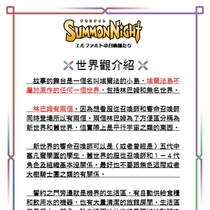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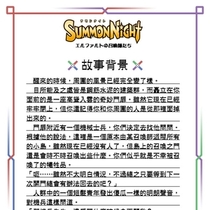


我……第……第一次佔位……不要殺我,明天就補上………………
長谷部+宗三,嫌惡組,no腐向,腐向評論也NG,謝謝合作。
attention!雖然連ヘイト創作的へ字都算不上(當社比)但是會出現刀劍之間認真地互黑,何でも許せる方向け
==========================================================
进入视野的第一样东西,是僧衣的下摆。
他在朦胧之中觉得有些奇怪。谁会把僧衣垫在刀架下面?难道是他被放在僧衣之上了吗?但如果是那样的话,视野中僧衣与自己的距离又有些微妙地遥远。
如果能靠近些看看那袭僧衣就好了。
这么想着,视野中的僧衣就真的急速接近了自己。
“……?”
最先感受到的,是某种难以言喻的沉重感。然后是离自己很近的地方发出了一声钝响,某种从未经历过的不快感觉从视野上方缓缓扩散开来。僧衣的格子纹填满了整个视野,他花了好一阵子才明白过来,似乎不是僧衣接近自己,而是自己掉了下去。他静静地留在那里,等着听到声音的某个下人来把自己放回去,但就在这样等待的时间里,让人烦躁的不快感也一直在主张自己的存在。
不知等了多久,不远的地方传来纸拉门被拉开的声音。有人大惊小怪地叫着他的名字,是一个高亢得有些奇怪的声音。大概是哪里的小姓吧,他忍耐着完全陌生的不快感,静静盯着格子纹的一点这样想道。
“我还想说为什么过了这么久都不见新刀出来……宗三左文字你这是做什么呀!你不会是被衣襬绊倒了吧!?”
开门进来的小姓咋咋呼呼地说着一些意义不明的话,却就是不把自己捡起来。宗三左文字恨恨地抬起头,看到的却根本不是什么小姓,而是一只长相愚蠢的狐狸。
——……抬起……头?
稍微开放了一些的视野边缘可以看到无力地投在地板上的白皙手腕,他想凑近一些看看清楚,那手腕却朝他的方向自己弯曲了过来。
他眨了两三次眼睛,试着让那条手臂朝右边移动,手臂就真的有些笨拙地朝右倒在了地上。
“啊——……我知道了,刀剑男士里偶尔也会有像你这样的呢,刚得到现世的身体结果不知道怎么用……你等一下,我去叫近侍过来好了!还有你一直这样趴在地上脖子不痛吗?”
痛?
虽然不太明白,不过宗三左文字也模模糊糊地察觉到那应该就是指正在折磨自己的陌生不快感。他笨拙地用两条手臂撑在地上勉强立起上半身,一个动作停了好几次才做完。
……近侍?
终于从名为疼痛的不快感中解脱之后,他才有空暇思考这个熟悉的单词。
这样啊,是要叫人来把我再放回刀架上啊。
虽然狐狸的话里还出现了好几个没听过的词语,不过那对宗三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笼中的鸟儿……就算对牢笼之外的东西发生了兴趣,又能怎么样呢。
狐狸像是完全没注意到宗三的负面思考,还在兴高采烈地啰嗦。
“对对,说到这个本丸的近侍是宗三你也认识的人呢,本丸里有认识的刀剑男士在你也会过得比较舒服吧!”
狐狸说了一个名字,是宗三完全没有印象的名字。谁让他历代的主人都喜欢搜集名刀呢,宗三左文字怎么可能记得住那些十把百把地排列在一起的刀的名字。
狐狸走后,宗三一个人在略显狭窄的和室里等待了一会儿,能够自由活动新得到的手足毕竟还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以至于和室的门再次被拉开的时候,他不禁感到有些不快。
“审神者有事不在,所以由我谨奉主命前来迎接。身体感觉怎么样了?”
与纸门之外的阳光一同洒下的是一个温和有礼的青年声音,听起来似乎是有那么一点耳熟,但果然还是记不起来。宗三懒洋洋地将视线投向声音的主人,依次进入视野的是金红两色的刀拵,西蛮教士风的服装,端正的脸庞和温和的笑容,……紫色的双眼。
“……啊,呀,是你啊……”
宗三抬起衣袖掩口而笑,而后第一次听到了自己发出的声音。
“下贱的无铭刀。”
宗三左文字是真的对压切长谷部这个名字毫无印象,不过不是因为不记得,而是因为不知道。在桶狭间的战场上第一次遇到那把刀的时候,他还没有名字。无论是开战的号角吹响的时候,还是义元的头颅滚落在尘土之中的时候,宗三左文字都没有被拔出来过一次。如果是新的主人……他怀着这样淡淡的期待被从义元的尸身上拔下来,还未习惯那个年轻人手掌的温度就被扔给了一旁的小姓。
“磨短。茎表里刻上……「织田尾张守信长」和「永禄三年五月十九日义元讨捕刻彼所持刀」,就这样吧。”
之后他几易其主,一再被刻上新的印记,然而只有最开始的那个年轻人漠不关心的声音,深深烙在他的记忆之中。
小姓恭敬地双手接过他的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了那道视线。
从那时起就被信长佩在身上,不知沐浴了多少鲜血的无铭刀,依然保持着温和的笑容,看着他的眼神却还是跟那时一模一样,充满了嘲讽与轻蔑。
“有力气说话的话,就表示已经可以自由活动身体了吧。站起来,无用的装饰品。”
说起来,无铭刀的名字的前半部分宗三好像还是有点印象的,毕竟他得到名字的时候,宗三和他姑且还是侍奉着同一个主人。他已经忘记了那天的天气是晴是雨,抑或那个茶屋主人到底犯了什么过错,依稀记得的只有信长静静起身时传到自己身上的震动,无铭刀出鞘的时候也没有声音,雪光般煌煌生辉的刀身朝下挥去的画面不知为何看起来缓慢异常,像是一个毫无真实感的白昼梦。
一瞬之后,刀身上溅满了鲜烈的红色。
如果宗三在那时就有人子的身体,他一定也是会蹙眉抬袖覆住口鼻的。信长空挥了一下无铭刀,甩去不断滴落的血珠,没有名字的付丧神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边,满身淋漓的鲜血似乎没对他造成任何影响。比起无关紧要的茶屋主人,信长似乎对爱刀的锋利更为关心,当天之内无铭刀就被赋予了名字,短短的四文字,既无雅趣也看不出一点文才,这样的名字还不如干脆就一直无名算了,你不这么觉得吗?——宗三那天难得主动跟无铭刀说话,也许是他刚好心情不错,也许是他很久没有近距离看过那么大量的血了。无名的付丧神……现在应该叫压切了,压切的表情微尘未动,只是轻轻抬起眉毛做出了一个勉强可以算是困扰的表情。
“无论名字如何,身为刃物只要能斩……敌人就够了吧?”
宗三到现在也不知他那句话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
听说给了无铭刀后半部分名字的,是他的第二任主人。远征归来的宗三走到审神者的房间前,听见无铭刀对审神者抱怨信长将他赏赐给连直臣都不是的家伙,擅自抱怨完一通之后话锋一转又请求审神者称他“长谷部”而非“压切”,连三岁小儿都看得出的本心。宗三站在纸门之外一动不动地听着他们的对话,指尖感受不到一点温度,想必脸上的表情亦然。
当初是谁说的,有认识的刀在就会过得比较舒服?
互为钢身铁骨的时候尚且无法理解彼此,何况如今这副连自己都不甚理解的人类姿态。
莫名其妙的不快感从身体深处沸沸而起,宗三伫立在廊下的阴影中许久,终究还是没能拉开那扇薄薄的纸门。
转身离开的时候,似乎又感觉到了那道令人厌恶的视线,他猛然停下脚步,门里传出的依旧是无铭刀与审神者疏松平常的会话。
数日之后,他与无铭刀同队出征,途中却遭到了名为检非违使的乱入部队奇袭。混乱的战场之中,碰巧身处同一个地方的两人自然不得不并肩作战。数不清是第几个敌人倒伏在地上的时候宗三抽回刀身的动作慢了一瞬,视野的角落似乎有什么以惊人的速度朝着两人中间直冲过来。
传入耳中的是衣袂割裂的声音,映入眼中的是长谷部脸上的新鲜伤痕。
“……哈哈!”
长谷部发出的声音,比起笑声反倒更像是渗满狂气的战吼。敌方打刀胸前的伤口喷出大量鲜烈的红色,全身溅满血液的青年顺着抽刀的势头已经回身冲向新的敌人,与此同时的宗三左文字则是抬起衣袖掩住口鼻后退一步避开了飞溅的血沫,两人的动作流畅得没有分毫冗余,仿佛他们从四百多年前开始就一直重复了无数遍这样的动作。
前进的一步与后退的一步,两人之间一瞬空开的距离,一如那个狭小的茶屋中鞘內的他与那道雪光的距离,遥远得近乎绝望。
只是如今,异族的野兽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发出厌恶的咆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