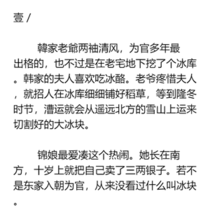不要问我为什么企划完结两年忽然写段子
------------------------------------
此时月色明得过分,竟有几分像冬日正午的光景。月光洒在园中如凉水,亭亭映出韩家女主人。大娘子执着一盏明灯,身旁两个自小伴在她身边的婆子一道站着。花园素来装点得雅致,锦娘最喜欢园中那一棵桂树。此时金桂正盛,那些如小金粒般的碎花随夜风漫卷,簌簌落下,纷纷停驻在堆放的财物辎重之上。这些黄白之物在此处本该格格不入,大娘子却浑不在意,只是静静立着。等人都到齐了,便将手中灯笼递给身旁婆子。
十五本是团圆的日子,阿郎却不在府中。锦娘还记得他最后一次回来,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那也是个如同今夜这般的月圆之夜。他同大娘子无声地靠在一起,坐在院中,就在那棵桂树底下。桂花落了他们满头满肩,二人就像两棵缠生在一处的树,枝叶相错,不得分离。时已入秋,锦娘担心主人受风寒,便提着行灯趋步上前,催促他们回房歇息。听到小丫鬟有些毛躁的声音,阿郎抬眼看了看她,古肃的面容上隐隐透出一线温厚的笑意。文人纤长的手伸过来接过锦娘手中的行灯,说道:"小丫头先回去吧,我同你大娘子在这里再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做什么呢?锦娘一步一回头地走开了。花园当中只余行灯罩里淡淡的一点光,阿郎和大娘子将那点烛火笼在二人之间,仿佛被束在布包中的流萤。锦娘已听不见他们的私语,心底却默默浮上来一丝怕。流萤命短,烛火也点不长久——她摇摇脑袋,轻轻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回到房中便睡下了。
翌日天不亮,锦娘便接到传令,抱着还没睡醒的小郎君往主院去。小郎君已经七岁,好吃好穿地养成了个小胖墩,白面团似的安安静静趴在锦娘怀里。阿郎已穿戴齐整,见到睡得正香的儿子顿时失笑,幞头上两根长长的硬翅也跟着颤了颤。大娘子见状本想唤醒孩子,却被丈夫温声止住。
"算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说。阿郎从锦娘怀中接过孩子,爱怜地摸摸小儿子的脑袋,又捏捏他的耳垂。院中一时寂然,只有桂花的甜香浮漾,惹得人心慌。
就在锦娘正想告退的时候,阿郎又把依然熟睡的孩子递还给她,随后伸手紧紧握住结发妻子的双手,低低说了一句。
"吾去也。"阿郎说。
大娘子浑身一震。她把右手从丈夫手中抽出来,在半空里停了半晌,又缓缓伸出去,将他肩头沾着的一瓣桂花轻轻拈下,攥在手心。爱笑的人不笑便显得格外冷,大娘子此刻不笑,看上去就像月正中天,清凛凛地照着人。锦娘只瞥了一眼她的神情便再不敢看,只觉自己窥见了二人之间不应由旁人看到的东西,恨不得就此化作一块顽石,无知无觉。
回到此刻。大娘子脸上正是那时一样的表情:既痛且恨——恨天意弄人,痛自己无能为力。应召而来的仆从原本各自按部就班做事,不将数旬以来日益阴沉的气氛挂在嘴上,仿佛只要当作不存在,便能让一切如常,永不更易。锦娘分了分神,想起小郎君——半刻钟前她才替他洗净头发,还没来得及晾干;接下来还得收拾好书房,小郎君前两日迟到惹了夫子生气,明日万不能再那样……可还未及理清思绪,便被大娘子清和的声音截断了。
"宫廷生变。"她说。"宫廷生变,韩家已不能再做大家一片遮头之瓦了。"大娘子从婆子手中接过一只手臂长的木盒,取出一叠卖身契与放良书。她一身缟素,对聚在园中的十来个仆人敛目垂首,盈盈点头。"这是你们各人的卖身契和放良书。取了这些,连同这些银子,便且去吧。"
她顿了一顿,轻声继续说。
"走吧,明日亥时之前离府。”她说,”就此别过了。"
院中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很快又安静下来。仆从们陆续散去了。锦娘却没有走。
她接过自己那张卖身契,双膝一弯,跪在大娘子面前,伏身叩首。额头磕在地上,触到几瓣冰凉的桂花。
"大娘子,"她说,"小郎君早已落水没了。大娘子怜念锦娘,就让锦娘把弟弟领回家去吧。"
大娘子本想接住她,听到锦娘的话,一颗玲珑七窍心千回百转,愣住了。
她深深地、深深地注视着锦娘,仿佛头一回看清这个仆人——不再是印象中那个寡言模糊的小姑娘。挺直的脊背跪在她身前,如一竿修竹。大娘子在心里反复掂量这句话:这是她想的那层意思么?这丫头,是要偷梁换柱,帮她把孩子偷出去,避过灭族之火?
她颤着嗓音,轻轻问道:"原来……是如此么?"
"是的。"锦娘抬起头来,清秀的脸上缀着一双晶莹发亮的眼睛。她看上去是极老实的模样,谁能想到这姑娘胆大包天,想要帮她。为奴为仆,她竟还是想要帮她。大娘子心跳如雷,听见锦娘继续说道:"事情过去很久了。坊间都传说有人产下鱼尾婴儿,大娘子您当初养着的,本就是这么一个孩子。"
大娘子又是一震。她耳聪目明,自己当初生的是什么样的孩子,岂会不知?她倏地伸手攥住了锦娘的手腕,力道极大,指节泛白。
"坊间流言蜚语,竟然传说我生了个长鱼尾的孩子。"大娘子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得像在自言自语,"我替他取什么名字了?妖孽降世,起什么名字?"
她停了停,忽然抬眼,目光落定在锦娘脸上,语调微微一转,轻而清晰。
"倒是你的弟弟——是叫寒生把。"
这句话从大娘子嘴里说出来的时候,锦娘就知道她听懂了。
大娘子缓缓松开手。方才攥得太紧,锦娘的手腕上留下一圈浅白的指痕。两个人跪的跪、站的站,在月光底下对视了片刻。大娘子的嘴唇微微翕动了两下,像是有许多话要讲,最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口。她只是弯下腰,双手托住锦娘的胳膊肘,把她从地上扶了起来。
这是头一回。
锦娘进府七年,从没有被主人这样扶过。大娘子的手比她想象中要轻得多,也薄得多,像两片干透了的桂叶,搭在她臂上几乎没有分量。锦娘站稳以后下意识想退后半步,被大娘子一把拽住了。
"你……想好了?"大娘子的声音很低。
锦娘点头。
"当真想好了?"
"当真想好了。"
大娘子没有再问第三遍。她转身走向木盒旁边,将那些银子重新码好,又从袖中抽出一把铜钥匙,递给身旁的婆子。
"春嬷,去我房里,妆奁下面第二层夹板,打开,把里头的东西都取来。"
春嬷愣了一愣,张了张嘴。
"去。"
春嬷应声去了。剩下另一个婆子还站在原地,眼神在大娘子和锦娘之间来回游移,似乎隐约猜到了什么,又不敢确认。大娘子向她摆了摆手,说:"秋嬷也回房收拾吧,明日亥时之前,照先前说的走就是了。"
秋嬷犹豫着,终于叹了口气,朝大娘子深深拜了一拜,转身走进夜色中。
园中只剩她们二人。桂花仍在落,夜风把甜香一阵一阵地往人身上送。大娘子背对锦娘站了一会儿,忽然开口道:"你方才说小郎君落水——这话从何说起?"
锦娘答:"回大娘子,数月前小郎君在后园池塘边扑蜻蜓,脚下一滑跌进了水里。我当时就在廊下晒被褥,听到扑水声便跑过去,把他捞了起来。前后不到一盏茶的工夫,并没有惊动旁人。"
"可那时候——"大娘子的声音顿住了。
"是。"锦娘垂下眼睛,"不知道为什么,传言还是传了出去。城中都在传韩侍郎家出了妖异之事。小郎君入了水,那东西就现了。尾巴。银色的,亮得很,从膝盖以下整条腿都变了。一直等到干透了,才变回人腿。"
大娘子闭了闭眼,长呼了一口气。
"我们都知道,那只是无稽之谈。"锦娘低声续道,"但传言一起,外头便不会再在乎真假了。旁人若要查韩家,一句私藏妖物,便是灭顶之灾。锦娘斗胆说一句:小郎君留在府中,便是留在火上。"
大娘子沉默了很久。月亮不知何时偏移了些许,桂树的影子斜斜铺在她脚边。她一动不动,像是自己也变成了园中一棵树。
"你没有弟弟。"大娘子忽然说。这一句不是疑问,是笃定的陈述。
锦娘抬起头看她。
"你进府的时候我看过你的身契。"大娘子缓缓转过身来,"父韩三,已殁;母刘氏,已殁;兄弟姊妹——无。"她一字一字地念出来,像在念一篇旧文,"你是独女。"
锦娘没有辩驳,只是静静地跪回了地上。
"你明知没有弟弟,还要编出这样一个人来。"大娘子的声音开始发颤,不是恐惧,而是某种更深的东西在嗓子里撑着,"你要把他带走,从此他就是你的弟弟。你要让全天下都相信,韩家当初养着的,不过是一个从丫鬟那里抱来充数的孩子……你想过没有?韩家若真灭了门,日后谁来查都好,查到你头上,你说小郎君是你弟弟——你拿什么证?户籍上无名无姓的一个人,你如何交代他的来历?哪家邻里见过你这个弟弟?哪间私塾记过他的名字?一旦拆穿,你就是窝藏罪人的从犯——凌迟都是轻的。"
锦娘伏在地上,额头抵着冰凉的石板。桂花的碎瓣这回黏在她的面颊上。
"锦娘知道。"她说。
"你——"
"锦娘都知道。"她重复了一遍,声音闷在地上,像隔了一层土,"可锦娘想了好多天,只想出这一个法子。别的路,锦娘都想过了,走不通。小郎君是大娘子和阿郎的骨血,锦娘打小带他,他头一回叫人叫的是锦娘的名字。"她顿了顿,"他叫我'阿锦'。谁家弟弟不叫姐姐的名字呢?旁人听了,也只当他是我的弟弟。户籍的事……锦娘的老家在岭南,山高水远,那边的县令换了三任了,旧档册早就被虫蛀得七零八落。锦娘多一个弟弟少一个弟弟,谁去查?"
大娘子没有接话。
“谁听了都会说:韩家哪里有什么妖孽?不过是主母丧子之后疯了,抢了丫鬟的弟弟养着罢了。”锦娘抬起头,膝行上前两步,仰望着她的面容:"大娘子。阿郎临走前同您说了什么,锦娘不该听的、也不敢听。可锦娘猜得到。阿郎一定说了——要您保住小郎君。"
大娘子的泪终于落了下来。
她没有出声,只是无声地流泪,泪痕就像两道银色的月光。她站了一会儿,忽然蹲下身来,和锦娘面对面,这个少女木讷、老实、不起眼,却在韩家将倾的时刻,成了唯一敢递刀的人。
大娘子伸手,替她拂开脸颊上的花瓣。
"好。"她轻声说,"就照你说的办。"
"从今往后,没有什么小郎君了。他叫寒生——锦娘的弟弟,寒生。七年前跟着姐姐来汴京讨生活,路上失散了,恰好被韩家收进来,养在府中。韩家的大娘子产了个怪胎,疯症犯了,抢了丫鬟的弟弟权当自己的儿子。如今韩家获罪,这才把孩子还了回来——就是这么个故事。"
她说得很慢,每一句都在仔细斟酌用词,像阿郎从前给她看那些公文似的,每一处折痕都要对齐。说完以后,她凝视锦娘:"你记住了?"
"记住了。"
"我再说一遍。"
大娘子便真的从头又说了一遍。有几处细节改了,锦娘默默记下。两人就这样蹲在桂树底下,一个说一个听,反反复复地将这个假故事打磨得严丝合缝。——哪年来的汴京,走的哪条路,在哪个村子失散的,弟弟身上有什么胎记。大娘子心思极细,连锦娘不曾想到的枝节都逐一补上了。锦娘在心中暗暗感佩,又暗暗心酸:大娘子这样聪明的人,却只能把聪明用在这种地方。
对完口供——锦娘心想,这便算是口供了,只不过还没有过堂——大娘子站起身来。春嬷已经回来了,手里捧着一只蓝布包袱,沉甸甸的。大娘子接过来放在石桌上,打开。里头是散碎银子和几件小孩子的衣裳,压在最底下的是一枚鱼形银坠,拇指大小,尾巴弯弯的,做工极精巧。
大娘子拿起那枚银坠看了看,拿在月光中转了转。
"这是阿平满月时阿郎找人打的。"她说,语气忽然平静下来,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银匠只知道东家要一条小银鱼,不知道为什么要做成这个形状。如今倒好——它终于派上用场了。日后若有人问起,你便说:这是你家乡的习俗,给孩子打的长命锁。谁也不会想到旁的地方去罢。"
她把银坠递给锦娘,锦娘伸手去接,被大娘子反手按住了。
"等一等。"大娘子说,"这东西……太扎眼了。你拿根绳子穿了,挂在他贴身衣裳里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拿出来。他日倘若——"
她没有说完。
锦娘等了等,见她实在说不下去了,便轻轻点了点头,将银坠收进怀里。
"银子一共二十两。"大娘子把蓝布包袱系好,推到锦娘面前,"也不算多。省点用,可抵你们三年用资了。出城以后不要住客栈,官道上盘查得紧,拣小路走。往南过了淮水就好些。"她想了想,又补了一句,"你到了地方,不论在哪瑞安顿下来,都不要写信回来。不要打听韩家的消息。"
"那大娘子您——"
"我自有安排。你不必管。"
大娘子的语气很淡。锦娘却在那淡淡的口吻底下听出了一种毋庸置疑的决绝——同阿郎那天说"吾去也"时一模一样。原来夫妇做久了,连这种时刻的神态都是相似的。
锦娘不敢再问。
"去把阿平带来。"大娘子重新拿起灯笼,笼中的蜡烛已经矮了一截,安安静静地燃着。她看了看那点微光,忽然补了一句:"也不必叫醒他。抱过来就好。"
锦娘起身快步往小郎君的寝房去。夜深了,长廊上没有旁的灯火,只有脚步声和衣裳的窸窣声。她拐过连廊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园中。大娘子独自站在桂树下,举着那盏快要燃尽的灯,一身缟素在月光里白得像一截薄霜。
小郎君睡得正沉。锦娘替他洗的头发已经干透了,软塌塌摊在枕头上,还带着一点皂角的清香。她小心翼翼地把他连同薄被一起抱起来。小郎君哼了一声,把脸往她肩窝里埋了埋,含糊叫了半个字。
"阿……"
锦娘拍拍他的背,没有应声,只是走得再稳一些。
回到园中。大娘子还保持着方才的姿势,连站的位置都没有挪动分毫。看到锦娘怀里裹着被子的小小一团,她把灯笼放下,迎了上来。
"让我抱抱他。"
锦娘便将孩子递过去。大娘子把儿子接在怀中,动作极轻极慢,像是在接一只随时会碎的瓷器。小郎君在母亲怀里拱了拱,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又沉沉睡了过去。大娘子低头看着他的睡脸,看了很久很久。月光照着母子二人,把他们的影子连在一处,印在满地的桂花碎金上。
锦娘站在几步之外,不说话,不动。她觉得自己又变成了一块石头。
过了不知多久,大娘子开口了。
"阿平。"她唤了一声,声音轻得像怕惊醒树上的鸟。孩子当然没有回应,只是均匀地吐着绵长的鼻息。
大娘子便不再叫了。她低下头,嘴唇贴在孩子的额头上——不是亲吻,只是就那么贴着,很轻很轻地,像是要把什么话隔着皮肉渡进去。
然后她站直身子,将孩子交还给锦娘。这一次她没有犹豫,也没有颤抖。只是甚为严肃,像是交托什么珍贵的宝物。
"寒生的事,你都记清楚了。"
"都记清楚了。"
"银坠贴身放好。"
"放好了。"
"出城往南,不走官道,不住客栈。过了淮水再歇脚。"
"记下了。"
大娘子点了点头。她退后一步,替锦娘理了理鬓边被夜风吹散的碎发。手势自然而随意,倒像是一个姐姐在给妹妹出门前整理仪容。
"天快亮了,"大娘子说。她看了看东边天际一丝极淡极淡的灰白,"你收拾好了就走罢。不必等到明日亥时。越早越好。"
锦娘抱着孩子,深深拜了下去。她弯腰的时候小心地护着小郎君的脑袋,怕磕着他。
"大娘子保重。"
"去吧。"
锦娘转身往外走。走了几步,听到身后大娘子又开了口。
"锦娘。"
她站住了。
"寒生怕黑。你若要赶夜路,替他点一盏灯。不必太亮,豆大一点就够了。他看见光就不怕了。"
锦娘没有转身,也没有应声。她只是站在那里,怀中抱着熟睡的孩子,感到有什么滚烫的东西从眼眶里涌出来,沿着脸颊往下淌,洇在小郎君后脑勺的薄被上。
她点了点头。
然后迈步向前,穿过走廊,走入尚且浓稠的夜色之中。
身后的桂花还在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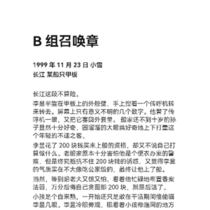
灾厄三十年前的前日谈,老头和嬷嬷还不是很熟的时候的故事。
我们大部分熟悉的角色都还没出生。
这样也ok吗?
↓ok的话请看下面
===================================================
艾德蒙此刻站在树上,视野极好。他原本视力就是猎人中的前列,现在站在有两人高的高处,更是看得又清又远。
他的老搭档,罗素在树下休整,把装备摊了一地。他们得定期把每一样都仔细擦拭上油,以求救命吃饭的家伙在危难关头能派上用场——在和吸血鬼那种体能五感远超普通人类的怪物对战,多一份依傍总是好事。
树林此刻很安静,天气很好,没有风,只有小动物细细簌簌移动的声音,夹着几声鸟鸣。艾德蒙似乎也没有怎么移动,几乎要让人忘掉还有这么一个大活人蹲在树上。罗素把一把短弩别回腰上,抬头对艾德蒙喊了一声:“喂!艾德!你在上面看见什么了?”
树上传来一阵含混不清的回答。茂密绿叶掩去他们的身影的同时也阻挡了声音的传播,他听不清艾德的话,于是罗素提高声线,又喊了一声。
树顶扔下来一个果子,有点青,还远远不是能吃的时候。罗素恼了,站起来抬头望向树顶。
“混蛋,你小心摔下来把血罐摔成渣渣。”他嘟囔了一句,把果子扔了回去。
果然人只会在被说坏话的时候听到别人的声音。艾德蒙的脑袋从枝叶之间冒出来,仿佛一个被挂在树上的人头灯笼。
他对树下的罗素抬了抬下巴,示意他上树。
“我不,”罗素说,“你像只猴子,而我比较喜欢脚踏实地的感觉。”
说完,他指指身上披挂的一堆装备,重点敲了敲腹腔的血罐:“何况我还有这个。”
玻璃罐子发出一阵空洞的回声。往常说到这里,艾德蒙也就算了。但是今天他却难得坚持,拍拍脚下粗壮的枝桠,说:“上来,给你看点没见过的。”
罗素又嘟囔几句,回头看了一眼周围,把地上的篝火弄熄以后才慢吞吞爬上树。他的技术其实相当不错,但是在艾德蒙眼中可能谁也没有他在树林中敏捷——他在浓密树林中穿梭跳跃的时候,有如游鱼回到养育它的江河,而其他人充其量算是搞了条船下水。
于是,等到罗素终于爬到艾德蒙身边时,他的脸上略有一种不耐烦,但是老好搭档隐忍不发,只是指着树林以外开阔的某处。
春天已经接近尾声,青草铺满了这片起伏温柔的平原。虽然花都早已凋谢,但是草绿色依然在蓝天下映着绝对无法阻挡的,生命的气息。罗素一时之间觉得有点刺眼,他已经习惯在黑夜中作战,在白日里歇息,几乎要忘掉青草绿地在阳光之下应该是这副模样,而不会只有惨白月色下幽幽的蓝绿色。
天色极蓝而草色极绿,还有几块嶙峋大石透着的灰,令天地中间那几朵红更为鲜艳。罗素瑟缩一下,他听见艾德蒙在身边低笑,说:“没见过,对吧。”
那是几匹马。即使是他们也能看出来,这些都是上佳的好马。这样的马在这里并不常见,只有更远的东方,那些人能在家乡的土地上抓着这些骏马,把它们驯服。那是齐马蒂的马。
罗素几乎要被那些美丽矫健的生灵迷住了。说是几乎,是因为他实在很难忽略马背上站着的人。也对,罗素心想,有好马自然就得有好骑手,否则马被驯服来作什么呢,只是拉磨和拖犁么?
齐马蒂的骑手穿着富有民族特色的长袍,白色为主调的袍子上铺满了艳红色的绣线,或曲或直,弯弯扭扭地勾勒出游牧民族的吉祥图案。这里的确是个好牧场,离乡别井的异乡人带着几匹离群的马在草场上奔驰。让人听不懂的歌词随着风送到森林的边缘。
齐马蒂的马不同,服装不同,歌声也不大一样。艾德很快就从风中撷取来几句曲调,轻轻哼了起来。听起来既不像酒馆里酒过三巡,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吼的祝酒歌,也不像他们在工会用风笛吹出来的曲调。齐马蒂的歌有着风的味道。
歌随着骑手的接近越来越清晰嘹亮,艾德蒙没唱几句就停了下来,像是要听清骑手接下来的调子。即使是罗素都安静了下来,不再说话。他也说不清为什么,就是觉得自己此刻不应该说话,就像他不应该关上窗子,让清风带走房间沉郁的空气。
这时候,像是被呼唤来一样,风犹如无形的手掀走骑手的头巾,歌停下了。
罗素轻呼一声。
怪不得他觉得歌声有几分耳熟,这里从来没有多少来自东方的旅人。
这些齐马蒂的马,齐马蒂的歌,自然会跟着来自齐马蒂的人。
露西娅一头像是蒙尘金块的头发披散在肩头,她回头看着被风吹走的白色头巾,哈哈大笑,又骂了一句她新学会的纳塔脏话。
她说得极为流畅自然,除了腔调不像纳塔人的短促,几乎就像在纳塔黑巷长大的姑娘。
但是纳塔的姑娘不会那样骑马,马匹在纳塔城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它们只会被绑在马车上,让年老驼背的马夫带领去接送养尊处优的贵族。罗素看着露西娅扯扯缰绳,落回马背上,双腿一夹马肚,骏马就像离弦弓箭一样窜出去。马很快就追上被吹走的头巾,她又把长长的缰绳缠在腰上,左脚离开马镫,几乎像从马掉下去一样,弯腰从草地上捞起自己被抢走的头巾。
“走吧,”在露西娅回到马背的时候,艾德蒙突然开口,几乎要把罗素吓得从树上掉下去。他抓紧了树干,怨怼地看向艾德蒙。对方拍拍他的肩膀,又像游鱼一样,从树上高耸的枝条滑了下去,融入树枝的阴影之中。
罗素跟着慢慢落到地面。 在到地面前,他又看向林木外的草地。风,马,还有歌声都留在了那边。
“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呢?”罗素对艾德蒙唤了一句,“我们该去跟露西娅打声招呼,她明天晚上还得一起来呢。”
“明天晚上是明天晚上的事情。” 艾德蒙回头,对罗素挥挥手,“留给女士一点私人空间,是绅士的美德。”
“说得像你是绅士似的——”
“我就是。”
蓟草注意到,修道院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一个隐秘的符号。
花园本来就颇有野趣,现在杂草蓬生,就更显得疏于打理。这个角落平常被几株长得异常高大的蒲公英挡着,加上夜幕低垂,如果蓟草不是拥有过人视力又实在百无聊赖,她是不会看到这里还有一个被人用刀刻下的痕迹的。
墙脚上是一个显得有点歪扭的圆形,圆心上是一个稍微刻偏了的指南针,指向东方的横臂上有一颗小小的星。
“这是什么玩意?”蓟草低声咕哝,往标志前的蒲公英踢了一脚,把那个奇怪的符号抹了。
“哎呀,”身后传来一阵轻柔的呼声,蓟草转过身,看见露西娅嬷嬷远远走来。身材圆润的年长女人半抱半捧着一个大藤篮,烘焙食品温润的香气透过包裹布料传到蓟草鼻前。蓟草侧侧头,对嬷嬷打了声招呼。
嬷嬷走到墙前站定,低头仔细端详被蓟草好一番蹂躏的墙角。大部分的蒲公英都已经被踩倒,压在墙角渗出一点汁液。还有几棵屹立不倒,就是迎着秋风略有几分外强中干,看着马上就要倒下。
“看到奇怪的东西了,我觉得还是遮住比较好,”蓟草抿抿嘴,说道。
“原来如此,好孩子,”嬷嬷笑了,撩起裙摆半跪在图案的左边。毫不犹豫就伸手挖下陷入刻痕的草泥。
“我不是孩子了,人类。”蓟草也一股脑蹲在嬷嬷身边,盯着她的动作,“我也没有太用力,你看,刻印还在呢。”
嬷嬷哈哈大笑,回了一句,“也对,你们的身体停留在很久以前了,但是你的灵魂一直在往前走。是我忘了。”
蓟草不想和她争辩这个问题,只是暗暗决定,在嬷嬷死了以后要喝点她的血。眼见嬷嬷一边和她讲话,一边手下不停,很快就把刻痕清理出来,显出本来面目。然后她左右张望,又在刻痕附近发现排列整齐的四块石头。看到石头之后嬷嬷点点头,才站起身拍去身上的尘土,提起放到大石上的藤篮。
蓟草看着她一连串的动作,想想就明白,这恐怕是给嬷嬷的记号。
一时之间,蓟草有点着急——是勾结外敌吗?嬷嬷几乎是最接近圣女日常生活的人之一,如果她是敌人的话,恐怕所有圣女都会有危险。一阵电流似的颤栗从她的脊椎闪过,蓟草浑身一激灵,猫一样拱起腰背,下一秒就掐着嬷嬷的喉咙,把她掐死。
露西娅嬷嬷在被杀前及时开口,说:“有个害羞的老家伙来这边了,和我打招呼呢。”
蓟草狐疑地看着她,这实在算不上是一个解释,丝毫不能解释她的疑虑——“害羞的老家伙”不算是什么正经的身份,老实说又害羞又老的人反而惹人怀疑。 老人见识太多了,已经没有害羞的纤细神经。羞涩属于年轻人还会迎风微颤的心弦。
蓟草有自信杀死叛徒,所以她也好奇地继续问下去:“打招呼?”
嬷嬷点点头回答:“我们猎人,”她忍俊不禁,又大笑了几声才继续说,“抱歉,抱歉,我没想到会跟吸血鬼说这个。”
蓟草扁扁嘴,有一点点的不高兴。但是她也说不好不高兴从哪里来,只能别扭地皱皱眉头。
“我们猎人不是每个人都识字,我就是个文盲。也有很多人缺眼睛缺耳朵,少个胳膊腿的,这种符号就是最方便的沟通方法。”嬷嬷一边说一边比划,示意猎人身体缺斤少两的程度。
她指了指墙角的符号和那四块石头,又说:“像这里,就是一种。我的老朋友回来这个城市了,却又不知道为什么不愿意来见我,就在这个角落跟我说话。”
“雷涅也会这个,我们用的是同一套符号。”
蓟草想起那个高大沉默,每次看见她都会有一刻呼吸粗重的身影,点点头:“是你的那个徒弟吗?就像已经燃尽了的炭一样的家伙。”
“他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工会猎人了,我们现在更像是朋友。”露西娅嬷嬷回答,没有回应蓟草的评价。
“嗯,你们挺像,”蓟草点点头,“都是看起来已经熄灭,但是会突然爆燃的东西。”
如果不是感觉到露西娅嬷嬷突然一顿,蓟草还没有留意到自己已经放松下来,几乎已经靠到对方的身边。她抬起头,又继续问:“那么那个害羞的老家伙也是这样的人吗?”
“他呀,他大概一直没有熄灭过,”露西娅笑笑,拍拍蓟草的肩膀,手上有一点泥草的香气,也有一点面包的香氛,混杂起来……居然也不算难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