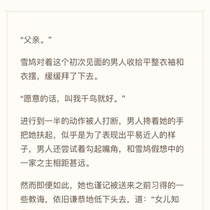火器在过近的地方出膛带来了剧烈的耳鸣,严重到方才还吵作一团的人声都逐渐远去了,连带着自己的体温也一并远去。温热的液体溅在了快餐塑料袋上,目之所及都是红的血。
“天羽……你的颜色可真晦气。”
从八幡第一次拥有意识开始,天羽行火就在八幡命身边,不过那也只是不到五年的时间。
并非指他们相处的时间,只是八幡命所记得的,只有仅仅五年不到的时间。更早的,他记得不甚清楚了,碎片化的记忆像是一团尚未开化的混沌天地,而眼前的红和旧忆里的红逐渐重叠,八幡不合时宜地恍了神。
不知是自己学术不精亦或是哪个步骤出了差错,八幡命曾经差点把自己的搭档弄到七窍流血而亡。
那个时候,鲜血也是这样的喷溅。
满地,满身,满眼,都是。
八幡命吓得坐倒在地没法动弹,牙龈紧咬也因为恐惧错位摩擦。面前的天羽行火直直立着,在他身上投下一片拉长的阴影。
他想喊天羽的名字,但他知道这个不是天羽。
那时的天羽像是有着天羽外貌满面鲜血青面獠牙的恶鬼,谁敢拦他他就要让对方死,就算做不到也要拉着对方在地狱的业火中同归于尽。
“天羽”弯腰,视线和瘫软在地的八幡一触即分,他捡起八幡掉在地上磨得锋利的法器剑,转身没有犹豫地奔向了围上来的八幡氏族人。
下一秒,鲜血再次飞溅而出。
一如今日之景。
天羽行火架住腹部中枪的命因脱力倒下的身体往后撤退,这样做的意义并不大,只是以看似不舍弃的举动让对方维持一个半坐的压迫伤口更痛苦的姿势而已。
他没有将八幡拖行出太远,八幡的身体越来越重,灵魂的重量只有二十一克,失去了灵魂的肉体却如千斤重。
很显然,双管猎枪的杀伤力不容小觑,八幡短而急促的呼吸和嘴里血泡的咕噜声没有持续多久就归于了平静。真是讽刺,话那样多的人到最后被剥夺了说话的能力,也是一种报应吧。天羽仿若颓了般将八幡放下,蹲坐在地。他低头看着——实际上是观察着搭档了无生气的脸。
枪伤的位置离脸很远,八幡命只是嘴角溢出一丝蜿蜒的血线而已,表情比起说痛苦,好像更像是在恐惧…或者说,在愧疚着什么吗?
…总的来说,好像和活着时区别不大。
即便是亲眼见证过五十岚四三死而复生,心知在这里死去是没有意义的,很快就会复活,天羽也有一瞬间的屏息,等待着所谓扭转生死的禁忌发生。
终于,在前几个枪下亡魂相继回归凡世之后,命睁开了眼睛。
“八幡…?”
命看着他,没有回应,眼神那般清澈,好像海浪冲刷过的天空,天羽甚至错觉八幡要像曾经那样喊他的名字。
——行火。
“天羽?我这是在哪。”
八幡爬起来,被枪击的记忆回笼,他原地转了两圈,感觉自己什么事都没有:“哦……我想起来了,我被流弹击中了。不过好像没什么事,如果不是一地血的话真的会以为是幻觉啊。看来神不想现在接我过去。”
“…神都拒收我了,你也等着吧。”
命看了看他的搭档,欠收拾地笑道:“其实你的诅咒起效了。我刚去的是地狱,转了一圈顺便给你探了探路,那里就像个大烤炉,待着还挺舒服的…比这里要好上许多。”
“既然那么舒服不如直接别回来了。”
“我会回来的,因为你还在这里啊。”他就那样把一句堪比诅咒的话笑嘻嘻地说出来了。
天羽认为,绝对不能再让八幡死了,不然这家伙脑袋一定会出更大的问题。
虽然他刻意无视了八幡那半句话,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他也这么认为。这不把人当人,不把鬼当鬼的地方,真的太令人讨厌了。
八幡命已经死过一次了。
在进NT乐园之前,在天羽行火都不知道的时候,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
——
“你们八幡终于把脑子退化掉了啊。”
“只是问问你的意见罢了,我们是搭档不是吗。”
“我很明显就是在受你的精神虐待而已,我有可能发表什么意见吗。”
今天也还是一如往常的火药味对话,伴随着大门开合的声音,房间里恢复了平静。大晚上出门不安全,但命没有去追。反正他总会回来自己身边。
命躺上床,柔软的床垫向他的一侧倾陷过去,如同难逃脱的陷阱。
八幡一族的通灵术多少沾点邪气,引魂上身总会消耗被附身者的阳寿,而全阳命格的人天生排斥亡魂,无法施术,没有成为通灵师的资格,但若是与全阴命格的人搭档,就不会是家族里的废物。
可是那样的人,哪可能说遇到就遇到。
命和行火会相遇,是冥冥之中已然算好的命数。
行火只是个外人,他不叫八幡行火,更不是八幡家的一员,却承担了八幡家的命运。
八幡家收留了克死父亲的他,却没有给他冠以八幡的姓氏。这也许是八幡家从未将行火视为一个人,只是一样趁手的工具的证明,但更有可能的是随便修改姓氏会拨乱命盘,便维持原样。
做这行的总会问命信命,无形的命数是一张巨大的网。
他们从未挣脱牢笼。
——
“以后竟然还能见到你,真可惜。”
预想之中的回嘴没有出现,行火看过去的时候,命已经进了房间。
这家伙是这么容易认瘪的人吗?
行火忍不住想,又后知后觉记起这句话在他们一并被逐出八幡家,肩并肩坐在马路牙子上没有去处的时候自己也说过。
那个时候八幡命仿佛霜打的茄子,却仍旧在面对自己的时候能保持一副温暖到令他作呕的笑脸。他说:“没关系,有我在。”
很奇怪的,他们相处的时间太久了,命的脸他熟悉得厌腻,闭着眼都能描画出七八分来,但一些回忆却又色彩鲜明,好像不会褪色的电影胶片。
命的眼睛,其实和他记忆里不一样了。那对淡蓝的玻璃珠子,他以前总以为亮着所有东西,尽管无法影响他分毫。可现在仔细看去,原来里面什么都没有,是一盏熄灭的视窗。
行火隐约察觉到,现在的命缺失了部分之前的记忆。
但是他懒得去问,就像命也不会过问他为何全身湿透了回房。
问了也没有意义,反正,对方总会回到自己身边的。
——
大脑神经末端传来疼痛的警告,那句话仿佛打开了某个沉睡记忆模块的开关,断续的影像冲击得命头疼欲裂。
他无暇顾及行火,更不想被他看到这副模样加以嘲讽,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回了房间。
头痛的间隙,命的眼前隐约闪过一些模糊的记忆。
自己曾经认为不应该让天羽行火背负他不应该背负的,所以一直不肯听从长辈的安排借天羽的身体引魂施术,没有哪个人生来该被如此对待。反抗家族的代价很痛,但命还能忍受。
可是他忍不了,忍不了行火的背叛。
那是一台被雨水锈蚀了回路的机器,有一双很不通人情的眼睛。
仿若幻觉的记忆渐渐消散,但心口的厌恨感却愈积愈重,扎了根,散了叶。
那种感觉让命干呕不止,胃里仅有的那点残渣也被他吐空了。眼泪是不受控制流出来的。
对行火的愤怒和憎恨比头疼更让他痛苦,如果他经历过濒死的窒息感,或许就知道怎么将它宣之于口了。
——也许我真的死过一次了。才会什么都想不起来。
这想法只在命的脑袋里转了一秒,另一个念头就占了上风。
我要更加、更加的折磨他,这是他欠我的。
于是他打开门,靠着门框对正在擦头发的行火说:“明天也要出门吗?我跟你一起。”
——
这句话出口的转天,所有闯入神的领域的游客都死了一次,海涛一般汹涌的稻草淹没了所有人,没有留出一丝呼吸的空隙。然后时间诡异地回溯,睁眼又是一月二十四号。
没有劫后余生的喜悦,没有重获生命的珍惜,只有雀鸟又被抓回看不见的牢笼的叹息。
命看着天空,那里本应盘旋着鸟雀,此刻空无一物。
“都死过了还是跟你在一起。”
身边行火的抱怨虽迟但到。命回过神,对行火笑了笑,很难得的,笑得并不洒脱。
“…毕竟,我们是彼此的命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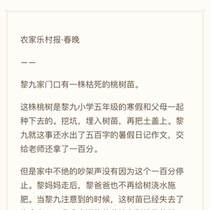


世界上没几个人找得到生活的意义,天羽行火也是如此,但他也不想死。即便不谈那么遥远的东西,就谈眼下,他也不懂他为何现在会身处于NT环球游乐园,但他还是来了。
拖着行李赶火车,在昂贵的酒店或者破烂的招待所之间做抉择,天不亮就来排队,挤到人与人之间没有应有的社交距离,以及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寒感都让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唯一的幸事是买到了双人的特价门票,但这对缓解他的情绪只是杯水车薪罢了——那门票上的游乐园吉祥物也丑得令人发指。
当八幡命问他有没有感觉到什么时,他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不想再在这待一秒钟。
“看来这里让你很不舒服,我们不会是白跑一趟了。”命点了点头。
行火明白搭档的意思。如果是假的灵异事件,就没有东西可查,客户那边就不好交代了。他们还是有职业操守,不会无中生有。
一般来说他们接的都是生者请他们为亡魂满足生前心愿好成佛往生的活计,这次纯粹是因为苦主钱给得太多,而世俗的他们无法拒绝。
可不管怎么说,工作就是等同于受罪,不论是精神层面还是身体层面。
“你又不招魂,难受的不是你。”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你很清楚你不会中止委托,”命直视他的眼睛,目光像是看一件没有生命的工具,在那之中还有更深的恶意,“不过你非要臭着苦瓜脸也没事,反正我也看习惯了。但接委托就是这样,你没得选,你也要习惯。大家各司其职各安其命,最后也各得所偿。”
行火怒极反笑:“这完全就是八幡会说的话,冠冕堂皇。所以我平等地憎恨你们八幡家的所有人。”
命无所谓地耸耸肩:“那是你的自由。我怎么对待你也是我的自由。”
如果是以前的命,总是能找到乐观的角度来看待苦难并安慰行火一切都会好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如此,引魂附体的时候如此,被逐出家门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那样的命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
行火并非怀念过去的命,曾经或现在行火对命的态度始终如一,就像他说的,他会平等地憎恨、当然也会反抗。
设计陷害命被八幡家除名是他的反抗之一,并且不会是最后一次。
非要说有什么不同,现在的八幡命让行火觉得更难对付了。也许是开窍了,人总是要开窍的。某种角度来说,他觉得命的改变是正向的,行火看不起只会忍气吞声和傻乐的家伙,尽管这让他自己的处境更糟糕。
然而,他不会天真地觉得自己能摆脱八幡,同样不会幼稚地为了和命怄气转头离开,诸如此类的对话对他们来说只是日常拌嘴甚至不算吵架。但很明显,交流已经失去了意义,所以行火翻了个白眼没有再接话。
游乐园热闹非常,游人来来往往,而他们默契地缄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