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滑铲打卡x
不好意思我这回连官方剧情都没跟只是个回忆杀(靠
终于能写到琅琅了!(捧脸)
日月真的好难选?!
风在吹。
百琅首次见识到所谓鬼之物,只见其额上生双角,饶是唇角抿成一线,仿若刚吸食过人血的犬齿仍是突出唇外。在那樱花盛开之地无缘见之,原以为不过是民间怪谈传说,没想到竟在隔海相望的地方目睹奇谈中的身姿。看来那些个口舌相传的怪事也不全是夸大其词嘛。
若隐若现的黑色雾气宛如丝绸缠绕在那头短发上,随着男人低头的动作向四处逸散。
狂百之器足下踏着一名酒气熏熏的男子,隔了大老远百琅都能嗅到烈酒味儿,可想而知这人醉得有多不识人与物。那人儿被浊化的器灵踩得胸口疼得紧,这样都不知惧,手臂因醉意打着颤举起,堪堪指着器灵的鼻尖,骂道:“我告你啊,你以为我谁?谁、谁会怕你个倭寇伙夫,趁早赔礼道歉!不然我就让你——吃、吃不了兜兜着走!”
“愚昧。”不愿搅进麻烦事的铃之灵被随风而来的怒声劝住脚步,夹杂着大阪腔咒骂的声音断断续续,“睁大你半瞎的眼珠子看看清楚!”百琅下意识地将视线落在男人一张一合的唇上,以他的眼力轻而易举地瞥见从獠牙上滑落的暗红色被男人用舌头卷走舔进嘴里,男人兀地皱了皱眉,重新摆上一张怒火中烧的面具,仿若先前的邪气只是不符合场景的拙劣演技,被人喊了卡之后消失得一干二净。
“人也好,器也好,哪来那么多高低贵贱。你是谁,我又是谁,重要吗?”倒提的短刀耍了个刀花,寒光闪闪,直指咽喉,“在这块土地上我连个名字都没有,但是这重要吗?天照来了我都照砍不误。”
“我高兴罢了。”
这哪是高兴脸?讨债脸还差不多。
避开横在脚下的断枝,百琅悄悄靠近对峙的一人一器。月光映照在葱葱绿色的发上,倒是衬得他不像鬼神,如果撇开他手中的凶器不看的话。
突然不想撇下无名之器不管。就此放任的话,必是要见血。也许这家伙费了这么多口舌,是想让脚下人憋出些什么话来,不过他也太高估那人的酒量了,百琅若有所思地盯着毫不见动摇的手臂。
一串风铃出现在百琅手中。
会有用吗?
哪怕是这样的我。
浑浊的音还能够……?
我希望能够帮助「他」。
夜风送上铃的问候,轻柔地抚过他的脸颊,在他的耳边缠绵。
铃声渐止。
深林中只剩断了胸骨的醉汉,两名器灵早已不知去向。
——铃声真的消失了吗?
只有伙夫,狂百器,无名器,牙,仇止命,随便怎么称之都行。
只有「他」才知道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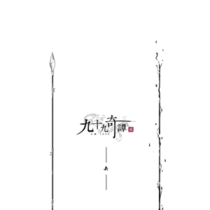
※最终打卡,快乐地汪汪汪
※大概不管徒然堂结局怎么样这个结局应该都不会变的吧……并不知道,求求官方手下留情.jpg
我走进这里。
无人发现我,就连地上飞窜而过的虫蚁也没有。
灵器就是这点好,不过我此刻已无暇感叹。
火光断续,连绵成线,在我头顶兀自挣扎。我听见有人梦魇了,嘴里不住说着“对不起”“我恨你”;有人还醒着,黑暗吞吐其沉重的呼吸;有人正来回走动,踩得稻草咯吱作响。
五感太灵敏也不是好事。浓重的血味和腐臭缠上来,形如幽灵,我不由加快步子,逃跑似的。幽黑的通道唯独听不见我自己的脚步声。
终于,我停下来。这里每个房间的墙壁上都装饰着一扇小窗,奇怪的是此刻竟透进了月光,一束,两束,误入迷途般徘徊,照亮了逼仄房间里男人低垂的头。乱发褴褛,再不复光鲜亮丽。
我唤他:“姞三。”
男人抬起头来,虚起眼辨认一番,淡淡笑了笑:
“……你来了。”
我轻松穿过结实的栏杆,在他面前站定。
“嗯,我来了。”
此次再见已隔五天。我并非每日都来看他,也并不是每日都能见到他。
男人从地上站起来。窸窸窣窣一阵响动,分不清是稻草还是老鼠。身体晃了晃,锁住他的金属随之重重连响。他似乎有些歉疚,又对我笑了一笑。记忆中清秀的脸庞上遍布血痕,新新旧旧,有些结了暗痂,丑陋的痂痕自他衣服里向上爬,断在脖子上。而本应露出脖颈的地方,此时却被坚实的木板所挡。这块木板缚住他的双手和头部,使他以可笑的姿势呈现在我眼前——他戴着枷。
我问他:“疼么?”
他答:“还好。”
我又说:“……傻子。”
他便只是笑了。我发现他今晚特别爱笑,我却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
“店的事你放心,广镜已经从衙门那边要回来了,本来就是个日用杂货店,没什么好搜查的,就是你那些‘宝贝’都上缴了,我想事到如今你也不会再有什么‘挂念’了吧。”
“嗯。”
“我会学着看店的。虽然还有很多没弄懂,不过昼间说到时候会来帮忙,广镜也说会来照顾生意。你不必担心。”
“好。”
我微微别过头去。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么?没有我就走了。”
“莲香。”
他终于唤我了。每走一步,锁头一响,无法拥抱我,就用手艰难地抚过我的脸颊,单薄得像月光下的影子。我不愿再看他,偏过头去,便听他说:
“乖,别哭了,啊。”
我才发觉自己流泪了。
说来可笑,化形已有半年,我仍未能彻底了解自己的情绪。纵然能掌控喜乐,也无法抑制怒哀。不过四个字,却难得像上青天——我自是无法上青天的,狐狸不会飞翔,石头没有翅膀,因此我的比喻听上去也很怪,可我无法再想出更贴切的词语了。我已是一尊残破的陶偶。
慌忙退后一步,“……我没哭!”我道。
“好,没哭。”他顺着我说。
“明天我不会去看你的!”
“好。”
月光乍盛,从顶至踵浇灌他身。我偏过头,又忍不住瞥他。而男人依旧在笑,仿佛明日太阳依旧会升起,他也不会被推上断头台,身首异处,饱受非议。
“那你记得等我,莲香。”
他轻声说。
我闭了闭眼,挤出一句“好”,还未等他说完,便飞快逃走了。我不在乎他想说什么,此刻说再多也是徒劳,而我还有很多事要做,趁黎明来临之前。还有很多。
不知不觉间,月亮远去了。
但我知道,它终将化作飞鸟,衔日光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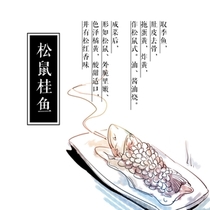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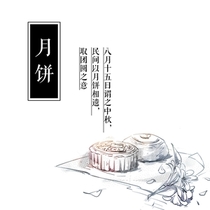
※虽然只是第一小节但这是正常的一章tag(
※渣渣写手抱着xjb写的心态结果卡了半个月也没写完
※题目大概未定因此一章写完后估计还会再改
※不管怎么样先给碑碑一个滑跪土下座
※(二):http://elfartworld.com/works/181837/
还有五天便是“中秋”了。
这些天来常从人们口中听到这个词,似乎是个节日,而且是顶了不起的那种,但具体怎么个“了不起”法,我就一无所知了。后来又听人说这是个除了“过年”之外难得一家人能团圆的日子,我心想原来如此,可我没有家人,自然不懂“团圆”意义何在,所以依旧不清不楚,落得个“面上装明白”,算是这几天以来我遇到的“憋屈事”之一。
那个告诉我“中秋”意义的人此时正懒洋洋地拨弄算盘,见我沉默,淡淡开了口:
“中秋晚上还有曲会。”
“‘曲会’?”
“就是那些个舞文弄墨的酸人大展才艺和歌喉的集会,”若有所思地瞥我一眼,男人轻叹一口气,“可惜您是个灵器。”
“哎呀,那不就是能唱歌么?我前些天刚从酒楼里学来了曲子,到时候岂不是——哦,我……我是灵器啊。唉,真遗憾。”
看我从兴奋跌入萎靡,他应和起我来:“是啊,不然中秋还能指着您赚俩小钱呢。摆个摊子卖个艺,可比开店来钱快。”
“……姞三,你别忘了,我们之前‘结缘’时最后一条定的什么。”
我当即冲他翻了个白眼,不屑地刺他道。
“瞧您这话说的,在下哪敢忘呢。”他眯眼笑了笑。
只是这笑容在我看来毫无真意,那双眼角微挑的眼睛里更含着三分悻悻。
分明是我“占上风”,却全无“赢”他的喜悦——要说来,这应是我结缘来碰到的“憋屈事”之二,跟这一比,连捉弄我的老仇都显得异常可爱。
我干脆闭上嘴,继续趴在柜台上观察来往行人。
“哦,对了,好像还会开灯会。地点都一样,在虎丘山上。”
他接着说了下去。
“……‘灯会’是什么?”终究败给了好奇心,我嘟嘟哝哝地问。
他浅笑:“到时候您就知道了。”
“你就不能不卖关子吗!”我瞪了过去。
“莲香姑娘,我们做生意的总是要‘留一手’的,”他悠悠道,“不过嘛,在下这次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和您解释。想来还是您亲自去看会更快,反正也没几天了不是么。”
全是废话。我撇撇嘴,自柜台上跃下。从狐狸化为人只消眨眼之间,我挥挥手,扔下一句“我出去玩了”,便三两步跨出了这家不大的日用杂货店。
姞三并没有回应。
我从未期待过这个男人的回应。
起初我还会一本正经地提议,让他别这么礼貌,“从今以后你我朝夕相处,犯不着‘您’来‘您’去,更用不着事事句句都在‘莲香’后面拖个‘姑娘’二字,生分得紧”。但他听罢只是笑——他这笑容往往是嘴角挑得高,眼睛却不配合,混黑的眼仁儿里容不下丝毫笑意——然后慢条斯理地说:“嗳,莲香姑娘,在下知您一片好心,可有些事,该生分还是得生分。”
当时我搜肠刮肚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他带给我的感觉。
现在我知道了,那叫“疏离”。
他那极度的疏离将包括我在内的万事万物皆拒之门外,但偏偏有一样,他从不拒绝,见之欣喜,甚至渴求——
钱。
这也是我最无法理解的一点。
并且,我猜这人世间的负面情感,或许大多都缘自这“不理解”。
虽说我身为灵器,平日里感受到的、涌上“心头”的情绪,很可能只是有如皮影戏般,在这块名为“莲香”的白色幕布上留下形影,但我对姞三抱有的“不理解”确是真的。我不能理解他对钱的执拗追求,于是这种“不理解”使我越发看不清他的为人。“看不清”是可怖的,更何况眼下我和他已被徒然堂的契约捆在了一起。
但我疏远他的缘由,也并不仅是“不理解”。
因为我能感觉得到——
灾咎之气正蛰伏在这个杂货铺里。
不过,我承认,我其实挺爱忘事的。迈出店门时我还在思考,姞三随手摆在货架上,平时擦也不擦、拜也不拜的那些神佛究竟有什么用,踏进徒然堂后脑子里便只剩下“好想吃烤土豆”了。常山依旧经不住我一番死缠烂打,最后黑着脸帮我烤好了土豆。我则顺便偷偷把眼泪鼻涕全抹在他袖口上。常山本人是全没发觉的,不过和我一起吃土豆的莓莓看见了,直笑得常山变了脸,横眉竖目活像话本里的包青天。最后他忍无可忍拂袖离去,离开前还狠狠瞪我一眼,说是再也不给我土豆吃了。
我自然是不信的。
说来,这位秀净书生和远在城外的仇止命倒有些相像之处,我也就是仗着这点才敢如此胡来。要我说,他们那样成天板着个脸、苦大仇深的才叫无趣,真是不想捉弄他们都难。
心满意足之后,我哼着调子,一蹦一跳地出了门。自莲池至入口尚有一段距离,路上桃花不败,秀色迤逦。而今日恰是秋分,徒然堂内四处可见有所求的客人和有所思的灵器,无论是迷惘而至、顿悟而离也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也罢,总之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我亦于此和她重逢。
眼熟转为疑惑,再淡去,化作激动,彼时泛着暑热的记忆便借机摇身一变,成了眼前的少女:之前绾在脑后的长发如今花苞似的缀在耳旁。她拢了拢搭在红衣外的素色褙子,打量着我,杏目微张。
“是你!”
粉面桃花相映红。
从未目睹过的春天此刻正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站”在我面前。而我除了挠挠脸,揪揪衣摆之外,也只能点点头,再笑一笑:
“是……是我,好……好久不见呀,嘿嘿。”
说来真奇怪,这次见面之前,我是早已淡忘了她的。自结缘后,我心中既已认定了与她彻底“无缘”,也就谈不上什么“再见”。哪知今日天公作美,叫我再遇上她,仿佛清风一缕皆有缘,桃花一枝便相识。
那么这次可不能“错过”了。
我便鼓足勇气,又开口:
“谢谢你送我的西瓜,特别甜!我——我叫莲香,莲花的‘莲’,你呢?你叫什么?你为什么会来这里?那时你怎么知道我住在徒然堂里?”
少女眨眨眼,“扑哧”一声轻笑起来:
“我姓朱,叫朱杏,杏花的‘杏’。是这里的清净师。”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清净师”。和我想象中的大相径庭,朱杏既没有刀剑加身,也不会凶相待人。她看上去手无寸铁,却对我这样刻意露了些兽形的灵器毫无畏惧——遑论我这模样与志怪话本中的“狐狸精”别无二致——好像她眼前的“莲香”只是姑苏城中随处可见的一个普通人。
且不提徒然堂里的几个店员,就连季远林初次见我时亦是惊讶连连。我原以为只有那个男人才会这样“泰然自若”,虽然我现在知道他的从容大半源于“我这个玉佩不能换钱”。
看来不是的。
看来我总归是感激多过诧异的。
“那你今天来……”
既然是清净师,那就少不了要面对“某种东西”。实际上我尚未见过“那种东西”,因此不免好奇,想从她的脸上看出些端倪来。而她敛了笑,眉头轻蹙,道:
“我今天,是来接‘委托’的——”
“是‘狂百器’对吗?!”
朱杏被我突然扬声的询问吓了一跳,略有迟疑地点头。
于是我笑盈盈地说:
“带上我吧,朱姑娘,我想去看看!”
答案自不必说,是否定的。
但我莲香别的没有,就是“死缠烂打”的功夫比其他灵器强。所以从走出徒然堂的那一刻起,我就决定了要缠着这位姑娘,而朱杏显然碍于我们之间刚认识,并不好态度强硬地拒绝,故而我得以一路从徒然堂“缠”到了她家门口,直到朱杏说要去和家里的灵器们商量商量,独自进了家门为止。
她原本还邀请了我,不过我说在外等也无妨,便笑盈盈地目送那红色衣角消失在了门后。
朱家坐落在街旁,推开漆红的大门便可置身闹市。
吆喝声。车马声。谈笑声。红尘四合,烟云相连。来自人世喧嚣明亮的一切就这样滚滚而来。我禁不住欣喜,却又满是犹豫。
我不过是一只狐,一个器,一粒沙罢了。
紧接着,“一个东西”突然而至。
它的到来如惊雷将我劈醒,而我足足反应了三秒,才拔腿向它追去。奇怪的是它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它——他在街市中过于显眼,我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循着那大肆散发的气息,寻见了他。
我不得不仰头望去,黑衣青年正立于我身前这座平房的屋顶。
这么说也不太准确,因为他“本人”是坐着的,站立的是他身下那只纯黑的兽——因被房檐挡去大半而无法看清姿态,我只觉那是黑乎乎的一团,眼神却十分锐利,像随时会扑下来撕碎我一般,死死盯着我。
目光再向上移,便可和他对上视线。青年较自己的坐骑要淡然许多。头生两角,黑发白面。光看这些总会错以为他和我一样,但他的气息——那股无意隐藏也无法隐藏的气息,着实异于灵器,安静又凝滞。
山雨欲来风满楼。
这就是“它们”的气息么?
这就是……“狂百器”么?
但事态已不容我再多想,陆续有普通人开始注意他。孩童不谙世事的提问,少女婉转含羞的娇笑,以及上了年纪的人戒备的低语,这一切都似发酵般逐渐膨胀,只待那个姑娘踏出门来,给他最后一刀,名副其实的“清净”。
不行。他还不能被净化。
在我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之前,他还不能失去现在这个“身份”。
但是——我转念一想——若多留他一天,他便能多伤一人。这会是一个普通人所期望的事吗?
于是我陷入了迷茫,本还在朝他费力挥舞的双手也僵在半空中。而青年仍是那副姿态,不悲不喜,不动不惊。我有些急了,索性跑进巷子里,希冀能找一点垫脚的东西,让我顺利上去。但这条仅容两人宽的逼仄巷子竟比从外看去时还要昏暗,青天白日的,只透得进一抹光亮,虚虚浮在脚边——正发愁时,一只手突然从我背后探出,紧紧捂住了我的嘴。
“别出声。不想死就……别出声。”
男声沙哑。那只封住我的手阵阵颤抖。
我一惊,心里已是百转千回。
唯一能确定的是,这不是刚才屋顶上的狂百器。可我为何没发觉?
不过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无法动弹,也不能说话,而且尾巴正被他毫不留情地踩在脚下,疼得我像吃了黄连,咽不下、吐不出。所以我艰难地摇摇头,希望这点小动作能证明我并不会“出卖”他。
但他显然不明白。
我所能听到、感受到的,来自他的喘息,不由让我想起了老旧的风箱,已鼓不出任何力量,却又拼命地“苟延残喘”着。
“那个清净师……那个清净师!”
他开口了。
“你也是她手下的灵器是吧?只要我放了你,只要‘我们’放了你,你就会跑去通风报信,是不是?!”
低哑的怒吼。
我赶忙摇头,可他全然没有察觉我的回应。在昏暗中,在嘈杂中,在朱杏和陌生灵器的气息逐渐迫近的一分一秒之中,他只是重复着一句话,用他那喑哑的嗓子和浑身的战栗,反反复复,不知疲倦。
残破风箱刹那鼓出冲天烈焰。
“我要,‘我们’定要杀了他,不然就和这‘吴国’……同归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