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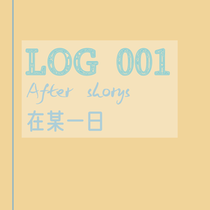



铛——铛——
单调的敲击声一下又一下,在烧灼的锅炉前,随着那扰人的声响,丑陋的铁块终于有了一丝令人愉悦的弧度。
在江户开分店是二人折中后的结果,霭之辅是断不可能答应她那任性的请求的,就算他当真听懂了。想来也是要装傻充愣、当这一切不曾发生过的。
关于武士斩鬼的消息已在坊间流传开来,锻刀的生意也逐渐好做了起来。柚叶偶尔会从客人及过路人的口中听闻又有哪家的鬼女吃了人、或是哪家的妖怪被逼现了原形砍掉了脑袋。人人都当这是一桩喜事,就好像在新年的钟声里,他们终于能彻底过上太平日子了。
虽说家中的生意见好,但霭之辅并未辞去原本的差事。若是家中有武士帮衬,想来开店初期日子也不会过得那么艰难。他说得冠冕堂皇,但柚叶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对她避而不见的借口。开店那日来祝贺的人有许多,心华也是其中之一。但她匆匆送上了一壶酒,便说店里还有事转身离开了。江户中人人都很忙碌,人人都沉浸在那和平的祥和之中,倒显得柚叶有些像个外人了。
“……心有杂念,学艺不精,回炉重造。”
她将霭之辅寄放在这里的断刀抽出,端详着那颜色已经有些暗沉的断面,良久将自己对他的评价如数奉还,在一声叹息中重新将之收入鞘中。她曾多次想要重锻这把刀,但试了多少次都不甚满意,只得一次次作罢,拖拖拉拉到现在,还没有将这份答应好的回礼还给霭之辅。
无论如何,唯独在这件事上,她似乎无法静下心来。她也想过干脆重新拿起画笔,但每次把手搭在画箱上时,终究还是摇摇头到此为止。
新的一年到了,而霭之辅还能再与她共度几个新年?
柚叶并非不知自己义兄的顾虑,正如她并非不知他那份差事实为同类相残,但是她不在乎,有些事她无论如何也无法妥协。
“唉……”
她叹着气,从怀中掏出霭之辅赠予她的簪子拿在手中把玩。也许她是时候该下定决心。
那吴服对夏天来说太过沉闷,对冬天来说却正正好好。
不管怎么说,也是新年伊始的日子,今天就吃天妇罗吧。柚叶心想。
然后等大哥回来,吃过饭,我们就一起去水天宫参拜,也算了了一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