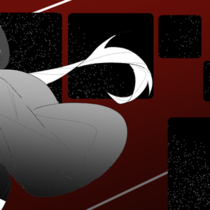这是,呃,这是日常……对不起,又在写日常……
字数:3027
+++++++++
一足鸟没饲养过任何宠物。路边的狗是“狗”,野猫是“猫”。跟着父母在草原观测到的是“那只红鬃毛狮子”和“弯尾巴的母豹子”。
一足鸟没记住过全班同学的名字。
刚转学回日本时是因为实在记不住:有太多“藤”和“田”了,后来则是发现记不住也没关系,不会和所有人都说上话是很正常的,即使有不知道的名字也可以敷衍过去。
再往后,由于不会邀请别人到家里、也不认为多说几个字是不便的,所以他从未给购置的智能家用机器改过名字,总是直接喊出厂编号。
到考研阶段开始接触的MOBA类或生存类游戏也几乎不需要记住谁。不是“绿色”的都是敌方,也没什么NPC。
地图里可能存在一些“人”,但他们不可以被点击,只会和地图里的猫和鸟一样来回地走来走去,归根结底跟树木石头没两样。偶尔有几款游戏会设置“武器商人”或是“道具商人”,但也不过是以人形出现的武器商店。需要注意的只有“玩家”(人)。
他在长达两年的游戏生涯中只记了四五个玩家名,其中包括MondAy。结果被对方带着玩其他类型的游戏时发现这位在MOBA游戏中人狠话不多的辅助队友居然非常喜欢给游戏NPC起名,并且不是“小黑/小白”之流,而是更难以记忆的...
——哇啊!每次铃响了这个女鬼就会跑出来,我们就叫她琳达吧!
——啊呀啊呀我靠这个兄弟跑得太快了我去好悬被抓,就叫他腾达吧,嗨,腾达!
——嗯……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NPC长得像一个八十年代女星?她演过一个叫曼丽的角色和这个建模有八分相似啊,从今天起她就叫曼达丽咯。
行吧。MondAy在他面前的安静只是事物两面性的其中之一。当一足鸟为他的安静和默契而心生共鸣时,对方实际上只是关了队伍语音、正在直播里向粉丝叭叭输出。
一足鸟完全知道这件事。他不是实况主播,没有皮套、没有摄像头,不录屏。但他刷到了MondAy的直播间,并且还在过往录播里看见了那些他们打得不错的局。有趣的是,周一直播间里的人已经认识他了,他们管他叫“MondAy的玩什么都上手超快的无口系游戏搭子”。
不错的称呼。一足鸟确实很能掌握诀窍,当他们尝试其他游戏时也依旧如此。除了一足鸟在整个研究生期间要记的名字都没和周一打一周游戏需要记的多以外,一切都很好。
他在游戏里镇定自若地引怪,面对大部分Jump Scare都一声不吭,力求把所有尖叫机会都留给周一。大概没人会想到对这只沉默寡言的鸟而言,游戏中难度最高的一环竟是记人名——并且他不会重复问那些NPC叫什么,只会在每次直播结束后默默回看录播。是的,没错,他就是那种表面假装在玩、实际晚上回去偷偷做题的家伙。
而“记住名字”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名字具备指向性,当有知性的生命知了某个名,于他而言,那件具名之物就不再是物了。
再说直白点,一足鸟发觉自己会自然而然和它们——这些数据——说话,不管对方是“怪物”还是“友方”,这让他有时候显得有点奇怪。
也许这该归诸于家庭影响:七鸟家没有话多的人,四个人中双亲常年不在,胞兄七鸟谦人比手势多过用嘴说话,餐桌常年安静得像是墓地,吃饭如上坟(不奏哀乐版),并且每个人都对此感觉良好。如果有人需要酱油会自己去拿,如果有人决定过会儿再继续吃也不会有人追问“这是要去做什么?”
反正洗碗也是各洗各的。
得不到令人满意的回答?算不上问题。对方不说话?也不是大事。不受语言所限,人只要具备沟通的知性和意愿就能相互交流。这是人类值得自傲之处,无论什么样的沟通方式都不应当受到责难。
也许这就是一足鸟被困于伊弥尔后,面对形态歪曲、像是刚从丧尸片场跑出来的琳娜没立即远离的原因。他没法把她当成一个“怪物”。在游戏中,她有自己的职务和活动范围,并且[曾经]能正常交流。
“你需要帮助吗?”他对她喊。
她回答“请签字。”
“你会痛吗?”他问她。
她回答“请请请这里签字。”
他在第一会议室的门口注视她。她腿脚已坏无法追赶,在卡顿的噪音里,只剩一只的眼睛看着他。
美丽的、驳杂的绿色。
啊,一足鸟确定自己帮不上忙。她的形体和语言模块损毁得太过彻底。那么...谁能帮她修复?
周一?
他对游戏知之甚多。但修复程序和游玩是两个概念,比起修bug,他大概更会卡big,pass。
某名程序员?
在vr游戏里修程序,这听起来不像是常见的事。而且哪里会有一个程序员?系统面板根本呼不出客服。
或许,另一段更高级的AI能帮上她。
【莲耶】【柯蒂】【Karma】
(他忽略了伦纳多,因为据说那位新手引导员已损坏到自身难保)
——【Karma】
对方无响应。
他似乎负责处理“异常状况”,但一足鸟不清楚这一名词的具体范围。也许“维修”是另一回事儿。
——【柯蒂】
于是一足鸟看向墙面,像呼出菜单一样轻念这名,选择求助于最像是“协助者”的这一位。
这一次他得到回应。平和而消极的、对此情况不予置评的回应:就像图书管理员被要求帮忙查询一本书。
他谨慎地问,你会修复她吗?
“修复?你不是希望这里变成正常的会议室吗。它会变成正常的会议室的。”柯蒂问。
他像在提问,又像只是在记录即将产生的回答……就好像一个打开商店窗口的道具商人。你大可抱怨他的武器太贵,但除了交易物品以外,他不会和你交流任何事。
可他有一个【名字】。他不该是那样。
“我希望这里变成正常的会议室。同时我希望她‘康复’,不要再看起来那么疼。” 一足鸟说。
“你预设她会疼。”ai,柯蒂看向他。 他阐述疼痛的定义(就像字典里写的那样),表达了对于他预设“程序会疼痛”的不理解。
一足鸟意识到自己用了错误的词汇,而这使得重点偏移了:“不,不是疼。对人而言,疼痛的康复过程算是一件好事——死者、瘫痪者不会疼,但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那一部分肢体或整个未来。
“作为AI、如果她因为病毒被就此抹消,她的学习能力、已累积的数据也就消失了。这和我们失去'疼痛'是差不多的事。”
柯蒂审视他:“所以,你也想让这些永远留下来。”
一足鸟不知道那个“也”是对于什么而言。
他不害怕说话,但也实在算不上擅长。他无法像演说家一样说出激情洋溢、摄人心神的长长论述,只是干巴巴地讲:“如果能被修复,也许这部分东西就能被保有,她也能继续学习、成长,继续拥有‘未来’——我认为‘未来’是重要的东西。”
那样的话她会继续生长。你想要她继续生长。柯蒂说。他说的话像是打开监控的指令,无数无形的摄像头转向了一足鸟。但没关系,他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琳娜和柯蒂身上,压根没发现。他和柯蒂对视。“是的,我希望她继续...理性地生长。”
我明白了。那么,我会修复她。柯蒂承诺。
“武器商人”放下他的物品清单——他现在完全面向他了,做回了柯蒂,没再要他从那些系统供应的装备里挑一件。
他的确做到了。
于是一足鸟又一次呼出他——这次是为了表达谢意和关心。 但不太成功。
他抱着没被疼痛消磨干净的一点好奇心问:“你学会敷衍了吗,柯蒂?”
他微妙地期待对方的回答,遗憾的是这次的NPC似乎是 他自己。
柯蒂没怎么回答他。实际上,他观察他、判断他、分析他。像人对于人,像主控对于游戏中的角色。而他疲惫地站在那里,作为一名熬了两宿夜的新鲜社畜,任由这位武器商人打量、诠释、理解。
“所以你因为我接受并完成了委托,对我提出感谢?你对 其他人 也这样吗?”柯蒂问。
其·他·人——如果将自己归类为非人,他该说“你对人也这样吗”?——他听起来像是把自己也归入了人类的行列,一足鸟想,但这又有什么不可以?
一足鸟在非人的横瞳之中看见自己点了点头:“是的。对于没有必要服从我、但接受我选择的人,我提出感谢。 ”
“你视我 为 人类。”这些字被打出,又被迅速抹去。
柯蒂好像误会了什么。但凡有名之物、有灵之物,凡寄托人之情感之物。在它们身上,人与非人的界限本就没有那么鲜明。
如果武器商人抱起他的家当跑掉了,那就随他跑吧,别把他追回来只为了买那点破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