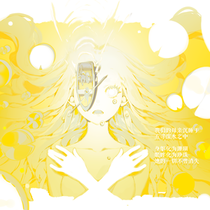还是接费恩的《迷雾》 http://elfartworld.com/works/9214499/
——————————————————————
还未踏入这座森林的时候,恩斯特已经有种不祥的预感。这种预感既来自于阴沉的天气,也来自于上一次被袭击的阴影仍笼罩在他心头。马儿不安分地在森林的入口打转,也在表达它的抗拒。恩斯特望向费恩,费恩则凝视着森林的深处,说:“前进吧。”此刻恩斯特已经对费恩抱有完全的信任,于是他点点头,跟在了费恩的身后。
两个人牵着马,步入了茂密的森林之中。天色极其阴沉,而这树林又格外茂密,四周的视野极窄,昏暗得像夜晚。这条路更像是野兽经过的小道,对两个牵着马匹的人来说显得太窄了。马依旧很不安分,走得不情不愿,还不停地打着响鼻。而四周极静,除了人和马的脚步声,衣物的摩擦声,似乎什么也听不见。
不知道为什么,恩斯特也敏锐地感受到,这奇异的安静也许是危险的预兆。
费恩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平时非常冷静的她,此刻警觉地观察着四周,偶尔还回头确认一下身后。恩斯特在心里祈祷着,希望这片森林不大,马上可以走出去。可走了不知道多远,恩斯特感觉双腿已经有些乏力,四周的景色仍不见一丝变化。回过头,来时的路也隐没在了浓密的树丛中。
森林内的湿润的空气让恩斯特有些喘不过气,他甚至感觉自己吸进去的只有水蒸气,没有氧气。他很想停下来休息一下,但是四周没有看起来适合休息的地方,而且他们已经前进得很慢了。他迈着沉重的步子向前移动,甚至意识都有些涣散。正在这时,天上突然闪起一阵白光,然后是一声惊人的巨响,让恩斯特彻底惊醒。没过几秒,雨滴从一点一滴,迅速变成了倾盆大雨落了下来,世界被嘈杂的雨声完全覆盖。
恩斯特戴上了斗篷的兜帽,仍感觉雨点打在头顶有些痛。可怜了那些没衣裳穿的马儿,任由雨水击打着身体,然后顺着毛发落下。小路变得泥泞,更加难以前行。恩斯特心中是想努力跟上的,但是身子有些不听使唤,渐渐地和费恩拉开了一些距离。
“费恩小姐……”他去喊费恩的名字,可他的微弱的嗓音被掩盖在了暴雨声下。
费恩的身影逐渐变得遥远,而恩斯特没有拉近距离的办法。他实在是太累了,最终只好停下脚步去休息。
只休息一下就可以加快脚步赶上去,他想。他靠在了一棵树边,抹去了脸上的雨水,也摸了摸马的后背。他确认了一下挂在马上的行李箱,被盖得严严实实,里面的纸张和衣物应该没事。
因为害怕落得太远,他只休息了一下,便决定继续前进。可是雨太大了,而所谓的小路也因为被雨水冲刷得看不清了,他张望着四周,不知道哪边才是正确的方向。
“费恩小姐!”他又试着去喊,可结果一样,仍然没有回应。
和那天一样,他再次和费恩失散了。
他的心开始砰砰直跳。即使知道自己已经迷路,他仍不敢多做停留。不安驱使着他去前进,去主动寻找费恩。旅行刚开始时他还觉得大自然优美动人,现在只觉得可怕。他原本觉得无论之后的旅途有多危险,只要有费恩在就一定会没事的,没想到自己竟会在这种情况下重蹈覆辙。
他向前——至少是他认为的前方行走着,一边叫着费恩的名字,而暴雨似乎断绝了一切的可能性,只是无情地冲刷着树木与大地。
突然,他感到了动静。他看向有动静的方向,但依然看不清什么,只感觉树丛有些晃动。也许是费恩在那里。他向有动静的地方走去,不见人影,却能感觉到了目光——而且并不是友好的目光。抬头环顾四周,那目光并不只来自一个方向。
强烈的恐惧再次涌上他的心头。他松开牵着马的缰绳,已经准备自己逃跑。但他又看向马——他的书、手稿、旅费,都在行李箱里,至少得带着箱子。他的脑中只是斗争了这么几秒,危险已经靠近——一双双血红的眼睛在树丛中显现,而且越来越亮,越来越清晰——它们正在向自己靠近。
马开始不安地叫唤,用力地把马蹄踩在水洼里。意识到只能不顾一切地逃走时,已经晚了。他已经被包围了。那些眼睛继续逼近,獠牙与身形的轮廓也逐渐浮现。他看清了这些眼睛的真面目——是饥饿的狼群,但体型庞大得接近狮子。
他的呼吸逐渐急促,大脑一片空白。没有任何祈祷或想象的余地,狼群已经走到了他几米旁的地方,那些血红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淋雨的身体显得极瘦,同时看起来更加残忍。而自己,就是他们今天的食物。
终于,一只狼突然扑向了恩斯特。恩斯特看着狼张开血盆大口,咆哮着冲过来时,他只想到了死。他想到了妈妈,想到了米娜,想到了教会的墓地,想到了数日前被费恩处决的吸血鬼——他想到了费恩。
“恩斯特——!!”
他回到了现实,本能让他不假思索地从腰间拔出短刀,向狼挥去。那一瞬间很短,但恩斯特感觉过程异常的漫长,而且清晰。动物的咽喉如此脆弱,以至于这把锋利的短刀毫不费力地切了进去,就像是拿剪刀剪开纸张。劲动脉喷射出的鲜血模糊了恩斯特的视野,但他看到狼从半空中落下,鲜红的眼睛失去了光泽,紧接着响起了沉重的身体落地的声音。
野兽变成了脚边一动不动的尸体,倒在了泥泞里。野兽的血溅洒在他的皮肤和衣服上,散发出强烈的腥臭味,让他想要呕吐。但他仍然紧握着刀柄。四周的野兽开始退缩,也许是因为看到了同伴的死。
然而事实是——手持长枪的猎人,形如死神,悄然而至。直至费恩来到他的身前,他都没有意识到那是真正的费恩。他一直以为刚才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也是幻觉的一部分。
“没受伤吧。”费恩看了眼一身血迹的恩斯特,低声问着。
“没有……这不是我的血。”
她微微点了点头:“注意我的身后。”说完,她举起长枪,走向野兽。
恩斯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右手——血沾满了袖口,刀尖上的血混着雨水正滴答地落下,又流淌至野兽的尸体。原来夺去生命竟是如此感受。一种诡异的满足感在他胸中膨胀开来,好像试图填充他心中原本空缺的部分。刚才的野兽草草殒命,而作为猎物的自己靠着武器将形势轻易地反转。尽管是无可退让的情况,但他仍然不可避免地享受到了主宰生命的权力带来的快感。暗处依然存在着贪婪的目光,但至少现在他不害怕了——费恩在他的身边,而且他手中还有一柄锋利的武器,还可以反击……
胸中的高扬感使他举起了武器,而在他的身后,费恩早已收拾掉了靠近的几只。狼群开始后退,眼睛里的光芒变得暗淡。最终,它们像普通的狼一般,呜咽着消失在了黑暗中。
世界又恢复了平静。暴雨继续落下,好似永远不会停息。
费恩甩掉了枪上的血,然后走到了恩斯特身边。
“你很勇敢。”她说。
恩斯特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短刀。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自豪——对于成功地保护了自己这件事,又夺去了其他生灵的性命这件事。他轻轻拂去短刀上的雨水和血水,放回了腰间的刀鞘:“费恩小姐,抱歉……我又跟丢了。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一次了。”
“可你没事,这是一件好事。”费恩回到了马匹的身边,“学会保护自己是在这个世界上活下来的第一步。我看到你攻击时的样子,你学得不错。”
“谢谢……”恩斯特长舒了一口气。安心感和疲惫感同时涌了上来。被雨淋得完全湿透的衣服包裹着他,带走了他身体内所剩无几的能量。
“接下来你走前面吧,这样也不会走散了。”安抚好受惊的马后,费恩重新戴好兜帽,将自己完全纳入黑色的斗篷下,“我们先找个地方躲雨。这场阵雨应该很快会停,在那之前可以稍作休息一下。”
“好的……”虽然这么回答着,但恩斯特估计自己的体力应该无法继续前行太久。也许走一下就找到休息的地方了,不然还是要继续淋雨。于是他拖着灌了铅一样沉重的身体,重新迈出了步伐。
再往前走一步,再努力走一步……他不断地在心中鼓励自己,可虚弱的身体和意志背道而驰。渐渐地,他的意识和身体几乎分离,感觉消失了,于是痛苦也跟着消失了。他的身体很轻,意识也很轻,视线开始泛白,一切都变得模糊,雨声也变得遥远……
***
旧日已经消散
曾经拥有过的宝石与欢声
罪恶或无数伤痕
化作风中尘埃
/
语言已经黯淡
牵起彼此的手
让界限融化在呼吸之间
直至审判来临之前
/
你存在过的地方
绽放着看不见的花朵
神将其采摘
装点最后的丰收
/
月亮牵引着命运的浮沉
潮起潮落间
忘却世间万物
和每一颗星曾经的名字
/
饮下这杯美酒就上路吧
默念他的教诲
“来到我身边
你将看见从未见过的美景
你将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
你将获得完全的自由
你将获得永恒的祝福”
/
审判已经来临
***
费恩阅读着碑上的文字。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但她隐隐约约读出这是一首圣诗。她抬起头,圣母像的头发和右手已经残缺,悲悯的目光中长出青苔,洁白的手臂和衣物上布满污渍。或许正是因为没经过打理,这座圣母像透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宁静与慈爱。
她回过头看,躺在长椅上的恩斯特依旧没有醒来的迹象。
这座森林她已经往返过好几次,但她从没有遇到过这么一座教堂。也许因为森林太大,也许因为这场大雨让人迷失了方向。费恩将昏倒的恩斯特驮在马背上时,心想也许这一切是神对他的试炼,但找到这所废弃的教堂时,她又觉得这可能是神对他的怜悯。
不过归结到底,和神也没什么关系。只是许多因素重叠到了一起,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可怜的孩子,也许就会倒在这个地方。费恩走到他身边,低头看他的脸。恩斯特紧闭着眼睛,嘴微微张着,好像想说些什么,可因为虚弱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能做的事情费恩都已经做了,接下来的事情只有等待雨停,以及恩斯特自己恢复意识。这种等待并不令人焦急,因为费恩早已习惯。她见过太多无法挽回的事情和脆弱的生命,她的心早已经冰冷。但她仍然一步不离地守在恩斯特身旁,盘算着之后的计划——雨停后就离开森里,去镇上找医生给他治病。自从她意识到恩斯特身体不佳之后,偶尔会想象他病倒的情形和应对方法。自己的任务只是护卫,照顾和治疗都是额外的工作,需要交给其他专业的人。只是她没想到,一切会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
这真是一件比预料中更棘手的差事。费恩坐在另一把长椅上,握住长枪。教堂外的雨继续下着,隔离在室外的雨声听起来反而令人安心。她看向破漏的屋顶,缝隙间透出来一点灰暗的光,和淅淅沥沥的雨水。至少情况不会再坏了,至少没有外伤。在这神圣的地方,她感觉不到任何的同情,或者受到感化。她试图通过教堂的破损程度计算这里废弃了多久,推测为何在森林里会有这么一座教堂,是什么人曾经在这里祈祷,这是否也是教会的战略的一部分。她想了很多,但时间仍然没有过多久。躺在一边的恩斯特一旦有动静,她就会起身去看。
不知为何,她突然觉得恩斯特其实不是在发烧,而是被困在一个无法醒来的噩梦里。有的时候她也会想到过去,当自己还极为弱小的时候,经历过的极为凄惨的日子。由于那种生活和现在过于迥异,她偶尔会觉得痛苦的记忆也许并不是真实的,只是一场短暂的噩梦。
也许躺在那里的,是噩梦里那个弱小的自己。她俯视着自己。那个自己蜷缩着,颤抖着,等待着被爱,被关怀,被拯救,等待有人牵住自己的手,带自己离开这里……
但她只是开口对那个人说:“活下去。”
***
雨依然下着,他看见了远处伫立着母亲的身影。他明白,只要看见母亲就一定是梦境,因为他实际上并未见过母亲。他过去只在家中的画像中见过她的模样。画中的母亲仍是少女的模样,有银色的头发,苍白的皮肤,瘦削的脸颊和肩头。随着自己的成长,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和画像中的母亲越来越像,不知道这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
他并不会经常梦见母亲,她只在自己十分痛苦的时刻出现。梦中的母亲比任何人都要温柔,比任何实际见过的人都要熟悉,都要亲切。她通常会出现在一片光芒中,仿佛和那光线融为一体。她会坐在自己的身旁,用轻柔的声音问自己,发生什么事了。恩斯特有时候会讲述,有时候会抱怨,说出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说出口的话。但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开始选择不去说话。他们牵着手,只是欣赏着梦中的景色,体验这美好的时光。即使没有交谈,他也会感觉好起来。这么多年来,他觉得母亲依然在守护着自己,在自己最为脆弱的时刻悄然而至。他多么希望这些梦是真的,或者永远不会结束。以至于他在之前看到吸血鬼幻化成母亲的幻影时,惊喜之情让他愣在了原地。之后他想起时,心里最深处甚至会游荡着一种念头——或许死在那个瞬间也是幸福的。
但是这个梦和以往有一些不同。母亲离自己很远,在雨中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他向母亲的方向走着,但无论怎么走也不见接近,母亲好像永远离自己那么远。他有些焦急,加快了步伐。最终,他走到了一条河的前。那条河好像是雨水聚集而成,河面漂浮着散落的树叶和花瓣,漂向下游。他被那些花瓣们吸引了注意力,想要抓住它们,于是他蹚进了河水中,跟着水流向着下游移动。
他听见有人在岸上叫自己,但他也没有回头。可那声音不断地呼唤着自己,使他渐渐意识到自己不是那个孩子,他现在的名字是恩斯特,正身处旅途中。
费恩正在教自己使用短刀的方法。
“恩斯特,你的刀没有握紧,这样武器会很快被敌人夺走,或者没办法刺穿猎物的身体。”
“那……这样呢?”他使出更大的力气握紧刀柄。
“……还不够。”费恩握住了自己的右手,仿佛每个关节都在发力一般,握得自己的手背生痛,“要这么大的力气。记住了吗?”
“知道了。”
费恩松开自己的手:“再试试看。”
这次,他紧紧地握住了短刀,向前挥去。突然,一阵强烈的闪光出现,伴随着雷鸣,他又回到了森林里。大雨依旧下着,他的手里握着短刀,地上没有尸体,但刀尖却淌着血。他心中不安,想扔掉手中的武器,但又害怕敌人出现。他环顾着四周,终于再次看见了母亲的身影。
他松开握住短刀的手,向母亲的方向走去。他走着走着,发现自己又身处河流中。温暖的水流包裹着自己,让他觉得安心,愉快……他觉得自己也要变成一片花瓣,顺着水流飘向远方……
活下去。
他突然听见了这样的声音。
惊雷再次响起。他突然清醒,发现自己身处湍急的河流之中,衣服已经湿透,浑身冰冷。他发现母亲正在河的对岸,还是那样的安详与慈爱地望着自己。他知道自己仍在梦中,但他需要快点醒来。继续还在旅途,他要拾起那把落下的短刀……于是他转过了身。他觉得母亲在身后目送自己,而他没有回头。
***
恩斯特醒来时,看到了一个纯白的,就像是梦中的母亲一样的身影——他很快意识到那是圣母像。而当他眨眨眼,视线更加清晰的时候,他看到了另一个黑色的身影来到自己的身边,手中的银枪反射出明亮的光泽。
他去看那光线的来源,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破旧的教堂。雨已经停了,阳光从屋顶的缝隙间落下,正好照在费恩的身侧。
“你醒了。”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时间没有弄清哪些是梦境,而哪些是真实的。他想要说话,却发现自己的喉咙发痛,难以发出声音。他意识到自己应该是发烧了,而他脸上的雨和血、还有汗水都已经被擦干,身上则盖着费恩黑色的披风。他支起身子坐了起来。尽管脑子还有点昏昏沉沉,但睡过一觉令他感觉好了许多。
“还需要休息吗?”费恩问着。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恩斯特觉得她的声音比以往要轻柔。
恩斯特摇摇头,努力地发出声音:“我……我睡了多久?”
“大概几个小时。”
他看向阳光,心想原来还在白天。这天内发生的一切让他觉得像经历了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趁着天还亮着,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恩斯特把斗篷递给了费恩。
费恩点了点头。
两个人稍作整理,便打算离开教堂。动身之前,他特地确认了一下短刀还在腰间。
面目可憎的森林瞬间变得美好而友善——雨后的新鲜空气里混合着泥土的特有的清香,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洒在道路和他们的身上,残留的水珠被照射得像宝石一样闪亮。在太阳的指引下,辨别方向变得非常容易。他们很快走出了森林。
夕阳将天空染成血色,而远处云层的下方,猎人工会清晰可见。
——————————————————
和上一篇不一样,这篇比较对应漫画的内容!
因为之前讨论了时间线,出发时是在夏季,正好和现在季节差不多,写了一篇有季节感的故事
部分意象和氛围参考了宇多田光的《真夏の通り雨》
https://music.163.com/#/song?id=430208484








那时恩斯特才刚回到教会不久,还是春天。阿尔文见恩斯特身体孱弱,缺乏自保的方式,而圣痕可以证明他的身份,保佑他外出时不被恶徒缠上,便建议他去接受烙印。虽然害怕疼痛,但恩斯特仍然鼓起勇气答应了。
烙印圣痕听起来像一个盛大的仪式,而与之相反,实际操作却在一个小房间里。这个房间窗户很小,朝向不佳,采光较差,黑暗的室内几乎只能靠炉火照亮,火焰烧得旺盛,空气令人感到燥热。恩斯特来到这个房间的一路上都充满了不安,而进来时看到烙印的人正是阿尔文,他稍稍有些放下心来。
“真巧,居然是你。快坐下吧。”阿尔文的语气还是那么亲切,甚至带着一种轻快。恩斯特坐在对面,仰头看着阿尔文。阿尔文挑选着烙铁的大小和形状,似乎在寻找合适的。恩斯特看着那些烙铁,想象着马上它们将要变得滚烫并且贴在自己的皮肤上,便害怕得直咽口水。挑选一番后,阿尔文转向恩斯特,他的白色长袍和面容被炉火照成红色:“让我看看,你的烙印在哪里更合适。”他伸出自己印着圣痕的左手,握起恩斯特微微颤抖着的右手,“你的手还得用来写字,万一烙伤了就不好了。”他松开手,去抬起恩斯特的下巴,审视了一番,“你的脸和头发都太白,印在额头上太突兀了。”他的手往下滑,落在了他的衣领的第一颗扣子处,“不如在这里,当你需要展示时敞开,平时依然藏在领子里,你还是和原来一样。”
脖子?恩斯特惊讶地想道。颈部那层薄薄的外皮真的可以承受烙铁的灼烧吗?不会出事吗?但他摸了摸自己的手背,想着如果手背这么薄一层皮都可以的话,脖子受到更多的保护,肯定没事的。恩斯特点点头,解开了衣领的几颗扣子,顺从地把需要烙印的地方露了出来。
阿尔文的指尖在恩斯特颈部划了一圈,好像在比划位置。恩斯特突然意识到,如果脖子上的不是指尖而是刀尖,又或者对面是吸血鬼或野兽,这都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场面。
“你抖得厉害,在紧张吗?”阿尔文收回手,“这样下去可不好烙印,会歪掉的。”
恩斯特点点头,却止不住身体的颤抖。
“那我们先来聊聊天。”阿尔文换了一个放松的姿态,将双手放在搭起的膝盖上,“最近过得如何?回到圣伯拉后一切还习惯吗?《圣女传》的书写顺利吗?”
“……我很好。”
“那听起来书写得不是很顺利。有什么问题吗?能够帮到你的我尽量做到,毕竟书写是件困难的伟业。”
“谢谢您,神父大人。我最近在阅读其他圣徒的传记作为参考,但是我总有些在意的地方。”
“哦?是哪里在意呢?”
“我看书中对神的描述,和教会的信仰有些差异。”
阿尔文直起身子,他的面庞遁入更深的黑暗里,只有头发和长袍的轮廓被照亮。“那大概是别的信仰?就算同一个信仰,也是有很多流派的,他们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形成。”恩斯特只能看到他的嘴唇在动,已经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明白,可是我找不到更多的痕迹……其他的信仰,神学书籍,历史书都消失了。我在海外读过一点点,但我不知道到在那些书消失之间发生了什么。我很迷茫,因为我不知道以什么为依托去书写圣女的故事。”
“依托?你不需要任何依托,便可以书写她们。”
“可我的迷茫仍未消失,神父大人。她们到底在为了什么样的信念,为了什么神而献身?我该怎么描写她们身上的神性与高洁?神到底告诉了她们什么,让她们愿意奔赴神的身边?”
“如果圣母像此刻流下眼泪,一定是为了你的发言而哭泣。”阿尔文回答道,就好像是打断了恩斯特的话一般接着说,“许诺你加入教会,是信任你。而你此刻的疑问,似乎有些多余。”
“难道不可以有疑问吗?”
“你已经是教会的神父了,除了相信神,还能有别的思想吗?因为这里只有我们,我才能告诉你这些。在其他人面前,这都是不可以说出口的话。”
“我……”
“嘘,”阿尔文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如果有怀疑,在最开始就要全部丢掉,孩子。更别说这一刻了。”阿尔文举起一块烙铁,伸进了炉中加热,“躺下吧。”
恩斯特不再说话,乖乖地躺在了长椅上。他看着天花板被炉火映照出一片红色,明暗随着火焰的跳动而变化。
阿尔文起身走到了恩斯特的附近,但恩斯特看不见他,只看得见烧红的烙铁举到了自己的脸边。阿尔文的声音还是保持着一如往常的语调,从一侧幽然响起:“我给予你书写的权力,可有些事你不该问,也不能说出口。”烙铁的热气不断靠近,最终移动到了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但即便这样他也闭上了眼睛。很快,当烙铁触碰到皮肤的那一瞬间,钻心的剧痛席卷了意识的全部,让他险些晕过去。他压紧咬着牙,绷紧了身体,双手抓住了压在身下的外套,很快身上的汗就浸湿了衣服。明明闭着眼睛,他却感受到眼前出现一片鲜艳的红色,还伴随着一阵阵炫目的光。但奇怪的是,人居然能够忍受这种疼痛,或者说大脑居然能麻痹这种痛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便觉得没有那么痛了,他认为是以前的病痛让自己习惯了痛的感觉。他听见了嘶嘶的声音,还闻到了皮肤烧焦的气味。因为闭着眼,这些感觉格外清晰。
突然,压在自己颈部的烙铁离开了,伤口暴露在空气中,带来所有普通伤口都会有的疼痛。恩斯特睁开眼,眼前的天花板却有些模糊。他意识到自己眼眶里都是泪水,而身体也因为突如而来的刺激而难以动弹。他微微转过头,望向阿尔文。他想叫他,却因为喉咙的疼痛发不出任何一丝声音。
“就算你这么望着我,也还是得继续。”阿尔文伸出手,把恩斯特的脸推到合适的角度,露出侧边的脖子,“这一个可不够呢。”当恩斯特的呼吸和思绪都还没得到平复,重新烧好的烙铁再次贴到了他的颈部,发出滋的一声。他感到自己的颈动脉被压迫,从而开始疯狂地搏动。第一个烙印的疼痛还未消减,紧接着第二个烙印叠加上来,带来更加剧烈的疼痛。恩斯特痛得想要叫喊,但叫不出声音,只能从喉咙底挤出一些呜咽。泪水不断地从他的眼眶中涌出,胡乱地流淌到整张脸上。紧接着是第三个,第四个……他几乎已经失去了意识,无法思考也无法感受,抓着外套的手也失去力气,只能祈祷这一切快结束,快结束。
终于,第五个烙印烙上之后,恩斯特听到了烙铁浸到水里冷却的声音。他庆幸终于结束了,可是此刻的呼吸已经有些困难,长舒一口气都做不到。滚烫的烙铁和灼烧的疼痛离开皮肤后,他浑身都被冰冷汗浸湿,身体里几乎不剩一点能量。轻微的焦味弥散在鼻腔中,挥之不去。
“这些圣痕意味着你将成为教会的喉舌,这是你的身份。你要牢记此刻,牢记你是谁,牢记你为谁说话。它可以保护你,你也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来,看看圣痕怎么样?我很满意。”
恩斯特现在虚弱得根本无法自己起身,但阿尔文讲的每一句话他都听得真切。他分不清这是残忍的训诫,还是温柔的提醒。阿尔文将他扶起来,面容依旧保持着慈爱,还替他擦去了泪水,仿佛刚做了一件善事。在这昏暗和疼痛的包裹下,恩斯特感到阿尔文有一种震慑人心的美,又或者是比美更高的某种感受。阿尔文把镜子举到他的面前:他看见了脖子上环绕的圣痕,还带着烫伤的鲜红色。他原本以为,没有人以及任何方法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而当他看到自己颈部的圣痕时,他在心中默念,我是教会的喉舌。
他缓过来之后,才离开那个昏暗的房间。他去修女那儿领了药,修女看着他的圣痕微笑。他心想,我现在是教会的一员了,这里就是我的归宿。回到房间后,别说写作或者记录,他无法思考任何事情,只想躺下睡去,而伤口又在空气中生疼。就在这剧烈的疼痛和疲惫的折磨下,他开始做一些半梦半醒的梦,一直到他真正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他起身,点燃了房间里的煤油灯,就着水吃了片药。他从抽屉中找到了一面很少使用的小镜子,借着灯光去照。那些烙下的地方已经变成了深色,而四周仍是一圈鲜红色。他强忍着没有右手去碰,把镜子放回了桌上。一夜休息,让疼痛淡化了不少,他的思想也恢复了正常。他的心中涌起一股悲凉——自己竟然只能用这种方式找到归属感,认清自己是谁。他本可以拒绝,但一切已经发生了。我的喉咙,我的身体,我的思想,都要归属于教会了吗?就像其他那些被烙印的修女神父、猎人,还有会被献祭的圣女一样,我终于进入了这一环?他一时半会想不清,也不愿去多想。
之后的几天,他一直高烧不退。他以为自己对神产生怀疑,神也拒绝了自己,所以服用的药也不起作用了。他又开始以为自己会死。高烧退了,他自如地从床上醒来,走到自己的书桌前,拿起了镜子。镜子里的人脸色仍有些苍白,但已经不是病人的神色。脖子上的印记处,新的血肉正在生长,颜色比四周要深得多,就像有些创口带来的无法褪去的伤痕。
这就是圣痕。
——————————————————
本来想写在第一章正文里但是太怪了还是单独发好了
感谢阿尔文老父亲的亲切出演和费老师的点拨!
圣痕的设定之后会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