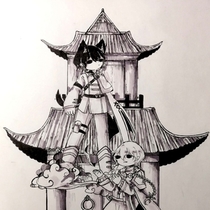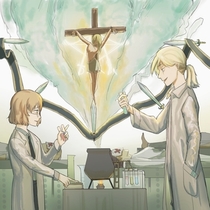『推荐配合音乐The Last String-Jacoo食用』
今天的大海,比以往要热闹不少。船只停泊得比以往哪一日都密集规整,高高挂起的旗帜在蓝天之下鲜明耀眼,举着香槟的镇民群众和带着徽章归来的船员们正在欢庆。声音远远地传过来,有兴之所至的模模糊糊的闲聊,还有高歌和大笑,让一贯怕吵怕热怕人多的人都不自觉远望出神。
真是难得,有这么快活的日子。
雪维利尔抿了一口小酒,侧着靠在墙壁形成的阴影里,半是惬意半是糊涂地眯了眯眼睛。
今天是属于海员们的节日。船只都靠岸开放展览了,甲板上的高脚杯和阳光一样温热透亮,沙滩上也满是参观庆祝的人。雪维利尔兴致忽起来看看,又懒得下去玩,就在最近处的酒吧高台上找个阴凉处坐下。
实话说她酒量不太好。今天她不知怎么的很有兴致和冲动,就点了酒;只是没想到,这才一杯就有些懒困。
喝吧,最多不过回家贪睡一觉。雪维利尔不在乎地想着,又抿了一口。酒液润上她的双唇,给平时的淡色带来轻红湿软的水亮,连着双颊也有些泛潮。她渐渐觉得身上发热,就拨开额角的碎发,闭上眼睛感受恰好吹来的风。
穆萨也是来游览的。相比起大街上,她更喜欢大海——尽管现在的大海也很吵。
她喜欢看着小孩子们举着玩具飞奔过细沙的样子,喜欢阳光温热地抚摸她的肌肤的触感,还有似乎随着节日一起欢快起来的海浪声。不论如何,她是喜欢节日的氛围的。
她过来得早,在沙滩上陪着小朋友们玩了一会,被折腾得身心俱乏,就到最近一座高塔上来寻清净。谁想才一上来,就看到雪维利尔这幅独自倚倒醉醺醺的景象。
好好的节日,她怎么一个人?
穆萨看得好笑,径直走过去坐在她对面,悄悄地也不出声。雪维利尔感觉有人来了,睁开眼睛,看见在风中微微飘扬的灰发和那双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失神的眼睛。
她愣了一下。“穆萨?你也来了。”
穆萨点头,一边把外套脱掉搭在椅子上。“嗯,我上来休息。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
雪维利尔举了举高脚杯。“不好吗?”
“你很少喝酒的。”
说得不错。雪维利尔一向觉得,酒精使人精神恍惚失去自控能力,虽然一时快乐,但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今天是节日,喝一点也不妨事。尤其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有风阳光和大海,多自在……
……哦,一个人。
雪维利尔终于觉出哪里不对了。看看底下金黄的沙滩,节日哪有一个人过的?
那就再喝一口吧。
雪维利尔仰脖把杯中红酒一饮而尽,杯底残余的液体仍是优雅摇曳的酒红,看得穆萨有些茫然。
今天的雪维利尔……真是说不出来的特别啊。
她这么想着,眼疾手快一把夺过雪维利尔才要伸手去拿的红酒瓶:“看你这样子……你今天喝了多少?”
“不多,也就两三杯……”
“……”
两三杯就能喝醉了……?穆萨看向手里红酒,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雪维利尔半点没觉出穆萨的惊讶,仍道:“你要来点吗?”
“……不用了。”否则待会就要出现两个迷迷糊糊的醉鬼了。
雪维利尔闻言放下杯子,探究地看向穆萨。穆萨对上她略显涣散的眼神,头痛地叹了口气。“要不,去沙滩散步醒醒酒?总在这里待着,会不会有点闷?”
她本以为雪维利尔会推拒一下懒得走动,但出乎她的意料,雪维利尔答应得相当爽快。她们收拾好东西走下酒吧高台,细沙遥遥返出的白亮不像在高处望见的那样明快,反而有点刺眼。
雪维利尔下意识望向海的方向,那里有过于热情的阳光。她不适应地皱起眉,将披肩展开披在肩头,遮去大部分光线,才垂着眼慢慢地往前走。
这时穆萨才发现,雪维利尔的步子很稳,大约真的只是小醉;而自己这个“下来走走”的提议,才有点荒诞。沙滩不比高台凉爽轻快,何况自己刚刚才从这里上去。
……不,不对。她希望雪维利尔能下来走走,这是真的,一点也不荒诞。看到她独自在远离众人的地方小憩的时候她就是这样想的。
于是她试探地问道:“你想去海边看看吗?”
雪维利尔一时没有回答。她看见停泊的大船,那上面仍有走下来的观览客与船员;浪花在船下,涌上来又退回去,永不止息地留下易逝的白色泡沫和沙子间深色的湿漉痕迹。
她现在有点大脑放空。好像想去做点什么,又不知道能做什么,模模糊糊的。
她费力地想了想,终于对穆萨道:“都听你的。”
真是难得。穆萨越想越觉得此时的雪维利尔可爱至极,像是懵懵懂懂的小孩子。她几乎是安慰地柔声道:“好,那就去海边。”
远望大海其实是她们都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大海很蓝,很深,很静,很遥远又近在眼前,望着它的时候有无限的遐想。
雪维利尔坐在沙滩上,盯着柔软的细沙,忽然问道:“你有的时候,会来这里看海,对不对?”
“嗯……嗯?”
“有很多次……我在这里见过你。”雪维利尔像是在喃喃自语,“但我没有告诉你,也没有去找你。”
她不等穆萨追问,就继续道:“因为我想,你那时候可能想一个人,独处,想一点只有自己知道的事情。”
穆萨无言以对。她的确时常会来,也的确有许多不愿被撞破的心事。可她没有想到,已经有一个人在她背后悄无声息地注视了这么久。
有很多次……她在注视着自己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呢?
穆萨忽然有点茫然,甚至悚然。她低下头,没有说话。
雪维利尔几乎没有注意到她的反应,仍自顾自地问道:“穆萨,你看海,是什么感觉?”
穆萨知道她在问什么。心里想着什么,就会感觉到什么——可她自己也说不清楚。里政府的战争、火山场的异动、受此牵连的那么多常人,还有雪维利尔……她已经数不清楚有多少次,雪维利尔突兀地出现在她的思绪里。她总给穆萨一种微妙的错觉,好像有哪里错了。
何况更多时候,她只是在情绪里对着水纹发呆。如果连面对大海都不能让心静一些,那生活里还剩下什么呢?
于是穆萨绕开了雪维利尔有意无意想问的,轻声答道:“没有什么感觉,我看不太清。大海有点像一个蓝色的色块……但还是很好看。”
雪维利尔不知道这句“看不太清”指的是她视力不好,还是其他那些事。她只知道穆萨很快就能看清了,从后者的意义而言。
她犹豫了一会,道:“我也很喜欢看海。如果还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穆萨眨了眨眼睛。“我们现在就在一起看海啊。”
雪维利尔没有说话。
浪声就充斥了她们身周,让气氛不至于凝固,也不至于被其他声音打扰。两种不同的心事在富有韵律的海浪之下潜涌。
一声——又一声。笃定的循环,永远也不会停下,从这个世界对她们二人产生意义之始至现在,预示着泡沫的破裂。
雪维利尔忽然开了口。“穆萨。”
“嗯?”
“我想说一件事。”
“……嗯。”
“我很对不起你。”
“嗯……为什么?”
“因为……”
雪维利尔停顿了很久,似乎纠结于应该如何解释,又像是因为不敢面对而止步不前。但她终于道:“……我并不是一个坦诚的人。有些事我没有告诉你,或者说……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但你并不知道我。”
她深吸了一口气。“我们是相对的。”
一只海鸥划过天空,弧线不留痕迹地画出孤单的弧线,又倏地消失在视野尽头。穆萨忽然意识到这些话都是极其严肃的、认真的、也许不能明言却也再明白不过的。
一根隐形的线悄然串起了她刻意忽视过的一切,曾经的怀疑被照得无所遁形。她的心猛地颤抖起来,却把刚刚浮起的念头重新压下去。
相对的……对立的……敌对的。她和什么人才是敌对的?这不可能!一定是……
是的,一定是她喝醉了,所以说了些胡话。穆萨强硬地告诉自己。也许她不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呢?
可是……她从来是一个那么清醒的人啊。她怎么会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告诉自己?
穆萨的思绪由混乱变得空白。如果眼前的一切难以理解或接受,她宁可自欺欺人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似乎不去想就不会发生。
就当是做了一场噩梦那样,她只是不慎多想了。
沉默变得无比恐怖。人群欢乐的笑闹声因遥远和模糊而显得不真切,而沉默在这一瞬间永恒。耀眼的阳光在遥远的地方连成夺目的一片,却在她们身后留下阴影。
也许这样就过了很久很久。
穆萨的嘴唇动了动,终究什么也没说出来。她几乎是逃避式地踉跄着站起身,不敢看雪维利尔的眼睛。“……对不起,我想起有点急事,要先回家了。你……祝你玩得开心。”
雪维利尔只能点头,站起身,一言不发看着她匆匆远去,背影被过强的阳光照的模糊不清。
她恍惚间回到了无数个她们之间告别的时刻,也是这样,只不过她们会微笑着向彼此道别,说下次再见。
她忽然惊觉,好像自己总是在目送她离开。那头银灰色发已经刻在她脑海里,她描绘得出阴天、晴天、微风拂过、雨滴落下时发丝轻轻晃动的样子,知道它远去时有多么美多么温柔明亮。
然而这一次是她亲手送她、推她、强迫她离开的。
这个念头掠过的瞬间雪维利尔几乎不能呼吸。她不敢再看她远去的瘦小的背影,重新回身望向大海。欢庆的旗帜竟然如此扎眼,在耳中放大的他人的玩闹声让她忍不住全身战栗。
她没有醉,从今天第一眼看到穆萨开始她就完全醒了,醒得极其苦涩。
这是她近几日反反复复辗转难安的心事——快要开战了。她装作一个正常人,已经藏了很多年,过了很久属于自己的日子,如今终究不能再藏下去。很快她就会投入这场战争,从世俗的世界消失……
……再以敌人的身份与穆萨相见。
难以想象那会是什么样子。她应该会痛恨自己吧?
所以雪维利尔说了那些话。以这两杯酒作为坦诚的借口,暗示穆萨自己并不是她一贯认识的那个人,总好过在不久的将来,粗暴地告诉她什么叫做势不两立。
可她除了隐喻这段可笑的谎言,给彼此一个分道扬镳的铺垫,其余什么也做不了。接下来的一切……失望也好、决裂也罢,那都是不容她更多加思考的事情。
因为她很清楚地知道,她骗谁都可以,唯独不能骗穆萨;她对谁坦诚都可以,唯独也不能对穆萨。这从根本上是无解的。
雪维利尔疲惫地闭上眼睛。黑暗在她眼前透出灼烧酸涩的红光,刺得她想要流泪。
随它去吧。
End.
【一个很重要的注解】
关于为什么雪维利尔会向穆萨透露两人敌对,我是这么想的:
首先,她们两个是可以超越友情的朋友。雪维利尔不愿意骗穆萨,但是需要通过欺骗来服务组织的时候,她毫不手软。
然而现在雪维利尔要上战场,魔法师身份要被里政府查知,穆萨不可能不知道。
雪维利尔不愿意彻彻底底把穆萨骗了,让这份友谊因此变质,所以她主动坦诚了自己的身份,给彼此一个缓冲的余地。
但是她又不敢直接告诉穆萨,自己是个魔法师,她怕会她们两个都会崩溃……所以她只能简短地暗示。
可能这也是雪维利尔在这件事上能做到的唯一的坦诚吧:(

年轻的医师在下午两点坐在烈日下,喷泉溅起的水花在日光下如同钻石那样璀璨。他棕色的双眼像是一对琥珀那样闪闪发亮,又由于强光而微微眯起,再被圆框眼镜一挡,徒留一张平平无奇的、只能算是清秀的脸。周围人来人往,医师(他穿着一件白大褂呢)的嘴唇贴在一只冰激凌球上,另一只手举着另一支甜筒,让它维持在身体的另一侧——它在热风奔流中融化,如同喷发的火山那样不可阻拦。
艾希礼看到这一幕时,乳白色的香草冰激凌“岩浆”已经顺着那人的手指流得到处都是,占据了每一个凹陷的指缝,并且一路从手腕往他的袖子里划。他无奈地上前去,把医师的袖子往上提了提,同时不着声色地把那支化得一塌糊涂的甜筒接过来,微弱的蓝光在强烈的阳光下几不可见地一闪而过:“抱歉我来晚了,西玛,但是你……”他的目光转而投向西玛惨不忍睹的左手。
西玛唤了一声他的名字,算是招呼,然后把甜筒的尾巴衔在嘴里,右手慢悠悠地从口袋里掏出块手帕,开始清理自己左手上甜蜜蜜的奶油。这个过程中,他一直近乎是狐疑地打量着艾希礼,从他站着,向自己解释来晚的原因,到坐到自己身边,谈起解咒的事情。
“你还好吗?”西玛没头没尾地蹦出这么一句。他的双眼直勾勾地定在艾希礼的胸部。
“你知道了?”
西玛轻哼了一声:“那只孔雀就差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把观星社的制冷机给揍啦。”他故意地现出一些对林的轻贬来,开着玩笑,好让气氛活络些——事实上,林遭受的打击绝对不比观星社魔法师家常便饭的受伤要小。他小心翼翼地捏造了一点情绪,不至于幸灾乐祸,但或许能哄骗面前的魔法师——“观星社的制冷机”。
艾希礼扭动了一下身体,偏开视线:“放心,泉堂的医疗可不差。”
“对于人体结构他们肯定没有‘我们’熟识。”西玛俏皮地眨了眨眼,“听我的,让我看看。”
艾希礼无力阻止医师的执拗。事实上,他并不觉得这是个需要极力反对的建议。西玛站在他的身前,那件白袍的下摆一直垂到膝盖以下,当行动起来时,它就在西玛的光裸的小腿处轻微地晃动,如同海浪轻柔地冲刷而过。艾希礼微微垂着头咬着冰激凌,看着地上西玛和他的袍子的影子左右摇晃,像是一只鸟儿在炫耀自己美丽的飞羽,余光中有他的手指——这双手正小心翼翼地检查着艾希礼的肋骨。它们白皙、修长,因为残留的糖分而有些黏腻——它们是否也是甜的呢?有香草和奶油的味道?
或许是太无聊了,他对这种毫无意义的事产生兴趣。艾希礼被自己吓了一跳,但很快便平复下来。他决意不再看西玛,而去观察熙熙攘攘的人群。
里政府医疗部的职员和观星社的魔法师,这样的组合还真是……有趣。在艾希礼几不可见的一丝哂笑中,这唐突的荒唐感便悄悄地溜走。
断的是这两根吗?最好做个胸带固定……用魔法做了吗?哇,那你们那的治疗师还不错欸。不过你不该来见我的,受伤了就应该好好养着。我?哈,我那事又不着急,你爽一次约又怎样?大不了,我吃两个甜筒呗。
笨蛋,你巧克力粘嘴边了。右边。
是吗?医师的舌从口中滑了出来,试探着舔舐着嘴角。他白色的长袍下只穿了一件看起来廉价且俗气的格子衬衫,最上面的那枚“风纪扣”没有系上,有些歪倒得领子下若隐若现地浮出有些濡湿的皮肤来——艾希礼用目光沿着扣子拆开那薄薄的衣衫,下头有一块丑陋的疤痕。
“艾希礼,你不热吗?”
艾希礼正出神,西玛的声音让他在这个炎热的、教人发困的下午清醒了一些——像是一颗薄荷硬糖那样清爽。医师已经完成了他的检查,正在越俎代庖地审视他的魔法师朋友的衣物——长袖长裤,只是脱掉了背心和大衣。银白色的短发下沾染着汗渍的额头,冰蓝色的眸子,如同棱角分明的蓝宝石那样澄澈,带着少年所独有的几分锐利的光。
“有魔法。”
西玛听到这言简意赅的解释后笑了起来:“走吧,这里太热,找个方便的地方坐坐?”
艾希礼对饮食并无热衷,但他还是说,有一家店有风扇,有甜品,还有睡在柜台上的猫咪。同事推荐的,离这里不远,去那里吧?
于是这对奇妙的组合从喷泉旁站了起来。当他们也开始移动时,就像是融入了尘埃中的两点微粒,由于随波逐流而毫不起眼。但西玛享受这种感觉,这意味着没有人会注意他们,而他却占有着艾希礼的视线。他们踩过被无数人踩过的地砖,呼吸着无数人共享的空气。魔法师的手,大概由于修习有关冰的水魔法,温度较常人稍低一些,像是一杯冰果茶那样让人舒服。西玛在艾希礼的左手边,稍稍落后一些,属于双方的两只手就如同风吹树叶,偶然间发生碰擦,又像是互相撞上后受惊的鱼儿般跳开了。
后来他们两个坐在甜品店靠窗的一桌,吃一个芒果味的观星派(夏季特供!)。西玛把自己塞在角落里,小声地和艾希礼交谈着,尽管店里的其他人根本对这些“年轻人的忧愁”毫无兴趣。西玛的嘴角还沾着晶莹剔透的橙色果酱,如同一只饱食的猫那样餍足。
西玛的吃相并不好看,这样的行动放在一只猫上或许还会让人觉得可爱——艾希礼这样评价道。他不太喜欢这样过于绵软的东西,甜蜜得就像娇气的、爱纠缠的女孩,顺着舌头嗲着声音爬上来。但西玛不一样。
他身上总有一种特殊的气味,甜美和冷清是同时出现的,而且互相相处的极为融洽——艾希礼习惯之后仔细揣摩,才分辨出:那是巧克力和酒精的混合气味,但少了一般巧克力的苦涩和酒精的醇香,以至于甜蜜下,有一点点微微的刺鼻。
意外的,不错的味道。
“还做噩梦吗?”艾希礼问。
“实话讲,更有些糟糕了,温彻斯特医生。”西玛调笑道,眸子中闪着光。
“我允许过你称呼我为艾希礼……你笑什么?”
“我想到我们初见面的时候。”西玛用手帕堵住嘴,但弯弯的眼睛暴露了他的手帕下有一张咧着笑意的嘴,“你对我说:‘那么,我允许你称呼我的名字。’。那时你甚至还提着剑!”他压低了声音,以模仿当时艾希礼严肃且佯装果决凶恶的模样。
艾希礼笑了笑。
在这场从交易开始起步的友谊里,艾希礼扮演了医生的角色,而西玛才是有求于人的病人。虽说一开始是艾希礼找上的这位容易落单的里政府职员。
“我也从来没想过会这么顺利,”艾希礼吊起眉毛,把饮料杯里的冰块含在嘴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咀嚼声,“你是我见过的表现得最淡定——甚至可以说是冷淡的。”
“毕竟我可没兴趣用金夸特尼来计算生命价值。我要的东西,是你所独有的——我也一样。而我们互相都抓着把柄。”西玛笑嘻嘻地说道,“而且,你不用担心会有别人用钱买通我。”
“如果麻烦不是接踵而至。”艾希礼说道,他稍稍蹙了一下眉毛,好像还是有些担忧的模样,“那么,回归正题,这次想起来多少?”
“差不多了。”西玛小声地说道,不知是因为周围的人群,还是本身对此事的忌惮,他的声音渐渐地低了下去,“还有一些细节……但是差不多了。能确定,那姑娘是我的堂妹,她是魔法师。”
艾希礼没说话。冰块被咬得更响了,它们焦躁地在他口中挤来挤去。
“是她……嗯?”他用下巴指了指西玛的胸口。
“恐怕是这样。我梦到她对我举起了魔杖……”西玛平静地说道,逐渐低下去的尾音却颤抖着被收回。他垂下眼,把甜品用叉子削下一块,塞进嘴里,咀嚼。
他在发抖。艾希礼从他翕动着的嘴唇上看出,尽管西玛用吃东西竭力掩盖这一点。里政府的医师并不喜欢在艾希礼面前暴露出一星半点的脆弱,尽管他不由自主,会。对于陌生人,西玛冷淡谦恭,表现得不温不火;而对于熟人,他却更不敢展现出自己的脆弱和恐惧,免得人对他改观。
总而言之,所有人都喜欢看光鲜亮丽的苹果,而非腐败的芯子。
艾希礼脑内蹦出这句西玛曾经说过的话。他有些懂了,但依旧不着声色。或许西玛对自己的想法被察觉都带着本能的戒备。
然而很快这个假设就被打破,西玛的脸抬了起来,像是小鹿一般湿漉漉的眼睛,不易碎,里面封存着那些被压抑的情绪,就像蜡烛的烛芯那样,细细小小一根,平时也看不见,可蜡烛化为乌有时确实从它开始。西玛的眼睛里藏着很多复杂的情绪,但艾希礼几乎一眼就能明白:西玛愿意把信任交付给他。
赌一把吧,从伤疤开始,无论是痛苦的过去还是煎熬的现在,都披露给艾希礼。就算还是有所隐瞒,但那的确已经是他最大的努力,就像蜗牛的壳破了一个小小的洞,已经是它的极限。
而艾希礼回以一个微笑,伸出手,握住他面前的饮料。他放开时,上面有水珠,和他的一个手印。西玛双手环住杯子,低头,二人静默无语。
什么时候,一起去看一回海吧?在这个炎炎夏日。
举起饮料杯,不知道是谁提出的邀约,不过既然另一位不假思索地同意了,那么是谁做出的邀请,大概也不重要了。

主线
“不错的剑,不错的剑术。你是我在这碰到的第一个把西洋剑和魔法结合的这么好的人。不过,我相信不会是最后一个。”双刀高速连续地击打对方手中的长剑,林在最后一击将艾希礼打退之后,大后跳收刀,“你对剑上魔法的控制,很准确。低温确实是金属兵器的一大克星,不过,相比金属对力的传导,温度变化就变得不值一提了。”
林的左手抚摸着左腰长刀的刀柄,凝视着人身上大大小小的刮擦痕迹:“如何?你的手,还能不能握得住你的剑?面对我的双刀,长剑术里的一部分格挡就完全无效。要是我不珍惜我的橙红,你已经命丧当场。“
“那可不一定。随着时间的推移,空气中的温度也会逐渐下降。再过一会,就超出了普通人类的忍受范围了。到时候,你的汗水也会结冰,手指会冻掉,而我将是活下来的那一个。”艾希礼仍然以犁位起势握着长剑,剑尖微不可查地微微颤抖着。显然,长时间高强度的击打,让艾希礼的腕部肌肉陷入了疲劳。
“到此为止了。”林叹了一口气,捡起两根钢管,“那就看看是你这架空调制冷快还是我拆空调比较快!”
话音还在巷子之中回响,林已经双手握着钢管冲向了艾希礼。在艾希礼的瞳孔之中映照出的林的动作完全违反他所学习过的一切西洋剑知识。只一个呼吸,林就跨越了半条小巷,左手的钢管由外向内横扫。艾希礼扭转长剑,以强剑身与钢管相撞,震开林的横扫,同时以牛位起势收势,换交击防御林右手从上而下的竖劈,同时以交替步保持重心。
“这个场景,你不觉得眼熟吗?”在持续的进攻中,林突然发问。“是呢。当时你看到我拿着双刀上来就砍,就是这个套路。”林的话语让双方都在脑中快速回忆了一遍当时遭遇战的情景:艾希礼为掩护被林追击的重要情报传递者,只身阻挡了林的追击。
——时间回到下午两点
“给我停住!”林追着提着一个布袋的年轻人进了一条巷子。巷子另外一端,艾希礼正在街上走。那个年轻人见到艾希礼,如同见到救星一般大喊:“救我!”艾希礼转头,看见一个穿里政府制服的人正在追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疯狂张大手掌,给艾希礼看观星社的标志。
艾希礼拔剑与那人擦身而过,长剑上的低温在空气中带起了白雾。林的双刀和艾希礼甫一碰撞就立刻弹开后跳:“你的剑,怎么回事?冷气?有趣。那么,人我是追不上了,就让我看看你的命值不值这个情报吧。”林摆开架势,左手红刃向前斜护在胸前,右手橙竖握,刀刃正对艾希礼身体轴线。
艾希礼侧跃交替步错开中央大空地,左侧身体掩藏在箱子之后,黑剑以牛位起势正对林的喉咙。海风从林的身后吹来,带着咸味的风使艾希礼微微的眯了眯眼。
如同猎豹的扑击一般,林的上身略略前倾,略往艾希礼右手边的墙一侧冲去。但并未如图艾希礼所预料的,林并没有用左脚承重转身,而是以右脚为支点,左脚在墙上着力转向,用左手的红劈下。
面对西洋剑中的经典攻击手段,艾希礼扭转手腕,以怒击撞上林左手的红,以骗位收势,交替步换交击挡住林右手的劈击。“剑使的不错,你的能力也很新奇,就让我看看你还有什么能耐!”
刀剑相碰,小巷中叮当作响。艾希礼始终以稳定的格挡防御林如骤雨般的攻击。正当林的右手完成了一次劈击时,艾希礼陡然发力,以防御林的动作收高位势,自上而下来了一记劈击。
林猛的一个后仰,左手红快速拉回偏转艾希礼的劈击。尽管如此,林右侧鬓角仍然被艾希礼的黑剑削去一截,超低温使林右脸的汗水瞬间冰冻。再看林左手的红,已经凝结了一层冰霜。“真是惊险。要是这一剑砍在我身上,必定会拉出漂亮的一条血色冰晶吧。”在快速后退中,林将双刀置于阳光之下,让红的刀刃慢慢恢复金属的弹性。
艾希礼不说话,只是保持着犁位眯着眼睛打量着林。林也不在乎艾希礼是否回应,看着红上的冰霜慢慢消失,转动了一下左手的手腕,林慢慢朝艾希礼走去。
艾希礼不断以交替步与林绕圈,尽量与林保持开式站立。同时抬高黑剑,从犁位换到牛位。紧接着,艾希礼突然发力,重心微微向前,以左脚承重,发出了一次快速的穿刺。
林左脚横移,刚好躲开了艾希礼的剑尖。趁艾希礼重心并未收回,右手的橙横扫,在意料之中的被艾希礼以倒挂势弹开,紧接着,如同骤雨打落树林一般,高频的撞击声在巷子中响起。
——回到现在
林手握钢管,只用钢管的最前端与艾希礼黑剑相碰。相比起橙红,更轻的钢管加快了林的攻击速度。在如此高速的攻击之下,即使是艾希礼也有些招架不住。在某一次的击打之中,钢管的末端被黑剑打碎,飞射的碎片擦过了艾希礼的太阳穴。这时,阳光刚好穿过林的肩头,穿过房屋探出来的窗台,打在艾希礼的脸上,打在林的后背,打在橙红的刀柄和黑剑上。
出乎意料的袭击让艾希礼有一瞬的愣神,阳光使艾希礼下意识眯了眼,但很快艾希礼就回过神来,只是已经来不及了。这一瞬的愣神,标志了这次战斗的终结。林左手的钢管由内向外挥出,发出了清亮的响声,钢管从中部断裂,黑剑被大力向外弹开。丢掉左手的钢管,双手握住右手完好的钢管,猛的击打在了艾希礼的胸口之上。
在钢管击打血肉的闷响之下,还响起了艾希礼肋骨折断的声音。艾希礼的眼睛因为震惊和剧痛而猛的瞪大,与林的眼睛直接对上。那是一双没有感情流露的棕眼,如同死水一般。
受到林双手击打的大力,艾希礼向后撞在墙上,墙反弹的力再一次使艾希礼胸腔受损。“估计你的肋骨已经快要刺穿你的肺部了。只需要我轻轻的再一下,就是里政府的医疗组都救不回你。”林提着钢管,慢慢走到艾希礼的面前。
艾希礼只觉得胸口剧烈的疼痛,血液从喉咙中涌出,艾希礼啐出一口血,慢慢抬头,仰视着林。
背对着光源,面对着劲敌,林丝毫没有注意到巷口那一道红发穿着修女服的身影。由于逆光,伊莉丝没有看清林的脸,只看到了一个穿着里政府的制服拿着钢管的人正要再次攻击艾希礼。
拿着手上的法杖,伊莉丝不断地小声念咒,而杖尖却只喷射出小小的闪电:“快啊,快啊。该死的我为什么就不能把闪电魔法练习的更强!”伴随着伊莉丝救人的迫切心愿,法杖在几次小闪电之后,爆射出了大腿一般粗的雷电束。
雷电束顺着发展尖端的方向,直直打在了林的胸口上。林只觉得胸口像是被老爹的铁锤暴锤了一下,整个人就被打飞到巷子的另外一端,落在了一堆纸箱之中。
趁林被击飞,伊莉丝也顾不上看是谁,急忙跑到艾希礼身旁,把艾希礼以不会挤压到胸腔的姿势带走。
慢慢从箱子堆里爬出来,林仍然觉得胸口传来剧痛。扶着墙走到巷口,吐出一口血,林慢慢地回到了旗塔进行任务汇报。
——旗塔,里政府医疗组
“我不仅把情报放跑了,就连那个拦我的人,我也没逮住。林撑着桌子,擦了擦嘴角的血。“好了好了,你少说几句话,把制服脱了我给你诊断一下。”说话的是夏佐,“要是拖久了留下来什么后遗症,我们可是又损失一员啊。”
转身轻轻坐在床上,解开制服上衣,从上衣当中丁零当啷掉出几块碎片,刚好掉在林的腿上。林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也不管碎片边缘如何锋利,抓起碎片,看着上面熟悉的纹路,和署名,眼泪和手心滴出来的血滴滴答答的落下:“老爹……”看着碎片上映出的自己的脸,林又回想起了当时老爹送护心镜的情景,和现在一样,也是夜里,老爹从铁匠铺打烊回来给林带了这块护心镜。如今护心镜碎了,人也不在了。
沉浸在回忆当中,林握着护心镜的碎片,眼里的泪水打在护心镜上。有那么短短的一瞬间,看着护心镜里自己的棕眼,林以为是老爹从护心镜之中看出来。深吸一口气忍住泪水,将碎片放在一边的桌子上,林收回思绪,对着夏佐道:“我缓过来了,那就麻烦帮我检查一下吧。”
随后就是例行的检查和行动记录归档,在做完了这一切之后,林去了一趟老爹的墓地,在墓碑的一旁,将护心镜埋在土里:“老爹你曾经说护心镜能佑我平安,如今它确实救了我。也希望它碎裂之后能保佑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