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茨格姆企划三期
这次是更加完整的世界观
估计也是最终回啦!
目前是2052年的高科技时代!
参与者需私信审核人设
审核通过后加入企划
——
企划群:245552006



【远古生物】
死精灵
[近期苏醒][不可捕捉]
传说:关于死精灵的记载总是语焉不详。但几乎所有的资料中都表示,他们只需要一声叹息就会给人带来厄运的种族。
出没地点:全世界都多多少少能找到他们的踪影。主要出现在澳洲。
寿命:正常的死妖精能活300年,和魔法师的寿命相等。
介绍:
千年前沉眠的远古生物。
光看外表,死精灵除了负责呈现出不健康的灰白以外几乎和人类一模一样。(耳朵也不是尖耳朵……ummmm,只是耳尖有一点尖而已)
死精灵的感情非常淡薄,对世间总是保持冷漠的避世态度,只有同族人才会得到他们的亲近。而传言他们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也并非空穴来风——死精灵几乎不会喜欢上死精灵以外的种族,否则会给两人招来不幸。
计字2016,这么巧就发了吧【喂
-----------
3.
山下的城市还亮着,灯光汇聚成人工的银河,仿佛城市的血管。
如果那是血管,里面流淌的是汽油和电吧,男孩这么想过。
月亮升得很高了,夜鸟在空中清啼着飞过,不远处湖面闪着银光,冷而无情。
腕表指向一点整,旧历年已经过去了,似乎仍然有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传到他耳朵里,偶尔还能在黑漆漆的天幕下看到几朵孤零零的烟花。
苍白的烟火亮了亮然后灭掉,像是生命那样周而复始,大概是城市的脉搏。
“新年好,今年晓晓缺了一份红包啊。”他对手中的枪低语,声音里带着温和的笑意。
4.
天气很好,碧空如洗,层林尽染。
海晓风背后背着个厚厚的包,手上拄着徐若霖拿给他的那根登山杖,粗细挺顺手,只不过有点长,差不多能到他肩膀。徐若霖那根更长,已经超过了他身高一大截,看得海晓风浑身难受。
“你不就比我高几个公分,拿那么长一根棍子不嫌别扭?逼死强迫症了你。”他磨着牙,恨不能把那根登山杖直接掰成正常的长度。
“习惯就好,反正我已经习惯了。”徐若霖朝他摆了摆手,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意。
飞来越冬的鸟在枝头翘着尾巴搭巢,往山上走着走着树荫竟然绿了。已经往西边斜起来的太阳不怎么刺眼,从树枝间洒下来暖得懒洋洋的,海晓风莫名想到一部四十年前的老片子,里面有个白富美跟个救生员说笑话,“你就像下午三点钟的太阳,想做点什么,可是时间总是不够;而不做什么,就会觉得时间很漫长。”
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做,却觉得时间完全不够用,而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够用。
徐若霖在他前面走,背上扛着个容量能有二十升往上的巨型登山包,心情很好似的吹着有点跑调的小曲儿。
山不算高,只是层层叠叠的很深,他们走着走着就把太阳甩在了身后,头上密密匝匝的树林子把天空捂的严严实实,地上不知积了多少年的叶子被四只脚踩成大大小小的碎片,破裂的声音不绝于耳。
“你到底要去哪?太阳都要落山了。”海晓风有点累了,他搞不懂徐若霖到底想要去哪里,也搞不懂他哪来的这么大力气扛着这么个大包走了这么远。
“快了快了——我还会坑你?”徐若霖把包往肩膀上又扛了扛,口哨他是早不吹了,只不过还在哼着那个偶像组合的最新一首单曲。
海晓风想说你坑我坑得还少吗,忍了忍还是把话吞了回去。
又走了一阵,徐若霖噤了声,海晓风头上闷出了细汗,两人渐渐并肩走起来,树林里只剩下脚步挪动的声音。太阳又出来了,这次不是在头顶,而是在他们面前。树开始变得稀少,红彤彤的光顺着树林的缝隙照进来,海晓风侧头看看,徐若霖鼻尖上那层绒毛在阳光下无比清晰。
“你该刮胡子了。”他总想损这家伙两句,毕竟徐若霖再怎么说也是个女孩子看了会脸红的帅哥,如果不找点平衡大概会被颜值的压力给压扁。
“到啦。”徐若霖咧着嘴在他头上敲了一记,一步踏进了红色的阳光。
豁然开朗。
海晓风眼睛里映入了太阳的影子,红色的太阳有一半倒映在闪着光的湖面上。杂草长出去三五米就是湖滩,灰白的沙子漫过去水,鱼苗银色的鳞片在浅水里隐现。
“怎么样,很棒吧。”徐若霖在他旁边吹了个口哨,捡起一块扁平的石头旋了出去,“还会打水漂不了?”
石头在水上跳了几跳,沉了进去。
“老早就不打了。”他叹了口气,看着湖面上被石头打出的粼粼水光,阳光在水面上扭曲着。
太阳落得很快,天边只剩了一线紫檀色的云,徐若霖支起了烤肉架子和帐篷——那个巨型登山包里就装了这么一大堆烤肉用具和野营必需品,竟然还包括了老早就没人再用的木炭。海晓风背的那个包里满是食材,什么鸡翅香肠牛排羊肉串牛仔骨汉堡饼,现在这些肉类正在被炭块烤红的铁架子上滋滋作响,香味一阵一阵往人鼻子里钻。
海晓风把鸡翅翻了个面,扭头去看徐若霖,那家伙表示他不会做饭大概会点了林子以后就跑去湖滩上生了堆篝火,现在正抱着把吉他坐在旁边一边哼哼一边弹,悠闲得不行。
“想吃自己来拿,我可没那个闲心给你送过去。”他提高了嗓门喊了一句,徐若霖扔下吉他就颠颠的跑到他旁边小桌子上开吃了。
吃得总是比做得快,两个小伙子半个小时干掉了整整一背包烤了快一个小时的肉食素食,也懒得收拾有点惨烈的野炊现场,干脆打着嗝坐在篝火边上看起了星星。
天上有几丝云彩,月亮悄咪咪的从山背后绕出来,照亮了一片天空。
“没有光污染的地方就是好,看星星都这么爽。”咬碎薯片的声音在海晓风耳边响起。
“没有光污染,有噪音污染。”他斜着眼看那把吉他,徐若霖的琴艺真的让人不敢恭维,也许是琴弦不好,吉他声音干涩难听,扫弦迟滞无比,再加上某人荒腔走板的唱腔,大概这会去钓鱼都钓不上来,全被吓跑了。
“你懂什么,这就叫青春——”被挖苦了的家伙不以为意地跳起来,一手指向天空,“这就叫生活啊!”
“中二病。”海晓风忍不住笑了。
徐若霖一手扫过琴弦,吉他发出杂乱的声响:“听我给你唱Goddessα的新曲!”
篝火的影子在他们周围跳舞,湖面上有风刮过,男孩扯着嗓子歌唱爱情和生活,几乎要把星星从天上震下来。
那时候海晓风还不知道,他再没有见过那么清澈的天空,也再没有听过那些蹩脚却轻松的吉他和歌声,而很多年以后他参加海晓晓的婚礼,乐队演奏这首已经变成了老歌的曲子,女孩笑靥如花,他却哭得像个孩子。
计字3152
------------
5.
海晓风是被冻醒的。
徐若霖东西带的很齐,防潮垫野营灯保暖睡袋防水帐篷,按理说除非刮台风他应该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精神充沛的吃完早饭下山去才对,可是他却被冻醒了。
那种冷不是冬天没有暖气整个人要缩在被窝里的那种冷,那种时候他还能捂上两层厚衣服,睡觉还可以用体温把冰凉冰凉的被窝暖热。这种冷不一样,这是彻骨的寒,好像冰碴子钻进了他骨头缝里,寒气似乎要把他的血都冻住。
他伸手去推他旁边睡得像死人一样的徐若霖,却摸了个空。
一瞬间海晓风全身的细胞都在叫嚣着危险,男孩天生的警觉性子告诉他一定出了什么大事。
“徐……”
他没能叫出来,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
“别说话,外面有东西。”徐若霖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低而嘶哑,完全不像他所熟悉的那种爽朗阳光的少年声音。
他用力挣脱徐若霖的手,同样压低了声音:“什么东西?”
“不知道,反正不是好东西。”
海晓风才注意到帐篷里有隐隐约约的亮光,不是野营灯的那种昏昏黄的暖光,而是柔和的白光。光源在徐若霖手上,长形的东西,像是两根棍子。
……登山杖?
徐若霖正扒在帐篷上的通风口往外看,海晓风能感到他全身都绷得死紧,有点像校运会上他起跑前的那一瞬间。他不敢妄动,又有点好奇外面的情况,再加上他实在是被冻得发抖,只好往另一边的通风口去。
他拉开通风窗旁边的半圈拉链,把涂着防水遮光涂料的帘子挑开。
射进他眼睛的是亮得吓人的月光,差点闪瞎了他已经基本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半晌才缓过劲来。
这边的窗户靠西,从里面看出去是那个不知名的大湖,他们睡前湖上还波光粼粼,现在却平静得如同镜子,一小弯月牙和漫天的繁星都倒映在上面。
——不对。
海晓风心里咯噔一声。
他意识到不对的时候听到了另一个声音,有点像是人气管炎时的呼吸,浑浊而沉重,然而显然不是他自己的声音,徐若霖也没有得气管炎。
他的视野中闯进了一只巨大野兽的背影,白色的野兽,在白色的天光里泛着蓝,它转过头时海晓风觉得自己的呼吸都要停止了。
——狼。巨大无比的狼。
他只有这一种想法在脑海里盘旋,那白色的野兽长着发出蓝光的眼睛,长而尖利的犬齿突破了它黑色的嘴唇,明晃晃地露在外面。
徐若霖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帐篷从他们头上裂成了两半,他们背靠着背暴露在冰冷的空气中。
十年前他和徐若霖带着一群市实验的孩子和隔壁区小学的一群小混混打群架,打到最后两败俱伤,对面人多他们人少,剩下还能动的十多个人围着他们两个光杆司令。小孩子打架有股大人不敢想的狠劲,他们不知道生命的重,只知道一股劲的蛮干,哪怕闹出了人命也不过是教育和罚款,他们借着这就更加的肆无忌惮。所有人手里都抓着板砖和钢筋,能搞到稀罕货的还拿着弹簧刀,不过只敢虚张声势的挥上两下。他的头早就被打破了,干掉的血糊着他的眼,徐若霖背靠着他也好不到哪里去。这边带头的是他们两个,对面带头的那个他们听别的孩子叫他“豹哥”,可那孩子在海晓风看来整个人却恰似一头正待出栏的壮猪,就差上上磅然后宰了卖钱了。
“妈的,伤了我这么多弟兄,今天也算让你们沾了便宜了。”豹哥拎着手里的钢筋空挥了两下,“以为去了红领巾就能跟我们比了,两只绵羊?”
“绵羊你老母。”九岁的海晓风咬着牙,“别以为看了两部古惑仔片子就了不起了,你穿开裆裤那会儿老子就跟人打架了!”
其实他也在虚张声势,豹哥跟他们年纪不差多少,他穿开裆裤那会儿海晓风也穿开裆裤。
豹哥愣了一下,似乎在思考“古惑仔”这个词的意思,只是没过几秒就又嘿嘿一笑:“行,你不是绵羊,你背后那个一声不敢吭的肯定是了,别是吓出屎了吧?”
“……恶心。”八岁的徐若霖用孩子的声音低声咒骂。
“你说啥?”豹哥故意把手放在耳朵边,嬉皮笑脸地喊,“我听不见啊小娘们?”
徐若霖小时候长得阴柔,卷头发鹅蛋脸细胳膊细腿,还真的像个女孩子。
只不过被人叫小娘们是最迅速的激怒他的方式。
“我说你——”
钢筋从海晓风头顶飞过去,徐若霖拎着另一根钢筋把海晓风拽到另一边,那根被扔出去的钢筋照着豹哥的眼睛飞了过去,胖孩子慌忙抬手去挡,钢筋尖利的一端噗地一声扎进了他的小臂,尚且年幼的混混愣了一下然后杀猪般地嚎叫起来。
“——吔屎啦!!!”徐若霖的下半句这才骂出来。
好的,出栏了。海晓风那时这么想。
那时候他们两个背靠着背面对一群小混混的袭击还打伤了好几个,最后还是徐若霖的亲爹徐政给他们救了场,听说他以前是个混子,不过后来改邪归正做了个小片警,当然回家以后一顿臭骂是免不了的。
现在他们再次背靠着背,只是成了面对一群海晓风从没见过的野兽,显然徐政也不可能再次给他们救场了。徐若霖手中仍然像当年抓着两根钢筋那样抓着两根登山杖,他手里却什么都没有。
“这群家伙不是我们能打得过的,待会我说让你跑,你就使劲跑,从湖上跑,往南边有条河,顺着它能下到澶湖去。”徐若霖声音很涩,说了两句话还咽了口唾沫,“下去以后去咱们老去开黑的那个网咖,跟他们说‘虎落平阳’,然后告诉他们这里的位置,和‘寒豺来了’。”
“你让我扔下你跟这群狼斗?”海晓风也紧张,野兽围着他们转圈,彻骨的寒气从他脚底冒上来,似乎带着野兽的腥味,“开玩笑,什么时候打架我扔下过你,你可是我弟。”
“行,哥,让我保护你一回?”徐若霖哑着嗓子笑了一声。
“那也得等我需要你保护。”海晓风捋起袖子,凛冽的空气刺得他皮肤发痛,“你忘了我学过以色列格斗术,还是跆拳道黑带了?对付几只野兽……”
徐若霖没有接话。
一呼一吸之间,野兽动了。
蓝白色的巨狼露出森白的牙齿,黑色的兽爪在月光下反射出不祥的寒芒,和海晓风的预测不同,它的动作快得惊人,只是一闪就来到了他面前,少年根本无暇抵挡,只有愣愣地感受冷风和腥气一起扑到他脸上。
“躲开!”徐若霖怒喝,不知是对狼还是对他,只是声音仿佛要撕裂空气。
海晓风被撞开了,一瞬间兵戈相击之声响成一片,等他抬头的时候徐若霖已经与那只先动起来的巨狼拉开了距离,狼的脸被豁开了一道口子,兽血落在地上洇湿了一小片,而另一边黑色的血正顺着徐若霖的手臂往下滴,墨染似的痕迹渐渐在他白色的运动衣上晕开。
“徐若霖!”他大吼。
海晓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叫他,只是觉得不能这么下去,如果他什么都不做,他们都活不了。
“你快跑!”徐若霖背对着他,肩膀剧烈地上下起伏。
“我不走!”他握紧拳头,手却在发抖。
“快跑!”徐若霖突然破了音,那根长的登山杖在他手中挥出一片白色的光,空气中极快地响起爆裂声,另一只巨狼向后退了两步。
然后它仰天长嗥,其他野兽跟着嚎叫,凄惨而磅礴的狼嗥在山间回响起来。
它们开始攻击了。
海晓风没心去看徐若霖了,两头巨狼向他发起了攻击。
较大的一只向他扑击,他被野兽的巨力撞倒在地,后脑硌在湖滩的石子上一阵剧痛。
他知道不能和野兽硬扛,只是尽力躲闪着那些匕首一样的指爪,然而还是被狼偷了空子,在他腰间留下一道不浅的伤。疼痛冲击他的神经,少年不由自主发出嘶吼。
“我说了让你跑了!”他听到徐若霖含混不清的声音。
血从他眼睛前面落下来,像是给世界罩上了一层红色的玻璃,一切都在摇摇欲坠。
白光从一片红色中刺出来,兽爪离开他的伤口,狼狂嗥着被挑出他的视线,徐若霖染着黑红的背影挡在他面前。
“我说过让你跑了。”他重复了一遍,声音像是被砂纸磨过。
“跑啊!跑远!现在!马上跑!”徐若霖怒吼,手中扫出两轮半月似的银光,狼血洒了两人一身。
“走!”他声嘶力竭。
海晓风被徐若霖推到了湖面上,偌大的湖面不知什么时候上了冻,惯性下他走得一步一滑,回头的时候看到那头被豁开了嘴巴的狼正朝着徐若霖肩膀咬下去。
“小心!”海晓风只觉得伤口痛得天旋地转。
徐若霖回头,反手将短杖扎进了那狼的脑袋,顺势一挑,红白之物便带着连海晓风都闻得到的恶心味道喷涌而出。
时间好像静止了一瞬间,然后他看清了徐若霖手中的两根武器。
那是枪。
银色的,修长的枪,在月亮下闪着光,白色的雾气一样的柔光笼罩着枪尖。
枪在离它的主人远去。
血在月光里划出泼墨一般的痕迹,美得触目惊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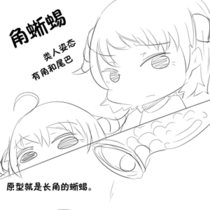

3271字。
--------
0.
男孩的影子坐在月亮下面,一长一短两把银亮的长枪横在他腿上,寒光在山上刀子似的微风里流着。
从背影就能看出他还并不很大,顶多高中毕业,甚至有点细弱的肩膀似乎随着风在抖,只是月光下那双黑眼睛却阴沉沉的,像是两块铅,里面的杀意比风还要冷。
男孩在等。
等他的仇敌。
1.
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让你事事顺利。
海晓风记不清谁说了这句话,总之他知道有这么句话,而且这句话对于他现在来说无比的现实。
现在是下午五点四十,海晓晓还没回家,许是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刚上初中新鲜学校的环境,都是这样。客厅里电视上有个胖男人在演示如何切出薄如蝉翼晶莹剔透的萝卜片,他手下锅里的杏鲍菇吱吱的响着,被酱油一泡变成了红褐色。
抽油烟机轰轰响得他心烦,铁锅铲狠狠往锅里一杵,连着铲断了三五块切成扇形的蘑菇。
海晓风,男,十九岁,高中毕业,目前待业在家。
谁也想不到一个从上学就被老师夸优等生的男孩子能栽倒在高考这条绊马索前面,何况他考得并不差,完全可以上个不错的一类本科。
然后他落榜了,原因是志愿报得太高。
蘑菇片还在锅里被他随着心意翻来翻去,眼看就炒过劲了,他赶紧关火,借着余温收了下汁。
他觉得自己就像这些蘑菇,被一些他自己也说不清的东西裹着翻来覆去,然后被装盘端上饭桌,被人评赏试吃。
刚放下盘子,电话就响起来了。
“毛毛?”电话那头是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开口就叫海晓晓的乳名,好像忘了家里还有个兼职保姆的儿子。
“是我。妹妹还没回来,有事?”海晓风拿两个手指头拈着听筒,锅把儿上的油沾了他一手,他不想等下洗锅以后再拿着湿巾把电话擦一遍。
“晓风啊。”女人的声音明显失望起来,“你也不出去转转,每天都待在家里怎么行。”
“我不在家谁给晓晓做饭啊。”海晓风把话筒换到擦干净的左手,尝试把右手在那块已经被用过一次的湿巾上蹭干净,然而几道油印已经黏糊糊地抹在湿巾上,他忍不住开始皱眉头。
“你让她去你秦姨家吃啊,又不是不好吃……”
“晓晓那么挑的嘴你让她在秦姨家里吃……”海晓风几乎能想象出自己年近五十的老妈噘嘴的表情,都一把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
——虽然她最近的照片真的不像个快到了知天命年纪的女人。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我就觉得你应该出去走走,你又不是立志要当个超级宅男的。”听筒里传来布料摩擦的声音,女人似乎在被窝里翻了个身,“不是说好了我帮你申请大学,你过个空档年嘛。”
“你说的挺容易,我要是跑出去乱玩谁来照顾晓晓?”海晓风心想谁不想出去玩,任谁天天待在家里都得憋成神经病,说不定哪天就提上菜刀上街砍人去了。
“所以才让你把她送你秦姨家啊。”她声音含含糊糊的,大概正趴在床上吃夜宵,“秦姨家都是咱们知根知底的人,多放心,你徐叔叔是警察,你跟若霖也熟得很,他好像考了本地的大学,让他照顾着点晓晓不也好嘛,再说女儿大了总要自立……”
“停停停,当年你把我扔秦姨家也是跟我这么说的。”海晓风毫不留情打断自己娘亲的喋喋不休,把对面呜呜囔囔的抱怨堵在耳朵外面,“我真是奇了怪了怎么秦姨就那么顺着你呢,我跟晓晓都快成她家的孩子了。”
“没办法呀,你秦姨跟我关、系、好——”
这不是一句关系好就能解释的好吗我的亲娘哎。
海晓风正想回她句什么,门铃响了。
“门开着,推!”他扯着喉咙往玄关叫了一嗓子,转头问电话那边的女人:“晓晓回来了,要跟你家亲闺女说话不?”
“不说啦我要睡美容觉了!”女人声音里全是撒娇的鼻音,搞得海晓风背后一凉,“来乖儿子妈妈啵一个——”
麻花辫的小姑娘从玄关转进客厅,看见的是老哥把电话一脸嫌弃地拿得离自己半米远,手上还拎着块脏兮兮的湿巾。
“睡你的觉去吧!”他正冲电话这么喊。
“哥,跟女朋友吵架啦?”海晓晓笑成了一朵花儿。
“去去去洗手吃饭去,妈打的电话。”海晓风把已经响起忙音的电话扔回去,电视上的胖男人终于做完了他的豆腐锅贴,主持人带着一脸假惺惺的享受小口吃着盘子里金黄色的不明物体。
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让你事事顺利,即使你并不要求事事如意。
2.
最后海晓风还是带着海晓晓去了秦姨家——就是海晓风的发小徐若霖家。
徐家和海家住在一条街上,两个人从小学就认识了,那时候海晓晓才刚出生,而这两个熊孩子简直是街坊邻里闻声色变的风云双煞。一个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山里霸王,一个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混世魔头,再加上母亲又是好友,两个人更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经常是一路从街头破坏到巷尾,他们俩都没少因为这挨过打。不过越长大这两人倒是越安分,到初中毕业的时候已经成了那种顽童们最讨厌的“别人家孩子”,几年前还把他们当孙子一样骂的邻居们也只能感叹小伙子长大了就是不一样。
然后他们像所有的学生一样,上完高中,考大学。
海晓风知道自己落榜了,而徐若霖到底上了哪里的学校,他也不知道。
他领着海晓晓站在徐家门口敲门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徐若霖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的往他家打夺命连环call,好像不去会有什么要命的事,还专门强调让他把妹妹也一起带来。
可是门打开以后他只看见徐若霖笑嘻嘻的脸,嘴里还叼着一盒酸奶,一看就是奸计得逞的表情。
现在他只想胖揍这熊小子一通。
“我妈是不是给你妈打电话了?”他黑着张脸看徐若霖。
“是啊,还专门叮嘱我拿毛毛开刀你就屁颠屁颠的来了——”徐若霖一伸手把海晓风拉进了屋里,“别用那张要掐死人的脸看我嘛,来来来我妈做了猪扒……”
海晓风看着他那张漂亮的贱脸有点牙根痒痒。
房间里飘着黑椒和芝士的香味,海晓晓进门就兔子一样蹿去了厨房偷吃,秦姨在柔声柔气地跟她说着什么,徐若霖坐在沙发扶手上把酸奶盒吸得吱吱作响,还跟着电视里又跳又唱的什么偶像组合晃着腿。
“你还迷着那个组合呢?”海晓风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只好从桌上抓了个苹果啃。
“不是原来那个了——现在喜欢这个。”徐若霖冲他晃了晃手机,一群红裙子的小姑娘在上面摆着经久不衰的V字手势,一个个都染着彩色的头发戴着美瞳,复古得不行。
他没话可说,只好笑笑。苹果汁水很足,啃着脆甜带劲,就是个头有点太大,如果是海晓晓大概得两只手抓着啃。
“落榜了?”徐若霖看着电视,冷不丁问了他一句。
一口苹果汁呛在嗓子里,海晓风咳嗽得喷了一地苹果块,徐若霖不声不响地,等他终于咳够了抬头的时候只看见他还在盯着电视,却明显没在注意电视上在唱什么,男孩有点飘忽的视线好像穿过了那堵墙。
“啊,是落榜了,怎么样?”嗓子还在发痒,海晓风心头无名火起,“我又不像你那样又聪明又帅,你也不用操心平时的生活,我跟你不一样,我还有个妹妹要照顾,我落榜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事?还是说你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像你那样养尊处优才正常?”
他说得有点急,又被呛得咳嗽起来,手里的苹果骨碌碌滚到地上,在瓷砖上划了一道黏糊糊的水痕。
海晓风觉得自己陷入了一阵奇异的寂静,电视上的女孩在无声地唱歌,酸涩的味道呛在他鼻子喉咙里,厨房传来的窃窃私语也消失了,徐若霖似乎在拍着他的背,什么尖锐的声音钻头一样刺进他的耳膜,无法忽略的不适感逼得他发疯。
他觉得自己对于时间的流逝出现了错觉,总之当他发现自己坐在地上时那首歌的演唱还没结束,海晓晓咯咯笑着的声音仍然从厨房传来,苹果已经滚了老远,在那里微微打晃。
“要是还生气可以冲我再发顿火,我不在意。”徐若霖蹲在他旁边,一只手扶着他肩膀。
“不生气,我生什么气。”力气好像被抽空了,海晓风靠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挑高到二楼的吊顶上安着耀眼的水晶灯,晃得他想流泪。
“你再不发发火就被憋出毛病了。”
“不发火,发火有什么用,发火人家也不会录取我。”他把脸埋在膝盖里,觉得喉咙有块棉花堵着。
“那就打起精神来。”徐若霖的声音从他手臂外面传进来,闷闷的,“我妈听我说你要来,专门做了你以前最喜欢的芝士猪扒,切开能拉丝的那种。”
“现在不喜欢了……太腻。”
“那也得吃,我妈做了一下午,腻了喝水,柠檬水,刚泡的。”
“那是什么金子做的猪扒居然做了一下午……”海晓风忍不住笑了一声。
徐若霖伸手把他从地上拖起来:“下周晓晓学校不是去秋游一周么,咱们也去秋游。”
“秋游个什么劲,多大人了。”他头有点晕,感觉头上的灯光闪闪烁烁地不稳定着。
“带你去散心。”徐若霖仔细看了看他的脸,“你哭了?”
“哭了你是我孙子。”他抹了一把脸,就算哭了也不能说哭了,不然会被他笑话一辈子。
http://music.163.com/#/song?id=33479465
十分强烈的给你们推荐BGM。
“我送她来见你。”
张炎打着伞站在墓碑前,穿着黑西装的人们分布在墓园周围,形成一个松散又严谨的网。
阴云浓重,牛毛般细密的小雨无声落下,把干涸了一冬的土地渐渐湿润。
张炎也穿着黑西装,好像某种丧服,火红的长发在肃穆中也显得不那么鲜艳了。
天边传来沉闷的雷声,树枝摆动了下,开始起风。她看了一眼缩在车里的少女,对方眼神沉郁,黑眼睛里有种叫人喘不上气来压抑。那里面装着山一般沉默又沉重的东西, 普通人只要看上一眼,就会胸口发闷。
此刻那双眼正看着窗外还未发出新芽的枯树。
“阿青。”张炎喊。
张青动了下,从敞开的车门中走下来。她没有打伞,两手空空穿过墓园细长的人行道,停在墓碑前。
周围那些黑西装们潮水般褪去,偌大的墓园中只剩下姐妹两人。
雨声变大了,张炎把伞往阿青那边倾了倾,被无声的挡了回来。
她轻轻叹了口气。
张青从她怀中素色的花束中抽出一朵来,轻轻放到墓前,说。
“我来看看你。”
五十年时间未曾在她脸上留下多少痕迹,除了几缕白发。她捻起一缕来,哂笑了下。那并不是时间带来副产品,而是悲苦和打击留下的伤痕。
她更瘦了,站在雨中愈发像一柄被刚开冻溪水冲刷过的枪,沉默冷冽,眼中突然亮起的怒火就是锋刃上闪过的寒光。
水珠从发梢落下,哒得滴在墓碑上,开出一朵透明的、转瞬即逝的花。
“跟你一样生白发了。”她用一种温柔到可疑的声音说,“想知道怎么来的吗?”
张炎闭上眼,感到心脏在剧烈抽疼。
“你死的当晚。”她声音有点恍惚,目光好像落在远方又好像看着眼前,“莫名其妙生出来的。还好没全白。我也比较喜欢自己黑发。”
张炎还记得那天她从门里走出来时的场景,大家都惊呆了,那个几十年从身到心顽固的不肯改变的人忽然变了,这之前所有人都以为一夜白头骗小孩,也不觉得张青有多看重那个男人。
“你之前总嫌弃我看不出变老,现在我们一样了。”她仔细凝视墓碑,“为什么讨厌呢?”
墓碑当然不会回答,她慢慢蹲下来,用手擦去灰尘,浑浊的水流落到土里,渐渐变得完全清澈。
“他们怎么走了?”张青问。
张炎等了一会,直到张青抬头看向她才明白这句话是问自己。
“谁们?”
“保镖,那些穿黑西装的人。”张青用手指描摹着碑文。
“有你在就不需要他们了。”
“他们在躲我。”一点,提笔,落笔,短短一横,折下来,再长长一竖,最后往上一勾,一个言字旁完成。
张炎点头:“他们怕你。”
张青了然,他们躲她就像躲病毒。男人在的时候还好,不在了之后几乎每个人对她都避之不及。没人喜欢靠近一个失去枷锁处在临界点的怪物。
“之前总不肯相信你死了,觉得一定又是你搞的什么把戏,血就溅在我脸上,但我还是没能立刻相信。 所以出殡下葬的时候都没来,只是在窗口远远看着。”张青描完最后一画,一个如同玩笑的双字姓名在指下生出。
那双从来不肯弯曲的膝盖抵进泥水,半跪着俯下身亲吻墓碑。
张炎觉得眼前一黑,握伞的手都在发抖。那是她妹妹,顽固冷傲桀骜嚣张,是她一直以来最担心的人,张炎握住自己发抖的手腕,恨不能把诺言从土里挖出来剁上几刀痛骂混蛋。
眩晕中张炎好像回到了儿时,雨水顺着屋檐滑落,她蜷缩在躺椅上假寐,阿青在门外听雨,阿爷把茶壶敦到火炉上慢慢煮着,和诺言在矮几前下棋。已经开始在前院帮忙的张倾鬼鬼祟祟钻进来,踏起一溜水花把从厨房偷来的点心交给阿青。
短暂的眩晕很快过去了,她又看清了眼前真实的世界。这个城市的雨水仍然很足,阿青站在雨中,就像小时候看着看着突然走进雨里转一圈一样。但还是有很多东西不同了,阿爷离世几十年,那个笑容冷嘲的男人也在成为黑道教父的几年后消失不见。她成了张家的掌舵人,不再是任由兴趣支配自己的武痴。只有阿青变化最少,除了那几缕白发和某丝心意,一切都和当年一样。
但放在她身上,改变本身就是最大的改变了。
雷声又一次滚来,雨还在下。
“你不说,我就只能瞎猜了,你知道在这方面,我一向很笨的。”她将额头抵在墓碑上,喃喃自语,“现在你总该满意啦,毕竟也算是……白头偕老。”
她看着上面那一行字,又沉默了会,站起来笑了笑。
“说错了,没有偕老。”
诺言,生年不详,卒于2052年1月20日。
1600,汪。
抽空再画有了白发的阿青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