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恋爱也许会死,不谈恋爱定会死。”
那么.....全力以赴地上吗?
也许剧中落幕之时,会出现一丝生的转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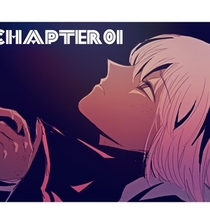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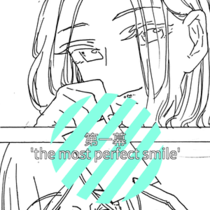
一些话:
市河是非常温柔的孩子,能力所限没有将他的温柔写出来真的感到很不甘心!还想写一下两位孩子的见面的,也没有能写出来,真的非常对不起糕老师。同时非常感谢糕糕老师!梗都是糕老师想的,画的也超强,糕老师又强又可爱!我跳起来亲
————————
“那么,秦小姐。”市河朝秦棠伸出手来,秦棠回应了他,她又触碰到了陌生的温度,这份温度顺着手掌一路延伸,直直地笼罩住她的心脏,使她再次开始浑身僵硬。
市河温柔地握住了她,他说:“请不要害怕,一切都可以交给我。”顿了一会,他又轻轻地补充道,“相对的,我也拜托秦小姐了。”
这句话让秦棠回过神来。她明白他们互相托载着对方的性命,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尚且能够被宽容的情景了,这个舞台上将要发生的东西已经在之前被规划出来,以便下方的眼睛细细品尝。这是一支不容失误的舞,她是伴曲里的一个音符,她怎么能让自己毁灭一首舞曲?
“好的,”她的声音还带着一丝颤抖,“我们开始吧。”
“开始吧。”市河公礼轻轻地说道。
他们的双手握着彼此,一同朝着前方走去,像是共赴一支舞。她的男伴握着她,他们即将出演一场盛大的节目,或者在这满溢了光的舞台上死去。
市河与她走到了光下。
“我送您回家吧,前辈。”市河公礼说道,拉开了这一次的演出的序幕。秦棠的身子软下来,又被市河有力地撑起。
如果想不到要说些什么,您可以说一些您生活的东西。市河在她耳边悄悄说,又朗声道:“您喝醉了……我送您回家。”
秦棠回忆着公司周边的东西,一句话不经思考地脱口而出:“真想吃楼下的小笼包啊。”为了让这句话具有酒气,她刻意说得磕磕绊绊,走得也跌跌撞撞。
“明天我买来带给您。”市河公礼即刻回应了她。他走得格外稳。在昏黄的路灯们的注视下,他们开始闲扯些别的,秦棠索性将公司里的那些烦心事都说了,而市河则是恰到好处地回应着她。秦棠甚至可以感到市河热切地望着她,而在她回望过去时,他又将眼神闪躲开来。市河在努力扮演着一名动情的人,而她,就像市河公礼之前安排的那样,只负责神智不清就好了。她觉得自己像一件扭曲的衣衫,正努力地想要站成一个漂亮的稻草人,以配合着赶跑那些饥肠辘辘的乌鸦。
他们到了演出处。秦棠知道他们到了,因为市河公礼的身子突然绷紧了,在房间里彩排的时候市河用一点水点在地板上定位,每每靠近那滩水时,他的身子总要绷紧。而现在换成了站的笔直的路灯,水和灯一样都是能发着光的东西。她故意一个趔趄,让市河公礼扶住了她,两个人有了借口在路灯下停留,并且彼此相看。
“前辈,请不要动……我想您脸上沾了一点东西。”市河对她说,昏黄的光照在他的侧脸,她顺着光看他浅色的瞳孔,那双眼睛里的感情过于真实,使她不禁真的相信了他所说的一切,不由得带着傻笑地凑近了搭档。
于是市河公礼的手指轻轻拂上了她的脸侧。这是第二次表演了,可她依旧为人体拥有的炽热温度而感到惊讶。市河也凑近了她,两个人的鼻息交缠着。她用余光确定着地上的两个影子,影子像鼻息一样,逐渐靠近,最后粘合成同一片阴影。
一切突然安静下来。他们默契地将这粘合的时间延长了。秦棠感到市河的手指有点微颤,她下意识地抬起手来,覆上市河的手。
市河被这突然的触碰提醒,他直起了身,影子重新分成了两块。那只手在秦棠的脸上再次轻蹭了一下,便离开了。
“好了。前辈。”漂亮的男孩子笑了起来,剧本中的“后辈”为自己悄悄达成了目的而窃喜,而现实中的扮演者则为自己的存活而长出了一口气。这份笑容发自真心而格外灿烂,“我们走吧。”
他们便依偎着,走向谢幕。秦棠尽职尽责地继续扮演醉酒的女人,而市河公礼也可靠地一直托着她走着。朦胧的灯光再次发挥作用,烘托着最后的表演。
“这是真的吗?”秦棠忍不住轻轻地问。
市河公礼听到她的问题,转头看了她一眼。他张了张口,想要说些什么。但他的温和阻止了他,市河公礼静静看着自己的搭档,只露出了一个笑容。他再次伸出手去,握住秦棠的手,像是上台时一样带着她离开了这片并不真实的街道。
“辛苦了,秦小姐。”市河公礼说,“秦小姐做得很好,我想之后秦小姐的演出也会顺利的。”他们坐在床铺上,隔着玻璃门遥遥地交谈。
秦棠轻轻摇了摇头:“我什么都没有做……辛苦你了,市河先生。”
“没有的事。”市河回应道。
“市河先生为什么能演那么好呢?”秦棠感到一身轻松,她开始找话题与市河打趣,“难道是把对方的脸想成梦中情人的脸么?”
“啊……”市河公礼愣了一下,他因这样的假设笑了出来,“没有哦。不过这是很有意思的提议,也许下次我会尝试的。不过如果能直接和她搭档就更好了。”
“原来是在这里认识的么?”秦棠有些吃惊,“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嗯……她是很厉害的人,能做到我做不到的事情,”市河说道,他的脸上因为想到了谁而变得柔软起来,“我想如果是她的话,说不定能带大家一起走出去。”
“走出去……”秦棠重复道。
“是的,秦小姐,”市河说,“我们都不会死的。”
“已经有人死了么?”秦棠突然意识到了这点。她没有再见过Moran了,自那次表演之后。
“如果一直没有见到的话,那非常遗憾,可是……”市河公礼愣了一下,但他只能继续说,“非常遗憾。”
秦棠有如被重物击中。她愣了半晌,想轻松地说出一句“原来如此”,但是她发现自己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秦棠想,这不应该,她已经感到轻松与庆幸,她幸运地活过了两轮,还在新的搭档那里得知了有一位可靠的人,“能够将大家一起带出去”,她可能不会像Moran那样永远留在这里——但是Moran已经将要永远留在这里了,“非常遗憾,可是……”。非常遗憾。
她张了张口,发出了一个单音节:“啊……”
市河公礼发现了什么,他试图过来安抚秦棠,像他一向做的那样。但在他跨过那个玻璃门之前,秦棠阻止了他。
她差点尖叫出来,但她及时控制了自己。她反复地说:我没有事,没关系的。请不要过来……请不要过来。直到男人的脚在那条线之前停下。暧昧的气氛被真实的死亡一刀劈裂,人与人的距离重新被一条直线画了出来。温和体贴的男孩不知所措,在那条线外看着她。秦棠捂住了脸,她多希望这时候抬起脸来看见的是那张熊猫表情包一样脸,然而不可能了。甚至表演结束以后,市河也不会再出现在她的隔壁。她将迎接一个新的陌生脸孔,全新的组合与故事,以满足观众的需要。
“那么,晚安。”市河公礼意识到这是一个不适宜进一步交谈的气氛。他担忧的眼神在秦棠身上转了转,最终只说出一句礼貌的告别语。
“晚安。”秦棠喃喃地回复他。
是的,该说晚安了。这黑夜不会是光,它无法聚集在一起,往人的眼中烧出泪水,再一并流入那瞳仁大小的黑洞。这是最后的时刻了。一切都将归于原处,所有的东西无所隐瞒,重的飘浮,轻的沉底。该说的话尚且还衔在人中往下一厘米的地方,不知会去往何处。
她曾经跨过那道线。在跨越过那条线之后她曾经如燕子一般轻盈。可是她再也做不到了。沉甸甸的现实把梦境扯碎了。
秦棠轻轻呜咽了起来。
——
辛苦企划组了,这篇文章无需记分了qwq非常感谢!




※捅刀不成只好来发糖了……
※字数:2399
※其实没啥好看的,全是聊天记录,over
(上)
她见过一颗星星。
漆黑的夜里嵌着那样一粒光。唯一的光。
但她醒了。睁眼仍是一片黑暗,没有光,也没有星星。
于是她怔怔地想:星星究竟去哪儿了呢?
男人还未归来。
少女揉了揉暗暗作痛的太阳穴。地板既硬又冷。长时间维持相同姿势令她的身体有些发僵。通过玻璃门相连的两个房间里,现在只有她一人。纯白的日光灯和墙壁将整个空间无限放大。她拢了拢厚外套,稍微动了动,接着又靠了上去。
明净的玻璃门上既已留下了皮肤的印迹。
那应该叫什么呢?油脂?她不清楚。
但她的目光未曾离开那扇房门。
雨果已经出去很久了。两小时、三小时……她没有仔细记,不过手机屏幕上的时间已逾零点。走廊深处的那一幕像是狠狠刻在脑海里:铁锈味、暗红色、面色惊恐的金发男人、那串她听不懂却又无数遍重复的喃喃自语。
优月不自觉蜷了蜷身子。
雨果仍未回来。
她不可抑制地想到很多种可能性,想起叶卡捷琳娜再三的催促,想起那个即将走出黑暗的可怖声音。
假如、如果、假设、万一、可是——
真岛优月一脑袋撞在玻璃门上。
这一撞颇有些狠,撞得她眼冒金星,不过她也因此清醒不少,骤停的思维遂将那些与“死亡”相联的可能性抛诸脑后。优月揉着脑袋,心想真疼啊,疼得她想哭,她还从来没这么“自虐”过。
她又想,其实她完全可以不必等他的。她没有理由等他,不是么?
她并没有忘记之前雨果是如何对待她的,那个冰冷的态度仿佛自心底、从血里渗出。冷血动物。她无数次在心中斥道。冷血动物。吸血鬼都是冷血动物。
冷血动物。
冷血。
……那么多血。他流了那么多血啊。
优月攥紧袖口。她无法忘记循着那段血迹向前走去看见的是什么、是谁,更无法忘记男人惊惶的目光与躲闪的动作,那样一个挺拔修长的男人,蜷缩墙角时竟也像小动物一般。她想哭,却不是因为被他伤害。
不知不觉间,那扇紧闭的房门似乎再也不会被打开了。
没有人从外面回来。
雨果再也不会回来了。
开门声唤醒——确切来说,是惊醒了她。
少女下意识从地上跳起来,重心不稳而打了个趔趄,不过堪堪扶住了玻璃门。这堪称滑稽的一幕令少有表情的金发男人微微瞠目。
“……你干什么?怎么还没睡?”
“……”
少女的脸一瞬变得极奇怪。她紧紧拧起眉头,却又全无威胁或怒意。那双有些红肿的眼睛里刹那晕起雾气,但她立刻擦去了,并迅速拉上深色浴帘。
“没什么。”
她若无其事地回答他:
“我去睡了。晚安。”
关了灯,浴帘上映出男人一如既往的颀长身影。不时的轻响隔门而来。
有没有血、认不认得出她、回来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已不重要。
至少,今晚不再重要。
少女闭上眼,很快便沉入安眠。
(下)
第二轮表演完毕之后,优月并未如想象中的那般感到释然。相反,因为哭得太用力,她一时不能对“突发情况”做出恰当反应——推开大门,她看见了静立门后的雨果。
而男人反倒更坦然,见她出来,便走上前,向她伸出手。掌中赫然一张干净的手帕。
“演得不错,”他淡淡说,“手帕记得还我,别随手丢了。”
真岛优月踌躇了片刻。她打量了一下他平静的神色,又看向他递来的手帕,垂眸想了想,这才不客气地接过去。“……我以为你早离开了。”语气埋怨,鼻音浓重。
“我不差这几分钟。”
雨果双手叉腰。他又恢复了上台前的衣服,当然,不仅是他,她自己也是。这也是“魔法”的方便之处。
他望向那扇大门背后的舞台,他们之前修修改改、最终定好的场景既已消失。顿了顿,男人重新看向她,突然问道:“你为什么哭?还是因为……想起了你的家人么?”
“……”
万万没料到他居然又提及这个话题,少女不禁牙痒痒,想咬死他。她磨了磨后槽牙,飞快擦了擦眼角,攥住手帕,然后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是啊,我就是想他们了,不可以吗?”
索性破罐破摔。
但话一出口,她又想起了他给的手帕。从他下场至表演结束大概还有二十分钟,男人似乎一直在门外等她——思及此,她不免暗暗后悔起来,只好又懊恼地别过脸去,补充道:
“一半吧。有一半是在想他们。”
“那另一半呢?”
他继续问她。其间,他绕过她,关上了通往舞台的大门。一声低响后,他又问:“还有另一半是什么?”
一边在心里期待他深究,一边又不愿他继续再问,但事实上男人的确如她所愿了。
少女回头看向紧闭的大门,心想自己三分钟之前还站在那里面,站在她和他规划的种种剧情里,最后动了情。这个“动情”,最初仅是“义务”和“必要”,但她似乎比自己想象中的更加沉湎剧情,因此她的确哭得很厉害。
好像要把这些天来所受的“委屈”、所尝的“辛酸”、所历的“恐惧”、所受的“担心”一齐发泄出来。她从未体会过如此复杂的情绪,心底的海啸不可抑制地吞没了她的回忆,并吞没了她自己。
随即,她将纷杂情绪都关进那扇门后,回头看他,眯细眼,轻声说:
“另一半,是因为你。”
“原来如此,”雨果点头,“挺有意思的……演戏。”
优月心下无奈。她心说这个人肯定又不知道她究竟想说什么。每次都是这样,好奇地刨根问底,又自顾自地得出结论。但她其实也不想再解释了,听不懂就听不懂吧,这才是她知道的雨果。
……可她到底知道他什么呢?
少女陷入沉默,男人也不再开口。舞台上表演的动静被隔在门内,场外便显得安静太多。它兀自在空气中浮沉,与光尘一同发酵。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很久,也许只有十分钟,雨果微微移开目光,忽然说:
“你没有其他事的话,我就先走了。……那个房间之后会有其他人类住进来,我只是回到原来的房间了。”
“等等,你的手帕……”她“啊”了一声,急忙叫住他,“之后我洗好了再还给你吧?……呃,是哦,要换搭档了,以后我需要摇铃找你了,是吗?”
“差点忘了,”雨果伸出手来,“直接还给我就好,不麻烦你。如果你有需要,就摇铃铛,我会来的。”
说罢,他偏了偏头,略有诧异:“我以为你不会再碰那个铃铛了。”
优月叹了一口气。
“……我会碰的。”
她望着他的碧眸。
“我会碰的,”优月重复一遍,柔和地笑了笑,“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嗯,那下次再见。优月。”
雨果收起手帕,转身离开了。
她的视力其实并不好,可她偏偏窥见了一粒光。
它就藏在他的眼底,透亮得像一颗星星。
唯一的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