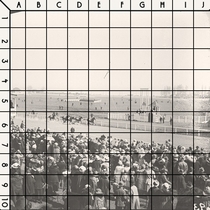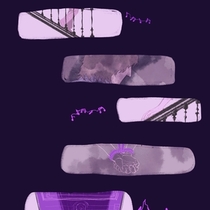My care is like my shadow
Laid bare beneath the sun
It follows me At All times
And flies when I pursue it
I love And yet Am forced to hate
I seem stark mute inside I prate
========================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魔女歌唱之时,化为人形。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在机械轰鸣的爵士年代,魔法与巫术在此暗中汇聚。
器物与人类,是否能找到与之结缘的彼此。
两者的缘分与命运,无论善恶,就从踏入徒然堂的一刻开始。
欢迎来到TURANDOT•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1、晨间
这寡淡无味,日复一日的工作像是一杯廉价的速溶咖啡,除了干涩以外没有任何值得品味的地方,但塔希尔的到来仿佛是一块抛向杯中的方糖。他端起杯子的同时抬了抬眼瞥向对面的少女,糖块彻底溶解后这杯咖啡与之前的样子看起来没什么区别,只有喝下去时才能感觉到这细微的变化。
他折起报纸放在手边,正面朝上的一页刊登着匪夷所思的文章,看起来像极了推理小说的片段。被称为吸血鬼杀人案的事件余波未平,风浪又起。若是对这些事的内幕完全不知情的人还能保持着事不关己的立场。斯图亚特已经依稀窥见了某些超出人类常识范畴的事,但仍未能完全理解其全貌,以这样一知半解的状态来阅读这些报道才是最为困惑的。
他想得有些出神,照着报道上的描述念道
『…它…来了?』
『…雷哲?』
少女眨了眨眼投来关切的目光,斯图亚特略微一顿才反应过来,他无需独自思考这些隐晦的神秘,在这些事件上,乌拉厄丝的见解更具有参考意义,她正是未知与迷题的化身。
『最近学院的人都在谈论,大概是某些有名的人物一夜之间不是自杀就是失去理智,不断地强调某种恐怖的东西来了。』
乌拉厄丝放下手里的刀叉,用手帕抹掉嘴角的蜂蜜,一时间,两人没有继续这个话题,沉默与寂静的氛围扼住了他们的脖子。许久,斯图亚特放下杯子,瓷器碰撞的脆响击碎了这静默。乌拉厄丝迟疑地抿了抿唇,雷哲没有追问,她的契约者总是会留下选择的空间,无论她是想要隐瞒或是全盘托出。她有些分不清这习惯是好还是坏,因为雷哲并不在意她的回答。
『我不确定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但如果是那个噩梦…我看见了,恐惧与绝望的恶魔将世界沉入深海,我……』
梦境常常是模糊的,她无法回忆起所有的细节,唯独那恐惧和绝望深深地刻在眼底,醒来时化为劫后余生的心悸。
『塔希尔。』
雷哲突然打断了她的喃喃自语,起身越过桌子握住了少女的肩轻轻摇晃。乌拉厄丝的唇颤了颤,她抬起头,在雷哲双目中看见了自己惊惶的神色。梦中的感觉太过强烈,如同落入海中不断沉溺,在那深邃的幽暗中,她只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普通人,面临比死亡更加可怖的东西。
『…我…没什么,雷哲。如果那些人与我所见的相同…那么,疯掉也不无可能。』
她伸手去拨开雷哲的头发,将手掌轻轻覆在契约者的额前。迸发而出的灼热温度与冰凉的指尖无比鲜明地落在皮肤上。
『我能做的只有这些,至少不能让你也被它带走,我会守护你。』
斯图亚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看了看手表,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解决掉早餐,将报纸叠好放在桌角,拿起资料和笔记。
『放心吧,我不会轻举妄动,当然你也是。待会儿见,乌拉厄丝。』
2、深夜
两人从徒然堂出来时已经是接近午夜的时分了,情报交流耗费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虽然只掌握了冰山一角,但也不妨碍斯图亚特猜测接下来更加深不见底的可能性。质地良好的纸张摸上去还能感觉到浮雕般的暗纹,还有些许香料的气息。尽管是非常符合礼仪的邀请方式,内容却令人不能轻易松懈。邀请家精与契约者一同出席舞会,在这奇妙的一夜,家精能够被所有人看见。
乌拉厄丝拿着信封反复研究,尝试用自己的能力去寻找线索,遗憾的是这封信确实没有更多的信息了,至少,与那枚奇怪的硬币不同,这上面没有被动过什么手脚。倒是斯图亚特板着脸暗自思考的样子让她拿不定主意。
『雷哲,不想去吗?』
斯图亚特的眉心拧了拧,衡量利害的天平在不断左右倾斜,机遇总是伴随着危险,况且他也无法完全置之度外了,那么这里就应该大胆举棋进攻。
『看起来有参加的价值。』
『咦?』
这让乌拉厄丝有些意外,毕竟雷哲对社交的态度非常冷淡,比起西装革履地游走在人群中,他更喜欢独自休息,上次去逛曼哈顿商会展似乎已经满足了他整个月的社交需求。斯图亚特将信件放在外套内侧的口袋。
『你在商会展上捡到了那枚硬币,以及随之而来的噩梦和事件,如果不是偶然…我们应该夺取主动权。』
乌拉厄丝露出了微妙的笑容,毫无疑问,她的契约者是冷静果断的人,但为什么会在奇怪的地方较真起来呢?她清了清嗓子尝试转移话题。
『现代的舞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表演的话我还是有点信心的。』
『…不…现代的舞会…跟宫廷宴席不一样。』
雷哲又开始感到头疼,如何让乌拉厄丝快速简单地明白现代舞会是为何物呢?总之先把误会纠正过来才行。
『现代的舞会,多数是两人一组互为舞伴……嗯?』
并肩行走的少女突然离开了视线,她怔怔地盯着出现在十字路口的人影,那是个与乌拉厄丝身量打扮相仿的人,英气的眉目看起来应该是个少年。他也正盯着乌拉厄丝,他抬起手臂时雷哲才发现少年的双臂是一对鹰翅,羽毛仿佛锋锐的刀刃。少年低声嚅嗫着什么,向这里靠近。雷哲感到自己被定在原地,除了脑子以外身体的任何部位都本能地拒绝活动,奇怪的念头占据了他的思维,就像是有人在耳边不断重复,你不应该去阻止他们。
——总有哪里不太对劲。
少女不可置信地睁大眼,提起裙摆小跑过去。
『真的是你吗?法…』
『塔希尔!』
带有警告意味的呼声打断了少女的脚步,她茫然地回头,与此同时契约者与她错身而过,用手臂抵住了少年正要伸展开来的左翅,另一只手快速劈向肩颈的压迫点尝试将其逼退。结实挨下了防反的少年却分毫不动,身体连一丝颤抖或倾斜都没有,他歪着头木然地盯着乌拉厄丝,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而惊慌起来的少女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
『雷哲…!』
『哇啊——!!』
少年机械地张口,喉咙深处发出了类似于新生儿的哭声。斯图亚特立刻后跳两步拉开距离。方才击中的感觉非常奇怪,就像打在一团半流体的物质上,甚至没有骨骼的触感。少女脸色苍白地揪紧了裙摆,雷哲确实为她挡下了一次近乎致命的偷袭,而这哭声将幻觉完全撕破,少年缓缓蜷缩起身体如同母胎中的婴儿,哭声愈发强烈,斯图亚特甚至感到脊背发凉。
面对未知的怪异,避战才是最好的策略,他朝婴儿的面部直线出拳却在将要接触的时候停了下来,转身拉起少女的手狂奔离去,被佯攻激怒的婴儿紧随其后。
『甩不掉…?!』
乌拉厄丝扣住了斯图亚特的手腕,宛如白色的孔雀高高跃起,低空飞行迅速拉开距离,两人在街道上持续了近半小时的追逐才成功摆脱那诡异的哭声。
『哈…哈…真是的…下次…要带好武器…再出门……』
周转了一晚上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上气不接下气的斯图亚特,看着桌上还没看完的资料和论文,露出了生无可恋的表情。比怪异更可怕的现实,工作,还没有,做完。

※每个月请假,每个月瞎写,这就是狗吧.jpg
※……写昏头了抓个虫,对不起又重新响应_(:з」∠)_
这是五月里的一天。
季节向夏天过渡,逐渐趋于晚春。公园的花坛与路边的花店为这座高楼肆虐、铁轨横行的城市增添一分奇异的春色。戴安娜·科尔曼走在街边,深蓝色宽檐帽和长裙在阳光下显得崭新又时髦。尽管还未习惯新衣,她走路时的姿态依然像一只静默水上的白天鹅。她缓缓走在街上,电车与汽车轰轰而过。忽然又停下,看了看手里的白色郁金香,有些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是路边一个花童忽然塞给她的。
小男孩看上去约莫十一二岁,抱着一大捧五颜六色的花来回吆喝。不时有行人会驻足,或是买上一枝,或是拿起一捧。她从他面前经过时其实并没有停下,反倒是他先注意到了她——脏兮兮的小脸上,那双棕色的大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随即,小男孩赶忙用袖子胡乱擦了擦脸,露出鼻子旁星星似的小雀斑,腼腆地笑着,从怀中抽出一枝花递给了她:
“给您,美丽的姐姐。”
戴安娜抿了抿唇。她想拒绝。他这个动作既已引来了不少关注,大家都在好奇怎么这个花童会突然向空气递出去一枝花。
但小男孩只是看着她。
“我没有钱。”她说。
“这是送的,不收钱。”他没有收回。
“为什么要给我?”她便问。
他眨了眨眼,“因为今天是个好天气。”
阳光从花瓣上滴落。洁白的郁金香在她眼里盛开。她一边思考是不是所有小孩子都是如此不讲道理,一边却又失去了拒绝的理由,收下并道了一声谢。
于是,现在她孤身站在街边,有些茫然地拿着这朵花。
她想起自己眼下的栖身之处——帕特里克·埃德温的家。那栋宅子里挂着名画,放着雕像,也摆着花瓶。尽管他看起来不像喜花之人,但经常都会有佣人耐心浇水,若是花瓣出现了枯萎的迹象,也会及时更换。
他是不会需要这样一枝不起眼的花的。
叮铃铃,一阵自行车铃从她耳边倏地溜了过去。这串铃声让她想起夏洛特——自己身上这套新衣服还是她挑选的——戴安娜抬起头,站在眼前的却并不是黑发女性,而是一名身材更娇小、笑容也更轻快的女孩。
是她。
那个皱着眉头苦恼询问“恋爱”的小小少女。
芙洛丽亚。戴安娜还记得她的名字,就像自己手中这朵郁金香的花冠一样饱满而可爱。
女孩似乎也认出了戴安娜,惊奇地睁大眼,随即拿着扫把颠颠跑了过来。
“好久不见呀,戴安娜小姐!”
家精的时间是停滞的。即便隔上两三个月重逢,芙洛丽亚也能笑靥满面、不带隔阂地朝她打招呼。戴安娜点了点头。“您换了新衣服啊,对不起,我差点没认出来。”芙洛丽亚打量着她身上入时的套装,“好像橱窗里的模特。”眼睛里流露出一丝羡慕。
戴安娜不知她的意思,只好生硬地换了个话题。
“有人买下你了么?”
“是的!”
“对你好么?”
“那当然——洛斯塔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最好的、我亲爱的爱人啦!”
芙洛丽亚夸张地张开双臂,仿佛用语言还不够,非得加上动作才能准确表达。她兜满了春天的碧绿眼仁儿里熠熠闪着光。那盈盈的光与商店的人造灯不同,是自然而然的,常出现在街头巷尾成双成对的情侣眼中,却又绝不会出现在戴安娜自己的眼里。
戴安娜点了点头,什么都没有说。
见状,芙洛丽亚好奇地问道:“那您呢?还在徒然堂里吗?”
“……我被人买下了。”
她其实不是很愿意回想起当时的事。帕特里克之所以会买下她,并不是因为他一眼相中了戒指,或是有心上人,只是因为一场闹剧。这让她心里隐隐有些不舒服,但她并不想承认。
“我能问问是谁买了您吗?您这样漂亮的戒指,能买下您的人一定很有品位吧?”
戴安娜思考了片刻。
自从帕特里克买下她也有一个月了,可她仍然不了解他,当然,她也从未打算主动了解这个人。他经常出门,也时不时会有警察上门盘问,之前他带她去的那个命案似乎仍未有个了结,于是拖拖拉拉了一个月。他那间宽敞的书房里摆着成排的小说,也堆着尚未上映或开拍的电影剧本,还有留声机与许多唱片,不过隐藏在那张友善面容下的帕特里克·埃德温似乎总是兴趣缺缺。
好像对任何事都提不起什么兴致。
于是她回答:
“……只是个无聊的男人罢了。”
芙洛丽亚“哎呀”了一声,好像还想说什么,远处传来的呼唤却将她的话语打断。她转身去应了一声,又招了招手,这才回过身来,有些歉疚地说:
“不好意思,戴安娜小姐,我得去帮忙了。我现在就在这家咖啡店打工,下次有机会的话,请您一定要来呀,这里的甜品可好吃了!”
她目送女孩跑进不远处的咖啡店。春天的阳光为一切都披上一件柔和的外衣。有一瞬,她好像瞥见了“外衣”之下悄悄积蕴的阴影,静静缠绕在女孩身上,好似黄昏逝去,夜幕就要落下。
戴安娜·科尔曼收回了目光。
什么也没有说。
“你要去看电影么?”
几天后,帕特里克·埃德温这样问她。
她正在他的书房里挑选下一本要看的书。撇开那些爱情小说,只剩下针砭时弊类的,或是悬疑侦探类的。那么——她将手伸向那本《怪诞故事集》——就这本吧,指尖已经扣在了书脊上,听见他的询问也没有停顿,从书架上拿下书来,看了看作者,又轻轻拍了拍硬壳封面,这才问:
“电影?”
“今晚的。”
“我去了也只能站着看吧。”
“不会,我这儿有两张票。”
她回头瞥他一眼,“邀请我做什么?之前那些女伴呢?”
“她们有些聒噪,”男人把剧本随手放了回去,“你要是晚上有事的话就当我没问吧。”
倒也没什么事。家精能有什么事呢?她淡淡想着,又看了看手里的书,朝他扬了扬,说:“那我要借这本。”
“借吧,下次不用特地说,”他看也不看她拿了什么,“你答应了?”
她点点头。
他“哦”了一声。
这种不咸不淡的你来我往已经持续了一个月。戴安娜本身话并不多,与帕特里克也不熟,或许帕特里克也是这么想的,因此他们除了必要的交流之外不会有什么更深层次的聊天。但他偶尔会在空闲时间带她出去,看看歌剧与杂耍,有些好看,有些一般,她也给不出更高明或感性的感想,不过他也不怎么问。
包括这次看电影。
这是她第一次去电影院里看所谓的“电影”。黑白画面里的男女主角飞快地做出动作和表情,电影本身是安静的,只有配乐起起伏伏,可电影院里不是,时不时会响起男男女女的笑声,尖利的、低沉的,还会有窃窃私语,批判的、赞赏的,随剧情发展,后来隐约夹杂起了抽泣。这似乎是一部催人泪下的电影,于是她偏过头,想看看男人的反应,却见他一瞬不瞬地盯着屏幕,好像是在看电影,又好像是在看电影里的某个人。
他在看谁呢?
如他这般淡漠的人,也会有想目不转睛注视的人么?
戴安娜第一次对帕特里克·埃德温产生了兴趣。
“两人一生再未见面。”
结局的字幕缓缓浮现,她瞥见,那不大不小的白字映在她空无一物的眼里,顺着落进了心底。这是一个爱情故事:男女主角以一个戏剧般的方式相遇,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最后女方先嫁了人,男方也未痴心再等,两人分别在纽约下雪的街头。
如此寻常的事情每天都在现实里上演,不知为何,在电影院里以第三者的身份旁观却更容易代入。
那低泣与叹息在她看来甚至有些做作。
男人并没有率先离场。他们所在的座位刚好位于电影院中央,等观众走得差不多了,才能起身向外走去。他一直看完了工作人员名单,她也跟着看,直到滚动的名单里出现了他的名字,她吃了一惊。随后,清洁工提着扫帚进来了,见里面还有人,便不耐烦地等候在旁。男人起身向外走去,她落了一步,也走了出去。
出去便是灯红酒绿的纽约街头。
与电影里唯美的镜头不同,真实的纽约从不会等待任何人告别。先前还一窝蜂涌出去的观众早已散得七七八八,帕特里克不急不缓地走在街边,让她靠里侧走,两人并肩。
一时无言。
喧闹将沉默挤得落荒而逃,霓彩流光,车水马龙。她不得不提高声音才能确保他听得见自己。
“你投资了那部电影?”
“是啊。”
“为什么?”
“赚钱。”
“能赚钱么?”
“只要是爱情电影,差不多都能赚上一笔。”
他的侧脸在来往的车灯下明明暗暗。任谁都听得出他回答的嘲讽,但她想知道的是,既然不相信爱情,为何偏偏要凝视电影里的那个人呢。
人的言行总是充满了矛盾。
戴安娜终究没有问出口。
“所以呢?那部电影叫什么?”
坐在对面的黑发女人饶有兴致地问道。
她总是湿漉漉的指尖来回摩挲着桌面,水珠在桌面上凝结得像一滴剔透的露。戴安娜看了看四周,她们正坐在一个偏僻角落,这里恰好有一张空桌。避开了高峰期的咖啡店里,客人进进出出,怎么也填不满空位。是女人拉她来这儿坐下的。
“记不得了,”戴安娜老实回答,“爱情电影的标题都差不多。”
况且她根本没怎么看进去。能总结出剧情是一回事,沉浸在剧情里又是另一回事。她从未真正沉浸在那场电影里,一切都太假,爱情哪能是那么美好且温吞的东西呢?它理应是触及皮肤与血肉的,热烈而又残忍,一厢情愿、不死不休。
这才是她知道的爱情。
这才是人类教给她的爱情。
黑发女人——夏洛特笑了笑。她就连笑容也沾着湿气,乌黑的长发妖娆地贴着两鬓,像小说插画里的海藻。她与夏洛特也是在徒然堂相识的,所有缘分均始于那家默默无名的古董店。至于如何相识的,戴安娜仔细回忆了一下,似乎是夏洛特之前邀她一起去看歌剧,一来二去也就渐渐熟络起来。
夏洛特并不在意她的冷淡。愿意与她打交道的人都不在意她的冷淡。
或许是所有人都默认她是一颗钻戒,钻石本身有多冷硬,诞生出的家精就有多冷漠。戴安娜觉得不少人都是这么想的,她也从不辩解。辩解什么呢?本来也是事实。
夏洛特比她更喜欢外出,因此每次总是她来分享大千世界。戴安娜一边听她讲话,一边将目光投向咖啡店的窗外。车来人往的马路边忽然跑过去了一个小男孩,怀里抱着一捧明黄色的花,好似一颗明丽的流星,从街这边眨眼间划过去,消失在了尽头。
她想起前两天送她郁金香的小男孩,又想起那一晚帕特里克·埃德温的侧脸。
他们其实经常这样一起走路,无论是去看歌剧的途中,还是回家的路上。他不一定每次都会坐车,尽管这身西装很有可能被路边的污水和尾气弄脏。也总有不知情的外人盯着他看,有些是好奇他西装革履的打扮,有些则醉在他不苟言笑的眼眸。但他不会在乎,更不在乎与她之间断断续续的对话是否会引起那些人的疑惑和反感。
——那朵花或许应该送给他。
戴安娜·科尔曼忽然有些后悔。
晚春初夏之交,纽约像一头沉默前行的巨兽,一呼一吸都震耳欲聋。它向前走,带着城市里的人们也向前走。没有人知道终点在哪儿,所有人都顺从于季节更迭。
阳光远远地照进,像游鱼的尾巴摆荡出的涟漪,波纹摇曳而来。于阳光之下透明无物的两个家精,没有点餐、没有笑闹,只是静静地享受人满为患之前的短暂休憩,谈论一些也许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比如爱情。
在这个寻常的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