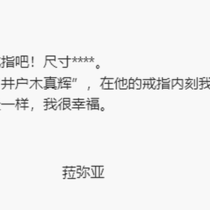全文字数3205
.
.
.
♧☆
这是很棒的旅游。
菅原梨纪再一次检查了行李和背包,确保自己已经带上了所有的东西,留给父母的纸条也好好地贴在了冰箱上。
这趟旅行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只是单纯地去往京都,看看不熟悉的风景,和那些结构精巧的建筑,当做给要毕业的自己的礼物。
最后一次确认了小工具包里没有不可以带上飞机的东西,菅原离开了家门。
今天天气很好,很适合旅行。
她独自坐在电车上,百无聊赖地看着车厢内来来往往的人。
菅原绝不是个喜欢安静和独处的人,她吵吵嚷嚷的性格和撒手就没的行动力,总给人一种精力旺盛的柴犬的印象。平时去什么地方,也总是会邀约上三两个朋友,一路聊天吵闹,再到目的地好好游玩一番。但这一次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行程和打算。就算是对父母,也只是含糊地留下“我出去玩啦~过几天回来!”的信息。
菅原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么乘兴旅游的感觉也蛮不赖。
她按部就班地到机场、过安检、登机,本想靠在玻璃上休息一会儿,没想到这班航班却意外地热闹。
菅原也与坐在自己座位前,叫做神尾礼耶的女孩打上了话,并自顾自又单方面地把她认作了自己的朋友。
她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远的地面和碧蓝色的天空,心中也不免有些雀跃。
想去旅行,想去见那些未知的风景,结实新的朋友,尝试新的美食。
菅原哼着小曲,小幅度地晃动着脑袋。
.
这是最糟糕的旅行。
冲击感后,世界颠倒。
菅原徒劳地按照之前空乘小姐们教的防冲击方式缩在座椅之间。
她紧紧地闭着眼睛,周围的尖叫和冲撞声扭曲了疼痛感和不停灼伤鼻腔的刺鼻气味。她徒劳地紧紧抱住自己,但这样是无法与重力相抗衡的。
她尝试回忆最后听到的正常的声音,但是怎么搜索,脑中循环播放的,就只有广播混合着电流,断断续续的诡异音效。
防冲击姿势也不再能帮得了她。
有什么东西快速且强烈地撞上了她的脊椎,瞬间的窒息感和剧烈的疼痛让她猛地睁大了眼,然后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中。
我应该在去年暑假,就坚定地说我要养一只狗。
一个有些荒诞的念头从菅原脑中飘出来。
长久的灰暗过后,让她醒过来的,是冰凉的窒息感。
她下意识张开嘴想要呼救,却被灌了一大口水。
混着血腥味的水。
她还活着,似乎还在机舱里,但周围都是水,身边的乘客已经断了气,面朝下半漂浮着,腰间还系着安全带。
菅原连尖叫的空余都没有——更多尸体在她周围沉沉浮浮,好像提醒着她再不采取些什么行动,就会变得和它们一样。
四围陆续也有其他人醒来,这让菅原多少安心了些。
幸存者中似乎有人找到了安全出口的位置,还活着的大家开始往那个方向聚集。
菅原解开安全带,尝试着跨过周围的尸体往机尾淌水走去。
或许能给其他人提供一些帮助,自己也或许能更多些活下来的机会。
当目光中看到一抹金色的麻花辫时,菅原多少又更放心了一些,至少这位新认识的朋友和她的朋友们都还安全。
血和水的噩梦之外,是甚至称得上美丽的风景。
夕阳撒满了天空和湖面,拂面而来的凉风清甜得想让人哭泣。连依旧散发着血腥味的湖水似乎都变得不那么让人反胃,远处深色的湖水还多了些让人心旷神怡的氛围。
菅原终于有了在自己还活着的实感。
她习惯性地摸了摸自己的腰间,总是带着的工具包登机时就放到了托运行李中,看来也是拿不到了。
周围的幸存者们开始尝试着向陆地游去,菅原定了定神,也行动起来。
大概是这场飞来横祸过于突兀和沉痛,让她晚了一步的情绪还没来得及做出什么反应。
她非常平静,一下下划着水,往岸边去。
.
这是还不错的旅行。
他们先后发现了几个其他幸存者,无一例外都失去了记忆,让人不由得好奇他们曾经发生过什么。
在看到某个人的时候,菅原愣了愣。
周围的人多少有些骚动,隐约能听到“内衣”“回避”一类的字眼,她没有太多在意,那个晕倒在地上的人的脸足够吸引她全部的注意了。
昏迷的女性倒在路边,额头微微出汗,散射着细碎的阳光。深色的头发铺开来,和路边的杂草泥土混杂,让人不由觉得可惜,这么好看的颜色是不应该被和其他东西以如此粗暴的方式糅杂的。但这份由深到浅,有些散乱的蓝,又那么适合流淌在泥土与青草之上,像反射了蓝天的水脉。
菅原的脑子乱糟糟的,浮现出奇怪的意向。
她甚至在很短小的一瞬间,觉得眼前的女性就这么沉睡着也不错,像是某种画作。
当然,她还是会被唤醒,毕竟救人要紧。
“这是……你们是什么人?”
那位女性睁开了眼睛。
菅原离得足够近,可以看到她还有些迷蒙的眼睛逐渐变得清醒,从柔软的混沌,一转为锋利与干练。
“你好!你还记得自己的名字吗?我们是因为空难过来的!请问你是谁?还好吗?需要帮助吗?还有这是我的外衣,不介意的话要披上吗”
大堆的问题咕嘟嘟从她嘴里冒出来,没有考虑过对于才清醒的人而言是否真的能回答这些问题,也没有意识到她的表情和语句,不论是对于刚刚遭遇了空难的自己,还是依旧搞不清状况的女性而言,都太过热烈和激动了。
对方谢绝了她递过去的外套,不知是关心还是礼节性地反过来对她说“小心着凉”。
那双像是被淬了火彩的蓝色眼睛看向菅原时,她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
菅原知道自己有时会被什么东西突如其来地吸引,一般而言是某种建筑结构,或是某个理论,甚至某种工具。这也让她以比别人更快的速度毕了业。
不过这样热情的承载对象是某个人还是头一次。
菅原没想太多,也没有脑子思考太多。只是像任何时候一样,拉也拉不住地,一股脑地,扑向自己感兴趣的事物里。
“就先……叫我欧泊吧。”
对围在自己身边的幸存者们,她这么说道。
菅原琢磨着这个失去记忆的她为自己取的名字,不住地看向她的眼睛。
菅原对于宝石没有太多的研究和了解,只大概知道欧泊是有缤纷的色彩和凝固底色的某种矿物,与剔透的其他宝石不太一样。
欧泊看着前方,步伐利落。
她的眼睛似乎随着光线在深浅中不断变换,隐约间又有淡淡的流光,映射出霞彩和流阳。
这确实是难得的宝石。
菅原眨了眨眼,快步跟在她的周围,短暂地忘了眼前的困境,冰凉的血水和重叠的尸体。
不论是受了伤的少女,满身是血的一对男女,不寻常的爆炸,还是在河里裸泳的怪人,甚至在面对倒地的尸体,欧泊都非常冷静,甚至为了不让尸体挡路,把它踢开了一些。
菅原并不想对此做出什么评价,毕竟就算是她自己,也在连续不断的刺激下渐渐失去了对“正常”的标量。眼前要考虑的,只有如何解决事件,她的大脑也似乎在渐渐学习如何把死亡当做布景板。
这不是坏事,至少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不是。
至于欧泊小姐,利落的言行只让人觉得更加靠谱,格外值得信赖。
.
建筑的情况不容乐观,但至少这里有些用于急救的设备,也给所有人提供了能凑合过一晚上的地方。
看着周围的人已经三五成群,和自己属熟识的人商量房间分配,菅原犹豫了一会儿,敲了敲欧泊选择的房间。就算她已经和自称琉璃的人一起住了进去,但只有两个人,或许能有一个位子给自己?
“请问你们那边还有空吗?”
菅原对欧泊露出试探性的笑,尝试着问道。
“抱歉,我睡眠不是很好。”欧泊回给她的笑淡淡的,不让人讨厌,但也足够疏离。
“而且,你和同龄的女孩会更有话题吧?”她又给了菅原另一个台阶,温和但坚决地表达了拒绝。
菅原眨了眨眼睛,有些委屈地点了头:“好哦……”
这也是常有的事。毕竟你也不能指望自己可以多快速地解开一道难题。
大量的计算,重复的试错,不断地积累。这会花上些时间,而这些时间也尤为必要。
“那,晚安。”
欧泊淡淡地说着,合上了门。
菅原以几乎称得上轻快的步调走向其他房间,向礼耶挥了挥手,寻找自己的落脚处。
有些热闹的屋子接纳了她,那位看起来似乎有些难相处的侦探小姐,也并不如看起来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
再说,她还是获得了一句温柔的晚安。
菅原梨纪穿着依旧湿哒哒的衣服,躺在房子里,闭上眼睛,强迫着自己多少睡一会儿。
.
这或许是没那么糟糕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