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在这里哦——”
幸若和花拉了拉姐姐的衣摆,然而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是某种捉迷藏吗?
和花看着努力叫着自己名字的姐姐,不解的歪过头。
“我在这里哦?”
她朝姐姐挥了挥手,还踮起了脚尖。
幸若和成依旧像是没有看到她一样,四处寻找着。
周围乱做一团,有人在安慰和成,也有人和她一起四下寻找和花。
和花抱着手机的几册书,还是那么呆呆地看着大家。
“我在这里哦。”
一步之遥的姐姐看起来越来越慌,冷汗顺着发辫和额角低落。她来回在书架下和窗台边走动,就是不看在她面前的自己。
“我在这里哦……”
从有记忆开,幸若和花的世界总是像蒙了一层雾,又或者说像与别人隔了一池水。她的声音和视线咕嘟嘟地透过某种无法驱散的介质,慢慢扩散折射到外界。有一阵的咕嘟嘟和呜噜噜后,别人有些扭曲的回话和动作再返回到她身边。一切都模模糊糊的,并不真切。
所以她会饶有兴趣地看着蚂蚁一点点把食物搬回巢穴,看蜘蛛慢慢在树枝之间来来回回织一扇网,或是天上的云渐渐流动,最后缓缓散开消失。
足够慢又足够恒定,可以慢慢地透过雾气,把双手和目光落过去,感受得真切。
那些变化得太快的东西,她就没法好好看懂。
光怪陆离,又遥不可及的世界中,和成是她的锚。
只要追逐着她,就能知道自己在哪里,之后应该做些什么。
和花看着已经开始崩溃的和成,周围吵嚷的声音一圈圈随着深海的波纹荡开。
她想了想,开始伸手给姐姐编辫子。
她喜欢给姐姐编辫子。
姐姐那么好的人,当然应该有更好看的发型。把能找到的装饰全部给她,让她变得更显眼也更好看。
而且这么做的时候,姐姐总是看起来很开心。散发着温柔又放松的气息。
和花认真地梳理着手中的发丝,细致地分成三股,再左右交叉。
和成比她高了不少,她要伸直了手才能编得整齐又漂亮——一般来说,和成这种时候总是会体贴地蹲下来,或是坐着,半靠在她身上。
不过没关系。
和花垫了垫脚,把手伸得更直。
或许编完这跟辫子,姐姐就知道游戏结束了,可以不用假装看不到自己了。
她想了想,还把自己的蝴蝶结拆了下来,绑到姐姐头上。
然而下一秒,蝴蝶结又回到了她的头上,自己精心编的辫子也消失了。
和花睁大了眼睛,大脑空白。活像见到比自己还大的鱼的三花猫。
这是什么?为什么?发生了什么?
和成在周围人的劝说下似乎是找回了些理智,在窗台放了一块糕点,和众人一起离开书房。
和花没有多想,只觉得姐姐放了,那必然是给自己的,于是伸手就去拿。
是担心自己会不会饿吗?明明之前才吃了东西。
还在震撼中的和花的脑子只来得及做这个反应,就看到自己的手穿过了糕点,什么都没拿到。
她有点委屈,这是和成特意留给自己的。
是姐姐给她的。
已经是她的了,为什么拿不到呢?
然后她后知后觉,开始慌起来。
和花本能地想到和成身边去,握住和成的手,让和成把自己抱在怀里。
但当她跌跌撞撞跑到和成旁边,拉住了和成的手时,和成也没有回头。
和花看着和成的背景,眨了好多好多下眼睛,看着和成消失在另一排书架后。
姐姐看不到自己了。
她不知道自己在这里。
自己走丢了。
她花了一点时间明白这一点,然后还是那么紧紧地抱着怀里的书——或许这几本书能帮到姐姐——走回到自己最开始和姐姐分开一段距离的书架旁蹲下。
姐姐说过如果走散了就在原地等她。
和花看着书房的天花板,一动不动,一点距离都没有偏。
她眨着眼睛,听着混沌又嘈杂的声音,像是珊瑚礁中的鱼一样吐着只有自己能听到声音的泡泡。
姐姐会回来找自己的。
在这里等等她吧。
姐姐是不会离开自己的。
和花像是对这个理论非常信服,还点了点头。
她看着天花板,一道道数那里的木板的数量,直到自己都有些困,迷迷糊糊打起瞌睡。
忽然,像是突然被从水中被捞起一样,她的五官突然清晰起来。
和花睁开眼睛,双手还抱着那几册书。
她四处看了看,又慢慢沉到自己熟悉的状态中,意识到这里是五楼的楼梯口。
但是比起好奇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来到这里,她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最熟悉的色彩。
“和花——”和成急急忙忙地朝她跑来。
于是所有的疑惑和担忧都随着气泡炸裂消散,她重新找回了自己的锚。
“我在这里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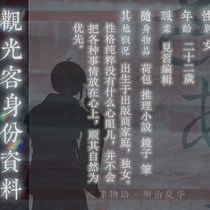


字数:2253
********
(五)
带着明显空洞的乳白色被刨除了。
更细致的空隙中填满人造泪水。
柔软的脂肪被薄刃压出肌理。
热度唤醒已失温的尸体。
粘稠的液体渗入包覆。
是时候摆盘上桌了。
池间纱洋推着餐车。
走道的灯光尚未恢复,成排的边窗揽不着日光,追随她的只有长长投影。
她点了一盏提灯,足够照亮身周,步伐缓慢,并不忙着从投影中逃离——她并没有意识到它们像拔地而起的牢笼,将她的影子框在其中。
地面铺了毯,但总有些铺了线管或年久翘起的地板磕到转轮,每每如此,那些娇气的餐具便用好听的声音细碎地抱怨要磕出缺角啦、要碰出裂缝啦,纱洋因此无暇分心周围。
她经过各式各样的房间。
有人趴伏于餐桌,尖利的刀叉一遍遍割开桌面。
洋馆主人们依旧悬挂半空,漠不关心地看着虚无。
使用人室里的佣人们窃窃私语,打着各自的小算盘。
花园中的蔷薇正开得茂盛,三位贵妇人正在影影绰绰中品茶赏花。
接待室的镜子立在高处,不知是谁扶正它、借它注视过往行人。
纱洋没有追溯它们的源头。她在这片耗费眼力的黑暗里仔细找寻着宅邸的主人,任由形形色色的身影从余光离去。
这不是件易事。
纱洋不会大声询问“您在吗?”,她行动起来总是无声无息,连呼吸也尽量放轻。而鹭之宫显然也不是会在阳台高唱歌剧的类型(如果有别人这么做了,他倒可能为其鼓掌)。
于是当她终于发现他坐在窗边,推车上的餐具已抚平发烫的内心,变得温温热热了。
“鹭之宫先生。打扰了,我带了晚餐来。”纱洋停在几步之外,稍稍欠身。
她的声音有些小,但鹭之宫敏锐地捕捉到了,从她手中接过餐碟:“麻烦您还亲自送来。非常丰盛,十分感谢。”
他身前是三杯散发出袅袅热气的红茶,等待着不存在的主人来取用。
“这空心面和炸肉排同汤水一样,不知是谁做了放在厨房,牛肉和豆腐虽是我等所作,但也是自各处捡来,很是神异。或许有神明在庇护此处吧。”
虽然嘴里这么说,纱洋自己却不大信——娼女与华族、武家同牛郎、警察与小偷、娇小姐与莽汉……他们中的一些都不把另一些当作人,神又怎么会平等地眷顾所有人呢。
可鹭之宫点点头,很是赞同地接过汤碗。
“哎,您说的不错。昼夜变化、时间倒错……如此有趣的世界,只可能是神迹了。”他掀开汤碗的盖子,将几点胡椒粉吹去一边,示意她同坐“‘只是巧合’……您能接受这样的想法吗?”
他看向纱洋。
她本不想坐在他面前:鹭之宫让她想起西洋人的照相机。
她那时候还小呢,穿的还不是这些将肢体拘起的衣裙,做起杂务十分便利。有一回听伙伴们说起有人来给花魁照相了,“把美丽的太夫永远保存起来”,她就偷偷跑去看。
她看见花魁化了隆重的妆,娴静地坐在冰冷房间的正中央。照片馆的人端着个黑乎乎的铁块对准她,郑重其事地比划了好一番,叫她看他。
他会变出一个永远不会老的花魁来吗?纱洋躲在门口,屏住呼吸跟着看。
咔嚓!!
刺眼的白光直直射进她的眼睛!
纱洋觉得自己的视力就是在那时落下了问题。照相机是了不起的东西,但它太刺眼、太冰冷了。若是刀光可见,必定也是那般模样。
什么都有的鹭之宫就像是神的相机。
“我希望这不是巧合。”她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边缘,双手叠放在膝盖上,视线盯着面前的茶盏。它从下午起就是这样冒着热气的了。
“那您想找出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鹭之宫问。
“我也不知道。”纱洋说,而后沉默——她大可临时找一个理由的。
可到真的再张开嘴,她没有改口敷衍过去。“商品与人、贱籍与良民。渡边大人是这样划分人群的。如在座各位是神明——是在更高处的某一位挑选出来的就好了。”
——那渡边康正的评价就没有那么要紧了。
鹭之宫轻轻地笑:“若是挑选的话,各位一定就是神所喜爱的了罢。”
他的笑声中没有嘲弄,更像是孩子看到了杂耍艺人、因新奇而发笑。纱洋更进一步地问:“您呢?您怎么认为……您觉得人该如何分呢?”
“我嘛……虽然这样说有些失礼。”出身华族的公子说着失礼,脸上却没有半点愧色,“或许只分有趣的人,和无趣的人吧。”
纱洋有些听不懂。
她或许该附和地笑一笑,说“这样呀”,就像面对渡边时那样。
她晓得如何让男人们发笑。
【不知道】【竟是这样】【妾身从未听说】
展现出无知便能逗乐男人们,但无知的人即是有趣的人吗?
游女们的腰背没有骨。
男人将它从她——从女人们——身上抽掉,继而以华美的系带取代她们的骨,赞美她们柔软的腰肢。但这是一桩好事吗?
她脊背挺直:“鹭之宫大人,在您看来最无趣的是什么人呢?”
茶盏轻响,鹭之宫的面容隐没在白气后,两边唇角似有似无地上翘,“池间小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一定要说的话,循规蹈矩,只做该做之事,只顺人流行走,从没想过踏出半步……那一类人,便是最无趣了。”
“您所说的'最无趣',正是以世上最多的那部分人的言行所汇成。如果神明以此为标准在做选,也无怪这里只留有这些人。”
“这便是了。既然池间小姐不认为一切只是偶然,就当这里的诸君都是被神明所偏爱的如何呢?”
神明偏爱的不是我。纱洋想。
祂爱那个人,取了他的性命做实现他愿望的代价。
她只是那个愿望罢了。
杯盏里的影像影影绰绰。“您甘之如饴吗?”她看着它,问。
这话从她心底溜到了唇外,于是鹭之宫对此作答,“会变成现在这样,我当然也是吃惊的。只不过这样的怪奇确实难得,不是吗?寻常可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如果无法再从这里离开,您这样的人会有后悔未做的事吗?”
“不。您心中会有列表,列出想要做的一项项事宜么?如果本身就没有那么一张计划好的表格……又要为什么而后悔?”鹭之宫依旧和熙地笑着。
“我没什么好后悔的。池间小姐,您又如何呢?”
【我——】
【沙羊——】
【快!逃啊沙羊!……我的纱洋。】
纱洋也弯起细细的眼睛。
“我不是个聪明人。大概要到真正死到临头,才知道到底后不后悔吧。”
【——您呢,政一大人。您会后悔吗?】

字数:1362
*******
渡边康正死了。
丝毫挣扎也无,这个说“如无亲族父兄可依靠,女子多半沦为玩物”的巡查部长便抛下幼妹死了。
他死得太过轻易、太过仓促,不但不像武士故事里那样勇武,甚至不如身负重伤的田端先生撑得久。
纱洋未见过这样玩笑般的“死”。她接触的大多低贱,死前眷恋的也不过数百枚钱、随便养大的小儿或并不貌美的妻,但即使只是那样,人们也是要挣扎一番的。
惨叫、痛哭、发狂……苟延残喘。
连害了病、全身都烂得不像样的游女也会喊上十几日救命,渡边却是一下便倒在地上。若非他向来是个一板一眼的人,她险些当他在戏耍不告而来的人们。
这死是在人们掀开箱子上的符咒后发生的。没人看得懂那些符,也没人想得到这方正的箱子会是柄杀人刀,谁想渡边会因此在片刻间丧命。
纱洋想,渡边大人或许不是人,而是类似扶摇阁活偶那样的东西。无论在听闻上司田端先生命悬一线或谈论相好的小冬音太夫不死平常时,他反应都万分冷淡,丝毫没有兔死狐悲之意。若他生死也有异于常人,这不把人当人的样子就十分能说通了。可无论她如何尝试,那些符纸都像已凋零的花叶,无论如何也无法回到花盘上了。
渡边康正这便死了?
【我以为,花街是任游人将花朵采颉、亵玩的地方。游人不再,花自然能更自在地开放了。】
——是我们掐下了这支花吗?
可盒子里没有什么诅咒物品,仅有一块损毁得厉害、刻着“康正”之名的木牌罢了。
她跪坐在箱边,远远望着渡边的眼耳口鼻像失了皮肤般冒血、痉挛着呕出许多碎肉。音岛照政在他身上搜寻针对恶疾的药物,衣服下襟很快就染得通红。渡边赠予他的佩刀被丢到一边,捆扎华丽的刀柄上全是原主人咯出的血。曾有力握持过这柄刀的手徒劳张了数下,什么也没握住便僵硬了。
那块牌子也在他停止呼吸时碎成了碎片。
密室里静得可怕,直到突兀地响起一声轻笑,人们才有纷纷商量起要如何收场。纱洋忽然觉得手心疼得厉害,低头一看竟出了血。她木然地擦擦,又抬头往密室门口看——空无一人
——渡边朝颜以后该怎么办呢。
她和她们生来不同。
渡边康正不把贱籍的女子当人,即使有肌肤之亲又极难见到的小冬音太夫,从他说来也不过是“昂贵些的商品”。他既付了游园费做了赏花客,认定这些花纵使生得再美也脏得厉害,理所当然该规矩地任人攀折至烂死园中。
【倘若被赎身、被归还自由,这些植株坚韧地长到了外头呢?】
【那也是盆栽,怎么可能做回人。】
【就算偶尔也好,您养了株漂亮的花,一点也不会想它的过去将来吗?】
【与我无关。】
他会说小冬音是“会因新玩偶而欣喜的小姑娘”,但纱洋很清楚,如果有人说“那和朝颜一样”,他必然是会大为光火的。不必说她也知道,渡边不许朝颜问花街的事,会教她“贱籍与良籍自然不同。花街之事是脏耳朵的东西”。
这小小的武家女挑剔极也正义极了,她性子被养得傲,嘴上嫌着这个俗、那个脏,却又很记得要关心众人惦挂朋友,会珍惜把一看就想到可怖尸骨的友人遗物收好。
昨日纱洋送荷包给她,她还提醒她小心安全。
纱洋问:“那你呢?”
小姑娘挺起胸膛,极是自豪:“有兄长在,小女自然不用担心。”
多叫人羡慕哪。有人结结实实地为她撑着天,叫这株小牵牛花无忧无虑地生长。
*
纱洋望着渡边。
他的血肉已开始萎缩,就如先前所有的死者……就好像,那并不是一具人偶,而是活生生的渡边康正的身体。
可她仍说:“将渡边大人带去找鹭之宫大人吧。说不定将这符贴回去……他便好了。”
他若不好,渡边朝颜又该攀缠何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