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食,依照教师拿来的字典解释,可作为是美味的食物之意。但更多时候,某样菜式会由于出现的地点,还有一起出现的人物而有了深层的意味。在进食的人的记忆里,会成为特殊的存在。一百种人里,总有一百种他们所爱的食物,端看各人喜好而已。有人喜爱简易好取得之物,有人喜欢精致且巧雕之物。
矢口堇吃过许多能称得上美味的食物,父母总说她若肯把此等心思花在女学,便事半功倍。她权当没听见,一股脑地钻进研究食物的学问里。浓厚大骨汤熬出的澄澈汤头、昆布与酱油腌渍的生鱼,用蒸熟的糯米揉制的团子,又或者是红豆熬煮而成的甜汤。更别说是那混杂各式迥异的香料,据说从遥远海边另一侧传来的名为咖哩的料理。
这一日,父母居然是找到了从京都来的和果子厨师替她办宴。
「你这挑剔的舌口,若是哪天让你遭了难,可不痛苦万分啊。」,用手指捏著堇的鼻尖,二姐表情无奈的斥责著她。她们面前是放置著做工精致的和果子,二姐的盘子皆空。就只有她每种都吃一口,却只吃光了喜爱的和果子,其馀全都给剩了下来。大哥一边嘀咕著浪费,一边却还是由著她帮忙吃掉。父亲板著张脸试图教训她,却在母亲的软言相劝中,放软冷硬的神色。
许多美味且珍稀之物,都曾被溺爱的父母和兄姐寻来讨她欢颜。甚至在附近的乡镇里,都能听见她挑剔食物之名声。但这样的堇,也是有几样深爱的小食。
她第一喜爱的是,糖葫芦,那是一种用麦芽糖包裹酸梨的甜食。在祭典的红色灯笼下,外层的糖衣恍若镀上的黄金闪闪发光。就像是她深深喜爱的宝石璀璨而美丽。尽管只需咬下一口糖衣包裹的果实内里,都会让她酸得皱起脸。
但这是兄姐第一次买给自己的零食,她一边嫌弃着酸,一边却又嚷着还想吃。她与亲人在忙碌人群的道路侧,坐在冰凉的石阶上细细品味着买来的小吃。「堇可真是爱吃鬼,再吃下去可要给虫子吃掉牙齿了。」那怕时间过去再久,她还是能记起那时身旁宠溺的大哥与温柔的二姐,带着无奈意味的斥责她。
对此调笑几句后,他们用由于练剑而带上厚茧的手,还有柔细无骨的手掌,握住她的左右侧,在人潮众多的祭典继续前行。掌心所传来的温暖,熨烫了第一次遇见他们慌张的心情。
那是让人嘴里生津既酸甜,却又让人心头发暖的味道。
她第二喜欢的是,那从西洋传来的草莓蛋糕,棉软的蛋糕体外头裹着从天上落下的云朵,装饰其上的圆润果实,就连每个有种子的凹槽都像在发光似的。在那人家中电气提供燃料的灯光下头,美味的果实更勾得人唾液分泌。
外面裹着一层甜而不腻,轻盈到彷佛在舌尖上舞动的鲜奶油。内里是绵密又松软的蛋糕体。最后则是点缀其上的红色果实,轻轻咬下便会在口腔里漫出鲜红的汁液。满足于舌尖的味道,最后喝下浓厚茶韵的红茶。她可以吃下好几块。堇边注视已然净空的盘底,边悔恨刚才的狼吞虎咽。这么好吃的东西,就该好好品味才对。 这小小一块蛋糕,可要价不斐啊。
「若是堇喜欢,那就全部都给你,也未尝不可。」身侧坐著的那人这么说,带着些许亲昵还有说不明的意味。白皙的手臂从宽大的和服袖口穿出,那人的另一只手小心的撩开拿叉的那侧衣袖。不知为何,在其纯黑的瞳孔注视下,她能感觉脸颊彷佛火烧般。那人用银叉戳进自己蛋糕上的红莓,优雅地递到堇的嘴唇边,就像是在玩笑似的触了下她的唇。
白色的鲜奶油沾到了嘴唇,不知为何她乖巧的张开嘴,用颤抖的牙齿咬开细腻的果肉,那甘甜的汁水又再度在舌尖上满溢。无法吞咽的液体顺其自然的滴落,染湿纯白的和服衣襟。她听见了那人带著怜爱意味的轻笑。「像个孩子一样。」
她印象里对于草莓蛋糕的记忆,从单纯明快的甘味,变成隐诲且甜腻,又会让人心头一紧的味道。
由此可见,食物会随吃的人的心情,还有其所在的地点,跟一起吃的人当下所拥有的感情,在回忆里占一席之地。但在这完全分不清日夜之地,伴随著不安与恐惧,再美味的吃食也仅能舒缓一二。
字数1225,一种前情提要。
碧蓝的晴空,偶尔有几朵飘动的白云。枝头啼唱的不同鸟儿,在满布浅色花朵的树枝上跳跃。若是在过些天,便能看见浅草公园里的各色花朵争相开放。待到春季的美景,肯定更让人愉快吧。熙熙攘攘的人群,都在往同一个方向前进。
那栋新建的扶摇阁,便是众人的目标,当然也包括她自己。矢口堇心情愉快的想道。她拎好装满首饰的深褐色小皮箱,与众人不一样的悠闲。和服内衬里用和纸谨慎包好的那东西,重量让人心安。等到见到那人,便能给予这件事一个结尾。无论是好的结局,又或者是坏的。她都会欣然接受,。
尽管昨晚才抵达此处,想在此绕绕看看的心思却在一路上挥之不去。好不容易来到东京,当然得先去东京新地标──扶摇阁一瞧究竟。以崭新的西式风格矗立在保守的东京市区,连里头也是华丽的……似乎是巴洛克风格吧?听说今日还有东京百美人的选拔,她怎么可能不去参加。指不定会有男子为了博美人一笑而掷千金,这可是大好的赚钱机会。皮箱里的首饰就是为这事特意去采买的新商品,无论是仅用平安绳结绑起的圆孔玉石,又或是近期大受欢迎的西洋款式。
矢口家的事业是与洋人进口那些舶来品,稀奇古怪的东西见识多了。甚至由于她的任性,兄长们便偷偷念些洋文书给她听。要是她是男儿身,肯定可以吸收无限广瀚的知识吧。堇有时会这么想,但比起那些虚无飘渺的如果。她更珍惜愿意支持她偷读洋书却不善言词的父母,还有嘴巴毒却比谁都珍惜她的兄长,温柔婉约却总板着脸教训她的二姐。身为女子身的不便还有繁琐的必须学习的礼节,那怕加上女子该学会的一切事务,跟他们根本无法相比。
光想到深爱自己的家人们,她胸口那处便会暖洋洋的。那怕得牺牲些什么,也得让事情往最好的地方发展。她想起游览之后该做的事情,收敛了些许雀跃的心思。但又再度展开明媚的笑容,头上的垂坠丝绸,随着她踩着木屐的缓慢摇晃,布料边缘的红线反射着冬日的暖阳。路过的某些人好奇的停住看几眼,偶尔会投来惊叹却又不赞同的目光。
堇却只是挺起胸膛,继续往她的目标前行。这可是父母亲给予她的年节礼物,全凭她喜好挑的布料振袖。上头的绣纹可都是请最好的裁缝,一针一线绣上。无论是那缀于布料尾端的纤细蛛网,又或者是绣娘仔细绣上的彼岸花。尽管在一些嘴碎的小人眼里,不照他们心思所想,这就是淘天大罪。但一想到今后变数,便觉得能穿喜爱的衣装时,就尽量穿上吧。
无论是擦身而过的家庭,又或者是三三两两的恋人或朋友也好。在这东京就连路人的衣着,都能看见最新的时代流向。就算那群守旧的老头子在不想承认,如今西化的潮流早已推着时代前行。待她走马看花的散步至扶摇阁,那排队的游客早已排到另外一处去。百般聊赖的堇瞇着眼,用手指从上一层层向下数。楼层实数就有13层,比周遭所有平房都来得高耸入云。以崭新的西式风格矗立在传统的城市。
她排在长长的人龙之后,仍然在心里愉快的清点箱子里的首饰。而这时的堇,并没有想到扶摇阁,会比另一处更早成为人生的转捩点。今后的人生,她肯定会无数次想起这个地方,但不知那时她会在在彼岸还是人间,又能否与那人见上一面,或者是直接再也见不上一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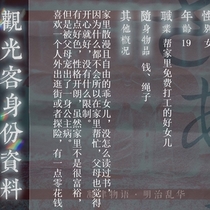
字数:4334
……写着写着,有什么变硬了。哈哈。
***********
(四)
一天又一夜,东京依旧是那副怪异模样,鳞次栉比的住宅被不知何处来的神明拆成积木,东一块西一块地丢到各处,祂对其中存活的小小人类或有垂怜,抛了张包裹皮,将尚未散去的阳光揽在了鹭之宫家的洋馆。
新桥一处则没有那么幸运——也可能是因灯光绚丽,夜色反被忽略了过去——沉沉地矗立在黑暗中。冬日不见虫鸣,夜间也无鸟叫,但新桥全不沉默,高声调笑隔着黑板高墙一刻不停。讨好话、吟哦声、器乐弹唱、男女闲话……说也奇怪,分明有那么多不同,听久了却单调得厉害。
池间纱洋站在墙外出神。
墙内灯火通明,她站在灯光投下的阴影里,身上无有一丝热气。寒气自脚底泛到身上,她搓搓手,呵了口气,往花街里头看:这样刻刻都相同的地方怎么能容人待上二十余年呢?
渡边康正就是此时到的。
他也未持灯,但与黑夜里难以视物的纱洋不同,他一手搭在刀柄上,离得老远就警醒地发觉了她,到离她不远时立住了。
她眯着眼,他瞪着她,先开口的倒是纱洋。
“渡边先生。”她怕鹭之宫,也有些怕渡边,但与面对前者时绷成一线的状态不同,她对上警员的双眼时要坦然不少(尽管对方正以严厉的目光批判她),“这里听上去很热闹。我想问一问,这里有没有其余生还者呢……?”
“当然会很热闹,这个地方每天夜里都很热闹,但新桥是不是正经女人该来的地方,尤其是在这个时间。”
这是句告诫了。
纱洋顺从地点一点头,说,“我是来找您的。听说您会在这一带巡逻,但我实在是不想进去,所以候在这里。”
“……找我?有什么事吗,是同伴又走丢了还是也来问我有没有食物米粮的。”出乎她意料,这位已做到巡查部长的渡边警员丝毫不摆架子,直接就从怀里拽了一本笔记本,一副即刻就要记录的样子。纱洋声音轻,大抵是下意识地,他还弯下了一些腰。
啊呀,啊呀,可靠之人。
“我与另几位先时去了警署,想要寻一寻其他人,但那间警局门口的招牌斑驳,警署内除一位气息奄奄的先生也别无他人。”纱洋将着警服的那人形貌描述一番,“……所以想来问问您,那是否是您相识的人。”
“至少从外见上来看确实是我工作的警署,至于人……我还没空过去探望,但鹭之宫的描述,像是我们署内的松野。”
那么,先前翻找的物品里也有属于他的了。
那支华丽的钢笔?那个放满票据的漂亮匣子?还是那些要投给玉菊小姐的选美券?
其实是不难辨认的。
纱洋把这个人和他的桌子对上了号,“这里古怪得很,我原以为说不定已经不在东京地界,没想还真是您所在的警署。”
“既然知道这里古怪,就应该更加小心,我记得你当时是和音岛一起去扶摇阁游览的吧?那么在出门的时候最好也能和他一起行动。”
的确如此,女性独身一人行动是很不便的,纱洋也是因此才请音岛照政同行。可如今事态非常,已没有那么多可畏人言要扯住她。
纱洋坦然地答他,“您说得对,若碰到什么坏事,我一个人是跑不掉的。”
女子身型弱小、衣裙又不便行动,再者大多终日坐在家中,如被圈养的兔儿一般,往地上摔打一番多半活不了。
渡边大概以为她是全听进去了,神色和缓少许,可纱洋接着又说:“但照政君本身并不勇武,相反,他性格温和细腻,我若时刻留在他身边,他又需得多分心照料我,相互拉扯之间,不是更容易两人一起陷入险境吗?”
她看向他,这是顶简单的算术了,一个人遭罪不比两个人都遇险要好吗?
然而渡边不假思索地说:“他是男人,不分是否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女人都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你也一样……既然已经有了自己的交际对象就不应该独自一人出来和陌生的男人交际谈话,这并不是什么值得称赞的行为。”
这话不对。
男人总有自己的女人,女人们却未必有自己的男人。
纱洋想。
音岛照政不属于她,相同地,她也不归他所有。这是男女间难得公平的买卖,因他俩都是孑然一身,不用将钱财外的东西放到称上。
可年轻的警员怎么想得通呢。他既把女子当作是男性的附属,又怎么能理解是她主动地、就像雇一位保镖、觅一位搭档似的寻了一位男性作陪?
纱洋低着头,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几缕头发落在她耳边,即使捋上去,立即又会落下来。她深深叹一口气,索性拆掉发髻、手指做梳重新理了一番——这几乎是视渡边为无物了——边这么做,她便柔和地反驳了他。
“我已经不是年轻姑娘,此刻也非因抱持男女之情与您搭话。比起我……渡边先生,小冬音小姐现下如何了呢?此处总是夜晚,并非好去处。我有些担心她。”
“她是天弥屋太夫,夜晚才是她最习惯的时间,用不着外面的人去担心。”
弱小的不能担心强盛的吗,习惯了的便能抛去本能坦然接受吗?
夜晚对游女而言本就非是好时光,现今拉成两倍长,就如一朵渴求日光花要在无光处待上更久,如何能不叫人担心?
那位太夫想来也是有些惊惶的,可就如已被训好的笼中雀,她是不会放声叫也不会奋力拍翅的,只微弱地问一句是否留宿。而渡边也就理所当然地、将她的彷徨与担忧全数无视了。
纱洋将发髻重新插回发丛,尖而细的簪尾刺着她的手指,叫她轻微地皱了皱眉,“嘶”地一声将争辩咽了回去。
罢了、罢了、左右这是位好兄长、好警员,之后还得要仰仗他。
“您的妹妹平复些了吗?我记着她被吓得不轻。”
“已经没什么了,不管外面怎么样,家里总归都是安全的。”
纱洋忍不住又看他一眼。
渡边警员身量高,步子又迈得大,丝毫未注意到身边的女性欲言又止。
鹭之宫君的家里可是大变样了,一下回到十数年前。若是渡边家的大宅也有同样变化,小姑娘独自在家不知该有多害怕。
既然听也听见了,纱洋便说:“我有些做点心的手艺。如那位小小姐喜欢甜点,我或可为她做一些。要是喜欢清淡口,酥软味淡的我也会。”
【若是有人能在我哭时给些、不、一小口点心,苦的时候让我尝点儿甜……那该多好】
渡边猛地刹住步子,纱洋险些撞到他身上,一抬头发现正被对方审视着,渡边严厉地上下扫视她,像是要从她身上摸出一把刀。
啊,这也是极熟悉的神情了。
纱洋如此前无数次面对质疑一般无害地微笑,“您想看着我做也没关系,只要有灶台就可以,用料您来准备,不必担心不好入口。”
——若是如此说了,一般管事的人便会满意她的乖觉、继续差使她做这做那了。
可渡边依旧面沉如水,一只手还慢慢按在了刀柄上:“为什么?”
“……?”
“你对我妹妹有什么企图?”
“女人关怀孩子,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纱洋温和地反问他。她的双手规规矩矩放在身侧,仰着细细的脖子与他说话,像是没有一点戒备。
“那并不是你的孩子,总不会告诉我你只是喜欢照顾只有一面之缘的小女孩吧,那等待你照顾的孩子还有很多,为什么选择我的妹妹。”
“这里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呀。何况又遭了大难……”
这位兄长是如何爱护自己的妹妹呀!戒备游人、戒备生人、戒备……根本不放在眼里的人。
纱洋无法否认自己正羡慕那个小小姐,可荒诞感压过羡慕之意,叫她险些笑出声。
她默默叹了口气,将高涨的情绪压下,偏过头去不看他。
“如果您觉得没有必要……也就算了。换作我小时候担惊受怕,想要个人关心也没有。我自己知道那样不好过,好不容易现在有些能做的事了,自然是想用这双手拉其它人一把。我的点心铺子开在乡里,您没有见过也是当然——平日里,我家的吃食也是会分给周遭孩子的。”
一阵沉默。
半晌,如同利刃的目光终于从她身上离去了。
“…………我知道了,只是点心的话应该也没什么关系。等回去之后我会问朝颜的意思,如果她很想吃甜点我会再来找你的。”
“如果有其它我能做的事,也请您不要顾虑。”纱洋小跑着,追他的步子,“生还的也就我们寥寥数人,我必不会束手等着的。”
“现在还有男人活着,轮不到女人站出来。你只要在安全的地方保护好自己就行了,别做多余的事。”
年轻的警员显然不赞同她。可如果等到男人都死绝,女人们又能多活多久呢?
……怕是只多出自裁的时间吧。
纱洋想着、想着,冲他微笑。她是练过这副表情的,乖顺又柔和,毫无主见,毫无威胁。
“那我就做好后勤吧。要是您有衣物需换洗缝补,可以交由我。”
“嗯,虽然并不需要,但缝补修缮正是女人该做的本分,这很好。下次不要再接近新桥了。”
“好,我尽量不独自前来。”
“回去注意不要走昏暗小道,路上遇到同伴就结伴同行。”
”好,我会去拜托照政君。”
“就算是和别人一起最好也不要来,和他人一起进入新桥的女人多半都出不去。”
纱洋渐渐地不笑了。
年轻的警员恍然不觉,仍在说着。
“……现在情况与平时不同暂且不说,女性和丈夫之外的男人有过多交往只会成为在街头巷尾口耳中流传的笑话,以后请多多注意。”
“若是丈夫已死呢。”
“那就应该回归父亲或者兄长的户籍之下待嫁。”
“若父亲、兄长也已身故呢?”
“那就只能投奔叔伯或者远亲了,女人一个人是活不下去的,就算不被卖进花街也只能沦为别人的玩物。”
“……您是说,被作为质押物留下吗。”她问。
“或者是商品。”他补充,“质押物并不多,更多的是被不成器的父兄卖进来的女孩,需要用身体养活家人的女人。”
这位渡边警员——他完全清楚花街的女子是从哪里来的。更清楚她们不是会被赎回的质押品、而是被做了一锤子买卖的消耗品。
“渡边大人,您怎么看待那些 沦为 玩物的人呢?您对她们是什么看法呢。”
纱洋喘息着、叹息着。为跟上他的步子,她走得实在太急啦。汗水要落到她眼里、梗住她喉咙。可她只是埋头跟着,不叫他等、也不去扯他的袖子借力。
长腿的巡警走在她身前,他太高了,成了一堵隔开光的墙,
“怎么看待她们?她们和我又能有什么关系,沦落到那个地方的人都是家里没有可靠亲属丈夫的倒霉鬼,过不了多少年也都会死在里头,与我无关。
“至于里面究竟是什么地方,这不是你该知道的事情,你身边不是已经有音岛了吗。”
我有音岛?
不、不、我有过许多人……我什么也没有。
纱洋的视线模糊着。
“这样的人、若她们有机会重返花街之外的世界,”她的思想慢了半拍,说了一半才醒悟过来,不由得顿了一顿,“……您觉得她们没有这样的机会的,是吗?”
“哼,或许会有吧,成为富商的外室,那是太夫才有的机遇,但是即使在那些人里也有运气不好待到色衰之后回到原来的地方……咳,别问这么多你不该知道的东西。”
渡边的步子逐渐慢下来了。纱洋一点儿也不想追上去,慢慢踩着他的影子调整呼吸。
放轻、放缓、降点儿调子。
“我希望小冬音太夫也能交好运哪。这么美的花,要是因比赛扬了名而更早被折下,未免太可惜了些。”
而这几乎是一定的事。
追捧头名、占有头名、为簪了漂亮的花而炫耀——直到更美的出现,先前那朵便一文不值了。它经过太多人的手,会受的摧残必定要更多。
“会怎么样呢……反正都是和你没有关系的事情。”渡边终于停住步子。他硬梆梆地摘一摘帽子,算作行礼,“夜深不便独处,我送你到鹭之宫家附近就离开——你从这里直走便是。”
纱洋小小地朝他鞠了一躬。
她还是听见自己细弱的声音:“都是女子。”
“良家和贱籍是两回事。”渡边不假思索地答道。
纱洋再说不出什么了。
她捉着自己的手腕,将想握成拳的一只牢牢压着。她太用力了,疼得不行,说话也弱了三分,柔弱又服从。
“这样呀。”她深深地、深深地朝那个背脊挺直的身影行礼,“多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