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正x少女歌剧
文画/主线/强制打卡/
撕卡/投票排名/适龄18+
「在约定之地,
将此花予你。」
报名参与企划前,请先在qq群过审,并且于elf上传人设卡。

第一次见到花道巧实的时候,是在晚上。白鸟还记得雾气带来的幻象,但那不足以阻碍她的步伐。因为信上那么说——因为她被舞台邀请了。
电梯下坠、下坠、下坠至黑暗之底。她曾经和百子一同来到白雾之中,但马上又会和同一个人在这里互相争夺。这是什么讽刺剧本吗?然而,黑暗中的身影是纯白的。白色的制服,白色的头发,唯有自肩头斜过胸前的一道暗红,宛如一个经年不愈的伤口。
“哎呀,你来太早了。对手还没有过来呢,请稍等片刻吧。”
白色的少女连语气也和雾岚一样。白鸟看向那双眼睛,警惕地轻声问:“你是谁?”
“不必紧张,我只是一个恰好在此,也仅能在此的观众罢了。如果非要找个称呼……我想,我该算你的「前辈」吧。”
以这句话为开端,花道巧实讲述了她的故事。失忆,top star,只出现在地下舞台……听起来就像是地缚灵。白鸟没有把这个猜测说出口。失礼只是小事,她不想冒更多的风险。而且,面前的少女可能会伤心吧。最后她只是试探着说:
“前辈身上的绶带和我的很像,但是没有披风啊。也没有武器。”
“是啊,也许这个舞台认为我不需要它们吧。”仿佛洞察了她的想法,巧实随口说,“怎么了,想和我打一场吗,小白鸟?”
“我当然也很想受到top star的指点。”白鸟说,“但不是现在。说起来,在我们revue的时候,前辈你在什么地方?”
“我会在观众席看着学妹们的精彩表现啦。”巧实的语气依然很平和。
“那我会努力的。”
听到白鸟这句话,巧实忽然笑了。但已经到了离开的时候;电梯正在缓缓下沉,舞台将为两名时花三期生拉开幕布,过去的影子就该退场。她们明明只相差不到三年,却隔着一整个舞台的距离。
嫉妒的revue、炎天的revue、无常的revue、戴冠的revue、业火的revue,白鸟每晚每晚都在地下舞台,与不同的少女们战斗着。但在最后这个晚上,她似乎比以往更加平和。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她还给巧实带来了一份和果子。
“啊呀,承蒙学妹关心了,但我恐怕配不上这份好意,请收回吧。”
即使听到这样的回答,白鸟也没有气馁的样子。她把盒子推给巧实,说法相当狡猾:“那么请前辈帮我拿着吧。今晚还希望前辈指点一下我。”
确实是不能拿着这个打架。和果子的表面雪白如牛奶,不知道里面包裹着什么样的馅料。巧实接了过来,笑着回答道:“呵呵,那我就替学妹暂为保管吧。不过,我不擅长教人哦?”
“我会试着在战斗里学到什么的。”
那确实是在五天的战斗中学到了什么的眼神。与她所获得和失去的闪耀无关,完全是在与他人的碰撞中,逐步磨砺出自己的形状。
“可以啊。既然你想要的话。”
于是白鸟心满意足地向她挥了挥手,钻进幕布之后。
巧实的双眼映照着舞台上的灯光。她明白这场revue中,两个人都没有打落彼此的面具,触碰到各自的内核——至少白鸟的秘密还好好地保留着。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白鸟在走到她身侧时,依然保持着笑容……甚至在道谢之后,把自己带来的和果子吃掉了。好像完全不担心长胖似的。这大约也是十几岁少女的特权……哦,从她咬牙切齿的表情来看,倒不是在享受美食,大概是觉得没打过瘾。小战斗狂。
白鸟舔了舔嘴唇,擦掉鼻尖上的一点白色粉末,目光炯炯地看着巧实。后者善解人意地去挑了一把胁差,如果要教学的话,还是相同的武器比较好吧。隔着一段距离,两人如同镜中倒影般对彼此行礼。小步舞曲在空旷的舞台上响了起来。
虽然平时完全没有架子,但一旦到了台上,花道巧实的能力就显露无遗。声乐、舞蹈、演技,每一项都是完美的。如白鸟所愿,这场revue……该称之为revue吗,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表演。但是,果然……没有什么手感。就像是在和精致的人偶共舞,虽然毫无差错,准确无比,却无法触动自己的心灵,也不知道对方是否有心灵存在。
舞曲停下来的时候,白鸟在巧实面前站定,胁差倒持在自己的背后。
“就到这里吧。非常感谢你,前辈。”
“你不想要胜利吗?”巧实歪了歪头。
“不。我想要的……只是一场与胜利无关的演出。”汗珠滑下少女因剧烈活动而染上绯红的脸颊,在灯光下闪耀得仿若小颗的钻石,“谢谢你一直在观众席看着,前辈。今后也请继续注视我。”
她玩味地笑了笑,说:“……好噢。”

双簧管在黑暗中奏响了柔和的曲调,如同一层层水波在空气里散开。白色的灯光打在舞台中央,在湖水中心,青绿发色的少女身着层叠白羽般的舞裙,朝舞台的一侧看去。另一道灯光落在金发碧眼的英雄身上,长袍自她的肩膀坠至地面,却不可思议地被风吹拂起来。伊塔卡岛的王、攻破特洛伊的英雄奥德修斯向天鹅伸手,要她行至自己的面前。
「你是一位水泽仙女,一名公主,又或者一个精怪?无论如何,让我们来跳一支舞吧。」
「您大可以把我当作一个共舞者,正如我看待您一样。」
天鹅缓步而行,足音与节拍令人惊异地一致。她牵住那只手,旋转、旋转、旋转至舞台中心,灯光亦步亦趋地跟随她们,照亮两人脚下波光粼粼的湖面。明明是初次起舞,动作却格外默契。舞曲舒缓而优雅,每踏出一步,足下就升腾起蓝绿的荧光。然而这时,幕布之后传来巨响。奥德修斯抬起头,发现天鹅的脸上并无任何惊奇之色。
「我的共舞者,恐怕我必须要走了。神祇们终于决定放我归返家乡,那就是催促我出航的雷声。」
「我们的舞并没有跳完,我的共舞者。在某一天,我会来索回它的。」
天鹅行了一礼,自舞台一侧转到幕布之后。湖面之下升起了一艘帆船,帆布鼓起,而奥德修斯就立在船头。魔女喀耳刻的声音自空中传来,仿佛殷切的叮嘱:
「我会告诉你如何顺利返乡。这一条海路高耸着两道崖壁,天空一直浓云密布,不见阳光。崖壁上的洞口中,有一名丑陋的海怪盘踞。你要迅速地通过那里,并为她献上起码六名人祭。」
「难道非要舍弃我的同伴不可?」
「这比全体灭亡要好得多。」
奥德修斯垂下头,仿佛思考,仿佛顺从;帆船在海面上移动着,旋律忽而变得沉郁而紧张。崖壁自两侧压来,然而,高处传来的是歌声。英雄附耳倾听,不由得感叹:
「这就是那凶恶的海怪所在之处。可是,真奇怪!这歌声如此悦耳,有如泉水,有如酒浆。」
悠扬的歌声停了下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开始说话:
「我原本不是海怪,是海神的众多女儿们之一。喀耳刻诅咒了我的形体,使我处在无尽的饥饿之中,无法再与你起舞。」
奥德修斯抬起头,朝空中看去。天鹅掀开半片幕布,露出她纯黑的裙裾。英雄将一只手按在自己的胸口,毫不犹豫地说道:
「无论是一支舞还是一条性命,若是想要向我索取,你便下来吧。」
「那正是我所想的。」
天鹅应声而落,奥德修斯却拉开了腰侧口袋的系带。风声呼啸而过,海水几乎倒卷起来,崖壁上的浓雾也尽数散去。金发的英雄眯起眼睛,启唇一笑:
「这袋子里是风神的狂风。」
无法平稳地在甲板降落的黑天鹅回以笑意,双眼仿若红宝石的切面。
「而你是个狡猾的人类。」
这下黑兹尔真的笑了。属于英雄的长袍在狂风中散开,精致的徽章轻击出声,苍绿的后摆猎猎作响,斜扣在左肩的墨黑外套上,有一点金色的星光闪烁。
“无法让手之物、无法回首之途,愿天佑荣光、屹立于万千之上。时花三期生、黑兹尔,让你看见这新生的我!”
黑色从天鹅的裙角褪去,化为深蓝,如同羽毛根根剥落。外套在风中危险地鼓动着,仿佛下一刻就会被强风吹开。然而,渊上白鸟仍然保持着笑容。
“于深渊之上、展翼之时已到。即使迎来泡沫之梦般的结局,时花三期生,渊上白鸟——我必须歌唱!”
杖剑出鞘,与自上方披下的胁差相击。对彼此而言都是一次试探——因为白鸟飞快地拉开距离,借风远遁。
“这不是个好位置。”她说,“如果风不停,你的船会沉没的;如果风停,那便到了我的时刻。”
“想掠夺的话就凭手中的武器来厮杀吧。”透过那片明净的玻璃,黑兹尔对上她的视线,“稍有不慎,你那美丽的羽翼就会被我折断!”
“你这狂妄又可悲的家伙。”白鸟眯了眯眼,“我会切开那些飓风,将你的血肉作为我的食粮。”
她们,毫无疑问,仍然在戏剧之中。若是说白鸟正与黑天鹅共鸣的话,黑兹尔便是奥德修斯的化身。白鸟只是一个转念,便从原典中找到了答案。
……是这样啊。你在思念着某个人,期待与她重逢啊。如同佩涅罗泊之于奥德修斯的存在,那份感情正是你站在舞台上的原因。
而对于白鸟来说,从头到尾就没有过那样的人,所有的路都必须一个人走。事实上,恐怕没什么比黑天鹅的故事与她的人生更加契合了。说着谎言行走在无底深渊之上,展开翅膀竭力飞行,但那只是对坠落的延缓。她总会有坚持不下去的一天。像用有毒性的药物吊命的重症患者,深知耳畔每一秒时钟的滴答声都是生命的倒计时,却不知道真正的终点在何方。
幸好黑兹尔不知道。但,这反而使白鸟感到不太爽快。明明应该看向她的对手,如今却望着更遥远的地方,简直就像自己没被放在眼里一样。
乐曲声忽然缓和下来,白鸟潜入风中,将呼吸埋藏在风声里。黑兹尔一个分神,便失去了她的身影。下一秒,白鸟已经出现在她的身后,轻柔的吐息拂过她的耳廓,仿佛一个逼近的幻影:“不注视自己的共舞者(共演者)是失礼的。”
黑兹尔斩向身后,刀刃刺入空气,没有任何实感。白鸟好像只是为了说那一句话而来的。但她究竟是怎么——黑兹尔抬起头,看到在风中鼓满的帆布。恐怕,她是从桅杆的顶端一路滑行下来的。但要那么无声无息,恐怕只有幽灵可以做到。
狂风骤起。水面翻起了滔天的巨浪,海水翻卷涨落,仿佛一场暴雨。即使在这样的雨幕里,黑天鹅也依然没有显现她的形体。奥德修斯拉紧束带,帆船顺风而下,越过重重大海,停泊在故乡的岸边。
——然而此处空无一人。城堡已然倾塌,城镇也化为废墟,仅有经年不息的雨幕降下。
太阳不落。
太阳不落?
凉意忽然抵在她的颈侧。锋锐的刀刃闪着寒光。幽幽的声音再度穿行在她的耳道中,潮湿的几乎滴水,让黑兹尔整个人后背发凉。
“……你回来得太晚了。”
已经没有人认识奥德修斯。
黑兹尔条件反射般地挥剑。只差一点,胁差便会切断她的穗带。白鸟在她颈后轻声叹息,但听不出失望。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必须守住这份闪耀。”
——为了创造出让彼方的你也能看到的舞台。那正是黑兹尔一路战斗的原因。
“原来不只是我,”那个身影一瞬间就闪到了她面前,红宝石的中心是不息的火,“你连自己都没有看见。”
咚!
白鸟的额头撞上了黑兹尔的。不痛,但是让人相当迷惑。她们再次刀刃相交,不疾不徐,落剑如雨,仿佛一场耐心的拉锯战。这样的交锋看一会儿还算得上享受,但越久就越显得无趣,就连乐曲的声音都停了下来。空旷的舞台上,只有金属相撞的声响。
——终于,胁差脱手而出,远远地落在地上。白鸟仍旧保持着原来的力道前冲,以至于一个趔趄,向地面摔去。杖剑斩断穗带的同时,另一只手接住了她的手臂。披风滑落于地,白鸟近乎跪倒,却终究借着他人的力度站直了身子。她的对手在想什么?她垂着头,想起一件之前发生的小事来。
那时她的心情很好——或许太好了,以至于边在口中哼着歌,边在低矮的护栏上蹦蹦跳跳,连路过了一名外国同学都没发觉。单镜片的金发少女扭过头去,她不知道那是不是一声偷笑。因为看不到对方脸上的表情,所以无法触及内心。就像现在一样。
然而,与她共享人生中数小时的共演者的声音从上方传来:“……辛苦了。”
常夏院咲常的耳边响起叮叮咚咚的声音。是水声?她疑惑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确实置身于一个洞穴里。有几枚水珠滴到她的脸上,冰冰凉凉。此外,好像很遥远的地方还传来呼喊她名字的声音。咲常,快点——
她站起身来,往那个方向走了一段。忽然,她听到了响亮的敲击声。仿佛金属撞击金属,铁镐深深地凿进石头。这么说起来,为什么她能看清周围来着?她吹开自己长长的刘海,抬起头来,看到洞顶投下一块块亮光,随着敲击的响声明灭,仿佛跟随着某种韵律。那些发光的斑点好像是小小的萤火虫,却安静而沉默,不会发出任何振翅的声音。敲击声越来越清晰了,她追着声音走过去,发现一名戴着纯黑安全帽的矿工正努力地用镐子敲击着地面。哦不,更正一下,那不是安全帽,就是她的头发。是同寝室的黑川十六夜!咲常安心起来,虽然是在这种古怪的地方,但一想到十六夜也在,就感觉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被十六夜扛起来带着跑的时候她也这么想。
这样移动起来虽然很快,但颠得有点晕,是不是该麻烦十六夜停一下呢?说起来,为什么十六夜一直不和她说话?咲常眯起眼睛,感觉自己终于在一阵颠簸里停了下来。清晰一些的视野里映出粉色头发的边角——是锻屋火花!她还来不及打招呼或者道谢,十六夜就将她放进了一个比人还高的大锅里。哎,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把盖子盖上了?火花满意的声音在外面响了起来:“谢谢你,黑川。找到这么好的材料,还给我带了过来。”
什么?原来是作为材料吗?不好了,要被煮熟吃掉了!咲常敲了敲锅盖,又听见十六夜的回应:“太客气了。你可是这里最出色的锻造师。”
……还不如被吃掉啊!如果煮汤的话,没准还能因为有水而浮上去呢!
仿佛听到了她内心的呼喊声,耳旁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曾经滴到她脸上的水珠,变成了一条湍急的地下河,轰隆隆地朝她直冲过来。大概是因为被装在锅里,咲常竟然毫发无伤,反倒在水面上漂流起来。在天旋地转里,她好不容易适应了船(船?)的摇晃,伸手想要推开盖子,却发现它很重。有点想要放弃了,可是,缝隙间突然透出一丝光亮。有什么把盖子打开了!咲常一时间十分庆幸,然而下一秒,她就觉得自己受到了命运的玩弄——因为一条腕足忽然伸进了锅里,将她的身体卷了起来。一只庞大的鱿鱼与她四目(四目?)相对。她尖叫一声,终于醒了过来。面前,是同寝室的同学们担忧的脸。
原来不是鱿鱼,只是乐乐浦世凪。咲常猛地松了一大口气。
“咲常同学……”世凪的声音幽幽地响了起来,“醒过来了,真好哟。我们已经带着睡着的咲常同学一直走到走廊了。还有一段路,就能走到了哟。”
就在咲常觉得噩梦已经结束的时候,教学楼里忽然响彻了上课的铃声。
“——快跑啊!!”
今天的revue已经结束了,对谁来说都是如此。白鸟随手擦了一把脸上的血,满手满身都是粘腻厚重的触感。很快,它们就凝结成干硬的血块,并在行动间剥落下来,露出少女的皮肤与时花校服的装束。落到地面上的红褐血块被风一吹,就碎成了尘土,只有鼻间还有淡淡的腥气。
她走出电梯时,与爱娃打了个照面。一贯以微笑遮掩傲慢的少女表情很糟,皱着眉头、紧咬牙关、眼中燃烧着熊熊的愤怒,却又因此格外真实。
“你这是在生什么气呢,爱娃同学?呼吸都乱了。”
白鸟收敛起自己的心情,虽然愤怒还积在心头,但与雨彼此斩下纽扣的时候,郁结仿佛舒缓了一些。现在她还有余力去观察爱娃的状态——绝对是在舞台上、revue中消耗了太多的精神,对方的手指还在微微发抖,呼吸也乱了,光是站着好像就已经用尽全力。
爱娃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还没来得及调匀气息,白鸟就开口道:“去湖边坐坐吧。你也不想这样回去面对室友吧?”
虽然白鸟不知道她寝室的情况,但骄傲如爱娃,应该不会允许自己在谁面前如此失态。白鸟自己是个意外,不过见其他人是可以避免的。爱娃阴着脸跟了上来,走得很慢,白鸟配合着她的步子,一路走到湖边的长椅前,善解人意地给爱娃留出时间,直到她拼凑起自己已经破碎的面具、重新戴上:“啊,刚刚还真是失礼,没能及时恭喜渊上同学顺利完成舞台。”
“我输了哦。”白鸟无所谓地说,“但对方也没赢。”
爱娃噙着笑意,却怨气深重地开口:“要知道有的时候赢了也同样……窝火。”
“没有人比现在的我更清楚,在更重要的事面前输赢没什么意义了,所以你就继续生气也没关系。”白鸟转头看向她,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不如说,不笑不也挺好的吗?”
这下爱娃脸上的笑容真的消失了。她压着唇角沉默了片刻,才说:“记得你当初向我宣战的时候,曾说过,我自视为神……你问我有没有见过自己燃烧的样子。”
那时她们几乎才刚刚入学。白鸟那时还称得上年轻气盛,既然已经看出爱娃的笑容只是面具,就直接点破了。
——你的性格该不会其实超恶劣的吧。
——呵呵,这是哪里的话……眼神这么坚强,可以给满分,但是好像……渊上同学,你很不愿意直视我吗?
——是你没有直视过其他人吧,爱娃同学?倒不是说这是什么坏事。只是我这边……如果直视你的话,恐怕会有点失礼。……会忍不住想,谁能让你从王座上坠落下来啊。
——王座。好新颖的比喻。但请别误会,我自始至终无意让任何人对我俯首称臣……至于“直视他人”,我想我很乐意看到这些孩子燃烧。因为他们能在我的舞台上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那仅仅辉煌了一瞬间的火光……然后成为我的养分。
——原来不是王座,是神座吗?你比我想的还要傲慢。但你和其他人一样,都只是人类罢了。爱娃同学,你有看过自己燃烧的样子吗——为什么这不是一场互食的盛宴呢?
——倘若你执意要把我放上一把椅子,那么可以。当然,你我在舞台之下都是人类。虽然从不觉得鸟儿那孱弱可爱的翅膀可以掀起什么波澜……但我承认我期待着。我将在舞台之上,等待你见证我的燃烧。
那如同戏剧一般的对话,至今仍然在白鸟的胸中回荡。
“我的火焰烧得比任何人都旺盛,明亮,只是……我现在却开始思考它终有一天要熄灭时的样子。”爱娃轻声说,“或是,我还能自由地挥霍它的光热,纵情燃烧直到熄灭吗?”
白鸟抬起头,看向仍然站在长椅边的爱娃:“你在害怕吗?”
“我绝不会!”回答离提问超不过一秒钟,“……或许,只是有点可惜。”然后爱娃又补上:“……还有一点不甘吧。”
“……你现在完全就是前两天的我的样子。”白鸟想起三津枝出现在背后的那个晚上——那也是在这个湖边。她的语气柔和了一些,甚至有些怀念。
“你在说我是过去的你?哈,真不知天高地厚。”爱娃猛地看向她,双眼又亮了起来,话语中再次生长出扎人的刺。
白鸟有些想笑:“怕寂寞的话直说比较可爱喔?”
“谁怕寂寞啊!把我拉到这里来吹风的人明明是你吧!”爱娃坚决地否认完,灵机一动地勾勾下巴,“还是说……其实你的心里也很不舒服?给你个机会,要不要我勉为其难借你怀抱哭一场?”
“精神恢复得不错。至于另一件事嘛……”
白鸟扯出一个微笑,站了起来。爱娃没想到的是,她忽然几步跑到湖边,对着湖面大喊起来:“我当然——不甘心!!”
声音传出很远,仿佛在水面上打出一个漂亮的水漂。爱娃沉默了一阵,跟着走过去大喊道:“自大的家伙真是讨厌死了!!!”
心里的郁气仿佛被吐了出去,新鲜的空气涌入肺里,带着湖水的清凉。白鸟忽然抱住了她,并在爱娃怔住的时候,小声说:“干什么骂你自己?”
这下就不是怔住而是僵住了。趁爱娃还没有恼羞成怒火冒三丈,白鸟连忙忍着笑拍拍她的背,不再思考这个表情是不是值回票价,开口问:“哎呀,总之,你喜欢表演吗?”
“当然。喜欢,非常喜欢,绝对不会输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喜欢。”爱娃的回答和任何一个表演者一样毫不犹豫。她是为舞台而生也愿意死在舞台上的。因为所有的光和热都汇聚在她身上,鲜花与掌声只献给成功者。所以,她一定要成为太阳。哪怕在自己划定的圈内,如同穿着被诅咒的舞鞋一般无尽地跳下去。
“那样的话,你就会把自己重新点燃。倘若你爱一团火,一定也会爱她摇曳、闪烁、爆裂、熄灭的样子。”白鸟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仿佛这段话已经在心头思虑过好久,因而可以不假思索地流畅吐出。
爱娃哼笑一声:“安慰人的本事真烂。放心吧世界上不会有人比我自己更爱我。”
“哦。你被安慰到了。”白鸟放开了她。爱娃直视那双红色的眼睛,没有否定,只是一字一句地说:
“告诉你吧……要永远为现在的自己感到自豪。”
白鸟停了一瞬,无奈地笑了笑:
“倒是你……偶尔也听听别人的声音吧。”
今晚我们不跳舞。我们在湖水的四周漫步。沉睡的天鹅不会歌唱,所以夜晚静默,乐音几近于无。两枚朱红的星星,可以栖息于深蓝的夜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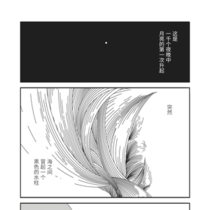

嫉妒的revue结束了。然而,对白鸟来说,麻烦才刚刚开始。
自从在地下舞台不欢而散之后,百子就一直想办法跟着白鸟转来转去。白鸟同学、小白鸟、白鸟同学,她这么亲热地喊着白鸟的名字,要不要一起去逛街、种花、或者喝下午茶?她抛来无数的邀请,白鸟尽量用班里的工作、学生会的工作、日常训练、和其他人的约定推了回去。然而,百子和她同在樱班,又同在学生会,能糊弄寻常人的办法,没办法瞒过她的眼睛。何况——百子的姓是九条。就连那个速水令,也不会想和她交恶的。对华族们来说,这样反复的拒绝已经相当失礼了,即使是最迟钝的人也能感觉到,白鸟不想与百子多加接触,可惜,百子并非是那么容易放弃的性子。她跟在白鸟身后,在白鸟工作的时候坐在一旁撑着脸颊,偶尔试图插话,烦人得让白鸟几次咬牙。不过,在搞清楚这部分的工作流程后,她就变成了助力。拜她所赐,白鸟的工作完成得早了不少,感谢的话刚刚出口,百子就牵起她的手,高高兴兴地问,那现在可以去喝茶了吧?
白鸟失去了所有拒绝的理由,话未出口,已经被她带去了湖边的小筑。白鸟眼看着百子拿出一个茶包,对路过的创造科同学甜言蜜语了一阵,对方就变魔术般地弄来了热水、茶壶和茶杯。无论多少次,白鸟还是会感叹,这真是天赐的才能。茶壶被摆在桌子中央,热水带着蒸腾的雾气落进壶口,没洒出一滴来。纤细的手指捻开茶包,丝毫没碰到其中的茶叶,就将一纸包全都洒了进去。因为道具简陋,茶道的礼仪也省去了许多步,白鸟只见那些深褐的茶叶在水中展开,是无数萎凋的新芽。百子盖上盖子,茶香却从壶嘴中漏了出来。这下就更不是白鸟平时会喝的那种了;她仔细闻了闻,辨出一丝麦芽的香气。
“是从欧洲带回来的红茶。要是小白鸟喝得惯就好了。”在等待茶泡好的时间里,百子先笑盈盈地开了口。
“谢谢你的邀请和招待,九条同学。”在没有第二个九条同学的时候,白鸟依然如此称呼。
“怎么还叫我九条同学……要怎样做小白鸟才愿意为我敞开心扉呢?”百子又撑住了脸颊,粉色的指甲边缘齐整干净。
“我不明白九条同学在意的事情是什么。”白鸟平静地回答。这句话如果说得重一些,就是“那和你没关系”了。
百子没有再纠正称呼,反倒以撒娇般的语气开口:“我想更了解小白鸟的事!”
“九条同学。”白鸟深吸一口气,努力把丝丝缕缕的烦躁压下去,“你知道之后要做什么呢?”
“当然是帮上白鸟同学的忙呀!”
她这话说得太过自然,让白鸟愣了片刻。百子拿起茶壶,向两个茶杯中倾倒下浅红的水柱,液面的翻涌尚未平息,却比一旁的湖水更加夺目。
“就算帮不上忙,有能够倾诉心事的人,也会变得轻松一些哦!”
听到这话,白鸟几乎已经维持不住脸上的表情,只好拿起茶杯遮掩:“实际上并不会。”
百子不依不饶地问:“那小白鸟曾经有把心事告诉过别人吗?”
白鸟点了点头,抿了口茶。仿佛被鼓励了似的,百子欢呼起来:“诶~~那多百子我一个也是可以的嘛!”
“是我母亲。”白鸟放下了茶杯,“没有别人了。”
百子看起来更期待了,眨着眼睛,颤动的睫毛仿佛那双浅色的虹膜更加清澈,清澈得像无云的蓝天:“是妈妈呀……妈妈和朋友当然不一样啦!朋友的话,说不定可以一起讲更多不好在妈妈面前讲的话喔?”
“有一些事是谁都不能说的喔。”
虽然白鸟已经尽量露出笑容,但仍然无法抵抗翻涌的记忆。百子失望地拖长调子,然而,白鸟已经没有回答的余力了。她又想起自己跪在母亲面前的那一天。自己的声音在耳边回响,凄惨而恐惧,却又不敢放大声音,以免传进谁的耳中。
——求你了,我不想做,告诉他们吧,妈妈,我不行的,真的不行!
而母亲只是抚过她的脸颊,带着一点温柔的笑容否定了她。
——说什么傻话。这都是为了你好。
她后退一步,躲开了那只手,身体因为某个想法而开始打战,就像赤身裸体地走进冰雪之中。
——妈妈,难道,是你……
母亲再次微笑着回答了她。
——说什么傻话。
“如果说出来的话我就会死你也要问吗?”白鸟忽然毫无预兆地开口,将茶杯抬到唇边,饮下一口滚烫的血液,随后才找补道:“……开玩笑的。”
“欸欸~~那样肯定不会再问啦。不过如果是我知道以后又告诉其他人的话我就会死,就没有关系哦?”
真不知道她是大胆还是怎么样。白鸟想了想说,很遗憾没有那种实用的东西。百子拉着长长的尾音说她好无情,白鸟才慢慢地补充道,当然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我也不会说的。然而百子仿佛受到了感动一般揉了揉眼睛,开口说,真是好人呀小白鸟……白鸟终于叹息了。
“你见过死人吗?”
“嗯……见过哦?你是说在眼前慢慢死掉的还是已经死掉的?”
这一刻她不像平时天真烂漫又无忧无虑的百子大小姐,反而只是九条百子。白鸟凭直觉就知道,她没有说谎。于是白鸟又问,是认识的人吗?百子用看过很多死人的口气回答,唔,都有啦。不过都不算是很熟悉的人就是了。不知为何,白鸟有些遗憾,却又松了口气。她说:
是很熟悉的人。这下百子终于安静了下来,看了看白鸟的表情,忽然站起身来,手臂越过桌子摸了摸她的头发,语气温柔:“那个人一直在以另一种方式,守护在小白鸟身边哦。”
——你怎么能这么笃定地说?白鸟几乎想要站起身来,打碎茶杯,然后高声怒吼。明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局外人!但她只是僵硬地坐在原地,反而是百子看到她的表情,担忧地收回了手:“对不起喔……我好像说错话了……?”
白鸟站了起来。天知道她是怎么逼着自己挤出“已经可以了”这句话的。在百子说着“斯人已逝,我希望小白鸟能早点走出来、希望能看到开开心心的小白鸟”的时候,她已经转身走开好几步。即使听到百子喊了一声“——啊!等等”,也没有停下的打算。
百子看着那个背影,放开嗓子大喊:“小白鸟!!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没有人会责怪你的!!!!”
理所当然,白鸟没有给出任何回应。少女的翠色长发束在头顶,随着她的脚步来回摇晃,如果披散下来的话,便是缠绕半身的群青囚笼。

“这位美丽的小姐!你叫什么名字?你有灵魂吗?你能够爱吗?”
听见这宛如戏剧般的问话,白鸟愕然地回头,确信金发的陌生女同学是在向自己搭话。她只是和室友三津枝一起走近了后者所在的龙胆班,并打算继续朝樱班的方向去,但完全没想到会被不认识的女同学——呃,拦路抢……戏。三津枝叹了口气,悄声向白鸟说:“这是我们班的鸳一花溪同学……恐怕又掉进剧本里了。”
确实是十分出色的演技。白鸟看向花溪,明明穿着与她的台词毫不搭调的院服,举止却仿佛一个挥着彩旗或鞭子的马戏团长;她的手里没有任何东西,单纯是靠表演使观众产生错觉。需要相当高深的技术,才能将身体的每一个动作控制到如此细微的地步。
“我是从蛋里孵出来的。”白鸟试图跟上她的步调,尽管收效甚微,“有人叫我奥杰塔,也有人叫我……丑小鸭。现在,秋天来了,我需要去往温暖的南方。”
三津枝从这个走廊中的暂时剧场退开时,百子恰好走了过来。她饶有兴致地从白鸟背后看过去,只在白鸟倒退着即将碰到她时伸手扶了一下。白鸟一时十分尴尬,毕竟“我是从蛋里孵出来的”放在现实中,只会让人怀疑大小姐的脑子是不是有点不对劲。毕竟她是班长,是渊上白鸟,不会把这种带着荒诞性质的玩笑说出口。
“真巧,我是从地里长出来的。”百子高高兴兴地走上前去,“我也要去南方,冬季可不适合花儿生长,我可不想在我的尖刺上,扎上一枚夜莺的心脏——要和我一起走吗?”
白鸟松了口气。毕竟,只要其他人不觉得尴尬,她就也可以不觉得。然而,花溪忽地朝百子伸出了手,而百子一手拉住花溪,一手挽住她,就这么飞快地在走廊里奔跑起来!
“现在——我们坐上了飞箱!”
百子跟着花溪的解说适时地发出欢呼,而白鸟看到了更加让人不安的东西——不行!为什么经过水仙班了啊!如果说全时花哪里有最多的贵族派,恐怕就是那里了!她急急地朝另一个方向转弯,然而在回身之前与因脚步声而抬头的爱娃对上了视线。金发下的紫色眼睛眯了起来,带着让人惊心动魄的笑……那家伙绝对在打什么坏主意。
然后白鸟意识到,自己面朝的是芒班的方向。会长和副会长为了查看是谁在走廊上奔跑,起身走到了门口——糟了,这下完全糟了!现在挡住自己的脸还来得及吗?三津枝没有加入这个狂奔的队列,真是有先见之明……她们一定也没有想到,会看到书记和执行委员长毫不淑女地踩在违反校规的一角。等一下,副会长,为什么手里还拿着摄影机啊!白鸟彻底熄了停下来向会长解释的心,跑得比原本领路的花溪还快,活像只真正在躲避冬天的候鸟。以这样的速度,摄像机即使开着也只会留下一片残影吧。她们在拐角处停下,听到没有脚步声追过来,才终于开始大声喘气。
啪!一束彩带忽然在旁边炸开。百子和花溪只是惊讶,白鸟却有点吓得魂不附体——好在,走到她们身旁的不是哪个学生会成员,只是芒班的黑羽狂夜。
“真是看到了很有趣的表演——能不能让我加入你们?”
团长还没出戏:“当然!马戏团欢迎每一位演员与观众!”
“你在恐惧什么?”狂夜向白鸟点了点头,又遥遥地指向人工湖,抑扬顿挫地念出剧本的台词,“可是,我却恐惧那哈利湖边,卡尔克萨立于遥岸!*”
不知道是谁敏锐地发出一声尖叫:“等等!这个可不能念啊,黑羽同学!”
*《黄衣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