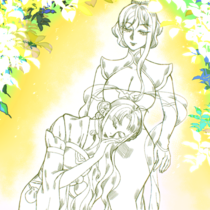「仗剑当空千里去,
为天且示不平人。」
基于《山海经》及相关国产古风单机游戏为灵感的仙侠企划。
玩家可创作门派弟子、村人、或是与其为敌的妖族,经历仙门日常、人妖纷争、仙门入世或出世等一系列主支线故事。
掌事嬷嬷们鱼贯走出房间,太阳的光影在她们脸上明明灭灭。李嬷嬷走到廊柱旁,压低声音对张嬷嬷道:“你瞧出来没有?曦月小姐近来行事,越来越有当年老太太的风范了。”
张嬷嬷回头望了一眼那扇合上的雕花门,轻声应和:“谁说不是呢?年纪轻轻,人情世故却这般通透。查账时一丝不苟,处置怠慢的婆子时恩威并施——谁能想到一年前,她还只是个在江南养病的娇小姐?”
“大小姐也到该出嫁的年纪了,”李嬷嬷拢了拢袖子,声音里带着几分感慨,“这般心性手腕,将来无论嫁到哪家,定能当得起主母之位。”
二人脚步声渐远,檐角风铃轻响。
房门轻掩,曦月终于松了松紧绷的肩膀。白日里在嬷嬷们面前端着的大家闺秀架子卸下,她轻轻揉了揉眉心,走到窗边檀木桌前。树影摇曳,抚过了桌上一封边角微卷的信笺。那是三日前从江南送来的,外婆的亲笔。
曦月小心展开信纸,熟悉的墨香混着江南雨季特有的潮湿气息扑面而来。目光触及第一行字,她便恍惚回到了老宅。
回忆如潮水漫来——
江南的夏夜,蝉鸣声声。外婆顾清容总是握着她的小手,指向浩瀚星空:“瞧见北斗七星了么?星如命运,轨迹可测,亦可变。”
十岁生辰那晚,外婆没有像往常一样带她观星,而是遣开仆从,领她去了自己房中。烛光中,外婆取出一柄青铜短剑,剑身仅一尺余长,刻着浅浅的月纹。
“月儿,今日外婆教你一套剑法。”外婆的手温暖而有力,“记住——剑不在重,在准;人不在力,在心。”
小小的曦月握着短剑,笨拙地模仿外婆的身姿。那时她并不知道,这套名为“星移”的剑术,会在多年后救她一命。
更深的记忆里,是某个雨夜,她偶然听见外婆在低语。那个总是端庄从容的当家主母,对着天空轻声呢喃:“若那个雨夜……我去了应山……”
“应山”——两个字像种子,落在曦月心底。
回忆渐散,曦月指尖轻抚信纸。 江南十载,虽远离父母,却在书香与星辰间养成了独立心智。她每月与母亲通信,字里行间皆是温情;而父亲的来信,总是干涩的问候后便是朝堂局势、家族荣辱——那个在信纸上谈论权术的父亲,于她而言,更像一个符号。
十四岁那年,京城来了马车接她回府。临别时,外婆将青铜短剑悄悄塞进她的行囊:“若遇绝境,记得星辰指引的方向。”
回到京城洛府,她很快明白了——自己成了父亲洛鸿远棋盘上一枚待落的棋子。父亲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在朝中步步高升,而她的婚事,便是下一步棋的关键落点。
“哐当——!”
前院传来的喧哗打断了曦月的思绪。她蹙眉望向窗外,正厅方向人影憧憧,劝酒声、笑声隐约传来。“父亲又在宴客?”她轻声自语。近三个月来,这样的宴饮越发频繁,今日不知款待的又是哪位亲王、哪位尚书。
正欲继续读信,却听见杂乱的脚步声往后院而来。曦月本能地闪身避到屏风后——这是她在江南养成的习惯,外婆说过:“有些事,听见比看见更明白。”
“……周尚书已经松口了!”是父亲带着醉意的声音,难得透出几分亢奋,“他家长子周子御,年纪正合适。”
大哥的声音响起:“父亲,我听闻那周子御风评不佳,常出入烟花之地,恐非良配……”
“你懂什么!”父亲打断他,脚步声在廊下停住,“风评?那些文人嚼舌根的话也能当真?周家手握京畿三万兵权,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如今朝局动荡,太子年幼,几位王爷虎视眈眈——咱们洛家要想站稳,必须有个倚仗!”
曦月的手无声握紧,指节泛白。
“可是母亲定不愿……”大哥还想再劝。
“妇人之仁!”父亲声音陡然严厉,“曦月是洛家女儿,享了十五年洛家的锦衣玉食,如今为家族分忧,天经地义!天下大事,女人家们不必多管,只需知道——这门亲事,定了!”
恰在此时,二弟放学归来,书童小跑跟在身后。父亲看见幼子,语气瞬间转为殷切:“回来了?今日先生讲了什么?好好用功,将来科举入仕,必是朝廷栋梁!”
屏风后,曦月缓缓松开紧咬的唇,深色晦暗不定,那一瞬间她忽然无比清醒——在父亲眼里,弟弟将来是运筹帷幄的棋手,而她,连上棋盘的资格都没有。
她只是要被递出去的探路石,提前下注的筹码。
订婚的消息如秋雨般冷透整座洛府。
曦月跪在祠堂青石地上三日三夜,膝盖从刺痛到麻木,最后失去知觉。母亲苏婉卿哭着求丈夫,甚至以死相逼,换来的只是父亲摔碎一套御赐茶具:“家族养你十五年,此时不为家族分忧,更待何时?”
瓷片碎裂的声音,像某种界限被彻底打破。
母亲最终病倒了。曦月守在病榻前,看着母亲枯瘦的手紧紧抓着自己,声音细若游丝:“月儿……你若不嫁,你父亲不会放过苏家……你外祖年事已高,还有你弟弟妹妹……”
曦月看着母亲眼中深如枯井的绝望,看着窗外阴沉的天,终于垂下眼睫:“女儿……明白了。”
她不再反抗。只是每夜夜深人静时,会从箱底取出那柄青铜短剑,在月光下缓缓擦拭。剑身映出她的眼睛,那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死去,又有什么正在苏醒。
婚期定在三月后。母亲拖着病体,偷偷在她嫁妆箱笼底塞了一张又一张地契——那是母亲全部的私己。
出阁那日清晨,曦月像个精致的木偶,由着嬷嬷们一层层套上繁复的嫁衣。大红的锦缎绣着金线凤凰,沉重得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最后戴上凤冠时,她抬眼望向镜中——那个面色苍白、眼神空洞的新娘,陌生得让她心惊。
花轿起行前,她最后回头看了一眼生活了许久的洛府。朱门高槛,檐角兽吻沉默望天,一如她记忆中每一次仰望。门边站着母亲,被丫鬟搀扶着,远远朝她挥手,身影单薄得像随时会消散的雾。
她轻轻动了动唇,无声地说:“再见。”
然后转身,弯腰钻进花轿。
送亲队伍行至苍岚山道时,日头已偏西。这段山路以险峻闻名,两侧峭壁如削,松涛声在谷中回荡,莫名添了几分阴森。
曦月坐在轿中,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袖中暗藏的剑——那是她偷偷带在身上的“违制”之物。
突然,马匹惊嘶!
轿身剧烈颠簸,曦月一把抓住窗框。外面瞬间炸开混乱的尖叫、兵刃碰撞声,以及……某种非人的嘶吼。
她掀开轿帘一线,心脏几乎骤停——
那不是山贼。是周身缠绕黑雾、形貌狰狞的怪物,獠牙外露,利爪划过便是血肉横飞。护卫们的刀剑砍在它们身上,只迸出几点火星。
“保护新娘!”有人嘶喊,随即是戛然而止的惨呼。
鲜血溅上轿帘,温热腥甜。
生死瞬间,外婆的声音破开记忆迷雾,清晰如昨:“星轨可变,人命亦可为。”
曦月眼神一凛,当机立断!她一把扯下沉重嫁衣,只着素白中衣,拔下满头发簪让长发遮住浓妆的脸。轿外正是混乱巅峰,她看准时机,掀开后帘滚入道旁半人高的草垛!
屏息,凝神。
透过草隙,她看见那些妖魔在尸骸间翻找着什么,对花轿仅是随意撕扯破坏。
不知过了多久,嘶吼声渐远。山道重归死寂,只余血腥气浓得化不开。
曦月从草垛中爬出,踩过黏腻的血泊。夕阳完全沉没,夜幕降临——而就在这一片黑暗之中,头顶的星空从未如此清晰明亮。
银河横跨天际,万千星辰熠熠生辉,它们齐鸣:
应山!
她仰头,看见北斗七星异常耀目,斗柄直指西北方。
曦月撕下嫁衣一角,裹住散乱长发。她最后看了一眼燃烧的花轿,火焰吞噬了轿身上那个刺眼的“洛”字,也吞噬了她前十五年的人生。
然后转身,朝着星辰指引的方向,踏入黑暗。
身后火光冲天,照亮了她前方的蜿蜒小径,也照见了她眼中重新燃起的、比星辰更亮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