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开始是这样的:我回房间,做梦,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又想了想Balivernes,又开始觉得眼睛朦胧要哭一场,只好逃避现实继续用Begging。
另外,是我和Dana两者控制的不同区域:我是夜晚,她是早晨。早晨的树是给外来者看的,黄金世界树本身就具有一种观赏性;所以夜晚的世界树是核心的管理区域,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掌有进入管理区的权利,但我从没进去过。一来觉得没什么意思,二来觉得麻烦。那一天是个特别的日子,简单地说就是心血来潮,我就输了密码跑进去瞧瞧。一进去就看到Melissa黑着脸要往外走。
“嗨,Melissa。”想了想,纠正为:“嗨,三月三十日。”
“Layla。”她说。
她停下来。
“刚刚进去?”我问。
“对。”
“怎么就走了?”
“看看而已,有没有运作正常。”
“噢。”
我想了想觉得我们也没什么可以继续说的,还是就这样算了吧。我打算继续走进去,她轻轻挡了我一下。
“你最近的使用次数是不是有点多?”她声音听上去很严肃。
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是呀。”
“不过也正常,你是个容易沉迷的人。我见你玩了好久的手机大富翁。”她顿了顿,“你现在还在玩吗?”
“没有。我好像半年没玩啦。”
“那你就是玩了有两年了?”
“呃。”
“算了。我没资格说什么。但是Begging的很大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这里,它很容易让人沉迷。”
我觉得气氛开始不对,收了收心,认真地思考起她的话来。
“目前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推广的话恐怕有点困难,我是说,会造成很多问题。”
“为什么?”我问。
“你不觉得这对逃避现实很有用吗?”她轻轻地问。
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仔细想想,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理所当然的事。说来我也是成年人,一定的自制力还能控制,精神也不是太脆弱,如果有人这方面不太行,恐怕是要被Begging拖死的。
“我自己是不怎么用,也没有兴趣制造梦境。”Melissa揉了揉额头,表情不太好,“虽然置身于第三人,但是如果太超出发展……”
“你要做什么去干涉?”
“不,我会放弃观测。”她冷冷地说。
很有她风格的答案。
“最好这里别变成一个永夜之城吧。”她喃喃道。
一个很恰当的比喻。梦境很容易让人深陷其中,如果自身不意识到,恐怕使用Begging的人会没日没夜地做梦,没日没夜地睡。那样后果实在太可怕了。最好不要。这并非我们制作出来的初心,我们也不希望它成为这样的东西。
Melissa突然轻轻地说:“Ecripes。”
“啊?”
“你要进去吗?”
她头也不回地用手指了指身后的门,一副淡然的表情。
我对她突然的话题转移有点摸不清头脑。“呃,为什么不?”
“最好别进去。”她说。
“你这样说,会让我很有兴趣。”我壮大了胆子说。
“Cain在里面。你知道他最近在干嘛吗?”
“他说他要调整核心。”
“唉,你别进比较好,真的。对你来说,这种场面不太好。”
这更让我一头雾水了。
“想去就去吧!让你小心灵受一次伤。”
她笑了笑。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在开玩笑还是怎么的。其实她就是故意这样,恶趣味地引诱我进去,去揭开真相。或许,我的存在对她来说是一种阻碍。我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在她的上帝视角里太过引人注目,所以她想了一个办法把我赶走,自愿退出。当然,她成功啦。
我推开门,然后就知道她成功了,目的达到了。Cain把我吓了一大跳,吓得我要哭。我还很愤怒。我不想说那是怎么一回事,总之他们都吓到我了。没有一个人安好心!现在我能那么平静地说出来,也是受过了很多时间沉淀的。
“Cain?”
“噢,Ecripes。”Cain有些惊讶地转过身,身后有一个卧躺的大玻璃柜。
“你怎么来了?”
“你在干嘛?”我问。
“转换核心。”他说,“之前的核心意念是代替的,我现在用一个比较有实质性的东西。”
我看了一眼,吓得不轻。
“你在干嘛!”
“转换核心啊。”
“干嘛用这个!”
“你误会了。”他稍微侧开点身子,给我看看身后。
“什么!”
“劣质的东西,当然不如本源有用。”他淡淡地说,“你不觉得吗?”
他们两兄妹都是恶趣味的人。纵使事情不是这样,我也还是被吓到了。好吧。我们不说这个了。
我退出了Begging的研究,决定回日本去。
首先是因为外婆回去了,妈妈那边催得紧。还有就是在这里总觉得不舒服,可能是环境的影响,我总觉得不管在哪里都有一种既视感,让我觉得处处相似,好像生活在轮回,让我很难受。
回去的时候和他们谈了谈。他们说能不能把Layla留在那里,我同意了。
Bret叫:“Mizuki。”
“怎么?”
他沉默地看着我,我也沉默地看着他。我们的离别本不带任何一丝伤感,现在倒是有些这个味道来了。
“好吧。”他说,“你要走了,我们和你相处得很愉快的,所有人。”
“谢谢。我也很开心,和你们在一起相处。”
我有点感动,他平时总是一副嫌弃我的样子,但是这时候还是愿意为我说好话。
“你想吃可丽饼吗?”他突然问。
我看他没什么表情的脸突然溶出了一个淡淡的微笑。
于是去机场前我买了个草莓香草味的可丽饼,坐在机场的凳子上一个人吃起来。吃得我觉得自己好可怜,没有理由的,不知不觉就泪流满面。这还是我第一次哭得那么安静。机场没有认识的人,所以即使大家纷纷侧目,但还是没有人插手。
我回家了。
妈妈抱了抱我,哥哥和纱绫也是感动的模样。他们逼着我说了一大堆事,然后又拿出了他们存的别人发的我的照片给我看,我看了恨不得立马自杀。
“晦月哥多好看。”纱绫给我看她的手机桌面,就是我的剧照。
“晦月一直是好看的。”
哥哥指了指家里摆着的相片,好几张都是Layla的剧照。
我想回来真辛苦。
“之后打算怎么办?”爸爸问。
我说:“没想好。先做一段时间家里蹲,然后再说。”
“你可以去试着医院,应该没问题。”
“暂时还不想做医生。”我颓废地说。
“那你可以来剧团,”纱绫再次展示她的手机屏幕,“我们剧团几乎所有人都对你一见钟情啦。”
“好主意。”妈妈赞同。
“别,求你们了。”我说,“我怕我一辈子都没有女朋友了。”
哥哥顿时愣了愣。“原来你还没女朋友。”他说。
我警惕起来。
“什么意思?”
“洋介结婚啦!”
让我哭一会吧。
回来不久,我过了28岁生日,很巧,但是巧得我很悲哀。因为我这么老了,还没有谈过恋爱。
我最终在洋介的帮助下找了个小诊所混日子,不过是打盹,玩手机,看电视剧,和人聊天。相比Cain院里的病人们,日本人民更加亲民和蔼,基本都可以小事化了,没什么太让人担心的。我不过是他们排解寂寞的消费品之一罢了。
我回来以后,很少想到英国发生的事。这里是个好地方,带着一种轻盈又沉重的文艺气息。现在还是晚春,来得晚的樱花开始凋谢,我在河边长久地凝视,樱花花瓣柔软脆弱,和我的价值观惊人的相似。我们两者在河岸相互凝视,我觉得一种怜爱之情涌上心头。
人不断地渴望,再不断地舍弃。我们的献身精神使自己变得一无所有,然后我们再次为一无所有而欣慰,将一无所有的自身奉献,投身于熊熊火焰,只为了自己溅起那微不足道的小小火花,实现虽死不悔的绚丽光阴。
——
惊觉今天4月28日。蚀哥生日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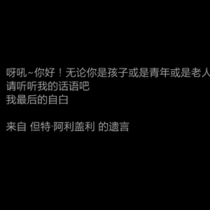


我在重温《Tender is the night》的时候总觉得Dick可怜,不过这的确是本文的一个重要体现。
“醒醒吧,你不过是把我当做消耗品。我只是一个趁虚而入的,被你当做知心对象的替代品。或许你会觉得我很好,但其实我们不是这样的关系。可能,你还会觉得我很可怕。因为我好了解你。我对你内心的弱点一清二楚,但我什么也没说。
“对呀,病人都是脆弱的!我是你生活中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一个转折点,只是想让你变得更好。但是我并非说什么浪费我自己的人生,我拥有献身精神,我愿意为你献身,但是你和我在一起不会幸福的,因为我是世界的旁观者,和你相处就是一个永远的局外人!”
我信心满满地写下这段话,甚至想好了说话时的表情和语调。我想我或许有点做导演的天赋,just或许。
如果我的病人和我告白要怎么办呢?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偏偏是你吧”。我一边写一边想。
然而事实上并不可能。
我的人际依然悲哀地停在原地。Cain那边也不怎么给我打电话,我的玩偶到了我也没想出能有什么理由给他们打,即使我们知道打电话不需要什么原因。没有遇见新的人,也没有旧识在这。遇见的都是擦身而过,我说过了他们只是寂寞的过程中寻求我的帮助,我引领他们,然后他们离开。就好像一个车站,我在车站里等车,路人们匆匆忙忙和我搭话问路,我指出他们应该坐的车,然后他们匆匆忙忙地离开。我依旧在原地,因为我的车实际上永远不会来。
我也不想和他们加深关系。加深关系我对他们的诊断就会带有主观性,这不便于我的工作。唯一的例外是橘君。他出乎意料地会经常为我打电话。我想或许很大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病:我之前有一个同学,每次都被他妈妈逼着,痛苦地打给他的医生,短暂地对话:
“你最近怎么样?”
“还好。”
“噢。”
(沉默)
“药有按时吃吗?”
“有。”
“你要是觉得情况好了一些,就只吃一颗。”
“好。”他说。
电话挂断。
有病的人一般很少愿意承认自己有病,还觉得面对自己有病这个事实很悲哀。
我和橘君聊得还挺多。他不知道为什么,打电话来的频率变得有点多。我或许也有纵容他,毕竟他身上的幻影虽然微弱,并被我努力地压抑克制,但是还是受不了地受一些影响。再者也是他身上那些迷人的特性,深层的那些东西,总让我忍不住去解析探求一下。把他当成一个研究对象让我很愧疚,然后我又不得不对他放软态度多聊了会,这么恶性循环。
但其实了解了一会后,他算得上是一个健谈的人,知识面也很广,我们聊得很开心。虽然我觉得那份健谈是出于礼貌(唉!社会人的交际手法)。
并且过了一段时间(很长!)他似乎才对我放下一些心防。我彻底地感觉到了他的内心究竟是什么形态。一种失望的欣慰。失望是因为他不像我想的那样,欣慰是还好,他真的很正常。一定要说,是一个被迫涉世过深而导致内心不安定的小孩。健健康康,没有任何毛病。反倒是我这种缺心眼的得出这个结论就觉得自己很愧疚(无端的)还有他的一点同情心。
他还很擅长撒娇。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不敢相信,呃,和最初的印象差别有点大。最主要是很多情况他说的一些问题我都无法拒绝,下意识地无法拒绝。我很怀疑我们之间到底谁才更了解谁。
“我觉得广场那家甜品店也很好吃。”他说。
“哪家?”
他说出店名,是我前几天看见的推荐餐厅。
“噢!”我说,“我周末带家人去吃一下,我记得她过几天有在那里的工作。”
“他家的蜜豆牛奶冰很好吃。”
这太让我心动了。
“医生,我前几天刚好拿到优惠卷。”他又说。
“啊,真好。”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地说,“橘君可以吃一大盆冰淇淋,真好。你要是下次来带点给我就好了,多好,我也好想吃蜜豆冰。”
“唔,”他的的声音带着点笑,“您可以和我一起去呀。”
这倒是想不到被直接说出来了。
“这样不好吧?”我委婉地说。
“您对我很照顾嘛。”
“这样说,就没办法了。谢谢你,橘君。”
“没关系。能和您一起吃我也很高兴。”
我又一次答应了这种私人邀请了。
回到家之后我和纱绫说过几天要去吃甜品,刚好就在她工作那个广场。她说:“那好,我工作完去找你。”
“呃,有人约我来着。”
“谁?”她看起来很警惕。
我找借口说:“一个朋友。”
她看了看我。
过几天我和橘君吃着超大份的蜜豆冰的时候毫不意外地看到了纱绫。她看到我对面坐着的人有点吃惊,然后和我做了个手势,就走了。我们回家之后她和我说:“原来你和他认识。”
这话让我太惊讶了。“什么?我知道他有钱,原来他还是名人?”
“算是,”她说,“我一个工作上的前辈经常谈他。她还偷拍了他的照片。”
她拿手机给我看。
“我以为他就是个普通的大学生。”我装傻说。
“事实上是这样。但是他在学校里还算有名,你看他爸。”
我凑过去看,惊了。“好有钱。”
“他妈也很有钱。”纱绫说,“而且学校刚好是我想考的那个超有名的大学。真可怕。”
我和纱绫偷偷摸摸八卦了很多橘君的事情,发现这个人果不其然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而且伪装得非常完美,简直是人生赢家级别的。我也慢慢对他好奇心越来越重了,一大堆问题想问他,但是碍于我们的身份关系,我不方便给他打,只好干巴巴地等他电话过来。但是其实如果他打过来我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很多事情就这样被忘了。
那之后过几天(不知为何,比之前的频率拖了几天)他又打电话给我。
“医生,我拿到了几张票。”
“啊?”
他说了一个剧团的名字,还有最近演的戏。我一听觉得有点好笑。
“那是我母亲的剧团。”
“——噢?”
我闭上了嘴,觉得不该说这么多私事。但想了想,觉得也没什么,又继续说:“她一般会给我留票的。”
“啊,那真可惜。”
我听着他淡淡的口吻听不出什么可惜的意思。
我想了想,又和他说:“你要是喜欢我可以给你票。”
“嗯?”
“我怎么看他们的戏的,你想要我把他们给我的给你。”
“劳您费心。其实不太用,这也是别人给我的票。身边的朋友没有这方面的喜好,而想到医生对这方面有兴趣试着邀请而已。”他说,“既然如此,那么就算了吧。”
这个说法让我好愧疚。我在床上滚了两圈,说:“好吧,哪场的?”
我又答应了。
那天我坐在很前面的位置(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得到那么好的票),所以不管是妈妈还是纱绫都看到了我。我甚至看到坐在我前几排特定席的洋介哥和他的老婆回头看我,看得我一股做贼心虚。
橘君倒是很淡定地看戏,什么反应也没有。看得很认真。我有点心不在焉,但是也想不出要和他说点什么别的,就也努力把注意力放在表演上。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他和我谈了谈自己的感想,各种观点都很有独特的见解。但我很怕他们几个突然过来找我,引起骚动,回答得有些敷衍。之后回过神来发现他也没有不高兴,于是我更愧疚了。
下半场开始的时候我决定认真地看戏以好在结束的时候好好回复他之前的感想。但到了高潮部分,橘君突然拍拍我的手。我歪过眼睛看他。
“晦月先生,觉得这段怎么样?”
我想了想,小声说:“女主角演得很棒。”
“唔。”他笑了笑,“我看得有点难受。”之后他就不再说了,我也不好意思追问。
在一番煽情的戏码之后,女主角终于自杀了,原因就是男主角还是没留下来。我虽然觉得情节有点过激,但是还是被感动了一把,抹了抹眼泪。
“就是这一点。”
坐在我身边一直不说话的橘君终于再次开口了。
“看得有点难受。”
我不得不回头看他,他注意到我的视线,对我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我不擅长这样的故事呢。”
“啊?”
“被拒绝呀,之类的,”
——醒醒吧,你不过是把我当做消耗品。我只是一个趁虚而入的,被你当做知心对象的替代品。
——因为我是世界的旁观者,和你相处就是一个永远的局外人!
我吞了口水,沉思片刻,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well,最终我没能说出什么话来。一句话都说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