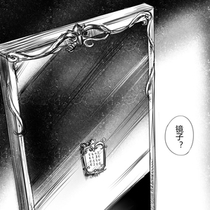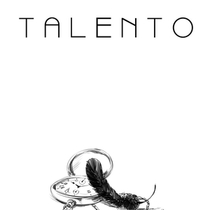守望者,是鬼见十分年幼时看的一部有关超能力英雄的的电影。
已经完全不记得当初是谁带着自己,还不到十岁的自己,去电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虽然以超能力英雄为主题,却根本和某位红蓝光鲜的英雄、浑身盔甲的英雄那样的电影毫不相似。
这是一部主题并不明朗,且气氛压抑的电影。
英雄迟暮,电影由所有人最光辉的时代过去,直至没落的时间——名为“笑匠”的英雄坠楼身亡开始。
笑匠的徽章在夹杂着玻璃碎片的空中飞舞,黄色的圆形笑脸上,粘着一滴粘稠暗红的血迹。
这个画面,在鬼见脑中至今难忘。
在那之后,他多次反反复复地看着那部电影,那原作漫画,以及,有关笑匠的一切内容。
笑匠虽然名为笑匠,也戴着微笑徽章,却并不是一个有趣的人。正相反,他是一头易怒的、暴躁的、只根据欲望行动的赤裸裸的野兽。
他仿佛不带任何正义的情绪,不过是刚好站在正义的阵营,去施暴、去暗杀。
他对曼哈顿博士说,“God help us all.”然而,这不过是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笑话,从笑匠嘴里说出的为数不多的笑话。
他根本不信上帝,也不信上帝会来拯救他们。他看到过社会最黑暗的一面,于是决定去模仿它,他知道世界的本来面貌,于是把一切都当成一个笑话。创作者用他来呈现人类的丑恶本性,笑匠把一切都当成笑话,他自己也是笑话——内心深处的他既最纯净又最邪恶,并且已经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无望未来。
鬼见被这个角色,这个人深深地吸引了。
即使是电影,他也一样无法分辨影片中的人脸。不过这没有关系,他记得,记得那个黄色的徽章,上面滴着一滴暗红色的血迹,那是深深刻印在他脑海里,关于笑匠最标志性的东西。
当新的题目出现,并且三条线索拿齐后,鬼见瞬间明白,自己的秘密被那个屏幕上的男人知晓得一清二楚,忍不住内心一阵颤抖。
不过,很快他便平静了下来。
在这个已经死去六人的白色封闭空间里,再说些什么,也不能显得有多疯狂了吧。
鬼见摸了摸胸前的徽章,坦言说出:“这个问题,有关我的秘密。”

•
天花板上冰冷而明亮的灯光照得镜子迷宫泛起一片刺眼的反光,仿佛黑夜中的警示灯,时闪时现,让人看着有些头晕目眩。
自从进入镜子迷宫后,鬼见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太妙。口干舌燥,感觉体热却并没有出汗,并且夹杂着不可控的晕眩,镜子里自己的倒影晃得仿佛有些睁不开眼。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在这样封闭的环境里,食物和水都极度匮乏,还有那不知道要进行到何时的无数谜题,太过于消耗人的体力,以至于体质较差的人,很快就会支持不下去。
比如自己。
难受的感觉愈发剧烈,只得逼着自己扶着镜壁,不停地向前走去。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鬼见身体一个不稳往镜壁转角倾去,却意外地发现自己走出了迷宫。
从那布满白色耀眼反光的镜子迷宫里出来,鬼见蹲在地上喘了好几口气,头晕目眩的难受之感这才缓解了一些。
剩下的人从后面陆陆续续地走了出来,似乎在交谈着什么,但是鬼见不想听。那些声音仿佛用耳朵贴着封闭的玻璃瓶听里投蜜蜂振翅嗡嗡作响一般,嘈杂、听着让人烦躁不堪。
他走到一边靠墙处,静静等待线索。
•
所有人就像是轮子上的仓鼠一般,不停地跑着,不停地越过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却不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跨越,这无限的谜题怪圈。
白板上只有简单寥寥几个字的问题。
“两个人之间的,是什么?”
两个人之间的,是什么?
仿佛条件反射一般,鬼见便想到巽现。
这些许自己有些厌恶的想法让鬼见心情更不好了,然而不容多想,争取线索的环节便进而跟来——问卷。
这是类似多数决一样的游戏环节,先让所有人进行问卷调查后,再让每个人根据题目猜测哪个选项较多人选择。
问卷上的问题很简单。有的人仅仅在十几秒内便填完了,有的人却是磨磨蹭蹭了半天——不过无一例外的,没有人和旁人分享自己的问卷选项。
因为白字黑字的问卷上有这样一题:认为只要自己能够活到最后就好。 A、是 B,否
不知是身体不适还是心理作用,鬼见觉得这白纸黑字看上去也是同样晃眼,一笔一划仿佛墨水滴在纸上即将晕开,让他难以集中注意力理解上面的文字,心跳感觉比平时更快,想吞咽一口唾沫也极为困难。
闭上眼几秒后再睁眼,鬼见趁着还未头晕的状态在极短的时间里填完了问卷。他环视四周。没有一个人想死。也没有一个人甘心做别人的垫背。迷茫和恐惧的气氛随着一道道题目的展开愈演愈烈,仿佛即将要被这一道问题点燃。
在他自己也没有觉察之时,鬼见却轻轻地弯起了嘴角。
关于多数项的选择问题,看上去是个概率题,但并不难猜出多数人会做出哪个选项,所以在正确选择了三道题目答案后,一道线索轻而易举地出现在鬼见眼前。鬼见拿起看完后,不留痕迹地,把线索塞了回去,然后离开了座位。
几乎就在他离开的同时,一个黑发的青年也走了出来——如果没记错名字,他应该叫龙墨。他是这里唯一的中国人。
他见鬼见打量自己,便有些戏弄的语气道:“哈,怎么,小鬼头还对我抢你喜欢的糖耿耿于怀吗?”
鬼见撇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双手插着口袋往远处走去。龙墨停了几秒,并没有发问,也跟了上去。
•
隔间里目前还没有人走出来,估计还在和问题进行着内心的抉择,整个空间里显得异常寂静。
快走到这个空间角落尽头里,鬼见这才停下脚步,示意龙墨弯腰。
龙墨倾下身子,鬼见便覆上耳际以微不可闻的声音轻轻说了几句话。
“......噢?”龙墨声音里带着几丝饶有兴趣,问道:“你干嘛把这个告诉我?我可不是那种会主动照顾小屁孩的奶爸,更不会关心你的死活,这样对你有好处吗?”
鬼见已经开始头晕得有点眼神涣散了,他强打着精神,反问:“如果我说能猜到你问卷上所有的答案呢?”
闻言龙墨沉默了一会儿。
鬼见望了一眼隔间那边,已经开始有人走了出来——便抓紧时间继续说道:“我知道你很聪明,而我也知道我在这里没有人的帮助,会活不下去。”他远远地看着几个人脸上不停晃动的黑影,道:“我不相信,所谓的能给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就一定能活着出去这种冠冕堂皇、信誓旦旦的废话,其中必定有人只懂得坐享其成。”
他又看了一眼依旧显示着游戏规则的显示屏,“他肯定也是一样的想法。”
鬼见十分疲乏了,忍不住扶墙坐在地上。他看不清龙墨的脸,更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样的表情。视线像水面上的油渍,被轻轻一搅,便四散晕开,带着仿佛要离体的灵魂,“咚”的一声,鬼见头一偏,倒在地上。
•
液体。
水。
带着咸味的,并不好喝的水被喂进嘴里,在并没有习惯的情况下,呛到了。
鬼见咳嗽着醒了过来。他周围围着一些人。脸上依旧带着晃动的黑影,鬼见移开了视线——看了一个拿着绿色水壶、半蹲着的人。
“你脱水了。”他说道。
鬼见点了点头,“谢谢。”
其实鬼见一直没有说。在走独木桥的时候,他往旁边看过去——就被热气氤氲的镜子被人随意地擦了一下,他好像依稀看到了这个人的脸。不是带着黑影,而是.......和自己一样,有五官的脸。虽然依旧还是有些模糊不清.......但是,那毫无疑问,自己已经能看到一张正常的脸了。
他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契机,那个巽现所期待的契机,让自己的壳,终于裂开了一条缝隙,黑暗中,那缝隙里的光在奋力地试图挤进来。
鬼见半躺在地上,盯着那张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的脸看,有些迷惑——原来大人的五官长得是这个样子啊,他现在这是什么样的表情呢?没见过,读不出来。
即使脱水的状态稍微缓解了一些,感觉整个人还是很虚弱。
一会儿也好,几分钟也好,好想睡觉......鬼见想着,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