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雪花把最后一个碟子抹干净,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回头去看,一大一小两人正撑得瘫在沙发上直不起腰。
“小稻。”吴雪花在厨房里喊。
“小稻。”瘫着的吴小宝学着叫。
“应该要叫郑叔叔,不对,郑哥哥吧。”郑部稻把小宝的脸横着拉得老长。
“小稻。”吴雪花又喊,“晚上带小宝去看哈雷吧。”
“嗯,好。小宝,要叫我什么啊?”郑部稻左右拉扯着小宝的脸,没有仔细听吴雪花说了什么,便答应了下来。
“那我出去一趟。别拉了,她长大了脸也小不回来怎么办。”吴雪花踩上了高跟鞋,背上了挎包,“你们记得锁门。”
“嗯,好。”郑部稻随口答应了下来。
“麻麻,你咬去那儿?”吴小宝被扯着脸含糊不清地问。
郑部稻颇感无趣地松开了手。
“小稻,我妈妈没说去哪儿呢。”吴小宝揉着自己的脸说。
“你姓了吴,挺好的。”郑部稻撑着头,突然冒出一句。他反正左右看不出小宝哪里像是他们郑家的血脉。
“小稻姓郑,就挺一般的。”
听小宝这么说,郑部稻哈哈大笑起来:“哎呀,那我跟小宝一起姓吴好了。”
“小稻,我们也出门。”吴小宝整理自己的麻花辫,又过来拉郑部稻起身,“我们去看哈雷。”
“哈雷是什么。”郑部稻虽然答应得好好的,其实根本是一头雾水。
“小稻是笨蛋,都不看燧山晚报。”
“看,看的。”不过只看体育版。
郑部稻踩在写着出入平安的墨绿色门毯上,慢悠悠地穿鞋拖延时间。
哈雷,哈雷。
总觉得在哪里听到过。
啊。
郑部稻半穿着鞋跑到座机边,拨通了好友店里的电话。
“喂,是我,部稻。店还开着呢?我过去一趟。”郑部稻看了看正在穿鞋的吴小宝,又补充一句:“你们店里应该有儿童头盔吧?”
先坐12路,然后走5分钟,转35路。
夜晚的燧山,路上虽然有路灯,但也没什么人在外头走,颇为冷清。郑部稻一路宝贝似地牵着侄女的小手,生怕她走丢了,却又大大方方地转身就走到一个灯红酒绿的巷子里。
“哟,还真带了个小的进店。”一个穿着时髦的男人掐了烟,依依不舍地别过头吐出最后一口,才走近两人身边。
就算如此,小宝仍然被烟味呛得一咳嗽。
“终于玩出了个私生女?”男人向郑部稻递了一瓶酒。
“不是,是我哥的女儿。”郑部稻把酒推了回去。
“你哥。”男人思索了一番,“那个不让你喝酒不让你抽烟,也不让你骑摩托的管事佬。哎哟,想起来了,上次见他还是他把你打了一顿拖出店里的……七年前了吧。”
“真的不好意思,这几年都没有怎么帮衬你家生意。”
“哪儿的话,看到你走上正轨,兄弟也很开心。”男人认认真真地看着怕生的小宝,“倒是那个管事佬,自己怎么不管着女儿。”
郑部稻不想当着小宝的面说这些,便含糊地回答:“他管不了了。”
便是成年人心领神会的沉默。
吴小宝扯了扯郑部稻袖子,让他弯腰在他耳边说了什么。
“怎么了,小姑娘说了啥?”男人好奇地凑过来。
“她说你看起来好像坏人,她不喜欢你。”郑部稻对着男人哈哈大笑。
“不是吧。”男人真心地感觉受伤,“完了完了,具体哪里像坏人?我女儿现在才一岁,趁着她还没讨厌我,我还有机会改。”
“全部……”小宝小声地说。
“别啊,要不还是把这酒吧改成餐厅算了……”男人盘算了起来。
“既然如此你打算转行,你店里的哈雷送我吧。反正也是放在那里做摆饰。”郑部稻直接伸出手。
“那不能,你知道这车多贵吧。”
“借我一晚上总行了吧,她妈妈吩咐的,叫我带她看哈雷。”
“嫂子呢?”
“一年一度,去找我哥聊天了。”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叹着气去吧台后面摸了一把车钥匙出来,又找出了一个女式头盔:“得,摩托总得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不然也会锈了。”
郑部稻接过女式头盔,扣在了小宝头上,还是大了一圈,便感叹到:“我天天拉你脸也不没变大多少嘛。”
(注意:摩托车禁止载未满12周岁的孩童,文中为艺术表达,以及对80年代的野蛮飞车族的致敬)
小宝摸着头盔,拉紧了绑带。
郑部稻只当她还在怕生,便直接拉着她上了放哈雷摩托车的展示台。
“抱紧我,一定不要放开。”郑部稻带上了挂在摩托上的男士头盔,兴冲冲地打火,黑黢黢蚂蚁一样的摩托车发出嗡嗡声。
店长朋友清了一条道路出来,仿佛赛马的指挥,打开后门的同时吹了一声口哨。
哈雷摩托脱缰地往夜色里冲去。
风声一直拍打着头盔,两个人像是在低空飞行,穿过空间和时间的跑道。
郑部稻感觉小宝的手臂紧紧地扣在自己腰上,似乎得到了小姑娘极大的信任,暗自感叹自己做得真圆满。
突然听到小宝像是说了什么。
“大点声!听不见!”郑部稻只能喊。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我爸死了!”
郑部稻脑子一片空白,恨不得躲进风声中。
不是爸爸去哪儿了,不是爸爸怎么了,而是直击要害地点明结论,一点让大人撒谎的空间都没有。
见郑部稻不说话,小宝又大喊:“你们总是不告诉我!但是我早就知道了!我已经八岁了!”
“小宝……我们是怕你难过……”
“听不见!”也不知道是真的听不见还是不想听他的解释,“小稻笨蛋!哈雷不是摩托!”
“啊?!”
“我就是想听听我爸爸是什么样的人!”
“啊?!那哈雷是什么!”
“小稻你抬头!”
郑部稻抬起了头。
他会一直记得。
无人的夜,路灯稀少的公路,大片大片树林,呼啸的风声。一条长长的星轨挂在黑夜的繁星中,和他们几乎同调。一瞬间,他分不清自己是在空中划过,还是流星正在地上行驶着。
吴小宝被蛊惑,伸出一只手想要够着宇宙。
郑部稻回过神,死死地抓住还扣在他腰上的另一只小手,不让她摔下去。
不要跟你的爸爸走,不要跟那个短命的哥哥一样,不要离开我。就算像彗星那么灿烂的死去,也不行。
郑部稻满头大汗,一边努力把握着平衡,一边降低速度。
吴小宝一个踉跄撞在叔叔背上,险些没有翻出去。郑部稻及时刹住了车,车身一歪,反身护着小宝倒在了草坪上。
“小稻。”吴小宝抹了抹郑部稻的脸,“别哭了,我不问就是了。”
郑部稻反而因为意识到自己落泪,而干脆抱住吴小宝哇哇大哭起来。
“我这下明白了,为什么妈妈不带我一起去呢。”吴小宝拍着郑部稻的后背,“她是要我陪着你,一个大男人还能哭成这样。”
“小宝……”郑部稻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捏住小宝的脸,“要有出息,像你爸爸一样。但是你要长命百岁,呜呜呜”
“知道啦。”吴小宝装作老成地回答。
哈雷彗星掠过两人,径直往前方奔去,不回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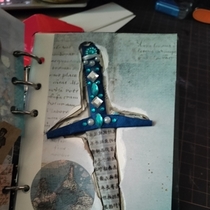


人的一生中会做很多错误的决定,会面对很多挫败,像是选择的队伍前进速度缓慢,像是犹豫再三买下的实体书没有想象中有趣,像是抓周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放在了乒乓球拍上。
于是你等着,花费自己生命中微不足道的十分钟站在原地,花费三个小时四十分钟读完了那本书然后束之高阁,花费每个周末的一个下午和父亲打乒乓球。
等着等着,直到有一个声音。
“好吧,来让我们修好它。”安好挥舞着扳手。
很快的,又将扳手放了下来:“呃,应该从哪里开始?”
马何戎找来一个锯子:“先把这块蛀了的锯掉。”
又突然想到前两天晚上盛虹宇跟他提的建议:既然对方喜欢男性,就应该展现出男性的魅力。于是并无必要地将脚架在桌子上借力,以展现自己豪迈的一面。
安好吐了吐舌头,摸着桌布退到了长桌的另一边。桌布是白色棉麻材质,和木制的桌子相得益彰。边缘是手织蕾丝,花纹向中间渐隐直至融为一体。单从装饰的角度来说温馨而沉稳,但在一众繁复的婚庆装饰中却并不打眼。
在每个人都充满个性的时代,接受自己的平凡并不容易。安好宽慰似地顺了顺桌布,感受它细腻的纹理。
以及它微弱的脉动。
嗯?
安好反复确认刚刚的是不是自己的错觉,或者是因为马何戎锯木头的振动让桌子有了生物般的触感。
在马何戎放下锯子准备拿起打磨工具的瞬间,桌布的脉动变得越来越强烈,然后迅雷不及掩耳地缠在他的脚上,把他往桌子底下拖拽。
马何戎始料未及,来不及做任何防御动作,身体就失去了平衡。地板先是撞在撑起的左手上有了缓冲,然后是侧肋骨,再是胯骨。并不是很疼,马何戎空出来的右手抓在桌脚上,不让自己再往下移动。
瞬息之间,安好伸出的手出现在了面前。
马何戎第一反应也伸出左手抓了上去,还未握紧又松了力度。
去叫人,或者去拿一个锋利的工具来,这才是符合逻辑的做法。
马何戎刚要收回手解释,安好的手立刻反握了上来。力道并不大,没有什么用,是不符合逻辑的选择。
但是却让人心脏一震。
于是眼睁睁地看着安好也被拖了进来,然后阳光刷地被遮蔽,两人被困于黑暗之中。
回过神来,马何戎试图抬起上半身,却很快碰到了桌板下方,只能又重新侧卧下来。虽然是长桌,却也容不下两个成年人的身长。两个人方向相反各自屈膝侧卧,面面相觑。
桌布边缘镂空的部分隐约露出只一点光来,并不足以让人看清楚对面人的表情,却照在两个人依然紧握着的左手上。
意识到这点的马何戎,立刻把手抽了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刚刚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拉住了。”
“是桌布!”安好言之凿凿。
“嗯?”虽然见过会说话的头纱,马何戎还是不敢相信桌布有这种力道。但是也不敢反驳,因为安好的鼻息正打在自己的下巴上,痒得很。
马何戎弯曲手肘,试图突破桌布的防线。桌布却像露营帐篷一样死死地钉在地上。又想起常看的影评视频博主发的生存挑战系列,决定用脚踹出一条生路。
“爱。”安好突然开口。
马何戎感觉自己呼吸停滞了一下。
“我记得罗曼说过,需要更多爱意。”安好又说。
爱意,爱意这种东西,要怎么给出来才好?马何戎死死地绷住自己的脸。
“我!安好!”
马何戎被面前的人气势压倒,往后退了一厘米。
“很爱漂亮的衣服啊!”
唉?
“我其实很爱不同布料的触感还有那种搭配在一起很和谐的感觉而且觉得闪亮精致的配饰非常的不错啊啊啊啊啊!”
马何戎感觉自己心脏又重新向四肢输送血液了,又突然想起也许是盛虹宙的那个,双胞胎中的另一个人,反驳了盛虹宇的提议:不对,应该展现的是女性般柔软的一面。
“我!马何戎!”
安好收了声音,听他的宣言。
“其实很爱毛绒公仔啊!”
真的可以说吗?心中有一点这样疑问,但是马上被压了过去。
“以前给前女友选礼物经常买公仔但是其实是我自己很喜欢啊为什么分手了不把礼物还给我我自己还可以收藏啊啊啊啊啊啊!”
两个人鬼吼鬼叫地闹腾了好一会儿,桌布还是没有松开的迹象。
“真奇怪,这不算爱吗?”安好推了推依然紧绷着的桌布,开始复盘。
“我猜想,至少得是人类间的爱吧。”马何戎把逻辑思考重新安装,清了清嗓子,“我爱我弟弟。”
“原来学长有弟弟。”安好哦地轻轻点头,似乎在赞同他身上的兄长气质。
“虽然平时不怎么表达,但是我其实很爱他。我弟弟比我小三岁,叫马何戈,但是因为拗口,朋友们都喜欢叫他何哥。”
“啊!”安好想到了什么似地拍手。
“哈哈哈对,明明是弟弟但是叫哥,大家都会这么说……”
马何戎讲了好一会儿兄弟的故事,还有不少弟弟听到一定会尴尬地想和他断绝关系的糗事。两个人倒像是在午夜的沙滩上闲聊的朋友,莫名想讲一些心底里不轻易说出来的,对家人的感激。
“我们被困了多久了?”马何戎突然问。
“不知道,但是有些饿了,是不是已经该吃午饭了?”安好估计着回答。
马何戎笑着看着因为适应了黑暗,而变得逐渐清晰的面前的脸,又想起那个晚上,钟意像是最后一个给睡美人送上祝福的仙子,总结陈词道:如果你确认喜欢对方,就从朋友做起慢慢追吧。
嗯,还是朋友般的感觉比较安心。马何戎轻轻地往后靠,却没找到支撑点。
午后的阳光倾泻进来,眼前的安好眯起了眼睛,然后笑了起来:“好像修好了。”
马何戎不敢多看,他不知道自己的表情是否合适,于是翻身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走到了另一边,对正在爬起来的安好伸出了手。
安好笑眯眯地借力起身,慢慢地视线和马何戎平视。
鬼使神差地,马何戎侧过头,在安好脸颊上亲了一口。
啵。
声音不大,但是在安静的空间里格外明显。
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错误的选择,这一定不是他最好的最合理的一个。
但是谁知道呢,来修好它吧。
“耶,我们逃出来了。”马何戎比了个剪刀手,笑得就像在恶作剧的最好的朋友。
我是说,以后再慢慢修好它吧。


阳光正好,从白色矮架中投射,穿过开得正好的粉色爬藤月季,终于柔和地罩在正在说笑的二人周围。两人长相一样秀丽,留着差不多的短发,衣着都偏向中性,一同坐下时默契得像是一对双胞胎。有心人却能看出,一人无忧无虑更加开朗,一人老成持重更加坚毅。
一人手舞足蹈讲述什么,另一个只是温和地听着,丝毫没有察觉到更远处有人无聊到和猫聊天。
“你说,这是不是就是耽美?”马何戎上半身都靠在栏杆上,看着眼前两个俊美的人举止亲密。
被大家称为管家的黑猫甩着尾巴喵喵叫了两声。
“说实话,长得好看的人站在一起确实赏心悦目……”但是其中一个人是和他同屋而眠的学弟,再想到昨天晚上奇怪的氛围,以及还余留在眼角下棉麻衣服的质感,“学弟的取向果然是那边?”
黑猫努力地想要给他翻一个白眼,奈何面前的人根本注意力完全在别人身上,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极力否认的喵喵声。
“你说得对,我昨天晚上的反应太大了。”马何戎有些懊恼地甩了甩头发,“我不讨厌,甚至……”
感觉非常温暖。
你是害羞了吧,管家的表情似乎在说。
马何戎伸手,按在了猫咪毛绒绒的黑色脑袋上揉了几下,把它的表情揉得远远的。想一想啊马何戎,以你引以为傲的逻辑思考能力。
喵喵。
“男人和男人也可以恋爱但是。”
喵喵。
“我知道男人和男人也可以结婚但是。”
喵喵!
“好,好,男人和男人还可以领养孩子。”
“噗,啊,对不起非常抱歉。”还没有回应,旁边突然出现的男人就自主完成了道歉。
“不,没事,是在公用通道里大声和猫聊天的人有问题。”马何戎泄气地把手从黑猫头上移开。
“我叫钟意。”
“马何戎,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很高兴,那么我就先……”钟意正准备离开,旁边的黑猫纵身一跃就挂在了他的肩膀上,他也不生气只是问,“你也要跟我走吗?”
黑猫顺着钟意的手臂又跳了下来,重新坐回到栏杆上。黑色的尾巴轻轻地拍了两下地面,然后转向不远处的二人组。
拜托了,帮我好好解释一下。猫咪似乎这么传达着。
钟也随意地靠坐下来,看了看那边:“白儿茶和安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和安好住在一间房。”
不远处的安好打了个喷嚏,白儿茶关切地递上纸巾。
“是,我和安好是校友,我大一届,所以一起住了。”马点了点头,“安好是个很好的室友,爱干净晚上还不打呼噜,和我以前大学那群衰人完全不一样。”
如果有人不知道猫咪着急时候的叫声,那么现在管家的声音就是。钟意连忙给管家顺毛,就像拉住侏罗纪公园里逃出栅栏的迅猛龙,又道:“冒昧地问,你觉得安好出现了性取向的问题?”
“我……并不想评判同性恋,但是什么男人恋爱结婚,还是很艰难吧。”马何戎径直走回了直男逻辑怪圈之中。
“那可不是‘什么男人’。”钟斩钉截铁地说,猫咪闻言舒心地叫了一声,开心地蹦蹦跳跳。
“你的意思是……”
“你要想那是安好。”猫咪已经蹭起了钟意的手背,完全把他当做了伙伴看待,“比起‘男人’做什么,‘安好’做什么更让你在意吧。”
“……是这样。”马何戎非常认真地想象了一下,“‘安好’和男人谈恋爱让我烦躁。”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钟意试探。
看着白儿茶和安好挽着手,完全没有男性间的社交礼仪。他与那两人物理上的距离是三十步,心灵上的距离却是三十光年。他怀疑起昨晚电影幕布下的拉近,到底是真实存在过的,还是他半梦半醒间的杜撰。
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不能是我。”马何戎从心底吐露出一个答案。
点头,鼓掌。钟意和猫咪像是好不容易送了一个问题学生毕业,心中是骄傲和感动。
“谢谢你,钟意先生。”马何戎留下一句话,就往他的学弟那边走去。
“加油小马。”钟意挥着手目送他越走越远,转头和管家说,“会馆是支持每一种性取向的,对吧。”
的确如此,猫咪舔毛认同,又觉得哪里不对,狐疑地抬头看看钟意。
“祝福小马和他学弟两情相悦。”
不对啊!黑色猫咪仰天长啸一声,人类的眼睛就这么不好用吗?心灵受伤的黑猫,三下两下蹦下栏杆,懊恼地钻进了矮灌木中不见了踪影。
钟意看了一会儿远处的三人,确认有在好好地聊天,便也匆匆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