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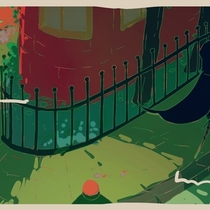
灯火,灯火,就像暴雨中摇曳的花朵。
爱意,恨意,有如风暴般骤降临此地——
现在明明是在地下室里才对……
不知源来的风猛烈地呼啸着,把普拉维斯的毛发连同思绪一起吹得一片混乱。
披着漆黑斗篷的魔女借着这阵风深吸了一口气,压低到看不见眼睛的斗篷帽里亦飘散出几缕末端稍卷的,黄昏色的发。
她抬了些头,面朝着半空中那团所有的风聚至一处后隐约可见的透明的球,缓缓地吐出那口气。
“现在,呼唤她的名字。”她淡然地说着,话罢又顿了一顿,继道:“……就像说好的那样,把魔力融入气息中,把不论是什么都可以的情感融入话语中,呼唤她的真名。”
些许的沉默之后,墙角边缘的那只黑色带花纹的小猫踩着不出声的步伐,应声来到了魔女跟前,忽视掉背后普拉维斯那大概表达着“就以这种状态去见她真的好吗”的意思的呜呜声。奥罗拉尽可能地抬高了脑袋,试着从那双潜藏了许多看不透的颜色的阴影下的眼里辨别出什么来。
“然后把我的魔力控制权交给你…对吗?”
被问到敏感问题的魔女只是极其轻微地点了一下头。
“……那么。”那只在房间里显得极其渺小的猫收回视线,转至半空中的透明球体,“希望你不会背叛我,黄昏夫人。”
被唤作黄昏夫人的魔女没有回话,仅仅是嘴角有略微的扬起。
“现在。回应我、缇米德——!”
随着她难得地用高扬的音调构成的呼唤,地下室里突兀地掀起一阵狂风,如波涛般汹涌地奔向那半空中的透明的球,然后不停地凝聚、不停地涨大,紧接着又急速地压缩;地下室里几盏微弱的烛光一个接一个地熄灭,瞬间便充斥了凄厉的尖啸、痛声的哭喊,以及夹杂其中的意义不明的低声的呻吟。
又忽的,“嘭”地一声,一切声音都戛然而止。
“……哈啊………哈啊…!”这才敢重新睁开眼的小猫突然喘不过气来似的拼命地深呼吸,就像肺部的绝大部分氧气被瞬间抽干了一样,然而无论她做了几个深呼吸都无济于事,所有的注意力都用于本能地、竭尽全力地抵抗缺氧的昏厥感。
还没等她从极其短暂的窒息中恢复过来,黄昏夫人就轻轻地笑了起来。
“你的魔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多一些呢……呵呵。”
“…哈啊……!你绝对是……故意的……!”
黄昏夫人笑而不语地随手理了下斗篷边缘,将下摆的部分往后抚了一些,而后她蹲下身来,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整个身体都像被什么重物给压住、只能下巴抵地地趴在地面上的小小的猫。
“你可没有时间像条落水狗一样趴在地上、奥罗拉。”
“……我……知道。”
她说着甩了甩脑袋,向下压着身子避开黄昏夫人的手匍匐前进到一旁,然后重新抬头,看向那漂浮在半空的光源体——
说不上微弱也算不上刺眼的光源中温柔地包裹着的娇小女孩,有着一头看起来蓬松的、刺刺的短双马尾,通体看上去显得半透明,其胸腹内心脏的位置隐约能看见一枚漂浮的刺。她蜷缩在光团之中,紧紧地闭着双眼。
“醒来。”
黄昏夫人轻声地吐出简单的字句,而后光源中的幼小女孩微微颤了一颤,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她先是疑惑地左右看了几眼,然后往上看的时候被过近的地下室昏暗的天花板又吓得一颤,紧接着像意识到什么似的往自己下面看了眼。
“为什么我会fei————”
“缇米德、告诉我——!!”奥萝拉即刻打断了幼小女孩的话,语速也变得有些快,“当年、当年杀害妈妈的那个猎魔人、究竟是谁!?”
“?!”
显然还没有搞清楚状况的缇米德被一连串问题愣在空中,然后仔细地在上面端详了一下下面的猫,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着:“主人的妈妈……?我记得……我记得是……”
“咦?比起这个为什么总觉得那只猫很像主人……”
“奥萝拉。”在一旁观望了一会儿的黄昏夫人忍俊不禁地插了句话,“这个魔法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具体能持续多久?……不对,我应该甚至没有时间来确定这个……啊啊啊、真是的,为什么这只刺猬就是能笨到这种程度……!”
“毕竟,你带过来的召唤媒介仅仅是一根刺而已。”黄昏夫人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没再插话了。
缇米德在半空中轻巧地转了几个圈,然后就像放弃思考一样接受了现状。她盯着地上的猫和狗还有魔女沉默了许会儿,然后忽的开口问道:“刚刚是在问什么来着?”
“在问我的母亲是怎么死的、被谁杀的,你这笨蛋刺猬——!!”
“呜哇?!”缇米德情不自禁地往后缩了一缩,“……这个气势难道是主人!?”
奥萝拉没有答话,朝着半空中又后退了一大截的缇米德投以愠怒的目光。那被盯得浑身发虚的胆小刺猬颤抖了一下,这才开始低下头、努力地回忆之前奥萝拉提及那个问题。
“那个……应该是女性的猎魔人,嗯唔唔唔唔……个子很高…嗯,比主人的母亲要高!啊,但是总感觉也没高那么多……”
“除此之外呢?!有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特征、有没有听到她的名字——?!”
“呜哇啊——!!主人又在强人所难、那种情况的那种事根本不可能记清吧?!”缇米德的身形突然闪烁了一下,“咦?!这么说起来我当时应该是死掉了但是为什么我会飞————?!”
奥萝拉下意识地看向黄昏夫人,后者则无言地摇了摇头。
“…听好了,缇米德,接下来你要把她念的话重复一遍。”
“哎?”
黄昏夫人也没等她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当即便往前踏了半步,捧高双手,用略微有一些低沉的、平淡的语气念道:“我于黑暗中消亡。”
在奥萝拉凶恶的注视下,缇米德怯生生地跟了句:“我……我于黑暗中消亡……”
“与黑暗融为一体。”
“…与黑暗…融为一体。”
在她话罢的刹那,地下室内又掀起一阵冰凉的寒风,普拉维斯在墙边缩了缩身子,尽量把鼻子蜷到自己身上的毛上,即使如此也还是在旁边打了个很大的喷嚏。也不知道缇米德是被这声喷嚏给吓到了还是其他的什么,她半透明的身体摇摆不定地晃荡了几下,亦神情紧张地看了看陌生的魔女又看了看奥萝拉。后者死死地盯着她,而后点了下头。
“……我逐渐失去意识。”
“我逐渐失去意识…。”
“宛如回到令人昏睡的襁褓。”
“宛如回到、令人昏睡的襁褓。”
…………
……
重归寂静的沉默让地下室的时间仿佛过了很久,地下室里的所有光源逐渐地熄灭了,余下的黑暗里仅剩下些许普拉维斯自喉间颤抖着嘟囔地发出的“为什么觉得好冷”的呜呜声。
“……哈啊。”奥萝拉叹了口气。
“啪”地一声,黄昏夫人打了个响指,让地下室原本尽数熄灭的蜡烛重新燃了起来。借着这些微弱的光源,她走至面前的那块空地上,蹲下身子捡起了一枚小小的刺。然而就在她站起身的时候,那枚刺就像不堪重负般彻底地化为了粉末,随着地下室内的最后一缕灵魂的寒风而去。
她毫不意外亦若有所思地收回手,目光往空荡的地下室天花板的一角望去,“已经过去很久了吧。”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着,“它无法负担灵魂的重量。”
奥萝拉则默然地小跑到普拉维斯的尾巴毛附近,往里面挤了挤,而后才应声答了句“没错”
。普拉维斯发出一阵代表着“之后去卜丽佐节放松一下吧”意思的呜呜声,而没有听懂的奥萝拉只是蜷起身子,神情复杂地思考着什么。
地下室里再次回归到一片死寂,站在地下室中央的魔女收回视线,轻轻地将自己斗篷上的灰尘拍去。
她们在沉默间踩着石制的台阶回到屋内。
嘀嗒。嘀嗒。伴着些水珠滴落的声音,狗在踩上跟地下室同样冰冷的地板时将自己的尾巴轻轻地夹起。
那名为贝洛的使魔始终神情复杂地看着一狗一猫身后留下的或浅或深的大小脚印,亦不忘先用沾湿的手帕将自己的双手洗净,再为抚平裙摆、悠然地坐进沙发的黄昏夫人递上一杯温度正好的红茶。
她端起茶杯,眼睑半垂着,与杯中茶液中的自己的倒影对视,又恍若喃喃自语般地少见地压低了些声音,问道:“这样,你的目的就算达成了么?”
挤在普拉维斯的尾巴形成的圈里的奥萝拉将一只前爪抬起来,几乎习惯性地先放在嘴边舔了几下,方才摆出一副沉吟思索的模样。普拉维斯则忍着想要摇尾巴的冲动,全身上下都透露着不安地微微颤抖了几下。
“不。”奥萝拉用那种极其轻微的声音否定着,“那只蠢货刺猬根本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有用的情报……”
“汪!”
“闭嘴,蠢狗。”
黄昏夫人倒也没否认她的说法,只是在心里整理了几下细碎的情报,猜测与揣测作为丝线交织在一起的结果自是难以再将之区分,她眨了眨眼,道:“你还会再来。”
余光中瞥到奥萝拉轻轻地点了点头,她便毫不意外地轻笑了声,又补了句“真是厚脸皮”。
“脸皮又帮不上忙。”那只猫显得稍微放松了些,索性闭上眼、舔了几下爪背,顺着自己之前的姿势洗了洗脸。
“这可说不好。”她说着抿了口茶,视线往客厅内摆放的各种“人偶”上移了瞬间,随即“噔”地将茶杯放回茶几上,“你不知道的用途有很多……”
“……我不想知道。”
“哎呀,是吗。”
紧随着的是听似颇为遗憾的叹息与沉默。
“……”
“……”
双方保持着一种不必要的保持这份沉寂的默契。
“…你接下来要去哪儿?”黄昏夫人没有抬头,率先打破了这份可有可无的默契,同时亦是问着无足轻重的话。
而被问到的那只此时仍然保持着猫的形态的魔女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在狗的尾巴里面调整着坐姿,将两只不久前本来收在身子下面的前爪露出,一副又重新开始有些警惕的样子,盯着慢悠悠地抿茶的提问者,两只耳朵稍微往后面撇了瞬间。
能轻易感受到这份敌意的魔女倒也没打算再多说些什么,与已经饮下一半的茶一起静静地等待着她的答话。
即将在这份对峙中败下阵来的是哪一方自不多说,她下意识地想要甩一下尾巴,又发觉因为在普拉维斯的尾巴圈里、自己的尾巴的活动范围就非常受限,这时又忽然有一些发生在前不久的事极其突兀地出现在她脑海里,似是受到这个形态的一定的影响又似是她本来就有些这方面的倾向、奥萝拉一下子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抬起两只前爪、站起来给了普拉维斯两巴掌。
“?!”
然而奥萝拉没有理会一脸震惊的普拉维斯也没有觉得有多消气,她抬高脑袋盯着黄昏夫人盯了好会儿,发觉确实盯不出个什么来,也就只能咬了咬嘴唇,不太自然地往狗的厚毛里面靠了靠,遂让普拉维斯更加震惊。
“我要去找住在法国的同派的魔女…。”她心不甘情不愿地朝黄昏夫人说着,“她叫……”
“克莉丝汀·戴叶。”
后者亦没有等她犹犹豫豫地说完,轻描淡写地补全了那个魔女的姓名。然后她没有在意前者瞬间就拉下来的气氛的温度,自顾自地又说道:“激进派呢。”
前者则相当明显地有些不悦了起来,尾巴啪嗒啪嗒地甩着拍在普拉维斯身上。
“你想说什么?”她不满地问道。
“快去吧,奥萝拉。”而她并不在乎对方的态度,甚至也没打算接上她的话,语气依然偏平淡地继续说道:“现在就去。”
“……?”
“因为最近的’那个’,激进派很快就会有动作。又或者说,没有动作才比较奇怪。”她说着,视线又往小只的猫身上移,其意味不言而喻。她亦不管奥萝拉理解的究竟是哪一层意味,便已是抬手示意让贝洛不要添茶,继而将杯内的最后一点红茶饮尽,最后站起身来往自己的房间方向去了。
“贝洛,送客。”她伸了个懒腰,头也不回地自言自语着,“我们也该准备一下了。”
“明白。”被喊到的那位执事打扮的男性应道,对着一猫一狗作出了“这边请”的手势,而后作为领头缓慢地往门的方向走了几步,他们也只得跟了出去。
一走出这扇门,奥萝拉如获释重地变回了人形。却又忽地在一瞬间失去平衡、往旁边踉跄了几步,所幸普拉维斯就恰好跟在身边。
“嗷呜?!”对此毫无准备的普拉维斯被突如其来的重压惊了一下,亦往同方向歪歪扭扭地踏了几下。
“只是突然忘了两条腿该怎么走路……”她拼命地甩了甩脑袋,耳边擦着普拉维斯的腹部侧边的软毛,“魔力…魔力也被那家伙、一次性消耗了大半。”
也许并非仅仅这个原因。她恍然意识到,保持着体型极小的猫的形态的时候,对体力的消耗没有现在的需要那么多。维持太久那个状态后,连呼吸的频率都错位了。
“你会忘记自己原本是魔女”那句话的意味,就只是指这个吗……?
碍于药物的时效还不能变回去的普拉维斯也只得咬着牙关以一种极其不适合作为支撑点的别扭姿势等待奥萝拉从晕眩感中恢复过来。然而后者似乎完全没有那样的打算,他等了很久预想中的她撑着自己重新站起来的画面出现也没能等到,取而代之的,他发觉脊背上的压力变重了。
“伏着我走,蠢狗。”她自说自话着爬上普拉维斯的背上。
尽管犬科动物的骨骼构造本身就不适合驮伏任何事物,但所幸二者之间存在体格差,奥罗拉本就是体重偏轻、体型极小的类型。普拉维斯尽管觉得背上沉重,但好在还能正常地往前走动。
她将半张脸都埋进普拉维斯那稍微有些硬的后颈的毛里,尽可能地把身子调整成不容易跌落下去的姿势。也不知究竟是狗的体温正合适的原因还是之前魔力一次性被消耗太多的缘故,紧绷许久的精神放松下来后,倦意就直冲冲地从脑海深处迸发至了全身。不、这样不行……她咬了下嘴唇,在短暂的片刻清醒中摘下自己的帽子,也不管有没有挡住普拉维斯的视野,就这么胡乱地扣在了狗的脑袋上,她语气微弱地说道:“除了…你我的味道、这里面应该还有……”
“汪呜、汪。”身下的狗抬了几下脑袋,用鼻子蹭了蹭那顶帽子,亦以这种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视野。
“……没错。有派别的味道。”见他似乎是理解了自己没说完的话的意思,魔女的语气变得放心下来,自然也就意识涣散了起来。
“……嗷呜?”
啊、不对,这条蠢狗压根就没有理解。但是来不及了吗……
…………
……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些许混乱的、重叠在一起的影像在她的眼前如同走马灯般来回的旋转。
眼熟的片段要多少有多少,哪怕再模糊、再莫名其妙的记忆也不知缘由地开始显得合理。对了…听说有的魔女能够利用一些能够干涉梦境的草药植物与自身的魔力调和成可以干涉梦境的魔法……不,也许那只是单纯的魔力的干涉,与梦境相关的魔法是一度被踏足的领域。其危险主要在于掌控这个梦境的本人意识到自己在掌控与否……不是这个。
“汪”的一声,脚下的星空…那个是星空吧,黯淡地闪烁着的漆黑的污水,“汪”地被震起阵阵涟漪。
她不知怎么的,有些不耐烦地踩了一脚,然后往前走了几步。
如果你沉醉于梦境,其中的另一个自己将替代你“醒来”。虽然记不太清楚是从哪里听来的说法,但说出那句话的女性的脸模糊又清晰,明明她从上到下的所有轮廓就没有任何让人看不清的要素,但为什么会觉得视线无法聚焦于她……也不是这个。
“汪”也好“喵”也好,人类也好魔女也好是不会发出那种声音的吧,既然无法发出人类的声音那么就并非人类,不需要让魔力也听懂的语言,单纯的单音节难以用作咏唱……无非类似于扇动一开始就不存在的翅膀的感觉,但是……不对,不对。
注意力从刚刚开始就涣散又集中,毫无效率的思考与混乱的思想于同根枝叶中招展。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想这些事的时候总会下意识地想到其他的事去。
“汪!”
……啊啊,对了。最终的最终,说到底,为什么自己会在想这些东西…。
“你醒了?”
恍惚中,她听见了比自己的心声更清晰的别的什么人的声音。
“呃……”伴随着阵阵欲裂的头痛,奥萝拉捂着自己的额头从稍微有些硬的沙发中坐起身来,再紧接着的是惊醒后的急促心跳,咚咚,咚咚地引领着她的呼吸的频率,于是一切都变得再次紊乱起来。
“汪呜,汪汪汪!”
对了,这次应该是对了…刚刚在半睡半醒的时候老是听见背景音里面的狗叫声,应该就是这条蠢狗的声音……虽然普拉维斯还是狗,但刚刚还听见了人声什么的。还在想着“怎么回事”的时候,奥萝拉方才反应迟钝地抬了头。
“…戴叶。”她认出了隔着空无一物的茶几、抱着双臂坐在对面沙发正中央的戴着眼镜的魔女。
而对方显然没打算掩藏自己脸上不悦的神色,其视线从上到下地把她的全身重新打量了一遍,最后定睛于她踩在沙发上的沾满泥土的靴。其眉间显而易见地抽动了一下,似是皱眉又似是加重视线的重量、被喊作戴叶的魔女带些愠怒地自鼻间轻哼了下。
“奥萝拉。你被谁袭击了?”她问。
对这个问题没有反应过来的奥萝拉顿了一顿,半饷后把自己下意识歪了一下的脑袋回正。此时之前在疯狂鼓动的心跳已经平静了,呼吸也逐渐恢复平常,但思维暂时没能跟上,她迟疑着、试图先把刚刚的半梦中被自己搅得混乱一片的思绪理顺。
这之前的话,从黄昏夫人家里出来后就迫不及待地追着自己的尾巴转了三圈…换句话说就是让自己得以变回两足行走的魔女的自我暗示,然后就觉得非常疲惫,索性在狗背上就这么睡着了。以记忆开始断层的这个节点接续到此时此刻的情况,中间应该有发生什么事…才对?
基于这部分像被拉走的抽屉一样的空无一物的记忆,她非但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甚至还反问道:“我为什么在这儿…?”
然后这招致了在沉默中等了许久的戴叶从那副圆框的眼镜中投来的更加刺眼的视线。戴叶抱着自己的双臂,右手的食指指尖在轻轻握住的左臂上点了几下,目光在奥萝拉的黑色的外套中藏着的内村、裸露在外的手臂、腿、脖颈附近来回移动着,随后将身子往身后的沙发里靠去,双臂也稍微放松了些许,应道:“你的狗背着昏迷的你跑到了我家附近。”她抽出右手、闭上眼,轻轻地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但在我看来,你的身上没有任何外伤,健康得就像刚挖出来的土豆。”
……土豆。奥萝拉疑惑地看了看自己身上又看了看戴叶。二者对视了一眼,后者颇为无语地用刚刚揉太阳穴的手顺势指了指她的靴子,前者则后知后觉地调整了坐姿,将自己的双腿从沙发上放了下来。
“…。”她稍微有些拘谨地,动作幅度偏小地理了理自己的衣摆,之后又随手拍了几下沙发上的泥和灰,“我从英国逃过来了。”
听见后半段话的时候,对方的眼神很明显地变了瞬间,她挑了挑眉,又问道:“哦?……你遇到了’那个’?”没等奥萝拉回答,她紧接着补了句“但你的身上没有外伤”。
“你希望我受伤?”
她并不擅长、亦或说没有控制自己语气,语调相较于之前偏高了一点。
“……”戴叶面不改色地眨了下眼,目光朝着老实地坐在沙发边上的那条大白狗那边去,狗接到视线后非常不安地猛地摇头,她就仿佛是被这幅滑稽的模样“逗笑”般、心领神会地轻笑了声。
“哎呀…说得真难听呢。但请别误会了,’情报’也是我的武器。”她顿了顿,从狗的身上收回视线,继续道:“你能毫发无损地过来固然让我省了些处理的麻烦,但这份省去的麻烦能够抵消失去的情报与否……”
“取决于你。”说着,她摊了摊手。
这几句话倒是让奥萝拉稍微迟疑了下,她皱眉道:“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据我所知,遭遇’那个’的魔女没有出现生还者。但你说你逃过来了……”
“与他们遭遇的魔女…。”
“…他们?”
“能逃掉也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吧。”
“也许。但基于情报误差,对于你身上没有任何外伤这一点我感到疑惑。很难理解吗?”
“不…我不明白。”她摇头质疑道:“按你的说法,你要看见我浑身是血地找到你才高兴?”
戴叶闻言默了片刻,自顾自地点头道:“那么为了照顾到脑子不太清醒的您,我先换个问法。”
“为什么选择逃来法国?”
出于种种复杂的说不清的原因,难免被这个问题问到的奥萝拉又迟疑了。
也在此时、从本就没有关紧的窗户忽地闯来阵短暂的风,将没有拉到底的窗帘轻微地掀起,带着独属于树叶枝叶的草木的涩味与湿润的空气。
坐在地上的狗下反应地甩了甩脑袋,那本来戴在狗的脑袋上的她的帽子也被甩得摇摇欲坠,奥萝拉眼疾手快地在普拉维斯打出喷嚏之前摘走了那顶帽子,回头看了戴叶一眼,而后戴回了自己的头上。
狗又甩了甩脑袋。
要说起为什么离开英国的话,自然是因为自己的疏忽被猎魔人发现……也不对,既然有猎魔人在那片森林里面游荡,那么被发现也是迟早的事。而至于为什么要来法国,其一是为了“缇米德”,其二是手边恰好有合适的“导游”,其三则是……序号排后的“顺便”。如果她是正常地“顺便”地找到戴叶,方还能理直气壮地与之谈话,但现在的情况稍微有些……
她想着想着,还没想到个合适的答案,嘴边已经迫于不便于再增加下去的沉默的指针,就像被追赶着一般脱口而出:“……与你无关。”
“…呼呼。”戴叶似乎也没想到奥萝拉会这么回答,但也只是再次轻轻地笑,一改之前的偏向淡然的语气,语调明显愉快了许多地应道:“也是呢。毕竟我只是您的’救命恩人’,不是您的’收尸恩人’什么的。”
“啪嗒”的一声,奥萝拉皱着眉头,还没能答上话,注意力又被窗户的方向吸引了去。那位人类的少年也恰好将窗户关上、窗帘拉拢,转过身时朝她们的方向微微地笑了笑,而后走至戴叶所坐的沙发的后面。
不对,那个不是人类…会出现在这里说明他应该是使魔。被现在魔力匮乏的影响、总觉得对魔力的“敏感度”也变低了。
反应力迟钝的同时,从刚刚开始她就对于戴叶投过来的那种视线稍微有些不适,自第一次对视之后就开始避免与对方对上目光,自然无法再观察对方的神情与潜藏于眼神中的意味。
说到底,从一开始就无法说出口的话,到现在再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了。
她看着那位少年模样的使魔贴近戴叶的耳边小声地说了些什么,而后戴叶若有所思地点头。
“怎么了?”猫的好奇心问道。她动作不怎么自然地抬手整理着自己的帽子,视线总是无意地往戴叶的方向飘,但又有意地从那边收回来。
戴叶则没有回答她的意思,她随口说着“比起那个”,看了狗一眼又看了奥萝拉一眼。
“我会给你准备帮助魔力恢复的茶,最里面的房间随便你用。”
她说着接过使魔递来的黑色的礼帽,奥萝拉这时也才注意到她身上穿着的是与往常见到她时不同的男士的西服。
“为了’招待’你所浪费的时间,日后我再慢慢找回来吧。”语气愉快地笑着边说边将礼帽戴在头上的魔女又将帽檐提了一提,以此对自己的使魔示意。待使魔将一杯温热的深色的茶端到奥萝拉的面前后,便与使魔一同头也不回地往玄关的方向去了。
被留下的魔女和狗目送着她的背影,魔女欲言又止地张了张嘴,接着又往沙发的角落里面缩,一种难以言喻的不怎么好的未知预感从内心的最深处顺着脊梁往上爬;她从沙发上起身站起来朝她们离去的方向喊道:“…戴叶……!你要去哪儿?”
戴叶的脚步被喊得顿了顿,然后她回过头来、笑容灿烂地应道:“与你无关。”
而后“啪嗒”的一声,这次被关上的是玄关的正门。
屋内安静了下来,封闭空间的安心感与与之相对的空间的主人不在带来的不安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但不管怎么说…能注意到自己魔力消耗的问题,还愿意不计前嫌地提供帮助,她的本性难道说其实是相对善良的那一类……?奥萝拉思索着,尽管怎么都没办法把那个笑容跟她当时说的话联系重合到一起,她亦愿意信任自己的判断,打消自己端起那杯茶时的疑虑,准备将之一饮而尽。
“…噗咳!?……咳!…咳……咳咳……!”
前言撤回,那家伙即使在不缺乏极端性情的激进派的魔女里面,也一定是性格最苦瓜最糟糕的那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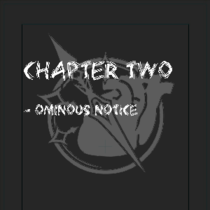






(1)
奥斯卡·盖曼的信仰并没有那么虔诚。
这话说来也许奇怪,他从属猎魔人公会,依圣灵之名行事;他们找寻人群中藏匿的斯忒律基并将其曝晒于白日;古老的沿袭流传至今,猎人们分食饱含寓意的餐饼……
瞳色相异的黑发男人只站在阴影里,看他们行早已被废弃多年的典仪。
——他也曾在夜晚呼喊狄安娜之名。
(2)
现在是夜晚,浓雾遮蔽了月亮。
玛丽戈尔德·沃伊德独自站在泰晤士河边。路上行人不多,女性更少,新近发生的案件引发恐慌,对魔女影响甚过常人。
可她仍站在这里。
有脚步声传来,伴随手杖点地的响动。
自称文员的奥斯卡低头走路,他心里想着事,并未对外界投入过多注意。煤气灯将女人的影子递到跟前,他这才抬起头,看见灯下的玛丽。
文员抿一下嘴,打算转身就走。
“奥斯卡先生……”玛丽喊他。
“奥斯卡先生。”
“奥斯卡!”
奥斯卡·盖曼停下。他先转一下鞋,接着才不情不愿地将身子拧过来。文员脸上还带着一点疑惑,可能在疑惑自己为何没有拔腿就跑,而是听从了对方的吩咐,好似被训斥的孩童(他忘了自己跑不快)。奥斯卡注意到曾在拉杰的小屋中见过的女性并未戴上眼镜,而她没了那两个圆片也能如常行动;身旁流经的河水经过治理也不如往年那般泞烂发臭,女性身上与吉普赛人不同的药草味道混进雾气,由微风送至鼻尖。他感到熟悉。
“晚上好,女士。”他勉强地说。
“晚上好。”玛丽回到。
然后是一片沉默。
片刻后,玛丽戈尔德开口:“你在散步吗?”
“……我从咖啡馆回来。”
“喜欢喝咖啡?”
“不……”奥斯卡有些冷淡地回答,“我去听戏。”
玛丽点点头,像是认同了这个说法。奥斯卡在这一点上倒真没遮掩,他去相熟的咖啡馆,同几个还算面熟的常客一起听留声机。事实上,他怀里还揣着一份抄录的曲谱。不过他并不打算将这些分享给玛丽。他准备开口道别。
“你喜欢听戏?”玛丽看出他的打算,抢在他之前提出新的问题。
“喜欢听什么?蝴蝶夫人,阿依达,茶花女?”
“……瓦格纳,也听一点法语。”
玛丽再次点点头。
他们又陷入沉默。奥斯卡想起什么似的,他装模作样从口袋里掏出怀表,做作地看一眼时间。
玛丽戈尔德第二次抢在他前面,说:“你的家……你过去住在朗伯斯吗?”
“听起来带点那边的口音。”她飞快补充。
“……”
文员深吸一口气,说:“是的,曾经。”
就在这时。
月亮从乌云中挣脱,狄安娜举起弓与箭,一片银色短暂地投在玛丽戈尔德·沃伊德脸上,照亮她沙褐色的头发与天蓝色的眼睛。
这两种颜色出现在了青年的梦里。
(3)
他在阳台上看见“她”,于是转身穿过走廊,咚咚咚跳下木质楼梯,柔软的手织地毯消弥急切的足音——织物有着复杂的花纹,来自传闻中流着蜂蜜与黄金的东方。奥斯卡打开门,尚且年幼的儿童冲向庭院里的女人,他直接撞向对方后背,两人一齐跌进春的绿意。他将脸埋进她丰沛的沙褐色头发,深吸一口气。是药草的香味。
女人转过脸,露出盈满笑意的天蓝色眼睛。
他们笑起来。
他喊她——
(4)
他也曾在夜晚呼喊狄安娜之名。
那时他正是少年,腿还没有恶化到如今的地步。奥斯卡成长得很急,无论是个子还是心灵,年轻的身体飞快抽条,四肢细瘦如柳枝,没什么力气。他反击不过老猎人。他对他教的一切感到厌烦。
启蒙时代的奥古斯特称巫师审判为“司法谋杀”,浪漫主义又提出新的解读,一个全新的范式代替过去邪恶的内涵。奥斯卡曾把疑惑对老猎人诉说。
“既然人是有限的……神灵为什么允许邪恶存在呢?”
在少年奥斯卡的幻想中,魔女说不定是什么天外来客,就像拖着长尾巴的陨石,她们——他们最初的模样是古怪的,身躯肿胀如虫卵,细纹叶脉一般攀附在柔软却结实的外壁上,利齿包裹的口器或许就藏在那圈环状肌肉组成的有力触须中。这些东西,这些说不清是什么的生物将现在被称为魔法的元素带入地上的血脉,魔女的血滴入河流,污泥涌动中生出长着人牙齿的鱼;魔女的血滴入土地,荆棘睁开无数眼睛,柔软灵动如活物;魔女的血洒向天空,鸟生三足三眼,始食生肉。也可能,魔女吃了人的肉,于是有了类人的形体;而人吃了魔女的肉,于是有了魔力。
这在他看来是合理的解释。
否则,魔女为何与人无异,能与人结合,却要夺去人的性命?
更何况,此时奥斯卡已产生动摇。
细微处的切片如同墙壁裂缝,一旦察觉便固执地占据了注意力,一眼扫去,你总会看向那里。换生灵们就是这样察觉自己的出身,现在奥斯卡也遭遇类似境遇。他是在哪里学的法语?又是从何处得知月亮之名?
裂缝逐渐扩大,露出墙后不曾闭阖的眼睛。
为什么猎人会在抽打他后又抱住他?为什么猎人在知道自己毫无魔力后露出片刻放松的神情?偶尔几次,在他刚被救出来、还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猛然惊醒。猎人会看着他。他以为他睡着了,就拿眼神盯着这个被他从毁塌的废墟中扒拉出来的孩子。男孩会因为注视醒来。他不敢睁眼。
——那是仇恨的眼神。
“听好了,那是异教的神,是striga unholda!”
老猎人果然大为光火。他听到过少年偶尔吐露的名字,那是与正统不同的传承。
“可是……”奥斯卡注意到老猎人握紧的拳头,他瑟缩一下。
“可是,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公会不也是秘密结社吗?!那同样是异端……因行魔法而从属邪恶,所有人都得上绞架!”
那时正是满月,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随着月光投向大地。老猎人背着光,眼睛却发亮,像树林深处桀桀怪笑的鸟枭。
“所有人,所有人……”老猎人重复着奥斯卡的话,“所有人!”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爆发出一阵大笑,又猛地咳嗽,眼泪从他已有皱纹的眼角流出,划过皮肤上苍白的伤疤。奥斯卡看着猎人,他心中生出一种恐惧。他推开猎人,拖着腿跑向门外。
第二天,猎人坐在家里,没多久就等到他回来。
他不再有别的去处。
老猎人将恨的毒液强行哺进他嘴里。
他吞下了。
(5)
玛丽坐在窗边。
她并不常沉浸在回忆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何况她做出了选择。只是这趟旅行让那些沉在心底的思绪上浮,她不可控地看着那些注定不存在的幻想,如阳光下易破的气泡:如果那时没有离开;如果那孩子还活着;如果……
如果我之后有好好搜寻。
她叹一口气,习惯性地将手伸向书桌的某个方向,又在摸空时想起这里并不是她的家,而她此行也并未将相框带上。
那么这次相遇是错误吗?
玛丽戈尔德想起黑发的文员,苍白、瘦削,阴郁如无人打理的古宅。他们又见了几次面,开始是她制造的巧遇,接下来几次如同无言的约定。奥斯卡·盖曼(她在心中喊他的名字,而不是姓)似乎从他们的相遇中发现了什么,他不再拒绝,也不急着离开,反而用探寻的目光看着她,疑问继而变为肯定。
或许她待得太久了。
魔女站起身,她不愿再过多地浸入人类世界,那会让她大意,大意招致灾祸,她又将失去重要的东西。
一阵翅膀的扇动声,是查理。
黑色的乌鸦官进入屋内,待魔女关好窗,它才嘎嘎叫起来。这次,它如真正的报丧鸟一般带来不幸的消息:
“那小子受伤了,倒了,白布盖在身上。”
玛丽戈尔德·沃伊德立在原地,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燃烧过后的废墟。
T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