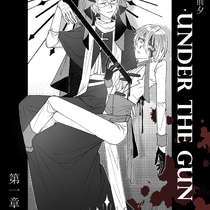※绝命社畜写3k字都要写一星期……
※擅自描写了瑟伯林的风景,如有出入请以官方描述为准。以及谢谢雷古勒斯和小雫,OOC都属于我(磕头
从酒店的床上醒来,意识会首先拾起窗外的海浪声。
这往往使她想起昨晚又没关窗。浪涛卷起忽远忽近的噪音,不知是楼栋里的旅客起了纠纷,还是楼外工人们照常的大嗓门。这时,意识已完全明晰,她不得不坐起身,一口气扒开紧黏皮肤的厚被褥,像撕下一张湿透的创可贴——扑通!什么东西应声落了地。她叹气,看也不看,便上半身侧倒下去,艰难地刨到了那个东西——自己的手机。
能自由落体在地毯上是它的运气。她悻悻地想。
关掉看了一半的电影,手机显示现在是上午十点半。3月9日,上午十点半。一个平平无奇的日期。她翻身下床,决定去冲掉积攒了一整夜的汗渍;对于刚熄灭却又陡然亮起的屏幕上的消息,选择暂时不予理会。
收拾妥当,森野深铃挎着贴身小包出了门。快到十一点了,酒店的电梯里陆续挤进各色各样的人。无奈身高有限,她被一层层的停靠挤到了边角,只能侧着脸,试图在体味与聊天交织的电梯中抓住一丝氧气。
所幸人堆在二三楼时终于有所分流,她跨出电梯,路过前台,耳畔掠过一句快活的问候——“Have a nice day!”——并一个激灵,下意识朝对方弯腰,直起身来只发现那位满面笑容的女服务员根本没有看她,而是正在接待新旅客。
她抓紧了挎包带。
将近十一点,港口区飘荡着海腥味。对直走,穿过仪仗广场,中心喷泉不知疲倦地抚慰行人匆匆的步履。相比于故乡小镇,瑟伯林的绿化难免显得稀疏。这样开阔的地方,至少应该像纽约那样拥有属于自己的荫蔽——又或许,它已被那栋气派的警察总部大楼握住了庇护的权柄?她不理解。她只觉得每次走在黑白分明的地砖上,都有种被当作国际象棋里的棋子的感觉。
她总是如此多心。
谁让这条通往目的地的路漫长得难以准确丈量?跨越广场还不够,还要找到那家外装粗犷的枪械店“熊常驻”……不,她不买枪。不论是因为故乡的禁令,还是考虑到接下来的打算,她都不需要(也把握不了)火力过猛的武器。隐约可见那藏在落地窗后的棕熊标本,深铃停下脚步,转头看向左手边:木栅栏划分出一片方正区域,修剪齐整的草坪向后蔓延开去。当中唯有一条直路,通向深处微掩的拱门。向上望去,这扇拱门属于一栋两层楼高的建筑,黑瓦白壁,十字高耸,静静地拥抱每一个走上前来的人——
只要你是祂的信徒。
可惜,她并不是。
今天既不是礼拜日,也没有举办社区活动,上午十一点过,恩典教堂的正门前只有她。轻轻推开门,正对面的彩窗立刻铺下一段光,迎宾毯似的。此刻,能容纳上百人的礼拜堂里,唯有一个背影伫立在尽头的圣母像前。那背影听闻响动,转过身来,捕捉到蹑手蹑脚的女孩,微微一笑便转回身去,继续刚才的动作——仿佛她的进入并不比一只野生动物的误入更让人警惕——这令她安心。
找到靠后的座位,坐下,并不祈祷或忏悔,森野深铃呆呆地望着圣母像后的彩窗,很快便陷入了思维的漩涡。她到底想了些什么呢?在那道背影走近她,并向她打招呼后,实际上不怎么记得了。这并非要归咎于外人,因为她总是想得很多,思考加剧了负担,所以需要强迫自己选择性地遗忘。目光重新聚焦,她看向朝自己搭话的人——不需要特意分辨也看得出,这是一名白人男性,身材高大,四肢修长。身上的深色长衣融不进瑟伯林的游客群里,但在“教堂”这个特殊的场所也有“牧师服”这样专门的叫法。
深铃微微并拢双腿,点点头道:
“您好……牧师先生。”
雷古勒斯·纳博科夫。她记得他的名字。只是有些为难舌头了,所以她只会称呼“牧师先生”。
接着,这位牧师发表了一段不短的讲话,着实有些难为一个刚发完呆的日本游客,于是话到半途又从衣兜里掏出了手机,点点划划半天却不见下一步,其间深铃也终于发觉他想做什么,赶紧掏出自己的手机,点开翻译应用,将话筒那端递了过去。
雷古勒斯有些难为情地笑了笑。
“不好意思,都这个年纪了还适应不了电子产品,实在是个赶不上潮流的牧师。我刚才是想说,今天你似乎来得迟了一些——哦,不,请不要误会,我不是批评,而是再过一会儿,我们将组织社区的‘午餐日’。社区里住着许多不同种族的居民,森野小姐若是方便参加的话,可以品尝到不同文化的美食。请问意下如何呢?”
深铃听完,摇摇头道:“谢谢您的好意,牧师先生。”
“我知道或许会有些吵闹,但大家都是好人。你已经连续到访了三天,我想,可能一位游客会更喜欢餐桌上的交流而非教堂里的沉寂……”
“谢谢您。”
她依旧摇头。
“好吧。”男性放弃了,如同他前天放弃劝说她入教一样,不算太干脆,当然也不算太烦人。他苦笑着请她原谅他的执着,因为她的年纪与社区里的孩子们相仿,而那些孩子们多多少少都抱有难以启齿的烦恼——顿了顿,那双白种人特有的嫩绿的双眼盯着她,几秒后,他才接着说:“不过你看起来不像有‘烦恼’,更像是正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不好意思,我的职业病犯了,如果有冒犯的话,请当我没有说过吧。”
森野深铃再次摇头。
愿主保佑你。
牧师的道别随身影一同淡去。在短暂无人的礼拜堂里,她重新望向头颅微垂的圣母像。光影因时间而逐渐偏移,落在雕像脸上,像一迹无人发觉的泪。
倒也没有说错。她想。
待了将近一小时后,森野深铃离开了教堂。这里已远离闹市,尤其今天还是工作日,过了午饭点,街上鲜无人迹了。沿着导航应用的提示,她路过“熊常驻”,忍不住透过窗户稍稍打量了一下店内的装潢——如何才能把一头笨重的棕熊标本摆成那样凶神恶煞的姿态?她想不通——随即快步走向下一条街,再下一条街,直到来到“莱西酒庄”附近才站定。看见一辆辆跑车或驶离酒庄,或进入大门,街边的每一家店门口都幽寂得像在拒绝无关人士的进入,她才意识到自己走进了“富人区”。
好吧,前两天图新鲜,三餐都在酒店解决了,偶尔感受一下高档氛围也无妨。不过,考虑到现在的穿着,也许不太适合出入太高档的地方,深铃最后选择了一家这附近看上去最“亲民”的西餐厅。
挑了个最靠里面的座位入座,她拿起菜单,特意让服务员待会儿再过来,这样方便自己拿出手机用AI翻译菜名,于是,看着这本没有插图示意的菜单,她开始纠结到底要靠什么填一填自己吵得要死的胃。
那条松散的麻花辫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晃进了她的余光。
还以为是猫尾巴,深铃抬起头,正想这种地方居然也会有野猫,却撞上一双眯细的眼睛,吓得没拿稳菜单,“嗵”的一声掉了地。
赶紧趁服务员没发觉时弯腰捡起(顺便瞥见了这条“猫尾巴”所属的身体:一双看不清牌子的运动鞋,不太打理的浅灰色袜子边),直起身来,发现原来是个不认识的少女,深铃皱着眉头,想问她为什么要坐到这里来,是有什么事——
“你是日本人吧?”
又被“猫尾巴”抢去了话头。少女眯着眼睛,饶有兴味地盯着她,手掌撑着下巴,后背微微弓起。
尽管得克萨斯州地处美国中南部,而位于该州的瑟伯林更是坐落在南边,却也因为近年来的特定政策及配套设施而招揽了不少外国游客。光是在这两天里,她就已经在港口区听见了不少家乡话,想必随着日期的步步接近,瑟伯林还会接收不少同乡人——但是,这并不能构成这个少女不经允许与她同桌的理由。至少在深铃的记忆里,她们从未有过接触。
“您有事吗?”深铃反问。
如同两条平行线,彼此都没有得到答复。
少女的穿着十分普通,外穿针织衫,内搭衬衣,适合初春时节。哦……深铃突然有些懊恼。怎么能假定她就是游客呢?这么寻常的穿搭,根本不能排除是本地人的可能性。可是,若非游客,那少女挑在这个时间点做出的行动就更让人不解了。等等,又或者,她并不是“刚好”挑在这个时候,而是从更靠前的某个时间点起就在关注她,也就是跟踪……
仿佛看透了她的心思,少女笑眯眯地,打破了片刻的沉默:
“你身上有股味道。”
“味道?”
“我喜欢的味道。”
森野深铃是个普通人。
在短暂的十八年人生里,她曾无数次体会到且一次次加深了这个观点:自己只是个普通人。
因此,就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她狐疑地寻找自己身上是否有奇怪的“气味”,又在过程中对莫名不设防的自身感到后怕,并抬起头,想要寻求店内的帮助——
麻花辫却已不见影踪。
猫一样的蓬松“尾巴”抖落下最后一句话,眨眼间便消失在面前。当然,假如仔细倾听,或许能听见后厨传来几不可闻的咒骂——但深铃捏着菜单外壳,半张着嘴,好一会儿才想起被打断的正事,匆匆点了两个菜,打发走了服务员。
手机振动了一下。她划开锁屏,手指却点错了位置,眼看着跳转的聊天框里蹦出三条几十秒的语音消息,不由有些后悔为什么要解锁,只好拿出耳机,依次点开消息。
第一条。
“喂喂,小铃?起床了吗?今天要去哪里玩呀?记得多拍些照片,也别光拍风景,自拍几张嘛。你这个孩子呀,从小就内向。对了,我看今天瑟伯林的天气不太好,像要下雨的样子,出门要记得带伞啊。”
第二条。
“喂?小铃?还没有起床吗?妈妈今天晚上做了你最爱吃的什锦饭,味道相当不错呢。等你回来再给你做哦。瑟伯林怎么样,安全吗?好玩吗?别往太偏僻的地方去,容易遇上坏人。哦,对了,今天可能会下雨,出门一定要带伞啊。还有,你爸让我问你,回程的机票订了吗?我这里没收到扣款的短信,你一定要早点订啊,快到日子了,机票不好——”
第三条。
“哎哟,这个语音怎么就发出去了……”几声刺耳的响动后,慢条斯理的女声变成了低沉的男声,“怎么还没订机票?再过几天就是放榜的日子了,考得上考不上你都得回来再说!一个人在美国无依无靠有什么好的?别跟我说你想在那儿待到‘杀戮日’后,前两年日本这边闹得还不够,死的人还不够多吗?天知道咱们森野家为了这个破日子花了多少钱,还好和神社本厅签的合同款拨下来了,不然逃都没处逃——反正,不管玩没玩够都要在20号前回家,听见了没?!”
女人的唠叨。男人的催促。跨越十五个小时终究抵达。继而耳畔无声。
接着,洁白的餐盘被一道道呈上,精致的摆盘仿佛鲜活的艺术画。
颤抖的手指拿不起刀叉,只能将目光投向远方。落地窗外,浓黑的乌云沉沉地压了下来。而天气的变化与餐厅里的食客无关,没有人感受到风雨前的压迫,唯有轻快和缓的音乐在餐桌之间流淌。
你身上有股味道。我喜欢的味道。
“死”的味道。
森野深铃只觉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