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うれし かなし
こひし にくし
想いは 万華鏡
さびし かなし
こひし にくし
絆は 蜃気楼
==============================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春秋时分,化为付丧神。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人与器物的命运与缘分,无论善恶,在踏入这扇门时开始。
欢迎来到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
一期完结
小组http://elfartworld.com/groups/1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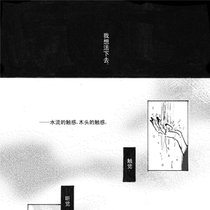
“阿啾!”來幸搓了搓自己的鼻子,“感覺好冷啊。”他把被子裹得更緊了一些,愜意地窩在枕頭上看著煙斗先生在書桌前工作的背影。這個噴嚏也沒能破壞他今天在和煙斗先生散步回來的好心情,他吸著鼻涕,悄悄在心裡回憶今天所見的景象,好像等不及要將那片被燈光照亮的櫻花寫在稿紙上了。
“都說了要穿大衣,這不是感冒了。”煙斗先生的背影與書桌上的燈光融成一片。來幸瞇著眼睛,迷迷糊糊地向對方說話。
“不是穿了嗎!這肯定不是感冒,而是被人掛念了……”
“哦?這是被誰掛念了?你父母嗎?”煙斗先生在桌前活動了一番筋骨,甩甩他的手腕,“買點別的東西吃吧?老吃米飯可是會得腳氣病的。”
“說是那麼說,可是沒錢啊。對了,煙斗先生,你覺得愛戶嶺這個名字怎麼樣?”
“還不錯,挺好的。”
反應太冷淡了吧,說說喜不喜歡嘛。來幸失落地摸了摸枕頭的一角,有些埋怨起煙斗先生對這般重要事情的冷淡。這可是我想了很久的名字呢……
“真的?那我就這麼叫你啦。嶺先生、愛戶先生……adore!”他在最後大聲說出來他在那個名字裡面所埋藏的意義,期待起對方的反應。
煙斗先生——現在是愛戶嶺了,在桌子前抖了一下。
“小孩子……別亂說。你知道那個詞是什麼意思嘛?”
“當然知道啦,不僅知道,我還要告訴我的名字來幸可以念做英語的like。”來幸說完,又開始為自己在外國人面前班門弄斧自己那夾雜著日本方言口音的英語後悔。他側過身去,好避開煙斗先生的反應,“睡覺了睡覺了,晚安,嶺先生。”
“晚安。”
“嗯,晚安……”
“怎麼了?”
“睡不著……!”來幸又翻了個身,他看到嶺從桌前起來,走了過來。
“我來給你講睡前故事。躺過去一點。”
來幸乖乖給對方讓出來能坐的地方。嶺俯下身坐下,不知道在想些什麼,遲疑了頗久。
來幸催促道:“快講吧快講吧。”
“那是挺久以前的事情了……某個男人生來就有作為榜樣模仿的長兄,還是說算不上長兄呢?總之對方是個值得尊敬的人吧。這就是故事的開端。”愛戶嶺緩慢地說著,來幸看到嶺那雙溫柔的眼睛在煤油燈下閃爍著十勝石般的光芒。不知名的火燃燒起來了,來幸抬頭看向自己的書架,正好瞧到放在書架頂部、好好保存起來的煙斗。
“他被當做長兄的替代品,被人們冠上了長兄的名號,名跡流傳於世。自己做過的事情也好,自己沒做過的事情也好,全部都被賦予了長兄的人生才有的意義。貴族,商販,平民,農人,奴僕……”
“長兄現在在哪裡呢?”來幸插嘴道,期待地等著故事的後續。
“不是這樣的,他的心裡有一部分在那麼喊著。我是不同的,我應該是與那個人不一樣的……然而,並沒有任何人理解,甚至連他自己也沒法說出口。被人期待的感覺總要比不被人期待的好。他就這樣與人們維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然後啊,某一天,叫著兄長的名字的人們請求男人道。”
來幸聽到了自己的胸口傳來砰砰的心跳,愛戶嶺輕淺的呼吸聲穿過厚重的棉被,送到他的胸口。他的眼睛透過愛戶嶺的話語,看到了那個年輕、被人們誤認為是兄長的男性。
被人當做他人的替代品,一定是很痛苦的事。
“‘你能為我們做一件小事嗎?’比起來請求,人們的語氣更像是在質問,‘如果是你的話,一定能更懂得如何討好權貴?如果是你的話,無論是怎樣的貴族婦人,都會忍不住瞧上一眼吧?如果是你的話,一定能很快地籌到足夠的錢吧?’……人們這麼說著,將他推上了高臺。”
“或許他曾經還說的上是討權貴喜歡,也或許他的樣子還算引人注目,但是只有那件事……只有金錢,他是確實做不到的。就這樣,他最終與人們失之交臂。意識到男人並非是兄長的人們,就這樣撤開了雙手……無論如何曾經努力去扮演他人,那個人最後還是沒有辦法討人喜歡。”
來幸看到嶺的雙眼被一團不定性的霧靜悄悄地凝結。而後,一種令人不安的瘙癢抓住了他的胸腔。自己並不了解愛戶嶺啊,他意識到這件事,感到自己之前的想法淺薄而愚不可及。對方不叫愛戶嶺的時候、對方不是自己的煙斗的時候、對方擺在貨架上的時候、對方擺在貨架之前的時候,這些全部都是松平來幸所不了解的。
“就這樣,他被遺忘在那裡,經歷漫長的等待。隨後,故事結束了。”愛戶嶺吸了口氣,揉了揉來幸的頭。力道很輕,但能感覺到對方的手指傳來的些微溫度。
付喪神也是有體溫的啊。來幸想。愛戶嶺沒再說話,只是為他掖上了棉被。
“嗯……”來幸想說點什麼,但他知道對方并不期待自己的話語,那股叫他覺得模糊而難以言說的感情,僅僅通過吞嚥的動過就能從舌尖上壓下去了。最終他鼓起勇氣,輕輕拉住對方的衣角。
“我可以要晚安吻嗎?煙斗先生?”他問。
“你幾歲了,小孩子一樣。”
“那麼,我可以給你一個晚安吻嗎?”來幸又問。
“請吧。”煙斗撩開了他額頭上的劉海。來幸象征性地、像母親對待自己那樣吻了嶺。
“我睡覺了,晚安。”來幸滿意地看到煙斗揉搓著頭髮,給自己捧起來自己的鼻子,“希望明天我的感冒就好了。”
感冒並沒有在第二天消失,反而更嚴重了。
來幸感到自己的喉嚨被一團什麼東西堵住了,一團病怏怏的氣還在向下走,頭腦也不怎麼清楚。狹小的房間在來幸看來就像燃燒來了一般扭曲,身體也是,無論是不是裹了被子,還是不停發冷。這種不適感催生出一種惰性,讓來幸不想起來。大概是發燒了吧。來幸想。
他很熟悉這種情況,每逢生病,最後都會發展成這樣的局面。雖然說不上什麼大問題,但父親就是以這作為來幸體弱多病的依據,不讓他出門。
不想起床……但還是要去打工。來幸想著,還是強迫自己起來穿好衣服。不工作的人沒飯吃。他提醒自己道。
“嶺,我出門了。”來幸向著在書桌前不知道在鼓搗什麼的嶺說道。
“你的嗓子怎麼啞了?”
“好像嚴重了一點。”來幸咳嗽了一聲,戴上自己唯一一頂帽子,“怎麼樣,戴得正嗎?看起來像不像紳士?”
“你先別去工廠了。”他聽到對方的腳步聲近了——一隻大手覆上他的額頭,付喪神的體溫傳達了過來,“你發燒了。”
“不行。好不容易找到了要我這種人也能賺錢的地方,不去工作怎麼行。”來幸嘟囔著,輕輕推開對方的手。腦子亂成一團,“我走了。不吃早飯去還來得及。”他給自己套上大衣,在地板微弱的傾軋聲中匆匆出了門。嶺原本想攔住他,卻被他躲開。
“真的別去了!”
來幸不知道為什麼有些窩火,或許是胸前那團叫人難受的霧氣讓他開始迷蒙了。他躲過嶺,快不下了樓梯。村上太太還在和家人吃早飯,並沒有注意到他。來幸就這樣上了街道。
路上的行人也變得不識相起來。來幸穿過擁擠的人群,但卻屢屢碰到陌生人的手背。七點的最後一班車算是勉強趕上,來幸和其他乘客擠在一起,等待火車慢悠悠地邁向洋火工廠。
像往常一樣,工廠的大門敞開著。製作洋火並不需要什麼技術,來這裡工作的工人多半像來幸一樣,沒有什麼長處。這份工作也收入低微,但比什麼都沒有要強一些。來幸回想起自己在逃出家門前曾經幻想的生活,雖然原本也曾預想過東京的生活會很苦悶,但多少對外界保持著一絲少年幻想。計劃總是高於現實所能帶來的境地。
他坐在桌前,包裝著火柴。工作單調又無趣,所有步驟只是像不停地向前滾動車輪一般運作。他擦拭了一會兒額頭上的汗,工廠很嘈雜,卻聽不到人聲。來幸在昏暗的燈光下分好火柴,他感到自己的頭腦緩緩下沉,如同浸泡在水中。
越來越冷了。
“怎麼沒精打采的?”來幸聽到身旁傳來了工頭的聲音。起初,他沒能明白過來對方是在和自己對話,直到成年的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才想起來。
“我不知道,可能就是狀態不好而已……”來幸聽到自己那有些刺耳的嘶啞聲音,唯恐對方識破了拙劣的謊言。
“感冒了,先回家去吧,明天好了再來。”
“可是工作……”
“我和他們說一下,不會扣你的。其他人能幫你做了你的份。”
來幸有些不知所措地接過這份好意。他支支吾吾地謝過了對方,帶上自己的隨身物品離開了工廠。不知為何,得到了對方的承諾讓他的腳步變得輕快了起來。現在還未到來幸平日下班的時間,街上冷冷清清,見不到什麼行人,只有出來買菜的家庭主婦在被樹蔭遮蔽的小道上閒聊。
回到村上夫婦的洋宅時,來幸想起他早上對煙斗先生生了悶氣。希望煙斗先生他不在意才好,要是他生氣了,就對他說抱歉。來幸這麼想著推開了洋宅的門。
愛戶嶺在樓梯上等著他。
“怎麼回來了?”
“在工廠裡叫人趕回來了……”來幸有些不好意思,他已經能想見對方笑起來的樣子。
但煙斗只是搖了搖頭:“我就說你這樣不行吧。”
來幸支支吾吾著上了閣樓。他脫下大衣和帽子,上了床。嶺叫他快點睡覺,自己則去樓下做了些什麼。身體還是很冷,但已經比早上時舒服不少。來幸裹著被子,迷迷糊糊地想到——煙斗先生是沒法被人看見的。隨後,他就在昏昏沉沉的知覺中睡了過去。
再次醒來時,愛戶嶺正坐在來幸身邊,讀著不知什麼報刊。閣樓的頂部傳來被雨水敲擊的一串聲響,嶺點了燈,讓室內還算明亮。
“燒已經退了不少,要喝水還是喝粥?”
“喝水。你會被別人看到的,想想一個水杯憑空移動向閣樓,那樣我就要被當成妖怪啦……”來幸嘟囔道,卻還是接過嶺遞來的水杯,小口喝了起來,“煙斗先生會生病嗎?”
“會吧?沒病過,所以我不知道。來,吃藥。”
來幸感到自己臉上燒成一片,他囫圇吞下嶺拿來的藥,靠坐在床上。他想象屋外的雨水打在屋瓦上,又跳起來,最後全都匯聚成涓涓河流,滲到地下去。
“好好躺著,買藥拿的是你的錢。”嶺又說道。
“那就好,不然我會愧疚的。”來幸聽從對方的指示,安靜地躺了下去。
“我也沒錢啊。”
“我知道啊,不是我在養你嘛!”
“好好,你厲害,你可厲害了。”嶺應付似的說道,來幸卻分明看到對方的嘴角掛著笑意,“快睡吧,吃了藥馬上就會想睡的。”
“我這不是在躺著呢嗎?嶺好像媽媽哦。”
“是嗎?應該是爸爸吧。”來幸聽到水杯被放下的聲音——然後是翻找書桌的聲響。
“不要爸爸。”來幸小聲說道,他拉上被子。閣樓的燈火還亮著,從書桌那邊傳來鋼筆莎莎的聲響。從閣樓狹窄的窗戶那兒,淌進來了半遮的月光。
“那我就當媽媽吧。睡吧,我就在旁邊。”
“嗯!”來幸窩在棉被裡,“晚安,我可以要晚安吻嗎?”
對方停頓了一下,來幸閉著眼,想到自己的要求或許太過分了點。他聽到自己的呼吸已經歸於平穩,身體也沒那麼冷了,到了明天,感冒或許就好了吧。他盡情享受著被對方照顧的這刻,直到感到額頭被對方蜻蜓點水吻了一下。
潮水般的暖意吞沒了意識。
“都多大人了還要晚安吻。”他聽到愛戶嶺這麼笑道。
终于有填了一点点……
越来越觉得物似主人型了……
---------------------------------------------------------
我想这个世界上是无所谓背叛的,背叛的感觉仅仅来源于对他人的不了解。年老的国王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也不过是因为误判了状况,继而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置信于不改信任的人最后又怎能说自己遭到了背叛呢?
好在我永远不用担心这样的失误。
合上那本文字未加润色的译本草稿时,我有些自得地想到。
近日来,大概是出于久寻线索而不得的苦闷,我没有再出门。这绝不是打算放弃的意思,找出当时那件事的原因是我唯一的目标,我这么告诉自己,而因为其他——我的情报搜集能力是一流的,这是无需证明的。现在只是遭遇小小困难时的稍作休息而已。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日子就变得清闲了,一方面,自如地控制思维的流向并不容易,也绝非可以和别人对练的招数;另一方面,家里时不时会到访一位争强好胜的大小姐——明明是她不了解的领域,却非要指手画脚。
简单来说是这样的,我主人家最近新来一位客人,也就是他妹妹,十文字绘梨佳,一个 “颇有主见”的姑娘。
原本她能看见我这件事已经够让我惊讶了,她却还嫌这样不够似的,一本正经正经地问哥哥:“这是谁?”虽然知道这主要是因为主人家一般不会常住什么外人——毕竟她不像他的胞弟那般好客——习惯于置身于人们思维之间的我一时之间还是受不了被别人打量的感觉。
更糟糕的是,这位大小姐还动不动要和自己的哥哥针锋相对,从处理某事的方法到最近某个新出台的政策……要知道,我向来是看不惯不懂装懂的人的,我并不见得比他们在座的哪一位少知道点什么,可我也更惯于聆听,更何况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呢?
于是我便试着在政臣离开时私下建议她安分一些,不要动不动就高谈阔论:“这样说不会讨人喜欢的,就算是哥哥,也还是收敛点为好。”
谁知她回了我一句:“这又与您何干呢,这位‘先生’。”
而我向她哥哥提起她时,又得到了:“她一直如此,你也别太在意。”的敷衍,一幅要当和事佬的架势,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主人呢?
果然这次的劝告也和先前的几次一样被当成了驴肝肺啊,我有些自嘲得想到。
不过,好在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为了一日日迫近的秋天而担忧了,这也算结缘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了。
于是我向那个整日游手好闲的家伙借来了他最近翻译的英文书。毕竟总是听到故事片段,但就是不知道完整情节也挺烦的,对吧?
这么想着间,我已经来到了那个家伙的书房门口。
“我来还书了。”我敲门的那只手还举在半空,门就自己打开了,确切地说,是房间的主人的就已经来开门了。
“我等会出去一下,你有空一起来么?”实际上,他当然知道我有空,我最近恐怕已经闲得肉眼可见了,所以才引来这样的安慰。
去他父亲家。我同样听到了他没说出来的后半句。身居要职的官员或许能给我带来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那是一位传统以至于古板的老先生,无限接近于自己曾“感受到”的那些形象:严厉,严肃,一丝不苟。让我在感受到这些想法的第一秒就迅速整理了自己的衣着,即使他并不能看到我。相比之下,我的这位出身行伍的主人却依然是日常着装,这家伙就没有正式一点的时候么?
就我所知,这次他被他父亲叫去,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弟弟又惹出了什么麻烦——恐怕是不听从长辈命令之类的老一套,那种事我早已习以为常了。多代的家族往往如此,颇有一些就算死后也要掌控着家族的架势。
而我身边年轻的主人则老套得抱着强烈而无力反抗之心,表面上阿谀奉承,内心却打着其他小算盘。这种事情我也不是第一次见到,最终往往会归于平静,就像严寒中的阳光,看似耀眼,却毫无用处。但是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阳光下的雪地上一无所有,干净的没有一丝阴霾;紧闭的大门上贴着小小的告示“内无武器”,反而让人隐隐不安。我忽然觉得,倘若他真打算计划什么,我倒是很想协助一下。说不上这是出于看热闹的心情,还是对不同结果的期待。
而他的父亲也同样对此一无所知,甚至对于份叛逆之心也毫无知觉,只是单方面继续着他的灌输,迟钝之处真是令我咋舌,有其父必有其子,看来这句话反过来说也不是不行。
不过做儿子的似乎并不急于谋划出一个计划,一如他安安静静地,表面顺从地听完了他父亲的训话,最后点头称是,保证自己会努力后劝说胞弟后,乖乖地夹着尾巴回去了,末了似乎是要装得更像一点似的,还可怜巴巴的朝我来了一句:
“真是想求他们别再针对我做些什么了……”
真是难看啊,大男人还要装可怜。但是表面上的安慰还是有必要的。
“他们根本没打算那样干。”
我不知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翻出一个白眼。


“咦,不是说开店吗,我怎么不记得现在放假啊。”来客垂眼往脚边的伞上看了看,又在走了。
“我都不知道他一大早急匆匆跑去哪儿了,别人怎么会知道啊,”就站在旁边的千茗揉了揉太阳穴,“看不到人还真不太方便..。”
…………
好久啊。
虽然很不想在意,但是头一回有出去了这么久的一次。想象着'一会儿'秋山回来又会跟他解释什么。
算了。这次我去找你好了,凭这独一无二的念…闭着眼瞎撞都能找到在什么地方。
“我出门啦。”
感谢苍叶啊啊啊忙期末忙的差点忘记……15分钟极限卡(……)作为强迫症打卡也要打的完整才行!!!!所以写了20字微小说(靠)
以下是规则。
CP:蕾・米勒x五月七日都
1.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欧美影集/电影/书籍/节目/音乐/动漫/电玩/中的角色或配对。
2.挑选十道你喜欢的文章类型,等级随意。
3.每一道题目英文以10个单字为限,中文以20个字为限。
(若完全以英文写作再翻译成中文,则中文部份无字数限定)
(若中英参杂(如人名和专有名词),一个英文单字算一字中文)
4.写完十题然后指定下一位。
5.大功告成,发文。
Adventure(冒险)
与蕾・米勒结缘,是五月七日都人生的第一次冒险。
Angst(焦虑)
她总是焦虑的。对于自己是凡人这件事情。
Crime(背德)
樱花雨下,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为蕾・米勒所倾倒的那一刻,都就已经成为了擂台上的输家。
Fantasy(幻想)
五月七日都总是抱着幻想的。对于自己其实并不普通。
First Time(第一次)
“都,第一次驱使付丧神是怎样的感觉?”
面对姐姐的疑问,她陷入了沉默。
与其说是驱使,不如说是自己已经沉沦
Fluff(轻松)
“您真是太坏了……太坏了……”
看着被欺负的都红透了脸颊,转过头去继续认真练习,蕾轻松地笑了出来。
Parody(仿效)
“你成为巫女的梦想,其实只是想仿效你的姐姐吧?”
Romance(浪漫)
她们曾拥有最为浪漫的、樱花雨下的邂逅。
Suspense(悬念)
却不一定拥有同样浪漫的未来。
即便指引命运的签牌书写着“大吉”,也未必是走向幸福的道标。
Time Travel(时空旅行)
就算再来一次,都还是会选择与蕾结缘。
她想要改变。无论重复多少次无用功。
Tragedy(悲剧)
若是有一日,蕾失去了她的心——
都只能坚持不懈地呼唤她,即便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拒绝。
而蕾的记忆将不再有她的冰山一角。
Poetry(诗歌)
黄昏漫步不忍池畔,淡月溶溶,莲荷残折,怎堪不坠相思泪?
独坐长酡亭饮冷酒,怎比你我恋住江,长饮如梦之甘泉,岂知‘永恒’不永恒?
(引自与谢野铁干的和歌《败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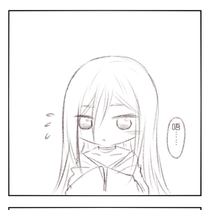

写作大暑读作小满【【【
拖了这么久还这么短小!!!!我真的是已经不会写中文了!!!!
大概会有修改——
扑通一声跪在落面前,以头抢地
------------
合上的眼帘之下看见的黑暗并非空无一物。他知道面前是那低矮略微倾斜的顶,想起不知谁人踩过木板发出吱吖的声音,感觉到碎屑悉悉索索落到他的脸上或被子上。他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悄悄抹去赃物的袖口上,留下朽木与灰尘的气味。
“该起来了!!!就知道睡!快点起来吃了饭,都给我出去干活去!!”
猛烈地捶门声伴随着一位老妇人的骂声传遍整间屋子,警报般刺激着神经。个室里模模糊糊有许多人影,闻声都纷纷迅速套上衣服爬起来,打开了门跑出去。
门缝间洒进的光仍是灰蓝色。他的视线追逐着那些人的背影远去,而自己只是缓缓撑起身体,犹犹豫豫地站起来。
这间孤儿院,他曾经的居所,弱肉强食的大社会中,五脏俱全的小社会。来自精神,现实的鞭挞,被赶着不许停下工作的步伐。他与众多和他一样的孩子一起经历,有的沉溺痛苦,有的变化适应。而自婴儿时期就接受如此“教育”的他,幼小的心中甚至都没来得及发育出接受感情的末梢,就已逐渐积起厚厚的茧,那些微的“感情”,几乎再无机会被触碰到。
不过这让他如期望一般变得十分能干。不存在同龄人常犯的叛逆,仅仅为了“生存”与“工作”而活——他是他饲养者的绝佳的赚钱道具。身体健壮(脚步虚浮),思绪明晰(视界摇晃),话不多说高效率完成工作(稍微两下推搡就跌倒在地),几乎失去睁眼的力气。
奇怪的接续,无数雷同的记忆中的特异点,抓住的这一天的感受似乎尤为鲜明而特别。
“没事吧?你怎么了?”
突然出现一个清晰的影子——用白色的轮廓来描述应该更为妥当。成年男性的体积,视觉和触觉上都感受到的可靠而柔和的光。
他应该是抓住了男人的大袖子。
“头晕晕的。”
“让我看看。”
蹲站着的男人伸出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有点发烧呢。我去给你拿些药吧。”
“时海先生!”
“我,今天想休息,可以吗?”
听见了希冀的话语,这一定是非常珍贵的,他仍保留的,仅存的孩子气。
“……不行。”
“今天还是不要呆在这里比较好,大概。”
男人握了握他抓住自己袖子的手,随后轻轻拍开。
“该去打工了,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头顶传来温柔的力道,取代了手心凉风吹过的刺痛。
“我知道了。”
睁开眼画面归为虚无的白,虚假的声音也听不见了。可是自始至终也没能从他眼中看见一张清晰的脸。他所想的……多半是那白色轮廓的男人。零零落落点缀散落在记忆的黑洞中,偶尔有一片如这天一般格外明亮,无序而自然得展开繁星闪耀的银河,如同具有生命的活力。
但那构成的本质,却并不是有生命的“生命”。
-------------
“!”
“怎么样?”
时江看起来已经等待许久,迫不及待问道。松井缓缓摇头,莫名放慢的动作像是在思考着什么,也像是不忍看到时江对着结果的回应。
然而他那细长好看的眉还是纠在了一起,组起那最为熟悉的愁眉苦脸。“嗳…还是不行吗……我以为借返魂香的力量,一定可以找到什么线索的……”
“时江,你有没有兄弟?”
“什么???”
突然发话的松井一问问得时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重新回忆了以后,才发现。小时候我遇到过一个人,与你长得很像。但也不太一样。叫时海。”
“这……”
“我是,不知道……”
化型之后大多数时间都是孑然一身的时江,别说与自己长得像的付丧神,就是一个与自己一样没用的付丧神都没见过。况且付丧神又不如人类,无父无母,无亲无故,兄弟姐妹之类的,听着就觉得荒唐极了。
“噢,这样啊。”
观察了好一会儿时江奇妙的神态变化,松井依然是平平淡淡地作出反应,普普通通地示意准备离店回家。
和时江不同,他是无法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
仍未察觉角色颠倒的两人,怀着各自的思绪踏入小雨夜幕中的东京街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