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うれし かなし
こひし にくし
想いは 万華鏡
さびし かなし
こひし にくし
絆は 蜃気楼
==============================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春秋时分,化为付丧神。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人与器物的命运与缘分,无论善恶,在踏入这扇门时开始。
欢迎来到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
一期完结
小组http://elfartworld.com/groups/1381/
*星星的故事来自《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
*女孩子的友谊真是太好吃了!入股闺蜜组!入股!爱子真帅啊!!^qqqq^
————————————
-0-
有一天晚上,一颗星星从天上掉下来。穿破一栋房子的屋顶,落在灰泥地上。
住在这栋房子里的女人听到轰隆声,跑来一看,发现了一颗星星。
-1-
这一天,鹿又凉子过得十分不顺心。
本想翘课去看看书,哪知半途遇上了难缠的幽灵(从年初起,自己的好运气便活像透了支,遇着鬼怪撒盐念咒都没用)。少女拔腿就跑,顺势拐进校舍,和一名无辜路人撞了个满怀,匆忙道歉,继续奔跑,终于在精疲力竭时甩掉了该死的“跟班”。她哪还有力气翘课,只能灰溜溜回到教室,挨过了最后一节课,好容易放了学,一路平安无事回到家,习惯性地掏出钱包——
“……”
凉子傻了眼。钱包不见了。
衣兜都快掏烂了,书包也翻了十几回,她干脆一步步从房间倒出去,扫雷似的左瞧右看,结果在门口又撞上了刚回家的兄长。
凉子被磕得七荤八素,心想自己今天什么都没做,光撞人撞鬼去了。
“怎么了你,这么鬼鬼祟祟的。”
鹿又诚一拍了拍凉子头顶。
少女想着自己钱包里还收着刚发的零花钱,真是哑巴吃黄连,苦着脸回答:“……没事。”
诚一仔细打量过她,像在确认什么,随后换了鞋,揽过她的肩,轻快地说道:“有事就说,没事就开心点。”
问题是开心不起来。少女把小脸拧巴成了抹布,在兄长的注视下只能扯出难看的笑容。见状,诚一叹了口气,揪了揪她的脸颊。
“丑死了。”
“……你走!”
-2-
不论怎样,零花钱还是很重要的。不然本月的买书大计未半,她的钱包就先“中道崩殂”,这也未免太惨了点。
于是,翌日,凉子揣着颗惴惴不安的心脏,边走边回忆昨天的逃跑路线。
从拐角退至走廊,沿着廊下慢慢步去——甩掉那鬼之前,她好像还“撞了车”……
“……啊。”
凉子眨眨眼,不由出了声。
陌生少女倚在窗前,原本正把玩着手中钱包,敏锐地注意到她,便转过头来。
日光从窗隙间漫进来,跌进她茶色的长发中,熠熠闪烁。那双眸里仿佛盛开着一树樱花,微风溜了进去,试图摇荡粉海,却掀不起一丝波澜。
真美啊。
凉子看得呆了,竟觉窘迫不已,搜肠刮肚也找不出话来,只好结结巴巴地开口:
“请,请问——”
“给,你的钱包。”
两人的话语撞在了一起。
凉子一愣。少女向自己伸出的掌心里,正躺着一个小巧的钱包,流苏挂饰自她指间垂下。
这式样太熟悉不过了,甚至还让她忧虑了一整晚——鹿又凉子赶忙接过钱包,确认无误后便深深鞠了一躬,激动地将钱包捧在胸前。
“谢、谢谢您!我还以为找不回来了……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才好……”
“不用了。”
茶发少女淡淡说道,想了想,又补了一句:“以后记得放好就是。”
“您说的是……”
凉子不免赧然。
“嗯,就这样。再见。”
她便不再多说,挥了挥手,径自背过身去。凉子慌忙又鞠一躬,再直起身时,少女已然踪影全无。她细细摩挲着手里的钱包,看了看女孩儿方才所站的位置,眨了眨眼。
……这位置和这女孩都莫名眼熟。
“啊。”
凉子恍然大悟。
——这不是昨天那位“无辜路人”么!
所以那女孩其实是碰巧捡到了她的钱包,今天特意在老地方“守株待兔”,想交还给失主是吗……
等等,她怎么成兔子了?
凉子被自己的比喻给噎着了。
-3-
事实证明,“路人”其实并非路人。稍一打听便能知道很多事,毕竟那头茶发在这学校里惹眼得很。只有凉子这种平日里翘课看书、没有朋友的“异类”才不知道爱子。
总结下来三个标签:翘课王。神出鬼没。高冷。
凉子哭笑不得,在高年级教室里挨个儿瞅了个遍,才不得不确认了标签的真实性。
看来再想碰面就只能看缘分了。
少女踏过上课铃,漫不经心地踱着步。甫一拐出校舍,迎面便撞上了熟“人”。
“……”
那双色迷迷的眼睛舔舐般紧盯着她的脸颊。她不由打了个寒噤。
天知道这色鬼怎么还没走!!
凉子抓狂了,脏话已经堵在了喉头,又被她死命咽了回去,因为经年累积的教养不允许她这么做。但就这么逃跑也未免太没出息了些——并且还不一定能逃得掉。
该怎么办?
她不甘示弱地瞪了回去。
“站在这儿干什么?”
“……嗳?”
闯入眼帘的倩影渐渐明晰。凉子吃了一惊,只来得及挤出一个音,色鬼便趁机黏了上来。少女一个激灵,赶忙躲开,下意识地挨近了爱子。
“你在干什么?”
爱子偏过头来,淡淡问道。
“我——抱歉,没什么,只是被缠住了。”
凉子使劲儿瞪过去。爱子则微蹙眉,似乎不明她意,四下望了望,复又开口道:“……‘九十九’?”
她一怔:“您怎么会——啊,不,不是的。是……”稍一犹疑,“是幽灵。一个色鬼。”
“这样。”爱子了然地颔首,想了想,问道,“在哪个方位?”
“嗳?”凉子呆住了。她就这么信了么?
“色鬼在哪个方位?”
女孩儿的气场竟慑住了她。凉子愣愣地伸出手去:“就……就在这里。”
“好。”
爱子毫不犹豫地向前迈上一步。
真奇怪。“九十九”和“幽灵”理应是不同的存在,但爱子表现得就像是……看得见鬼一样。
只见爱子双手并拢放于身侧,沉下重心。那色鬼并不惧怕她,流着口水还想继续骚扰。说时迟那时快,爱子瞄准时机,扬手劈下——刹那间风啸云息,似有虹光迸溅。
色鬼竟被“砍”中了!
他哀嚎着,在半空中盘旋了两下,便化作了一团青烟而去。
鹿又凉子目瞪口呆。
女孩儿继续问道:“色鬼还在吗?”
“……消,消失了……”
“那就好。”
爱子这才拍拍手,转过身来,看着瞠目结舌的凉子,挑眉道:“你怎么了?”
“我……”
舌头活像打了结。有太多想问的问题了,可她什么也问不出来,只能干巴巴地说:“谢,谢谢您……我欠您太多了,真不知该如何报答才好……”
爱子眨眨眼。
“那就别用敬语了。”
“可您是我的恩人……”
“那恩人的话你不听?”
“不、不是……”
“嗯。哦,还有,叫我爱子就行。”
“嗳?可是……”凉子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爱、子。”
这一字一顿的重音让凉子觉得莫名的憋屈。
“爱,爱子……”
“好。”她满意地轻笑了笑,“你叫什么?”
凉子仍有些怯怯,张了张口,声音却仿佛不由她控制了。
“——凉子。鹿又凉子。”
-4-
发生了什么事。女人的丈夫问。
一颗星星,女人回答,我们没有小孩,我们可以把它留下来。
但是丈夫可不高兴。我们要星星干什么?它没有眼睛,看不见东西。
但是她会发光。女人回答。
它没有腿,不会走路。丈夫说。
但是它会滚。女人回答。
-5-
她们的熟络从乌龙事件开始,仿佛命运的顽童随手一拨弄,两条本应平行的直线便就此交汇。
许多时候是偶然的。这学校很小。翘课,散心,甚至只是走在廊下,都能碰面。爱子不喜她三番五次提及答谢,凉子便只好默默收进心底,偶遇时相视一笑,或淡淡交谈两句,不外乎“去哪里”“没碰见鬼吧”一类的关心,还有诸如“来找我,我替你收拾”这般的保证。凉子心头一暖,嘴上倒习惯性说着“没什么”“很安全”,往往得到的都是爱子一针见血的指摘。
“逞什么强。当心再丢钱包。”
凉子扁扁嘴,没法反驳。
而那一日之后,她本该有许多问题,却一个也问不出口。
爱子不说,她便不问罢了——就当是回报爱子无条件的信任。
然而,这学校的确是很小。小到不知不觉间,她们的谈话竟被旁人当成了谈资。
凉子是从不去管其他人背地里说了什么的,一怕麻烦,二是没必要。她只是觉得歉疚,让爱子也因此遭受流言蜚语,正思考着如何是好,脚步一刹,差点又撞了上去。
“别东想西想的。“来人淡然提醒,语锋一转,带上了促狭,“小心钱包。”
“抱歉……”凉子哭笑不得。
“没事。”爱子打量着她,又伸手拍拍她的脸,“有什么心事么?”
“……没、没什么啊。”明显底气不足。
“不说也行。不过,憋在心里不好。”
爱子轻描淡写地转了话题,“凉子这是准备去哪儿?”
少女还未回答,楼梯上便落下了女孩子们谈笑的声音。掺着嘲笑的对话重重砸了下来。
——你还别说,“异类”和“异类”做朋友,还真是般配。
——哈哈,算她们有自知之明。
……
凉子闭了闭眸,攥紧了拳,再缓缓松开。笑声戛然而止,女孩们站在阶梯上,紧张地望着刚才对话里的“主角”。凉子拽了拽身旁人的袖口,想了想,轻轻唤道:
“爱子。”
顷刻间,茶发少女变成了台风眼,刀光般凌厉的怒气化作了呼啸过境的台风,而爱子浑然不觉,只是死死盯着女孩们,樱色的眸子里火光冲天。
“……爱子。”
凉子抿了抿唇,索性捉住了她的手——那细微的颤抖令凉子顿时失了言语。
“你,你们要干什么!”
其中一个女孩被爱子的气势吓住了,先发制人的问话里底气全无。
不能这样下去。鹿又凉子深吸了一口气,强自镇定后,微微一笑。
“三位贵安。”
闻言,两个女孩不由面面相觑。她们这里哪来的“第三个人”?
凉子见状,不疾不徐地继续说道:
“在您身后的这位一定是长工阿姨吧?看上去真和善。”
那女孩瞠目,顿时脸色大变,面如金纸。她哆哆嗦嗦地拉过身边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踉踉跄跄地和凉子二人擦肩而过——还瞪了她们一眼——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总算吓跑了。
凉子在心里叹了口气,整理好心境,朝着仍旧怒气冲冲的爱子莞尔说道:
“走,咱们翘课去。”
-6-
推开杂物室的木门,“嘎吱——”一声悠长地溜了进去。空气中弥散着同样古旧的尘粒,在泻进的阳光里泛出薄金色的光萤。书架歪七扭八地立于房内,凉子步伐轻快地走上前去,拍了拍书脊上的灰尘。
“爱子你看,好多书呢。”
而爱子仍是不答话。
凉子自顾自地说:“这里看样子已经废弃很久了。我也是前几天刚找到的。环境和氛围绝对有保证,是吧?”
爱子望着她,眼神晦涩难懂。
片刻,凉子才苦笑出声:“你那时……感觉随时都像要冲上去打人似的,我不想你为了这事被她们抓住把柄。”顿了顿,她狡黠地眨眨眼,“而且,我可没说谎。”
——的确是有个长工模样的鬼魂跟在她们身后,看上去像是惨死,面带怨恨。
爱子愣了愣。
“不过,说到底,都是我的错。”凉子垂了眸,“如果我不是个怪人的话……”
“等等,你在说什么?”
少女终于开口了,急匆匆地掐断了她的话,“明明是我——”
两人皆是一怔。须臾,一齐笑了开来。
原来如此,你我都是他人眼中的“怪人”啊。
凉子侧转身去,随手拿过书架上的小说。她听得爱子斩钉截铁的语气:“我知道你不是。”
“嗯。”凉子应了一声。我也知道你不是。
时值三月。万物复苏。暖风轻巧地揉乱鬓发。
鹿又凉子从书中抬起头来,瞥过身旁抱着书沉沉睡去的爱子。
她笑了,忽然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星星的故事。
-7-
不久星星开始上学。老师教的东西,它一学就会,而且不会忘记,但是它不会说话,所以大家都以为它很笨。
一颗不会说话的星星。丈夫说。
但是它会唱歌。女人回答。
它唱错了。丈夫说。
但是很好听。女人回答。


【上接【http://elfartworld.com/works/137045/】的簡短間章(過渡)……完全沒有什麼可以看的超短超平淡無聊日常】
【劇情的一小步,水龍敬本的一大步,5%】
從岡山到兵庫花了些時間,但並沒有來幸想象的那樣漫長。途中交通工具多半是坐馬車或是伸手攔下去集市的農民、戲團之類。到了兵庫後,來幸在當地兜了圈子,這才在打聽後坐上去往大阪的火車。
“小哥是真的不知道去東京要坐火車?”回想起自己發問時,對話的農夫詫異地問道。
“確實是不知道啊……”
照著車站的販售的地圖所寫,來幸坐上了去往大阪的火車。
途中的風景漸漸從明媚的田園風光變成了發達的城市模樣。龐大的工廠盤踞著,吐出濃濃煙霧,與在照片和書籍中所見到的景象比起來都要宏偉,完全超出了松平來幸的想象。他趴在車窗上,聚精會神地看著車外的風景,那小小的愉快被喚了起來,三等車廂污濁的空氣瞬時便被忘得一乾二淨。直到鄰座女人的孩子哭了起來,他才回過神來。
臉上長了麻子的婦人低聲哼唱著,好讓孩子安靜下來,接著她又不好意思地低下頭去,小聲向身旁一位打扮得漂亮的女人說了什麼。另一個女人在聽過這位母親的耳語後,便脫下自己的羽織,立刻站了起來,用羽織擋住了這帶孩子的婦人。
來幸好奇地看著她們的一舉一動,卻被時髦的女性瞪了一眼:“男人不要看這裡!”
“對不起……”來幸漲紅了臉,移開了視線。對面坐著的中年男性咳嗽了一聲,車子裡的人便低下頭去看報紙或是望著不知哪裡發呆。
過了一會兒,嬰兒的啼哭聲止住了。女子華麗的羽織後傳來了吮吸的聲響。
列車還像往常一樣發出來規則的聲響,可是,這對來幸來說好像已經有些不一樣了。他倚在窗戶上,想象著那兩位女人的關係——看年齡,大概是姐妹吧,不過,也有可能是好友,或是親戚,兩個人一同踏上旅途——正當他胡思亂想的時候,火車靠站了。那帶著嬰兒的婦人匆匆將行李拿上,小跑了出去。留得衣著華麗的女人在原地。
車廂又陷入了寂靜。
大阪之後,是京都。京都是來幸曾在小說裡頻頻見過的城市,因此他在這裡停留了一陣。不過,大概是因為自己的路線不太對,並沒有看到書裡所描繪的景象。
一直以來期待的金閣寺倒是相當夢幻。且不提淺金色的廟宇,光是水景便能讓人沉浸進去。湖邊的樹木生機勃勃,建築腳下的湖水燦燦生輝,恰逢夏末,天色也被映得明亮。
進入昏暗的寺廟內,來幸看到了苦讀經書、赤裸著上身的僧侶。
大堂中央裡擺著來幸叫不出來名字的佛像,父親對宗教向來是不聞不問的態度,因此來幸並不能叫出那尊雕像的名字,只是呆站在那裡盡可能去理解那宗教的象征所蘊含的美。
直到黃昏落幕時,他才像想起什麼,飛也似地逃出寺廟。他奔跑著,感到腳下的地面在不停地湧動,好像要追上他似的彎曲、延伸、吞進他的腳步。心跳劇烈地搏動著,等到跑到他再也跑不動的時候,他便低下頭喘氣。
完全不一樣啊。
他在那個書房裡看到的世界,和真正的世界完全不一樣啊。
他大口喘著氣,為這件事恐懼又欣喜,隨即趕忙前往下一個地點。古都遠遠沒有金閣寺要來得驚喜,不過,在旅途上見到的趣事和厲害的人,都比以往要多得多。
京都之後,離家出走的旅途又加速了許多。
火車先是經過滋賀縣,再到愛知。接著,從愛知的碼頭出發去往東京都。甲板上比平日要更難感覺到四季,日子更是過得緩慢。
一開始看到海景時的驚喜,慢慢成了對再次登上陸地的期許。船上真的很無聊,原本來幸想試著寫些東西,卻發現船的顛簸讓人坐下來就暈。
不得已,來幸只好和船上的水手聊起天來。對方的口音很濃重,一開始時有些聽不懂在說什麼,日子久了才逐漸習慣起來。不知是不是因為旅途太過無聊,對方總會帶著在岸上聽聞過的故事過來。
到了西曆十二月初,船終於穿過狹長的東京灣,停泊於東京的港口。
再度站在結實的土地上令來幸不禁鬆了口氣。他伸展開四肢,慶幸再不會聞到海港的腥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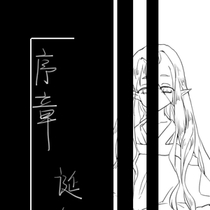

改完版
修正了一些小bug
添加了伏笔
引用的作品不符合时代背景请见谅
空太郎从咖啡馆走回了二楼,夹在指尖的是一盒没开过封的火柴——“徒然堂咖啡馆”,底下还印着些地址联系方式之类的小字——每天只点一根的话,这盒火柴大概能用上好一阵。
烛台上的半截蜡烛静静地立着,与昨天熄灭时别无二致,不过以它的长度来说,撑不过今晚了。
这是空太郎再次醒来的第三晚,也是自己点燃蜡烛的第三晚。
醒来或许是个不恰当的措辞,他只是处于什么也看不见因此不得不假寐度日的状态罢了。只要燃起烛火,即便没有人形,他也能“看”到别人的想法。并不是听到别人脑海里响起的自言自语,也没有什么嘴唇的开合、声带的震动,仅是一种以他能理解的方式将别人的思绪呈现在他眼前的,和嗅觉听觉别无二致的感官方式,他习惯将其视为阴影。
的确就像日光下得人影那样清楚分明。
如果天上的太阳也的确穿透人心,那就无怪乎一代代人类将其奉为神明了,他这么想到,没有什么他穿透不到的地方。
刚得到人形的他将这归功于点燃的烛光,然而那个能够点燃油灯的“少年”则否定了这一想法。
“你看不到么?”几年前的今天,自己也是这么端详着自己的本体,询问那个与自己本体相似的付丧神。外貌平凡的烛台除去抓握的部分外,铜制的主体已不再光亮,底座花纹的缝隙里泛着些绿色,述说着它所经历的的不短不长的历史,烛台上蜡烛的顶端仿佛富士山的山口,被熔融的蜡液迫不及待地溢出那个不大的凹陷,又在冷空气的阻拦下不情不愿地停下脚步。
不远处,貌似少年的付丧神愣了下,四下望了望并无他人,才意识到是在和自己说话,下意识地张了张嘴,似乎有什么答案呼之欲出,然而它终究没有出来,少年又将它咽了回去。
最后还是空太郎不耐烦地把本体放回桌上:明明简单的否定就好,冒出来的却全都是毫无头绪的话语,既混乱又无聊。即便不用能力,也能读出对方满脸的疑惑。
然而就是这个畏畏缩缩,满肚子混乱想法的家伙,却莫名其妙挺过好几个造化之日,该说是傻人有傻福么?不过自己也没有维持人形的必要也就是了,所谓的有缘之人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困惑哪怕一分一毫。
空太郎并不是喜欢自讨没趣的家伙,这也不是他第一次交流失败。回想起去年……
微寒的春风吹进来,并没有听到习以为常的风铃声。尽管是旧式的陶土风铃,甚至没有一层釉,而底下坠系着的纸片上用好看的花体字——那是什么字体?意大利还是其他什么国家的?——叙说着一句话“I had the keys but no instructions*”。
不过这句话的含义并不是由本人告知空太郎的,说本人或许有些不太恰当?总而言之,是他自己知道了这件事,而疑惑的源头并未开口说过一句话,尽管她的思绪曾使他感到好奇,甚至可以算得上有一丝着迷。
犹记得当时,新装的路灯并不比天上的繁星逊色多少,深紫色的最后一丝晚霞也即将匆匆谢幕。时至今日他也说不出,风铃声和那沉沉地思绪,究竟哪一个是晚风先送来的。
他走向窗边,旧日那个风铃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不知何时站在窗边少女,那并不是他所熟知的少女。
印象中出游的日子就是这天晚上,同时也就是俗人眼中所谓的百鬼夜行,然而随着现如今上至数学、物理,下至电灯、水瓶一股脑的传入,这种说法越来越被视为无稽之谈,警觉如夜巡的的士兵,也没有发现分毫的异常。
当年旧主手下操练的士兵,是绝不会如此懈怠的。空太郎并没有亲眼见证过作战时的种种,但他对此坚信不疑,要是他是能够带上战场的武器就好了。
尽管不满于那些夜巡兵的粗心大意,他还是套上了一身类似的军装,毕竟这也是离他心目中的军人最接近的概念了。
在他还没有化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不能分清说出来与没说出来的话语。没有谁是可以真的不假思索说出什么的,而他看来,说话不过是将一句话重复几遍,和那些在脑子里一遍遍打转的念头毫无区别。直到他所悉知的第一位主人的孙子的孙子都能用与他父亲如出一辙的话语教训自己的孩子,他才第一次睁开了双眼,意识到了浓重的训斥来自于谁,浅浅的不满又来自于谁——稚嫩的思想给予他的刺激并没那么强烈,就像声响有大有小,影子有深有浅一样。
这一点对于付丧神来说也不例外。
付丧神之间的经历大相径庭,思想也因此千差万别,不论是样貌年轻却背负着重重阴影,还是像他身边这位着巫女装的少女,身量已足,想法却与孩童无异的,都不足为奇。
“我是你的话,现在已经在准备晚上出门了”军绿衣装的付丧神适时打断了那些毫无营养的怀想,“一朵云根本就不值得看那么久……”
原本柔和的思绪瞬间像碰到火星的爆竹那样炸了开来,爆发出怒火几乎可以灼伤自己,不单是言语上被冒犯到的不满,也包含有被人捅破秘密时的气恼。考虑到空太郎的能力,怒火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喻。不过挑起事端的一方并没有直面这阵怒火的打算。
“行吧行吧,你好自为之。”触了霉头的空太郎摆了摆手,向楼梯走去,难得好心却被当成驴肝肺,果然自己应该少管闲事。
年轻人往往是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这句话似乎也同样适合用在青年模样的空太郎身上,尽管他的年纪早已不是一个青年了。
“之前那个风铃,怎么了?”
浊化了。浮现在他脑海里的只有这短短的三个字,诚然,词语即沉默的一部分,是可以被说出来的一部分*。但没有声息的三个字此刻比白纸黑字的判决书更加鲜明,此外就是无法辨识杂乱声音,仿若收音机里的白噪音。
“……然后呢?”
消灭了。
怎么会呢?
空太郎几乎要喊了出来。
当时明明没有感受到混乱的情绪,即便是一丝一毫不满也没有。难道是因为哪一晚忘记点上蜡烛了?
仍旧处于错愕之中的付丧神魂不守舍地走下楼梯,对不慎在楼梯撞上的男子也不过是略略点头致歉,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交汇过一瞬间的视线,没有发现这远不能算上是常事。
你看到的不过是些在日光之下,阴影之上的东西而已。
阅读思绪的付丧神猛然收住踏出的半只脚,扶在楼梯上,忍不住回望向沙发上那个小小的人偶。徒然堂的店长端坐着,空白的思绪如同收不到信号的收音机,而方才不慎蹭到的男青年,已经拐过弯,去到空太郎出来的房间了。
*珍妮特·温特森《守望灯塔》




序章时候摸的鱼,时间不对就放到现在才发……
看不到的人也有看不到的乐趣(?)
————————————————————————————————
他感觉到视线。
转过头时,却空无一人。
「……」晓之助沉默地看着那把似乎想假装自己只是路过、但一直竖在原地还可疑地颤抖不停的扫帚,不管是左看,还是右看,都没有看到有人操纵的痕迹。
他看到一把浮空扫帚自己在动。
有那么一瞬间,晓之助突然想起了那些关于这座宅子流传的传言。
他曾经觉得那些「幽灵宅邸」什么的都是无稽之谈……所以传说还是有那么些可信度的吗?!
如果要这么想下去,当时十文字政纯热情邀约他住进来的态度也变得可疑起来……
突然「啪」的一声,就在他胡思乱想到天边去时,抬头一看那把扫帚已经被突兀丢在了原地,而刚刚的视线感也瞬间消失。
他一头雾水地走过去,蹲下身看着孤零零躺在地面,怎么看都是普通竹帚而已的扫把,陷入无限困惑。
「什么跟什么啊……」
「嗯?那个哦……」
次日听到他的疑问,屋主则是也露出茫然的表情,过了好一会儿、才「啊」了一声,「我明白了,你说的那个嘛……」
「不用管也可以的啦?」然后男人吃吃笑起来,像是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般,拐弯抹角地不打算解释更多,「总之,不会有伤害的,倒不如说也许是『幸运』也说不定呢。」
「幸运……」
晓之助无言,完全不知道自家房东在卖什么关子。
正打算追问时,就被塞了很难找到的偏僻书籍,他下意识地啃下去、再一抬头,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转到傍晚,而对方早已逃之夭夭。
……结果,他的困惑反而更增多。
又是转天之后,他无意中再次目击灵异扫帚。
还是同一把,在中庭里勤勤恳恳地扫着落花、落叶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靠近,过了一会儿才像突然发现晓之助已经站在原地看了许久的样子,扫地的动作整个僵住。
不会有危害……吗。
看着那把扫帚、或者说是他看不见的扫帚使用者战战兢兢的模样,他不知为何忍不住笑出声。
确实啦,如果说是做的事情只有在扫地,甚至被人看见还要怕到逃走的幽灵,那确实没什么好怕的。
该不会不是幽灵,是所谓的座敷童子也说不定。
「辛苦了,座敷小姐。」
这样想着,他朝自己无法看到的对方微鞠了个躬,觉得自己再待下去大概又会目睹扫帚被吓到丢下落跑的惨状,于是也就直接离开。
深宅里有辛勤扫除的座敷,写成故事的话,或许会变成一桩美谈吧。
「兄长会想听这样的故事吗……」
喃喃自语着,晓之助开始为下次能和兄长攀谈的话题打起腹稿,并再次忠告自己,谨慎斟酌用词和说话方式。
而在他所不知道的身后,视线紧紧跟随,长发的付丧神满脸迷茫。
「座敷……小姐?是在说我吗……」
名为夜半的男性灵体百思不得其解,最终只得将其归为人类美好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