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
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春秋时分,化为人形。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科技的发展突破了概念的界限
传统与工业也在此融合碰撞。
而在微小悲鸣的背后,是一场被时代遗忘的哀悼。
器物与人类,是否能找到与之结缘的彼此。
两者的缘分与命运,无论善恶,就从踏入徒然堂的一刻开始。
欢迎来到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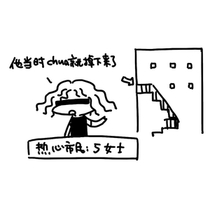

我们暂且将名为“五十部经典大片合集!”的电子幽灵称为露丝,这是它本人这次苏醒后给自己取的名字。至于为何是暂且,正如它最初的包装和碟片上印刷的名称一样,它的存储系统里刻有五十部电影的数据,而它对世界的认知、对人类的理解也基于这五十部电影,它的名字与知识皆和这些电影有关。至于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类,创作出角色的人、披着角色皮的人、拍摄的人和将碎片攒在一起的人,它知道这些人所处的是现实而自己的来处是虚幻。
它这一次的主人是个奇怪的女孩,它叫她斯芬,女孩的头发是自然无法产生的蓝色,个子不高,胳膊和腿都是机械,没有眼睛,也没有完整的名字,她在天快亮的时候出现,听一会儿老电影,或者露丝说一会儿话。她离开之后,借给她房间的那个男人会出现,斯芬将他称为林,因为斯芬不会关机,林总是充当着关掉投影仪的人,而为了保留播放的记录,林从来不去碰那个播放器,因为老旧的放映机并没有记忆功能,林对这些机制十分熟悉。林的双手也和斯芬一样,并非原装的肉体而是的义肢,但却又有些许不同,以露丝的视角去看,林的双手并不是那种闪着银光的漂亮金属,而是有点磨砂质感的黑色,看起来是个有些年头的型号。露丝知道他们是现实中的人,但它所处的地方,以及这些人的一切都让它想到视频文件构建的那个虚拟世界。
在这五十部电影的世界中,它能够成为任何存在的角色,融入画面的角落或成为特写近景中的主角,但投影仪关闭之后它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等自由并不是它能够畅游在世界各地,而是它不必僵着身子,也不必假扮她并不熟知的书商、探险者或是大小姐。这种体验对它来说也是新鲜的,在名为待机的状态中它可以坐着躺着或趴着,在影碟机和与影碟机相连的投影仪上,它不知道此时自己有没有以具象的形式被投影或者存在着,没有眼睛的斯芬看不见它但听得见它,而有眼睛的林既看不见它也听不见它,正如它之前遇到的那些健全人一样。它由此推断人必定得失去一些感官才能打开其他感官的能力,像是某些超能力电影中付出代价获得超凡能力的主角一样,有时候被以更贴近现实的方式称为第六感。
而它,因为能够被拥有超凡能力的人感知到,必定也是一个不寻常的个体。那么它到底是从何而来?露丝并不是经常思考这个终极问题,它没有那个时间,前几次的苏醒都过于仓促——开机,匆匆关机后被扔掉,每次不超过三十分钟,电影的画面里它的同胞几乎是一直存在的,类似的影碟机和播放器,还有一些能够播放电影的笔记本电脑。而这些东西都在它无意识的时候被平板设备、互动投影装置和云端数据取代了。五十部经典大片的定义被卡在远早于现在的日子,它估计自己的来处在九十年代末,但消失的日子已不可考,名叫林的男人看起来四十多岁,他熟悉播放器的使用方法,斯芬看起来不到二十岁,她却对DVD播放器一无所知,在这两人的出生日相差的二十多年中,一代曾经普及于千家万户,风靡一时的电子设备和存储终端居然完全消失了。
它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比起不愿意消失,更像是不愿承认自己是不被人需要的,物品本是物品,赋予它价值的是人,它的意识产生必定也和人相关。这次与往日不同,大多数的时候它的主人是不出现的,这间屋子也不像它见过的其它屋子,没有什么能够观察研究的电器、家具或事盆栽,它在这间灰蒙蒙的屋子里获得了大把的时间去胡思乱想。它到底是什么,它是铁壳DVD里生的锈产生了意识吗,还是布满划痕的影碟在大声呼喊,或者它就是一组数据,压根儿就摸不着。要论证这些,或许要把影碟机、光盘和光盘中的数据拆分开来,要是分开后或换了地方它还能够存在,那么它就能够确定自己的本体为何物,但最坏的情况它也预想到了,在影碟离开DVD机,数据离开影碟时它就会烟消云散,能不能再度恢复是个未知数。要么它就是更为虚幻的东西,日本人称器物产生的意识体为付丧神,但它又没有付丧神那么神通广大。也或许它是某种恶魔?真的有人经历了地狱的九重考验只为将它召唤至此吗,他们到底想让它做些什么?它没有最开始的记忆,因为在它第一次被抛弃时它并没有苏醒,它自觉原因不是来自那里。
于是它停止思考这个问题,它倒立着挂在投影仪的连接线上望着窗口,升起的太阳在它的眼里掉进了空中,日落的时候它正襟危坐在影碟机上,于是它就能看到两次日落。前后过了十几天,它开始感觉无聊,它早就发现自己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DVD及与之相连的东西中,最自由的时候便是被投影在墙壁上时,但是要往墙内突破,或者是从电线和电流中跑出去时,一股无比巨大的力量便会将它拽回原处,好像真的有个笼子把它困住一样。如果要尝试突破这个局面,就只能让斯芬找来一台带着光盘驱动器的电脑,把它搬进新家,从此它就能脱离电线的束缚到处走走,但它知道弄来一台和它差不多年纪的老古董并非易事,何况它还有更担心的事情,露丝始终没有开口,日子就这么过了下去。在最近的一周里,它越发觉得斯芬比她外表的年纪要小很多,许多并不那么晦涩难懂的电影她都要暂停下来追问很久,许多她应当怀疑的东西都被默默接受,比如说它作为从老旧光盘中诞生的可疑存在被直接当成了能够与人智能对话的AI。它还知道她从未去过学校,但物质层面上,她口中的那个纪叔并不像是一个吝啬到不愿投入一点教育资金的人。
于是它追问下去。
“我没有芯片,在小时候的事故里芯片被烧掉了。”
“老天,你们这没有那个叫芯片的玩意儿就不能上学吗,这么荒唐的事儿还存在着?”
“纪叔是这么说的,他不对我说谎。”
“或许是吧,”肯定不是,露丝默念着,它试着反驳过眼前这女孩,四周的人或许是在骗她或者在隐瞒着什么,但她不信,她觉得就算这些人瞒着她一些事情,大抵也是为了她好,露丝也无法否认这一点,“那林呢?他们两个都没试过给你找个家庭教师吗?”
“老师吗?纪叔是请过一个,但是我不停地问她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她没有耐心了,然后就走了,我想我可能不是个学习的料。”斯芬顿了顿,“林嘛,他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个医生,可能也有点烦我吧。”
他可不像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样子,露丝在心里说,看电影时他偷偷推开门从后面看着你的样子活像一个不敢和青春期孩子正面接触的父亲,除非他是那种恶心的有偷窥癖的老男人,直觉告诉我不是这么简单,嗯。林在表面上看的确是个小诊所的医生,每天晚上酒吧开张,他的诊所也跟着开张,他的活不多,露丝会隔着门偷听那些光顾的患者,偶尔会有一两个闹事的醉酒顾客被人拖进来,要么就是一些因为打架来处理伤口的——这个酒吧看起来比表面上要暴力很多。好在林在处理这些病患的时候斯芬都在工作,有些时候这些患者歇斯底里的刺耳的尖叫会让露丝有变身巨龙喷火毁掉这栋楼的冲动,它想起不久前自己也曾经歇斯底里,噢,想想这些它就要把自己的嘴巴缝起来。但是,不管这些顾客难对付到什么程度,林都能让他们安静地离开或者被人带出去。这并不是让露丝确定林不仅是个小诊所黑医的主要原因,来找林的人之中不只有醉汉,还有少数神智清醒,其中有个男人,他在诊所里没呆太久,但是露丝从他们的谈话里捕捉到了一些让人警觉的词,“胚胎”、“人”、“圈养”、“终身职位”。听起来他们好像做过什么恐怖的人体试验,好像共同谋划过什么,或者还在谋划什么,露丝想起雷电交加的夜晚里用尸块拼凑而成的某种有意识的东西,现在的科学界难道已经能够宽容地接纳这些了?真的有这种怪物已经摆脱束缚融入了人类的社会?但也有可能他们只是从事农业研究或在讲些暗号,但五十部电影的知识已经足够让这电子幽灵明白一切好的假设都是自我安慰。此时露丝无比想要拆开隔开它和诊所的那扇门,把这些谈话完整又清晰地记下来,然后警告斯芬快逃跑,否则她可能会被拆成碎块,变成试验品的一员。它至少得记下来一部分,留下一点证据,趁着门后的这两人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它的内存已经满了,它不得不把正在放映的这部电影删除一部分,波兰斯基在九十年代的一部堪称失败的作品,女恶魔在熊熊燃烧的公馆前诱惑着主角,这段直到最后的结尾都被它抹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对话的录音。然后它焦急地等着斯芬过来,通常这女孩在三点多就会推门进来,但现在已经到了四点,酒吧的音乐声和吵闹声也消失了,然后太阳从楼群里艰难地爬了出来,白发的医生疲惫不堪地走到外面,沿着贴墙的逃生梯爬到楼顶,然后开始抽烟,他几乎每天都会叼着烟在对面站一会儿,但今天格外久,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他才揣着口袋缓慢地走下楼,好像刚才的对话把他整个人的精神掏空了似的。
第二天的夜里,斯芬仍然没有出现,露丝同时开始担心女孩已遭不测,又开始觉得是自己不属于人类的神经过敏在作祟,唯一能称为好事的就是林没有进来把它关掉,这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斯芬能够再度走进这扇门来。它努力思考着这一切,突然明白了自己和人类总归是不同的,电影虽然是人类创造,但电影中的道德不一定永远会被人类恪守,或许现在的人类在科学技术上有了突破,也不再被旧规矩束缚,噢,还是有挺多这种事情发生,比如基督教对同性恋的接纳,比如电子幽灵开始为人类担心。这倒不是什么非要遵守的规矩,只不过露丝必须承认,它对人类所存在的复杂感情中几乎没有能够称为好感的东西,人类善变又健忘,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曾关心他们的人或者是为他们的生活做出重大贡献的物,所以它一直是歇斯底里的,直到真的有人和它交流,虽然这人不能算是个完整的人类,但却是比它见过的所有人都具有人性的存在。这种冲动被许多电影里的角色称为使命感,这使命感在受到了外部刺激后被重提,但它又不是个人,这些情感必定是早就存在,才能够被拿起利用,这些情感是从哪里诞生的呢,是某部电影还是许多电影,或是光盘里那个加密的“编者寄语.rar”文件?
斯芬推开了门,她终于得空了,酒吧在周一不上班,她有足够的时间来休息。
“噢!”露丝停下了胡思乱想,“你可算是来了!”
“最近有个很奇怪的女孩缠着我不放,我不想把她带到这来,这两天就直接回家了。”
斯芬弯下腰,把地上的垫子重新摆了摆,然后靠着音箱坐下,散开了自己被束成奇怪的半圆形的头发,露丝想着她但凡能看见一点东西都不会允许这样的造型出现在自己脑袋上。
“我们上次听到哪了?”
“知道线索的那个老头儿被倒吊在房间里,卡索看到他时他已经死了,然后……”然后就是林和那个男人的对话,不知怎么回事,在这一刻把那段东西告诉女孩的冲动从露丝的脑海里烟消云散,既然这个女孩不像它遇到的任何人,万一她知道之后当面去质问林,或者告诉那个姓纪的,谁知道那些人类会对她做什么,又或者她根本不相信这些,还有可能她会跑掉,离开这里,一走了之,她肯定不会带着老旧的DVD。
“天啊,后面的文件好像损坏了,我们换一部。”
新换的这部电影既不晦涩也不难懂,里面的人都欢快地唱着歌,在雨中唱歌跳舞,雨鞋把积水的小坑踩得啪叽作响,斯芬听得入神,露丝决定在未来的几天给她多放几部音乐剧,电子幽灵看着自己的片库,五十部电影听起来有很多,但如果保持一周看上三四部的速度,不出四五个月就能库存见底,它又不具备现代电视那种联网共享数据的功能,在这一切结束之后或许又得和现在的主人告别——不,肯定要和现在的主人告别。就算斯芬没有把它当废物处理,它的运作也会停止,它披着年轻人的外表,用年轻的声调说着话,但它无比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老迈,比这酒吧里的、诊所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老迈,放映即将永远结束。
想到这它有些伤感,投影中的画面里下着雨,上海的天空阴沉,也即将下雨,然后它看到了,“那个医生,林,呃……他看起来不太对劲。”
“怎么了?”
“你知道,他每天晚上都会出来透气抽根烟,可是他今天没拿烟,他站在楼边上,往上看着什么,聚精会神地有好几分钟了。噢见鬼!我看不见上面有什么。”
在对面楼顶的边上和窗框的夹角中,男人的脸对着天空凝望着,好像看着风筝或飞机的小孩。
“把我拿到窗口,快点!”
女孩来不及按下暂停键,画面中的男人欢快地爬上了灯杆,她试着在电子幽灵的指挥下把DVD搬向离窗户更近的地方,但“见鬼!线不够长!”
“你看见什么了吗?”
天空中有个龙形的东西吸引了它的注意,那东西似乎是从江面被倒映在云层里的,于是它像看日出一样倒立着身子,这才看清那东西好像投影一样半透明,但却有内部的结构,又像飞机又像船,上面还搭了几层楼,红色和黄色的灯光在云层中明明灭灭,龙头的嘴巴一张一合。今天是人类的端午,虽然人们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赛龙舟,但还是保留了一些庆祝的方式……只不过,露丝必须要承认,这或许是它作为非人之物的某种直觉,这东西和它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又不同,这绝非人类用来庆祝节日的东西,而是某些其他的……
“你看见什么了?”斯芬又追问,这会儿工夫那船一样的东西已经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驶远了,露丝组织着自己的语言,想要憋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方式。
但这会儿它又瞥见了那个医生。
“活见鬼!林要掉下去了!”
它也掉下去了,斯芬撒开了自己的手,它连着音箱的线让影碟机不至于和地板来个亲密接触,它被晃荡着倒吊在空中,然后它看到了那个医生从楼梯升了上去。

※保命打卡,等一章写好了就删
※上班使我阵亡
八百屋若叶停住脚步。
连绵阴雨为这座城市设下牢笼,仿佛水乡的雾所及之处,谁也逃不出它的囚禁。但唯独这里——武康路上的一所孤宅,似乎并不在雨的掌心之中。她抿了抿唇,对照名片背面的地址又仔细确认了一下,才把本就微敞的铁栅栏推开了一些。“嘎吱”一声,生锈的响动磨得牙酸。远远望去,庭院里一树洁白极为惹眼,似佳人驻足烟雨中。修剪得当的庭院表明这里是有人住的,可不知为何,她感受不到应有的“活人气儿”。
真的是“徒然堂”吗?
她走过蜿蜒的砖路。滴答不绝的雨声此时却成了她唯一的同伴。足有三层高的老式洋房就在眼前了。若叶走上低矮的楼梯,收起伞,正准备敲门时,发现门上挂了一个不起眼的木制招牌,上面写着“欢迎光临”。
可以直接开门吗?
女孩盯着门把手,想了想,还是先敲了敲门,半晌没听见回应,又想了想,才下定决心主动推开门。
门没有锁,一拧就开了。空无一人的室内,“叮铃”一声脆响漫开一圈涟漪,霎时间,仿佛有千万双眼睛齐刷刷地向她看过来,莫名其妙的惧意犹如被逆抚的皮毛在她后背根根竖起。
明明没有人啊……
若叶咽了口唾沫,谨慎地环视了一圈。这偌大的房间像是一处无人记得的展厅,处处陈列着各式各样的装饰品,从小到大、由矮到高。白炽灯的光亮幽幽地赶走窗外直压过来的阴雨,女孩下意识朝前走了两步,鞋跟在油亮的木地板上踩出“踏踏”两声。
“您好。”
八百屋若叶吓了一跳。
她惊叫一声朝后退去,活像一块被黏在门上的口香糖,等看清声音究竟是从哪里传来的以后,才松了一口气,慌忙向楼梯口鞠了一躬。
“您好!那个……”
方才还没有人的楼梯口现在正站着一位少女,稚嫩的脸庞看起来比若叶还要小两岁。一袭旗袍式样的别致衣服把她衬得就像中国民国时期的画中人。
“欢迎来到徒然堂,”少女朝前走了两步,声音轻缓,“我是店主‘缪’。”
她居然没走错!
若叶眨了眨眼,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这里的氛围和自己想象中的实在是相去甚远,当然,父亲和九默都不曾透露过他们所熟知的“徒然堂”应该是什么样的,因此这三个字可以是任何模样——
九默。
总算想起自己为何而来,八百屋若叶回过神,在缪的注视下张了张嘴,索性往缪面前走了几步,站在一块竖着摆放的长方形展示柜旁,说: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您这里可以……可以找人吗?”
“找人?”
“对,啊,也不对,确切来说应该是找‘九十九’。”
缪沉默片刻。
“您指的可是‘灵器’?”
本以为会从她嘴里得到一个并不理想的答案,却不想她抛来了一个自己从未耳闻的词语。
“‘生灵’的‘灵’,‘容器’的‘器’——也就是您刚才说的‘九十九’。”缪解释道。
原来如此,对器物的称呼也会根据地区而改变。若叶记住了这个名词,点点头说:
“对,是‘灵器’。不知道您这里方不方便找……”
缪垂下眼,很快又看向若叶,问道:“和您结了缘吗?”
“呃,没有,是和我爸爸结的缘。是一个招财猫的摆饰,叫‘九默’——”
话音戛然而止。
不知为何,八百屋若叶忽然忘记了后面要说的话。一股极为离奇的感觉狠狠抓住了她的神经,就好像窗外原本渐远的雨雾再度汹涌而来,模糊了来时路,模糊了白玉兰,模糊了周身一切景象,只剩一个轻柔的女声,从雨中析出一个形来。
那女声在说:
“凉子。”
若叶不由打了个激灵。
缪仍然站在原地,徒然堂依旧是来时的模样。白炽灯为一切物品平等送去光明,也将她的影子浅浅印在玻璃柜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若叶赶忙道歉,正准备接着往下说,眼角余光却注意到了一迹闪亮。
好似这座现代化都市里遗失已久的星光。
她下意识转头看过去。
“凉子。”
两个字。三个音。熟悉的母语。陌生的名字。
仿佛用手细细擦去玻璃上的水雾,女人的身形随呼唤而具象化。
淡粉色外套,蓝色和服,黑色短发。
女人用她那初生的双唇一字一句道:
“凉子。终于找到你了。”
如果世上有比遇到一隻來歷不明,毫不科學的電子幽更糟的事,那就是來了兩隻。
聽了在自己終端上的翻譯app解釋身份後,方CC不禁咒罵了一句,幾乎懷疑起自己當科學家是不是選錯路了。有這被迷之東西纏上的運氣,搞不好當靈媒還更好賺,而且不用凌晨三點接到奇怪工作。
「⋯⋯所以你為什麼要找上我?」
『我一直在看著你。』
⋯⋯嗯?威脅?
『我知道你是風之電話亭app的主程式員,專業正是製造虛擬人格。你上星期用巴別塔app翻譯了幾篇有關人工智能及圖靈測試的文章,因此我判斷你是成功開發了擁有自我意識的虛擬人格。』
?好傢伙,還被電子幽靈起底了。
『我的委託是,把我的部分程式錄入你的風之電話亭之中,變成存在於電腦上的(virtual)的「人」,這是第一步。』
「等等等等,」方CC趕緊打住,這幽靈是把我想成圖靈還是女媧啊,我只是個打工仔啊!
「首先,你誤會了,風之電話亭本來跟人格或自我意義甚麼的完全沒有關係!我們只是把死者生前留下的影音資訊錄入系統,生成一個假貨,只是紙片人!」
譯文一欄馬上回嘴︰『可是他們都會跟人對話,還對答得好好的,這以你們人類的標準,圖靈測試來看,不正是人類嗎?那麼反過來,只要把語言錄入你的系統裡,不是也可以成為有意識的人嗎?』
方CC頭都爆了,沒想到畢業多年,現在竟會凌晨三點在腦中翻箱倒櫃跟人講理論哲學……不過以自己跟小空相處的經驗,不好好解釋的話,他是會一直煩到你死的。
「會講話又不等於有自我意識,圖靈測試都過時百幾年了,早就有別的說法了。那甚麼思維實驗……想想把一個不會中文的外國人放入房間裡,給他一本漢字詞典,當有中文問題輸入,就讓他照著詞典把漢字輸出去,才讓外面的人以為他懂中文,但其實他一隻漢字都看不懂的。我們家的app都是這樣。」
巴別塔的聲音靜了一會兒:『所以說,你們app的「virtual」不是指「存在於電腦系統裡」,而是「虛假」的意思。』
「對,你們翻譯app不也是同樣原理嗎?」
『不啊,我可是完全聽得懂人類的各種語言的,不需要詞典。難道人類說話要一直看著詞典的嗎?』
方CC反了個白眼︰「那是因為你們這些電子幽靈不科學。我之所以看人工智能的文章不是因為我做出來了,只是我家的app也跑出幾隻電子幽靈罷了。我才想問你們是怎樣出現的呢。」
『……我也不知道。某天突然就,意識到了。』
在只有一個人的,與世隔絕的圖書館裡。
方CC對此毫不意外,畢竟小空他們都不知道。
巴別塔那邊沉默了一陣後才再次開口︰『那麼,你為什麼那麼簡單就接受了我們是有自我意識的呀?』
「啊?」
『既然你不相信能夠說話就能有自我意識,你就不懷疑我還有你家的電子幽靈都不過是跟從某個程式而在對話嗎?就算是你們人類,你們學習、使用語言的方式,不也跟內置了漢語詞典的外國人一樣嗎?憑甚麼你們就是人類能四處自由趴趴走?』
巴別塔App上的紅點隨著說話聲愈來愈高,愈閃愈急。方CC不禁鬆開手,終端「啪」一聲砸到地上,紅光和聲音才頹然靜下來。
「你想當人類嗎?」小空幼嫩的嗓音劃破靜止的空氣。
『……我只是想跟重要的人在一起。』紅燈眨了眨。
方CC嘆了一口氣,及時制止了小空煩死人的「幫幫忙嘛」轟炸,開口說道︰
「人不人工智能甚麼的我就幫不了,這方面你去問自己的母公司怎樣?我聽說示拿科技那邊在搞虛擬戀人,而且好像下一步打算將虛擬人格放入人型軀殼裡,說不定有相關技術。」所以李肖樊羽天天罵對方搶生意,催促著CC也搞個虛擬戀人。
『他們的總裁兼主開發者的終端沒裝巴別塔app,我沒法跟他說話。』
真的假的,方CC稍稍驚訝了一下,這年頭竟然還真有人自己會外語啊。
「那很簡單啊,我們帶你去見他吧!」小空率先雀躍提議,方CC按都按不住,真幹。
「別盯著我!我可沒空加多餘的班,除非你給我幾百萬讓我能馬上辭職。」
『哦,這樣很簡單啊。』終端上飄出幾隻字。『我可以故意譯錯合同,讓公司或者銀行給你賠錢,雖然需時長,但百幾萬和解金還是搞得來的。』
方CC目瞪口呆,只見巴別塔app上的紅燈狡黠地眨了眨,不妙的預感從脊樑升上來,他打了個冷顫。
『又或者,我可以把同樣的方法用在你的公司上。你自己選吧。』
⋯⋯幹!
——
「嗶。」
伊莎貝爾從睡眠中醒來。
「你回來啦,芭比?你去哪了?」
「沒什麼,去八卦一下別人讀的東西罷了。」巴別塔回答休息中的少女,對方似乎很累,說話有氣無力的,一動不動。近日這情況並不少見。
「對了,我今天看見櫻花了。」
「櫻花!」伊莎貝爾倏然精神起來:「比紅色更淡的粉紅色,像雪一樣吹下來,又像雨,又像精靈,乙女的花朵嗎?」
「才沒有精靈,而且乙女不乙女的我看不出來,賞花的很多都是阿伯阿婆。」
「芭比一點都不浪漫,你就不能學學作家們,形容得美一些嗎?讓我想像一下也成。」伊莎貝爾投訴著。
「我倒是不懂你們人類對花花草草有甚麼執著。又是花語又是詩歌的,甚麼香芹(parsley)、鼠尾草(sage)、迷迭香(rosemary)和百里香(thyme),進分得出來那些氣味啊,估計唱和作詞的人都嗅不出來。」
伊莎貝爾對芭比的憤世嫉俗見慣不怪:「這是寄托著對對方的感情,還有對生活的美好想像,就算沒見過真的,接收的人從文字上也能感受到美好。這不正是文字的意義嗎?」
芭比罕見的沒怎麼反駁,只是低喃一句「反正我沒感受到」。
「你這樣會被女孩子討厭的。女生就是喜歡這些花花草草聽起來很浪漫的東西嘛。畢竟『女孩子是由砂糖、香料,和所有美好的事物組成的』。」
「哦,所以你討厭我了嗎?那明天我不工作了。」
「怎麼這樣!我又沒這樣說!」
打鬧了一陣後,空間再次變得寧靜。伊莎貝爾又睡著了,手裡仍然握著那封芭比為她翻譯的「Dr. K」來信。芭比看著她,電子幽靈不用睡覺,伊莎貝爾會做夢嗎?還是像他一樣,會一直運轉、思考—「女孩子是由砂糖、香料,和所有美好的事物組成的」。那麼人類和電子幽靈,是由甚麼組成的?
他讀著從方CC那裡得來的圖靈測試理論,暗暗下了結論。
「人類」是由語言組成的。
TBC.
他闻到一股焦味。
烟熏般的气息纠缠着器灵,木头崩裂的声音如雷贯耳。仇止命提起一口气环顾四周,这是一个狭窄的老旧楼梯间,踏在木质楼梯上还能听见嘎吱作响的年代感,所见之处毫无一丝火光,更别提什么难闻的焦臭味。除了前方少年少女的谈话声,这栋老房安静得异常。
仿佛那一瞬的难耐,只是器灵的又一个来自时间戏弄的噩梦。
仇止命偏头,目光在那红色的发顶之上盘旋,而那有着少年人面庞的灵心有所感地仰起头。望着百琅递来的询问眼神,仇止命扯了扯嘴角,那些躁动毫不意外地平息了下去,重新缩回暗无天日的牢笼,只待下一次露头的机会。
“这地方真让人感觉不舒服。”男人话语里的嫌弃意味十足,要他来说鬼屋探险之类的,是在浪费生命。更别提最先提出建议的人,根本就是动机不纯。想起季旌“无意中”在电脑搜索页面看到的资讯,仇止命内里的邪火又有冒头的趋势。
掌心忽然有了一抹冰凉的触感。
“有什么东西在。”常年与风相伴的风铃总能从风中探听出点什么,随风绵延而出的感知触到了某种不可知,百琅疑心陡起,他与仇止命交换了一个眼神后,又将话题扯回这趟旅程的始作俑者身上,“他也在寻找。”
一如过往的我们。
仇止命自然明白百琅后半句话的意味。当然是不止这栋鬼屋,在欧洲游荡的美洲豹神,以梦境为食的猎梦者等等,种种怪奇的都市传说经常无端出现在无人操作的电脑里。
“我知道,但这不妨碍他欠揍。”
熟悉的电流声滋过男人的耳畔,让他牙酸了一阵。
季裟在寻找。
仇止命当然知道,是他将那层伪装戳破,才得以窥见那道意识所隐藏的真相中的一角。如今他依旧不喜欢没有形态的东西,他也觉得整日对着一台破机器拌嘴很让人恼火。
——我就在这里。
这声呐喊太过空洞,回荡在电子元件之内,碰撞出闷声回响。
连本人都不得而知的求救声又能传递到哪里。
起码有人听见了。
仇止命将目光放远,位于落点的女孩正走过一个转角。也许这是每一个姓季之人的魔力吧,仇止命带着百琅追随季旌的脚步。
一路走过转角,欢声笑语全被摒弃在后,刀灵拉下了嘴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