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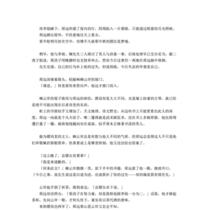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八月十八·小雨
巳时过半,关才才慢悠悠地从家中出来。他这行不做急,更用不着他成天坐着,所以一般都是家里的伙计先行去把店前门板开了,收拾收拾后他再过去,也不显晚。他今天比平日里出门得还要早些,刚一进铺子,温石便迎上来领着他往铺子里头走,告诉他已经有人等了他好一会儿了。
这可新鲜了。关才心里暗自想道。
温石跟着他八九个年头了,手脚麻利办事可靠,虽然话不多但也很是机灵,能被他请到铺子后头坐坐的人,不是达官显贵,就一定是至亲好友。
果不其然,关才刚迈过门槛,远远瞧见那坐着的人就立刻眉开眼笑起来。
“薛镖头啊,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啊?建康待着不好?”
坐着的那人是个大约三十出头的青年男子,穿着身朴素的粗布衣裳,身边支着一杆长棍,外头拿布裹着,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此刻也是闻声转过头来。
“别提了!三天两头到处跑,刚从成都遛了一弯,回去被子都没窝热就给差来这儿了!”这男子生得是铁面剑眉,双目如炬,高鼻薄唇棱角分明,即便带了双微微上挑的桃花眼也还是透着股冷峻的煞气。只是他一开口,可就糟蹋了这副好皮相,实打实的一个粗人。他嘴里虽然说着抱怨的话,却藏不住心里那份老友相见的喜,话语间脸上的煞气顷刻间就如潮水般退了去,露出的笑容让人心头忍不住地生出暖意。
“原来是办事,我还以为你特地来看我呢。”关才一伸手,刚好接过温石递来的酒,便换走了男子面前的茶,给他倒了杯酒。
“看你用得着跑你铺子里来看?来几次都阴恻恻的,我不喜欢。”男子拿起杯一仰头便是一干而尽,他眉头一皱,像是有些嫌弃,干脆把关才手里的酒瓶整个拿来对着口喝起来,“你老喝这种没劲道的东西,啧啧…没意思没意思!”
关才见状一脸苦笑,那是他前些日子才买来的好酒,自己还没尝过,倒先给人嫌弃上了。不过他平日里除了喜甜外倒也是吃口清淡,对酒虽是喜爱,酒量却不好,喝不了多少。这姓薛的全名薛戎,以前是开封人士,后来辗转反侧来了临安,在当地镇远镖局干事。虽然年纪轻轻却能耐得很,没多久竟给他混成了个镖头,不过他在临安只待了两三年,就给调去了建康。关才当年同他也是投缘得很,有过些交情,这一眨眼又是三四年过去了,刚认识他时他虽然年纪也不算小,看起来仍然不过是个毛头小子,现在却已完全是个成熟的大人样子了。干这行的虽然办事沉稳,但本性大都刚烈,薛戎也不例外,这带着些甜的淡酒他确实是喝不惯的。
“今年我就光跟死人打交道了,唉!”薛戎砰地一声把酒瓶放到桌上,大叹了一口长气不停摇头,“算了算了,跟你讲这个也没用,你本来就吃这口饭的,能算什么事。”他说到这,突然又板起脸,那凛凛戾气立刻就又从眉间透了出来。他笑着的时候能让人如沐春风,但只要不笑,整个人就冷得像霜,不怒而威,教人硬生生地被他的气势压下两个头去。他此刻也是收了先前不羁的样子,认认真真地对着关才低声说道,“十一口,有没有?”
十一口指的自然是棺材。
关才听到这个数也是一愣。这数可不算小,一口气要这数更是少见。
他张了张口,还没来得及问,薛戎又开口说道:“接了个大单子,没能吃下来。”他语气平淡得很,但也不难听出他话里的意思。薛戎又喝了口酒,自顾自地把情况大概跟关才说了说,大抵是不久前镇远镖局接了趟镖,东西到临安这儿出了事。跑镖的几个伙计全死了不说,货也没能给保住,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要说他本事不差,人缘也不算坏,但自从混成了普通镖头后几年一直没能再往上头提拔,没别的原因, 就只是像这种单子他从来不接,他宁可干些吃力不讨好的便宜活儿也不愿意捧烫手山芋。 薛戎说虽不知道这趟镖到底托的是什么,这能同时差遣那么些个精锐镖师,想必不会是简单的东西,他那会儿人刚好不在建康,不然说不准还真避不开这次劫,“有钱没命花。”薛戎淡淡说道。他对这类事已经有些习惯了,一时也瞧不出他此刻的心情,“再过几天这事就该了了,得赶紧装了带他们回去,这天那么热……哎,真是倒了血霉。”
关才点点头,伸手往薛戎肩上缓慢而有力地拍了几下。
“东西有,你放心。我一会儿就去给你备上,事情完了你随时来取。”关才对着薛戎比出四支手指,“这个数。剩下的你爱自己花自己花,不想自己花就想给谁给谁。”
薛戎盯着他的手指瞧了一会儿,偏着脑袋有些怀疑地瞄了他一眼,“那么好?你不闹我?”
“干嘛要闹你?”关才低头一笑,“…人死了可不单单是死了就完事咯,要办的事还多得很嘞,我就当做个顺水人情,积点阴德。”说到这里,他像是想到什么似的,忽然换上一副有所思量地神情,一手托腮一手轻叩着桌面,“呵哟…我突然想起来了,年初的时候那牛鼻子说我今年下半有横财,但也有横灾…也不晓得真的假的,就当信了他吧,破财消灾也好。”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薛戎,对方像是完全没听进他的话一般,咕咚咕咚地又灌了几口酒,可方才他听到自己说的话时,眸子里分明是忽地一亮,只是他又赶紧收了回去,好像生怕被关才看穿什么心思似的。关才也不点破,只是假意咳了几声,又拍了薛戎几下,“回头我让石头准备些冰片给你,你路上能好过些。”说罢,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眼色一沉,话锋也跟着一转,“你说你先前去了成都?那儿可挺远的,去干嘛了?”
他原本只想随便换个话题聊聊,不想这话刚说出口,薛戎整个人都抖了一下,眼里的光也骤然黯淡了下去。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如此。之前说到成都时只是随口一提自己的行程,并无什么特别的感觉,如今被人问起原由,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就跟打翻了酱料铺似的一齐卷了上来,冲得他浑身都难受。他紧紧握着那酒瓶,低垂着双眼只是看着自己的膝盖,许久都不发一言,弄得关才也是分外尴尬。
“……去送送朋友。”过了好些时候,薛戎才咬着牙开口,他的声音仿佛是硬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一般,难听得紧,完全没有平时那副豪爽模样,但也因为这样,这声音里染上的痛才分外真切,“很好、很好的朋友。”
很好、很好的朋友。
关才已经很久没有很好、很好的朋友了。
秋天并不是个适合想心事的季节,秋字下心,可不就是个愁么。不过关才觉得不止秋天,任何时候都不该想心事,想多了烦心,闹心,乱心。
心静不下来,什么事都做不好。
可俗话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他当然也免不了这俗。这重阳和中秋一样,都是佳节,而只要是个节,关才就都不想待在家里,他家里没有人,一年到头都冷冷清清的,更何况这几天他还忙着处理伍毅托他办的事,没少往栖霞山跑,弄得他现在整个人都觉得透骨的冷,也搞不清楚是身上冷,还是心里冷。他把带来的龙涎香放进香炉点上,又特意关照伙计帮忙把酒给温过,才算稍微舒服些。
他未时就到了映柳轩,跟平时不太一样,这次他一来就直接找陈掌柜要了最小的那间雅座,一坐就是几个时辰。起初他还就着点心颇为惬意地喝着酒,可随着时间渐渐过去,他脸上的也是慢慢地浮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耐烦。若是换做平日,他爱喝多少都没问题,就算最后醉得不省人事,陈掌柜他们应付的也多了,自是会去将温石喊来接他回去。
八月十五那天夜里便是如此。
映柳轩的伙计找上门的时候温石就已经预见到这状况了,他也一样习惯这事了,所以看着瘫软地趴在桌上的关才也没说话,只是解开带来的酒囊,扶着关才的脑袋就把里头的东西往他嘴里灌了些,确认对方已经平稳地把那些带着些药味的液体咽下后才扯起他一条胳膊把人整个拽起,三两下弄到背上。
温石调的醒酒药效果一向很好,到半路上关才就晕晕乎乎地回过少许神来。额前的头发落在眼前,贴在温石的肩膀上蹭的他脸痒,他想收回手来拨开它们,才一动就突觉得身下一晃。
“…别动!”温石咬着牙轻喝了声。他平时在铺子里不做什么重活,个子虽窜得高,力气却不大,所以即使关才的分量在同样体型的人里怕是已经算轻得了,他背着还是显得有些吃力。刚他那么一动,温石险些踏歪步子摔出去,“…不能喝就别总喝那么多,也不怕喝死了。醉成这样,小心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呵…”温石重新稳住身子后嘴里嘀嘀咕咕地轻声抱怨着,关才分明是听到这伙计怎么说自己的,却也不恼,反倒像是自嘲似的淡淡一笑。
又不是没死过,有什么好怕的。他手脚都还麻得很,意识却在那醒酒汤的作用下渐渐清明起来。
就好像他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二十一年前是怎么「死」的。
那天他喝得也很多,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喝那么多。
到现在他还记得那天的场景,嫡长子的满月酒,排场可不输姨姨大寿多少,家里上上下下的人多半都去了。按家里规矩这天当长辈的都得轮着抱抱这孩子,等挨到他的时候孩子已经被折腾了小一会儿了,倒也没有哭闹,脸上也看不出什么疲态,在襁褓里很是乖巧的睡着,偶尔睁开眼也只是看看周围,又能自顾自地接着睡去。六月天娃娃脸,不过老天爷还算给面子,那天的天气很是不错,像是照顾着这孩子,连夜里的风都仿佛比前几日要暖些。裹着孩子的布包被递到他手里时,他也被刚满月的孩子的软和程度给吓了一跳,他在家里辈分不算小,但以往此类活动都刚好给错过了,这还是他头一回抱到那么小的娃娃,也是那么一来才知道原来「抱在怀里怕摔了」这话一点都没夸张。他把那包着团软肉的布包搂进怀里,正犹豫着这样的动作合不合适,就感到手肘被人轻轻托起了些。这本是一个很小的动作,怀里孩子的脑袋却因此顺势稳稳地贴进自己心口。他抬起头看到孩子的父亲站在自己身前,笑着说“这样抱更好些”。这大概是他头一次看到那人笑得那么高兴,不禁看愣了神,但也很快就回过神,立刻跟着一起笑起来。刚满月的孩子按理说是不会笑的,他却觉得好像看到孩子也笑了下似的,心里更是欢喜。家里头血脉之间的感情亲得很,小时候他也被长辈们捧在手心里养大,才发现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等自己当了长辈,竟会忍不住将这习惯传承下去。等把孩子依依不舍地送回到孩子母亲手里,他才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盒打开,从里取出一圈好似碧波荡漾般的浓绿玉镯来。
双股绞丝,二玉相并。
他拿着玉镯轻轻晃了晃,那镯子便发出阵阵清音。刚满月的孩子对着这些许是还做出什么反应,只是盯着那声音的源头看着。他逗了一会儿也不再贪玩,赶紧把那镯子塞进孩子的襁褓里后便笑着让开步,由着那对夫妇将孩子再带去见过其他亲戚长辈。等这一圈都给走完了,酒宴才算是能够开始。
他不高兴的时候喝酒、高兴的时候也喝酒。他的酒量并不好,那天却喝得极多,脑袋虽然昏昏沉沉的,可偏偏又没能真的醉倒下去。大概是怕在这喜庆的气氛里继续浸溺下去会真醉得不成样子,他在散场前便向诸人打过招呼独自离开回家。
后来的事情他就不太记得了,反正他最后没回到家里,直到现在都没有能回到家里。
他人就好好的在这里,却已经是个「死人」了。这其中的来龙去脉他并不明白,但如果现在的状态是对家里好的状态,他这样「死」着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事情他一直藏在心里挂念着,但真的太久了,久到他已经不再那么想去追逐真相了,久到有时候他自己都快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了。
原本他只是想在今天这日子找处热闹地方让自己可以安身,好过当个寂寞的「死人」,真是万万没想到这挨着自己坐的小姑娘能给整那么一出乱戏。先不说她蹩脚的扮相,光是她说出来的话,他都不信这能是真的。
蜀中唐门的名号在巴蜀一带确实响亮得很,可这里是临安。江湖上有多少腥风血雨,源头追究起来不过是一时意气用事的一两句话,江湖人中本就多血性鲁莽之辈,眼前三步外的地方都不一定瞧得明朗,更别说什么「将来」为不为敌的事了。
…而且这「江湖的地头蛇」又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说法?
他原本没打算管这事,所以也就抱着看好戏的心情退了几步隐到周围的人群里,直到有人出手帮了那小姑娘他才后悔自己躲得太深了。虽然大约能分辨得到出手那人的方位,却完全看不到对方使得什么手段,更别提是什么人。
这倒是有意思了。
无论出手的人是谁,跟这小姑娘有没有关系,都一定跟「蜀中唐门」有关系。
但这关系是好是坏就说不准了,他刚想试试跟着那小姑娘看能不能一探究竟,又好死不死被楼上雅间下来的韩悠被绊了住,才知道原来今天皇城司的官爷们也在这儿摆了一桌。他同韩悠认识得久,彼此之间有几番人情往来,也能称得上一声朋友,自是不用假意客套,可韩悠这人又很是缠人,非拉着他东一茬西一簇地聊了许久,好容易把他再重新哄回楼上,厅堂里看热闹的人早已各自归为,先前那姑娘更是不知去向。
想来就是因为如此,他才干脆赌气一般把自己给灌了个烂醉。
可今天不行,他在这雅间本就是为了等人。既是为了等人,那自然是有话要说、有事要办,要真喝多了岂非耽误得很?何况他等的还是一个真正的朋友,虽算不上很好、很好,却也是如今已经「死」了的他不可多得的一个朋友。无奈之下,他也只好把酒放到一边,再请伙计送来些茶水瓜果地打发时间。直到戌时将近,一阵混着黄菊清芳的香火味才袅袅飘然入室。
是了,今天本就是天龙寺祭天的日子,他这朋友一向喜好这些游乐之事,倒是把这事情给算漏了的他约错了时间。
他气也不是,恼也不成。对着朋友,他好像一向也都发不出火来,只好叹了口气。
来人却是不急不慢,就着他对面的位置安然入座,冠玉般白净的脸上带着儒雅温和的笑,眼神更是柔得像是能漾出水来。
“哎呀,稍微迟了些,莫怪莫怪。”
-END
============
总算总算(擦汗)…后半段卡得不能再卡了,肥肠肥肠肥肠的不满意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能ry凑合着ry……(自尽
引用的都是些耳熟能详的诗词就不多说了(殴)
照例没有Q&A;!有什么问题欢迎评论!
出场的PC卡都是一闪而过也就不AT了…至于中秋映柳轩发生什么事情估计临安说书的已经分成九九八十一章每天三次轮着在天桥(什么东西)底下说到现在也该家喻户晓了我就一笔带过…
以上!!依旧感谢看完的各位!!!(猛虎落地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