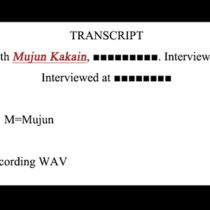在魔女之夜前,芙洛丽亚还不叫芙洛丽亚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反复退货的大致故事,以及跟戴安娜姐姐的贴贴!!!日后她也还会这样保持家精的身份单纯快乐好一会儿
以下正文
少女醒来的时候还没有名字。
但这不要紧,因为就在她缓缓睁眼的瞬间,一名金发青年正又惊又喜地望着她,喊她“玛丽”。
玛丽,玛丽。少女无声地念了两遍,嘴唇轻碰了两次。这真是个好名字。这么想着,她挽着金发青年的胳膊幸福地笑了。
金发青年的家前有一片小小的田地,上面栽种着应季的水果。擅长料理的玛丽花了一个上午把已经成熟饱满的草莓挨个摘下并清洗晾干,又花了一个下午将它们和砂糖一并倒进大锅里搅拌熬煮,然后在酸甜的草莓酱的气息之中迎来了工作完回家的金发青年。他们会嬉笑着一起准备晚餐,满足地享用完了之后,在床上分享一个亲吻,相拥入眠。
休息日总是金发青年与玛丽的二人世界。他带着少女上了街,两人牵着手走近了一家看着就价格不菲的店铺,橱柜里码放着的戒指们整齐又闪亮。
我想,是时候了。金发青年望着少女,眼里带笑。
少女的世界天旋地转,她享受着这幸福的眩晕,对着她的爱人灿烂地笑着。
那应该是两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之一。他们难得地没有在家享用亲手制作的晚餐,而是去到了浪漫又优雅的餐厅。金发青年身着笔挺的西装,赶着甜点上来之前在玛丽的面前单膝跪地。对于他那并不令人意外、但对当事人来说惊喜丝毫不减的问句,玛丽含泪笑着,点了点头。
在周围的人们的掌声之中,青年试图为他的准新娘戴上精心挑选的婚戒,然而却发现那精致小巧的圆环怎样都无法与面前的人的左手无名指相契合。玛丽无措地说着或许是这段时间做了太多的点心,再过两周便能正好戴上了。她慌乱地抓着握住自己的手,却看到了金发青年好似在望着陌生人的困惑神情。
那天的晚餐没有甜点。金发青年说着这不对,不该是这样的,然后像是在寻找着什么一样跌跌撞撞地离开了餐厅,留他的未婚妻一人在原地掩面哭泣。
待金发青年失魂落魄地回了家,少女就在烛光之中乖巧地等待着他。青年快步走上前抱住了少女,喊她玛丽,玛丽。然而在他抬起头时,眼中的困惑却丝毫未减。
我的爱人究竟在哪里?
金发青年茫然地望着少女,他们未能携起双手亲昵地接吻,但眼里却是有着近似的悲伤。
少女认真地哭着又努力地笑着,晶莹的泪水一颗颗地滚落,可笑容也依旧宛若初见那日一般烂漫。
Goodnight, my darling.
少女抚开脸旁的发丝与头纱,与他吻别。
仿佛花瓣扫过脸颊的触感终于让金发青年回神,自此,那团柔软的白色再也无法映照入他的双眼。
少女记得那晚哭累了之后便失去了意识,并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来到了这家古旧的二手店铺,只感觉得到自己似乎累的一下子睡了好几天。她被店长摆进了路边的展示柜里,可以天天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作为消遣。少女对这样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怨言,美中不足的便是身边没有恋人的陪伴。
啊,若是能有所爱之人时刻相伴左右的话,就算每天只能一起团坐在总有扫不完的灰尘的橱窗里,那想必就是连一个对视、一次呼吸也能感到甜蜜的幸福吧。她望着在初春的寒风中正分食冰淇淋的一对情侣,由衷地想着。什么时候才能遇到自己的“亲爱的”呢?
店门上的铃铛发出轻响,少女不知第几次满怀期待地望向了后方。也终于如少女这一整周里期待过的那样,那名头发有些斑白的中年人径直走到了她的面前,朝她伸出了手。
跟我回家吧,安娜。
安娜,安娜。少女无声地念了两遍,舌尖轻弹齿背。这真是个好名字。这么想着,她牵着中年人的手幸福地笑了。
中年人是一所大学的教授,假期期间他鲜少出门,多数时候喜欢在书房里的桌前做研究。安娜则喜欢在有着暖阳洒进书房的时候轻手轻脚地溜进来,从书架上挑选出还未阅读过的最厚的那本书,然后抱着它忽地钻进中年人的怀里,请求他为自己讲解书上那些深奥的东西。午后的时光就伴随着茶香和书香、翻页声与轻声细语,在两人之间静静流淌。
少女喜欢这样坐在中年人的腿上撒娇,她享受着来自另一个人的体温,温和的声音在耳边以一个令人舒适的语速缓缓地念着书,时不时还会有亲昵的触摸与亲吻落在发顶、耳边、后颈、掌心、腰间……在这温暖之中她仿佛就要融化成世界上最幸福的一汪糖水。
那个阴天的午后,安娜抱着一角带血的书,哭着跑出了家门,女人悲愤的尖叫响彻了这不大的屋子的每一处。
你都对你的女儿做了什么!你这畜生!见鬼去吧!!!
器物碰撞的声音过后,衣衫凌乱的中年人闯入书房将自己反锁,任凭歇斯底里的女人在外敲砸。
少女惊恐万分地看着他还在淌血的额头,虽然忍不住颤抖,但仍旧试着伸出手去用包裹自己双手的洁白布料去为他擦拭。她的关切询问还未出口也还未碰到流血的伤口,便被中年人一把抓住了手腕。
我年轻又美丽的安娜,我最爱的人儿啊……你不会拒绝我的吧。
少女说自己被抓疼了,没能忍住让泪水溢出眼眶。似乎是被这一幕刺激到了,中年人的脸越发地扭曲。
是你先勾引我的!你从未拒绝,甚至穿着那样的衣服,主动地扑进了我的怀里!
面对着中年人疯狂的咆哮,少女难以扯起自己的嘴角一丝一毫,只能悲伤地闭上了眼,依旧宛若初见那日一般无暇。
Goodbye, my darling.
最后的最后,少女祈祷着自己的拥抱能够为他带来些许安慰与宁静。
杰西卡。爱丽丝。露西。奥利维亚。蒂娜。……。…………
少女短暂地拥有又失去了好些个好听的名字,她在苏醒与沉眠中反复,期待着每一次的邂逅,又在每一次的分别为对方献上最美好的祝福,然后继续满怀愁苦与欣喜地期待着下一次的有缘人与恋爱降临。几经周转,不知不觉间已经飘洋度海,有所缺失的首饰在曼哈顿唐人街上的一家名叫徒然堂的古董店安顿了下来。不知为何,就算被再次抛弃也依旧能回到这里,而更加不可思议的则是这里似乎还有不少与少女同样的存在,正在此地等待着什么。
相较一层的店铺,似乎总是楼下的酒吧更加热闹。再一次被退货回店铺,因为伤心而耐不住寂寞的少女趁店里人少的时候小心翼翼地走下了楼梯,新奇地望着这自己难以融入其中的空间。打量了一圈后,还是被吧台边一位女性的美丽背影吸引了视线。
少女知道那名女性,同为婚礼用饰品的她们被摆放在了极其近的位置,且在两天前离开店里之前,亲眼目睹了她的苏醒。
“戴安娜小姐……”
待有些笨拙地扯着蓬蓬的裙摆坐上一旁的高脚椅,少女憋不住长久以来的委屈,可怜巴巴地喊着她的名字。
“…………”
戴安娜没有具体地回应,但她轻轻地放下了手中承接着琥珀色液体的玻璃杯,似乎是在等待着下文。
“恋爱原来是这么困难的事吗……”
“男人没什么好东西。”
“可是、可是——”
少女在戴安娜冷淡的语气下变得更加支支吾吾。戴安娜终于看了身侧的小姑娘一眼,稍作思考,然后淡淡地笑了一下,看得纠结着的少女都忘了继续去蹂躏搓弄手中攥着的薄纱。
“为什么要去追逐幻影呢?你还有大好时光,推开门去看看吧,五光十色的曼哈顿足以让你忘记无聊的爱情和爱情的坟墓——婚姻。”
婚姻。少女默念了一遍这个单词,意识到自己似乎还未能想到那么远、又被戴安娜说得那么可怕的东西。思路单纯的少女很快便把这种复杂的问题抛到了脑后。
“出去看看……对啦!两天后好像说是个大日子?当天、或者说在那之后是不是会有很多人来店里?那样的话是不是就能更快、更有可能遇到我的亲爱的了!”
想到这里,先前的阴霾似乎都已不复存在。少女快乐地晃动腾空着的脚,双手捧着她的小脸蛋,已经陷入了和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一起在繁华街道上闲逛的幸福幻想里,然后发出了一声软绵绵的叹息。
恍惚了一阵后,少女从快要被粉色泡泡盈满的妄想里回神,突然想起了什么再次转向了戴安娜:“前些天有件事没来得及跟戴安娜小姐说。”
“……?”
“你的裙子真好看,非常合身!”
没能料到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的少女只是为了说这么一句话,戴安娜不由得稍稍愣了一下。她依旧不失优雅,适时地回以了一个没多少温度但礼貌的微笑。
“以及谢谢你陪我聊天!”
软蓬蓬的少女对冰冷的美丽家精送上了一个轻轻的拥抱,随后便快活地跳下了她坐不习惯的高脚凳。
戴安娜没有急于重新拿起酒杯,稍稍目送了一段少女,直到她消失在楼梯的拐角。
少女重新回到了她该在的位置,亮晶晶的双瞳第无数次饱含着憧憬,望向店门的方向。她不曾气馁,也永远不会,因为她就是为此而生。痛苦也好,失望也罢,若是他们统统由爱而生,哪怕要经历漫长的等待,哪怕要为此献上自己的全部,那便都是幸福的吧。


*高冷与多洛希的hp paro,是be呢
我死于2003年的盛夏,年仅二十岁,无论怎么看都是英年早逝。死因听上去很匪夷所思——我跌入了帷幔的后面。谁能想到仅仅是跌入了帷幔后面就会死呢?但我确实是死了,死得尸骨无存,没有人知道我遭遇了什么,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如果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建议,以避免沦落至与我一样的境地,我只能告诉你,要小心神秘事务司里的一切,那里随时都能要了你的命。还有,当个好孩子,不要犯罪。
我十七岁的时候就是个绑架犯了,受害人是个比我小两岁的女孩子,有着漂亮的金发和白皙的皮肤。三强争霸赛结束,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返校的那天,我给她喝了点安神剂,把她塞进了我的行李箱。因为此事,我也没有回到学校去,而是直接租下一套单身公寓,从此与她两个人住在那里——跟美少女同居,听起来就如同梦一样,是吧?
做出这种事的我,被当成变态也完全不奇怪。我幻想着她醒来后会尖叫反抗,会大声求助,为此我甚至犹豫过要不要把她绑起来,后来还是没有忍心那么做。如果她真的这么做了,我反而会觉得开心——看起来更像个变态了,是吧?我不否认这一点。
可是她没有。她问我她在哪里,我为什么把她带到这里,我如实说了,她却一点也不吃惊。她没有尖叫没有逃跑,只是平静地对我说,我期盼的事是不可能达成的。
我当时傻得冒泡,对事情的严重性一无所知,以为只要把她从那个男人手中解救出来就万事大吉,为此我还特地学了几个实用防御咒语,没想到根本没用上。整件事就仿佛我带着必死的决心造访恶龙巢穴拯救公主,却发现恶龙根本不在那里,而公主说什么也不肯离开一样,滑稽至极。
抱歉我把自己说得太高尚了,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我做的事跟绑架并无区别。
哦不,还是有区别的。我并没有向她的家属索要赎金。所以该定义成非法拘禁吗?大概吧。
她已经没有家人了,帕佩特提亚家族只剩她一个人,唯一的监护人也是个变态。全是他害的,她变成这样全都是他害的,她成为了他的提线木偶,他用她的嘴巴来说,用她的眼睛来看,这让我毛骨悚然。我本应该去斩断那些丝线,可我却什么也没能做到。
哎呀,我还真是没用。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没用。我最拿手的咒语是兰花盛开,其次是荧光闪烁。我的变形学和魔法史学得不错,但黑魔法防御术课就一塌糊涂了。具体来说,就是我很难对着人施魔咒,尤其是攻击性的咒语,比如全身束缚咒或者蝙蝠精魔咒之类的。大概是因为童年阴影?我其实也记不清了。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的理想其实是当个艺术家,艺术家有什么必要攻击别人?我只想让世界充满美好的东西而已。
但那都是之前的事了。偶尔我会想,如果我是个优秀的决斗者,也许就能救下她……但不管是怎样的幻想,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来回忆一下我跟她的初次见面吧。霍格沃茨举办三强争霸赛,我抱着免费旅游的心态申请成为随行人员,居然就真的通过了。晚宴当天,我站在布斯巴顿的学生队伍里东张西望,看到不远处德姆斯特朗的队伍里那个小小的金发少女。
她戴着眼罩,只露出一只蓝色眼睛,在队伍里相当显眼。德姆斯特朗真是残酷,我不禁这么想。要是我的话,可能入学第二天就被开除了吧……我打量着她,脑子里全是些奇怪的想法。她似乎注意到我在看她,又或者只是单纯地想活动一下颈椎,总之我们四目相对了。
我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的东西。她的眼睛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她没有在看我,也没有在看任何东西,那个小小的躯体似乎只是一具空壳……
我竟然有点兴奋了。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自己居然能察觉到这一点。我向来是个迟钝的人,通常要等到挨了打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但我居然察觉到了她的异常。难道成年之后,我也变得敏锐了?
“哥勒姆,你在看什么呢?”站在我身旁的凯莉压低了声音问我。
“那个女孩,不觉得哪里怪怪的吗?”我也压低了声音回答她。顺便一提,我的名字不叫哥勒姆,只是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会字正腔圆地念出我的名字,就用读音相近的哥勒姆代替了。
我的名字是高冷,如你所见,一个中国人。哥勒姆,Golem,读起来跟高冷很像吧?也许有那么一点点不像,但我也不是那么在意。
还是说回我与那个少女的第一次见面。凯莉也察觉了对方的异常,小声嘀咕:“简直像个瓷娃娃。或者是……傀儡?”
紧接着她就像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一样,捂着嘴巴偷笑。
“傀儡……Golem,你也一样是傀儡嘛!”
被凯莉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我这个被胡乱安上的英文名意思是会动的石像,泥人机器人一类的东西,大概也能跟傀儡归为一类。我为这个巧合而感到兴奋,后来我去跟她搭话,多少也有这个名字的原因。
总之,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一门心思地想认识她,想跟她多聊聊天。结果是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多洛希·帕佩特提亚,就读于德姆斯特朗五年级,仅此而已。她对自己的事只字不提,而我在听过她说话之后,草率地认为她只是性格内向,全然忘记了她那双空洞的眼睛。
没多久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多洛希·帕佩特提亚有时会表现得判若两人,她眼罩下的蓝色眼睛比露出的那一只颜色来得更深,有人通过那只眼睛去看,去听,去说。那只眼睛也跟我说过话,那个人用轻浮的腔调嘲笑我的愚蠢,对我发出警告,诸如此类。我因此知道了多洛希还有个“父亲”,以及对方将她当做“作品”的事。
多洛希是他的人偶,是他最完美的作品。多洛希明明活着,却没有为自己而活。
“怎么可以这样呢?人怎么可以这样活着呢?你明明是个人,为什么要做别人的提线木偶呢?”我发出一系列疑问,多洛希不回答我,那只眼睛只是看着我,甚至有点怜悯的意思。
我真的很生气,所以我打定主意走上犯罪道路。
在此之前,我一直是个遵纪守法的好青年,成年之前甚至没有在校外施过法术,但我飞快地适应了自己从守法公民到犯罪分子的改变。在我看来这十分有教育意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善恶一念间,每个人都可能变成魔鬼。
总之,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我掳走了多洛希。她没想着逃跑,我也不必费神关押她。至于她的“父亲”,我想他已经发现了,只是还没找到这里而已。我对自己的反追踪魔法还算有自信,不过对方找到这里也只是时间问题。我当时的打算是利用这点可贵的时间,让多洛希摆脱对方的控制,成为一个普通女孩。
首先我调查了多洛希身上的魔咒。那个人果然在她身上下了很多限制,但似乎没有直接控制精神的咒语。这件事震惊到我了,也就是说,多洛希是完全自愿成为那个人的人偶的。
多洛希坐在椅子上,像一个精致的木头娃娃。我心里不由自主地觉得难过,她明明是个如此可爱的女孩子,可我甚至没有看到过她的笑容。
于是我决定让她笑出来,发自内心地笑出来。
此后的三天,我们两个看了整整一百集《猫和老鼠》。
每每看到汤姆被杰瑞恶整,我总会笑到不能自已,我不相信有人能在《猫和老鼠》面前保持扑克脸。结果,多洛希确实笑了出来,但那笑声让我不寒而栗。
诺奈·坎特菲尔德大笑起来。他一直欣赏着我上演的这出独幕喜剧,并无从中干涉的意思,但我的愚蠢终于还是突破了他的忍耐上限,于是他从那只眼睛后现身,毫不留情地粉碎了我的幻想。
多洛希没有逃跑,不是出于对我的信任,也不是出于对诺奈的恨意,只是因为她没有接到逃跑的命令,仅此而已。她一直被诺奈玩弄在股掌之中,现在连我也是一样了。
后来我再看《猫和老鼠》的时候,我也笑不出来了。
但事到如今,我更不可能接受我的失败,把多洛希乖乖送回家。既然诺奈并没有把她抓回去的意思,这段时间我当然要好好利用。不必再躲躲藏藏之后,我带着多洛希走出了家门。我们去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看哈姆雷特,看第十二夜,看仲夏夜之梦。我们去坐轮渡,去喂鸽子,去酒馆喝黄油啤酒,去看魁地奇球赛。多洛希从不主动开口,只在我提问的时候才回答。我总会问她,你开心吗?她也总会回答我,因为没有接到指令,她没有开心的必要。
我并没有那么容易气馁。虽然感到失落,但我执着地相信只要这样下去,多洛希总有一天能够摆脱控偶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但我却忘了,这段时光本就是他人的施舍,只要对方愿意,他随时可以收回。
所以某天早上,多洛希从我的身边消失了。她依旧忠实地执行着那个人的指令,并没有因为我做的事情发生任何改变。
我什么都没做到。
按照常理来说,我也应该放弃那幼稚可笑的想法了,但我无法放弃,因为多洛希向我求救了。
也许那是梦吧。她抱住我,眼泪从蓝眼睛里滚落,那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表情,却比任何时候的她都像个人类。她说:
“求你了……带我走吧。”
然后我是怎么说的来着?不重要,总之我许下承诺,我要带她走。
我是个言而有信的人,就算梦里的诺言也会遵守。
诺奈当然会笑我天真,但我不在乎。我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只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后来的故事就很简单了。我试图寻找多洛希,但彻底失败了,诺奈自然也下落不明。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被严防死守,根本不可能寻找到他们的踪迹的时候,我开始思考其他办法,一些匪夷所思的方法,比如……时间倒流。
结果就是现在这样。我闯进了神秘事物司,试图寻找一个时间转换器,结果被警卫追赶,跌入了帷幔后面。就这样我的犯罪生涯跟人生一同落下帷幕,这出滑稽可笑的独幕喜剧究竟能否让观众开怀大笑,我是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
关于我死掉这件事,我并没有感觉有多悲伤,这从我的语气就能看出来。我唯一挂念的,只有多洛希。
我没能带她走。我到得太迟了,她空洞的眼睛这么告诉我。我应该出现得更早一些,应该在她成为“完美”的人偶之前就赶到的,如果那样的话,她总有一天能露出真心的笑容吧……
可惜我看不到那一天了。
我死于2003年的盛夏,也死于2000年的早春,死于在晚宴上的那一次对视。十七岁那年我便注定英年早逝,只是因为看到了那只眼睛。
多洛希,看到有人竟然如此愚蠢地为此而死,你会笑吗?
你的笑容很好看,真的,我在梦里见过的。 在那个梦里你对我笑,很多很多次。我们一同度过很多时光,也许有很多很多年……
虽然知道那是只有梦里才出现的光景,可是,多洛希,我好想再次见到你的笑容啊……所以,请允许我抱有幻想吧,也许未来的你会在某个时刻露出笑容,不是出于诺奈的命令,也与我这个愚钝的罪人无关,只是为了你自己,哪怕只有短短一瞬间……
多洛希,笑一笑吧。
*本篇的一些设定:
高冷,就读于布斯巴顿,麻瓜出身。
魔杖:山茱萸,独角兽毛,十二又四分之一英寸。
与六等星世界一样,不擅长攻击,但擅长把东西变好看。
守护神是苏格兰牧羊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