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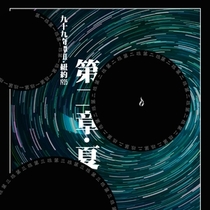




结束啦!
fw告一段落就过来把br的尾巴给补上。
虽说已经是和阿一关系不太大的一章了。
谢谢br期间一直看着阿一故事的大家,发生了很多事,好歹都告一段落了。
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啦。
↓
【第?日】
爱、罪疚与修复
只在很偶然的时候,牛果果会思考,四十岁的女人该是什么样的?这一回她开始思考是由于窗外忽然降下的夜雨。春季的南方,湿冷已经成为城市的本性,渗透性极强的水汽把屋子里里外外都侵犯了一遍。玻璃柜门上挂了几道潮痕,底部垂着颗豆粒大的水珠——去特教学校的时候,牛果果见过他们的康复方式,让不受控制的手们联系捡豆子,先是黄豆和黑豆、而后换成红豆,最后是绿豆——练习豆越变越小,结着的水珠倒吸饱了,妊娠般越变越大。
奇怪,为什么生育膨大这类事情放在自然界,就显得生机勃勃真理澎湃,换到了城市里穿着衣服的人身上,就变得不堪下流了?牛果果摸摸她的屁股——四十岁女人,一个膨大的臀部,不饱满、不上翘、不柔软可谈,只是一整块完整、不受意识控制的肉。她的文凭证明上,生育这栏是0分,没能给社会留下新的生产力,走在街上,只留下一道不太靓丽的风景线。她借着这个零分想向世界证明,一个女人变得膨大不总因为生育。构成她的大屁股的是薯片、可乐、软沙发和不良基因,是她的历史遗留问题——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
但不幸,牛果果发现当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拥有了一个膨大的身躯,她就手握一个同等比例膨大的奖杯,社会习惯会为她证明,她对人类生殖繁衍作出了伟大贡献。
四十岁的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牛果果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她猜测可能很多走在她窗户底下的行人能说出答案,乐观估计中规中矩和天马行空各占一半,统计起来也没法得出一个有显著结果差的答案。
她在冷得要命的窗口,看着从天上像线一样画下来的雨,听它在叶片上敲出打击乐,在心里把这个问题做了类比,问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就像问全世界的人类一个人应该是什么样。所有人都会回答,人应该是多样的(我这样的),他们的存在和回答证明了这个问题的愚蠢。但如果问一个已过四十的女人——比如此刻站在窗前的牛果果——四十岁的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她会忽然没法回答。她不是没有说出如我这般的勇气,而是四十年的生活经验让她产生了巨大的怀疑感,世界对于这样愚蠢的问题是不是真的没有准备标准答案?是不是真的不存在更高维的意识为我们的一举一动打分评判?
牛果果也被一些同样愚蠢的问题困扰。比如出门时邻家阿婆叫住她,问,几多时结婚生子。比如读者写信给她,问,爱情的定义。比如每天下午五点半钟站在灶炉边,看着被铁线球刷得干干净净的锅碗,问,今晚吃什么。牛果果给这些问题打分,愚蠢的数值旗鼓相当。她给自己煮了科学面,配的是昨天剩下的卤味,在桌子前一边挑面条一边拿出信纸写回复。爱情的定义,她捏紧手指在纸上绘出如幼儿般圆鼓鼓的字样——几十年过去了,时间侵害了她的面庞、她的躯体、她的手指甲,却没让她的字有半点变化,她是一个提笔就能写出日本女高中生字体的四十岁欧巴桑。她把这个问题写在信纸正中,另一只手的筷子停了,她催动左手挑起一根面条,对准嘴巴送了进去。她本不是左撇子,初中时期为了应付考试和同座一齐练了大半年,才学会怎么用左手吃面条的同时用右手写作业。一般,越是讨厌的作业越会被分配到这个时间段解决,面对这个愚蠢又宽泛的问题让她不禁想起了过去的数学作业。叹气,她咽下面条,又提笔写。
爱是什么?
她脑中忽然出现一个女孩的声音,青涩中夹着落寞,那个回忆中的声音喃喃道:「爱是什么?」
「爱是……我还没有学会的东西。」女孩说。
爱是我还没有学会的东西。
她跟着思绪写下这行字,这才发觉文不对题。不过,她不打算这么快就修改这句话。她打量着还带着未干墨水的幼儿字,想从等待墨水干掉的这段时间里偷出一半用于发呆,另一半则打算全部浪费掉,堂堂正正地偷懒。然后她就在这刻想起来了,一周前的电视采访,她言之凿凿地对着镜头说——爱是媚俗。
爱是媚俗。成双成对的人都不能幸免于难。人的爱媚俗,跨越不了柏拉图,精神的快慰只关乎米粒大小的结构是否快马加鞭的工作,甚于的部分,从头到脚全身,只是一块不会思考的肉。牛果果不知从哪里看到柏拉图是位素食主义者,她于是续写道,肉是无法理解一位素食主义者的理念的。
爱是媚俗。牛果果想,全人类都做的一件事,就是不停地爱、爱、爱!什么才构成爱?冲动体验和生理变化构成爱的反馈,再下一步才把这种错觉输送到大脑。爱是突发疾病,一开始只有一个人身患此症,而后,因为他耽于快乐的模样,更多的人加入了,世俗风由此吹起,所有人都在逐爱的道路上狂奔。可笑。又可叹。
这样写就完美了吗?她反问自己,一个四十岁的中国女人,想必和异国十八岁的男子高中生对爱情的期待不同,她此刻写下的话语会否伤害到他?若他正酝酿一场告白……不,牛果果否认了这个想法,他若想做什么,便不必写信来支支吾吾地询问她。因而她也只写自己的想法,不堪在意会造成的后果。她写道:
如果人人都歌唱崇尚爱情,那么世界定要一团糟。把一切初始都归结于爱,是无能者逃避现实的手段。因为爱所以畏畏缩缩,因为爱所以患得患失,因为爱所以痴狂疯癫,因为爱所以废寝忘食,因为爱所以了却闲情,因为爱所以一切过错都可以被推上光冕堂皇的情感王座,因世人都将爱视作最珍贵的宝物。
你询问我,所以我回答。我不理会这会带给你什么结果,我回答。爱不是最高贵的东西,不是许愿就会实现的流星,不是明烛点亮就能祈福的圣堂。充其量,它只是有溃烂表皮的陨石,是只余废蜡断芯的烛头,你不能从中汲取力量。你才是被点燃的蜡烛,你才是要坠落的石块。这绝对是世间仅一门的亏本买卖。
你可能又要问,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这条路上前仆后继?为什么你的父亲和母亲会结合、会生育你、会抚养你?或许你也从达尔文那里,从动物进化和人类繁衍那里求得答案,可我要说的是,并非如此。爱是媚俗,而人构成了俗世,继而生,就无处可逃地堕入俗途。逃离的人总是少的,清苦的,无人解的。
海子写,她们从我的墓上走过,讨论着蝴蝶的外衣,我再少一点勇敢,就会和她们走在一起。你知道,正是因为你的父母少了这点勇敢,你现在才和百亿人走在一起了。该感谢还是该忿恨,我把选择权交还于你。
这样的事,写信来问一个四十三岁的女人是不妥当的。孩子,你想从我这儿听到什么回答呢?我解答不了,我苦渡不成,我苦渡不成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回你这封信。凡想解答这个问题的人,从一开始就已经失掉勇气了。
牛果果停下了笔,把信纸推到桌的另一头。如今那里空荡荡,整个家都归她一人使用,不必与人分享。她换过另一只手,用筷子夹起一颗鸭胗,嚼碎了,吞下去。卤汁浸得刚好,微微发甜,也让她忘了远方还有另一种泡卤的味道。
答完了信她想起最开始的郁结,此刻窗外,雨幕仍旧绵密,逼得人在春夜也渗出一丝薄汗。她想到自己,四十三岁,仍不愿承认中年女人的形态。她还爱学猫般,做些异于人的举止,等待着幻梦中的人抚摸她的脑袋,蹭过她一根一根发丝,说褒奖的话。也会有人替她倒咖啡,替她烤热面包片,和她手挽手走过掉秋叶的大街。
她第一次夜里惊恐爆发,对着白墙叫,惊觉自己的声音像哑掉的老猫。她压了响声,不想叫邻居家多嘴阿婆听了去,于是整夜整夜地睁眼睡不着、发抖、寒战,没有人知道。第二天睡醒,窗外又是雨。
烦闷的日子。
四十三岁,失掉了爱的日子,她觉得没甚么好过。那封信已经封好了,放在玄关口,迟迟没拿出门投递。甚至她出门,还特地拐去邮局,寻一张面值足够跨海的邮票。自打知道了邮票的设计是可以以口涎黏着纸上的,她便常常用舌去封那信。娇秀的人写,以吻封笺,她没有kiss了,但还能用舌头糊上邮票,省下点浆糊钱——邮局总爱用浆糊,她小时候听闻,浆糊是可以吃的,每每去寄信,总对着那白色塑料盒中的糊状物吞咽口水。
什么都想用嘴尝尝。这是老师上课时提过的,口唇固着。是婴孩最早认识世界的方法。她想,放进嘴里常常也没什么,她吃过很多灰尘,细细品了之后发觉没有半点味道。也吃过一小片香皂,辣喉咙。而后她意识到,这些物件之所以没能登上饭桌,不因为它们不可食用,而因为它们——不、好、吃。
她去邮局的时候,就这样捏着买来的一排邮票看着回忆愣了好久。柜台小姐脾气好坏,不仅不让她买单张,还冲她嚷,要她快些掏钱。她把硬币都放在那人送她的红色小口袋里,唰得拉开,眼泪就掉下来了,赶忙丢下钱就躲到一边去。今天糟糕,她的餐巾纸全用来擦脚上溅上的脏水,没有预备擦眼泪用的。
她又有好久没写诗。编辑那头也没动静,体贴地让她自己钻玻璃瓶颈。大多数时候她觉得大家对她的诗不甚喜爱,她并非真实讨人喜欢的女孩,牛果果心知肚明。母亲在某夜吵架时忽而飞出一句:「你不过是装得很好罢了!」而后她又哭了一整晚,每每想起这句话,眼泪总就止不住流下来——全因她知道这过分的话说得完全对。她是只披着外皮做梦的空管,竹子外边看着翠绿,内里则是和她大脑一样的空白一片。
她原本完全不读诗,高中时期装模作样买了本,在没人的客厅举着书读,摸不出半点头绪。没过五页,那书就被她搁下了。一直读到大学,某天又翻开诗集,忽然觉得都懂了,忍不住在书页前为那些字词鼓掌。读了两三年,她自己也开始写。也不知要写什么才好,大学宿舍的锅炉总坏在冬天,冷得不行还没半滴热水,洗澡成了用自己体温温暖洗澡水的苦差事。牛果果愤而写下第一首,烧锅炉的阿姨一定嫉妒我和她喜欢的小女孩住在一屋,这是情杀。
跑远了。可她想到这些事,又把自己的诗翻出来读了两遍,过了舌尖就没再出声,只自己高兴。于是泪止住了,只剩两道痕。她摸了摸脸,把邮票夹进小包,撑起伞又淌着脏水回家了。
到抵家中,电子邮箱一响,电视节目的邀请又发来了。她现在对镁光灯棚生出一股厌烦感,不想坐在饱和度过高的彩色板前说胡话。邮件打开,客气礼貌,是上一个节目的后续剧集,宋体字工整地告诉她,那比赛——BR?——结束了。
牛果果想,结束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她一周前说,这是不齿的活动,纯洁在其中无处可寻,只是加速青少年污浊化的杀人游戏。甚至还激发没有参加的人,把他们坦荡的丑心剖开来,叫呼着捧了,端到街上给人看。怎么,还要她再来个一周总结不成?她不愿意干。
电视台又给她挂电话。让她来台里看录像片段。牛果果讶异,怎么,我们已经变得和那头一样了吗?这些片段也可以摘录、可以赏阅、可以评说?台里的人下最后通牒,你必须来,若是不来,今后的宣传全都取消。她慢吞吞地走到房间里准备包包,往里塞了鼻通、眼药水和邦迪,她去哪儿都不落下这三件。又出到餐厅,用暖水瓶给自己冲了袋桂花乌龙,倒进保温杯里,一同塞进包袋。
出门了,外边还是雨天。台里说报销打车费,她于是上便利店叫车——懒得在雨天掏手机一阵捣鼓。因雨,车来得慢,她又在店里闲逛起来。看到包装鲜亮的甜食,伸手想拿,又想起早饭午饭都已经吃过,瞥了眼标价,悻悻放下了。
车来了,在店外按喇叭。于是收了伞,缩着脖子冲上后座,司机从前排镜中指了指她身边座的扶手,上边系着一沓红色塑料袋。她点点头,挪动她的大屁股——衬得这个空间有些仄闭了——往另一头去。这个时候她才生出一点儿要运动减肥的冲动,她的屁股给别人带来不便了,真抱歉。可她顺利地解下了塑料袋,把她的长柄伞的硬尾巴塞了进去,打上结。她想起过去坐爸爸的车,爸爸总备着个裁过的洗洁精桶,雨天时,就直接把伞丢进去,可方便。但爸爸也已经很久没联系、没见面了,这样的方便,已很久没享受到。
车驶在路上,牛果果总觉得今天有些不同,连日的雨也特别闷人,一块湿海绵一样压着胸口。车窗被她和司机呼出的热气糊住,她忍不住伸手指在上面画画。看到手指她想起来,忘了补涂指甲油,右手食指上半掀起块速干绿甲油,是她昨天洗衣服时蹭到的。她于是把整块绿色都撕扯下来,除开毛躁了些,倒显得更整齐。
今天定是要发生什么事。她这样想。
到了台里,她从塑料袋中取出伞。伞柄已变得湿漉漉的,撑开时,不时往下淌水,弄湿了她的手。只好将就着打到大堂,她把伞交给门口的迎宾小姐,让她帮忙套新的塑料袋。空出手往包里掏了掏,拽出餐巾,擦干了水。
负责节目的人在沙发那边等她,很快认出她来——四十三岁还敢染亮绿色短发的女人,好少见!——请她去准备室详谈。她跟着人走进去,负责人看来三十几岁,身体比她年轻,心灵比她成熟。他们各自寻了一张椅子坐下,牛果果坐的是张皮椅,不舒服,雨季让皮上也挂着湿气。
她打开包取出保温杯,喝了一口,偷偷伸舌头嫌烫,急急忙忙把盖子又旋了回去,被子搁在脚下,包放在膝头。负责人挠了一下他因潮气软榻的发型,刘海已经根根分明了。
「哎呀,抱歉叫您来,有些事要和您讲一下。」
「是什么呢?」她不解。
「上一期的节目,不是请您谈了谈对BR法的看法么?这活动他们现在已经结束了,就……」
「有人死去了吧。真的只剩一人活下来了?」
「真的只剩一人。」
「好残酷。死掉的小孩没了未来,活下来的小孩也不好过。」
「是这样,这次找您来就是因为这些小孩。」
「小孩怎么了?」
负责人把他坐着的旋转靠背椅转到另一头,从桌子上拿起一个文件夹,照着念:「我们发现死去的小孩里头,有一位是您的书迷。」
牛果果的眉毛跳起来了——该不是、怕不是、不要是——她又想到家门口玄关上躺着的那封信,她原打算今天连着带出来的,可她忘了!
负责人继续说:「在他的屋子里搜出了您的诗集,各种版本的都有,他不懂中文,竟然还收了四本不同的国语版。」
「他叫什么名字?」她追问。别是那个名字就好!可她明明知道,若不是那个名字,她又会有种惋惜,像与世界擦身而过了那般。
负责人翻过两页材料,才找到那个小孩的名字。
「是一个男生。十八岁,名叫利根川荣一。」
她心里跟着窗外一同打下一道雷。那个写信问她「爱是什么」的男孩子,果然就是这个已经死掉的小孩!她没及时回信,误了时间,而今她永不必回了!永不必了!牛果果感到一阵痛楚,她虽不怎么喜欢他提的问题,但她还是在心中构筑了个他的模样,再提笔给他写信的。这个她想象出来的回信对象,如今已经死掉了!
负责人摘下一张用曲别针别好的照片,递给她看。她凑过去,是那个小孩的照片,和她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模样,眼神很凶,头发乱糟糟地扎在脑后,一副轻浮样。
不是她中意的小孩。这样的小孩就算长大,也变不成好人。
「您有收到他的信吗?」
「没有。」她撒谎了,这下更不想让旁人知道她回过一封信。一定有人要指责她的懒惰和拖延。
「好可惜。这下子也没人知道他写了什么。」
她坐在那里,突然生出一种古怪的灵感。这个孩子,写信给她,问爱的定义,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告白吧?是为了知晓爱而后实践爱吧?她愈发坐立不安,皮椅好像被浇了水,从她的大屁股开始,全身都开始变湿。
「还有哦,他们家不一般。有一个爸爸和两个妈妈,三个人和和气气地住在一起呢。」
她抬起头,用好大的声音又问:「什么?」
「是说他们家是新型家庭,一个爸爸和两个妈妈。爸爸和其中一个生了他,三个人一起抚养。」
她长出一口气。如果是这样,他的来信能做别解。他可以是为父母父母来信——那样她的负罪感或会稍稍减轻。
「节目你上吗?谈谈这孩子?」
「不上。」她抓起脚边的水杯,「这种事根本不该存在。」
她落荒而逃。
到家,玄关上还躺着信。她收起伞,水滴滴答答顺着伞柄留到木地板上,她不管,只是盯着那信封,像要把它灼穿。
她要毁了这封信。连带利根川寄来的另一封信,她想要一齐毁掉。丢在盆里用火烧得干净。她取来烟灰缸,这东西不是她的,是另一个人留下的,她讨厌烟味,从不抽烟,但没勇气处理这些东西,只是任凭它留在玻璃茶几上,连烟蒂都没有清。她不敢看那些小东西,脏脏的,带着只有她觉得的沉重气息。她取来火机,是网络购物时跟包裹一起送来的附赠品,上面写着:「幸福笔业」。信给她提起来,点了火着了半角,她把纸全放进烟灰缸,任它烧去了。
她穿过客厅去阳台听雨。还是连绵不断的,雾气大到吞下半栋对楼。行人们打着伞,机车上笼着亮蓝色或彩粉色的雨衣。大家都好忙碌,社会急急忙忙往前冲,一点儿不怕摔跤。她躲在屋檐下,怕得要死。她溺于虚构的苦痛中,没半点实感。总做没用的事。流没用的泪。妈妈的话又响起来了,二十年过去还是硌得她心疼——「你只是看起来、看起来、看起来的东西!内里什么都没有!」——她撇嘴,又想哭。
她想到杜拉斯,想到广岛之恋里,男人问女人如何摆脱疯病。女人说:「后来,当我有了孩子……病也就不可避免地好了……」她或许也该去做母亲,做一个四十三岁终于讨到孩子的母亲,让她的病不可避免地好起来。然后她又觉得这小题大做了,她病得不重,病完全是出于自怜,不值得一提。
她拉上玻璃隔门,走回里屋。看到信已经被烧得干净,成了一堆灰,躺在烟灰缸里,随着风摆动着,做遗体告别。她用两只捏起烟灰缸,没带伞,出了门,把那些灰烬连同没清理的烟蒂一同倒在了社区垃圾桶里。
没盖的桶满了一半,其他家的生活垃圾飘在臭水里。她把灰倒了,站在雨里看了会儿,觉得时间够了,就返身归家。
那天夜里,她久违地写了诗。
《写给有诗的情人》
牛油果
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
那我要不停地写诗写诗写诗
写上整整一天来填补空白
如果明天就是离去之时
那我要不停地读诗读诗读诗
把更多的天才之作留给你
等到你明了了我的心意
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作也就应运而生
[BRSA-第?日]
牛果果--苟且,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