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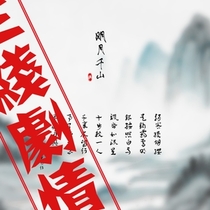

我居然纯写文了。。。。啥也不说了先去切个腹。
错别字和病句请无视,答应我不要为难一个画手好吗(有脸说吗
----------------------------------------------------------------------------
1.
阮岑做了个梦。
梦中他被一条通体漆黑的巨大的蟒蛇缠绕,身体被紧紧箍住,骨头都发出悲鸣。蛇身冰凉而黏腻,坚硬的鳞片划过他的皮肤带出丝丝血痕。蟒蛇的头升起,悬停在他面前,吐出的信子带着浓重的血腥味拂过他的面颊。
只差一点。
阮岑的指尖已经触到刀柄的末端,但不管怎么用力也无法再向前一寸。只差一点就能拔出刀宰了这个畜生。阮岑表情扭曲,死死盯着蟒蛇大如灯盏的一对招子。
忽然那蛇笑了。
阮岑头皮一炸。蛇的笑声嘶哑又癫狂,又好像随时都会断气一样破风箱一般漏着气,听着说不出的诡谲。阮岑认得那笑声,他这辈子也不会忘记的笑声。
笑声戛然而止,蟒蛇的脸仿佛被打散的水波,慢慢汇聚成一张熟悉的脸。
那蛇一字一字地说:“我早说过,你逃不开的。”
然后阮岑惊醒了。
他背后出了一层冷汗,身上的疼痛和意识一起渐渐清晰起来,梦魇留下的恶心和厌恶如鲠在喉。
“阮大哥!你终于醒了!”一个惊喜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阮岑转头看到库夏的脸。他被库夏扶着坐起,发现自己正在皇城司自己的卧室内。天色已晚,只有少年一个人守在床头。
“唐珏呢。”
库夏没想到阮岑开口头句话竟是问这个。他的笑容一下子僵住,好一会儿才像蚊子哼哼一样支支吾吾地道:“……让他跑了。”
阮岑猛地一把甩开库夏,少年趔趄几步坐在了地上,一时回不过神。他的阮大哥从来都是笑盈盈的,让人感到如沐春风,想要亲近。阮岑对他格外纵容,从未说过重话。即使他犯了错,阮岑也只会佯怒对他象征性的稍加惩戒。他从没有见过阮岑像现在这样的表情。那双以往总是弯出一个温柔的弧度的眼睛冷的结霜,仿佛在看什么碍眼的脏东西。库夏眼眶一下子红了,不知所措地向后退了些许。
忽然“哐”的一声响,门被谁粗鲁的踢开,打破了屋内凝固的气氛。
只见杜秋晏双手端着药跨进门内,后面跟着的越泽回身将门关好。望望床上那个,再看看地上这个,杜秋晏翻了个白眼,张嘴就喷:“你在床上睡了两天两夜,小夏也不眠不休的照顾了你两天两夜。谁知道你一睁眼就把起床气往人头上撒,阮大人好威风,区区长见识了!”
越泽一言不发的拉起库夏,发现他竟微微发抖。紧接着两人都被阮岑的惨叫引的望了过去。
“杜秋晏,你他妈想烫死我!?”阮岑端着药碗像端着烫手山芋,差点一把丢出去。
“难不成你还想区区吹凉了喂你吗?”杜秋晏早已经退开了好几步,省的药汤洒在自己身上。“反正你这个白眼狼也不知感恩,小夏你说是吧?”库夏忽然被点名,吓了一跳,抬眼见阮岑也看了过来,不禁一哆嗦。
阮岑打量库夏片刻,少年确实眼下发青,眼中都是血丝,看起来很久没有合过眼。长的那么人高马大,却被吓的一副战战兢兢快要哭出来的表情,着实可怜。他干咳了一声,放轻声音向库夏招了招手:“你过来。”
库夏鼓起勇气走到阮岑床边,单膝跪下,低头道:“都怪属下没有按阮指挥使的交代及时抓住唐珏,使计划功亏一篑。请您惩罚我吧。”
半天没说话的越泽也上前抱拳跪在库夏身旁:“属下失职,在地宫脱队,没有保护好阮指挥使。库夏因为从未见您受如此严重的伤,一时乱了阵脚,才让唐珏有机可乘。是属下的责任,请您责罚。”
“……”阮岑支起腿,颇为无奈 “我说这还没过年呢,在这儿跪一地我也不会给你们发压岁钱的。”
库夏闻言抬头,面前的阮岑眼中含着三分笑意,又变回了他熟悉的那个阮大哥。
“行了,你们先下去休息吧。别打扰大人说话。”阮岑挥手赶人。
杜秋晏也道:“别担心,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这厮一时半会死不了。”
于是库夏一步三回头地硬是被越泽拉了出去。
临安冬夜的风冷的刺骨,越泽将披风递给库夏时,发现他已经换了一副表情。库夏的眼窝比中原人都要深一些,月光打在他脸上在眼中投下一片阴影。他的神色中再没有像先前要被抛弃的孩子般的无助,而是近乎阴鸷地沉静。
“唐珏……”库夏喃喃道“……都是那个人的错。”
“阮伯渊,我从来没有发现你对找死如此有天赋!”屋内,杜秋晏变脸也如翻书快,怒不可遏地将药碗在地上摔的粉碎,气势汹汹好像接下来就要扑上来把床上坐着的人掐死。
阮岑从来没见过这位喜欢冷嘲热讽的公子哥这么失态地发飙,摸摸下巴想笑不敢笑:“我的错,是我托大了。秋晏先别着急……”
“不着急!?你知道姓唐的给你的身体里埋了什么吗?走脉针,等那根针到了你的心脉,华佗在世也救不回你……!等你一命呜呼了我再着急还来得及吗?”
“放心,我不会死的。”阮岑淡淡笑了笑,目光投向微弱的烛光。他又想起那个梦,那些曾经想操控他的人,想践踏他的人,想要他命的人,都已经被他杀死了。今后也不会有人可以妄图左右他的命运。
“我的命,只有我自己说了算。
2.
十二月初十。
清晨的薄雾未散,一个披着斗篷的白衣青年敲响了皇城司的大门。
两侧的侍卫仿佛没有看到他似得直视前方。半晌厚重的大门被从里面打开,开门的士兵扫了青年一眼,便一言不发的把他让了进去。
青年本想和领路的士兵客套两句,谁知抛出去的话皆是石城大海,没一个回响,也就不再言语,只时偶尔向周围打量。他们穿过长廊,一边的校场上数十身材魁梧的年轻军官正在操练武功,身手皆不同凡响。
忽闻一道凌厉的破风声,白衣青年挥手,掷出的暗器和射向他的箭在空中相撞,箭支被从中间切成两半,落在青年脚下。他抬头向箭射过来的方向望去,一个束着马尾的卷发少年持弓站在不远处的屋顶,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目光如同鹰隼。带路的士兵浑然不觉般自顾自的向前走,转眼间那少年又搭了两只箭拉满弓,对着青年放出。
青年抽出腰间的扇子,一边向引路人的方向退一边劈手击落箭支。随着箭支而来的还有从房顶跃下的少年,他飞身逼近了白衣青年,冷着脸二话不说拔刀就砍。白衣青年只好皱眉接招。奇怪的是不管是带路的,还是在附近练武的军官,都好像又聋又瞎,对这场打斗熟视无睹。
两人打了有三十几个回合,才听到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出来阻止。
“慢慢慢,小夏,叫你出来迎接唐公子,你怎么和他打起来了?”来者正是阮岑,身着一袭红色官服,倚在柱子上笑的神采飞扬,完全看不出和一个月前被抬回来出气多进气少的是同个人。
库夏闻言马上收了刀,规规矩矩地背手站到阮岑身后,再不看唐珏一眼。
“唐公子,别来无恙。这小子不懂事,喜欢和人切磋,没有恶意的,还请不要介意。”
切磋?刚才那副架势明明招招要命。唐珏不以为然,还是挑眉笑道:“无妨。”
阮岑一路有说有笑,带着唐珏来到一间客房。杜秋晏已经在里面坐着了,看到唐珏也不起身,只是微微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库夏关了门立在一边,板着脸好像一尊门神。
“那么事不宜迟,我这就给阮大人推针吧。”唐珏说着微微沉吟“只不过还要请这两位无关人等出去我才能开始。”
“无关人等?”杜秋晏眉毛纠结在一起,眼看就要发作。阮岑却按住他的肩膀,点头道:“唐门的绝学是不容其他人窥视,是我疏忽了,你们先出去吧。”
杜秋晏瞪了一眼阮岑,依言带着库夏离开。房内只留下阮岑和唐珏二人。见唐珏还没有动作,阮岑道:“唐公子还有什么要求?但说无妨。”
“正如阮大人所说,唐门绝学不容外人窥视。阮大人亦非唐门中人……在我为大人推针前,需要给你点穴闭气。大人没有意见吧?”虽是询问,唐珏却有恃无恐。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能有什么意见?”阮岑笑的无奈“唐公子,请吧。”
一炷香过后,阮岑被唐珏点穴唤醒。试着运气,阮岑没有发现异样,看来唐珏真的是要给他续命。
“那么,下月初十我还会在同一时间登门拜访,先告辞了。”
“唐公子不忙走,辛苦了你这么久,不如留下来吃个午饭吧。”阮岑嘴里这么说着,却刚睡醒般打着哈欠,一脸我就是和你客套一下你可千万别当真。
唐珏驻足眨了眨眼睛,干脆答道:“好啊。”
“啊嗷?”阮岑的呵欠打了一半走了调。他马上调整表情,好像自己真的很热情好客一般祭出招牌笑容“那再好不过。”
阮岑说要请客吃饭时虽然没有什么诚意,真招待起人来却是一点儿也不含糊。不一会儿客房的圆桌上就摆满了酒菜,虽然不见得是什么昂贵的菜肴,但都做的非常精致,别有一番风味。除了偶有仆人进来送菜,屋内还是只有他们两人,一时静的有些尴尬。
“我平日不是和弟兄们混在一处,就是和人出去应酬,这么安安静静的和人一桌吃饭倒有些不习惯了。”阮岑没话找话。
“唐门人多,每次吃饭也是很热闹的。”唐珏应道。虽然是他自己答应要留下吃饭,坐了半天,却并没有动筷子。
“每次请唐公子吃饭,唐公子都只坐着看。我倒不知原来唐公子是用眼睛吃饭的,光看就能看饱。”
"只要能吃饱,你管我用哪儿吃呢。”
阮岑算是明白了,这讨人嫌的家伙根本不是想吃饭,是在找麻烦呢。阮大人的脾气众所周知的好,最不怕人找麻烦。他不以为意地微笑,拍了拍手。不一会儿便有人推门而入,端上一个雪白的酒壶。
“不吃饭就陪我喝一杯吧,这是前些天别人送的葡萄酒,听说是从西域买回来的,很是难得。唐公子尝尝?”说着阮岑亲自为唐珏斟满了一杯,红色的酒液几乎要从白玉杯中溢出,鲜血般扎眼,散发出奇异的香甜味道。
唐珏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赞道:“好酒。”
阮岑总算满意了,坐下一边聊天,一边和唐珏推杯换盏,一派宾主尽欢。
然而唐珏看似喝的干脆,其实那酒一滴都没有入口,借着袖子的遮挡,全倒进了藏起来的小瓶里。
“嗯……也差不多是时候了。”阮岑半闭着眼微醺,撑着脸把玩着酒杯,忽然冒出了一句。
唐珏本想问是时候什么,忽然感到手脚发凉,整个人开始慢慢下沉,头脑发昏。他想站起来,却发现下盘无力,又跌坐回椅子上。再看阮岑,哪还有刚才要醉不醉的样子,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双眼不能更清明。
“你……”后半句还没说完,唐珏就彻底昏了过去。
3.
夜阑更深。
阮岑坐在离床不远的椅子上静静望着床上好像睡熟了的人。那人眉眼精致的有些凌厉,只有这个时候看上去才像卸下了防备,显得柔和很多。
阮岑至今为止见过许多形形色色的人,对忠厚老实的人他施以恩德,对有所求的人他给予他们想要的好处,对懦弱胆小的人他以其弱点牵制。顺应他的人他毫不吝啬的回报,和他对着干的人大都被送去见了阎王。
很久没有人让他觉得这么棘手。
然而不知为何他还是忍不住去探究,以至于他有那么一瞬变得不像自己,为此几乎命悬一线。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想到这儿他的眼神沉了沉,但阴霾马上又被和往常一样的笑意冲散。
“醒了?”阮岑近乎温柔地开口。
唐珏从床上坐起来,默默检查了一下自己手脚有没有缺件后才抬起头:“阮大人这是玩哪出?”
“唐公子不胜酒力,小憩了片刻。”
“可那酒我一滴也没喝。”
“要是喝了,你现在也不会在这里。”
唐珏顿了顿:“熏香里下了迷药,酒里是解药?”
“不错,唐公子果然聪明。秋晏的迷香真是厉害,无色无味,连唐门都能放倒。”阮岑笑道,语气忽然多了几分伤感“我原以为和唐公子同生死共患难一番,已经是过命之交。没想到唐公子还是对我如此戒备,让我怎么放心把命交到你手上呢?”
“大人到底想做什么?”唐珏微微皱眉。
“我想还钱。”
“什么?”
“唐公子为了我用了极为珍贵的金风玉露,又耗费真气为我疗伤,那一百金不早日还给你,我寝食难安。”
“……”唐珏忽然感到不详“什么意思?”
“床头有镜子,唐公子照照便知。”阮岑微阖双眼,笑的意味深长。
唐珏狐疑地端起镜子看了半晌,身形一震,脸色突变,。
“我专门找了临安最好的工匠为你打造的,唐公子可还满意?”
唐珏扯开衣襟,只见自己脖子上戴着薄如蝉翼的金色的项圈,上面刻有细密精美的流云纹样,还镶嵌着数颗价值不菲的宝石,流光四溢。项圈的正中刻着一个狼纹,中间有一很小的“渊”字。
“这项圈工艺极为复杂,用的是自称鲁班传人柳老板特制的奈何锁,没有钥匙世上任谁也打不开。材料是极品玄铁,虽然轻薄,最锋利的刀也没有办法将其斩断,为了美观还特意镀了层金。加上上面的雕花和宝石,算下来花了我两百金……”阮岑若无其事翘着脚扳着指头吹嘘道“不过看着和唐公子这么相配的份上,多出来的算我的一份心意,便不用找了。”
阮岑又道:“唐公子既然握着我的小命,江湖险恶,我自然要保证唐公子周全。只是无奈公务繁忙,分身乏术。这项圈中间的刻印是我的私印,若唐公子在临安遇到什么麻烦,只要让城里的士兵看看这个印记,定有人会帮你解围。”
“……”唐珏盯着阮岑,虽然脸上没有表现出咬牙切齿,估计心里是被气狠了,一时竟无言以对。
“啊,差点忘了说。”阮岑才想起来似的一拍大腿,明快的笑容却沉了下去,摇曳的烛光映在他的眼睛里仿佛鬼影幢幢“……若是我有什么不测,戴着这项圈的人也会被认为是凶手,无论海角天涯都会被我的人击杀。唐公子切勿忘记。”
“这样一来,才是真的同生死,共患难。你说是吗?”
Q&A
1. 阮岑梦里看到的人是唐珏吗?
不是。是他的老相好(不是)。
2. 为什么唐珏让阮岑让闭气他就闭气,一点不反抗?
唐珏敢在皇城司杀人,出门就被剁了。而且要杀早杀了,也不会特意跑到皇城司。
3. 唐珏为什么会晕倒?
进门的时候熏香里有毒,到了一定时间才会发作。其实两个人毒中了毒。葡萄酒里面有解药,如果唐珏相信阮岑喝了酒就啥事儿没有直接回家了。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啊。
4. 阮岑为什么要给唐珏戴项圈而不是戒指手环脚环?
戴别的地方万一对方是个贞烈男子一气之下把手啊脚啊的砍了怎么办。横竖头砍了会死,还是戴脖子上吧。
5. 阮大人给唐少戴项圈是出于啥心理?
报复?控制欲?
性命握在别人手里是阮岑的大忌,是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为此甚至会做出鱼死网破的事情。别看他笑嘻嘻的其实也是非常窝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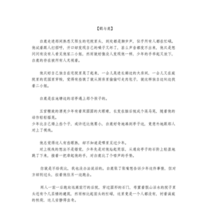



昨夜闻笛落梦中,去也匆匆,寻也无踪。
楼外华灯应幢幢,旧瓶新装,对影成双。
城南有双儿,五岁入朱门。
钟礼模模糊糊地觉着有人牵着自己在往前走,转头看时却发现那人太高大,脖子仰疼了也见不着他的脸。钟礼叫了那人一声,那人也只是点了点头。
“等你们长大了,就不用仰头看人了。”
那人一手牵着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却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样从衣物到五官都分毫不差。从孩子的高度只能看到那人的佩剑,那把剑好好地装在鞘里,又狭又直,泛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光芒。剑的主人也像剑,也是又狭又直的,一脸难相的男人牵着他们,不知要走到哪里去。
“……这世上毕竟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人。”
男人不知走了多久,在一扇门前停了下来。回廊是雷家本堂的回廊,房间是大当家的房间。两个孩子对望了一眼,他们都听得出那声音是霹雳堂的徐长老。
“两个都是一般的机灵懂事,可悟性这玩意儿毕竟是天给的,求也求不来,甩也甩不掉。就算他们一般的潜心习武,有希望能成一代高手的也只得那一个。依我看,着另一个跟着堂内的行家学习经商之道,将来富甲一方,也不算丢了钟小姐的脸。”
房里有人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像是霹雳堂的大当家雷掣。
跟着又有一个人咳了两声,这人的声音却不像雷掣那么沉,那么重,倒像是对徐长老说的那些都无甚关心一般。
“你要说机灵,那可就说对了。你是不知道,前几天礼儿到我房里玩,我出去再进来,他已经乖乖坐着在玩我的火药了,乐儿就更加了不起,他拿着我画的图纸啊……”
“四……四当家,这些东西让小孩儿乱碰不太好吧!?”
房里的人像是起了小小的争执,两个孩子垂下眼睑不约而同地拉了拉那人的衣袖。那人一句话不说,便牵着他们慢慢又走远了。
“你的剑是好剑么?”
一个孩子突然这样问他。
“白浪是我的爱剑。”
那人答得有些牛头不对马嘴,孩子却也没有追究。
“真好啊。你是在哪里得来的?我也想要一把好的兵器。”
“归剑门里有不少铸造兵器的名家,你若想要的话,我就帮你问问。”
“真的吗?”
那两个孩子放开了男人的手,肩并着肩仰头看他,两双眼睛里都闪着奇妙的光芒。
“那我要一把刀。”
十二执斧钺,十二修百草。
正午的太阳烤得路上的黄沙都像是冒出了一阵阵的烟,人烟稀少的荒道上没有几棵树,却有不少影子。十数个手执兵器的男人正围成圈朝一辆运货马车慢慢接近,拉车的马已经被解了下来,马车上只有一个男人和两个十二岁的少年,奇的是那两个少年相貌生得一模一样,神态气质却大不相同。
“子岐,你骑马回去通报大当家,叫他派人过来接货。”
看上去老成稳重些的少年一动不动地盯着慢慢靠近的强盗们这样说,稚气未脱的声音里还有些颤抖。那中年男人同样紧盯着不速之客们,只用右手轻拍了拍马背。
“季离说得对,你年纪虽小,功夫却已颇高,你从西南角冲出去,那里守备最弱,三五个贼人轻易拦不住你。”
那看起来机灵活泼些的少年逡巡一瞬,随即用力点了点头。
“我马上就回!武叔,季离就拜托您照顾了。”
最后一字的话音还未落地,说话的人已经翻身上马朝包围圈的西南角疾射而出。也许是他势头太急,那些强盗竟一个个都退了一步,像是给他让开一条道。骑马的少年去得极快,到他消失在众人的视野里,他都没有再回头一次。
自然也就看不到雷武的刀已经抵在了留下的那个少年颈上。
“季离,你虽然武艺不高,却很聪明。只是你运气不太好,你不该轻易相信人的。”
雷武本来不是个话多的人,但人太紧张或太高兴时都容易管不住嘴。
“我没什么才能,但毕竟给雷家卖命大半辈子,这些是我应得的。季离,我是看着你们长大的,别人认不出你们,我认得出。你的那些鬼主意对我没有用。”
雷武越说越快,声音里逐渐带上了笑。那些强盗——现在该说是他的那些手下——也稀稀落落地跟着他笑了起来。雷武的笑声很快停了,他发现那个叫做季离的少年也在抖着肩膀笑。
“我们让你认,你才认得出来。雷家让你活着,你才能活到现在。”
那少年还在笑,像是他眼里看见的,心里想着的,都是这世上最快活也没有的事情。雷武却已笑不出了。
雷武直勾勾地瞪着那少年从货物顶上拖下来一个比他自己还高些的布包,慢条斯理层层解开,精钢的寒光从旧布底下若隐若现。
“您不该轻易相信人的,我才是钟子岐。”
钟礼早就下了马,盘坐在土路边摊开几个小包,一心一意地调着些什么。曾几何时的那人就站在他身边看他调药,仍是那把又狭又直的长剑,仍是那身素衣青袍。
“武功再高的人也会受伤,所以我就去学药理。”
钟礼也不管那人有问没问,只是头也不抬地淡淡说了一句,就将调好的药粉装进小罐里站了起来。青衣人看着钟礼悠然上了马,往回行得几步,忽然又转过头来深深看了他一眼。
“托你做的刀,做好了没有?”
十八广交游,十八通商贾。
雷威总是青楼花街里最受欢迎的那一类人。年轻俊秀,豪门之后,出手阔绰,既通音律书画又会猜酒扯笑,也不会与某个人过分纠缠。他请客吃饭总爱设在花街,客人和花街的人都总会给他几分面子的。只有跟钟乐吃饭喝酒的时候,他不太爱去花街。
雷威受欢迎,钟乐却比他更受欢迎。钟乐像是跟一块石头也能做朋友,他能让人人都觉得遇上自己就是钟乐这一天最快活的事情。雷威不愿意跟钟乐去花街,钟乐却是最爱跟他去那些地方的,两人在街上走走停停,不时遇到跟两人打招呼的认识或是不认识的人,见着了合眼缘的酒肆就进去喝一杯再出来,行过三四间的时候,听见酒楼的掌柜在门前陪着笑谢客。
“真是对不住,今儿钟四爷已经把这二楼全包了,这位爷不如还是另择个日子……”
钟乐和雷威对看了一眼,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钟四爷,你也是钟四爷,楼上那位钟四爷往家里带银子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往你嘴里带酒啊,威哥。”
楼上正是一片觥筹交错,华光之中的钟礼并听不到有两个人正在楼下说他的长短。钟乐跟雷威在街口分了手,回身就见到了那个人。那人正板着脸将他的剑入回鞘中,钟乐却像是见到多年的好友一样,笑嘻嘻地走上前去一把揽过了他的肩膀。
“嗯,是你啊!我记得你,你怎么总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你才见过我几次,说不定你刚好都碰上我不开心的时候。”
那人盯着他认认真真地这样说,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在说笑。
“说不定我也不过是你做的一个梦。”
他不像是在说笑,但钟乐还是放声笑了起来。
“你真有趣。今天没空招呼你,改天一起喝酒吧!别忘了托你找的那把刀。”
“……就快完成了。你要去哪里?”
“挡酒。”
秀气的青年朝他眨了眨眼,随手指向刚才走过的那座酒楼。
“两个人一起走回去,总比一个拖着另一个回去好吧?”
龄二十二,习刀术。
钟礼给自己斟上小半盏酒,细细品着喝了,背后传来一个轻而稳的脚步声。很少有人能这么接近他背后,但他一点也提不起回身攻击的念头,不知怎么的,他就是觉得这人不会对自己有威胁。
“你来得不巧,我没准备多的酒杯。”
“也不用。那把刀找到了,我只是来送给你。”
他站起身来回头去看那人,现在他的视线已经足够高,不必再仰起头来才能看见那人的脸了。那人手里掂着一柄刀,刀身色泽沉郁,造型古朴,像是有了些年头。钟礼淡淡道了声谢,伸手去接,手却扑了个空,他看着那人手里的刀,不知怎么的突然有股淹没全身的疲惫感。
“是了,我都忘记问你了。报酬要什么?钱还是物?”
“都用不着。我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那人垂下眼睛看着手里的刀,跟着视线又落到了那把叫白浪的剑上。
“那时候问我要刀的,究竟是哪一个?”
“……!!”
钟礼猛然惊起,才发现自己仍躺在床上。手边自然没有什么古刀,那个青袍素衣的剑客即使在梦里也不认得曾经在哪里见过,醒时自然更记不起何时何地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钟礼摇着头下得床来,顺手拿过桌上的酒壶给自己斟满了一杯。酒早已冷了,但他一仰头一饮而尽,却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他自己的声音回荡在狭小的房间里,听起来既陌生又困惑。
“什么怪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