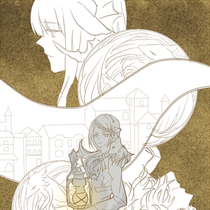秀色可怜刀切肉,清香不断鼎烹龙。
锅盖掀去,热浪如雾腾来,肉片浸在汤中光鲜夺目。白单秋本就饿得发慌,时至正午,胃部的绞痛愈发强烈,见着此情此景恨不得连同砂锅一并吞下。可手指刚触到筷子,又迟疑的收了回来,抬眼去瞟坐在对面的人。
方才他在街上晕厥,幸好被这人扶住才没闹出更大的笑话。恍惚间听他调侃自己,定了定神还未回嘴,肚子便不争气的响了一声,直惹得白单秋伏下身,只想找个洞钻进去静静。
对方却是闻声就笑了,笑得快意十足,引人侧目。待他笑罢,兀自抱着臂,目光在周围转了一圈,定在路边酒楼的招牌上:
“萍水相逢确是缘分,”那声音懒洋洋的,“恰好到了时辰,不如兄台陪我去喝两盅如何?”
——话至此,便知这场宴席可是对面那位做东。东家还没起筷,他白单秋又非言行无状之徒,怎敢先吃?
白单秋攥了攥袖角,向四周望去。方才这人可是孤身前来,待进了雅间,才看出他居然带了这许多仆从,屋内四角俱有卫士负手而立,座位两侧也各侍一人,当下心中不免有些迟来的惶惶然,不知是偶遇了哪位达官显贵。
倒是那立在街中的护脉神小姐见着这位,忙抬步跟了上来,眼下也随在一旁。虽说两人之间暂无沟通,却无疑是一对主仆。哪怕这屋内气氛并不轻松,白单秋想,美人配美食,也算值当。
“还未请教兄台尊姓大名?”他突听对面人问。
“不敢,在下姓白名单秋。”白单秋赶紧拱手。
“哦——”对方拖了长音笑道,“我可说是缘分吧,你我本家,我也姓白,拙名景页。”
“景页?”白单秋愣了愣,“是哪个景哪个页?”
“一花谓一景,一纸谓一页,这两个字。”白景页答。
白单秋空写了两笔,脸色古怪。白景页好似知道他想什么,不动声色的继续说,“拆字而为,也不算是范了当今圣上名讳。”
当今皇帝名苍颢。
“我想什么有这么明显?”白单秋脱口而出。
“我不过是按寻常人的想法推断,请别见怪,”白景页呵呵笑着,顺手拿起筷子夹了筷鱼搁在碟里,“白兄请便。”
可终于能吃东西了,白单秋克制住席卷全身的雀跃,姑且矜持的也挟了些菜。白景页瞧他束手束脚的样子,禁不住又笑了出来,那眼睛眯成一弯,末梢斜斜挑着,直让白单秋觉得他是故意拖了会儿时间,专门瞅自己美食当前求而不得的憋闷神情。
“不过是吃一顿饭,你们都杵在这儿干什么?”白景页忽对周围人说,“搞得紧张兮兮,连饭也吃不安生,都出去!”
左右侍从脸色一紧,忙不迭的俯首和周围卫士一同倒退出门。
他说话时明明也是满脸笑意,白单秋又想,这些人怎么就怕成这德行?
“碍事的都走了,”白景页转过头又对他道,“白兄请吧。”
白单秋感动的差点热泪盈眶,不禁为刚才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行为默默愧悔了一下。机不可失,他赶紧举筷,“你我都姓白,白兄长白兄短的多难受,叫我白单秋就行。”转瞬间白单秋已经塞了满嘴东西,咕咕哝哝的说道。
白景页又笑了,还是那副懒洋洋的态度答道,“那我也一样吧。”
昨晚开始白单秋就粒米未进,现下着实是饿,见对方无过多反应,也不再说什么,豪气万丈的吃起东西来。席间他留意,眼见白景页是一点儿不饿,却也顾及了他的想法,并未干坐着,慢条斯理在挑鱼肉里的刺。顿时觉得对面这人真是善解人意,实在是一等一的大好人,好感度又蹭蹭窜了几分。
贵人相助,佳肴当前,美人随侍,小白虽跟了过来,却自始至终都没开口。雅间里的香气袅袅绕绕,四周静谧只余若有若无的古琴声,白单秋想,生活如此富足,良辰如此使人懒惰啊。
“白单秋,你不是本地人吧?”估摸着对方吃了大半饱,白景页开口问道。
“不是,”白单秋也放缓了进食速度,“我家在昊州。”
“眼瞅着快过年了,不尽孝堂前倒跑京城来玩?”白景页用手指有一搭没一搭的扣着桌面,“你也是很自在。”
“哎,家里有意让我参加明年的国考,”白单秋听他话里笑意,也没恼,“趁着还没被投入苦海,先游一游这大好河山,见识见识,这不腊月正好跑帝州来了。”
“你不想参加?现在朝中广纳人才,国考并不难。”
“人外有人,可不一定能选上……再说我人太懒散,怕真选上给皇上添麻烦,”白单秋说的很诚恳,“我爹说要志在四方,我只觉得逍遥一世,不如志在四州,阅览江山,顺心而活最好。”
白景页闻言大笑,边笑边道:“四方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要阅览江山,也得先成就四方,等天下太平了再浪迹江湖吧?”
“为政以德,我看天下挺太平。”白单秋说。
他这话不算奉承。
自先帝驾崩,新帝继位,改元弘成,先头两年是摄政王把持朝政,架空内阁,自成一党。到了第三年,形势骤变,京城连着下了三天雨,愁云惨雾之中,宫里突然传出消息:新帝昭告天下,摄政王图谋不轨,妄图篡位,现已伏诛,着清理余孽,整治朝纲。开国门,废海禁,通商贸,于是气象一新,拨云见日,天边架起长虹,短短几年已有中兴之势。
这位皇帝出生不久即被立为太子,十二岁继位,十五岁亲政,逾今不过十七,而民间风传他为人亲厚,性格和顺,几乎不曾动怒。
夫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有此明君,如何称不上一句天下太平,四海和乐?
白景页神情变也未变:“听了你这话皇上非常高兴。”
“大家都这么说。”白单秋总觉得这话哪里别扭,也未细想。说话间他也吃饱了,搁下筷子望着桌面,这好几个菜还没怎么动呢,心想实在是奢侈浪费。
白景页给他倒了杯茶,另起话题:“你家里是不是有人在朝中任职?”
这话题转的突兀,白单秋下意识接了句没有,“怎么这么问?”
“白姓是本朝大姓,大多为官,”白景页回答得很坦然,“随便问问。”
“我家远在千里之外,高攀不上,”白单秋笑了一声,“你不也姓白?”他隔空去接茶杯,“难道你也是朝中官员?”
白景页把眼睛一眯,茶杯递过去,手却未松。
“我是淮顺王。”
“???!!!”白单秋猛地一抖胳膊,白景页一副我早料到的神情,安安稳稳执着茶杯搁在了他面前。
白单秋总算是缓过了神,还在踌躇自己是该下跪还是磕头还是先下跪再捣蒜一样磕头的时候,白景页已站起来按了按他肩膀,笑道:“行礼不过是排场,没必要。”
“呃……”白单秋又愣了半天,“……谢谢王爷。”
皇上没有子嗣,所封王公大多是亲戚功臣。除却驻扎在封地的,住在京城的王公里倒确有一两位异姓王,只是白单秋素来不谙政事,不知道具体,一时他说的是真是假也搞不清楚。不过单看刚才那群护卫侍从,倒也由不得他不信。
估摸着白景页的年龄与他相仿,身份倒是云泥之别。白单秋暗自摇头,人各有命,要真让他去笼子一样的王府里锦衣玉食,他宁可大年三十在街上当游鬼。
“嗯,不用谢。”
这话脸皮太厚,一时冷了场,白单秋干笑了两声,忽然瞟到立在白景页身后却动也未动的护脉神小姐。
自白景页出现起,她就一直跟随着,可两人之间并未有任何交流,难道是有嫌隙?
天生通灵者,除人妖结合诞下的盅外,便都是有皇家血脉的人,这一点白单秋身在其中,自然是知道的。他心直口快,只估摸着白景页也通灵,一时没想到会把自己的身世也套进去,张口便问:
“王爷和护脉神小姐吵了架?”
“……什么神?”
白单秋听他反问,吃了一惊,抬眼去看看站在白景页身后的护脉神,她面无表情,只是略略摇了摇头。
……合着白景页是不通灵的?
“没有没有……”白单秋底气很弱的说,“一句歇后语,后半截我忘了。”
得知白景页看不见自己,小白终于开了尊口,“哧”的一声:“这谎撒的你自己都笑!”
白单秋闻言还真笑了。白景页原本满脸茫然,见他笑的牙都露出来也跟着动了动嘴角。
“主子,该回了。”门被扣了两下,传出声音。
“知道了,”白景页扬声回了句,又转头对白单秋说,“那就后会有期吧。”
白单秋点了点头,这人倒是雷厉风行的很,他想,不过也很难再有什么交集了。
白景页也没多话,一撩袍角出了房门。白单秋看着他的背影,身后侍从鱼贯而随,很快就转角不见。
他跳起来,和小白来了个大大的拥抱,“你说我能不能把这菜都打包带走?没问题,王爷人那么好肯定不会介意的!”
“没出息!口无遮拦!”小白骂他,“幸亏人家不通灵,以为你昏头了胡说八道,万一他通灵不就暴露了你自己也是皇族后裔的身份?”
白单秋回想起来,灰溜溜的哼了一声。转头看见白景页墨黑的大氅搭在一侧软榻上,哎呀一声扑过去推开了窗,正看见空旷的街道上落满了雪,散落如毛还在纷扬,红红蓝蓝的侍者衣衫晃花了眼,白景页由下人扶着,正欲上轿。
“我说——王爷——你的东西!!”白单秋拍着窗框喊。
视线模糊中他看见白景页偏了偏头,好像面色平静无波,好像又很高深莫测,“改日再取!”他毫不停顿,也不见细想自己落了什么,略提了声音回完就上轿里去了。
大雪纷飞,一行人踽踽而行。
白单秋回身抄起那大氅,笑笑的说:“得了,这下可又有交集了。”
·
陈广已当了半生太监,还是头一次在京城遇着这么大的雪。天寒地冻,轿子走的不快。午后的白光明晃晃的照下来,沿着厢壁流动,紧接着在窗角一晃,原是锦帘被里面的人掀起来了。
“陛下有何吩咐?”他忙问道。
雪粉洋洋洒洒扑进车内,白景页也不在意,“靖国公之后,前中督察院左督御史白书邈大人被先帝流放的事,你记得么?”
陈广愣了愣,忙答道:“老奴记得。”
“嗯,”白景页顿了顿,“靖国公开国元勋,其后更是人才辈出。可惜了,他偏要替盅说话。也不知道他家子嗣后来如何?”
“白书邈一时糊涂,质疑国策,动摇民心,皇上不必为之多思。”陈广说。
“倒也是没什么好思的,”白景页斜觑着他,“因为一纸奏章就被流放,你说你甘不甘心?”
陈广抬了抬眼皮,慢声答:“皇上知道,老奴打入宫起便和旁的人不一样了,老奴不敢违背圣意。”
白景页点了点头: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天地之广,映入眼中皆银装素裹。他望着窗外飞雪划落利如刀片,不无笑意的道,
“陈广,你说白书邈那么心高气傲一人,他被流放,他的子孙后代恨不恨朕呢?”
·
待续
引用了一堆名家名句凑字数///(划掉
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
年关将至,京城上下也融起一片新意。站在街头打眼一望,除却泥墙素瓦,披红挂朱外,再也难寻半分杂色。日头刚起,街面上已是人声鼎沸,小贩掬起腰带,挎篮年货走街串巷,更有售卖早点零嘴儿的穿插其中,好不热闹。
若换了平时,皇城空场外的大街上更是喧嚣,今日却肃穆的渗人。街上百姓俱未赶走,只被隔成两股,两行卫士扶刀而立,使中间空出一条可供车行的走道来。晨雾未散,在空中徐徐罩罩,将乌压压的人群隐去。
忽而雷霆乍惊,隆隆而至,只见得一辆囚车由道上缓缓行来。这车与寻常所见俱是不同,似铁盒般封的严严实实,只在沿角留出些气孔。车头上有扇低矮铁门,挂着足足五道大锁,怕是光开也要费一番功夫。四周护卫排场更是与这车相衬,足一道可动的铜墙铁壁。
“来了来了……”人群中传出窃窃私语,“大过年的,可真是不吉利。”
“你甭乱说,妖人生的后代本就是祸害,难不成还得看着时节秋后问斩?”
议论声中,囚车已行至空场前,再行便是午门了。那囚车内突地一响,继而传出了难以抑制的呜咽。顶头的将军回眼一瞟,几不可见的冷笑了声,驱车而行的众人更是不为所动。车轮缓缓碾上了皇家的砖地。
人群内又是一阵低语,间或夹杂着嘲讽。
车行到门前,咔的一声,顿住了。
将军下得马来,目光浑然不晃,提气喝道:
“带囚犯!”
车内呜咽骤止。
重重铁锁开解。
晨间透白的天光登时照入车中,车里人似乎还未适应这强光,缓了一刻才探出头。是两名女子,一高一矮,似是姐妹,看年纪大不过二十小不过十五。二人俱披头散发,伤痕累累,戴着枷锁镣铐,寸步难行的勉强蠕动着。
好容易挪出一段距离,身后卫兵长枪一推,二人便双双跪倒在地。似是妹妹的腿上伤口又裂,血滴在砖上,她一阵痛呼,又惹的人群议论纷纷,仿佛这惨状倒是件令人十分快意的乐事。
那将军一展手中卷轴,问道:
“昊州人氏常德,可是尔父?”
大一些的女子听了会儿人群嬉笑,这时竟平静了,坦然答道:“是。”
“柜山之妖狸㭤,可是尔母?”
“是。”
将军两手一合,将卷轴掷在地上:
“斩!”
女子骤阖双目。
·
听说早上斩了盅,满城茶余饭后的谈资又多了一桩。饶是未曾亲临现场的人,在茶楼来回转了几圈,也能眉飞色舞的说上一段:“……手起刀下,端的就是干净利落!”
“也不知那人怎的迷了心,竟也愿同妖族交好。”
“实在是大逆不道,罪责当诛。”
无人不面色大好,仿佛杀了一盅便保得他们世代平安一般。是国法森严,是兵盛马强,是天地之精华山河之宝藏尽归人手。
天下一统人为主,而民心凉薄。
——可眼下这民心再是凉薄,恐怕也与白单秋无关。
已进腊月,京城下了薄雪,他虽穿了件光鲜亮丽的湖绿锦袍,却再无旁的衣物祛寒增暖。眼下正是化冻,天寒的很,白单秋抚了抚额,不觉又生出几分是否已经着了风寒的疑心来。
“秋儿秋儿,你看那糖葫芦做得好不好?”
白单秋闻言,也不自觉的往身侧瞟了一眼。京城的糖葫芦处处可见,这家倒是出类拔萃的漂亮。端看选用的山楂,个个圆润,饱满如屋檐上悬着的灯笼,透出喜气;熬糖的锅嗞嗞作响,气泡连绵不绝,筷子一挑抽丝如蚕。手艺人执着木签,将山楂在热糖浆里略略一滚,透亮的糖浆便裹满果皮。薄脆均匀,出锅即冷,令人望之垂涎。
白单秋眼睛都不眨,条件反射的吞了吞口水。伏在他肩上的白狐并未就此住口,反倒是滔滔不绝将四处小吃报了个遍,大有语不弑主死不休的气势。若是旁人能瞧见它,只道它心情极好,大尾巴扫来扫去,登时在白单秋眼里许多行人便如吞云吐雾似的,笼在一阵烟中。
“小白,你能不能少说两句?”窥窥四周,见旁人各忙各的,他才敢压低声音同这位护脉神大爷抗议,“我都饿的前胸贴后背了,你何苦这么刺激我?”
“你怨谁?怨谁?”白狐非但毫无歉意,反倒把嘴一撇,“逃出府的时候不知道多带点盘缠,京城人杰地灵的,哪来那么多妖给你除?好容易接了活计赚了钱,即刻就跑去打麻将;赢了钱也不好说你什么,倒是去置换了件新衣裳。这下可好,年衣你小子是不缺了,可是年夜饭咱俩就只好喝西北风了哎——”
“你小点儿声!”白单秋只恨不能抬手去捏它的嘴,“你明明是个护脉神,吃不着也喝不着,惦记年夜饭干什么?”
“我虽不能吃东西,可好歹也是只狐狸。这天底下有不馋嘴的狐狸吗?江山之大,无论是普通的狐狸,还是如我这般具有神力的狐狸,没有不馋嘴的,不可能有!”
“……”
饶是白单秋活泼口快,也架不住腹空之际听它这一顿翻来覆去的废话。当下便不再接茬,缩手缩脚的向前溜达。只是一想到自家百年之后,就由这厮来接掌生前记忆,跑出去信口雌黄,顿时胸口一闷,只觉得身后凄凉。
人各有气,遇灵成形,是为护脉神。这神明虽与世间的妖灵一般,非人非鬼,却只有极少数的通灵之人才能瞧见,大多数人连其所存都不曾感知。自人诞生之日起,护脉神便如这光阴的见证者一般,虚虚浮浮跟随一生,死后承接主人生前的记忆,再代他看这尘世一程。
小白虽然聒噪,好歹也是从小陪他到大的伙伴,白单秋自然不可能为它几句话就动气。只是被它一叨叨,腹中空空如也的感觉便愈发强烈,仿佛胃已经磨无可磨,五脏六腑发着烧,叫嚣着需要及时进补。
可白单秋交足了驿馆费用后,实在再无大吃一顿的闲钱,他不过是出来透透气,竟也能平白受一顿刺激。
正想着,肩上的白狐又叫唤起来,却终于换了话题:“秋儿,秋儿!你快看,那个护脉神是人形的!”
白单秋闻声望去,凭着天资,一眼便找出并非人类的护脉神来。她背对自己,只窥得小半张脸,睫毛弯长,肤白如雪,朱唇微抿,只是大半背影,却生出一股出尘而高绝的气质。长发分股,绾在脑后,一排半月白玉簪在头顶。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着件雅色襦裙,轻纱罩身,不留神便看不见,看见了却道几欲飞天。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白单秋正值年少,本就对同龄异性多加关注些,见此少女竟一时也呆住了,胸腔之内心跳乍然剧烈,直教一旁的小白连连摇头:“人心不古少不更事,白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白单秋虽年少气浮,贵在并不以色取人,看了一时也就回神了。虽说护脉神都可化为人形,却有诸多不必要,因而少见。如今这模样,恐怕是受主人命——护脉神不宜离主人过远,言下之意,便是这附近还有一位通灵之人。他略向周围望去,尽是些平头百姓,人来人往的将那少女穿身而过,她立在街当中,不闪不避,神态自若。
相伴一世,却终不能为多数人所察觉。不知怎的,他竟凭空生出些悲戚。
正恍惚间,远远有个一瞧就非市井中人的身影信步而来。白单秋把眼一看,先看见的是他一袭白衣下摆,随着步履纷纷扬扬,流纹云动,露出内着中衣,竟也是白的;外面罩件大氅,豪奢贵气,漆黑如墨,一看便知是上好的兽皮。待他走近些,才看清他的眉眼,长得很是好看——他想到的竟不是俊逸英挺,而是好看——眼角十分狡诈的挑了上去,眼底却尽是笑意,连上眼下卧蚕,足足将狡诈化成了温潭水。
街道长长,青石铺路。这一人像是天光落地,两边路人恐是哪家富贾少爷,自觉的给他让道,他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白单秋看那毛料大氅越来越近,忽觉得身上凉意倍增,加上空腹难捱,冷不丁一阵头晕,将将掩着鼻子打了个喷嚏,脚步一跄就往前倒。
恰好这人也走到了近前,眼见白单秋就要倒过来,眉间一拧紧走几步,堪堪出手撑住了他的右肩。
·
彼时大昆立朝三百九十余载,正当弘成六年。京城的茶楼里时常响着南戏伶曲,今儿正演出《琵琶记》。盛世安乐,年关也有捧场客,单听鼓笛声去,拍板顿止,裙裾略翻,台上人转袖而语:
“人老去星星非故,春又来年年依旧。
最喜得今朝新熟酒,满目花开似绣。
愿岁岁年年人在,花下常斟春酒。”
天色一转,转眼又开始飘雪。
街道人行匆匆,小童高喊着“瑞雪兆丰年”忽而跑去。
他被那人撑着肩晃了一忽,乍惊之下还抬不起头。
突听得头上传来轻笑,有个十分清冷,吐字薄淡的声音对他道:
“我看兄台神色恍惚,眼中迷惘,总不能是看我看呆了吧?”
·
待续
不太会写东西了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