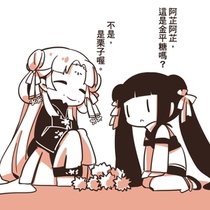"我想去治病。"曲花花说。
"哦,好,那你走吧!"美男巫师冷酷的挥挥手,并不打算拦着,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找到自己重要的东西,比如赶紧吃顿饭。
曲花花试着深吸一口气,然后伸出手按住自己左边的胸口。那里传来富有节奏感又充满力量的跳动声,心脏是如此的健康,可是却缺少了最关键的东西,而曲花花对此也毫无感想。
“…保重。”抬起头朝美男巫师道别的曲花花发现自己的身后空无一人,美男巫师早就不见踪影。
真的是巫师啊……曲花花想,觉得应该佩服一下。
雨后的梅山格外清新,湿润的充满植物气息的空气钻进曲花花的鼻腔,附在他的皮肤上。曲花花这就抬起脚,深一步浅一步地往低谷处走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山脚处隐约传来了人说话的声音,曲花花仔细看了一会儿,又听到了器械碰撞发出的叮咚声。但是距离太远了,他不能听清这些人在说些什么,于是曲花花默念了一遍“我现在很振奋!”后加快了脚步,朝着声音的地方赶去。
映入眼帘的是热闹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品摊贩,曲花花从没见过这种热闹的景象,梅山总是很安静,就是一百只鸟同时唱歌也抵不过这种人来人往的气氛。
太过震撼甚至让曲花花完全没有留意身后早就消失不见的山路。
不过,很快他意识到了更严重的问题,这儿的人,操着一种难懂的语言,实在和自己的语言差别太大,曲花花顿时一个头两个大,完全听不懂,不要提寻找名医了,甚至可能买不到一个馒头!
山下的世界好可怕…曲花花只觉得头大,但并不会影响到他的判断,母亲以前讲过,日本是一个国家,国家又分成很多城市,也许是会有完全听不懂的方言。
这种时候,最好买一份地图,然后冷静下来吃点东西。曲花花冷静得思考着。
“这位小哥,瞧你白白净净的,怎么穿这么破烂的衣服啊,瞧瞧瞧瞧…连个鞋子也没有,你脚疼不疼啊?”路过的大婶无比担心,实在忍不住拉住这个站在街道中间半天没动的青年。
曲花花回头,以一种绝对的迷茫面对热心的大婶,怎么办,她在说什么。母亲说过就算是方言,也一定有迹可循,可眼下这种奇特的语言,硬生生是一点母语的痕迹也没有。
"呀…这怕不是个傻的吧……"大婶一下撒手了,看他的眼神都不对了。
怎么这种眼神…曲花花觉得奇怪,又想起母亲说过,微笑是重要的礼仪,于是曲花花扯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试探地说:"您好?"
也许是太久没有看到过这么秀气的小伙,大婶刚刚松开的手就又抓了回去:"哎呦,是外来人啊,这可真是…来来来…我啊,是茶馆的!"她腾出一只手,做出倒水,喝水的动作道:"茶馆,茶馆,喝水的,吃饭的!"
曲花花若有所思的看着笑的满脸褶的大婶,得出了她可能在要饭的结论。
"这…我身上也没有值钱的东西…"曲花花立刻开始摸腰包,但他哪里有什么钱,只掏出个雕刻挺精致的木头小雀,这是他的拿手绝活,没事会刻着玩:"这个…这个…可以卖钱…!"他也学着大婶,开始比划,指指小雀,指指大婶。
两个人一老一少,在街上互相比划,场面很是滑稽,曲花花一把把小雀塞进大婶的手里,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神情,快速转身走掉。
大婶顿时一懵,也忘了继续比划,看着曲花花的背影,大婶一喜:"外来小哥好兴致…还送人家这种见面礼…"
曲花花逃也似地快速走开,也不忘左右看看人声鼎沸的街道,看起来像是祭典一样,连招牌上的字都连接很困难,那么这里,究竟是不是日本…?可梅山明明就在日本境内……
美男巫师漫不经心的那句"梅山的错吧"究竟是什么意思,梅山不是普通的山吗?
发生这种快速思考的情况,应该会紧张吧,曲花花默念"我很紧张!"
天色渐晚,曲花花从最热闹的时候,逛到了散场的时候,街边渐渐燃起了许多形状好看的灯笼,酒楼里也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聊天声。
再然后,形状好看的灯笼也渐渐消失了,只留下有些无措似的曲花花,和高悬空中的弯月。
入夜了…曲花花终于感到一丝凉意,不由打了个寒战。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他意识到这里很可能并不是日本,而是别的什么地域,这下子可难办了,原本就从未谋世面的自己,一下还来到了如此遥远的地方…
怎么来的?曲花花回想,似乎也就只有,走下了山,走来的?徒步?徒步走到了别的地域?这下曲花花开始思考,他是不是应该脚痛了。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曲花花打了第二个喷嚏之后,他看到了视线可视范围内唯一一个有灯笼亮着的建筑。
门匾上有三个字符,曲花花看不懂,屋顶却突然传来一声惊呼:"霍!好一个拾破烂的!"
曲花花当然是听不明白的,但是既然路上就他一个,可也只能是对自己说的,于是他抬头,看到屋顶上垂下一双腿,不一会儿又冒出一个脑袋。
"你能看到我!"房顶上的人一下就感受到了视线,兴奋的爬了起来:"收破烂的,你能看到我!!"
无论怎么看,上面的人都很兴奋的样子,曲花花迫于外来人暂时宛如残障的压力,还是露出了礼貌性的微笑。
屋顶的人更高兴了,头顶的大草帽都掉了下来,隐约看到凌乱的后脑上扎着一个小小的辫子:"我眼神好,你长的真好看!哈哈哈哈,我的有缘人是个帅哥哈哈哈哈!"
曲花花静静地看着那人自言自语,清澈的声音句尾总是上扬,听起来还不错,只是不知道这人在笑什么,半夜这么大声没问题吗?
门匾上的三个大字被曲花花暗暗记下,但他并没有进去看看的意思,身无分文,还饥肠辘辘,他决定看看哪里的破楼还有空地…
治病的路好艰辛,曲花花觉得这种时候肯定要充满决心,于是他默念"我充满了决心!"开始寻找今晚的栖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