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到如今还在赏花,察觉到死亡的气息
☆在此郑重感谢十文字 政臣先生(
养虺成蛇。
松井家的一楼是以皮薄馅厚得恰到好处而远近闻名的铜锣烧店铺,其休业的时间并不固定,全看前一天的营业额扣除琐碎款项后结余的份还能换回多少米面与豆馅。等到个子不大的布袋瘪瘪躺倒在地上、活像只猫咪懒成一滩,店主人就会从尚带余温的铁板前走开,关上朝街的前门,接着整整供人歇息的桌椅和井井有条的碗柜,最后上到二楼去。
“你在的吧?”“是的。那什么,今天天气很好,我本打算趁这机会晒晒被子、做个扫除什么的,结果——”说话的人拖长了尾音,最终还是选择省去细节直奔主题,由这副口舌吐露而出的这般言语实在是重复了太多遍,以至于浓浓歉意拉扯坠地的字音复又高高弹起,反倒染了些轻描淡写的意味,“非常抱歉,主人。”
人类青年绕过衣物、箱盒,以及所有者都不记得从何而来的杂物所构成的一地狼藉走到坦荡荡大开的窗户边上,确认完这间屋子里唯一一条被褥现在只是一动不动地横陈在于后街更后疯长的灌木枝叶之间,他转过身,但又并没有执着于在这六叠的空间里找到什么人。
“我说过你时刻都得让我看见。”“啊。”“我也说过不要乱动屋里的东西。”“你说过。”年轻人现出身形的同时向侧走了一步以保证自己确实出现在对方的视野里,多此一举的因牵动相应的果,他因此踩上什么东西,白瓷质地的物件干干脆脆地碎成几截,甚至猜不出本来样貌,“……我很抱歉。”“去把掉下去的被子拿回来,这边我来理。”“好。”
鹤见时江逃也似地蹿下楼梯,还差点在最后一阶上绊倒,他推开屋子的后门走出去,阳光劈头盖脸地轧下来刺透身躯,它们不曾给他造成过任何伤口,也不曾给予他过任何温暖。
自从护身符的付丧神离开徒然堂以来,就没少给松井没有名字先生添麻烦。他累计已摔碎俩盘子仨杯子一个豁口的茶壶盖子,绊倒过鼓囊囊的红豆白费过半斤面粉,现在又折腾得好好的房间乱得和进了贼似的一片混乱,事到如今,要说自己的初衷只是想为了主人做点事,也只会显得像个拙劣蹩脚的借口罢了。
“你。”青年将手撑在窗框上居高临下地喊,狭窄院子里傻愣愣站着的年轻人循声仰首,这般视角下,后者金色的眼瞳藏在圆框眼镜后、比往常看上去更加模糊不清,“被子,是够不到吗?”“呃,不,抱歉,我走神了。”“等会我要去趟集市。”“知道了。”
松井消失在窗口,两秒后窗户也关上了,时江没有余裕继续胡思乱想,他拉扯过勉强也能算是好好摊开来晒过的被子抱在怀里,边顺手拣走背侧粘着的几把枯枝败叶,边快步往回赶。
既然有缘同住一个屋檐下,房客和房主总需要在各个方面达成共识才能开展和谐生活的共同建设,松井与鹤见在落笔成文的契约之外又做了许多口头约定,其中就有这么一条:付丧神只要通报去处就能自由行动,而人类要出门的时候,他就得时时刻刻带着护身符。
“我知道这绝不是个好提议,可你带着我肯定比不带好。”时江讲述过往经历的时候虽是好好地看着他正与之对话的对象,却也巧妙地避免直视对方探寻的目光,“上一个把御守落在屋里就出门给人上课去的教师先生被人烧掉了半个书房,另半个也给烟熏得过了头,花费数年收集了几排的手抄古书一本都留不下来。你肯定也不想遇到如此飞来横祸。”
话音落地之前,些许的窘迫便匆匆地追上他,实际上,这场灾难完全可以追因溯果,不必复杂的推理就能得出结论——[一切都是由他招引而来]的缘故。
听来足够荒谬,但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厄运这般虚无缥缈的概念,在名为鹤见时江的同为虚无缥缈的存在在场的前提下,是可以具体量化的,这些既有方向又有大小的箭矢指向他,让他的世界、与他有所联系的他人的世界一并笼罩在自己庞大的阴影下——这一点在与他结缘的人类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雨水落地会向低处流走汇入江河,江河上涨便会吞噬岸堤、甚至形成洪流,而最接近江河的人自然而然就会被江河卷走,就是与之相似的道理。
难道不会觉得把付丧神的意识与本体剥离,又把付丧神的躯体与本体联结,如此行径是造物主过于恶趣味的安排吗?既然赐予他一副无法与他人长久相处的身躯,又为什么要许诺他向往与他人相伴的心灵?而他自己,他作为一个独立意识所拥有的理性,又为什么要纵容强烈似执念的愿望如同蛇咬般侵蚀内心,导致他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犯下错误?
青年并没有看穿时江这会儿格外复杂的心思,或者也可以说他并不在意,松井只追问了一个细节,就爽快地将这算得上冒犯的要求答应了下来。
于是亲爱的倾听者们便可得知,等到多余的麻烦以及顺势开展的真正扫除终于告一段落、两人终于可以出门的时候,时间已经有些晚了,想要在这个点儿的集市买便宜新鲜的食材怕是很困难。松井没有说什么,时江也开不了口,只在对方身后三步左右的位置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们离开后街,经过前街,房屋与房屋之间拦起一片焦黑的土地,其中一些木质结构的建筑残骸已经和数日前撞毁于此处的车辆一起被拉走了,一些仍没有,它们无言地伫立在原处,供人辨识一场席卷了此地的无妄之灾。
“你是不是说过,那天早上你来过这里?”走在前面的人突然问道,把跟在后面的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我领你回来那天。”“是的。”九十九一边回答着,一边在脑内搜刮记忆,“我想应该是的,先前听说河畔有几株樱花有了花苞,所以那天早上就趁没什么人的时候从店里出来,想要去找来着,后来的事你也知道了。”“你喜欢樱花吗?”“不知道。”这次时江给出的答复简单而干脆,“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喜欢没有亲眼见过的东西。”
松井看向他,年轻人笔直地站在午后倾斜的日光之中,脸上不带什么表情地回望过来,他的容貌姿态分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并非人类的异物感却陡然膨胀,给人以一种仿佛是什么完全无法理解的生物披着人偶、或是别的什么徒有其表的东西在与自己对视一般的错觉——也只是转瞬即逝的错觉罢了,再者,论说躯壳内所存的内容,松井拥有的未必就比鹤见多。
“那要去赏樱吗?也快到时节了。”沉默了一会儿,青年开口说道,没成想得到一个反对的答复:“不了吧,人会很多的。”“那正好可以卖铜锣烧。”“不不不,我的意思是人多的地方容易出事,特别是小偷扒手之类,还是别去——”“你难道就不想看看樱花吗?不是说从来没看过吗?花期很短的,错过了可就看不到了。”“……你就不觉得用这样的说法劝说别人十分狡猾吗?”“什么?”
“没什么。”九十九撇撇嘴,该说的都说了,说服不了你算我输还不成吗,“就如你所愿吧,我的主人。”
“那就这样说定了。”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九十九所能记住的第一个四月,松井如约将他带来了上野公园,也正如他自己所预料的那样,热气腾腾又物美价廉的甜食是前来赏花野餐的人们的心仪之选,不一会儿小推车前就人满为患。付丧神这会儿是帮不上什么忙的,当然也可以说,就算他想帮忙也只会让自己的主人忙上加忙,于是青年就打发他四处逛逛,赏赏花,最好能挑一个僻静又没什么人的地方占上一席,也不算白来这一遭。
这也算是物尽其用的一种了,时江十分擅长找那种没什么人的偏僻角落,这是几分天赋与丰富经验的积累互相结合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不知觉之中嚣嚣的人声便被喳喳的鸟声所替代,他顺着不成路的泥土小径寻到了所谓[理想的场所]。
御守是在秋分的时候化的形,他见过漫山遍野的蹡蹡红叶,见过铺天盖地的皑皑霜雪,但确实没有见过如此之多的花,它们颜色浅淡如云絮,瓣片柔软如绒羽,粉粉白白,赏心悦目。美丽的事物会对一个人,或者将范围算得更宽泛些:一个灵魂,起到多大的影响呢?时江站在盘根错节的古老樱树下,步伐挪不动分毫,直到眼球因接触空气太久而刺痛难耐、甚至涌出泪水,他这才慌慌张张地低头抬手擦拭,接着看着自己袖口洇湿的痕迹哑然失笑。他认为有必要总结一下刚才的感受与体验,不过在这之前他听到脚步声,来人好像肩上担负奖章一般身姿挺拔——可能有点太挺拔了,他不得不伸手拨开挡在面前的枝叶才能自由前行。
“失礼了,我还以为这个地方没有别人找得到。”不知为何有些面熟的陌生人也在树前停下,他朝着时江的方向开口道,后者愣了愣、露出奇怪的神情:“……那个,是在向我搭话吗?”“对。”“哎呀,这可不好办了。”“不用介意,我也只是顺路过来看看,席位已经在别的地方设好了,你随意就好。”“啊,恩,十分感谢。”虽说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喜欢樱花吗?”“是的。”时江回答,他马上就将普通人能够看见他时都会发生些什么事的思考抛到脑后,像是正等着谁来问他这个问题一样夸张地眉飞色舞起来,“非常喜欢,非常、非常喜欢!先生!这大概是至今为止我最喜爱的事物了!自然也好,神明也罢,究竟是如何才会想得到创作出这样梦幻的风景呢?而且,而且啊,比起欣赏到它们,我更开心的是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出‘我喜欢樱花’这句话啊,先生!不是从书上、不是从插图,而是亲眼见到它们!为它们天然的美所彻底折服!这多不可思议!”
当然他真正想表达的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难以解释清楚的细微情绪于胸腔中一并炸裂开来,这是一个行走了数月的生命所能承受的对于这存在了数不尽的岁月的世界的感动,这是无法和已经生活了数十年的生命分享的感动,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安静了下来。
“咳咳,抱歉,说了些奇怪的话。”“没关系,我明白你确实很喜欢樱花了。”男人礼貌地点了点头,这让时江更加窘迫,他尴尬地想要转移话题:“那个……虽然很突然,请问你喜欢甜食吗?”“喜欢。”“那么,作为如此良辰美景的酬谢,请让我介绍一家铜锣烧做得很好吃的店给你吧?”年轻人抬手邀请后者同行,“今天店主人也到了这里来……啊,当xin——”
他出声得太迟了,想要警告的对象快上九十九两秒,踩上青苔脚下一滑、一头撞上粗壮的树干之后花瓣兜头淋下,将整个人染得粉粉白白,很是春日风情。
……希望他之后吃上铜锣烧时不会被烫到嘴吧。时江真心实意地如此祈祷。



1888年某个隐秘、潮湿又狭窄的暗室,她出生。那个夏天有无数只蝉死去,而她诞生在女人的尖叫后,那久久的尖叫如同蝉鸣,划破了整个夏天。
那之后过了很久,年复一年的夏天来来去去,唯独不变的是本港炎热潮湿的天气。也许还有,味道不同却颜色如一的灰白色烟雾。
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捞出外套里金属质的铂金色烟盒,舶来品,三十块钱。手指转动烟盒,随意挑开,抖出定制的女士烟,她再熟练不过的动作,轻佻又冷清,这个动作发生在她身上本就是矛盾的。接着她微微张开唇瓣,塞进那根烟,动作大得有点粗鲁,显示出她的怒气,继而手指一划,燃起一根火柴点烟。在风中摇摆不定的火光,与洁白的烟身接触后马上被熄灭,它存在不过三秒,马上化作烟雾散在空气里。
她深吸一口气,烟通过气管进入她的肺部,一时间她胸腔疼痛,喉咙似乎断开,仿佛她只剩大脑,余下部位被一切两段。这样也很好,她勾起唇角,有些促狭地想,这样她就没必要因为日益发育的身体被当作待价而沽的商品,受到杨太异样的眼光。
嘉玲想起来,那时她十二岁。逐渐成熟的年纪,胸部有一点点隆起,脸侧细小的绒毛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轮廓模糊,她才刚过完十二岁生日。
她讨厌夏日,毋庸置疑。苍蝇狂欢的季节,汗淋淋的季节,她为什么要喜欢?她能想象一切不美好的东西都在夏日,她痛恨的夏日,她不得不出生,不得不在夏日生不如死。
嘉玲穿着一身很普通的浴衣,浅绿色竹纹印在衣摆,腰后扎起一个素色的结,她挤在人群中生不如死。现在是她讨厌的季节,而让她更痛恨的是夏天的传统节日。
祭典,多么好听的名头,人们总是能借不同的名义庆祝。她费力地从成群结队的人们中穿过,将将要达到对岸的空地,突然间万物俱静,她厚重的呼吸明显得要掀翻她的脑袋。
晴朗得容不下一丝云的夜空闪过一颗星,只划过一瞬,快得只瞧见它拉长的尾巴。有人看到了,也有人没有,嘉玲只觉得眼睛一痛,她眯起眼睛,试图缓解疼痛。紧接着又一颗星下落,天的那一边仿佛崩塌般,无数颗星星坠落,静静的河面倒映着这幅景象,星星就好像掉进这条河里,熄灭了。
那应该是这个夜晚最沉默的时候。所有人都止住了呼吸,嘉玲多希望能停在那一刻,但随后当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议论声惊呼声大过一切,她觉得头更疼,似乎最初那颗流星坠进她眼中后将她的脑袋从中间劈开。
噪杂的交谈声,在这片夜色的衬托下带着许多希望,人心沸腾。一年一度的节日,死者的灵魂回归的日子,那或许真的是也说不定。既然这样为何不一起带我去,嘉玲心下一片烦躁,咬了咬下唇,手指捏紧衣袖,她面上还是那副波澜不惊的冷脸,看不出她急需一根烟压下她不定的情绪。
空气凝滞沉闷,人群的呼吸重重的阻碍了风的前行,这就是夏天,闷得人透不过气。嘉玲转身,试图向人群稀疏处前行,她的正对面,站着一名青年人。
显而易见,那位青年大部分的脸庞掩在拉低的帽子下,而他下巴的轮廓苍白又清晰,瘦削得像是锋利的剑刃,唇抿着,用力得狠了,连带着唇线都看不明晰。他穿着特别,西洋人打扮,但他的脑后露出得一点翘起的头发却是那么黑,浓重的阴影般。嘉玲不禁停下脚步,侧过身仔细观察他。他腰杆笔直,不属于祭典这样热闹又平凡的地方,他——应该生而不凡。
这样奇特的人突然抬起头,偏向嘉玲这侧,正巧直直对上她的眼眸。这才终于看起那人的全貌,却是比想象中更要清秀的五官,单薄的面孔,一切都藏在这里,嘉玲后知后觉的意识到,原来那是位女性。
黑崎注意到身后那道视线有些久了,她才有些不快地转身去看视线的来源,被人瞧见纯属意外,她一点也不想理会。她正忙,夏天到了,唉,夏天。她第一次经历这块土地的夏天,四面被海包围的夏。
正巧对上对方的眼睛……不是那样的。眼睛藏着一个人所有的想法,是通向未知世界的秘密入口,而且说话时看着对方的眼睛才算礼貌。黑崎看向对方的眼睛,想也不用想就轻易地找到眼睛的位置。
如果说一颗流星的坠落代表一个人的死亡,那么眼睛里的流星则代表着人对死亡的渴求。那双眼睛,藏着流星。黑崎眼前有片刻模糊,她对总是能看到这样的眼睛感到厌烦,也对那本身无可抑制的痛恨。
不止一次,眼中飘忽不定的星星划下,一颗一颗像在给人生划下休止符,无聊透顶。这样的场景总是带她回到那个年份,第一次呼吸的时候,记忆是那样清晰又模糊。
这一刻,人群的另一边,少女的眼睛一眨不眨,其中一颗将要落下的明星挂在她夜幕般的眼里,黑色的浪潮般的眼睛,要将那颗星星带下。这一边,黑崎握紧拳头,止住愤怒带来的颤栗,以及无边的厌烦。这一刻谁都没有动,人群化作一道道拉长的速度线,压在两人的中间,世界好像只剩下加速后尖锐的风声,她们对望着,一句话也没说。
*先打卡,能补就补上吧
TB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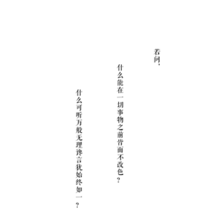
我并不在意事物的形体,我眼中的他们不过是物体所反射的光。
我走进一楼的咖啡店时,摆在大厅里的西洋大钟刚敲响第四下。晚春的阳光仍旧是迟到早退,懒散的光辉将空气中的微尘,着洋服的年轻女性,以及她手中花纹繁复的骨瓷杯都勾勒的一清二楚。明明是毫不相同的场景,我眼前的光景却和墙上挂着的那幅油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照见光的地方明亮,照不见光的地方黑暗,这全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此刻是下午茶的时间,人头攒动的咖啡馆里,只有我的脚下没有影子,光线穿透我的身体,一如我看穿别人的心。而我也得以旁若无人地离开了咖啡馆,或者说是咖啡馆若无其事地吐出了我,这并没有区别。
好在我并不为此困扰,声音与图像本是迟来的嘉宾,观察他人的表情和倾听别人的话语一样多余。我既不靠别人的宣讲了解世界,也不靠人们的行为认识他们,尽管他们想做的不过是在别人心中留下一个他们想要的倒影,而上述两种方法是他们仅有的手段。但实际上,这在我心目中称得上是滑稽可笑的。
然而可惜的是,我并不知道如何向你们分享这份笑料,它并不比了解洋人们的笑点更容易。因为要知道,我是可以知晓别人的想法的,这是我与生俱来的能力,就像听觉,视觉,嗅觉等等很多感官那样,它也是我的感官之一。看到人们耍出这些小小的花招,就像看到蚂蚁无法不爬过圆圈的边缘就离开画在地上的圆圈,就像人们无法不打破鸡蛋就取出蛋黄一样,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就可以不打破鸡蛋就取出蛋黄,但是我可以不撬开人们的嘴就取出他们的思想。
在我还只是桌上的一个小小的烛台时,我的某一位思绪复杂些的主人——请容我这么叙述,因为那会我并没有化形,没有办法为每一片飘忽的思绪对应上一个实实在在身体——那位主人决心要逗一逗思绪简单的另一位,恐怕是他年幼的儿子吧,便在他儿子恶作剧时假装并不为所动,现在想来,恐怕还会摆出一副严肃的神情吧?不过他当时恐怕并没有笑,因为在感受到他想要放声大笑的同时,年幼的小主人的失落之情却像暴风雨前的乌云一样肉眼可见,可见当时他父亲忍住了将要绽开笑容。
虽然这段经过是如今我推想出来的,确切性并不可考,但是我从那时便意识到了有很多事往往并非是它表现的那样的,就像一个人不笑并不意味着他不开心。而我之所以觉得它们有趣,不过是因为我与你们的的视角不同罢了。
这份能力仅是单向的,窃密者不会让失主知晓自己的存在。否则像我这样闲逛在街上时,恐怕有无数人乃至于非人之物想要冲上来杀我灭口。而我觉得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不知在你们想来,我的能力究竟是听到人们在脑海里自言自语的默念,还是让他们想到的东西浮现在我的眼前呢?这大概也是旁人想象的极限了,这就像让聋子鉴赏婉转的女高音,用黑白照片向人们描述色彩一样不靠谱。
或许照片还是个可取的想法?毕竟图像有着明暗度之分,而情感也有平静和强烈之分。就拿街角那个小吃店来说吧,那个奋力吆喝的店员声音是洪亮的,行动是富有朝气的,然而在我的黑白照片上,他却算得上是明度最低的,就连他自己也早已厌烦这份工作,换行大概是他的唯一选择;相比之下,另一边的店员看上去笨手笨脚,连收拾餐具都要担心他是否会摔碎了碗碟,但他确实是一心一意想要学些手艺,恰如照片上亮度分明的人脸。
然而更多人只是趋于暧昧不明的灰色:
买菜回家的主妇行色匆匆:“今天做什么菜色比较好呢?能让家里人都爱吃。”仿佛他们的全部人生都维系在这一件事上。
回家路上的女学生们叽叽喳喳得聊着小说——“我很喜欢这句话‘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但爱就在里面。那意思是说,爱在外面寻找破门而入的机会。*’听起来很浪漫。”
抛出一个东西的优点是对朋友推荐东西的惯用伎俩,小女生的常见行为,我对这种毫无营养的话题早已深恶痛绝。
“这话要是放在三年前我会很喜欢,但是现在看来,不过是一堆空话。”
后者的回答也是我司空见惯的,她讨厌说可以。她是那种人,觉得“可以”是对罪恶和失败的许可,“不可以”才是权力。*
看吧,即便是相同的亮度,也有如此多纷繁不同的想法,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有时就是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这就是为什么黑白照片并不能完完全全地类比我的观感,同样的亮度下也有不同的色彩,不是么?
但即便是同在黑白的底片上,也有着曝光过度的部分,他们或许常常默不作声,但他们的思绪确实熠熠生光。
就如迎面走来的那一位。
靛蓝色的眼眸和高挺的鼻梁都昭示着她出身异国;即便是对西洋所知无多的我也能从她打扮中感受到一丝所谓“贵族的气息”,如果不是由于付丧神的特性,她一定能吸引一整条街的目光。长款的风衣后摆跟不上她追随自由的速度,微微地飘了起来,露出了里侧抽象的星光,那是和自由与存在一样模糊的东西。
“我就在这里。”
这是就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骄傲甚至有些自负。尽管在别人眼中她只是匆匆走向她的下一个目的地,毕竟她的结缘之人是个承担责任的清净屋,但或许她自己都不知道她的道路通往何处。
她是燃烧的星星,追寻着不知是否存在的原因。
然而星星终究是要燃烧殆尽的,在这一点上,它们和立在烛台上的蜡烛没有区别,我也曾想知晓自己存在的原因,不过如今,比起追寻自己缘何而被点亮,我更在意我想要照亮谁。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的名字叫黑崎。
尽管我不在意别人的音容样貌,那并不意味着我宽心到挑战世俗的礼仪,春分以来打这段时间我终于习惯了在见到别人时问好,在说话时直视对方(或者是他们脑后的墙)。因此我还是在走近时对她打了打招呼,她似乎那时才发现我,突然被人撞见的惊讶之后,她还是向我点头示意。
我回到咖啡馆时五点的钟声刚刚敲响第一下,呆在一楼的九十九示意店长在找我。
“你或许完美错过了你的有缘人,”小小的人偶依旧毫无表情,她是极少数习惯我单方面对话而不觉得有何不妥的存在之一,但她这次却一反常态的开了口“刚才有位先生想要买下你的本体。”
的确是一件重要的事,结缘对九十九来说和人类的婚丧嫁娶一样重要,而我也不打算当一个任人宰割的“弱女子”。
“是什么样的人?”
“你离开时在楼梯上撞到的。”
是么?我当时撞到人了?我仔细想了想在发现先前的不对劲:普通人是不会看见我的,更不会朝我道歉。或许我该改一改对外界毫不在意的态度了。
“我和他约好明天这会再过来,不介意的话留下和他谈谈吧。”
“……好的,有劳费心了。”
或许见到了的时候,我会知晓我所想要的事物了。
*珍妮特•温特森《守望灯塔》(没错老是这本书,谁叫我最近刚读完它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这个大家估计都知道
------------------------------------------
上一篇:http://elfartworld.com/works/137113/
一个结缘前春分后的故事,原本想接在上一篇后,结果发现有些怪怪的,大家就勉强无视这个bug吧
尝试了第一人称
希望大家看的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