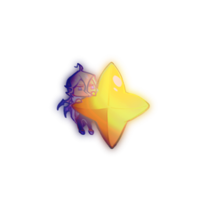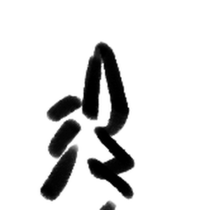

千千阕歌
《魔弹论破》第三章日常相关
cp:法华津伊御x悠木南
WARNING:
全文8086字,不是在设定就是在吵架……实在没力气排版了,刚刚赶完,纯文字将就一下
全篇cp向,有耶耶和mmr,出场有点少如果tag不妥请告诉我
引用的歌词和标题来自陈慧娴《千千阕歌》,刚好这一章的标题是“你我共奏的旋律”,觉得很贴切就顺手用了(?)和文章内容毫无关系,是的我还听很多粤语歌(……)
☆
来日纵使千千阕歌,飘于远方我路上;
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
☆
悠木南手中的塔罗牌掉了下来。
她没有动,倒是对面的法华津很自然地伸出手,将那两张从他眼前坠落的纸牌接到了手心里。悠木的塔罗牌是褐色的,背面的中心有一个橙色的菱形,让它们看起来与随处可见的那些套牌并不相同。他不知道这些牌是哪儿来的,眼下这似乎也不是一个该关心的问题。他把塔罗牌用两个手指夹着,翻过牌面,上面用鲜艳的配色画着漫画插图一般的人物形象。
“这是国王吗?”伊御问,“这个是……小丑?”
南没说话。此时此刻,短发的少女正瞪大眼睛,用一种介于不可置信与欲言又止之间的表情注视着伊御的动作,仿佛要从他手上看出颗星星来。伊御没得到反应,笑了一声,却是与他平时的狂妄自信大不相同,带着些自嘲的苦笑。
“是皇帝和愚者,对吧,”他眨眨眼——
“我想起来了。”
南还是没有说话。少女木木地点了点头,算是确认了对方的推测。虽然是推测,但在手中拿着写有文字的纸牌时实在称不上精明,尤其是当他第一次尝试还失败了的时候。伊御一向是个自尊心很高的人,但这会儿他忽然觉得自尊心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他迫切地需要悠木南给他一个反应,然而对方从他的第一句话开始就一言不发。
这样的沉默让他焦灼。
伊御并不是不擅长应付沉默:他的双胞胎妹妹,法华津纱夜,也是个并不多话的少女,但他总能将对方逗笑——至少以前还是如此。小时候他们的交流要多一些,后来两人渐行渐远,也就变成了现在这样有些微妙的关系。
在一个多星期之后的现在,伊御不得不承认,自己退缩了。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他不敢也不能像在自己的国度里那样肆无忌惮地宣誓主权。在这座“学园“”里,他没有能力亲自保护纱夜,也没有能力确定纱夜是被保护着的。他没有能力阻止死亡的发生,也没有能力阻止死亡发生在纱夜的身上。他没有能力让这出闹剧结束,也没有能力让两人毫发无损地离开这里。兄妹两人之间的天平,在很久很久之后的现在,终于又回到了原初那种完全的平等。
如果非要说的话,或许纱夜比自己还有用些,伊御自嘲地想着,她是个医生。也许妹妹已经知道了很多长兄不知道的事情,但他并没有能够确认这一点的手段。
第二次的死亡,伊御是在现场的人之一。当时在他身边的人,之后又被抹去了两个。他与这些人并不熟悉,因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如果说整件事给他印象最深的地方,大概是身体上的印象吧——他的左腿肚被子弹打穿了。尽管接受过永生的治疗,但那人的魔法最多也只有表面愈合的程度:作为佐证,他治疗过的葵就死在了裁判进行的过程中。
腿伤不可能在三天之内愈合,所以他现在走起路来还是有些一脚深一脚浅的。若是放在平时,法华津家的大少爷绝对是“不遵医嘱”四个字的具现化,这种程度的伤不搞到开裂三四次都不好意思说出去。
然而,现在的情况怎么看也称不上“平时”。
如果不能用自己的能力保护纱夜,至少也要恢复到能够自保的程度。怀揣着这样的想法,他这几天的行动几乎乖得像是变了个人——作息都按照规定的时间来,空闲时就坐在剧院的观众席上看舞台,或者在准备室里弹弹钢琴。能坐着绝不站着,能静止绝不移动。好在他以前该练习过的乐器都学过,弹出来的琴声也不至于不堪入耳。
说起来,那之后伊御弹腻了能背的几首曲子,闲得无聊,就一个人把准备室翻了个底朝天。本来想找找有没有什么隐藏的宝贝,结果除了一大堆备用的乐器和配件之外,只找出两本黑白封面的诡异曲谱。他照着弹了几个音,不和谐感一路从手指尖冲到脑门,像是用所有最不搭配的音符放在一起写出来的曲子。要说好听,绝对是根本听不下去的级别,然而弹多了却有某种诡异的洗脑感。伊御泡在准备室里弹了两天黑白琴谱,惹得路过的人频频开门制止,最后终于被自家妹妹忍无可忍地请了出去。
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地方去,伊御是不会选择秘传之间的。那个图书馆的排布完全是个迷宫,又强制静音,实在是全世界最没有吸引力的地方。况且,他已经完成了属于自己的魔法,用“学生”的角度来说就是已经考完了试没挂科,那还去学习什么呢?
然而,神使鬼差地,他就是去了,因为他忽然有点想去。
再然后,事情就一路急转直下,毫无预兆地发展成了现在的样子。伊御将体重放在完好的右腿上,手中还在把玩那两张纸牌,挂着若有若无的笑容等待南的回应。
他们两人此时都在秘传之间外的走廊上,没有魔法的静音指令,可以随心所欲地交谈。明明是在阅览室相遇的两人,却双双罚站一般杵在门口,这其中的原因说起来实在不算光彩。尤其是伊御——他几乎可以算是被赶出来的——然而这人似乎一点自责的意思都没有。
“不打算说些什么吗?”伊御问,他的音量比平时要小,语调也很自然,这就让这句问话听起来(这说法真有趣)完全像个正常人了。灰发的少年将塔罗牌举到少女眼前,作势就要往口袋里揣。“你刚才你怎么说的来着?不解释一下的话,我就要把这牌当做进献的贡品收下了哦?”
——好吧,后半句就又不太正常了。
南眨了眨眼睛,抬手摸摸下巴,又郑重地清了清嗓子,嘴唇张开又合上,似乎却还是不知道要怎么开始。她在一分钟之前获得的信息量有点大,而且让她不得不反思起了自己对面前少年的态度。南不打算承认,也并不认为自己做错过什么,但伊御现在就像是个突然洗白(并且仿佛要成为真·男主)的反派——
她一下还真拿不准自己应该用什么语气和这个人说话。
要说整件事情的缘由,还要从大约十几分钟之前说起。离开准备室之后,伊御去吃了个饭,随后进入了秘传之间。他并没有查询什么魔法的打算,因此也没有登记姓名。
顺着迷宫走向阅览室的时候,他在路上遇到了埋在书架里(不,这只是并不幽默的夸张)的褐发少年。伊御记得这个人,他们说过话,而且对方在之前的裁判上也做了很有趣的演出,和他一开始对这个人的印象不一样——因为不一样,所以忽然产生了兴趣。伊御站在书架前看了一会儿看书的人,对方十分警觉地注意到了他的存在,然后两人不知为何就开始用手语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沟通。
其实伊御根本不会手语,也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但即兴表演一向是他的特长。最后八木沢大概是终于发现了这个人只是在胡搅蛮缠,于是用宇宙通用的手语——低下头,翻开书页——结束了这段意味不明的交流。
灰发少年撇撇嘴,插着口袋继续往深处走。
他推开阅览室的门的时候悠木南已经在里面了——茶发的少女正在看一本不像是和魔法有关的书,脊背挺得很直,坐姿规规矩矩的。她看起来很十分投入的样子,随着书页的翻动而紧缩眉头,随后又很快舒展表情。左边鬓角的一缕发丝顺着她的脸颊垂下来,在尾端弯起一个小小的弧度。
伊御觉得那发丝看起来很软的样子,走路的话大概会一弹一弹,在阳光下应该也是很通透的颜色。他自己的头发天生半翘不翘,不好打理,索性就留成了这种不伦不类的发型。伊御想起自己以前曾经为了给纱夜一个惊吓而染过黑发,结果也因为忽然闯入两人之间的,关于不同道路的话题而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
如果再染一次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呢?伊御抱着胳膊站在门口思考,也许能学到相关魔法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也说不定。
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他想,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事情本身有什么错误。伊御曾经被私立学校联名挂上入学的黑名单,也曾经骑车撞断了自己的腿,然而后来他上了普通的公校,也骑车在同样的路上带着被撞的女生兜过风。
没有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只有不正确的尝试而已,这是他的信条。如果有想做的事情,那就去做——
伊御走进阅览室,在南身边拉开椅子,大刺刺地坐了下来。
专心看书的少女被他突然的出现吓了一跳,整个人都要从椅子上弹起来。她注意到伊御的视线落在了纸上,于是啪的一声迅速合上面前的书本,努力做出一个质问的表情。
“你来干什么?”她用口型问道。
“来看你咯。”伊御随口回答,“看你看书,你在看什么?”
南对他讨巧的回答并不买账,甚至在提到书的时候表情变得更加凶狠了——她瞪着伊御,两人的身高差距因为坐着的关系并不明显,因此视线就交织在一个近似平视的角度上。伊御耸耸肩,意思自己说的是实话——虽然明显不是。
南白了他一眼,转回去。伊御的眼神在封面上打转,于是茶发的少女坐在那里捻捻衣角掸掸桌子,理理头发玩玩扣子,就是不肯重新翻开书。
“怎么,不看了吗?”伊御凑上去问。
然而因为静音的缘故,悠木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在说什么。于是伊御将整个身体放到南面前,占用她和书之间的空间,然后手指着桌上的书,一字一顿地比口型:“还,看,吗?”
“你烦死了!”
悠木哗一下转身,脸上有可疑的心虚表情。“我看什么你管得着吗!”她似乎很激动,“说到底,你为什么要坐这里啊,周围明明有那么多空位置!”
“你说太快了,我听不懂。”伊御说。
其实他看懂了,但他就是想说这么一句。果然,南看起来更加生气了,她鼓着腮帮子,像是在犹豫要不要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
然而生气这种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南酝酿了一下,找不到一开始爆发的那种情绪,也觉得重复说过的话有点傻——她现在捕捉到了伊御语句里的调笑意味。少女坐在凳子上,气鼓鼓的,伊御看着,觉得有些好笑。
——于是他就笑了。灰发的少年像是被点了什么开关一样趴在桌上大幅度地笑起来,肩膀一抖一抖的,差点要笑到椅子下面去。如果不是强制静音,这应该是极具穿透力的放声大笑,光是看动作就能感受到喷涌而出的磅礴情绪。伊御笑得开心,南死死盯着他,脸上的表情从黑转红再转白,最后终于忍不住了,抓起桌上的书就朝伊御的肩膀拍了下去。
“有什么好笑的啊!”她边打边说,“你是不是就会嘲笑我啊,很有成就感吗?!”
伊御被有点厚度的硬皮书打了一下,也没看见她说什么,有点懵,“哎我……”
“这书是放在图书馆里的,我当然可以看了!谁规定在这里只能学魔法的,再说魔法这种东西,很自然地挂在嘴边不觉得很奇怪吗?!”悠木说着又打了一下,“之前也是的,什么杀人之类的随随便便就说出来,你不觉得自己很冷血吗?!”
“哎哟我靠,你打人打上瘾了是吧?!”伊御翻身挥开那本书,表情也不好看。“老子跟你说是看得起你,死个人就在那里惨兮兮的,难道是指望别人安慰你吗?!他们不杀了你就不错了!”他从南手中抢下那本书,一把扔到桌子的尽头,书籍摊开摔到墙角,摔折了几页纸。
“我告诉你,”伊御指着自己说,“不杀人,谁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杀掉?我跟你说,是想救你——”他一拍桌子站起来,“老子没好到好心帮人还要被当驴肝肺的程度,操,你给我好好看清楚了,是谁站在你这一边的,对你笑的人明天指不定就对你的尸体笑呢!”
南一拍桌子,也站了起来。“我算是看清楚了,”她一字一句地说,“你就是个可以把所有人都当做道具利用的人——”少女的披风随着她的动作划出一道弧线,“因为你心里从来不信任他们,你随时都可以杀掉他们,所以你才认为大家都是这样的人!该看清楚的应该是你自己才对!”
伊御气极了,反而露出一个笑容。
“悠木南,你是不是说过一句话啊。”他说的很慢,每个字的口型都看得很清楚,“你说,你就是杀掉我,也不会让我去杀人——”
南愣了一下,随后不甘示弱地反驳,“是啊,怎么了?”
“——那你说,”伊御笑,“你和我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
“如果我要去杀别人,你就会杀掉我。那么杀掉我的你算什么呢?正义的使者?阻止了暴行的发生了?不是吧。”
伊御撑着桌子俯身凑上去,让两人的鼻尖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距离。
“你也是杀人犯。还是说,你觉得我的命不如你口中的‘大家’的命来的有价值,所以杀我就可以被原谅,嗯?”
“不是这样的!”南后退了一步,带到椅子,险些要被绊倒,伊御眼疾手快地捞住了她的腰,于是两人现在的姿势就更加暧昧了——除去这剑拔弩张的氛围之外。“所以你就是这么看我的吗?”她猛地从禁锢中挣脱出来,“我那么说,是因为我不想看到你杀人!”
“混账东西,我还不想看到你死呢!”
“你骂谁呢!”南忽然将手伸进了裙子口袋里,像是在翻找什么东西。“我才没那么容易死!”
伊御刚想反驳,却看到她掏出了一把纸牌,将其中的两张摊到桌面上。于是他的句子就卡在了喉咙里,不上不下,有点咯的难受。
“法华津伊御,我告诉你,”南指着其中一张画着国王的牌面,扭着头,咬牙切齿地说,“你以为你是这个,”说着,她又去指旁边那张画着戴尖帽子人的牌面,用力之大让纸牌都在指尖粘着跳了起来,“其实,你是这个,懂吗?”
说到这里,她忽然意识到什么似的,将第二章牌反过去,变成倒立的姿势。“这样,懂不懂!”
伊御很坦诚。“不懂。”
南抓起第二张纸牌,举到伊御鼻子前面,几乎要戳到他眼睛里去。“你读!”
“我不会读!”伊御急了,“我不知道你想跟我玩什么比喻,这种破玩意我半点也看不懂!”
“读上面的字啊!”南戳着牌面顶端反写的片假,颇有种不做不休的气势。“就读这个,读出来!”
“我不会读!”伊御几乎要打她了,右手都抬了起来,却又攥成拳头收了回去。“随便你骂我好吧,”他说,“别玩这个了,我们出去说,行吗?”
南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把牌面反过来,回到正位,又拿的离伊御的眼睛远了一些。“你给我读,”她说,“这张牌就是你自己,我不会让你继续自欺欺人下去的。”
伊御盯着牌看了两秒钟,叹了口气。“我不会读。”
南原本平复下来的情绪又有些被挑起来了。“你这样有意思吗,”她问,“读一个单词很难吗,还是你自尊心高到这个程度,连别人递到你面前的现实都可以视而不见?”
“你给我递了个什么现实啊!”伊御终于炸了,“混蛋,老子不会读!要是会读我早就读了,你以为我跟你玩游戏呢?!”他凌空夺下那张纸牌,踹开周围的椅子,又一把将桌子推了出去。
一时间,整个阅览室里一片狼藉。
灰发的少年深吸了一口气,撑在桌上的骨节用力到发白。
“我不识字,”他说,“行了吧!”
这句话落地之后,两人忽然沉默了。
虽然秘传之间本来就是强制静音的,但此时的寂静又与刚才疯狂的无声争执不同,是真正的,没有任何声音的,虚空一般的安静。在这份安静之中,胸膛里心脏的跳动声就显得格外明显,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那种咚咚的声响一下下冲击着骨膜。只有听到这个声音,伊御才忽然确认了自己还活着——
方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台本在进门时就被扔到了天外,他一不小心把最不该说的话说给了可能是最不需要知道的人,所以他们现在正在脱稿表演尴尬的后续。
为了掩饰这份不自然,南摸了摸鼻子,移开视线,却忽然愣了一下。伊御随着她的视线转头看过去,急促的心跳声还在继续,他喘着气,在阅览室门口看到了一个抱着书的,红色短发的少年。永生まもる看了看他们,又看了看四散倒地的桌椅,默默地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你们做的?
南点头也不是,摇头也不是,情绪复杂地看了伊御一眼,后者反倒是放松了下来。
“出去说吧。”他用口型示意一旁的少女,随后很自然地越过翻倒在地的椅子走向了门口。永生站在原地,皱着眉,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伊御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句“就交给你了兄弟”,也不管对方能不能看懂他的口型,就这么自顾自地走了出去。南跺了跺脚,回身打算扶起椅子,却被走上前的永生阻止了。
你出去吧,红发的少年示意她,你们似乎还有事情没解决的样子。
南看了他一眼,确认对方的意思之后,道了谢,抓起桌上剩下的塔罗牌揣在兜里,便匆匆跟了出去。
然后,两人就站在秘传之间的门口,发生了一开始的对话。
“我有阅读障碍,”伊御淡淡道,“不是在故意气你,是真的力所不能及。”
南瞪大了眼睛,盯着他的表情,一脸的不相信。伊御看懂了,摇摇头,把手里捏着的已经发皱的纸牌还了回去。“这样吧,”他说,“你把刚才的想给我看的牌拿出来。”
少女犹豫了一下,按照对方说的做了。她从口袋里找出「皇帝」,又接过伊御递来的「愚者」,举到对方眼前水平的位置。“喏。”她眨了眨眼睛。伊御也跟着眨了眨眼睛,然后扯出一个学表情得逞的小孩子一样的笑容,让周身的氛围都变得轻松了起来。“第一个音节是ウ……还是ス?”他问,然后从对方的神情分析出了答案。“唔,都不是吗?”
悠木南手中的塔罗牌掉了下来。
☆
何年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
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
☆
“你确定要听这个?”悠木南问。
“我确定啊。”法华津伊御回答,“我就喜欢听这个。”
“行吧,那我读了。”南翻开书,感觉自己现在的姿势实在是有些影响风评。算了,她想,虽然自己没有需要道歉的地方,但看在这家伙还蛮可怜的份上,委屈一下就委屈一下吧。这样想着,她摊开书,翻到第一页的时候就愣了一下。“……我这是要从哪里开始读啊?”
“第十一章吧,我最喜欢这段。”
这样说着,伊御正躺在南的大腿上,翘着二郎腿,看起来十分享受的样子。反观蓝色长裙的少女则不得不靠着墙角盘腿而坐,姿势实在称不上舒服。一开始她以“直接坐在地上太脏了”为理由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但伊御二话不说就脱下风衣披在地上,笑嘻嘻地让她坐下,这样的殷勤实在没办法拒绝。这都是因为他有点可怜,南在心里确认,我这是在帮助有学习障碍的同学,仅此而已。
伊御伸手弹了弹头顶的封皮。“读嘛。”
“读读读,马上就读!”
悠木在他看不到的位置翻了个白眼,找到第十一章的开始,清了清嗓子,“你哭啦?对,卡索尼娅。说说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就算你爱德鲁西娅,同时你也爱过我……”
“Stop!”伊御嚷嚷起来,“能不能有感情一点?这里,这里是卡利古拉理念转变,冲突的正式开始,而且卡索尼娅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角色,她作为卡利古拉的身边贯穿始终的一位女性——”
悠木深吸了一口气,阻止了自己松手将书砸在对方脸上的冲动。“那你说,”她努力平缓语气,“我应该怎么读?”
“这你就是问对人了,我敢说没人比我的悲剧更有感情——”伊御顺着竿子就爬了上去,“你好好听着,‘就算你爱德鲁西娅,同时你也爱过我,爱过许多别的女子啊。’懂吗?”
“懂!”悠木学着他的腔调,又加了点阴阳怪气,掐着嗓子读道,“‘就算你爱德鲁西娅,同时你也爱过我,爱过许多别的女子啊。’”
“这就对了嘛。”伊御晃着二郎腿,别提有多自在了,“继续继续!”
“她这一死……”
读了大半章,伊御除了开始点了点头之后,后面就闭上眼睛,连回应都不给了。南阴阳怪气地读得难受,嗓子也渴,瞟了一眼膝盖上的人呼吸均匀,仿佛睡着了一般,忍不住嘴上都偷工减料了起来。“……假如我不能改变事物的秩序……手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不行……那么我是睡觉还是醒着,也就毫无差异了……”
“可是,这是要和神平起平坐。真没见过比这还疯狂的念头!”
一个激昂的声音忽然打断了她有气无力的朗读。“你也一样,认为我疯了。其实,神又算什么,我为什么要和神平起平坐呢?”
南拿开书,看到膝盖上的伊御睁开了眼睛。他金色眸子里的亮绿与灯光混成了一片流光溢彩,在那张称得上英俊的脸庞上熠熠生辉。“今天,我竭尽全力追求的,是超越神的东西。我掌管起一个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不可能者为王。”
少女被少年身上所散发出的魄力震惊了。
“让天空不成其为天空,”她本能地按照台词接着读了下去,“让一张美丽的脸变丑,让一个人的心变得麻木不仁,这种事你办不到。”
法华津伊御笑了一声,朝天顶张开了双手。
“再要让天空和大海浑然一体,要把美和丑混淆起来,要让痛苦迸发出笑声!”
因为两个人姿势的原因,他这样一伸手,左手就从南的手臂和书本间穿了过去,在她的眼前挥舞。悠木猛地站起身,把沉浸在戏剧之中的伊御从身上掀下去,然后将书砸在了他的脸上。
“好你个法华津伊御,”她指着还没反应过来的少年说,“你不是会背吗,还叫我帮你读?!”
“不是你自己说要给我读书的吗?”伊御半个身子没爬起来,反论已经习惯性的后发而先至。南被他气得不行,一脚将书从伊御身边踢开。那本小开本的《卡利古拉》就顺着平滑的地面一路滑到了秘传之间的门口,撞在门框上,随后静静地躺在了那里。
伊御此时已经爬了起来,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书。它被一只从门内伸出的手捡了起来,于是从两人的角度就看不见了。伊御转回头,注视着南,对方不知为何在平静的视线下感到有些心虚。她定了定神,双手扯住裙角。“……怎么啦,我说的,不是实话吗。”
“没怎么,”伊御回答。他看着南,朝前走了一步。“没怎么,”他又重复了一遍,“你现在开心了吗?”
“……很开心。”南梗着脖子回答,“非常开心。”
法华津伊御忽然就笑了。
“那很好啊,”他说。
“那就好。”
☆
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
因你今晚共我唱。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