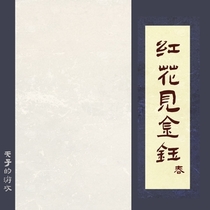一辆马车碌碌地滚过夯土的地面。黄土地上早就有的车辙印被压得更深,扬起一阵细碎的黄色灰土起来。长安的街巷大多没有铺青石板——那是三公九卿之列的门前才有的殊荣,平常的街道不过是一层略比路边高的黄土夯土,一年中任由来来往往的车马在上面留下越来越深的车辙印,直到每三年一次的冬至大祀之时,为了让天子的车架顺畅地从皇宫驶向祈天坛,才会在冬日组织民夫将大街上的黄土夯过一遍又一遍。然而陛下这些年来对国事不甚上心,连三年一次的大祀也不愿参加,那辆缀着轻薄丝帘的车架也许久没有启用过了。也是因此,长安城里的街道也许久没有翻新,不下雨还好,若是下了雨,那便是一地黄汤的腌臜场面。所幸秋雨还没有下,这一道马车的车辙只是给长安城里多留了一道痕迹罢了。
驾车人拉起缰绳,马车缓缓停在了一处路口。周拂桢下了车,一手笼着一张绢花纸写的挺括礼单,另一手局促地抓着一张灰石色的卡牌。又看了两眼前方小巷里的府邸,周拂桢将手里的礼单与卡牌统统收进了袖子里。
“劳驾,只能送到这嘞。”车夫举起草帽给自己扇了扇风,“里头太窄,进去了就不得出来哩。”
“无事,你在此等着我便是。一会有人来与你接洽,这马车上的东西便让他们搬走就是。”
街上的人相比以往少了不少。这也难怪,自圣上倾举国之力欲与赤梁血战的消息传来,长安的百姓似是闻到了这风声里的危险,纷纷躲进了家门里。这倒不怪他们,打仗首一个最紧要的便是士卒,更何况这样一场大战了:虽说打仗时倚重的是老兵,可只靠老兵可能独自打完已整场战役么?新兵是用之即退的马前卒,既然是马前卒,那么更没有训练一个月或训练一整年的区分了。被临时征召的二郎们就这样扛着淘汰下来的旧刀,往西一步一步走上了战场。但那些被征为士卒的良家子们还算好命的,若是出身更低,则是被征为民夫。若是征为士卒,在打仗时得了几处功绩也能得到些许提拔,但若是征为民夫,那就得背负辎重、修灶做饭、修补兵器、修葺城墙。民夫的工作更为辛苦,且少有补偿。因此一时间长安街头反倒萧条起来。
“后生!您平安……”街角的一处声音叫住了周拂桢。他低头一看,原来是一位老花子,披着破烂衣衫,摇着有几个烂铅钱的碗朝着周拂桢看:“大人才高八斗,平步青云……”
周拂桢皱了皱眉,从腰间掏出一枚铜板扔在了老花子的碗里。
“哎哟!”老花子心喜,拾起铜钱擦了擦,宝贝似的将其藏进了腰带里,又抬起头,对着周拂桢拜了又拜:“您真正是星宿下凡……”
周拂桢不耐地皱了皱眉:“老丈,这些闲话旧莫要说了。”
“那俺也没有不闲的话可以讲么!”
“老丈就不怕被抓去做民夫么,竟也不躲上一躲?”
“躲,躲去哪里么!老头子没得地方住,每日还得吃饭哩。”老花子呵呵一笑,“大人予我这一枚铜钱,倒使我今日的饭食有处去了。”
周拂桢叹了口气,也不与这老花子纠缠,径直地向前走了。那老花子倒也不恼,嘻嘻地端着碗对着往来的人说上两句吉祥话,等着下一个愿意往他那破碗里丢下铜钱的人。
王府的门柱半新不旧地立着,周拂桢连忙向门童递了名剌。按照此时的礼节,连衡已在昨日便递上一天后派人前来的拜帖,而这位王大人也回了相应的回帖。门童带着自己的名剌往内走去,不多时便出来喊道:“我家都尉请你进去。”
折冲都尉王焕荼是一位魁梧女子,身材高大,剑眉星目,周拂桢见之便心生敬意,低下头去双手递出礼单。
王焕荼“嗯”了一声,接过礼单。礼单上无外乎一些白银、丝绸之类,王焕荼只扫了一眼便失了兴致,将纸条递给一旁的下人,吩咐了两三句话,下人便识趣地走开,唤人去接收礼物。
周拂桢小心翼翼地探手摸了摸袖管里的卡牌——还没碎,难道只递出礼单还不够?思绪转动间,便听到王都尉豪爽地一挥手:“请坐,为先生看茶!”
一杯清茶于是被端上了周拂桢桌前。照着礼节,周拂桢微抿一口茶水,随即开口道:“我家主人问王都尉安。”
“好么,就是忙了些。你也知道,前些日子的桃树灾搞得长安乱七八糟的,这些日子醒来刚喘口气就得考虑怎么处理了。”王焕荼吹一口茶水上的浮沫,饮了一口,“倒是连大人,可还好?听闻你家大人有意建功立业……”
“是,这次陛下西征,连大人说可断赤梁一臂,可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事。”
“是打算随军出征么?这一道路途遥远,战场可不比长安,还得多加小心哪。”
“多谢大人挂念。”周拂桢拱一拱手,“行伍之人,哪个不是将脑袋挂在腰上来的呢?更何况陛下又有扫清寰宇之意,此次出征,必然是个建功立业的好时机。”
“倒是我多嘴了。”王焕荼一笑,“既然连大人心意已决,我也祝他前路顺遂。——倒是你,也与子仪一道去么?”
“既入官场,为上官分忧便是我的本分。”
“好么,一个两个的,倒使我劝不住了。”王焕荼饮尽了杯中的茶水,“路途艰险,若是有什么我好相助的,及时与我说了最好。”
“倒确实有一件事,非得王大人您首肯了才行。”
“哦?竟有此事?某还有能帮得上兵部尚书的地方?”
“数月前,大人为防霜原南下,曾购了一批好马——”
“噢哟,我想起来了。那马如今在……”
“正在朔方的马场上。”
王焕荼点了点头,“本想着练一批骑兵抵御霜原的,不过骑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霜原也未能南下,这批马儿因而就耽搁了。”
“正是那一批马。只是如今将要西征,打的虽不是霜原,倒也是西北的蛮夷……”
“这有何难,借了你便是。”王焕荼一挥手,未等周拂桢开口便敲定了借马的事宜。见着周拂桢愕然的眼神,又飒爽一笑:“既是为了保家卫国,打的是霜原、是赤梁又有什么区别呢?”
周拂桢连忙道谢。王都尉转而又问起周拂桢的境况,周拂桢不敢托大,一五一十地详细告知。一番宾主尽欢后,王焕荼点茶送客,周拂桢这才退出了王府。
走过小巷的拐角,周拂桢突然皱眉,闻得一股尿骚味,只见原先那老花子坐着的地上落了一滩臭烘烘的水迹,又歪歪扭扭地拖向了远处。周拂桢心下不免生出一股兔死狐悲的悲凉出来:那老花子多半是被抓民壮的人抓走了,吓得失禁,只是那老汉拗不过抓壮丁的人,挣扎着被拖走了。
又向前走了一段,见王府派出的下人正在将马车上的丝绢搬回去,周拂桢忍不住又摸了摸袖中的卡片。
“还不成么?——是送礼不行,还是送的礼不够?”
-
淮南道,和州,历阳郡。
张三扯了扯号坎,这鬼热的天!这月头到现在未下过一场雨,秋老虎正呼着热气对众人虎视眈眈。日头晒得他头发痒痒,伸手挠了却不得劲,只得作罢,听着操场上主官嗡嗡地叫。
主官说到哪了?前不久还说到忠君报国,不知现在又在说些什么?大军要开往西边和赤梁人打是人尽皆知的话题,这次想来便是开拨前的动员了。只是发粮饷的环节怎得还未到?上一轮欠饷已有三个月未发了,饿得自己只能喝些米糊汤过日子。只是那主官的亲兵自己有些印象,前几日执勤时见着他们浑身酒气、互相搀扶着进得军营来,嘴上还带着未擦净的油花!张三恨恨地盯着主官身后挺胸叠肚立着的几位亲兵,只觉他们肥头大耳、面目可憎。
主官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似是说到“为了圣上的恩典奋勇杀敌”什么的。发饷环节呢?怎得还未到。大军开拨前,不都是要补齐拖欠的饷钱,再添置一笔赏钱么?这狗入的主官,竟是连这都要吞么?
主官催着开拨,士卒却未拿到钱粮,与张三一同在太阳下晒得头昏的士卒便鼓噪起来。这个说“不发钱粮,这个兵当得还有什么用处?”,那个说“入你娘贼,兄弟们的钱全是给你吞干净了!”,又有一个再说“再不发钱,咱兄弟就投了黑刀会,让这狗官与赵大头领讲道理去!”
眼见操场上的喧闹声浪越发响亮,主官竟一声呵斥:“为国效力可是尔等殊荣,竟为了一些阿堵物在此鼓噪么?”说罢,主官身后的亲兵便自腰间拔出刀来。明晃晃的刀刃反射着阳光,使得吵闹的声浪安静了不少。“不想挨军棍的,即刻出发!”
张三朝着地上狠狠啐了一口,想象着那口痰便是主官的脸,狠狠用脚后跟碾平了那块泥土。待得军队在主官亲兵的刀光底下磨磨蹭蹭地列完队,向外走出不到二里地,队伍前方便又喧嚷起来。这喧闹仿佛传染一般,顺着队伍传到了后边。
“三哥,你评评理,哪有这样的事呢?这样大的调动,怎得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花呢?”又有人这样喊着,似是很不服气。张三摇了摇头:“这狗入的主官!我看,他这是明知我们要送死了……”
众人瞪大了眼睛。这年头,当兵可不是冲着为国捐躯、保家卫国来的。他们只是被征兵选中的良家子,期待着当兵挣来的军饷能在服役结束后带回去。谁可曾当真想过打仗——乃至于战死呢?
“那狗官自己有七八个亲兵服侍,倒让我们走在前面替他挨刀子……”
“我早说咱们逃了,莫要受这鸟气……”
众人七嘴八舌地发着牢骚,前方的队伍突然分开,几个着甲的年轻人摸了过来:“三哥,你是这一块的什长,我们长官差我们来与你商量件事。”
见两人愤愤不平的面容,张三心下一凛。今天这趟开拨,怕是怎么着也完不成了。
“我们什长说了,与其在这营里受那狗官的鸟气,不如我们杀个回马枪,斩了那狗官,再去三公山上投了那甚么黑刀会……”
“好啊,好啊,我早看那鸟官不爽了……”二人话音未落,人群里就有了附和的声音:“那狗官屋里定藏着金银宝贝,我们砍了他之后再将宝贝分了……”
见这局势再弹压不住,张三当机立断:“好,就算我一个。挨了这么多年军棍,怎么着也得找回点场子……”
懒懒散散的队伍乱了套,过了好一会,才整得利落起来。只是这一次非是向着县外,而是冲着军营浩浩荡荡、杀气腾腾的奔将而去。
当日晚些时候,三公山上。
三公山上原本有一处道观,据说是大烨还未建立时,有几位道人在此处修道,然这山不够高,也未有甚么灵气,在这道观中的道士越走越少之后,这道观便被废弃了。直到五六年前,一队响马自北边来,鸠占鹊巢地占了这处还算宽广的道观,自称一个“黑刀会”,便以此为基地做些打家劫舍、压榨百姓,偶尔也能称上除暴安良的活——山间匪患众多,一处村落往往要挨上三四个土匪窝子的压榨。然这黑刀会装备精良,竟然主动进剿了这群袭扰无度的土匪,至于官府,他们也乐得将土匪袭扰减少这件事当作自己的政绩上报上去,自此这历阳郡的百姓便只需受官府和黑刀会的压迫了。
张三领着一群披甲执锐的士卒战战兢兢地站在三清殿前。那三清殿没有三清像,那木偶外的一层金箔早被兵油子刮了卖钱,内里的木头被砍作柴烧。不多时,又一位半披着圆领袍的士卒从大殿后面转了过来:“可是名唤张三的?赵大人要见你。”
张三赶忙走上前去,从怀里掏出散碎铜钱递给了那士卒。那士卒掂量着铜钱,看来颇为满意,开口说到:“我名唤李四,是大人的亲兵。”
“赵大人可有意收编我们?”
“近日里来投的不止你们一家。”李四只说了这一句话。这话使得张三一下子揪起了心,虽然自知是那亲兵拿捏自己的手段,此时却仍为自己这一营军士的未来担忧起来。
后殿坐着一人,身披黑袍,身材魁梧,脸色阴沉。
“来人便是张三?”那人声音低沉,却叫张三听了不由得膝盖一抖,跪了下来:“回大人的话,小的正是张三,早知赵大人威名,今日特地领兄弟们来投……”
那赵老大——赵百成并不出声,屋内一时间仅有张三紧张的呼吸声回荡着。又过了许久,张三脸上的冷汗涔涔地落着,才听到了赵百成雷鸣般的声音响起:“嗯……我看你也是个好汉。起来吧,带弟兄去长青殿歇息。”
“谢大人恩典!”张三磕头不止,强撑着站起来,点头哈腰地随李四退出后殿。又过了许久,那名唤李四的亲兵这才回来,恭敬地垂头立在赵百成身侧。赵百成一挑眉,李四立刻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都还安分,像是被您镇住了。”
“没见过血的小兵娃娃。”赵百成嘟囔一句,闭着眼,手指在膝上一点一点地敲着,不多时又睁了眼:“昨日来投的那帮人呢?他们可是不安分的。”
“照您的吩咐,将他们的主官与士卒分开安置了。那主官还有些不满,士卒们倒还安分。”李四回答。
“嗯……”赵百成摇了摇头。“看来,咱们在这三公山呆不下去了。”
tbc


(点卯前的故事)
梅瑛乔装撞刑堂,盐帮推舟昧银两
梅瑛换上一身短衣,趁着船到码头,来往的船工忙着卸货,蹑手蹑脚从船舱摸出来。
天已然尽黑,连月也不曾出来照亮,正是月黑风高时。船工节俭,随身捎带火把,要用的时候甩一两下, 火把里隐而不发的虚火随着晃动,像饮饱了水的菌干,噼啪着借力燃烧起来。不过一豆亮光,仅仅照亮面前几步路。梅瑛蹲身在火光的阴影里穿行,一路摸到一座浮岛的边缘——如果线人没说错,这里就是此处盐帮的一座落地。
浮岛上盖一座竹楼,油布拼接覆盖用以防雨,里面隐隐有人声顺水飘来。梅瑛犹豫片刻,决定再往前探探,觉得不对再撤回来。
官员贪污一案已经在案前搁置半年,官职不大,银两却不少。府邸搜过,人也审过,偏只是些稍微多些金银罢了,同品级的贪官私吞多如牛毛,比起来这人端的是个“两袖清风”的好官模样。搜不到归搜不到,但白纸黑字的账可对不上。卷宗交到梅瑛手上,前面已经接手国好几任,现在大理寺已经准备结案,剩下的不过是往刑部递个流程,让同为六扇门的同僚知道这个事罢了。梅瑛看似和气,偏对当朝大理寺卿——陈怀澈——生得一颗七窍玲珑心。案件里关键人物,官员的庶弟像是隐身了般,如此明显的问题,陈怀澈不可能置之不理。梅瑛双手一合,揣着卷宗就要上门让对方给个说法。
“梅大人,陈大人说了,这件事情牵扯甚多,已经追回大部分赃物了。”
大理寺的小吏半推半拉,阻止梅瑛冲到大理寺去。
“这不是丹青兄的作风。”梅瑛表情淡淡,难得带上几分锐利的审视。最终,他不愿意为难眼前两股战战的小吏,挥挥手放人走了。
行啊,这般避讳,既然交到我手上,就让我探探虚实罢。
梅瑛深吸气,屏住呼吸放缓脚步,距离竹楼不足十尺,听到了里面传来的告饶——
“我不知道,剩下的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哪里敢瞒着您‘覆海狼’啊!”
随即而来是中年男子沙哑的低笑,竹棍有节奏得打在地面上,俶尔停止:“这不是还能花言巧语吗。”
梅瑛再靠过去一点,忽然脚下一软。
“噼啪”
一根晒干的竹子被他踩断。
“谁!”竹楼里传出暴喝,一短衣粗褐的年轻汉子冲出,目光如炬,一眼就看到了行状鬼祟的梅瑛。他朝着梅瑛大步奔行,浮岛随着汉子的步伐上下晃动。梅瑛或是慌张或是受了摇晃影响,急切中两腿如软烂面条,每一步好似踩在棉花上,反身只见那汉子丝毫不受影响。坏了,是枚练家子,梅瑛想。
他索性不逃了,让汉子把自己押进去。
竹楼内主座上坐着一位高颧骨的中年人,头上好似营养不良的棕发,蓝色抹额,单侧系着一绺辫子,他杵着竹棍,眼里闪着财狼一般精明的光,上下打量着梅瑛。
“格当码子打哪儿来的?”中年人问押送的练家子。
“生面孔,怕是拆梯子。”练家子恭敬地答道。
中年人冷哼,言辞间带有火气:“拆梯子?饭桶!哪里在玄,明儿自个儿找那装木鎯照镜子。”(1)
练家子更是低头,一言不发,像是知错。
梅瑛见他们切口混杂,自然没全懂,但大概想到是斥责练家子办事不利。他放宽心,看这里人也没对他动粗,自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江湖组织。随即他又看之前跪在地上告饶的人...和贪污的官员怎么有六成相似?心上盘算了一阵,大概确定这人就是官员的庶弟。
“不知我们这小小码头,怎么让大人大驾光临?”坐上的中年男人走下来,对梅瑛和善地笑,“松手,像什么样子,给大人看座。”
练家子松了手。有人搬来竹凳,有人放上小几,还有的人端来清水。梅瑛安之若素坐下,没动杯子:“你认得我?”
“我等小人物自然不认识大人名讳,大人可赏脸告知一二。”
梅瑛被这做作的殷勤弄得左右不是滋味,这码头头子看似恭敬,实则处处透露送客。伸手不打笑脸人,梅瑛还是生硬地报上名字:“梅瑛。”
“!是你!刑部的那个!”官员的庶弟后退两步,“你怎么找来的!”他又转身指向中年男子,”你们言而无信!”
官员的庶弟像是发了狂,指着四处乱骂一通,竟要冲到中年男子面前:“你们盐——”
练家子不等人说完,一拳把人掼在地上,对方呜呜咽说不出话来。这时候,中年男子才摸了摸下巴:“见笑了,刑部的梅大人。草民是码头的小管事,姓武,单字一个奎。”
梅瑛见他强调官职,忍不住呛声:“‘覆海狼’武奎?”
武奎摆摆手:“水上叫着玩儿的诨名而已,算不得什么。倒是梅大人,看起来深谙让人说话的办法啊。”他一只手拖着竹棍,慢悠悠坐回座位,“梅大人可是在追查案子?六扇门办案,我等自然全力配合。”随即低声道,“我们这里问些什么,可比刑部顺手多了。”
顺手。
这个提议的确令人心动,不知道陈怀澈当时是如何考虑——或是受制于人——梅瑛指尖在小几上来回敲击,在口中舔着下唇。
这码头头子,果真是精明的商人,自己一来,转眼间出卖才和自己合作的官员庶弟,只怕靠不住。
心念回转,梅瑛朗声道:“我们刑部自是有规矩,只能使用杖刑,隔二十日一审,拷打不得过三次,总数不得过二百杖,且不得更换行刑人。”
他站起身,明暗晦涩的火光照得他梅色的头发,像是梅树下生出的花魄(2):“但...此处不是刑部,我更想试试脑箍呢...鼠弹筝也不错。”他对着官员庶弟笑了笑,“脑箍知道是什么吗?以绳束首,木楔打紧,渐至眼耳出血。鼠弹筝呢,就是把你的指头、趾用细绳反绑”梅瑛在对方惊恐的眼神里指了指对方的指头,“我会以木棍弹击绷紧之绳,每弹一下,绳子便绷紧一份,最后关节绛紫,你的手指也会随着一寸一寸烂掉....”
梅瑛又低语似的说了许久的酷刑,再看过去,对方已经吓晕过去了。武奎斜睨梅瑛,又瞧了瞧地上昏死过去的官员庶弟,一副思考的模样。
“梅大人,”武奎正色,“此人就交给我们吧,我武奎定会让您看到我等的诚意。”
梅瑛注视武奎,转身离开,众人纷纷为他让开一条路,无人敢阻拦半分。他走后,众人心有戚戚,望着座位上的武奎。武奎没事人一般,示意找人把官员庶弟泼醒:“看我干甚,可算把那聪明的梅大人送走了,下次谁敢再往帮里请大佛,那位大人说的内容,可是给老头子我不少启发啊。”
哗啦——
官员庶弟浑浑噩噩醒来,惊魂未定地看着武奎。
“你们家怎么就惹上六扇门了呢?”武奎蹲下,拍了拍对方的脸,“我盐帮也不是言而无信之人,说吧,别藏私了,除了老头子我,其他都帮不了你。”他比了比一个手势,“得加到这个数。”
官员庶弟喜极而泣,他颤颤巍巍说出:“一千两,都在....”
武奎侧耳听了听,忽然哈哈大笑!
“好!这样,我们盐帮给你取来!”又过了一个时辰,银两在竹楼放置妥当,武奎做了一个请的动作:“来,拿走吧。”
“没有车船吗?”官员庶弟愣住了,看着竹筐,布料,还有零零散散堆在地上的银子,他竟有一种身在宝堆却带不走的错愕。
武奎啧啧:“我们谈的时候,就说的是我们用竹筏,您带着银子离开,不是吗。”
“话虽如此...那带不走的...你们!好大的胆子,算计我!我!”
“你可和刚才那位朝廷命官不一样啊,”武奎狞笑,“我听闻造银厂的人偷银子,把银子置于谷道里,不如您委屈委屈?”
言毕,周围传来众人的哄笑。官员庶弟一脸屈辱,双手紧抓裤头。
武奎挑眉:“这可是一千两,靠他一个人可不行,怎么,不帮帮他?”说着便往竹楼外面走去。
那官员庶弟突然意识到什么,但回头就被练家子狠狠按在地上。
月黑风高,水面上传来隐约的惨叫声。
“这梅大人还真是...启发老头子我了。”武奎拎着着竹竿,往码头走去。他从兜里摸出半个发硬的馒头,一路走,一路碾碎扔进圈出来的鱼塘中。
各种鱼儿浮上水面抢食,其中夹杂着几分艳色,几尾锦鲤沉浮。
==================
第二日,刑部门口挤挤挨挨围着一群人。
梅瑛走进人群,竹席包裹着尸体,没人知道谁放在这里,仿佛凭空出现。有人掀开竹席,不是别人,正是那贪污官员的庶弟。他面色惊恐,身上遍布淤痕,未着寸缕,显然死前受到莫大的酷刑。
人群中有人恨恨道:“匪帮手法,他们好大的胆子。”
仵作细细验尸,尸体的谷道撕裂,脱垂的肠子里找到一百两银子。
梅瑛皱了皱眉,这是威慑。
线索已断,此事就此结案。
(1)都是江湖黑话,混了丐帮和洪帮的,时代对不太上。只是理论知识,没实际应用作者只有照猫画虎:
“这个人打哪儿来的”
“不认识,怕是要走漏消息出去的。”
“走漏消息出去的人?没用!这哪里是圈内人,明儿自个儿找到那间谍把双眼挖了。”
(2)清·《子不语》——“此名花魄,凡树经三次人缢死者,其冤苦之气结成此物,沃以水,犹可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