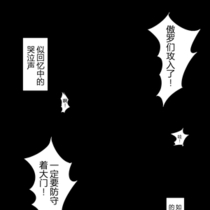
雪和雨不同,雨水会变成一支支箭穿透空气入侵地表,浸润泥土,打湿衣服,让人们不得不寻找掩体躲避它们的进攻,但雪只会摇晃着飘落,安静地落在物体的表面,直到升高的温度融化它们。
这天晚上的东京连空气都冻住了一般,一点风都没有,细碎的雪花缓缓落下落在八云慎和古雪霖的身上,他们的发丝因为些许融化的雪花而被打湿,但是八云慎知道他脸上水滴流淌过的痕迹并不是因为那些雪花。
他用力吸了下鼻子,从肺里交换出的气体刚一从他口中呼出就被染成了白色,而他面前的女人仍旧事不关己——或者说让自己看起来事不关己?飞舞的雪花和氤氲的水汽模糊了他的视野,这让他看不出她的表情,而在他胸中涌动的情感也使他失去判断,他脑海里关于她的一切现在仿佛都成了一厢情愿。
雪渐渐在湿滑的地面上堆积起来掩盖了泥泞的黑色,但却洗不去他平时干净的皮鞋上此刻沾上的泥点。而对方平日里时髦又漂亮的靴子也是一样的狼狈。
他们两人谁都没有开口,雪掩埋了他们的静默,直到他率先在这场无声的对峙里投降。
“你以为我只是在玩玩?”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不要发抖,尽管他的眼泪已经出卖了他的真心,“沢城雪,你怎么敢说出这种话——”
“说得倒挺像那么回事,”雪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融入了空气中,和冰冷的雪花一样落在他升温的心上,“你不就是很喜欢和女孩子玩吗?一个腻了就换另一个,正好,我也腻了。这不是正合你意吗?”
或许丢掉那些无所谓的脸面难看地哀求她,和她解释说不是她想的那样,同她诉说他的真心,他的爱情,他的全部,或许还可以挽回这场危机中的感情?可是他心里一股奇怪的冲动却不允许他输掉,曾经母亲对父亲的哀求和眼泪淹没了他的童年,如今也冲垮了他的理智,“哈,是!你说得对!我玩腻了,”他拔高声调,苦涩的泪水淌进他的嘴里,“就像你没有爱过我一样,我也没爱过你,所以也该结束了吧?!”
雪的声音没有再响起来,最后这里只剩下渐行渐远的脚步和压低的啜泣。八云慎跪倒在地,雪花落在他颤抖的脊背上。
中国的早春和日本相差无几,或许是因为纬度相近吧,八云慎在中国的第一个春天平平淡淡。来到中国的医学交换生每天辗转于实验室图书馆医院研讨会和宿舍,埋首于各种实验报告和大部头专著,忙着忙着一天就过去了,和室友回到寝室时两个人都疲惫万分,糊弄完洗漱简单互道一声晚安便各自换了衣服上床睡觉。睁开眼又是同样忙碌的第二天。
他同往常一样起床,从柜子里随便拿出衣服换上,室友已经在冲咖啡,香气充满整个房间。他径直拐进卫生间,镜子里的男人睡眼惺忪,盛在手掌里的水被泼在脸上,他拿过毛巾用力擦了擦脸,这会儿镜子里的家伙看着才精神了许多。等他刷完牙走出来室友已经将白大褂搭在臂弯里,嘴里仍在咀嚼还没咽下去的面包片。
“我今天得早点去实验室,”他的肩膀被拍了拍,“等会儿记得把面包的包装袋封好。”
“知道了。”他挥挥手送走了连告别都来不及说的室友。
今天他要去医院跟着老师实习坐班,不用火急火燎地赶去,医院也离得很近。他从袋子里拿出面包片叼在嘴里捏起桌子上包裹着塑料片的钢丝把带子绑紧。等他三口两口吃掉面包拍掉手上的面包屑,他拿起手机和书包,而他的白大褂搭在椅子靠背上等他拿走。
古雪霖瞒着她的妹妹古雨霖偷偷改掉了去医院复查的时间,她把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等在外出差的古雨霖按原计划到家她都已经坐上去医院的公交车了。兵贵神速,七点五十分整古雪霖已经背着包站在了医院大门口,她提前从包里拿出上次的诊断报告跟着人流进了电梯熟练地摁下5楼的按钮等待电梯把她送到顾客的楼层。
说来也是倒霉,谁能想到曾经东京大舞团的首席舞者金盆洗手若干年后竟然会在一个小小的舞室折戟,因为一个简单的旋转摔倒把腿摔折了呢?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古雪霖已经好了个八九不离十,今天是她最后一次复查,情况顺利她就可以过回之前的家里蹲生活——当然这也要看医生的意愿,不过古雪霖大概猜得到医生准会对她说什么“要多运动,多晒太阳”之类的生活小建议。不过只有她一个人的话谁会知道医生说了什么。
很快,她站在骨科的主任医师办公室前,灯光透过磨砂玻璃温柔地落在她的脸上,她抬起手,门板被她的食指关节敲响。
“请进。”
这是个令她感到熟悉的声音,但却并不是她的主治医生,而是好像来自一段曾经令她痛苦而欢愉的久远记忆,跨过遥远的日本海被她丢在了那个岛上的一个繁华都市里。
她推开门,看到八云慎同样惊愕的面容。


在某天看到那条微博时,安乐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这不就是我吗”的想法。
具体内容她也记得不是很清楚,大概就是有的人工作了还像小孩一样,投资、房产都是零,工资条有几个项都没摸清楚,未来完全没在考虑。周围的人好像背着他们悄悄长大了——他们结婚生子,走上了成熟大人的正轨,自己却还在乐呵呵地看动画片,做那些家长从小时候开始就觉得“不务正业”的事。
倒也不是说有什么不好,人生的意义都由自己决定,谁又能说哪种才是绝对正确的呢?只是在某一刻,在回忆起曾经的朋友们都迈入了婚姻的殿堂,逐渐没有共同话题,走上交集逐渐变少的人生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自己还停留在十年前——执着的用笔写下藏在日记里的梦想,想象着自己成为大人的模样。
我现在不就是个大人了吗,在某天下班路上看到橱窗里的婚礼蛋糕时,她有点好笑地想到。标签的价格不再是高不可攀的数字,只是没有购买它的理由。装饰精美的三层蛋糕上,有用奶油画下的花纹,举着喇叭的小天使,还有一种轻柔又梦幻的氛围。它包涵着的爱,共度一生的承诺才是自己无法购买,也没有体会过的东西。
手指触上玻璃时,中间透明的间隙浮上一层水雾,带来冰凉的触感。爱情在现实里真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她想。作品中的两个人可以因为任何的理由在一起,但是现实中的人呢?要考虑的似乎不只是单纯的“喜欢”。
“人要如何才能证明自己相爱?”
“言语和物品真的能够承载起这份诺言的重量吗?”
“人如何能保持这份爱走过一生?”
“......会是谁,因为什么爱上我呢?”
“你考虑得太多了,相爱哪有那么难?有些时候是要看眼缘的。”这是还在学校生活时朋友的感想,她们笑着制止了自己继续纠结下去:“那个人说不定就在未来等你。”
“你太纠结了。”这是选材讨论时听完自己没完没了感想的学长,顺便还用册子打断了下一段感慨读条:“磕cp的时候倒是半句就能磕到了。”
“那是因为......”不同时光中的我解释道,然后逐渐接受了这个我二十五的人生好像还没有等到这个人,甚至连对他的描绘也逐渐模糊的事实。
我的幻想中,我的笔下,我剪辑出的视频里,相爱的人总能重逢,他们携手走过余生,在平凡的街道、海边、城市的高楼上举办自己的婚礼。因为每份感情都弥足珍贵,他们珍重地探索着无数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能性,我为这份感情感到喜悦,却只能做一个观众。
因为我渴求着爱,却又觉得自己爱非常沉重。这割裂的感情我花上一生大约都无法解释清楚。
我可能还是没长大,安乐想到,但是也没关系,因为我现在也足够快乐。
啊,这个可以代。这样漂亮的婚礼蛋糕应该摆在我产品的婚礼现场,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一对,但是光想想都磕到!她拿出手机,把偶尔窜出来的沉重感想用代餐大师的“魔法”变成了下一次视频的素材。结婚什么的,哪有磕cp快乐!她的视线不再定格在不会出现在自己人生的蛋糕上,顺便越过人群,发现了冷藏柜里的抹茶蛋糕。
“带去工作室吃好了,买几份呢......”她小声地和自己对话着,推开了蛋糕店的门。
风铃在头顶叮铃作响。


·鸟蛋协二人转。如果有四个声音的节目也可以叫二人转的话。
·这里除了冷笑话与过剩的家族爱一无所有。
——————
1、珀加萨与艾利亚斯在霍格沃兹
珀加萨与艾利亚斯在霍格沃兹的第一年。
珀加萨:你好,你好!很高兴见到你,艾利亚斯。
艾利亚斯:你好。
珀加萨与艾利亚斯在霍格沃兹的第二年。
珀加萨:你好,艾利亚斯!自从假期过去就没见到你了。还好那段时间已经让我们变得无与伦比的亲密了。还是很高兴见到你!
偏见:你好!你好!艾利亚斯!很高兴!哈哈哈!哈哈!
艾利亚斯:你好。
艾利亚斯:你好,偏见。
珀加萨:是的,是的。我很好。偏见也很好!谢谢你的关心。
偏见:是的!是的!是的!偏见!很好!
珀加萨与艾利亚斯在霍格沃兹的第三年。
珀加萨:你h……
艾利亚斯:你好,珀加萨。
艾利亚斯:你也好,虚荣。
珀加萨:噢,艾利亚斯,你真棒!你的进步让我大吃一惊。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你可是我的伯母的姐姐的儿子。我们最终都会好好记住自己的家人的。
虚荣:gua~~jia!
艾利亚斯:我不太确定。不过如果你一直说话,我可能就不会弄错了。
PLUTO:你说话的方式有时候就像‘偏见’。
——————
2、珀加萨与艾利亚斯在特拉法尔加广场
珀加萨与艾利亚斯第一次去特拉法尔加广场。
珀加萨表明自己更喜欢它在市井里流传的诨名。
珀加萨:是的,我记得很清楚。小姨告诉过我,我记得这个很棒的名字!特拉法加鸽子广场,伦敦著名的有很多鸽子的地方。这里有很多、很多的鸽子,是的!很多的,永远很饿的鸽子。
珀加萨已为这一天绸缪许久,在深谙麻瓜文化的伯母指导下配备全套的军资。她摩拳擦掌,身负墨镜、厚外套、手套和一袋鼓囊囊、炒的喷香的谷米,感到自己简直顶天立地,无所不能。
所有的鸟儿都会为她所折服!此刻的她握着苞谷袋子就像攥住了命运的咽喉。她相信自己绝对魅力四射,没有一只名叫鸽子的灰毛禽类能够抗拒。
艾利亚斯基本同意,但提醒了堂妹,也许是表妹——仍要小心刚刚穿上的新衣服;如果没有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她就不应当贸然迎击这些海兵般前赴后继的凶猛羽族。
艾利亚斯:嗯……它们都很热情。远超你想象的热情。
PLUTO:但那是对苞米的。至于你,人类——鸽子并不在乎苞米架子的感受。
珀加萨大叫着没关系,我会接纳从小家伙们那里海浪般涌向我的真挚感情,如果它们爱我,我就加倍地爱回去!她快活地舒展双臂冲进了鸽群,身体如风车般斜向旋转,指缝里谷粒沙沙流泻,在空中螺旋飞舞,扭成两条灿金的瀑布。
最后艾利亚斯只来得及救出她的偏见。它少了两根头毛,不过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寻觅并啄食羽毛缝隙里的谷子上,因此心情尚可。
好在有热心游客及时向广场的派出所报警。
这不是什么特别少见的事情。警察们见惯不惊地评价。——检查一下有没有贵重物品丢失就好。虽然丢了也没什么办法。
艾利亚斯点点头,坐在纪念碑边上等珀加萨过来找他。
珀加萨:艾利亚斯!天啊!我还以为要被拖到威尼斯去了!我还没有去过威尼斯,但是听说那里也有鸽子广场。也许鸽子们会想请我过去看看。
偏见:天啊!
艾利亚斯:你好。
艾利亚斯:我猜你是珀加萨。
艾利亚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可以回家了。
PLUTO:说的真有道理。毕竟珀加萨不可能是那边下水口里粘着谷壳的碎片。
——————
3、珀加萨与艾利亚斯成立B·E·C的始末
珀加萨与艾利亚斯成立B·E·C的起因是艾利亚斯又一次认错了他的表妹。
他尽管犹疑,还是和恰巧猎捕了发卡之一的偏见进行了长达五分钟的不知所云的对话;并在真正的珀加萨出现时来回观察她们到一个相当失礼的时间。
艾利亚斯:我很抱歉。
PLUTO:然而其实,他真的看不出来你们有什么区别。只是认为这样说比较有礼貌。
珀加萨在得知他的父母,和过去特殊学校的老师们,都曾为了帮助他辩识人脸而佩戴特殊的饰品,直到他能够独立记忆才摘下(这通常需要花费数月到数年)后,热烈赞同这个主意,认为它睿智,天才,并且充满了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的温暖气息。
珀加萨: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家人就应当帮助家人。给家人打上特别的标记实在太酷了!我们可以做一个徽章。它会是金属的,有羽毛和蛋和字母,闻起来是玉米的味道。
珀加萨:但我们要如何跟其他人解释呢,艾利亚斯?如果他们也觉得这很酷并且希望来上一个……这个学校恐怕很快就会到处都是珀加萨了!
艾利亚斯:那就给他们。喜欢鸟蛋和羽毛的人……值得这个(deserve it)。但每个人的都要不一样。譬如你是00号,我是01号。大家同处一个……家?而又独一无二。我们的学院也鼓励同一性中的差异性。
艾利亚斯:我应该……见过和这个模式很像的,呃,组织形式?
PLUTO:那叫俱乐部。傻瓜。
珀加萨:噢!谢谢你,PLUTO。你真聪明。没有你我们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你必须得是元老级别的02号了。你为俱乐部的成立做出了特别突出的贡献。
珀加萨:俱乐部,好的。我喜欢俱乐部。我们马上就要拥有俱乐部和俱乐部徽章了,艾利亚斯。这实在是太令人激动了。那么我们的俱乐部该叫什么呢?
偏见:嘎嘎嘎嘎嘎!
珀加萨:偏见也很高兴!它可以成为03号。而不幸的虚荣只能明年再加入为04号了。不过我觉得嘎嘎俱乐部这个名字还有待商榷。你觉得呢?
艾利亚斯:为虚荣感到难过。
珀加萨:鸟要混的好有时候也需要一点运气,别太在意!
艾利亚斯:至于名字。嗯。我不讨厌嘎嘎俱乐部。但这会让偏见的存在感太强,对我们的其他朋友不够公平。
珀加萨:你说的很对,我们必须是公正的,不能够厚此薄彼。
艾利亚斯:所以我们应当用’bird’这种覆盖面更广的词。
珀加萨:好的。我同意。但是B·C?这听起来像是中国的银行!也许我们可以再加点什么。
艾利亚斯:加一些蛋?
珀加萨:加一些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