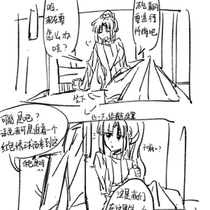出乎意料的是,老裴和小林相处得还不错。
现在他们已经在老裴初见时面露嫌弃的英伦范套房住了几天,在小林心中,这算共同出差的关系了。他们一来就被告知要举办婚礼,塞小鸡崽似地被分在一起,素昧平生的两个人得住在一起,别说老裴了,就连小林都想跑!可跑又能跑到哪里去呢?不如住下,还算白赚一个假期,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要代自己的课,还好自己不是班主任。老裴不一样,他心里紧张,又不愿表现出来,面子上还要摆出一幅人生老前辈的样子,有什么问题非夹在一大段对话中才说得出。那这个小林就会了啊,现在的小学生懂得多早熟,一个一个真觉得自己是大人,但条件限制摆在那里,所以小林也得听他们叽里咕噜一大堆再来一句“老师,你能不能……”。
按这个方法处下来,他俩竟都觉得还行。
除去被绑来这里的惊讶和刚见面时的无措,林琴不再表现得像个刚入职场的愣头青。她把这一切当成是某个领导凭心情布置下来的任务,做一做弄一弄,大家面子上过得去就行。裴乾显然也是糊弄学的个中老手,他无愧于自己干到退休的公务员身份,虽然不至于健谈,但随口就来的话也是不少。一来一去,可不就聊起来了。小林喝一口热茶,怀疑是老裴在外头憋狠了,只能回房间猛说。
“唉,现在的年轻人,”老裴靠着软垫,“一天到晚只想着自己过得舒服,不考虑家里的长辈。早点定下来多好呢?老老实实过日子才是正经话。”
小林趁他不注意撇撇嘴,心里想,那你一把年纪也没定下来啊。
说完这句话,老裴像是想起什么,倒沉默下去,不唠了。他们之前抽到的迪斯科灯球默默转着,一闪一闪的,还挺寂寞。
说到这个话题是有缘由的。
今早他俩去吃饭,看见礼堂的破败样,还以为这地方终于要露出什么黑暗真面目,接下来就该卖保健理财保险三件套了。可谁知小猫咪喵呜几下,开口就是一段爱情咒文。老裴愣了,小林也愣了,他俩吃完饭回房,关上门讨论起来。然后退休老头讲着讲着就将话题拐向小林并不想要的人生商谈,还顺便批判了一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当代年轻人。
当代年轻人小林问:“怎么弄?咱俩去帮忙吗?”
抱怨过“哪有让客人动手道理”的老裴没说话。
小林又说:“老同志,发挥一下助人为乐的精神啊,组织需要你的余热!”
老裴还是不说话。
小林深吸一口气,学着年级主任:“老裴同志,在大家都在辛勤工作,力图为早日修复会馆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的时候,我们怎么能置身事外呢?而且越多人做事,说不定就能越早得到那个什么……爱之力,搞不好我们就能离开了!”
还没等老裴开口,小林又模仿道:“不要因为一个人耽误所有人啊!”
老裴看她一眼,最后还是皱着眉头站起来了。
他俩逛来逛去,最后拐进一条走廊。走廊两旁没窗户,全靠壁灯照明,倒还有点气氛。他们走进去,很快被走道两旁的画框吸引视线。两人边走边看,此时还未发现事情的严重性。
“嘿,你看!”小林指着其中一幅,“国产帅哥!”
画框里是个年轻人,梳着80年代流行的中分头,穿着黑色皮夹克,戴着那时候算得上时尚单品的蛤蟆镜,有点不情愿地看着镜头。小林越看越觉得眼熟,她对着大幅照片沉默许久,最后凭那个熟悉的皱眉解开谜题:
“老裴,这不是你吗?!”
裴乾戴上眼镜,装模作样地咳几声,面上倒显出一点得意来。
“嚯!”小林又仔细品鉴了一下,突然对后面的照片充满好奇。就在她兴致勃勃地往后看的时候,老裴叫住她:“小林!”
他指着走廊另一边一幅照片,问:“这是你读中学?”
小林猛回头,发现那正是自己最不堪回首的造型:遮住半边脸的厚头发(自以为能挡住老师上课的视线),眼睛下是黑眼圈(熬夜看小说的证据),再加上不知天高地厚的自信表情(懂得都懂)。
站在讲台上才知道往下看有多清楚的小林当即发出一阵惨叫。
老裴当然不清楚年轻人的潮流,也不知道什么是“中学二年级”,只是单纯地感叹“年轻人造型花样真多”。
小林叫得更惨了。
“对着喜烛念诗?”老裴问,“你怎么不念,光要我来?”
“我教数学的啊!”小林光明正大划水。

楼道里的灯被高跟鞋的声音唤醒,白炽灯的刺眼光芒登时驱散所有黑暗,刚从电梯里出来的女人面容疲惫,但脸上的妆仍在勉强维持着她的面色让她不至于彻底失去神采,披散的棕色长发因为走动飘起又落在她的肩上。她将手伸进挎包里从夹层里摸到了冰冷而坚硬的固体,金属碰撞的声音回荡在走廊里。脚步声停在了某扇门前,灯光下她分辨出家门的钥匙而后捏住对准门上的钥匙孔,金属嵌合进了锁孔里的精密结构,稍加转动便让这扇门敞开了心扉。
屋内的玄关被走廊的灯照亮,属于一个孩子的鞋子摆在门口,鞋柜紧闭,玻璃水缸里的金鱼华丽的尾鳍像一张丝绸在水中摇曳。她关上门,灯光又消失了,屋子里再次陷入寂静,直到开关的声音带着电灯的闪烁让光明充斥整个玄关与客厅。
挎包从她的肩上被拿下,扑通一声掉在地板上,她的脚步不加停留地从瘫在地上的包旁路过,卧室和厨房的门被打开,但是门后都没有她预想之中的身影。
“妈妈……”男孩的脚步声从客厅响起,但是她的质问盖过了他的尚未完全清醒的嗫嚅。
“你爸呢?”
男孩的神情中闪过疑惑与不知所措。金鱼摆动鱼鳍无声地游动。
“是我先和小米求婚的。”盛虹宇的语气中带着些获胜似的炫耀,但是他的弟弟对此嗤之以鼻。
“那又怎样,说的跟你求了小米就答应你了似的。”盛虹宙把手里的纸片子撕碎了往垃圾桶丢,但是轻飘飘的纸片只是在空中唰地转了个漂亮的圈最后慢悠悠地飘落在地,给这个会馆不知道存不存在的保洁工作徒增负担。
“那还不是因为你把她搞糊涂了!”
“不是我说,那啥,你们……都没成功,是吧?”Luna的手指在他们之间打了个转。
“虽然从结果上来说——”
“那你们不就平局吗,还吵个什么劲啊。”他已经坐在这儿听这俩活宝吵架足有十分钟,尽管被绑来以后的生活无聊又乏味,但听了十分钟的相声还是要换换口味的。
然而强行转移一对同样无事可做的,且性格算得上恶劣的双胞胎的注意力的下场通常都比较悲惨,因为这意味着这位可怜的天选之子会成为下一个他们共同的目标。
“抱歉抱歉。”盛虹宇在脸上堆起不怀好意的笑坐到Luna的左边。
“是我们考虑不周,毕竟我们没您这么有经验嘛。”盛虹宙用一模一样的脸挂着一模一样的笑坐到Luna的右边。
被左右夹击的Luna直觉接下来大事不妙,他的目光下意识地瞟向不远处正在撕香烟塑料包装的八云慎,但对方只是笑笑,而后强行没有看懂他的求救信号,继续去扣弄塑料包装上的封条了。
“什,什么经验……”
“别装傻呀,”盛虹宇说,“就是你和陆鹿的事儿啊。”
“都是兄弟,没啥好见外的,”盛虹宙拍拍他的肩膀,“没准我们俩还能给支个招呢。”
“拉倒吧,我看你们俩自己一亩三分地儿都没搞明白呢还支招,八云肯定比我有故事,去找他去。”
但在他们之前八云慎已经被其他人找上了门,而他手里那包大红色的香烟刚刚撕开封条。
“我不知道……”
玄关处的开门声打断男孩的回答,换了拖鞋的男人关上门随手将钥匙扔进鞋柜上的塑料筐,鱼缸里的水面因为微弱的震动产生了些许波纹,“回来了?”他走到女人的身边,却并不打算停下脚步。
“你去哪了?”
男人没有回答,他走进厨房打开冰箱从里面拿出一罐啤酒用食指勾住拉环,易拉罐的封口在简单的杠杆作用下发出声响,气体在易拉罐中升腾,“不做饭吗?”他关上冰箱,照在他脸上的白光因而消失。
“我在问你去哪了?!”女人拉高语调,男孩瑟缩着后退一步。
“不关你的事。”
“不关我的事?宫村了介,这是我的房子,你是我的丈夫,还是孩子的父亲,你觉得我应该对你的事感到事不关己?!”
男人对女人尖锐的诘问感到不耐烦,但他仍坐在桌前端起啤酒罐喝下一口啤酒,“绘美,别这样,你吓到慎了……”
“你自己把他扔在家这么晚才回来少在那装什么好爸爸!”但是宫村绘美还是深呼吸一口气,她的声音变低了一些,“你去见哪个女人了?”
“……女人?”
“你可真是小瞧我,你该不会以为我能被你哄骗一辈子吧?”
“哦,那你可真是聪明,还要我夸夸你吗?”
女人,八云慎曾以为让父母分道扬镳的是那些父亲曾带他去见过的陌生女人,但后来他长大了,才知道婚姻的破坏者并不一定存在于家庭外部,大部分时候破灭的种子只是……潜藏在人们的心里,等待一个时机。
就像他和古雪霖,没有第三者,没有外遇,他们彼此之间就只是——一方觉得该停下了,而觉得该停下的居然该死的不是他。尽管最后提出分手的是他,但那又如何,古雪霖潇洒地走了,他难看地困在原地徒增年岁。他看得出来这个曾经在一段婚姻里受了伤的女人觉得现在是个修复他们关系的时机,他们像以前一样,一起洗澡,吃饭,打炮,盖上同一张被子,第二天在一张床上醒来,那当初为什么要分开呢?是她丢下了自己,现在又自顾自地要重新开始吗?
古雪霖可以对任何人施展她的手段,但是那些对八云慎通通不起作用。我们是同类,不是吗?
因此当古雪霖拿着那本书被吴玉珂几人推着过来时,八云慎甚至头都没抬。
“那个,八云先生,雪霖有话和你说呀。”她的小姐妹们替她开了口。
这会儿八云慎才抬起头,脸上带着那副通常展示给陌生人的微笑,“有什么事吗?”
被推到前面的古雪霖抬起手,左耳边的一缕碎发被捋到耳后,她另一只胳膊下夹着那本深蓝色封面的书,眼神短暂地停留在他身上,但更多时候则在四处乱飘。
“呃,这本书叫做银河铁道之夜,你还记得吗?”她的声音有些发紧,听起来她有些紧张。古雪霖快速眨着眼睛,但她的视线越来越多地扫过八云慎。
“当然,我们以前……一起去看过音乐剧。”
她的眼神中立刻闪过一丝期望和欣喜,但是很快被她隐藏了起来。她在期待着什么呢?记着又能怎样,他们过去的一切不会对她想要的事情起到任何帮助。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看来你对以前的事记得还挺清楚的嘛。”
“我当然记得,但那又怎样,你那个时候不也没忘,最后我们不还是分手了。”
对方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她身后的人们的表情也立刻变得尴尬十分,古雪霖低下头用鞋尖蹭了蹭地面,而后才抬起头,“这么说,你还是在怪我咯?”
“我说过,我累了。我倒是奇怪你哪来的力气,啊,也是,你本来就是这种人,这次怎么了,又对我恢复兴趣了?这个会馆里这么多别的男人就没有新目标?古雪霖小姐,总是对同一个男人动心不会腻吗?你不是也说我玩腻了吗,我们不就是因为这个分的手吗,你怎么一点记性……”
“啪!”
他的脸被砸的偏向一边,那本银河铁道之夜可怜兮兮地掉落在地,封面上乔邦尼和康贝瑞拉一同仰望着那片闪烁的银河。
“抱歉,我就是记性很差,多谢你提醒,八云慎先生,让我想起来我们两个一样的贱。”
古雪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八云慎抠开香烟的纸封,从里面抖出一根烟叼在嘴里。对,他们两个人一样的贱,谁也别装什么深情的人,各取所需才是最适合他们的,这样就够了。
他想要摁下打火机开关,但颤抖的手指却屡次从开关上滑开,直到Luna从他手里接过打火机,他拿着打火机手足无措,张嘴支吾半天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年轻的电竞选手显然不太擅长安慰人,好在推他出来的双胞胎良心未泯。
“他帮你点火。”盛虹宇说。
“啊……对,对,我帮你点烟。”
打火机开关被摁下,小小的火苗立刻燃起,八云慎点点头,让香烟的前端被火焰包裹直到变黑,白色的烟雾从变黑的香烟上升起。
“那你也差不多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宫村绘美拉开宫村了介对面的椅子坐下,“离婚吧。”
“你对我是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了。”
“有什么感情,”宫村绘美冷哼一声,“被骗也能算有感情?”
宫村了介笑了起来,他用手指敲着易拉罐的边缘,“被骗?但是我看你被骗的也很开心啊。八云绘美,问问你自己,骗你最多的是我还是你自己?”
绘美撇开头,不再看即将成为前夫的这个男人,尽管她抱紧双臂,声音维持着平静,但剧烈起伏的胸脯和双肩暴露了她的情绪,“……滚出去吧。”她说。
他站起身走向玄关,但是稚嫩的童声停滞了他的脚步。
“爸爸。”
直到门砰地一声关上,宫村了介的目光也没有看向慎。金鱼仍在鱼缸里无声地打转,一串泡泡从它的嘴里吐出升上水面破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