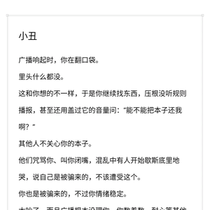对啊,我是为了什么而开口,又是为了什么而发出声音的呢?
————
你不会真的觉得,站到‘超高校级’的评委面前然后把他们晾在一边,用他们宝贵的时间想你脑子里那些有的没的的事情是个好主意吧?
我当然不这么想……!
那你为什么不张嘴?
……因为、爸爸和妈妈都让我闭嘴。
你面前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不是的。
那你起码说点什么也好啊。
…………张开嘴的话,肚子里的酸液就会涌出来。比起勉强自己说些什么,还是起码不要弄脏评审室的地板吧。
————
上次泛起如此浓重的呕吐欲是什么时候?
一天前?三天前?一个星期前?记不太清楚了,倒是医生一边开着药方、写那些根本就没人看的医嘱,一边把“试着不要频繁呕吐”之类的话翻来覆去地在嘴里滚了又滚的时候,自己却只是因为医生的视线和气味就快要吐出来了这件事又一次随着酸液一同被卷了上来。那时从问诊室尽量保持着脸色逃了出来的自己甚至还在为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体面这种不足道的小事而窃喜,尽管下一秒就被火山爆发预兆一般的呕吐欲推去了洗手间,但想来如果被问到:“最近发生的一件让你开心的事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的话,诚实的孩子应当回答:“没有在医生面前吐出来,很有成就感”。
然后呢?然后是……拿着药回家,发现存着还没修完的音乐的电脑被砸坏了,家里空无一人?还是爸爸妈妈又在吵架,连门都不敢进?还是干脆在电车上睡过了,又挨了妈妈一顿骂?究竟哪个才是那天从医院离开之后发生的事情?对了,去医院又是几天之前的事情?这几天以来,自己见了爸爸几面?妈妈又几面?吃了几餐?每餐吃的什么?有没有按时吃药?练习了几首歌?吐了几次?……
……
试图以分散注意力抑制呕吐欲的计划最终以贪吃蛇拐了个弯转了一圈咬到自己身上一般的方式宣告失败,也自觉这种时候在脑海里反刍这种事情根本对眼前沉默的窘境根本于事无补——
我颤抖着移开捂住嘴的手,舌头狠狠地抵住牙齿,用尽全身的力气弯下腰,捏了个手势——行了个引人发笑的礼。
————
你还要这样一言不发到什么时候?起码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我会的。
评委们已经露出不耐烦的眼神了哦。
我又不是没看见……!!别说了!!
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开始唱的话,还有那么一点可能能赢回评委们的欢心哦?
……、…我会努力的……
————
那么,来想点关于唱歌的事情吧。
你最初开始唱歌,究竟是抱着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又是以什么为目的的呢?
想要作为唱见,在大名鼎鼎的N站上冲上日榜,或是作为新秀以前无古人的速度杀入殿堂级别?
不是的,我又不是只能记得一两年事情的金鱼……。而且谁会为了这种超具体的目的而突然开始唱歌啊。
想要在众人面前出风头?想享受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我,没有。……不如说,我从来都不喜欢。不是的。
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才能,证明自己并不一无是处?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
…………
啊——也就是说,唱歌对于你来说就是“救命稻草”一样的存在吧?这样可不好哦。
我没办法……。
是是。
————
我当然也知道,如果谁把什么东西当成自己生命的唯一支柱并把自己的一切都往上堆砌,失去它的代价将会大到他完全无法承受。
但我别无选择。
——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从小体弱多病的我在和同龄人玩时总会感到力不从心,成绩也不够好,更是不够聪明,即便朋友们既没有嘲笑我也没有欺负我更没有不耐烦,但我的自卑仍然在沉默地发酵着。为什么是我呢?我就没有能够让人喜欢的地方吗?我只能是个累赘吗?我也能因为什么成为足以让谁自豪的人吗?所以我哭着去找爸爸妈妈。他们和我说,伊织的声音很好听,可以试一试唱歌。
所以我从七岁那年开始唱歌,一唱就是八年。
这八年里也许我没有变,也许我变了,但爸爸妈妈一定变了许多。
他们说好会永远爱对方、会永远爱我、会再要一个孩子、会出席每一次有我的节目的,我也和他们说好,我会永远爱他们、会永远努力、会做个好孩子。
但也只是说好而已。他们并没有永远爱对方、并没有永远爱我、并没有再要一个孩子、并没有出席每一次有我的节目的集会。他们变得愈来愈忙,他们之间的争吵变得愈来愈多,他们愈来愈少地爱对方,愈来愈少地爱我。
是因为我做得不够好吗?即使他们并不和我说什么,但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试着接触了网络投稿,试着去参加歌唱比赛,试着去勉强自己。我不知道我是否做错了什么,但是我所做的并没有起到效果。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做得还不够多,做得还不够好。所以我更加地努力,更加地勉强自己。
爸爸妈妈好像每周都要说离婚的事,我也开始每周都会呕吐。但是我没有勇气没有精力没有时间说,因为如果说了的话,只会加剧他们的争吵,只会更得不到爱。
然后,一切都朝着不可挽回的方向发展了,我却才回过神来。
父母之间的争吵愈来愈频繁,我的呕吐也一样。我的作息和饮食开始混乱,嗓子也因为过于频繁的呕吐而开始发疼,发出声音时像是撕裂一般痛苦。我依稀记得我在来到这里之前最后一次见到他们争吵,我拿出全部的力气求他们不要再吵我会做个好孩子,他们却齐声让我闭嘴。
————
评委们显然不会知道面前这个走上来之后就脸色发白满头是汗的女孩子究竟在想些什么,她只是死死地攥着话筒,用力到指尖发白;这个女孩子其实也并不知道面前的评委们其实看过太多像她一样,因为或主观或客观的种种而被推到这个位置并因此在他人的援手或是悔悟抵达前就飞速自我毁灭的可怜人。他们对此只是又一次长叹,然后在手中的纸上稍作涂写。说到底,人类仍然是脆弱的生物:尽管智力以其他形态的生命无法企及的速度上跃,精神却没能一起变得更加强韧,维持了千百年之久的原地踏步,因此无论何时人类还是无法挣脱束缚,也正因此人类才仍是也只是人类。北极熊不属于雨林,热带甲虫一生都不会知道什么是冰,人类却会强迫自己或者他人前往本不属于他们的栖息地。于是感受到了这里不属于自己,自己不属于这里的野兽会试图逃离,试图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地方,人类却只能怀抱着自己视若珍宝的知性在痛苦中挣扎,越痛苦越挣扎,越挣扎越痛苦。
评委们开始交头接耳,这也是难免的事情。头顶的时钟在这落针可闻的安静一室内已经三十有余次宣告了时间的流逝,而受试者的第一句话到现在都还没能撬动她那紧闭的嘴。天才们往往优秀得千篇一律,他们的努力好像标好了价码,总能从命运的手中换到对应分量的果实,所以他们平视命运,甚至压过命运一头;而在迷茫与混乱之中乱冲乱撞,眼前看不到路的人,他们各有各吐不出口的滑稽与苦衷,或头破血流,或碌碌无为,或一步之遥,或终于苦尽甘来。奈何人们注定只会去欣赏画布上被精心涂抹出的色彩,那些调色盘上马上就要干透的颜料,被揉成纸团的废作,很快就会被水洗去或者被扔进垃圾桶里,不再有人关心。当多了画板上的颜料或是纸篓里的废作,想要当一次成画的难度谁都明白,所以他们也许是在最大限度地给予她站上画布的耐心。
————
所以,你就是来这个世界顶级的舞台现洋相的?
…………才、不是……
你这不是根本连准备都没做好吗。
…………嗯…
所以你啊,一开始为什么会想成为超高校级?
……说不定,如果我能成为超高校级的话,爸爸妈妈还能重归于好……爸爸会道歉,妈妈也会原谅他。然后……
你明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
快说点什么啊,马上就要被赶走了哦?
……你、自顾自地说了这么多……你到底是谁啊!!
——我就是你。看来就到此为止了呢。
——我猛地抽气,抬起头来,胸膛里的那个声音却已经消失了。
无论如何也要殊死一搏,我第一次开口,即使大脑一片空白。
“那个、我是……”
“山鹿伊织小姐,对吧?我们感到非常抱歉,很显然,你的状态非常……令人担忧。所以,还请进行一段时间的疗养再来尝试吧。我们希望在下次审核中见到你的身影。”
————
然后呢?我再也没有听到过那个声音,再也没有听到过爸爸妈妈的声音,再也没有听到过其他人的声音。
等我再次清楚地意识到我身处何处时,我正写下疗养院合同上名字的最后一笔。

下雨了。
街上湿热的空气和办公室的比起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一定要说的话,大概是那小小的屋子里要加上旧年尘土和人行走坐卧时候毛孔吐出的油脂味,而室外沉沉压着刺鼻的工厂废气。无数从那些林立的烟囱底部升上来的颗粒被水汽裹挟着,扒上没能被雨伞遮住的裙摆布料,实在是让人心情好不起来。我在飘洒的雨丝里加快了脚步,只想赶紧回家脱下这身被汗水和纤维织就的衣裙。
忙碌又烦闷的一天本来该在这里收尾。
如果不是在打开浴缸的水龙头之后,才想起浴室多了那一双眼睛的话。
有规律的水声从身后传来,我一手握着散开的头发回过头去,是安德莉雅在用她的尾鳍轻轻拍击着玻璃缸的水面。她看上去有些无聊,也许是因为我还没来得及在水池里布置一些小玩意的缘故?我没来得及更进一步发散思维,而人鱼从水里探出了头,脖颈上的鳃盖在水雾里一张一合,她的声音空灵又奇异,发声的方式像是在弹奏空气,我却奇妙地听懂了。
她说,吉......里安。
吉莉安,要用舌尖抵着上齿。我回应道。
她点了点头,再一次念出了我的名字。再一次,再一次。
浴室的环境狭小而封闭,她的声音在瓷砖间回荡,就像是在礁石环绕的海底呢喃。实不相瞒,我其实有些微微的好奇,属于人鱼的话语只会携带它本该有的一点信息,他们的歌声却如此......让人迷醉,仿佛用来与人类交流的只是喉咙,却拨弄灵魂的弦来歌唱。安德莉雅,一条仅仅在水缸里生活了四年的人鱼——而我那天偏听到是倒悬的冰刃下翻卷倾泻的巨浪,有万顷天光撕裂波涛,于是漫天星汉也映在海面。
我突然想,也许我挣脱一切后的目的地不再是这里。
耳畔回荡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她不再张口,只是歪着头好奇地盯着我的脸。啊,是回忆让我下意识做出了什么夸张的表情吗?我揉了揉脸,踏出浴缸,带着淅沥的水珠赤脚向她走过去。人鱼的尾搅动起水来,她微微晃动的躯体和玻璃上倒映的我的裸体重叠在了一起。安德莉雅的眼睛晶亮得像是切面精妙的钻石,闪烁着、反射着我的渴望——跳出那些死气沉沉的规矩和命运,走到只有”我“才能到达的所在。
我那时和安德莉雅认识的时间还太短,因此忽略了一些事实。
钻石是不会倒映出影像的。
那是”我们“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