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后的最后,经历了曲折的9天,诸位游客终于解开了福音镇的谜团,重新回到了“现实”。
恭喜各位,度过了一个平安的假期呢。
企划六期已经结束,更多后续信息将在企划群内及微博公布,敬请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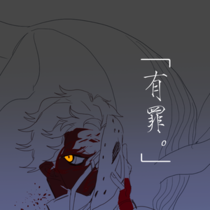


(字数:3446)
丢失了大量log的我,姑且把写一半的先发出来去写别的了(卑微。
“还给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嘶哑怒吼着的那东西,无论怎么看都只能被冠之以怪物的名号。
皮肤严重烧损,只勉强存留着人形的外观,肢干因为脱水而枯凋谢扭曲,陈年遗落却鲜艳如新的火灼痕迹在糜烂的躯体上长蛇般攀爬盘绕。
想必是遭遇事故时已紧紧烙印在背后的巨大十字架,事到如今再也没法与肌肤和衣物分离。滴落地面的水迹呈现出荧光的污红,或许是泪水夹杂血浆而形成的混合物。
它……然而我却依旧想用“她”来作为称呼,那位曾经音容宛然的姑娘,站在黑黢黢的,兽口似的大楼入口处,悲恸无助地发出惨叫,对向无法容纳她的残酷现实,乞求着绝不会朝如今的她伸出的援手。
梦魇般离奇的现实,就像是冰冷的篝火,刺破了覆盖夜空的黑暗,在我们讶然回故的视线中飘摇飞散,熊熊燃烧,终于化为流萤般无可捉摸的光点。
披星戴月返回旅馆的途中,我小跑着缀上森山雅人的影子。这位自称警员的青年身量伟岸,赶路时素来一心一意,坚实有力的髋带动着长得晃眼的双腿,信步前行也有一骑绝尘的架势。
“呼……没想到能遇到那种东西啊。雅人哥是对灵异事件绝缘的体质吗,感觉类似的场合你的反应都非常迟钝呢。”
“或许……是吧?”察觉到我想要交谈的意向,森山雅人体贴地放缓了步调,迟疑地说道。旋即摇头一笑。“在我看来,反而是大家的表现都太激烈了。”
“感知不到冷热的变化,嗅不到奇怪的气味,连最后的那个……”光是回想起夜色中溃烂流脓的怪物,以及她可能的前身……我便不由自主皱起眉头,忍不住问道。“也没有看到吗?”
他无奈苦笑:“最后的那个,倒是看到了……但其他东西似乎我都不太敏感。”
“可真是令人羡慕的体质啊~”我半数是真心实意,半数是试探性地感慨。“——是天生的吗?”
“大概是吧?”他自己也不太确定地说。“这个,怎么说呢,也没有什么办法来检验……只是,中学的时候,有一阵子不是很流行那种心灵感应之类的东西吗?还会附加各种不知是真是假的灵异体验。嗯……从那个时候起,我似乎就在学校周边,所有会举办这种类型活动的组织的黑名单上了……”
时至今日,回忆起青春时期的糗事,他竟仿佛仍会感到不好意思,只是略微感应到投诸己身的促狭目光,便本能地偏转头颅避开。若非耳垂堪堪维持着固有的肤色,还尚未灼烫发红,简直要让人怀疑他是否被从某段青涩年华中生生铲起,来不及度过那段按部就班习惯成长,也习惯周围不断变化的视线的岁月,就忽然一下长成了自己都暂时理解不了的大人。
超龄的高中生叹了口气:“因为在参观部活的时候,一个人游离在气氛外,还搞砸了那次招新……”
他似是感到迟来的好笑,而又犹然铭记彼时场景的无措与惭愧,勾着嘴角摇了摇头:
“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灵感这种东西。大概我就是,完全没有灵感的那种人吧。”
“哈哈哈哈,我都能想象得到那些孩子脸上挫败的表情了。”捧场我是绝对配合的,当即就不顾夜色的沉默而笑了起来。“想来雅人哥就是根本不懂顺应着氛围表演或者说些谎话的人啊~”
“可能是因为没有必要?现在想来,那时候我也是够不懂事的。”
回忆往昔时,他目光柔和,嘴角挑含浅浅笑意,使人不禁产生如何冒犯他都不算过界的错觉——当然,我想那也仅仅只是错觉。当那浅色瞳眸映衬冷银的月光,因失神而朝向黑暗空空望去时,某种难言的寂然便径自发散了。沐在宛如隔绝空间的这一方微妙气氛中的他,看起来与正确切身处的这个环境,相距甚远,明明启唇诉说的是专属于自己的往事,却又像在翻看书本念读不相干的他人的故事。
我及时打住跑歪的危险思想,浑不在意般的拍了拍他的肩膀:“嘛,嘛,倒不是坏事,这个世界上的诈欺师和演员已经够多了,偶尔诞生些认真的人来支撑柱石,也是很有必要的。”
——想来也是,那压迫感十足的东西,硬生生划破地狱的缝隙挤进现实,要想无视可太难了。
便是再如何散漫粗犷的神经,也不至于熟视无睹,强行遗漏吧。
确认过这位警员姑且还有基本的辨识能力,不至于一头扎进他所看不见的深渊,某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催促着我转移话题,好避开他脱离回忆的气氛后突然的回眸。刚巧,我也不愿过多深那令人不适的场面,便若无其事与他并肩同行,问出了在意至今的另一个问题:
“说起来,森暎先生好像也非常不相信这些东西。不管遇到什么奇怪的现象,他都在拼命努力,试图用常识去解释,去说服自己。不知道今晚过后他会受到怎样的冲击啊。”
“森暎先生……”果不其然,森山雅人闻听那个名字的瞬间便一时窒住,忘了适才凭空跳过的追忆,张开口想要说些什么而又难于编织言语,许久方才复读了自己,缓慢滞涩地凑出半句食之无味的评价。“森暎先生……除了有些冒失之外,某些地方倒还意外地蛮可靠的,吧。"
“……”我盯着他,他便佯作不知地看向远方,论及装傻倒真的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师。我一方面是经过这段时日的捶打,也算习惯了,另一方面是实在拿这软硬不吃的态度没有办法,便只好勉强展现出敷衍的演技,脑袋转向另一侧,轻飘飘地念叨着:“……看来好像不是那样?嘛,确实,他也是雅人先生‘不要太信任刚认识的人’范畴内的存在啊。或许他的本质,并不是表现出来的这么简单吧。再怎么说……好歹也是成熟的警部呢,我可不相信他真能从里到外都一尘不染。”
“22岁就当上警部,森暎先生也相当了不起。不过……”他话说一半,再次停顿,老毛病地留着欲言又止的另一半叫听众自行揣测。“……不,没什么。说到底,我也并不是非常了解他。”
午夜时分,深重的暗沉沉压盖在丛林上空,包裹福音镇的这片黛青色,如同守卫着洞穴的龙的臼齿,在万籁俱寂的时点呈现出异样的冰冷。
实在不擅长在蒙昧林地埋头跋涉,应了森山雅人突如其来的邀请,随他闯入厚纱般徘徊着腥浓瘴气的郊外,一言不发,也不明目的地快步行走了将近一个钟头,我再也挪不动脚步,也无力说出完整的句子,软绵绵地举手示意,随意倚靠了块坑坑洼洼的粗粝树皮,撑着膝盖呼哧呼哧粗重喘气。
“果然是有那什么结界在吗……”我抬手抹去额头淋漓滴挂的汗珠,并不意外旁边四处观望的森山雅人,与出门时毫无差别的干爽模样。洗得挺括整洁的制服衬衣,历经林木重重剐蹭,竟仍旧一尘不染,发散着皂液浅淡朴实的香气。比起警察,他果然更适宜报名参加铁人三项——不知道是第几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一波三折地长长叹气。“……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边际啊。就像是无限循环的迷宫,不,要更加无序一些,简直就是被撕碎后随便揉在一起的拼图游戏。”
“是啊……这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简直像是真的是有什么东西存心不让我们离开一样。”森山雅人同样微蹙着眉,颇为矜持地表露出一丝忧虑,但或许是层林遮掩,阴影深重,他压在帽檐下的表情总叫人感到莫名森冷。
“无论如何也没办法用唯物主义世界观解释啊。”我喘匀了气,撑直疲倦的身体,仿着大侦探的姿态将食指翘起。“阿夜平时会读很多推理小说,我也被迫懂一点梗,我听说啊,推理的时候,如果面前的所有路都走不通,剩下的那个选项,即使再不可思议,都只能是真相了。”
“唯物主义看来在这里不适用,就像是真昼你们不断遭遇的那些怪事一样。”他平淡地说,好像诉说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旋即目光沉了沉,略微沉默后征询意见般望向我。“真昼觉得,现在……还剩下哪条路呢。”
“……我们,被神隐了啊。”我斟酌着用词,同时关注他的反应,做好情况不妙就迅即撤退——但恐怕也没什么意义——的准备,慢慢地说。“消失的,果然是我们才对吧?被抹除了在真实的那个世界的存在痕迹,从所有其他人的面前活生生消失,被无法理解无法抵抗无法言说的,什么东西,带走了的,是我们才对吧……?”
“神隐………吗。”
像是被输入正确关键词的计算机,或者更失礼,也更且贴切一些,像是……忽然被戳中了痛脚的,本应只具有简单反射的软体生物,那湖泊般清透的眼眸里,漂浮着的幽黑瞳孔陡然收缩。真实的森山雅人因而如同外露于水面的冰川,因一瞬的失控而棱角分明。
他几乎是用要刺杀自己的力道扶住额头,无论神情、状态还是语气都支离破碎,喃喃地同我所无法目视的惨痛辩驳:
“之前……明明不是……明明,不一样……”
那修长伟岸的身躯竟也有站立不稳,被迫借助外力的时候,他摇摇晃晃地扶住最近的树干,注视着足底的阴翳却宛如正在用目光杀灭一个梦魇。难堪而令人畏惧的沉默持续了片刻,就在我忍耐不住,即将开口打破寂静的刹那,他突兀地弯下了腰,再度起身时手上已握着微微荧光的珠串。
“雅人哥?”
“这是……”
他皱眉看向手中不合时宜的精细腕饰,我举起电筒照过去,映泛出柔和圆润光辉的珠子,的确是曾隶属于某人的贴身物品吧,比起装饰,更像是用途明确的念珠,沾着少许湿润的泥土,陈色看起来并不簇新,但表面受损氧化的痕迹倒很稀淡,遗失时间应当不久。
“这东西……我似乎在哪见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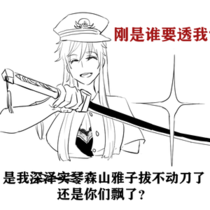
总字数:2026
中奖回礼
ooc有,凭空捏造
#真没转型
温度
水结成冰的温度的零摄氏度。
钻石的熔点是约为四千摄氏度。
人的正常体温约为三十六点五摄氏度。
而泉千里觉得森暎希的温度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大家总是会说“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这种情况。”
不,这次不一样。对方明确地友善地提醒了“我可是会吃人的哦”,并且在千里装傻的情况下摊开来说“可以成为官能小说家”,千里是没有资格说出上面的话来的。
与吹笛人不同。吹笛人带着被他的笛声迷惑的人不知去向何方。而希则是在等着千里, 等着他过来牵着自己的手,将他带进自己的世界里。
温泉旅馆的榻榻米看似会比普通的床更加方便,只是缺少了一些高度差,也失去了一些便利。
好不容易按着网上搜索的步骤一步一步穿好的浴衣被解下来只需要简单的几步。被温柔地托着后颈接吻只要接受就好了,无需思考他是从哪里学的,习得后又是练习了多少次才能变得如此娴熟地就能将自己吻得呼吸频率错乱。
明明比他年下几岁。千里想,人生阅历不同就是不一样的。
将自己交给他就好。他听从着希的话,任由他摆布。无论是坐到他的腿上也好,被放倒在早就被放置好的被褥上也好,近距离看着对方如同装进了一整个宇宙的眼睛也好。语言里没有魔力,尽管在这个荒谬得如同实验箱庭的世界里充满了仿佛是使用魔力才能做到的无法理解的事情是很正常的,只是情感在催化一切。
说不紧张是假的,事实是紧张得要死。正常男人都看过的黄色影片和图片都只是最低级的感官体验,亲身体验的时候谁总是能够保持一贯的平和心态呢。
幸好希有足够的耐心和温柔。他似乎害怕会弄伤自己,所以忍了很久,至少在千里看来是这样的。
希会温柔地,小声地询问他。但这种事情难以说出口,千里只能够支支吾吾地点头摇头,要说一句完整的话都觉得太难了。
奇怪的感觉填满了从里到外的每一个细胞。莫名的兴奋感,快感,痛感,被充满的感觉混杂在一起让他呜咽出声。从未体验过的刺激让他变得更加兴奋。
体内的激素加热了血液,似乎要沸腾起来,让人变得口干舌燥。
他搂着希的脖颈,像是在茫茫大海中抱紧了浮木。他被汹涌的海浪推动着,不知要去向何方,只有自己怀抱当中的浮木是唯一的最后的依靠。
空气变得灼热,因为他拥抱着的是太阳,是光,是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
长期家里蹲的后果是千里体力远不如为作为警察的希,从身材上也显得瘦弱一些。更重要的是他完全打不过希,在认清了这一点以后他并不打算要和他争什么了,顺其自然,什么都好。
他不抗拒什么,他接受着来自年下有力的狂乱的冲撞和在他身上故意留下痕迹的啃噬,接受着他的索取他的情感。
每当千里感觉到自己漂浮在空中没有实感的时候希总会拉着千里的腰让他迎合自己让他降落。这样的起伏对于千里这样的完全新手来说过于刺激,他咬着下唇想要把让人羞耻的声音全部吞回去,但只要是希凑过去和他接吻,就会无法避免地会有些许的声音从唇齿之间漏出。
这无疑是最好的催情剂。
也许是刚刚说过的话激怒了他,也可能是因为别的,总之千里觉得和平日里接触的希不一样,但他确实也还是森暎希。
千里的脑袋里已经无法思考其他事情了。他觉得自己在颤抖,被用力地拥抱着也无法抑制这样的激动。
我会很努力的。
请更加喜欢我吧。
他像一只小动物一样瑟缩着接受陌生的没顶的快乐,甚至小声地啜泣。快感似乎带走了他所有的体力,连悄悄从眼角划过的泪痕都没有去擦。希凑到他的耳边和他说了一些话,千里除了震惊以外还有害羞,耳根开始变红。他无力地用手臂挡着自己的脸,不想看希,也不想被他看到。
希非常体贴,似乎能读懂千里的想法。
于是千里只能撑着梳妆台,把脸埋进臂弯里,努力不在意在他身后的希。只是人在闭上眼以后,对四周的注意力就会加强,也会变得更加敏感起来。
保持着一个羞耻的姿势,千里可以感觉到体内的一团热量。它霸道地进出,带起了让人面红耳赤的黏腻的由液体产生的声音。 擦过敏感点的时候千里的腰就会塌下去一些,希揽着千里的腰固定着,俯下身去亲他的脊背。细碎的湿润亲吻如同夜幕中的星星一样都落到千里的身上。漂亮的安静蛰伏在背上的蝴蝶马上就要展翅飞翔。脊柱是最脆弱的地方,就这样暴露在他的面前。
如果可以,我会永远相信你的。
所以如果你在背后伸出手扼住我的脖子,我也不会反抗。
千里啊。
抱着他的可爱的小恐龙钻进他臂弯里跟他撒娇的人说。
我会保护你的。
所以没关系的。千里想,要给予足够的信任。
将背后交给你,和你一起重新闯进古怪又危险的地方。
只要你和我在一起。
最后千里体力不支被希抱着一起倒在榻榻米上。汗涔涔的皮肤贴在一起仿佛拒绝两个人再分开。他们接吻,交换唾液。千里看着希的眼睛,他的眼里全是他。
请多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吧。
请多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吧。
在这个没有办法能够获得实感的世界里,只有你有重量。请不要放开我吧,我会很努力地想办法的。
请不要让我做不听,不看,不说的人。
我已经感觉到了寒冷。
算不上是全程在哭,只是眼泪时不时在流。是控制不了的泪水,也没有空闲时间去擦干。眼睛应该红了,总感觉有些干燥,千里闭上眼,希望能够缓解一下。
他感觉到有人在亲他的眼角,也有柔软灵活的物体轻轻地扫过泪水留下的痕迹。
除了躺在他身边的人,再无其他。
为什么哭了呢。
在碰到这么多灵异的事情的时候都没有哭。仔细想了想,在普通日常里,千里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哭。为了不表现出自己无用的一面,强行将泪水留在眼眶里,睁大眼试图让它蒸发。
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也许是因为希的拥抱吧,虽然接触的时候感觉皮肤是凉凉的,但是是他让自己变得燥热,变得无法思考。
我的体温是零下二百四十八摄氏度。
是你将我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