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生异世界,但现代》
你过去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冒险者、吟游诗人,骑士,还是村民?
人类,精灵,矮人,还是人鱼或龙?
……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对吧?
请享受平和的现代社会吧,亲爱的。
本企为文画企,请确保自己至少拥有绘画或写文中的一项能力
已圆满结企,感谢大家的陪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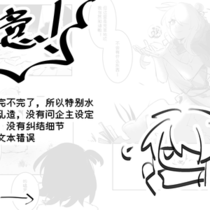




相信我,下半段就能写到游乐场了。
明明只是个非常简单俗套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我塞了好多废话。另外还编造了很多并不清楚的东西,请不要当真。
不知道也没关系的小tips:家里只有艾琳也是奥庇沙人。
一章·下:https://elfartworld.com/works/9599819/
一
双脚踏上石板路的瞬间,一股诡异的熟悉感涌向全身。罗伊低下头,看见破旧的靴子上溅满泥点,鞋带松垮,俨然一副远行多日的模样。他拉紧了身上薄而陈旧的斗篷,裹住肩膀向前走去,早已磨毛的领口扎得他有些痒。他不知道这里是哪里,也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只有脚步毫无迟疑,自动拉着他走向石板尽头的小镇。那是一个阴沉的秋日,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甜味,是干草混合炉火的气味。街道旁的景象影影绰绰,宛如边缘泛白的水彩画,仿佛一切都只是朦胧的幻影。他如同混入其中的一道影子,蹒跚着穿过清晨的广场,径直走向街道尽头。
直到跪倒在井边,罗伊才意识到,他根本就不累,也一点都不渴。
但他还是喘息着,低着头,以一种仓皇的方式用力扶住井沿,仿佛一个穷困潦倒又走投无论的流浪汉,只能以避免摔倒维持住最后的一点尊严。然而当他向自己的内部探寻时,罗伊只感到一种微薄的虚无。他是空的,这张脸,这幅外表下,在面具之下没有更多的东西。仅有隐约的一点点成就感,宛如火星飘摇在谷仓上空那般不合时宜地悬置于他的心头,也像演员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一幕。现在,该说台词了。
“你需要水吗?”
声音从他头顶落下。罗伊抬起头,斗篷的兜帽滑落,遮住了他的大半视线。那人抓住他的肩膀,半拉着他靠着井壁坐下,又往他手里塞了块面包。罗伊抬起手,将脸凑近,嗅到了一丝黑麦烘烤后的温热余香。
“你先拿着,我来给你打水。”她将水桶投入井中,闲聊般与他攀谈起来。“走了很久的路吗?你看起来快晕过去了。或许你可以跟我说说,我可能会知道对你有帮助的事。”
她的语气不含一丝怜悯,就像她确认这只是一件平常的小事。水桶被放在罗伊的手边,垂下的金发在阴沉的天色中显得有一点泛棕。她的围裙上还沾着一点面粉。一只手拨开他眼前的布料,罗伊看到了她灰色的眼睛,或许在眼光下,它们能呈现出更接近蓝的颜色。
她轻轻笑了。“你看起来真年轻。我以前还想过要有一个你这么大的弟弟呢。”
“艾琳娜。”罗伊忍不住叫出她的名字。
然后,他想起了他为什么在这里。
罗伊睁开眼,胸口剧烈起伏。望着天花板整整十秒,他才意识到自己正躺在一张床上。猫咪呀咪呀大叫着冲上床,在他枕边炸成一团,罗伊捂住眼睛,低声骂了一句,翻身坐起打了个响指。刚刚燃起的窗帘角啪地熄灭了。他于是轻轻揉开龇牙咧嘴的猫,将它重新团成一捧柔软的白色毛绒。
真是糟糕的清晨。
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这样,也有很久没再想起那段回忆了。不是他记忆中最惨烈的一次,也不是最血腥的。恶魔,某种程度上的不死生灵,即便他被消灭时不过三百来岁,他也已经执行过无数相似的计划,镇子、村落、城市,都曾在他的操纵下土崩瓦解,无数平凡善良的人因此丧生,抑或扭曲出可怖的嘴脸,对彼此兵刃相向。这之间并不应该有什么不同,然而在此之中,他也最不愿回想起这一段。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起,也许是因为前天晚上他回拨了那个电话,但那只是一时软弱。当艾琳的声音隔着信号传来时,他几乎感到一种茫然的不知所措。只有她未能说出口的诉求是他清楚知道的,她所希望的不过就是能够常常见到他这个漂泊在外的弟弟,哪怕只是多练习几次也好。然而艾琳娜·贝尔福德,无知的、失去记忆的、残酷却温柔的艾琳娜,你能够回答吗?一个人要怎样才能面对一个他杀死过的活人?
他不会如此询问,艾琳也不曾给过他回答。只是在意识的某个角落,他始终都无法忘记那双灰色的眼睛,它们沉静地望着自己,在火光中,比起蓝色,或许更接近金色。他可能要凑近些才能看清楚。
“是这样吗?”幻想中的艾琳轻轻微笑,问他:“这是什么时候的记忆呢?”
罗伊猛地从床上站起身,跌跌撞撞地走进盥洗室。他感到疲惫。如今,他早已失去恶魔无尽的精力与自愈能力,但他仍然需要工作。今天不是休息日,可能还是他最满的一天。罗伊一边刷牙一边点开手机里的日程表,上午他要去市中心参加新年份的红酒展示会,然后赶去老城区的两家餐厅与经理谈合作,下午他得接待从新奥尔良来的买手团,晚上还有个对红酒收藏感兴趣的富商客户,商谈地点约在了海边的私宅。还有奥庇沙,前天晚上论坛上提到了有可能出现异常事件,他还得时刻关心论坛……
他重新感到一种安定与镇静。工作能将他重新锚定回现实,尽管销售的某些行为总让他想起恶魔的诱骗,但至少红酒是这里唯一可能出现的红色。他也想过要不要换个行当,但在工作时看不到红色也总让他有些焦躁。事实证明,这就是他唯一能做、也是最适合他的事。
罗伊穿着妥当时,门铃响了。也许是他买的猫砂终于送到了。出差时他走得急,只记得带了猫,却少带了猫用品。
他打开门,带着点棕的金发出现在他的眼前,与梦中如出一辙。
艾琳歪了歪头,扬起眉毛:“罗伊,你是不是又不看猫眼就开门了?”
二
艾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流星雨结束,最后划过的光辉却如伤痕般深深印在她的视网膜上。电话挂断,仿佛将她独自抛至水底,周围只有长满青苔的沉默石头。艾琳握紧手机,松开,再握紧。然后她跳了起来,动作比意识更快。她拉开衣柜,把最常穿的毛衣、两条牛仔裤和那双走很远脚也不会痛的鞋塞进行李箱,缺乏计划,没有清单,甚至忘了她平时随身携带的祷告本。她把化妆包胡乱丢进去,连护肤品的盖子有没有扭紧都没检查。她又塞进去两件薄衬衫,只为有备无患。
她必须要走,她要问清真相,她只想知道为什么自己现在才动身。
艾琳隐约记得,在感恩节的餐桌上,罗伊随口和爸爸说过,一月起他就要去个新地点驻扎,那里叫……埃芬市。她立刻就订了车票。她还翻出一张圣诞节的就贺卡,那是罗伊刚刚工作时寄来的,附赠两瓶红酒,其中之一还被妈妈珍藏在橱柜里,舍不得开封。卡片背面印了logo和公司地址,顺着这条线索,艾琳搜索到了公司官网,在客户服务一栏中找到了一个电子邮箱。
她没抱什么希望,已经做好了要在埃芬市大海捞针的准备,但还是发去邮件,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希望得到罗伊现在住址的请求,一到清晨,她就前往教会学校请假,却无法告知时间长久,艾琳知道这与请辞无异。“我们还能找新的老师,”神父对她露出安慰的笑容,“但如果你愿意,你随时都能回来。”
艾琳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回来。
出了门,手机弹出一条通知。公司发回邮件,语气冷静却略带关怀。对方告诉她,出于保护隐私的缘故,他们无法提供具体的住址,但可以告诉她所在街区的名字。同时,他们也会将她的来信转告给罗伊。于是,直到坐上长途大巴,艾琳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将决定告诉丽娜。
她拨通电话的时候,信号有点不稳,车窗外不断掠过连绵不绝的的原野和冬日尚未褪尽的灰褐树枝。
“我要亲自去见罗伊。”
“现在?”丽娜的声音有些惊讶,随后便了然起来。“也好,你想去就去吧。别担心爸妈,家里还有我和帕克,没了你也不会炸上天。”
“……谢谢你。”
“艾琳,别想得太多了。”
她挂了电话,把头靠向窗边。车厢里的暖气有些热,艾琳解开围巾,昨晚起便消失无踪的困意终于席卷而来。
在梦中,她看见从未见过的城市。那不会是埃芬市,也不是她曾见过、听说过的任何地方。天空被淡金色与暗紫色分为两层,远方的地平线上耸立着白色的高塔,街道上走过穿着破旧斗篷与镶银长袍的人,孩子们在飞舞的花瓣中嬉戏打闹,空气里回荡着银铃般的细碎笑声。一个人走在她身边,亲昵地牵住她的衣角,五官却如搅动的油墨般晦暗不清。艾琳伸出手,想要触碰他的脸,钟声轰鸣起来,它们喊道——
“终点站,埃芬市到了!”
她猛地睁眼。车已经停下,零零散散的其他乘客已经开始收拾行李。混乱的梦境如同潮水般迅速隐去,消失在她视网膜后的某块黑暗之中。艾琳提起行李箱走下车,重新踏上现实的土地。
艾琳原以为,罗伊会住在那种配有门禁、靠近市中心、能看见海景的高档公寓里,因为他上次穿着的衣服看起来就像是那样。但跟随着指路,走到一处略显老旧但整洁的街区时,她竟在心中松了一口气。从这里走出十多分钟,似乎就能到达海边。公司给出的范围意外狭小,她一路询问,很快便得知街道尽头来了个短租客。红头发,金眼睛,来去匆匆,表情有些捉摸不透,性格却意外温和。一听就是罗伊。
走到街尾,一栋双层的木造民宅映入眼帘。一楼是一家卖日用品的小店,二楼有个独立入口。楼梯年久失修,踩上去时还会发出轻微的吱响。
艾琳在门口站了一会,调整呼吸。随后按响了门铃。
三
恶魔的记忆于他而言,最可怕的不是他为残暴与恐怖兴奋,而是他从未因此兴奋过。他并非为了娱乐毁灭和残害生命,那种行为中没有快乐,什么都没有。他只是如呼吸的本能一般,摇唇鼓舌,伸手便将人们送往绝望的明天。就连成就感也只有浮在表面的浅浅一层,触碰就会开始皲裂。恶魔没有荣耀可言。
门打开的瞬间,罗伊的思维短暂冻结。他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出任何事,直到艾琳伸手推了他一下,力气不大,却让他退后了好几步。艾琳侧身进来,关上门,自然得就像回到她自己的家。
“你住的意外是个生活化的地方,”她环顾四周,轻巧而娴熟,“我原以为你会住得很精致。”
他站在原地,喉咙发紧。艾琳回头看他,眼神平静:“你希望我离开吗?”
“不。”他不由自主的开口,然后猛地捂住嘴。罗伊抓起外套,走回门前,迅速穿上鞋子。
“你可以待在这里,但我今天很忙,我要出门工作了。”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身后传来一声猫叫,仿佛在嘲笑他与逃避无异的行为。
罗伊今天真的很忙。上午,他站在展台前,脸上挂出职业微笑,向客户解说一款西班牙进口的干红,描述他的黑莓香和一丝的甘草气息,以及醒酒四十五分钟后会出现的更柔和的回甘。他把酒斟入酒杯,注视着对方满溢赞赏的眼睛,心知这一单多半已没了问题。然后,他分别赶到老城区的两家餐厅,换了两种口吻:对年长的经理要表现出温吞和礼貌,对年轻的主厨则可以多谈论些品酒搭餐的经验。而下午他比上午做得更完美,晚上也是如此。他熟练地调节语气、节奏、话题,偶尔还会注意韵律。他能感到自己被重新运转起来,回到正轨,回到那台功能良好的机器中,成为数千万螺丝零件中的一员,效率优良,机器便嗡嗡作响。
但他心不在焉。晚上回去时,屋里已经被收拾过一遍。艾琳没有动太多东西,但散乱的文件被重新码放整齐,沙发上的毛毯叠得四四方方。猫粮袋子和新到的猫砂都放进了收纳筐,就连猫——他没给猫取名字,所以猫就叫做猫——都对她叫得更为甜腻了。罗伊走进门时,艾琳正背对着房门,挽着金发,站在厨房里擦着碗。听见他回来,她侧过脸,低声抱怨道:“你要是不回来吃饭,倒是联系我一声啊。”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有段时间艾琳喜欢上了烘焙,经常窝在厨房里捣捣鼓鼓,混合甜蜜的奶油与铺满砂糖的黄油,坐在小板凳上紧张地盯着烤箱内的面团膨胀又膨胀。每次做完,她都会叫他来试试味道。一开始还会太甜或是烤过头,但渐渐地,那就成为了周围最有名的美味,艾琳时常将饼干与蛋糕分给附近的孩子,而罗伊总能独享最新鲜出炉的一份。
这就如同一个幻梦,仿佛他从未离开过家,拒绝过任何联络。他还身处路易斯安那州的那个小镇,每天都能回到这个散发着淡淡甜香气的房间,然后第二天再出门,走到社区学校里去,就像艾琳曾期望过的那样教授绘画。但当他低头寻找例画时,他只看到那张被艾琳从画本上轻轻扯下的涂鸦。
他做不到就像撕下这一页那样抛弃那个曾为恶魔的他。
艾琳平静地等待着,没有要求他做任何事。但罗伊清楚地知道,艾琳娜·贝尔福德,温和却固执,对认定的事绝不退缩,有时还会爆发出惊人的行动力。她执着地渴望揭开他潦草的掩盖,却丝毫不考虑自己是否能够承受背后的真相。他无法理解这种执着。罗伊一度甚至动用过恶魔的能力暗示她放弃,最好尽可能地遗忘掉一部分的自己。如今证明,这似乎也只能起到短暂的效果,而现在他也不愿意再用第二次。因此,他也只能继续度过第二个、第三个忙碌的今天,因为他还尚未做好准备面对那双眼睛。
他走过已然倒塌的教堂,火焰燃烧起来,他闻到烧焦的木块和血肉被焚烧的味道。他走向倒在血泊中的人,看见她仍能抬起头,灰色的眼睛在火焰的映照下,显现出近乎与他等同的金色。
“你是个恶魔。”她清晰地说。
艾琳把罗伊从梦中晃醒了。第一天晚上,他们就争论过睡觉的问题。艾琳坚持说,如果罗伊要去睡沙发,她就直接躺在地板上,于是他也只得妥协,与艾琳一同占据这件屋子里唯一的床的两侧。看见他睁开眼,她重新躺回去,手却还贴在他的脸上。她问:“你做噩梦了吗,罗伊?”
我梦见你了。罗伊摇了摇头。艾琳低声叹息,摩挲了一下他的耳垂。
“罗伊,我不是说你不能逃避,但你拖了太久了。为什么离开家?为什么总是不接电话?哪怕偶尔联络一下也好,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
她的声音在黑暗的房间中显得细碎。“是因为……你讨厌我了吗?”
“……不是。”他情不自禁地开口,便听见艾琳小声笑了一下。
“你只会否定这个,”她说,“如果你能肯定,我反而能够知道原因。”
罗伊沉默。她又说:“我们需要谈谈,也许应该在某个能放松的地方。你明天有什么安排吗?”
今晚,奥庇沙论坛上的通知浮现在罗伊的脑海中。“游乐场……”他开口道,“我明天要去游乐场。”
艾琳小声笑了。“那我们明天一起去吧,罗伊?”
他点头。艾琳抽手离去。指尖在黑暗中轻轻划过他的脸。罗伊听见她在翻身后睡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