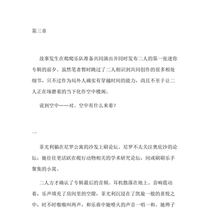《转生异世界,但现代》
你过去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冒险者、吟游诗人,骑士,还是村民?
人类,精灵,矮人,还是人鱼或龙?
……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对吧?
请享受平和的现代社会吧,亲爱的。
本企为文画企,请确保自己至少拥有绘画或写文中的一项能力
已圆满结企,感谢大家的陪伴!

*听着打卡里提到的钢琴曲写完了
*又是一如既往只记得把醋给泼出来就完事了的东西。
*有非常多余的感性描写。
*字数:3252(含小标题及重复的句子)
你知道“唱片”或“磁带”吗?是的,一片中心镂空的圆盘、一个内部由齿轮状的卷盘缠起一卷卷黑色塑料带的长方体盒子。
置于唱针下,在转台上开始旋转。
置于播放器的空槽中,随着咔咔声将带子从一边转向另一边。
——这是A面。
翻转唱片,将另一面置于唱针下。
翻转磁带,将另一面嵌入播放器的空槽中。
——这是B面。
明明在刻录在同一个媒介上,两面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对此,你又怎么想呢?
当然,我知道你已经得出自己的答案了。
现在,分别听听A面和B面的声音吧。
-A面-
黑色的键、白色的键。
纤细的指节、交错的指节。
和音、杂音。
一首毫无章法的乐曲,而后是没有敲下指节却兀自弹奏或修正的琴声,杂乱的音符从下压的琴弦里流出来,乱七八糟地散落在地上——这根本算不上是在演奏。
“啊啊啊啊钢琴活了啊!”穿着校服的男性发出了尖叫声。
“哎?”穿着校服的女性反应慢半拍地歪了歪头。
夜晚的学校,两个毕业已久的学生,和仿佛在呼吸、仿佛在吼叫、仿佛在躁动着的钢琴,空气中充斥着不协和音。假设从内部上锁的音乐室是一个密室,那么,可以明确的是,将穿着校服的男性称之为A,女性称之为B,音乐室内,此时此刻,没有除AB以外的第三个人类,不论死活。
然后——
“唧唧!”密室内发出了第三者的声音。
是一只红松鼠,在钢琴的腹腔中穿梭,将琴弦向下压,将螺丝、弦,甚至是木制的外壳都撕咬得松动而摇摇欲坠,使得有着漂亮黑色皮囊的钢琴内里溃烂不堪,发出失真的惨叫声。
“哈哈,哈哈哈。”男性干笑两声,“还以为真的有鬼呢。”
……
1、2、3、4,5。
无论怎么走,向上的台阶总有盈余。
“你知道彭罗斯阶梯吗?”她这么说了,“透过视觉的错位,展现出不可能的…‘无限’的光景。” ……就像是,现在的状况。
“那是什么?”提问的人已经将脚步迈向阶梯的拐角。绵延无尽的长蛇般的楼梯折出一个新的角,稳稳地承托住了他的鞋底……当然,这只是经过主观加工的说法,事实上,他只是在几乎一眼望不到头的阶梯上又踩过了一层。
“一个有名的几何学悖论。假设我们被困在四维……或者更高维的空间里,假设我们所在的世界受到某人的操控的话……罢了。到现在为止,阶梯数到多少节了?”
“我看到尽头了,但是……”男性犹豫着放慢了脚步。
661、662、663、664,665。
“666。”女性接过了他的话,先一步踏上了最后一节阶梯,楼梯的尽头是一座宽敞的礼堂,里面已经有人了。
“看来我们已经来到阶梯的奇点了。”她笑了笑。
-B面-
黑色的键、白色的键。
无形的指节、不存在的指节。
和音、颤音。
漂亮的韵律随压下的琴弦处发声,一下一下,以《小星星》开始,在琴键上由慢而快地跳跃着,仿佛能看到窗外有流星闪过。实际上,流星从天上撒下来已经是两周前的事了,或许这是两周前的星星的余热吗?杂乱地在琴键上左右跳动的星星仿佛迸发出了灼热的火星子,想伸出手去触碰的时候,星星的温度与音符一同落到了地上,发出了干脆的声音,没有再跃起来。
“这就是那个所谓的自己在弹的钢琴吗?”一个看起来还是能穿上校服的年纪的男性敲了敲陷入寂静中的立式钢琴,就像是在确认某个野生动物是否还有呼吸一样,钢琴没有回应,他就顺势把琴盖合上了,黑与白的齿列被关进了木制的嘴唇中,不作一言。
“它应该还在这里才对,但不清楚具体的对象是谁,就算是寻人寻物魔法也需要具体的媒介……”一旁的男性抓着形状奇特的叶子、蜥蜴的断尾一类的东西,沉思片刻后作出结论:“把钢琴拆了吧,用里面的琴弦或者螺丝钉之类的做媒介。”
“故意毁坏财务罪最低的刑罚是……”一旁的第三个男性正要开口,此刻,钢琴却先撬动了唇齿,音符发出轻快的跃动声。几人看向那架钢琴,琴盖仍是合上的状态。音乐室内的四人并不知道,但这一曲是麦克道威尔的《女巫之舞》,琴壳内未知的世界里正以极快的速度弹跳出一个接一个清脆的跳音,像是音符一个个跳进翻涌着绿色浪潮的坩埚中,飞溅出无数无害的水花。心头鹿似乎正不自觉地随着女巫的舞步而撞得头破血流,好不容易才随着乐曲渐渐缓和的节奏而得以找回自己的呼吸。四人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眼,最终四人中唯一的女性开口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现在要怎么办?”
“不知道,要不把钢琴砸了?”手上捏着奇怪的巫术道具的男性看待世界的方式总是很干脆。钢琴叫嚣着又弹起拉赫的《小丑》,像是正发出轻盈又让人头晕目眩的抗议声。即使琴板盖上了,也能从四处跳跃的音符中明确地感受到像有两只手正快速地在八十八个交错的黑与白的琴键上跑动着,平稳而精准、如节拍器般牵动人的心跳的乐声,就像是面前并非是一个需要他人操纵的乐器,而是一个自行轮转的纸带八音盒,随着不知何人打好孔的长长的带子,吞进去,在既定的孔洞处发出空灵的乐声。
“一千美元以下的罚款、社区服务、缓刑,以及一周的象征性监禁。”似乎对本地法律了解颇深的男性一边说着一边掰出四根手指。
“别的不说,我觉得它弹得挺好的。”唯一称得上是学生的男性发表了中肯的评价。
“那怎么办?钢琴又不会说话,我们怎么知道它想要什么?”捏着蜥蜴尾巴的男性叹了口气。
“或许…它想要的是一场合奏?”女性用指腹摩擦着盖上的琴板,琴壳内发出温和的低鸣声,像是一只正打着呼噜的幼兽。
黑色木质生物轻柔的呼噜声,慢慢地、渐渐地,转为风暴般的嘶吼。当然,一台钢琴自然发不出野兽的怒吼声,只是错落而杂乱、时而低沉时而尖锐的乐声渐渐变得刺耳了。
“好主意!”像是学生的男性身先士卒地拿起贴着墙面放置的吉他,稍微试了下音,“我已经准备好了!”
“好。”女性清了清嗓子。
“我不会。”干脆的男性作出了干脆的回复。
“要不试一下那边的尤克里里?它只有四根弦,相对好上手一点。”已经轻车熟路地把吉他挂在腰间的高中生指了指一旁墙边如面试者一般等待被选择的乐器们。
“这个?”
“不对,那个是贝斯。四根弦的那个才是。”
“这个?”
“对,那夏露露呢……?沙锤吗,真是古板又缺乏新意的选项啊,罢了,也很有你的风格。那么——
“开始表演吧!”
……
也就是说,这就是一个临时组建的乐队被愤怒的钢琴赶出音乐室…的十分钟前发生的事。
“它干嘛这么生气?”始作俑者不解地一边在楼梯上奔跑着一边发问。
“大概是因为有人连c和弦都不会弹吧。”女性冷冷地回道。
“话又说回来,你们有没有听到后面的脚步声?还有……斧头、摩擦地面的声音。”四人中最小的男性一面说着一面频频回头,脚下的影子被阶梯拉得长长的,像是被折成了数叠。
“比起这个……”存在感略低的男性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准确地说,是看着脚下的阶梯:“这条楼梯,我们已经……”
“走了666节阶梯了,对吧。”跑在最前的男性停下脚步,楼梯的尽头是一座宽敞的礼堂,里面已经有人了。
“……”一个陌生的女性不知正说着些什么,她转过头,朝四人打了个招呼:
“初次见面。”
“请说英文。”气喘吁吁的男性如此回答。
-杂音-
“所以,你们的名字是?
“……
“这是哪国的名字?
“好吧,亚洲人,欢迎你来到奥庇沙……开玩笑的,这里是美国,埃芬市,罗卡里兰高校。
“开场白…或者说结束语已经说完了,那么,你们想怎么样?想回去的话,我这里有认识的小叮当和任意门,又或者…你想组个临时乐队吗?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两个音痴所以那边的钢琴很生气,是的,音痴是在说我自己。
“哼…你们能答应就太好了,希望你们能让它满意……你是说希望渺茫吗?我会期待的。”
-和音-
称不上和谐、称不上优雅、称不上漂亮,甚至略显狼狈的一曲随着最后一个音符、最后一根颤动的弦、最后一句即兴的歌词落下而画上休止符。三个人弹唱,而另外三个人坐在音乐室的椅子上只负责了鼓掌,据说,“这是最好的安排了”。
钢琴没有眼睛、钢琴没有嘴、钢琴没有毛发、钢琴没有四肢,“钢琴”并不是活着的生物。
穿着校服的男性手中的红松鼠在安静的音乐室内一跃而下,蹦跳着跑向那架有着漂亮骨架与外壳的钢琴,就像寄居蟹找到了全新的壳,它钻了进去。
被沉默所充斥的室内,不知是钢琴或是松鼠送来了一曲《月光》,月亮温柔而沉静,如隔着层纱幕般垂下眼睑,圆而白,投来明朗而慈悲的目光。
某个人轻轻哼唱、某个人弹起和弦、某个人打着拍子、某个人跺着脚,某个人轻叹出声:
“真是…像魔法一样。”
“这种话,现在才说吗?”
钢琴没有眼睛、钢琴没有嘴、钢琴没有毛发、钢琴没有四肢,“钢琴”变回了它应有的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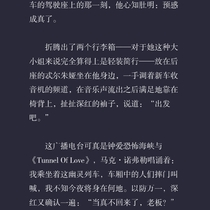

字面意义上故事开始前的时间线。
通篇全是流水账。
写不下去了总之先丢上来。
角色归亲妈ooc归我。
——————————————————————————
一
在十岁生日那天,斯贝内洛.桑吉内涅斯生了一场大病。年幼是身体似乎无法承载奥庇沙时期过于沉重的记忆和知识,断断续续的高烧持续了将近一周后才完全褪去。
在那之后他就变得格外粘人了。
安珀叽叽咕咕的向父母抱怨着,不管是吃饭睡觉都一定要人陪着,稍微离开一会就满屋子乱转乱叫,即使都把门关上了也还是会扒着门缝往里面看,一点也没有尊重别人隐私的意识。这算什么呀,斯贝都多大啦,我从五岁就可以自己一个人睡觉不用陪了!
斯贝纳趴在母亲腿上打了个哈欠。父亲正揉搓着安珀的脑袋安慰他气鼓鼓的小姐姐,鲁比姐姐蹲在旁边帮她重新系好睡衣上的蝴蝶结并没收了口袋里偷藏的小饼干,于是两人开始争论起睡前食用甜食对心灵的好处与牙齿的坏处。更远一点的地方,亚列哥哥有些不知所措的从书中抬起眼睛。舒适的夜风摇晃着窗外的蔷薇花丛发出沙沙的响动,昏黄的灯光令人昏昏欲睡。
“因为我爱你们呀。特别,特别的喜爱,所以不想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分开啊......”未经思考的话就这样流淌而出。“每天都像做梦一样,这幸福的太不真实了。所以我想如果我再多注意一点,一直粘着你们的话,你们是不是就可以不要死掉了......?”
房间里的吵吵闹闹停了下来,所有人都看向了他的方向。斯贝纳眨眨眼睛,隐约意识到自己好像说错了什么话,“......或者......这次可不可以让我最先死掉?虽然死亡是好痛苦的事情......但是如果可以和大家一起的话......”
“区区一个斯贝,在说什么啊!?”安珀第一个跳了起来,扑到他身上狠狠的抱住他的脖子,“闭嘴闭嘴,小孩子不许说这种话!”
在斯贝纳真的要被勒的喘不上气之前,鲁比把安珀抱了起来,叹着气拍了拍他的头顶,“虽说死亡是人生无可避免的终点,但你考虑这些还太早了一点,你才十岁呢。是亚列又给你看什么不该看的书了吗?”
“啊?怪我吗......?”他的哥哥好脾气的挠了挠头发,“唉,好吧,好吧,没注意让小斯贝纳感冒发烧确实是我的错,但我可真没给他看过奇怪的书了......医学简史和人体解剖不是什么奇怪的书吧?你不是也经常给他看生物图鉴......”
哥哥姐姐们再次嘻嘻哈哈的吵闹成了一团。斯贝纳真想沉浸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里什么都不要想了,可是,再不考虑的话就来不及了呀,上一次......
“斯贝纳。”妈妈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真是抱歉,让我们的斯贝纳这么担心。但是没关系,一切都过去了。”
像是知道轻飘飘的话语无法安抚敏感的幼子,红发的女性微笑着拉起他的手,引导他按住自己颈部的动脉。指尖传来规律的律动,扑通,扑通。
“垂筒花,梧桐叶与十毫升的鲜血,在生日对应的月相时缝进皮质的容器,咒文是守护,连接与心脏,用三重环的方式书写。如果这个小小的魔法成功了,你就能从容器之中听到我心跳的声音。”女性的声音温柔的像是在念诵一个童话故事。斯贝纳愣了愣才反应过来,那并不是他出生至现在,并不是在地球上应当有人会使用的语言。
只要还能感受到心脏的跳动,就证明你所珍爱的家人还好好的活着。这样可以让你安心一点吗?
那是来自遥远的前世,奥庇沙的语言。
我们始终血脉相连。
二
桑吉内涅斯家的孩子们年龄差了很大。
在斯贝纳十五岁的时候,姐姐鲁比阿娜就已经准备结婚了。新郎来自附近的城市。虽然驾车过去只用一个多小时,但到底是离了一段距离,不能每天都住在家里了。
再之后,是哥哥亚列决定接受导师的推荐去美国工作,和安珀提出想要报考生态学,以后去各处探险。
离别是不可避免的,想要再聚也很容易。虽然理智上很清楚,但斯贝纳还是闷闷不乐了很长一段时间。
“斯贝纳也该考虑一下未来要做什么了。不能总是一直呆在家里呀。”哥哥姐姐看向他的目光多了几分担忧,“不怎么和人接触又没什么朋友,这样下去要变成自闭儿童了。”
未来要做什么吗?重生以来斯贝纳还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好好活着就足够了不是吗?
在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家人之后,他们表现的更加担心了。
“明明兴趣很广泛,书也看了很多,但是就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这样不太行呀。”
以后会尽量尝试看看的,烘培或者照顾植物之类的......最感兴趣的果然还是魔法,但他自己的魔力至今还没恢复。虽然理论与仪式都还记得,但无法提供足量的魔力,前世能够驱使尸体大军的魔法如今也只能字面意义上让烤鸡跳个踢踏舞。
“或许换个环境会不会好一点?离家远一点,但也不能太远,照顾不到还是不太放心啊。”
啊,这个不行,绝对不行!要和家人分开的话一天都活不下去的!要怎么才能劝他们打消这个想法......
“去美国怎么样?安珀和亚列也都在。”
......如果有哥哥姐姐陪着的话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
“东海岸和落基山脉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不过美国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希望能让斯贝纳也学的活泼开朗一点。”
活泼开朗有安珀在就够了吧。但如果这样能让他们更开心一些的话努力多说说话多笑一笑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虽然舍不得斯贝纳,但是羽毛丰满了的小鸟总要离巢才能更好的飞翔呀。”
五比一胜,斯贝内洛.桑吉内涅斯转去美国读书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三
理想很美好,但现实总有各种各样的意外发生。
落地美国后,连行李箱都没拆开就被导师叫去办公室呆了三个小时,回到临时落脚的宾馆同时带来了将要陪同导师观摩手术最近都会很忙的消息。
简而言之,他太忙了,完全没时间照顾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弟弟。
“所以我请了个......帮工?据说他前世也是奥庇沙人。对了有些转生者还办了个论坛你感兴趣可以去看看......”
大忙人亚历桑德罗就这样留下一句有问题给我打电话后匆匆出门。留下斯贝纳和站在门口的红发男人面面相觑。
非常漂亮又耀眼的红色长发,和鲁比姐姐很像.....所以,和人打招呼,应该怎么说来着......?应该说意大利语吗,在美国或许用英语比较好吧。但亚列说他前世也是奥庇沙人,那或许奥庇沙的通用语.....斯贝纳思考或者说发呆了足足能有五分钟。被介绍是帮工的男人也没有催促或者进门的意思,就站在门口等着,像是一株安分的植物。
“您好我是斯贝纳。很高兴认识您。”终于他决定好了,果然还是入乡随俗的英语,配上乖孩子的标准微笑。
“我是深红。”男人点了点头,报上名字。
接下来就是租房,入学,收拾行李,一堆琐事。好在斯贝纳并不是完全的懵懂无知的小孩,上辈子十岁起就带着只被各路追杀的怪物到处乱跑还成功活了接近十年,生存能力不可谓不强。这一世虽然被家人养的娇惯了一些,但身边没人的时候打起精神也算是能勉强自理,把该做的报道与交涉处理好。
深红乐得轻松,安分守己的充当了司机,搬运,与清洁工。虽然明显不是健谈的性格,但他前世的事迹传播太广,抽空在论坛上随便翻翻就能知道。斯贝纳很是好奇他的红荆白锁到底是什么原理,但到底没好意思出声询问。
两人相安无事的相处了两天半,直到彻底收拾完屋子,深红做了晚餐。
炖菜,面包和速食意面。斯贝纳吃了一口就放下了勺子,询问坐他对面的主厨,炖菜和面包可以放冰箱,意面你一个人能吃完吗?
在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他二话不说转身进了厨房,花了十五分钟给自己弄了一盘奶油培根意面外加沙拉菜。
“很难吃?”被嫌弃的临时厨师已经吃完了他自己那份,抱着胳膊坐在桌子边,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斯贝纳眨眨眼。深红的厨艺其实不算糟糕,炖菜中规中矩,咸度适中,没有夹生也没有糊底,所有食材都在熟了的范围内。面包和意面更是超市里最普通的那一种,放碗里加热一下就端上了桌。老实说,再难以下咽的东西他也不是没吃过,但斯贝纳并不想委屈自己吃这种凑合的速食品,于是他最终选择了实话实说。
“可以吃,但我想吃点好的。”
“都是意面,有什么差别么?”深红露出不理解的表情。
在传统意大利人眼里两者从面到酱汁到配料到做法就没有一样的地方,不,速食罐头甚至不配称之为意面。但斯贝纳懒得费力解释,他直接分了一些进深红的盘子里,示意对方尝尝。
深红依然是一脸不理解,看起来情趣缺缺,也可能是已经吃饱了,但还是在少年无声的催促下拿起叉子把分给他的部分吃掉了。
“还行。”他最终点点头,也不知道有没有尝出区别。
“如果有自制的培根会更好吃。”斯贝纳咀嚼着食物,尤其考虑到往后至少还有三个月雇佣期,以及自己在魔法材料方面有可能的需求,他提议,“以后我来做饭就好。还有购买食材时也请带上我,谢谢。”
“......?”
“会做你的份的。”
“好的。”
四
斯贝纳在新学校的生活总体来说很顺利。良好的家庭教育带来的知识应付课业绰绰有余,足够乖巧可爱的外表则帮助他迅速赢得了老师们的基础好感。
也有不太顺利的地方,比如说,体育运动。
斯贝纳不能理解,为什么这里的每个小孩都和安珀一样吵吵闹闹精力旺盛,跑来跳去也不觉得累呢?
好不容易以步行速度坚持完成据说是热身的两千米慢跑,斯贝纳觉得自己已经快要虚脱了。而之后居然还有球类运动的训练。就这样还有人嫌不够,在练习结束后兴致勃勃的组队玩起了抛接球。
即使是上辈子在奥庇沙的时候,作为魔法师到处逃窜的斯贝纳也极少有剧烈的运动的需求——东奔西跑的活自然有好用的血肉傀儡可以代劳。而他这辈子一直黏在家里,有机会做的最耗费体力的事也只有收拾花圃和整理书房。
虽然,按照他的魔法的属性来说,或许稍微多做些运动锻炼下身体比较好......
正在斯贝纳靠在围栏旁边休息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尖叫,抬头时候就看到不知是谁抛出的橄榄球高速旋转向着他的脑袋飞过来了。
啊,来不及躲开了。
斯贝纳从善如流的闭上眼睛,但嘭的一声后,预想之中的痛感并没有出现。少年困惑的睁开眼,视线中是一大团毛茸茸的红色长发。
深红色长发的少年及时接住了橄榄球,往球场方向丢了回去,朝着嘻嘻哈哈大叫sorry的球员们喊,“你们小心点,差点砸到人了啊。”然后才转头问,“没事吧?”
当然是没事的。斯贝纳只来得及摇了摇头,他就一溜小跑离开了。
盯着毛茸茸的同学跑远,斯贝纳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道谢?但是对方跑的太快了,没能来得及。
有着漂亮皮毛的少年,似乎是理科课上见过的同学.....?叫什么来着,艾丹?
斯贝纳趴在桌子上,从手臂间的缝隙打量旁边的同学。体育很好,理科的成绩一般。很喜欢看窗外,发呆的时候会叼着东西。话不算多,外表看起来有点凶,但是和同学们关系都不错,应该还算好说话,大概。
应该再去道谢吗?还是就这样算了。两辈子都没有什么同龄朋友的少年有些困惑。按照礼仪来说自然是应该好好道谢才对,但是好麻烦哦,错过机会后再搭话会不会让人不太对劲......
然后,那团红毛挪动到了他的面前。艾丹扒着桌子边缘蹲到他座位旁边,和他双眼平视,斯贝纳这才看到,毛茸茸的少年也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并非天空或者花草,而是接近宝石矿脉般的质感。
“斯贝纳是吗?你今天一直盯着我,是有什么事?”
啊,被发现了。斯贝纳眨了眨眼睛,露出友善的笑容,庆幸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应有的说辞,“之前谢谢你帮我拦住球,作为感谢,要吃牛肉干吗?”
艾丹挠了挠头发,露出了有些迷茫的表情,“之前什么时候的事......?不用客气,应该的。”他伸手接过斯贝纳递过来的肉干,嗅了嗅,咬了一口。
“这个挺好吃的,从哪里买的?”
五
同班的同学熟悉起来是很容易的。
在几次分享过食物和课堂笔记之后,艾丹提议周末一起去逛集市。
“就在公园旁边,会有很多小商贩,卖手工艺品,旧书旧衣服,还有各种小吃,现烤的肉串和五花,还有香肠,想吃什么我请客。”
“可以吗?我饭量很大的。”斯贝纳想了想,哥哥还在赶报告,姐姐说要去徒步登山。总之,都没什么空闲陪他,正好有时间可以出去玩。
“没问题,因为平时吃了斯贝纳很多的储备粮。”艾丹比比划划。“斯贝纳你看起来...不像吃很多的啊。怎么总是随身带那么多好吃的?”
“啊,是习惯。”红发少年眨眨眼睛,有些心虚。实际上那些肉干和香肠最初并不是为了食用而制作,本质其实是施展魔法所需要的原料。但是,如今的生活环境太过和平,并没有太多突然需要使用魔法的机会。那些精心准备的肉类到最后几乎都得吃掉。不想浪费粮食也不想虐待自己的舌头,斯贝纳花了更多的时间料理那些食材。反正盐和胡椒粉对施法效果没什么影响,有些香料甚至还有对魔法还有增益作用呢。
但是,和认识不久的同学说这些大概会被当成神经病笑话,家庭的教育又不允许他随便说谎,于是斯贝纳找了个折中的说法,尝试糊弄过去。幸好艾丹并没有深究,反倒是拍着他的肩膀说要多吃一些才能长高。
“对了,你不怕狗的吧?”
周末见面的时候,艾丹带来了一条巨大的浅色猎狼犬,和主人一样毛蓬蓬的,但热情得太多。一见面就蹦蹦跳跳往斯贝纳的身上扑,吓得艾丹赶紧把它拉住。
“......薯条,坐好,别这么没礼貌!”
“没关系,我很喜欢狗狗。他叫薯条?”斯贝纳主动弯下腰拍了拍热情过度的大狗子,刚刚就觉得有点熟悉,听到名字他想起来了,之前在论坛上见过有个头像就是这只长长的嘴筒子,而且,id好像也是CHips。
奥庇沙转世的狗狗吗......?说起来,狗是可以上论坛的吗?狗是能打字的吗......?
捏着大狗的爪子,斯贝纳陷入了思考之中。
互相熟悉后他们汇合进热闹的人群,目标明确的前往烤肉的摊子,之后是果汁饮料和炸点心。在双手都拿不下更多的食物后他们在草地上找了个地方坐下,放开薯条和其他狗狗及爱狗人士们一起玩闹。
薯条是一只好狗。意思是,它有着一切好狗狗的特征。热情,友善,活泼好动,听得懂基础的命令。但是,似乎没有更多了。招牌上的文字它视而不见,对捡树枝的游戏兴致勃勃。
斯贝纳趁着艾丹不注意对它说了奥庇沙几句的语言,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的反馈。
“你盯着薯条看了十分钟了,它怎么了?”
斯贝纳歪了歪脑袋,“没什么......”他在询问薯条的身世来历还是日常行为是否有异常之间犹豫了一会,最终决定有话直说。“我在论坛上看到过CHips这个名字,头像也是这种狗狗。”
“啊,那个应该就是我。”艾丹愉快的打开手机,给他看满屏幕车座子狗的照片,“薯条很可爱吧,所以借用他做头像来和网友拉近距离。”
“这样....”
“你怎么一副很失望的样子。”
斯贝纳偏过头,“......我以为是薯条学会上网了。”
听到这话艾丹笑得和薯条抱成一团,过了好半天才直起身子,“怎么可能啊!虽然薯条很聪明,他也只是普通的狗狗而已。狗没可能自己打字的吧?”
“也是啦。”斯贝纳也被自己异想天开的想法逗得笑了起来。
这里并不是奥庇沙,而是并没有魔法与神迹存在的地球。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20X6年世界杯小组赛德国对阵波兰的比赛。埃芬市灯光如昼,数以亿计的目光投向这片承载过欢笑与泪水的草地。即将展开的,是一场无法避免的碰撞。”
“日耳曼的严谨和斯拉夫的热情,历史的经纬曾在这两个民族间编织过复杂而深刻的纹理。数百年过去,莱茵河与维斯瓦河滚滚流淌,铁与血的奔涌已然退出舞台,时间的车轮缓缓向前,足球的版图上,双方各自占据着独特的坐标。”
“德国,这支曾四度问鼎世界之巅的铁血之师,从不以花哨取悦观众,却总能以秩序与效率书写传奇。他们的足球哲学,如同精密的仪器,追求着环环相扣的运转。他们背负着荣耀,也背负着对复兴的渴望。”
“而波兰,他们是东欧大地上不屈的雄鹰。波兰足球的灵魂里,始终燃烧着一种野性的骄傲,往往能在逆境中迸发惊雷的力量。他们的反击就像是裹挟着东欧平原上凛冽的寒风,足以刺穿任何严密的堡垒。”
“双方球员进场!正在朝镜头挥手的是德国队的门将莱昂纳德·舒尔茨,他是球场上坚不可摧的城墙,不仅用一次次世界级的扑救守护着最后的防线,更用他观察全局的视野驱动着整辆德意志战车。”
“走在他身侧的是波兰前锋拉多斯瓦·切尔温尼,两人效力于同一家俱乐部,是可以互相托付后背的队友,如今却在这片对他们而言无比熟悉的绿茵场上各自为政——这是很常有的事。拉多斯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边锋,但他的速度不容小觑,屡屡如一把尖刀撕开对手的防线。这是波兰雄鹰最锐利的爪牙,是他们在阵地攻坚之外破局的重要武器。”
“今晚,站在命运的分岔口,历史的厚重感或许会无形地笼罩这片球场。但足球的伟大恰恰在于,它能在90分钟、乃至120分钟里,将所有的过往,熔铸成纯粹的、关于意志和梦想的较量。让我们屏住呼吸,迎接这场注定不凡的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