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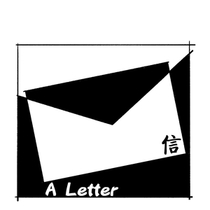
(……因为今天再不发可能就没有勇气发了所以闭眼丢出.jpg)
虽然写了一些理论上是间章的剧情,但既然还有两周就湖骸入侵我说它是一章它就是一章!【震声(
关联剧情:
·费老师说有冒失猎人丢了身份证让我看看是谁啊哦原来是我:http://elfartworld.com/works/9220955/
=========
雷涅在勉强能从教会医院的病床上把自己挪下来的时候就执意离开了大教堂。倒不是他非要逞能,或是什么无聊的面子问题,主要是由于他实在无法在有血族近在咫尺的环境下顺利入睡。不知到底是因为这些不同于人类的脚步声中确实有着特殊的频率,又或者只是出于一些猎杀者多年积攒下的直觉,雷涅的神经总会在巡逻的教会猎人经过时突然地绷紧,条件反射般地试图伸手去够武器,然后在断骨的刺痛中浑身冷汗地惊醒。
这着实不利于伤员的恢复,为此露西娅嬷嬷——他作为猎人的师父,因为一次围猎事故被迫退役,现在是圣伯拉大教堂一位普通的修女——也没有过多阻拦,只是交代了她的另一位徒弟尤莱亚替他在镇上寻了一处落脚点养伤,间或趁外出采买时过去照料一二。
赦罪演武那天傍晚发生在百合花广场附近的事故很快地传播开来。当然了,就像一切传言那样,流转在口耳之间的消息或多或少地添加了口味不同的猜测佐料,导致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为什么一个血族在教会眼皮子底下当街发了疯似地攻击一位人类的猎人,又是为什么一名教会深居简出、虔诚苦修的圣女竟会在没有教会猎人护卫的情况下遭遇这样恐怖的事件。据说教会猎人们在事发后迅速组织了人手前去追捕这位胆大包天的吸血鬼,然而却空手而归,由此引发的关于“教会猎人也不过如此”和“前来挑战的血族必然早有预谋”的辩论甚嚣尘上了好几天。
无论如何,沸沸扬扬的离谱传言同时也模糊了对真正当事人的关切,至少雷涅在养伤期间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关注。那些高谈阔论着并非亲眼所见的细节、从他的窗下信步而过的闲人们根本不会意识到,他们话题的中心人物之一就在一墙之隔的床榻上安睡。
受伤与痊愈,对于刀尖舐血的猎人们来说,如果不能说是家常便饭,至少也算得上一种习以为常的事故。雷涅曾经从比这严重得多的伤势中恢复过来,他很熟悉这些流程:敞开的创口逐渐合拢,撕裂的筋腱慢慢粘接,被石膏限制活动范围的骨骼一点一点生长回原本的模样。人类的身体不像那些不老不死的怪物那样会飞快地修复,但总有一天最终还是能够痊愈。
复健花去的时间比他预想的要略长一些。撑开僵硬的肌肉与关节所带来的疼痛固然可以忍耐,然而新生的骨骼和神经还需要多用一些时间去反复适应,才能找回他原本所习惯和掌握的灵巧。秋天的脚步就这样在单调而重复的恢复性练习里匆匆滑过,到了白天也需要点起火盆取暖的季节里,雷涅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打开房门的时候,先朝他面门抛过来的是个泛着金属光泽的小物件。他下意识地接住,摊开手掌,躺在掌心的是他熟悉的东西:一枚猎人工会的徽章,并不是簇新的,带着显著的使用痕迹,左上角有一处豁口,如果翻过来的话,会看到徽章的反面用粗糙、拙劣的笔迹刻划下的,那个在他记忆里永远也不会磨灭的日期。
“还以为能看到你有些长进。”来人逆着光,嗓音里的冰冷却像是丝毫没有沾染到这样一个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副一心求死的模样。”
雷涅眯着眼睛看向面前的来客。很年轻,身材算不上高大,银白的发丝剪得很短,锐利地从下往上审视着他的眼睛是很浅的碧蓝色,毫不客气,绝不回避,甚至带着几分难以形容的苛刻意味。
“……我们认识吗?”他问。
银发的猎人挑了挑眉毛,似乎在掂量他问出这个问题是在挑衅还是在戏弄。
“费恩·莫里斯诺。”
猎人最终简单地报出自己的名号。或许是为了表达不满,又或是为了强调与提醒,提在手心里的一杆造型优美的纤长银枪被不轻不重地顿在地上,尖锐的枪尾扎进松软的地面,甚至没有带起一抹尘土。
雷涅听说过“银枪”的名字。这个猎人在工会的传说中是个频繁被提起的人物,即便雷涅绝少参与那些茶余饭后的闲谈,他也总在招募与悬赏的委托单上见到这个名字,与猎杀成功后的鲜红印记并肩出现,无端地带几分矜持的骄傲气息。然而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位出色的猎人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在他的门口,一脸仿佛兴师问罪般的表情,甚至还带来了那枚他以为在广场事故中遗失了的猎人徽章。
他的沉默并没有让费恩过多在意,对方平铺直叙地径直往下陈述,仿佛不曾被他无礼的提问所打断:“我在广场附近的树下捡到了这个。你们闹出的动静太大了,可能是因为卡住的位置太刁钻,才没有被人马上拿走。要不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你的东西,我也不会碰第二下。”
徽章背面盛放圣血的小瓶子大概是在遗落的过程中碎裂了,珍贵的血液渗漏殆尽,对于普通的猎人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功用。雷涅用拇指擦过徽章的表面,发现有人曾经仔细地清洗过它。徽章很干净,干净得连那些新新旧旧的划痕里也没有留下曾经积存过血液的痕迹。
“谢谢你。”他说,语气诚恳,就像平常人在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帮助那样。然而费恩轻微地停顿了一下,似乎诧异于他的坦诚,但随后便理所当然地颔首,接纳了他的谢意。
“重要的东西自己保管好。”猎人冷淡地说,“下一次可不见得还会有人替你留心。”
费恩提起长枪转身离开,厚重的长斗篷在寒风中猎猎作响,勾勒出猎人纤细矫健的身形。雷涅凝视着她的背影。
知名的“银枪”费恩·莫里斯诺是位女性这件事,说实话他今天也是第一次知道,但谈不上有多大的惊讶。女性猎手在工会之中的比例不算高,但在最优秀的那批猎人之中从来不乏她们的身影。雷涅自己的恩师曾经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女性猎人,他不会因为性别就对她们产生偏见。
但他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好像他遗漏了一些不言自彰的细节。作为初次见面的人来说费恩的态度实在有些过分严厉,他不明白她那莫名其妙的不满师出何名,就好像他们先前有过什么过节,而雷涅完全没有留下印象。他试图回忆自己曾经在什么时候和她有过交集,什么也想不起来,然后他无意间瞥向停留在他手掌上的那枚徽章。金属的表面上那排笔迹深重凌乱的凹痕,那个年份和日期。
他突然电光火石般记起她说过的话,在打开门之后,费恩说的第一句话。她说,“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是那个小女孩。
*********
“她只是个小女孩。”
雷涅说。他审视般地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小姑娘,还没到他胸口高,斜拖着一根长木棍,银白的发丝半长不短地垂在脸侧,眼睛是很浅的碧蓝色,毫不客气地从下往上回应般打量着他,看起来似乎比他本人更加不满。
“她是艾德蒙的徒弟。”露西娅回答道,笑容可掬地抬起睫毛,瞥了一眼靠在边上的自己搭档。艾德蒙佯装没有注意到她的眼神,卷了卷手里的烟,专心致志地把它点燃,然后塞进嘴里抽上一口。“况且吸血鬼之中也有不少凭借弱不禁风的小姑娘外表来迷惑人的家伙,不要根据外表来判断他们的实力。试试看,当心点。”
一开始他以为这句当心的意思,是要他对面前这个看上去只有十岁出头的小女孩手下留点情,直到他试探着伸手去抓她的肩膀,女孩露出明显嫌恶的表情,在他的手掌碰到自己之前沉肩躲开,手里提着的长棍轻巧往上一挑,啪地一声清脆地敲打在他胫骨上。
雷涅本没太把那杆还没他拇指粗、质地看起来也轻脆易折的木棍放在心上,可她敲打的位置特别凑巧,比起疼痛,带来的更多是一种从膝盖下方朝整个小腿扩散开的麻痹感。酸麻的感觉让他险些打了个趔趄,挣扎着站稳之前木棍借着从他腿上弹开的角度划出一道流畅的弧线,利落地指向他的侧腰。他收不住向前的冲劲,看起来就像是把自己送到她的棍尖上去,只得下意识地去抓她斜斜挑起的棍身,意图阻止它刺进——如果它装上枪尖的话——自己的腹部。
意料之外地,女孩十分坦然地任他握住棍子,与此同时却毫不容情地一脚踹向他的另一只膝盖,雷涅刚刚把身体的重心从被击中而麻痹的那条腿转移到另一条,挨了这一下彻底站立不稳,狼狈地单膝着地。女孩的长棍轻松地从他松开去撑住地面的手掌里抽出来,虚点在他喉咙上,俯视的碧蓝色眼睛里没有胜利的笑意,依旧是一副不甚满意的表情。
“腰放低一点。”露西娅平静地指出,似乎完全没有对这样的战况感到意外,“注意她右手的动作。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并没有改变他无法靠蛮力战胜女孩手中灵巧得像条活蛇的棍子这个事实,再来两次也没有。最后一次他甚至被借力掀翻在了地上,长棍的尖端点在他胸口,女孩冷冷地看着他,然后雷涅听见她用清脆却同样冰冷的声音清晰地说:“你好弱啊。你这样要怎么给家人报仇?”
在愤怒来得及化成白热的火焰,沿着血管窜上他的大脑之前,一直没过开口的艾德蒙直起身来,把烟从嘴边拿开,打断了徒弟直白的责难。
“费恩。”他说,语气平静,但调子很严肃,“这不礼貌。”
女孩把长棍收回去,轻轻点在地面上,没有吭声,但她移开了视线。
露西娅走过来,向躺在地上的雷涅伸出手。她朝他微笑,齐马蒂的红玫瑰已经没有当初那样年轻了,但那双饱含柔和笑意的眼窝还是跟她跨着爱马从家乡远道跋涉而来时一样美丽。她把自己的徒弟从地上拉起来,笑着拍掉他衣服上沾着的灰尘。
“我亲爱的。”她亲切地说,口音里带着还没有被这么多年在纳塔城的工作与生活完全洗去的集落人的悠长拖腔,“在这一点上你恐怕得原谅雷涅,他还没有正式接受过战斗的训练。事实上,在你之前他还从来没有尝试过。”
“……抱歉。”女孩看着地面,生硬的语气里透着不情不愿。
雷涅保持着沉默。那团没有成型的火焰很快平复下去,融化成冰冷的水,又或者是毒液,流淌过他脖颈后面的脊柱,将他过去所熟悉的一切,他骄傲和自豪过的一切,将麦田的颜色、苹果的芬芳,将笑容与歌声、温暖的炉火、甜蜜的吻,统统都冻结、蚀刻、封存在了那个刻骨铭心的日期。他再也走不出的日期。他再也回不去的日期。
他第一次拿到那枚象征着接纳和认可的猎人工会徽章的时候,大腿上新装不久的储血器还没有让他完全适应,持续散发着不算疼痛却很难忽略的异物感。盛放在里面的第一份良药换了这片薄薄的,比他掌心还小上一圈的金属,代表着他从此之后有资格随意出入这座几乎每个时刻都充满活力的厅堂,接受庇护、补给、工作委托和其它可能的支援。
雷涅坐在人来人往的工会大厅一角。那不是在一个寒冷的天气,没有点燃的炉火,窗户为了通风打开着,透进来明亮的天光和偶尔麻雀的吵闹声。他用一把匕首在崭新的金属背面刻下那个日期。工具不是很趁手,在光滑的金属上打滑了很多次,留下不必要的划痕,字迹也全然谈不上工整,毕竟在过去的二十来年中,他几乎没有得到过练习的机会。然而他依旧执拗地、一笔一画地在徽章的背面刻下那个日期,不是为了纪念,而是为了祭奠。就像在他亲手埋葬的亲人和朋友墓碑上刻下那些无法回应的名字。就像他为自己提前刻下的,本应一同在那里沉眠的墓碑。
*********
雷涅带上门扉。门开着的时间太长了,漏进来的冷风让火盆本就微弱的热力愈发聊胜于无,还没有完全好透的手臂在温差中敏感地散发出微弱的酸胀进行抗议。他活动着小臂,用掌心的热度试图安抚它的不满。那枚失而复得的徽章也沾染上了他掌心的温度,在被小心地塞进贴身衣兜时没有冰凉的触感,只是温和而妥帖地,停留在那里。
他想或许再过两周他需要去一趟纳塔城。弹药固然暂时还不需要补给,然而他的储血器似乎在冲突中受到了一些损伤。圣伯拉大教堂固然不缺少优秀的医生,但安装在他体内的储血器有点特殊,除了在纳塔城的猎人公会,很少能找到合适的人为他做调整。他盘算着在走之前应当去向师父道个别,或许还有露缇娅。这个小姑娘身上有种偶尔会令他觉得为难的固执,特别是在她非要将他受伤的过错揽到自己身上之后。若是还像之前一样,只让师父转告而不亲自和她见上一面的话,恐怕又要收到来自她的一番书信轰炸。
最后他才无端地想到费恩·莫里斯诺。艾德蒙的徒弟,“银枪”猎人。在此之前他从未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如果他早知道……
雷涅哑然失笑。
算了,他想,也没有什么区别。


要是没有这声巨响,罗斯差不多都要忘记那两个家伙了。她发现上一次见到他们还是在十五号的晚上猎人们在城外据点的篝火旁边分晚餐,本来是这样的,但她和两个在血罐身上绑炸药的人渣吵了一顿后,事情就像枪管炸了膛一样混乱起来:莫名其妙之间猎人们就决定了“给湖骸炸他妈个大烟花!”。十五号就这样混乱又离奇地过去了,多少显得有些疯癫的狂欢结束之后,“炸他妈个大烟花”就像段群体的梦境一样悄然无踪,猎人们依旧照着原来的计划轮班守夜和巡逻,伤者仍然不分昼夜地被送到斯塔夫罗金医生这里。她跟着医生的指示在工会大厅里外来回穿梭,把能动弹的伤员交给运送伤员去城外森林安置点的猎人,不记得天是什么时候亮起来的,不记得中间自己见缝插针地打过几个盹,也不记得天色是什么时候又变暗了的——直到她获得了短暂的休息,从多姆神父那里讨到一块烘软了些的干面包打算补上午饭时,工会大厅斜对面一处应当空了的屋子里发出一声爆炸的巨响。
罗斯这才想起来,十五号的晚上之后她就再没见过洛多维科·里奇和亚伦·桑切斯,那两个为“炸他妈个大烟花”提供了绝大部分舆论气氛和技术助力的家伙。城里已经空了一大半,工会大厅附近的猎人大多是回来修整的,疲惫不堪地抬了头朝那爆炸声处望了望,都指望着别人过去瞧一眼,最终竟也只有罗斯一个立刻向那里冲过去。
她一边跑着,一边才后知后觉地想到:天杀的,这两个家伙真的在做炸药,我们真的要炸了纳塔城。
当她冲进了那间空屋子,又发觉自己对这两个家伙的担心很是不值当,当即把脑袋探出门外,朝往这儿看着的疲惫猎人们大喊:“别看了!没事儿!”。尽管被爆炸震得东倒西歪趴作一团,但两人都全须全尾,精神得很。洛多维科首先看见了她,跳起来大声说:“我们尊敬的提案发起人、我们的小老板来啦!噢,”他用大过了头的嗓音嚷嚷:“还带来了面包!天哪,我们俩多久没吃东西了?”他用手肘顶了顶正从地上爬起来的亚伦,独眼的年轻猎人晃了晃头,像是还没从爆炸的余波里回过神来。
罗斯低头看了看,面包在跑过来的路上已经被自己捏得变了形,松了手就倏倏往下掉渣子,她愤愤地踢了一脚“松鼠”洛多维科,“这是我的午饭!”
“你说什么?”洛多维科仍然用大过了头的嗓门说话,“我耳鸣!你刚刚说什么?”
而亚伦在他耳朵旁边大声回答他:“我们今天还没吃过饭!”
最后亚伦从包里找出了最后一张干净的纸,把面包垫在上面切成了三份,并礼貌过头地表示自己不怎么饿,主动选了中间被捏扁了的这段面包。他们盘坐在被炸得七零八落的屋子里,洛多维科耳鸣好了,便显摆似的向罗斯介绍刚刚炸出吓人巨响的东西:“我打赌给你三天你也猜不出,是白糖!嘿,这年月纳塔城里还能有白糖。那你猜猜这是怎么弄出来的?”
罗斯翻他白眼,往独眼的陌生猎人那里看去,这个叫亚伦·桑切斯的猎人说是雷涅的伙伴,常在西南那片活动,是以很少来纳塔城,罗斯自然也不认识他。年轻猎人发觉她的目光,挠了挠鼻子,说:“白糖能烧,在火药里配一份会炸得更远,熬成糖浆配进去效果更好,但是火候和配方得再调试……”
洛多维科听到被揭了谜底,顿时咋咋呼呼起来:“我们这已经差不多了,马上就能弄出够多的火药。”
罗斯早就习惯这“松鼠”的吵闹,索性也不理他,低头吃面包的时候正看到刚刚被垫在面包下面的纸是一封信,信封上不怎么好看的字迹写着“纳塔城玛格街二十八号,诺利亚先生收”。她觉得奇怪,也没有多想就说道:“纳塔城哪有玛格街?”
洛多维科也探过头来,问:“这是你的信?”
“我替人来送这封信,到了这里正好就遇上了湖骸。纳塔城没有玛格街的。”
“噢……”洛多维科这会儿的反应快得惊人,俨然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我猜猜,讨债的信?还是姑娘的信?”
亚伦仅剩的眼睛惊讶地看了他,答道:“姑娘的信。”
这下罗斯也明白了,用力撕咬了一口硬面包,说:“人渣,满嘴都是——”
“谎话。”
G夫人的声音像是从极高的地方落到他头顶上。他觉得寒冷,手指冻得发麻,冻得骨头发痛,全身的血都像凝固了。他应当已经不会被冻伤了,连过去手指上得冻疮留下的淤血块也消失了,但他还是会感觉到寒冷。后来亚伦·桑切斯的故事总是用一个谎言结尾:“最后天亮了”。实际上天没有亮,他从流淌着血横陈着死尸漆黑的矿道逃了出去,逃进了一个无月的漆黑夜晚。
亚伦·桑切斯出生在北方群山下的一个镇子,这镇子上的所有东西都是依托着它背靠的矿山存在的,这座山叫做达纳山,所以镇子就跟着被称作达纳。有很多事情都环环相扣,但亚伦并不知道,或者很久以后才知道其中的关联,比如说因为突然出现的死腐病和血药、突然变得疯狂的吸血鬼,外头出现了“猎人”这个行当;因为猎人兴起,需要许多武器,铜铁生意也连带着兴盛了,达纳山的矿上就需要更多工人;工头从南方招募来新的工人,南方来的工人就把死腐病也一并带来了达纳矿。不久之后死腐病就成了这里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得了疫病的矿工拼命地工作,期望自己在身体腐烂不能劳动前攒够买一份“良药”的钱,最后自然死在了这里,被抛进废弃矿坑里草草掩埋。人们总感觉死腐病是一种横加给所有人的灾祸,但后来想起来时,发现它其实也没有改变世界许多,死腐病出现前就有干旱和洪涝,有饥荒,在矿区就是矿难和塌方。亚伦没有感染上疫病,他遇到的是矿难,被困在坍塌的坑道里。所有人都死了,死亡本来是这里最寻常的事,得了病的矿工因为身体腐烂而死掉,健康的矿工因为事故而死掉,亚伦虽然因为一瓶被患病矿工偷藏着带下井道的血药而长出尖牙变成食人血的怪物,但未必没有机会苟延残喘下去,老矿工们喜欢对矿上的小孩讲这样的故事:一群矿工被困在坍塌井道里,等不来救援,开始互相残杀、同类相食,最后活下来的那个就会变成“鳄鱼”,变成一种嘴角裂开、牙齿尖锐、四肢干瘦但迅猛的怪物,那些废弃的坍塌的矿洞深处传出尖啸似的声音,就是饥饿“鳄鱼”的啸叫,它们仍然游荡在矿洞里,把落单的矿工当做食物拖走。矿工是很习惯亚伦这样的怪物存在的。
但一个老猎人为了这场血案来到了矿山,在这偏远矿山以外的地方,吸血鬼也划分出了许多派别,有杀人的,有中立的,也有通过血药治好了疫病却成了吸血鬼的,因此亚伦必须经历一次老猎人的审判,判决亚伦是否恶鬼,是否应当为矿井下死掉的人偿命。亚伦开始一遍遍地描述那里发生了什么,他作出了很多合乎情理的解释:偷藏了血药的伯尼病了很久,已经不能做重活,他害怕自己变成第一个被分食的猎物,因此用了药变成了吸血鬼,但他仍然很虚弱,他决定将被困者之中最年轻的亚伦也变成吸血鬼当做帮手;而亚伦逃跑了,他获得了超过人类的力量,于是从原本爬不上去的洞口逃了出来。老猎人未必完全相信他,但也没法从错综复杂的矿井里找到证据。G夫人——那瓶血液的来源,一名教会猎人,一个白肤冷面的女人,因为感应到了自己的血造就了一个新生吸血鬼而赶到这里——打断了老猎人的犹豫,她说:“把他交给我。”
G夫人的声音干涸嘶哑,像是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过话了。她指了指脸颊上证明她身份的圣痕,说:“他的血来自我,我用教会猎人的名义为他担保。”
他藏身的洞窟外面仍然是看不见月亮的漆黑夜晚,老猎人空着手离开了,G夫人即将带他去往他一无所知的远方。他想说点什么,但G夫人走近他,铁钳般掐住了他的下颌。
“谎话。”
她冷冷地说道。
“我最想不到的是雷涅那样的人也会有搭档。”
到了十七号,城里终于不剩下多少伤员,重要物品也都陆续搬去了城外的临时据点,倒是像把纳塔城让给了湖骸似的,医生那里的活计少了,罗斯得空便帮着布置炸药的猎人从洛多维科和亚伦的小型军火厂里运送火药出来。她一进门,就听到停不下嘴的洛多维科·里奇大爷一边忙活着配火药,一边闲扯些雷涅的事,分明是打算把雷涅和亚伦的家底一并打探清楚,好在下次合适的机会占些便宜。
“你们是怎么搭上伙的?雷涅那样的家伙,”他比了个夸张的手势,“吃饭都恨不得一个人坐到天边去。”
这叫耗子女士也忍不住好奇了起来,她只抬了个头,就被洛多维科发现了,松鼠朝她挤了挤眼睛,招手示意她过去坐着一起听:“别急,休息会儿,等我这包做完了一起搬。”
独眼猎人正坐在屋子另一头小心翼翼地熬煮着什么东西,屋子里飘着一股隐约的甜味,想来锅里煮着他们说的白糖,回答说:“就是……那么样呗,我帮过他,他也帮过我,不知不觉就经常一起行动了。”
洛多维科显然不太满意这个回答,继续问他:“那怎么不见他在纳塔城也有搭档!你是西南那边来的?比昂人?”
“不是,是靠海湾那里的一个小镇子,那里没有工会,猎人很少的。”
“不对啊,你这是矿上的手艺,海湾那里哪有矿区?”
“我小时候在北方那里的矿上做工,达纳那里,出铜矿的。”亚伦手上边搅拌着锅里的东西边回答他,好像正自然地说着他真实的经历一般,“后来矿上闹疫病和吸血鬼,乱得很,我又遇到了矿难,被困在矿底下,困了好多天,幸好来了猎人。”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我也不知道地面上发生了什么,最后天亮了,我获救了,就跟着当了猎人,去了南方。”
“那你可走得真远。怎么样,会想回家乡吗?”
“那么你们呢?”亚伦突然反问,“你们都是纳塔人吧?”
洛多维科和罗斯不约而同地点了头,他就接着说:“你们要炸掉自己的家乡。”
“有什么不行吗?”洛多维科轻快地说,“城市不过是一堆石头和砖头,我的家乡已经被诸位同行搬去外面的森林里了,对吧,尊敬的猎人罗斯女士?”
“我们亲自炸掉,我们亲自重建,”一直坐听着他们说话的罗斯突然挺起身子,好像一个迷你版、完全不像斯塔夫罗金医生的斯塔夫罗金医生,“就该这样。”
洛多维科点了点头,刚好配好了一包火药,包装好交给了罗斯,又不知从哪摸出了一个三指见方的小油纸包,塞到了罗斯的另一只手里。“这叫职务之便。”他故弄玄虚地说。罗斯打开小包的一侧,看到里面装了浅浅一角白糖。那洛多维科已经转过脸,又孜孜不倦地继续打探:“你说西南那里没有工会?那有没有什么生意好做?我们现在也是过命的交情了,你可不能骗我……”
对不起,他说,对不起。
“骗子。”G夫人仍然这么说,“你根本没有在忏悔。”
她冰冷的手按在他的头顶,她说:“你杀了人,你不是被人变成吸血鬼的,是你抢了血药,是你杀了所有人。”
对不起,他说,我不想杀他们的,我流了很多血,我快要死了,那瓶药刚好在那里,我只是想活下去。
“你只是想活下去。”他听到G夫人的冷笑,“你只是想活下去,所以把他们都杀了,你只是想活下去,所以说谎也是可以的,做什么坏事都是可以的。”他放在地上的手被她踩在脚下,他听到骨头咯咯断裂的声音,却不再感觉疼痛了,骨头断了很快就会恢复,然后再被打断,大概时时都在疼痛中,反而就感觉不到痛。G夫人按在他头顶的手向下滑过他的右脸颊,自从他喝下西比迪亚的血、背后被打上圣痕烙印,他的右眼就看不见了,也不会再流泪了。她的手掐住他的下颌,逼迫他张开嘴,她说:“那么向你的‘朋友’说谎又是为什么呢?假装猎人是为什么呢?也只是为了活下去吗?”
他感到背后发凉,烙印在背后的圣痕却发烫,他好像听到烙铁在背后,皮肉滋滋作响的声音。对不起,他说。
“卑鄙的骗子。”她说。
十八号的清晨,天还没有完全亮起来。亚伦·桑切斯即将去炸毁一座他毫不熟悉的城市。寄给纳塔城东城区玛格街二十八号诺利亚先生的信还在他的背包里,猎人们正在将湖骸往陷阱里引诱过去,火焰将会吞没这座城的东城区,吞没破坏这里的怪物,也吞没他们要守护的街道,吞没真实存在的许多人的家乡故土,自然也会吞没那条不存在的玛格街,吞没虚假和谎言。
最后天亮了。
———End———
Q:为什么盖亚女士总是被称作G夫人呢?
A:因为小编总觉得喊盖亚夫人她会突然变身。


“英格丽……”奈杰尔·戈林的声音抖得不像样,他大口地喘着气,尽管他的眼睛看向自己但是视线却颤抖着,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更是模糊了他的双眸,“英格丽……我,我……可能要死了……”
英格丽诗觉得自己的呼吸好像停滞了一瞬,过了几秒她才想起怎么使用自己的呼吸系统吸入氧气,也想起刚才奈杰尔同她说了什么,但她仍下意识地反问他,“什么?”
她希望自己听错了,或者这只是个玩笑。
那天风和日丽,蔚蓝的天空上只有几缕云被风推着飘过,阳光灿烂,当微风拂过树叶时叶片上的日光也因此摇曳,学生们三三两两穿过走廊前往教室,只有这片角落被太阳遗忘,他们藏身在此谈论不被日光所欢迎的死亡。上课的铃声准时响起,树梢上的鸟儿们发出受惊的鸣叫拍打着翅膀离开了,但是他们谁也没动。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医生说我……得,得了疫病……”他的声音逐渐变小,仿佛他用来谈论此事的勇气也正被逐渐耗尽,那双眼眸渐渐垂下,本来明亮的绿色染上一层阴翳。
“那你今天是来……”
那张已经签过字的退学通知现在正躺在奈杰尔的书包里。
“英格丽,要是我不在了——”
“别说了!”她立刻用力抱紧奈杰尔,他的颤抖通过接触的身体一览无余,无论她如何想要把自己的力量传递给他都停止不了,最后她的声音也被这不安传染了似的不住地发抖,“别这么说,一定会有办法的。”
她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已经躺在冰冷的墓穴中的母亲。濒死时那可怜贵妇人不再容光焕发,她整日卧床脸色苍白,两颊凹陷,嘴唇上是皲裂造成的细小伤口,双眸中如同蒙了一层擦不净的灰尘。最后她连话都说不出,只是张开嘴徒劳地想要吸气,难看的挣扎片刻后她在家人们的哭泣中离开了。英格丽诗被那无神的眼眸钉在原地动弹不得,直到父亲合上母亲的眼睛,兄长走来牵起她的手。
“尼尔,”她松开奈杰尔,抬起手臂用袖子擦掉没有掉出来的眼泪,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她不想让这双眼睛里活人的神采消失,“我会去找凯蒂小姐,她是最厉害的教会猎人,她一定会有办法的。只要你说你想活下去我什么都会为你做的!”
“英格丽……”他张开双唇声音却陡然变化,“你可真是个傻孩子啊。”
眼前的玩伴忽然变成了白发赤瞳的教会猎人,她嘴角上翘微微露出牙齿好像在嘲笑英格丽诗。
“什么意思?”眼前的那个她一直崇拜着的教会猎人仿佛忽然变了个人,英格丽诗的脚步下意识地后退一步想要远离她。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会有什么办法能让人既不用变成血族也能治好疫病吧?真可惜啊,英格丽,要是那个时候多听听安纳托的话就好了,不过我想就算这样你也肯定会相信我吧?”
奈杰尔在被凯蒂接走治疗疫病后便音讯全无,而当她找来教会猎人的聚居地时面对的却是一反常态不再温柔的凯蒂,她掉进迷茫和无助的泥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一点点地按进绝望越陷越深。
“所以之前也是……在骗我吗?”
“当然了,不过我也没怎么骗你啊,是你自作多情呢。现在崇拜的泡泡被戳破是什么感觉?”
她记得那时的无措,但是这茫然很快变成了愤怒,她咬着牙握紧拳头,但还是克制着自己,“那奈杰尔呢?为什么他没有回来?你对他还做了什么?!”
“那我就不知道了,真不知道那条可怜的小狗摇着尾巴去了哪里呀。哎哟,他居然没去找你吗?也是哦,他可怕变成血族了呢,毕竟那样就会被你讨厌了。”
她记得当时自己被其他教会猎人拦住,但是现在这里没有别人,她冲上前去扼住凯蒂的脖颈将她按倒在地,原本稚嫩的身躯忽然变成强而有力的成年人的体型,那双不知夺去过多少血族性命的手现在死死掐住凯蒂的脖子,但不知为何凯蒂不仅没有露出呼吸被遏制的痛苦神情,甚至那恶毒的话语也仍不停地从她一张一合的嘴里倾泻而出。
“你要杀了我吗?因为我骗了你还是因为我是该死的血族?那你为什么不杀了奈杰尔·戈林?是想从他身上捞一笔?觉得他还有用?”
不是的!
“把他关在地下室里就能让他待在你身边了吗?给他喂了自己的血就能拴住他了吗?那为什么还要钉死窗户更换门锁防备同僚,你也觉得他其实变了不是吗?”
不是的!
“承认吧,英格丽诗·阿忒利亚,因为你的愚蠢变成现在这副模样的奈杰尔,你把他关起来可不是什么伟大的友情和责任心,”凯蒂的声音忽然凑近她耳边,“你真正的想法——要是他就这么消失就好了。”
“不是这样的!”她大吼一声举起拳头打算砸下。
她想说不是这样的,她想和奈杰尔说的不是这些,因为她的愚蠢变成血族的奈杰尔,因为她的弱小无处可去的奈杰尔,她一直想对他说的是——要是我能拯救你就好了。
奈杰尔尚未从窒息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捂着刚被松开不久的脖子蜷缩着身体大口喘气好让空气再次灌进肺部,但是喉咙被压迫的不适感让他想要干呕,他也因而剧烈咳嗽起来。
当他终于止住咳嗽恢复正常呼吸时不远处的缠斗也已然结束,胜利者逆着月光站在他身前不远处,对方的黑发被月亮镀上了一层银色,那人的面容却在阴影中模糊不清。他用手臂撑起上半身而双腿则屈起推着身体向后挪动。这个人是谁?他是血族还是人类?不管是哪一方对于奈杰尔来说都很糟,尤其是对方的实力足以制服英格丽诗的情况下。英格丽……他甚至不知道倒在不远处的英格丽诗是死是活。
“奈杰尔……戈林?奈杰尔?是你吗?”
就在他还在拼命动用大脑寻找对策时对方的问句和那熟悉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考,那个曾经坐在他的对面,在他叔叔拉着窗帘的书房里同他一起念诗的男孩的身影从他记忆的角落里被打捞出来,而当那人走到他身前缓缓蹲下时那面容渐渐和他的记忆重合。
“洛基?可是,为什么……”他本想抬起手抚摸那张熟悉的脸但是却猝不及防地被拥入怀抱,像是生怕他再次突然消失洛基的臂膀紧紧箍住他,尽管这让他感到不适但是对方的颤抖和啜泣却也因此通过接触的身体同样颤动他的心,奈杰尔尚未放下的手只能顺势抚上他的背。
过了好一会儿洛基才冷静下来,尽管他看起来已经是个成熟的成年人,但是当细小的泪珠挂在他的睫毛上时奈杰尔还是能想起那个小时候总是撒娇假哭的男孩。他伸出手想要擦去对方的眼泪,但意料之外的冰冷体温却让他一愣。
洛基用和他一样冰冷的手掌握住他的手抹掉自己下睫毛上的眼泪,而后他抬起头看向不远处的马车,“那是你们的车?”
“嗯,那边的祭坛上有一个钟,英格丽用它击退湖骸之后就……”
“那我们可能要先走,湖骸很快就会回来。”他起身将奈杰尔从地上拉起来,“我去搬阿忒利亚,你先回车上。等会儿我来驾车”
“好。”
好在不远处就是工会猎人的营地,凭着英格丽诗的徽章他们得到了在这里短暂休息的机会。他们也终于得以了解这些年来彼此的故事。
“没想到我走不久以后你就……”
“哈哈,别那副表情,成了血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今天多亏了阿忒利亚状态不佳,不然倒地上的就是我了。”洛基说。
“那你怎么会在这儿,教会猎人的总部不是在北边吗?”
“你该不会以为湖骸的事闹得这么大教会猎人什么都不会做吧,上面这些大人物可会差遣人了。”
“原来做作业偷工减料的家伙也会努力工作。”
“这么久不见你讽刺人的本领倒是见长,”洛基抽掉最后一口烟把烟头丢出车厢拉上车门,现在他们的谈话不会有第三个人听见,除了还在昏迷中现在靠在奈杰尔肩头的英格丽诗,“所以阿忒利亚用了那个钟,你们怎么知道那个的用法的?”他朝着英格丽诗抬了抬下巴。
英格丽诗闭着眼睛,身体随着呼吸有节奏地起伏,确认她没有醒来后奈杰尔才看向坐在对面的洛基,但他没有直接回答洛基的问题,“……你来这儿的时候看到凯蒂了吗?”
“那可是个大忙人,就算在总部也要撞大运才能看到她呢,”但是很快洛基就反应过来这当中的意有所指,“是她告诉你们的?”
“她就是喜欢透露这种消息不是吗?”奈杰尔冷笑一声,而洛基的脸色很快变得认真而严肃,他忍不住问道,“怎么了?”
“……我不是很能确定,但是……等阿忒利亚醒来之后你最好提醒她,你自己也要注意,”他的手放在奈杰尔的肩膀上,“有血族知道你藏身在阿忒利亚家。”
“你是说凯蒂把我的消息透露给血族?可是……”忽然一个可能性闪过他的脑中,他用手捂住嘴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放下,“被她取了血做良药的血族没有死,而他需要我。”
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任何可以折磨英格丽诗的事情,无论是治疗疫病的谎言,把自己变成血族,透露他和英格丽诗的藏身之处,凯蒂都不遗余力地做到,而且效果很好。英格丽诗因此伤痕累累,但他却无能为力,甚至被她拿来变成折磨英格丽诗的工具。
“我也说不准,我只是在舞会上偷听到一些消息,但是小心为上,”说完洛基推开车门将右腿跨出车厢踩在地上,他回过头看向奈杰尔,“我就不等到阿忒利亚醒过来了,我可怕死她了,以后有机会我去找你。”
“说的也是,我可不敢保证她见到你不会先揍你一顿,”奈杰尔挥挥手,“再见。”
“再见。”洛基眨了眨眼而后关上车门。
被窗帘遮挡的车窗外逐渐亮起来,光线被阻挡在外面只能模糊地让车厢里摆脱些许昏暗,英格丽诗沉睡中的脸庞也因此清晰了些许,奈杰尔摸了摸脖子,现在那里已经感觉不到任何疼痛,好像被英格丽诗扼住脖颈只是一场噩梦,他将头轻轻地和英格丽诗靠在一起。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英格丽诗才能从这一切里解脱出来,什么时候自己才不会成为凯蒂胁迫折磨英格丽诗的手段。他合上眼睛,如果可以的话,他想,或许那个时候没有和英格丽诗说“想要活下来”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