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绝不见死不救。
第二,绝不放过任何邪恶。
第三,绝对公平正义。
兀烈卡卡牧师,参上!
已经彻底变成了特摄片片场。
——————————————————————————————
如果每一次冒险都有一个高位的、无形的“神”来评分,那么这一次行程中的赢家无疑是奥菲利亚。整趟行程中唯有她达到了自己的愿望:亲耳听一听海妖的歌声。
并且不止听了一次。
据人类战士与空木桶女士无情的描述,在他们循着落单海妖的歌声抵达第一个小岛的过程中,在疯诗人执意要亲耳听听歌声而摘下耳塞后,诗人忽然失去了自我,并将所有的力量都投入了“去往歌声的来处”这一事业中,最终以一己之力把载满人(和精灵以及鸟人)的小船划到了海妖所在的小岛上。
但那一趟歌声的代价是一场宿醉,就像她偶尔变得阔绰并逃脱了追捕后,去什么小酒馆里痛快喝了一顿酒后的经历:她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是最后一杯苦艾酒下肚,再醒来的时候要么在监狱里,要么躺在一地在她的演奏中昏厥的人中间(然后她很有可能又得去监狱)。
昨天也和那些宿醉差不多,她醒来时,脑袋里嗡嗡作响像有三百只蜜蜂乱窜,她的“队友”们已经在和海妖和乐融融地交谈,而她压根不知道自己刚刚渡海的壮举——于是她发明了一个新的名词“醉歌”。
现在,卡隆撒和梵塔西娅都能有幸体验一下“醉歌”了。
被他们放出笼子的海妖们一同歌唱着,盘旋在小岛上空,像即将远行的候鸟。食人魔被歌声困住,虽然它们的脸上很难看出脸色和表情的变化,但奥菲利亚猜想他们的表情应该和卡隆撒以及循着歌声赶来的梵塔西娅差不多,活像吃坏了肚子。
原本奥菲利亚会因此感到些快意,因为她分明地记得自己“醉歌”醒来后人类战士和精灵牧师投来的表达了“噢,一个醉汉”的眼神,而现在是个回报他们的机会,毕竟奥菲利亚比他们多了点宿醉的经验。但现在有另一样东西吸引了她,门,那个非常明显跳进去后生还概率会极低,怪异的紫色的门,在海妖们的合唱中扭动起来了。
此行中的赢家是奥菲利亚,此言非虚。她现在不用跳进那扇门就能知道门里有什么了,或者说知道了部分:门里伸出了半透明的须状物,也可以叫它们触手,因为它们看上去九成九地是一个庞大生物的一部分身体。
那会是什么?一只巨大的半透明鱿鱼,盘踞在一片蛮荒土地上?是退化了的远古巨兽?或是某个世界独有的自然现象?
她入神地看着那些东西,海妖优美而刺耳的歌声也渐渐模糊,仿佛从极遥远的地方传来什么人的说话声“就是那个!是那个家伙指使的食人魔!”可她完全没有听在耳中。
她的眼中只剩下了那些触手。它们像裹挟着整个北地的寒风而来,像她阔别已久的寒冬,像深林城外碎冰漂浮的河流的拥抱,又比那些更冷酷,如冰冷的矛戈刺入骨缝。触手的冰冷让海妖歌声带来的头痛也减弱了,她敏锐而冷静地发现,触手的动作会因海妖的歌声而变缓慢一些,以至于疯诗人错觉自己的头脑前所未有地清醒,她决意要做的事情也无比地理智和富有价值——
第一,绝不见死不救。
第二,绝不放过任何邪恶。
第三,绝对……
梵塔西娅·轻歌,深受兀烈卡卡眷顾的牧师,年轻的剑客,在耳膜和脑袋共同的刺痛中,已经来不及想第三条了。
在她想明白任何事情之前,她就已经一手抓住疯诗人的斗篷,一手扣住她的脖子,拽着奥菲利亚向他们上岸的方向狂奔而去。海妖们在头顶盘旋。
她的脑中一片空白,并不知道自己这么做的具体理由,一切都凭着直觉和本能。在狂奔的途中,她的大脑才有些许机会缓慢地运作:她记得在她做出这些动作前,看见疯诗人不知从哪摸出一把小匕首,奇怪,那是藏在哪里的?她看见奥菲利亚拿着匕首,缓缓地,带着痴迷(很明显犯了疯病)的表情,走向离他们最近的一根触手。
她不知道奥菲利亚想做什么。这个疯诗人就算是想去切一块触手下来带走也不奇怪。
她只知道诗人想做的事情无比地、极度地、仅次于跳进紫色门地危险。
众——兀烈卡卡牧师——所周知,第一,绝不见死不救。
至于被她扣住脖子拖走的奥菲利亚喉咙里发出的窒息的咕噜声,抱歉,她得跑到相对安全些的海岸边才能听到。
“每一片歌声都有自己的岛屿。”
奥菲利亚忽然说道。
可是她的话又没有了下文,好像她只是在刻意地为这趟任务点题一样。
他们(主要是卡隆撒和梵塔西娅,奥菲利亚正趴在一边缓着喘气)在追兵到达前成功地用小船的残骸拼凑出了一个能运载三个人的东西。海妖拖着他们的小舢板,往不远处的另一片岛屿航去。
渐渐远去的岛屿上传出了古怪的歌声。那应该是那生物愤怒的咆哮,不可思议,他们都能听出声音中的愤怒,可那听上去又实在是一种古怪的歌,一种古怪的语言。难以名状的怪异围绕在他们心头,又很快地,被死里逃生的庆幸盖过了。
诗人哼起了歌。梵塔西娅警惕地看向她,接着发现她确实只是在哼歌。于是积攒至今的疲倦一下子向她袭来,她倚靠到舢板的边沿上,抬头看着成群的飞翔的海妖们。小舢板在海浪中摇摇晃晃,令梵塔西娅想起过去读过的某篇童话,童话里描述了一艘由天鹅拉着航行在天空中的城堡。
诗人的嗓音低沉沙哑,像被无尽的风沙和冰雪打磨成这样粗粝的样子。
她听到诗人含混的哼唱里混杂着几句熟悉的句子,
“……缱绻白云之上,
那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群鸟环绕,金碧辉煌,
天鹅拉着这座王国航行……”
她想说,原来你也会唱这样的童话,但她疲倦得不想开口。夹着风沙的粗粝嗓音唱着童谣,和梵塔西娅爱听的密林歌手的歌声截然不同,但又难以笼统地称为难听。她刚想因这温柔的童谣对疯诗人改观那么一点点,就听到歌词忽然变得陌生,
“……不可名的邪恶侵入城堡,
将国王刺杀在王座,
昔日荣光就此黯淡。
今日旅人见它驶过,
鬼怪群魔,盘踞在此,
飞鸟的骷髅拉着这座魔窟航行……”
……
算了吧。梵塔西娅极其难得地想。在听过会把大脑搅成土豆泥的海妖之歌后,这胡乱的诗歌听上去也令人愉快。
他们走后,海妖去了新的岛屿,不可名状的门和怪物占据了海域一隅,人们继续在阿尔沃兰航海。
END
字数2245
草率结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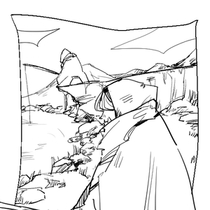


字数3516
“你在生气吗?”
没有人回答他。
巡林客等了一会儿,又问道:“你在生气吗?”
这一行有三个人,或者说,三个类似人的生物:一位海豹妖精,一位狗妖精,还有一位兽人。提问的是浪歌,虽然他没有指出姓名,但显然,他询问的对象是文丘里。
也许是他们沉默了太久,激发了弗洛斯缇肩上鹩哥的些许责任感——也许鹩哥天赋的责任就是这个——它忽然发了声:“你在生气吗?”
文丘里还是没有回答,他默默走在最前面。在兽人中也不算矮小的身材堵在两位娇小的妖精前面,如同一座会移动的堡垒。
树林里静悄悄的,天气渐暖,连融雪滴落的声音也没有了,只有鹩哥孜孜不倦地重复着:“你生气了吗?你生气了吗?你生气了吗?”
这好像不太妙。
弗洛斯缇想。
她知道这幅情景的起因。上一次出来狩猎的也是她,浪歌和文丘里,如果说文丘里因为什么在生气的话,多半就是因为兔子和鹅了。因为他没能吃到兔子,也没有吃到鹅。前者被饲养了起来,这是个好的决定,因为其中一只怀孕了,马上就能有更多兔子;后者成为了他们的看门狗,那只鹅说不定比真正的看门狗更凶悍。
也许每个种族都有外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但至少热爱肉食不算对兽人的刻板印象。在这段只有腌菜吃的日子里,弗洛斯缇几乎可以看见文丘里的眼睛里露出凶光。
她忽然打了寒颤。
上一回就是她和浪歌拦住了想捏死兔子和鹅的文丘里。
但好消息是,浪歌和文丘里更熟悉一些,而不断询问文丘里是否生气的也是他。这么想着,弗洛斯缇眼疾手快地捏住了鹩哥的嘴。
我们都别卷进去,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没有了鹩哥的声音,树林里又重归安静。浪歌忽然拽住了文丘里的斗篷下摆,又问了一遍:“你在生气吗?”
文丘里停住了脚步。
不妙。
弗洛斯缇把鹩哥捞到怀里,小心地退了半步。
好在文丘里没有发难。大概武僧的修行真的很修身养性,连兽人都变得好讲道理了一些。
文丘里说:“没有。”
弗洛斯缇松开了鹩哥,它扑棱几下又跳回了她的肩膀,打定主意要在那里安家。
虽然她听不出兽人的语气,但常理来说,生气的兽人是不会委屈自己忍耐的。她轻松了一些,决定不管他们,专心地观察起林子里的情形。
热爱肉食一定不是对兽人的刻板印象,但其他的可就说不好了。兽人确实都不怎么喜欢忍耐愤怒,可弗洛斯缇认识的这位兽人,可是一个实打实的武僧——武僧的第一课就是忍耐。
文丘里学到的第一课就是如此,忍耐你的愤怒,不再像兽人一样用怒火作为自己的力量和武器。虽然他的头脑是一颗兽人的头脑,但他做到了这些。
这也许算个悖论,至少文丘里想不明白。他离开部落,选择成为武僧是为了复仇,向他的酋长复仇——他输了,被揍得半死不活,被所有人嘲笑。他可以选择站起来,向酋长的背影冲去,并被杀死,被遗忘;可以选择带着失败者屈辱和羞耻,继续活在部落里;或是像他选的那样,离开部落,寻求力量,最后回去复仇。
这是个俗套的兽人故事。兽人故事差不多都这样,人们看他们作破坏者、混沌者、愚昧者,但他们也因此过得简单又明了。
他的老师,在听完他故事后却对他说:“如果你想获得力量,那么你要忘记仇恨。”
这多奇怪啊,文丘里想要复仇,那么他就要活得力量;但为了获得力量,他必须先忘记仇恨。
他当然想不明白。
想得明白这件事的兽人也许能够做个法师。
文丘里还是照着做了。你看,兽人就是这样的,他们想不明白很多事情,但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决定了的事,哪怕这事是要他们忍耐。他努力地忘却那些事,即使他常常会想起粘附在自己身上的耻辱。对于兽人来说,这是最大的耻辱了。
武僧的身份高于兽人的身份,他的老师说,你先是一个武僧,然后才是一个兽人。武僧的守则排在最前面。
忍耐到最后总会有收获的,他的老师还说。
——如果陨石没有来的话。
这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陨石毁灭了这个世界,当然也包括他的部落和酋长。酋长死了,可他丝毫不觉得自己复仇了,对他来说死于天灾和寿终正寝有什么区别?可他再也没机会真的去复仇,因为他不能再杀死一个死人。更糟的是,文丘里的复仇是为了洗刷他的耻辱,对兽人来说,失败,并苟延残喘着是最大不过的耻辱了。
他无法报仇,就无法洗刷这份耻辱。可知晓这份耻辱、在乎这份耻辱、施加给他这份耻辱的部落都已经不在了,那么这份耻辱还存在吗?
这比前一件事还要复杂。老师让他忍耐,至少还许诺了他力量,但现在连老师也死了。连回答他问题的人都不剩了。
文丘里在生气吗?
他确实在生气,让他生气的事情有很多。
专注于环境很快就有了收获。弗洛斯缇高兴地喊了她的队友们(他们好像在默默无言地交流点什么,但鬼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男人太难懂了):“有动物的脚印!”
武僧和巡林客立刻凑了过来。融雪让林中的土地变得泥泞,于是动物的脚印被保存得很完好。那是动物的蹄印,但本该对此经验丰富的巡林客却没有立刻说话,而是德鲁伊弗洛斯缇欣喜地说:“是鹿,有好几只。”
武僧和巡林客一起发出了欣喜的声音。
几乎是在同时地,他们两个说道:
“太好了,我们可以把鹿也养起来。”
“太好了,我们可以吃鹿了。”
树林里忽然安静了。
不妙,太不妙了。
弗洛斯缇又迅速地抓住了鹩哥,把它护在了怀里,并且捏住了它的嘴。
如她所料,兽人和海豹妖精看向了对方。
“我们吃鹿。”文丘里说。
“养起来慢慢吃更好嘛。”浪歌仿佛没有听出他话语里危险的气息,又或者是他根本不在乎兽人的危险,他快活地说,“像兔子一样,鹿也会生小鹿。”
噢,你为什么要提兔子。弗洛斯缇退得更远了一些。
尽管如此,她还是幽幽地、冷酷地、打破某些人幻想地说:“那可是鹿,你就不能好好想想吗。”
上一回林子里有水禽,这一回有好几只鹿的足迹,说明这个林子里至少有一处能供它们生存的水源。天气已经转热了,融雪和村里的井恐怕不能维持供应给所有人,找到一处水源的意义远大于几头鹿的肉和皮毛。稍微动动脑子就能想通,就算是兽人的脑子。
下一瞬间,在弗洛斯缇考虑要不要离开去找鹿,让两位男士自己交流的瞬间,她看见文丘里拎起了浪歌,拎着他的海豹皮斗篷,然后——
——他把浪歌扔了出去。
像过去,某些地方有的那种掷铁饼的游戏一样,把浪歌扔了出去。
至少天还是很蓝的。
弗洛斯缇绝望地看了看天空,想到。
大家都知道浪歌失忆了,也知道他是依靠自己随身带着的武器和身体记住的技能发现自己是个巡林客。这说明浪歌至少在巡林客的技艺上,是相当合格的。
他被文丘里扔了出去,理所当然地,他在空中灵巧漂亮地转了个身,借着力踩在树干上,再用力一蹬冲向了文丘里。得益于妖精小巧的体型和巡林客优异的敏捷,浪歌冲向文丘里时快得如同一支弩箭,一颗弹丸。武僧的反应不算慢,相比于体型得天独厚的巡林客还是慢了一拍。
浪歌在落地前扭了半圈,避开了兽人的拳头。那拳头比他的脑袋小不了多少。他落了地,手扶上了腰间的匕首,但仍然没有抽出它。
有一瞬间,他闻到了血腥的味道。没有人流血,自他和文丘里到达这个镇子、遇到其他的幸存者开始,就没有闻到过新鲜的血。他从空白的脑海中搜寻,并不能想起上一次闻到血是什么时候,也不能回忆起与血有关的场景。
可他偏就知道这是血的味道。这一瞬间的幻觉,是血,新鲜的血,刚从血管里喷涌出来,还带着蒸腾的热气。
他眼前是兽人的膝盖。他按在匕首上的手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青绿色皮肤被割破,血液喷涌而出的场景仿佛就在他眼前,和刚才血的气味一样一闪而过。
武僧的拳头也相当迅疾。浪歌迅速地停止了臆想,在逃开前狠狠地踹了一脚兽人的胫骨,并借着力向后退开躲开了下一拳。
难以言说的感情在他胸口激荡,他的心跳却规律而平缓,仿佛身体已经准备好了进入战斗。
匕首仿佛在呼唤他,拿出刀,给这个不识好歹又愚笨的兽人来一刀,不一定会要他的命,但可以让他清醒一点,知道到底谁是头儿。
也能让他闻一闻血的气味……
他回过神时,匕首已经被他握在了手里。
他对此惊异了片刻,在他迟疑的时候,文丘里的拳头砸碎了他落脚的树枝,让他被被迫跳上了更高的位置。文丘里也看见了他抽出了匕首,可那兽人眼中竟然流露出兴奋,兴奋,却并没有多少杀意。
这也让他意外。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又来不及想通透。血腥味消失了,甚至难以想起这份气味。
他的身体自己动了起来,匕首划破了文丘里的手掌——文丘里悍然伸手握住了他次过来的刀,另一只手捏住了他的脸——他想捏的应该是脖子,但他的手掌相对于海豹妖精的脖子过于大了一点。
“你不错。”文丘里竟然这么说道,“你算是个勇士。”
他送了手,让浪歌落到了地上。
浪歌闻到了血。真正新鲜的血,刚从血管里流出来,温热,腥臭。他看了看手里的匕首,上面兽人的血还在散发血腥味。
可是这真正的血腥味,竟然如此索然无味,好像血本是一样普通极了的东西,他刚刚对血的渴求真正是幻觉一样。真奇怪。
他撇撇嘴,在树上蹭掉了血,把匕首收回了鞘。
“那么我们可以沿着鹿的脚印去找它们了吗?”
弗洛斯缇问道。
她想了想,补充道:“首先,我们应该跟着它们,找到水源。我们的水已经不多了。”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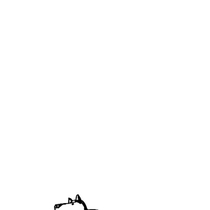


奥菲利亚给一切找到了最合理的解释。
她被捕了,显而易见地,愚昧之人因为她拿走了一本两百年没人翻过的旧书就拘捕了她,拿走她的手风琴,要把她流放到学者最讨厌的海中孤岛上。在那种地方纸张很难保存,还会有比愚昧之人更愚笨的狱卒监督着囚犯们做苦役。
这趟有个烦人的红发小牧师喋喋不休的旅途,显而易见地是一趟被幻觉修改过的押解,是一趟流放。奥菲利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会习惯梵塔西娅聒噪的规劝,她会从梵塔西娅身上寻找“正常人”的锚点,在过于孤寂的夜晚她还会希望梵塔西娅发出些噪音。最后在她真的接受梵塔西娅的存在时,忽然之间就会醒来,发现“梵塔西娅”是她的臆想。这是三流诗人最喜欢的故事模板,连奥菲利亚自己也编过一两首这样的叙事诗。
名叫卡隆撒的战士大约是真的存在的,可能是和她一起被流放的囚犯,因为狱卒很少像他这样快活轻佻;记不清名字的商会人员大约是什么官员,记不清名字的疯人大概是那类评估犯人能力和精神的牧师,奥菲利亚知道有这道程序,她有经验;海妖作为故事中囚徒的意象倒是很有意思,也许其中有关于吟游诗人的隐喻,而食人魔作为狱卒就有些中规中矩了。
但也是一种很合适的意象。它们丑陋,愚笨,对待囚犯恶毒而狠辣,是一种仅仅出现在那里就会让囚犯恐惧的形象。确实是这样,奥菲利亚更确信了一些,因为那只被他们一行人从另一个孤岛上带来的海妖面对着食人魔狱卒的尸体难以自制地发抖。
没错,他们杀死了一个食人魔。这幕俗套剧目终于有点趣味了。
一个巨大的、凶恶的、拿着大棍的食人魔,獠牙有半个梵塔西娅那么长,皮肤厚得像七层小牛皮皮甲。它戴着耳塞,毫无疑问,在一座海妖之岛上的食人魔毫无疑问会在耳朵里塞点什么。奥菲利亚的歌曲因此大打折扣,她本来一个人就能放倒这种家伙的。
如果那只吓得快昏厥的海妖能开开尊口帮帮她,说不定这个食人魔就不会锤断墨利安的腿了。
她是个海妖,这岛上明明有整个养殖场的鸭子那么多的海妖。她们只要动动嘴,把随便什么怪物引到海里去,就根本不会有这趟见鬼的任务了。
于是他们不得不在食人魔的脚下绕来绕去,像在陪食人魔扮演踩蟑螂的主妇。梵塔西娅和卡隆撒持着装饰精致的细剑,造成的效果类似于用牙签戳发疯的公牛,让公牛更加暴怒。最后是墨利安立了功,敏捷的巡林客从树上跳到食人魔的脖子上,用他的双刀戳进了食人魔的两眼。
代价是他被食人魔的棍子扫到了左腿。
幸好卡隆撒和萨穆尔的速度足够快,他们及时割断了食人魔的气管,让它来不及因为痛苦和愤怒而变得更加难缠。感谢需要转脑袋的生物都有脆弱的脖子。
最后他们一起坐在食人魔小山似的尸体旁边,(除了奥菲利亚)沉痛地决定让翼族青年把受伤的巡林客带离这座岛,因为这座岛上的变数太多,对于一个伤了脚的巡林客来说过于危险了。
奥菲利亚忙着研究食人魔的尸体。梵塔西娅没时间管教她,于是她踩在腥臭的血液里,爬到食人魔的背上,用小刀费劲地割了一条后颈肉下来。她试了试,这条应该是食人魔身上最柔软的肉也又硬又韧,完全不适合食用,严重的异味和泛着黑紫的血说不定还有毒性。要知道,在某些记载里,食人魔是会吃自己的排泄物的。
奥菲利亚叹了一口气。她想,这也许是个真的食人魔,要不就是这个丧心病狂的海岛监狱雇佣了食人魔来当狱卒。
“我的……我的同伴就是被这样的怪物抓住的。”在萨穆尔带着受伤巡林客离开之后,海妖说道,“它们突然涌到了岛上,在我们有所反应前就将姐妹们抓住了,剩下的姐妹也因为害怕其他人被杀而没有办法反抗……”
梵塔西娅率先开口问她,“这样的怪物还有很多吗?”
她似乎是负责交谈的人。可她甚至不一定真的存在,几乎像悖论似的。空木桶小姐,悖论小姐,奥菲利亚幻想中的小姐。
卡隆撒也开了口,询问食人魔是怎样来到这里、怎样攻击她们的。
海妖啜泣着回答他们:“在我离开的时候,它们有一只小队……那之后、我就不知道了……我能够记得的就是那天……有姐妹说,空地上忽然出现了个奇怪的东西,接着我能记得的就是它们突然出现……”
这是一场监狱的权力更迭。奥菲利亚想着,突然调来的新典狱长迅速地铲除了前任的势力,用更严苛的手段在囚犯中树立威信,老套,但还算有趣。
她听到自己的手风琴尖锐地响了一下。
奥菲利亚惊醒般看向梵塔西娅,但随即发现她并没有在警告奥菲利亚的走神,她只是漫不经心地把手搁在手风琴上,不慎扯出了一声锐响而已。梵塔西娅甚至没有在看她,她皱着眉头,思索着对策,红发覆盖的漂亮脑袋里装着莫名其妙的悲悯和梦想。
她分明是奥菲利亚早就抛弃的所有事物。奥菲利亚背叛过的、不屑一顾的、抛在身后的、属于“正常世界”的良善、正义和慈悲,都装在“梵塔西娅”小巧的身躯里。她究竟为什么出现?她是来自奥菲利亚抛弃的世界的鬼魂,要向奥菲利亚复仇吗?她是奥菲利亚不愿承认,不再想要的对还是正常人时生活的眷恋吗?
又或者梵塔西娅的存在并没有什么隐喻和深意,她只是存在着,像她空木桶似的头脑、像她坚守的现实和真实世界一样,仅仅存在也确实存在着?
奥菲利亚说不清自己想到了什么,她说不清现下心中怪异的感受。于是她只是突然加入了问话,像自始至终在一起认真思考一样:“再然后呢?就这样绑着养你们?”
海妖瑟缩了一下。她的眼泪快要落下了,她说:“他们强迫我们不断歌唱引诱船只……通常我们只会在需要男性时才诱惑他们上岛……一旦有姐妹没法歌唱了就会被它们……它们……”
她说不下去了,但他们都知道,食人魔被叫做食人魔显然不是因为它们饮食均衡。
梵塔西娅安抚着濒临崩溃的海妖,同伴的厄运让她一时无法再继续说话了。她终于把视线分给了奥菲利亚一会儿,发现刚刚才问出一个似乎有些意义的问题的疯诗人又神游般望着天空。
“你在想什么?”她忍不住问道。
疯诗人仍望着天空,漫不经心地回答她:“我在想,食人魔能设计出绑架海妖引诱食物的捕猎手段吗?”
她停了停,又说道:“我还在想,我们的任务是阻止海妖继续引诱船只。我们到底在烦恼什么呢?为什么不连着海妖和食人魔一起把这座岛烧掉呢?”
刚刚才平静了一点的海妖猛地一颤,又小声地啜泣起来。
卡隆撒责备地看了奥菲利亚一眼,连他都收起了笑脸。但在他真的责备疯诗人之前,梵塔西娅先站了起来,大步迈向了奥菲利亚。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她的声音因愤怒而压低,红发像真的烧了起来一样,“你怎么能这样说?”
疯诗人把目光从天上收回,盯着牧师碧绿的眼睛,脸上满是不解,倒像她是正常人,梵塔西娅才不可理喻似的。
“我说得不对吗?”她慢悠悠地反问,“还是需要我把‘清剿’翻译成兽人语你才听得懂?”
“她们是被胁迫的,这不是她们的错,不该让她们承担。”竟是卡隆撒替梵塔西娅回答了,他轻抚着海妖发颤的肩膀,像是在回答奥菲利亚,又像是在向海妖做出承诺。
奥菲利亚毫不掩饰地嗤笑了一声。她说:“是你们主动去商人那里接受的任务。”
“我们做这一切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船员不再受伤害,我们是为保护他人而来的,现在我们要保护受到伤害的海妖,这有什么不对吗?”
梵塔西娅的语气变得冰冷,假如奥菲利亚再说出什么不合适的话,卡隆撒毫不怀疑她会一拳揍上诗人的下巴。
“当然不对。”疯诗人完全没有感觉到卡隆撒的担忧,她兀自说着,不在乎任何人的目光,“仅仅因为你们发现在这座岛上的海妖是受害者,她们此前作的所有恶就一笔勾销了吗?在被食人魔绑架之前,她们从没引诱过水手,从没让人发过疯吗?”
“这是两回事,诡辩家。”梵塔西娅说道,“食人魔胁迫海妖捕食商船和海妖习性是两回事,我们,只,解决食人魔。死亡超过了海妖该为自己的习性付出的代价,这件事可以用其他的办法,在我们回去以后解决。”
“这就是关键所在了,悖论小姐,”奥菲利亚又嗤笑了一声,“这就是你的正义吗?你的正义只光顾眼下的弱者,你在不自觉地给弱者洗脱罪名。你凭什么判断什么人该付出什么代价,假使现在岛上没有食人魔,你的任务是为独生子发了疯的老父报仇,是为新婚的妻子寻回她的丈夫,你又要怎么宣判?”
梵塔西娅的手紧紧攥成拳头,她说:“我不宣判任何事。我只阻止弱者被伤害。”
“你在自欺欺人。被你杀死的时候,食人魔也是弱者。”奥菲利亚的神情出人意料地冷静清醒,一点不像她过去说胡话的样子,让人忽然意识到也许这残忍冷漠才是真正的奥菲利亚。她还想继续说,“护弱者是最愚蠢的事情……”
而梵塔西娅的拳头已经揍上了她的脸。
奥菲利亚被这猝不及防的一记重拳打倒在地上。她刚蹲坐起来,梵塔西娅就拎着她围在脖子上的斗篷,和她面对面地、一字一句地说道:“这就是我的正义,我,保护弱者,阻止一切不该发生的伤害。这是弱者应得的公正,这就是我的正义。”
红发的牧师和疯诗人沉默地对视着,诗人突然笑了起来。雪精灵的眼睛是极浅的蓝色,过浅的瞳色让她看上去更加不稳定。她擦了擦鼻子和嘴唇上的血,说:“好,那这样呢,你怎么判断这样的事?”
她猛地捧住梵塔西娅的脸,用还在流血的嘴唇狠狠碰上了她的嘴。
噢,那应该算是个吻。
FIN
字数:3546
(我不知道我在写点什么,我是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