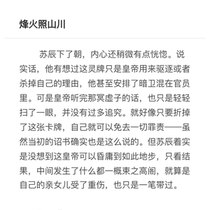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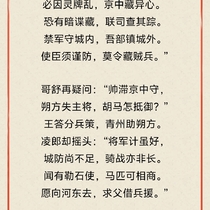



谢谢陈怀澈大人借的银征服。
周郎妙计安天下(大概)
-------
草原的天暗得比中原晚些,夕阳的光烧得草场红彤彤的连成一片,带着暑气的风吹过,金红色的海便波光粼粼地鼓动起来。
夏季的草场尚且青着。一个牵着马的身影劈开了草浪。人烟、马粪与牛羊的腥膻顺着晚风飘来: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几近看不出的道路向前走去,此路向前不远便是一处大集,羊毛织成的大帐层层叠叠地将中心的牙帐围住,旅人紧了紧马背上的行囊,事到如今,在离大集不到半座山头的地方,旅人长叹一口气:自己在这草原上见了十次日出日落,终于将这条长路走到了尽头。
从大集处远远的有几个人影见着了旅人,聚集了六七人近来。为首之人牵着马,披挂着半身皮袄,正一副霜原好汉的模样。那人隔着老远便叽里咕噜地喊起话来,指着青衣旅人,身后六人散开至半圆,隐隐地包围了来人。旅人辨着顺着风传来的词,似是霜原语中的“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于是远远地向着那霜原好汉作揖,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霜原语高喊:“我是周拂桢,乃是大烨来的使者!”
果然,那几人听了这话,互相交头接耳了几句,犹豫着散开了包围圈。为首那人点了队伍中的两人,不知说了些什么,那两人便行了个礼,策马朝着大集中央的牙帐飞驰而去。旅人——周拂桢心下了然,那二人定是向帐中的头人报信去了。才歇了口气,却听到那领头人对着自己高呼:“贵客不如将马放一放,与我一同往帐中歇歇腿脚,喝口茶水!”话音落定,又有一人前来牵马,周拂桢也不推辞,只拍了拍陪着自己走了十个日夜的劣马脖颈,将缰绳交予了来人。
“不知这位好汉如何称呼?”
“你叫我别日得便是。”
周拂桢借着暗淡的天光打量着别日得,一身半旧的袄子,磨得看不出颜色,身后背着的弓箭却是光滑漆黑。是个用弓的好手。周拂桢当下便有了定论。待到别日得领着周拂桢进了带着膻味的帐篷,两人在帐中坐定,饮了一碗劣茶,这才使着半生不熟的霜原话聊了起来。
“周兄弟来这里倒是颇废了几分力气。”
“别提了,这日头晒了一路,草原的路实在不便……”
又敷衍了几句,周拂桢饮下一口茶水,引着话题往时节上走。
“真不愿这时间走这些路,正是农忙的时候呢。”
“怎么不是呢,这时节该是羊儿吃草的时候……”
夏日的牧草鲜嫩饱满,正是牧人放牧的好时节。牧人最恨冬日,冷风与枯草如刀子一般将羊群的肥膘刮下。捱过一个冬天,羊群、马群饿得瘦骨嶙峋,春日的新草只是堪堪给牧群续上了命,只有到了夏日,牧草鲜嫩饱满,这才是牧群上膘的时候。平常的牧人自然是不会在这样的夏日驱使着牛羊马匹远赴千里地奔驰的,但话又说回来了,霜原也并非寻常牧人:受可汗驱使的族群,在宝贵的夏日抛弃了各部族的草场,前来为可汗取得下一场胜利。然而胜利是可汗的,那些耗尽了肥膘的马群却是各部族的,没有了积攒着的宝贵脂肪,这一个冬天对各家来说定是格外难熬。
别日得抿了口茶水,摇了摇头:“若不是为分些草谷,谁家愿意将马儿赶出草场,奔上这许多路程呢?”
“别日得兄弟也真是为部族考虑。”
“在夏日里征发这样多人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若是这次带不回够多的粮食铁器,这才是真亏呢。”
“草原的英雄倒会被粮食铁器难住么?”
“英雄也得起锅做饭哪。”草原的勇士用衣袖抹一抹嘴,“春里的局势也不好,部族还没赶得及去南边交易……”
粗劣的茶水在陶碗里打着旋——泡茶的茶梗用的是应当被择下的老枝,茶碗也未上过釉,挟裹着茶水泛起土腥味来。自然如此。周拂桢想。哪怕在中原,也不是所有军爷都能吃香喝辣的,再好的良家子,谁没有挨过两次饿呢?更不用说资源匮乏的草原了。天赐的大雨在关中转身离去,留下草原这片贫瘠的土地,这些甚至无法看天吃饭的人必然比中原人更饿、比中原人更渴,必然比谁都更渴望一碗浸着咸汤的饱饭。
“春日的集市没有赶上么?”
“是,去年买的盐都快吃完了,挨饿也就罢了,谁家没有饿过几顿呢?但是省着这些盐,族里的娃娃都没得力气了……”
周拂桢心中一动,却不说话,将茶碗放回桌案。披挂敲击的声响从帐外靠近,帐门一掀,一人大马金刀地叉手立在门外:“谁人是大烨的使者?”且看此人衣着规整,披挂甲片,衣摆上绣着缝边,腰间还挂着一柄大刀,想来就是头领的信使,于是立起,不急不慢地行了个礼:
“正是在下。不知有何吩咐?”
“随我来。头领想要见你。”
-
牙帐比起其他帐篷高了不止一倍。除去那些经过鞣制、缝在一起的皮子外,还缠着不少来自大烨的丝绸作装饰。十数个身穿皮甲、披挂金银饰品的部将吵吵嚷嚷地围坐着,即使是语言不通的大烨人也能从他们的神色中看出此时的愤怒。而在铺着羊毛毡地毯的牙帐中心,一座胡桃木色、饰着皮草的胡床上正坐着一位不怒自威的老者,此人不仅披挂齐全,甚至外袍还缠着丝绸光泽的布料——在大可汗南巡之时,这样的头人自然是这一整个大集的话事人。
而负手立在头人面前的青衣使者,尚未擦去面上积攒的尘灰,不卑不亢地与头人对峙着。
“人都说中原人好那劳什子礼节,可我未曾从使者你的身上看出礼节呀。”
沉闷的霜原语从大帐中央传来,四周也随之涌起哄笑和嘘声。霜原的将士尚未学会礼节,狼群正以明晃晃的恶意对着使者龇牙。
“你带来的……是钱粮?还是城池?”头人摇了摇头,“既无钱粮,又无城池,竟敢发话让我们退兵?实在是不知礼数呀。”
“头人好大的口气,这几万人马在这谷地白耗军粮,怕不是撑不过下月便要退兵,却要大烨给你送上钱粮城池,可打的好算盘。”
“既如你所说,我等下月便要退兵,使者又何来求我?不如抛了这天子命令,在边关等着退兵便是。”
周拂桢摇了摇头:“我非是天子使者——”
嘈杂的怒火又一次自四周响起,霜原的将士们似乎再也掩饰不住怒意,愤怒地咒骂着来人。
“哼,哼哼。”头人对着四周挥了挥手,只对着周拂桢冷笑道:“既非天子使者,那更拿不出什么东西了。送客吧!”
一时间,牙帐里混乱得好似一锅沸腾的粥,早已按捺不住的草原人从座位中跳了出来,更有动作快的甚至伸手够到了使者的衣领,试图把人扔出去。“慢——!”周拂桢眼疾手快地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盒子,高举起来对着众人大喊:“我非是天子使者,乃是可汗使者!若要逐我出去,先看了此物再说!”
帐中的声音霎时一静。头人勾了勾手,抓着使者衣领的年轻将领便骂骂咧咧地将人一推,从堪堪站稳的周拂桢手里抢过那个小盒子,恭敬地递给头人。轻薄的木盒三两下便被拆了个干净,盒子中的事物如此便落入了头人的手里:一束缠着发绳的断发,发茬处坚硬凝固,呈现出血迹干涸的状态。——可汗落在他们手里?什么时候?是否出兵?要不要杀了使者?其余部族会不会散去?一连串的问题在头人脑海里打着转,不到两个呼吸间便下意识地做出了回应。
“呵哈哈哈哈,我道哪里来的野崽子也敢喊我们退兵,原来是可汗派来的使者呀!”头人将手中的断发随手一抛,咧嘴大笑起来。“不必这样紧张!既是我霜原的贵客,我们当设宴招待你才是啊。”
周拂桢只觉双腿打着颤,如此一来,对方在拿到信物之后便会意识到可汗在南方不得脱身,更不会有什么动兵的命令可以传来;因可汗之命在错误的时节聚集的众多部族,在得知无法动兵劫掠后,原本便有怨气的部族们会各自为政四散而去;然而放任部族四散,对可汗的君威与草原上的信誉又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因此最合适的方法便是使出手段扣押住自己这个报信的使者,软禁或是暗地里灭口——最后等待可汗的军令从南方传来,纵兵劫掠。如此一来,自己最重要的目的,留在霜原大集内便可以成了。只是将性命交予异族人实在是胆战心惊,但与科举的难度相比,拿一条命换一个官身倒也算便宜简单……
头人的神情换得轻巧,帐内的气氛也随之一变。又有人搬来新的胡床与矮桌请使者落座,头人哈哈一笑:“贵客可敢与我族勇士一同饮酒吃肉?”
“有何不敢?”周拂桢坐在胡床上,拾起桌上的短匕,学着周围人的模样,刀口向内,从盘中切下一块烤肉送进嘴里——咸,太咸了!然而这咸味反倒是霜原待客之道的体现了。内陆不比沿海地区,无法煮海作盐,但人又不能不吃盐——缺了盐,人不说劳作,连站起都有困难。中原靠一套盐铁专卖的制度将海边盐场的盐源源不断运往内陆,其中催生了多少私盐贩子暂且不提。然而草原上却不同,没有直抵海边的盐场,没有连接国都的道路,没有漕运,没有盐税官,也没有——盐。
草原缺盐。人要吃盐,牛羊马也要舔盐。然而盐在这片草原上的唯一来源便是与中原的贸易,凭着几张薄薄的盐引,中原王朝通过少数几个关隘便将草原上的劲敌锁死在这片土地上。盐的稀缺又造就了草原的礼仪:贵客的食物里自然是要放盐的。不仅要放,而且越咸越体现对客人的尊重。更何况开春的局势紧张,与大烨的贸易几近停止,今年直到现在,草原的部族都没有一粒盐的进项。
周拂桢努力咽下这块过咸的烤肉,对头人露出了一个微笑:按自己被看重的程度,对方怕是根本没打算放自己走。
-
五天后。
“那使者。”头人倚靠在胡床上,握着匕首,用丝绸细细地擦拭着。他向着周围的侍卫微微仰头,慢条斯理地说着:“没见他耍什么花招吧?”
“这可是我们的地盘,谅他也不敢……”
“唉!”头人提高音量打断了侍从的话,依然不紧不慢地擦着手中的银匕。牙帐是这一整个大集中最高的,十几柱高耸的木柱将它的穹顶撑起。在那木柱上,霜原人用羊毛制成的毛毡缠绕它,于是那夏日里毒辣的阳光被阻拦在了外边,唯独在接近穹顶处留出了几个通风的窗口,昏暗的天光就这样从那口子中朦胧地落进来。光洁的匕首表面将昏光影影幢幢地反射至头人花白的胡须上。老头人也不言语,只是半阖着眼打量着手中的匕首,过了良久才开口:“……你已二十多岁了,不错吧?你是从几时开始捕猎的?”
“我从五岁便上了马、拉了弓。”
“你与那使者,谁人更善猎?”
侍从并不言语,双唇抿得死紧。将自己与那孱弱的中原使者放在一起比较狩猎?这简直是对草原儿郎的侮辱。他想不出该如何回答。
“你与那使者,又是谁人更善搬弄文字、搅弄是非?”帐中尚未点起篝火,天光只一个劲地暗了下去,头人几乎无法从残存的光亮中看得见匕首上的污垢了。“你从五岁就开始骑马捕猎……我们在马上摔下来的次数比那使者见过的马还多。但是那群中原的官人,从五岁就学了文字,若是他用言语欺你,你认得出么?”
侍从低下了头。
“你还是不服气。”头人最后一次擦过匕首。“罢了,是谁在盯着他?”
“一个小部族里,名唤别日得的。”
“你差人送半斤青盐给他,让他把人盯紧了。”
“是,这就去办。”
“让他们把火升起来吧。”
大帐中的篝火尚未被点燃,却又有侍卫跑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喊:“不好了!外面……外面乱起来了!”
-
“贵客,今日可要赴头人的宴?”别日得挂着笑,大大咧咧地入了帐,坐在周拂桢对面的毯子上。
“再不想赴了,那宴会吃得我食不知味的……”
“怎会这样!”别日得义愤填膺,怒得一拍大腿:“他们竟不给使者的肉食放盐么?这实在不尊重……”
“不是!”周拂桢连忙解释,“盐,自然是给我放的。只是头人及几位将军实在威风过甚,某与其同宴,实在不敢下口呀。”
这话乐得别日得一笑:“哪那么多想这想那的,你们中原人真是规矩多得很……哪里需要这样担忧呢?”
“别日得兄弟是霜原的勇士,这些场面自然是不在话下的。”
“呵!使者有所不知,两年前我也经几个头人赏识,赴过一次宴……”
别日得饮过一碗马奶酒,又说了几件那时赴宴的趣事,似是显得分外开心。这几日周拂桢有意通过这位霜原的小头目结交其余部族,屡次佯作好奇询问对方经历,几碗马奶酒下肚,以别日得为首的几个小部族头领也聚到了一起,几人吹水闲聊,而那闲聊中不经意吐露的消息就是周拂桢这几日的目的。
只是今日,别日得显得格外开心。周拂桢知道自己在这大集中被盯得紧,只装作对好兄弟的境遇感到好奇:“兄弟,你说与头领一同饮酒是你最开心的日子,不过我看你今日也不遑多让哪。”
别日得乐得摇头晃脑:“也托了使者你的福……”
“我?”周拂桢也乐于做出一副茫然的样子。自己这几天认的这位便宜兄弟是个多嘴的性子,自己只需在对方说话时捧上一捧便能知晓不少新消息。
“看看这个——”别日得撑着地毯挪到了周拂桢身侧,一股子膻味冲得周拂桢做出的疑惑笑意险些破了功,好在他从皮袄里掏出一个小布袋,对着周拂桢晃了晃,吸引了使者的注意力。“若不是照看使者有功,我是断然拿不到这五两粗盐的。”
“盐也能做赏赐么?”周拂桢大吃一惊——或者是看起来大吃一惊。
别日得瞪大了眼睛,似是思考了少许时候,又作恍然大悟状点了点头:“你是大烨人,尚不知这里的情形。难怪了。”
“还请兄弟指教。”
“也说不得指教。”别日得将那包粗盐收入怀中,“兄弟你也知道,我们草原不曾产盐,若要买盐,非得从关口与大烨买来才行。只是与中原人买盐需得盐引,往日里只有头人有这样大宗的生意往来,得以收入盐引。我们这些小部族,只好买些粗散盐两,若是要大量购入的话,只得从头人处转一次手才行。”
“这样岂不是有不少耗费?”
“耗费虽有,总是看在同族的份上减免些的。只是路途遥远,又多加转手,草原的盐总是要贵上一些,往日里也是不够敞开来用的……只是今年又是别的事了。”
“是关贸……”
“不错,正因关贸未开。”别日得的脸上泛起苦笑,“往年用一车皮货能换的盐,今年是拿三车皮货也换不着了。若说往年,粗盐虽然紧俏,若是省着吃,也堪堪够一年的,年景好的时候几车皮货还能换一斤青盐尝尝。然而今年不提青盐,连粗盐都得争破了头去抢……”
“居然成了这样!”
粗盐是苦的。海水煮成了盐,百姓吃到的却不尽是盐。海水里的杂质煮不干净,那种带着涩味的白色晶体随着盐一同被装上车,跋涉了这样远的距离,经过了层层加码,从草原人的手中换成了皮货。粗盐苦涩,却便宜。像别日得这样的部族,能有粗盐吃已经是足以欢喜的事了,然而头人与可汗吃的却是青盐:一种咸得精纯、没有涩味、粉如白雪的好盐。这种盐出自青池山的盐矿,他们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井盐。蜀郡的盐工在山上打下直上直下、碗口粗细的井,从井里提出溶解着纯正盐矿的盐水,那盐水煮出的盐最终上了王公贵族的餐桌,也以极高的价格打入了草原,成为头人与可汗桌上的盐。
“唉,若是我也能赴头人的宴便好了。想必可汗的桌上,煮肉时撒了盐,切完还能蘸一圈盐,连马奶酒都是咸的……”
“我竟不知兄弟你的日子过得这样辛苦,只是……”周拂桢慢慢俯下身,一种紧张的喜悦传遍了他的全身。若他是个钓鱼佬,他便知道这是“鱼咬钩了”的感觉,可惜他不是。“只是兄弟莫要怪我愚钝,为何不往宣威渡的集市上去买盐呢?”
“宣威渡?”别日得露出茫然的神色来。周拂桢见着他这副模样,故意做出一副惊讶的神色来:“别日得兄弟,你竟不知么?——也是,近来兄弟被困住此处,也无从知晓别处消息……”
“局势这样紧张,竟还有集市敢开么?”别日得急切地问道。
“据说是朝中有人向天子上策,以怀柔拉拢霜原人,只是我非是官场中人,对此事不甚了解……”
别日得的神色显出焦躁,起身在帐中乱踱着步子,思考了一会,复又转身对着周拂桢道:“我当给族里传个信……我带族中子弟应召,将族里的好马带出来不少,得让她们往那什么宣威渡去看看……”
“别日得兄弟,可是有困难?”
别日得心神不宁地坐下,“若是她们能将今年积攒下来的皮子卖了……盐、粮食……唉,我还有十几位其他部族的兄弟,得和他们说一声……”
“兄弟!”周拂桢猛地拉住了别日得的手,凑近了低声说道:“扰乱军心可是大忌!”
“可我族里的孩子快要被饿煞了!”别日得似是反应过来,虽压低了声音,却隐隐透出愤怒来:“你怎得不早几日告诉我?我也好让族里早些去买盐……”
“兄弟,兄弟!”周拂桢的脸上浮现出一副后悔的神色来:“我不该说的,此时你也万万不该告诉别人……那些盐引是我用来收买头人用的,事成便可去宣威渡提货,你千万不可——”
“你还带了盐引!”别日得的声音越发压抑,他扯住周拂桢的衣领,神色变幻了几下,又狠狠将他扔在了地上。别日得从腰间抽出刀来指着他,喘了几口气平复了一番,小心翼翼地退出去,招来在一旁发呆的部族年轻人:“快收拾东西——帐篷不要了,我们带着马和财货走……让他们不要惊动别人,出去之后在山谷集合,我自有安排!”
他想走了!别日得想偷偷溜出大集,带着财货换走盐带回部族。周拂桢仿佛早有准备似的,从怀里掏出一叠盐引。
别日得又把视线转回周拂桢。周拂桢害怕得发起抖来,哆哆嗦嗦地将手中的盐引递到别日得手里,又是恳求又是作揖:“兄弟,看在我们这几天兄弟的份上,我不告诉任何人,求求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千万不要让其他兄弟也来抢我的盐引……”
别日得心中一动。自己自然可以偷偷摸摸地一走了之,只要混过去,过了这个冬天没有人能记得自己的失职,自己如今犯下的过错自然一笔勾销,然而那些兄弟们呢?他们也与自己一样缺少盐,他们部族里的娃娃也因为缺盐四肢无力地躺着,可这狡猾的中原人,手里的盐引还有很多,难道就不能分润一些给自己的兄弟,让他们也救救族里的孩子们吗?
“妈的,抢的就是你!”别日得恨恨地暗想,胡乱将周拂桢手里的盐引一把夺过,那盐引花纹细腻,哪怕这大集的消息是假的,盐引也该是真的。别日得的心中更加怨恨,将颤抖的手塞进袖管里,佯装无事发生一般离开了分给大烨使者的帐篷。
不多时,几人带着骏马号称巡视离开了大集,又过一会,几辆马车号称联系其他营地,驶出了大集,安静得犹如水壶里冒出几个气泡一般无人注意。
不到半炷香后,几位年轻的族长聚集在使者的帐篷前,周拂桢仿佛早有预料,恳求着递出盐引请几位兄弟饶自己一命。得了盐引的几位推推攘攘地吵了起来,几人各自回了营地,大集就好像水微沸一般鼓噪起来。
太阳尚未落下,两则消息便如风一般传透了营地:
大烨使者的手里有盐引!
宣威渡正在卖盐!
大集喧扰起来,往常与别日得及几位年轻头领陪同着四处走动的大烨使者已不见人影,只是他的帐篷里散落着一地盐引。盐!有了这盐引,就可以在宣威渡买到盐!众人躁动着从地毯上捡起盐引,揣进怀里,驾着骏马或马车往外奔去。草原上的众多部族间,他们是被压迫的最底层。他们平日里放牧劳作,战时便是大部族的马前卒,吃不饱、穿不暖,自然也没有多余的金钱买盐。
可是盐多么重要呀!在这草原上,连含着盐分的泪水都是宝贵的。缺了盐的孩子迅速虚弱下来,他们无法劳作,无法站立,使原本就挣扎在贫苦生活中的牧人家庭受了一记重击。然而此刻散落的盐引可以救下他们。可以让孩子健康。可以救下许多生命。
必须得换到盐。
散落的盐引飘散在大集中,昭示着使者逃亡的方向。一架又一架马车驶出大集,往宣威渡的方向飞驰。头人从牙帐中钻出,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混乱的局面。头人暴跳如雷,喝令军士维持秩序,然而那些最底层的军士早已揣着盐引离开,无人可用,无人可挡,整个霜原大集就好像一头嗅着盐水气味的老牛,被盐引了过去。
篝火仍未升起。篝火不会被点燃了。
-
大烨使者周拂桢,以盐引一千二百斤收买霜原将士,霜原之围已解。这次不合时宜的出兵使得霜原离心离德——一年。或许明年的秋后,霜原会再一次举兵南下,但是这与今年的霜原再没有关系了。荒废了一整个夏日的牧民需要休整,恐怕在下一年之前,霜原再也无法聚集起足够的兵力了。
当然,事后回到大烨的周拂桢因此受到嘉奖,甚至蒙恩主连衡的上书得了个官身,甚至乐得差点得失心疯的事就与此无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