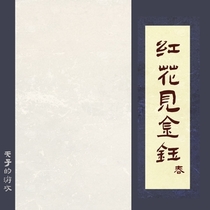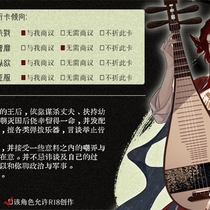不写完序章浑身难受、序章挑战不一样的文风浑身难受、写完了发现折卡死线近在咫尺浑身难受(尖叫)
总之,前传和构史,全文2046字
————————————————————————————————————————————————————————
十五岁那年,我哥死了。
那是个涝年,稍微往南一点的,十里八乡都被水淹过一遍。水灾之后便是疫,我那想脚踏实地,做中州司马的兄长,很快累倒了。好巧不巧,他暂住的地方又闹起了鼠患,虚弱之中的兄长又得了疫病,抬回家的时候,人就剩口气了。
天下又哪有那么巧的事呢?
丧事办得匆忙,兄长又是因疫病而死。家中避讳,最后只有远远的灵堂,厚重的纱幕,还有呛人的艾烟。
兄长留下的孩子不过总角之年,披麻戴孝站在前头,像个小草人,和他爹一模一样的倔强。我去叩拜敬香的时候,那孩子只是看着我,他眼睛哭得红肿,我看不清他的想法。
不过,那大概是恨吧,恨死的人为什么不是他体弱的小叔,而是他年轻力强的父亲。旁支侧室应该也吹了不少风,总不过是那些以后我会继承家产,欺负他们孤儿寡母的臆测,我那早慧的小侄子一听便懂。
兄长的头七刚过,小侄子就跑来找我。他问,小叔,我爹怎么死的。
我屏退了丫鬟小厮,又让人在外面守着。人都陆陆续续退了出去,房间里就剩下我和他。我安静地看着他,我听见自己冷着声反问,“小小年纪,问这些做什么?”
我听见他说:娘每日抱着我哭,我问她,她也不说,表叔、表姑总围着说些钱财家产,却不说我爹,更不像真的。还有,爹死前说,让我听你的......小孩子几乎要哭出来,我拉着他进了我的书房,问他是不是真的想知道真相,知道之后也死守秘密,谁也不说。
他用力点了点头。
那还要答应小叔,你要好好读书,读很多很多的书,也要去学骑射,去游历,但不能去科举。我说。
他疑惑,但应下了。
我拍拍他,尽量用他听得懂的方式讲述了一切,倔小孩听完又红了眼。唉,明明最不擅长哄小孩了。
“我要让那群家伙血债血偿!”他哭着喊。
我搂着那愤怒而哭泣、发抖的小身躯,轻轻拍着他的后背,“有小叔在,小叔给你爹报仇,也是要给小叔的哥哥报仇。”
“但是啊,你要在家里保护你的母亲,让她不要被欺负,你会有很好的老师,你要去多看看人间。”
“等你明白了今天我说的一切,你就可以离开家了。”
那时候我才明白,恨的人是我。
我差人送我那小侄子回去,葬礼结束之后,府中的流言也逐渐平息。父母长辈旁敲侧击,推着我去科举。族中传承术数的人本不应入世,可是啊,这天下要乱,没有个人撑起柯氏的门面,那是真的要被大浪淘尽了。
我掂着手里的铜钱想了一夜,它们还是丁零当啷地落在了桌上。卦象摇指京城那位陛下,还有一位看不清的......
天地不仁,圣人不仁啊。
十六岁,我大病一场,几乎去了半条命。家里似乎以为我是为了参加科举操劳过度,补品流水似的送进我屋里,总算是保住了这个家族唯一的出路。
十九岁,我入京城。
朝堂混乱,世家都在安插自己人,清流也不得不紧随其后。很幸运,我找到了伯父的同乡至交,年过六旬、时任礼部尚书的林大人。他给我安排了六品的员外郎,一个合适的位置,不会风头过盛,又能看清京城的形式。
他大概想把我作为接班人培养。
可惜天不遂人愿,烨帝在修道路上剑走偏锋,不问政事,这如何让一个两朝老臣忍得下去?
“林大人......”
“莫要在说些什么,我心意已决。”
我劝不住。
回去的路上,我见着一小摊,挂着算命占卜的招牌。那人自称李半仙,见着我就开始招呼:“哎呀,老爷您也是修道中人啊,有缘,有缘!”
我猜他看到我刚刚收进袖子里的铜钱了。
不过也好,这摊子上该有的都有,我也不必对着六枚铜钱劳心劳力。我微笑着走过去,“有缘,那就帮我占一个解忧卦吧。”
李半仙递出一个签筒,我随意摇了两下,便蹦出一根竹签。
“哎呀大人,接下来您是平步青云,逢凶化吉啊!”他捏着那根竹签,还要说下去,我抬了抬手,打断了他的话。
“既已逢凶,又如何能成吉?”
他愣了一下,怕不是又在肚里诌些说辞。看天吃饭尚且不易,看人脸色吃饭又能好到哪儿去。
我摸了摸荷包,掏了几块碎银塞他手里。
“多谢前辈解惑,这些碎银就当是晚辈请您喝茶了。”
李半仙大概没见过一下子给这么多的,趁他愣神的间隙,我快步离开了。
逢凶化吉?不,只是有人得敲碎了牙,把苦果咽进肚子里。
年末的祭祀总是肃穆隆重的,肃杀的寒风几乎要渗到骨头里。林大人还是越过了御史台的职权谏言,年迈的身躯匍匐在地上,抱着必死的决心。
烨帝的眼神冷得要结冰。
我从百官队伍中站了出来。
提前备好的说辞、伪造的卦象、几卷青词,我把老师在殿前贬低得老眼昏聩一文不值,我扯出身上的骨头把它们砸碎、磨成粉、捻成线,把它们交到这个昏庸的皇帝手里。
烨帝大笑,他看上去挺开心,便丢给林大人一句轻飘飘的归老,然后把我放到了礼部尚书的位置上。
“谢主隆恩。”
你看,做不了忠臣、奸臣、权臣——
做个弄臣,也能成为一颗不错的棋子。
是夜,我暗中拜访林大人,他似乎想通了,有似乎没想通。事已至此,我劝他快些离开京城,不要让烨帝起疑心。
“烦请大人回乡之后,指点一下我那不成器的侄子......”我深深作揖。
林大人沉默良久,最终叹了口气,“好吧,老夫答应你。”他深深看了我一眼,“你知道你要走的是个什么路吗,你......”
我只是把身体压得更低。
“难走的路,晚辈替您走。”
像我这种没骨气的,死了也罢,就当是平一平这崎岖的乱世路,你们也好走得顺利些。





(点卯前的故事)
梅瑛乔装撞刑堂,盐帮推舟昧银两
梅瑛换上一身短衣,趁着船到码头,来往的船工忙着卸货,蹑手蹑脚从船舱摸出来。
天已然尽黑,连月也不曾出来照亮,正是月黑风高时。船工节俭,随身捎带火把,要用的时候甩一两下, 火把里隐而不发的虚火随着晃动,像饮饱了水的菌干,噼啪着借力燃烧起来。不过一豆亮光,仅仅照亮面前几步路。梅瑛蹲身在火光的阴影里穿行,一路摸到一座浮岛的边缘——如果线人没说错,这里就是此处盐帮的一座落地。
浮岛上盖一座竹楼,油布拼接覆盖用以防雨,里面隐隐有人声顺水飘来。梅瑛犹豫片刻,决定再往前探探,觉得不对再撤回来。
官员贪污一案已经在案前搁置半年,官职不大,银两却不少。府邸搜过,人也审过,偏只是些稍微多些金银罢了,同品级的贪官私吞多如牛毛,比起来这人端的是个“两袖清风”的好官模样。搜不到归搜不到,但白纸黑字的账可对不上。卷宗交到梅瑛手上,前面已经接手国好几任,现在大理寺已经准备结案,剩下的不过是往刑部递个流程,让同为六扇门的同僚知道这个事罢了。梅瑛看似和气,偏对当朝大理寺卿——陈怀澈——生得一颗七窍玲珑心。案件里关键人物,官员的庶弟像是隐身了般,如此明显的问题,陈怀澈不可能置之不理。梅瑛双手一合,揣着卷宗就要上门让对方给个说法。
“梅大人,陈大人说了,这件事情牵扯甚多,已经追回大部分赃物了。”
大理寺的小吏半推半拉,阻止梅瑛冲到大理寺去。
“这不是丹青兄的作风。”梅瑛表情淡淡,难得带上几分锐利的审视。最终,他不愿意为难眼前两股战战的小吏,挥挥手放人走了。
行啊,这般避讳,既然交到我手上,就让我探探虚实罢。
梅瑛深吸气,屏住呼吸放缓脚步,距离竹楼不足十尺,听到了里面传来的告饶——
“我不知道,剩下的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哪里敢瞒着您‘覆海狼’啊!”
随即而来是中年男子沙哑的低笑,竹棍有节奏得打在地面上,俶尔停止:“这不是还能花言巧语吗。”
梅瑛再靠过去一点,忽然脚下一软。
“噼啪”
一根晒干的竹子被他踩断。
“谁!”竹楼里传出暴喝,一短衣粗褐的年轻汉子冲出,目光如炬,一眼就看到了行状鬼祟的梅瑛。他朝着梅瑛大步奔行,浮岛随着汉子的步伐上下晃动。梅瑛或是慌张或是受了摇晃影响,急切中两腿如软烂面条,每一步好似踩在棉花上,反身只见那汉子丝毫不受影响。坏了,是枚练家子,梅瑛想。
他索性不逃了,让汉子把自己押进去。
竹楼内主座上坐着一位高颧骨的中年人,头上好似营养不良的棕发,蓝色抹额,单侧系着一绺辫子,他杵着竹棍,眼里闪着财狼一般精明的光,上下打量着梅瑛。
“格当码子打哪儿来的?”中年人问押送的练家子。
“生面孔,怕是拆梯子。”练家子恭敬地答道。
中年人冷哼,言辞间带有火气:“拆梯子?饭桶!哪里在玄,明儿自个儿找那装木鎯照镜子。”(1)
练家子更是低头,一言不发,像是知错。
梅瑛见他们切口混杂,自然没全懂,但大概想到是斥责练家子办事不利。他放宽心,看这里人也没对他动粗,自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江湖组织。随即他又看之前跪在地上告饶的人...和贪污的官员怎么有六成相似?心上盘算了一阵,大概确定这人就是官员的庶弟。
“不知我们这小小码头,怎么让大人大驾光临?”坐上的中年男人走下来,对梅瑛和善地笑,“松手,像什么样子,给大人看座。”
练家子松了手。有人搬来竹凳,有人放上小几,还有的人端来清水。梅瑛安之若素坐下,没动杯子:“你认得我?”
“我等小人物自然不认识大人名讳,大人可赏脸告知一二。”
梅瑛被这做作的殷勤弄得左右不是滋味,这码头头子看似恭敬,实则处处透露送客。伸手不打笑脸人,梅瑛还是生硬地报上名字:“梅瑛。”
“!是你!刑部的那个!”官员的庶弟后退两步,“你怎么找来的!”他又转身指向中年男子,”你们言而无信!”
官员的庶弟像是发了狂,指着四处乱骂一通,竟要冲到中年男子面前:“你们盐——”
练家子不等人说完,一拳把人掼在地上,对方呜呜咽说不出话来。这时候,中年男子才摸了摸下巴:“见笑了,刑部的梅大人。草民是码头的小管事,姓武,单字一个奎。”
梅瑛见他强调官职,忍不住呛声:“‘覆海狼’武奎?”
武奎摆摆手:“水上叫着玩儿的诨名而已,算不得什么。倒是梅大人,看起来深谙让人说话的办法啊。”他一只手拖着竹棍,慢悠悠坐回座位,“梅大人可是在追查案子?六扇门办案,我等自然全力配合。”随即低声道,“我们这里问些什么,可比刑部顺手多了。”
顺手。
这个提议的确令人心动,不知道陈怀澈当时是如何考虑——或是受制于人——梅瑛指尖在小几上来回敲击,在口中舔着下唇。
这码头头子,果真是精明的商人,自己一来,转眼间出卖才和自己合作的官员庶弟,只怕靠不住。
心念回转,梅瑛朗声道:“我们刑部自是有规矩,只能使用杖刑,隔二十日一审,拷打不得过三次,总数不得过二百杖,且不得更换行刑人。”
他站起身,明暗晦涩的火光照得他梅色的头发,像是梅树下生出的花魄(2):“但...此处不是刑部,我更想试试脑箍呢...鼠弹筝也不错。”他对着官员庶弟笑了笑,“脑箍知道是什么吗?以绳束首,木楔打紧,渐至眼耳出血。鼠弹筝呢,就是把你的指头、趾用细绳反绑”梅瑛在对方惊恐的眼神里指了指对方的指头,“我会以木棍弹击绷紧之绳,每弹一下,绳子便绷紧一份,最后关节绛紫,你的手指也会随着一寸一寸烂掉....”
梅瑛又低语似的说了许久的酷刑,再看过去,对方已经吓晕过去了。武奎斜睨梅瑛,又瞧了瞧地上昏死过去的官员庶弟,一副思考的模样。
“梅大人,”武奎正色,“此人就交给我们吧,我武奎定会让您看到我等的诚意。”
梅瑛注视武奎,转身离开,众人纷纷为他让开一条路,无人敢阻拦半分。他走后,众人心有戚戚,望着座位上的武奎。武奎没事人一般,示意找人把官员庶弟泼醒:“看我干甚,可算把那聪明的梅大人送走了,下次谁敢再往帮里请大佛,那位大人说的内容,可是给老头子我不少启发啊。”
哗啦——
官员庶弟浑浑噩噩醒来,惊魂未定地看着武奎。
“你们家怎么就惹上六扇门了呢?”武奎蹲下,拍了拍对方的脸,“我盐帮也不是言而无信之人,说吧,别藏私了,除了老头子我,其他都帮不了你。”他比了比一个手势,“得加到这个数。”
官员庶弟喜极而泣,他颤颤巍巍说出:“一千两,都在....”
武奎侧耳听了听,忽然哈哈大笑!
“好!这样,我们盐帮给你取来!”又过了一个时辰,银两在竹楼放置妥当,武奎做了一个请的动作:“来,拿走吧。”
“没有车船吗?”官员庶弟愣住了,看着竹筐,布料,还有零零散散堆在地上的银子,他竟有一种身在宝堆却带不走的错愕。
武奎啧啧:“我们谈的时候,就说的是我们用竹筏,您带着银子离开,不是吗。”
“话虽如此...那带不走的...你们!好大的胆子,算计我!我!”
“你可和刚才那位朝廷命官不一样啊,”武奎狞笑,“我听闻造银厂的人偷银子,把银子置于谷道里,不如您委屈委屈?”
言毕,周围传来众人的哄笑。官员庶弟一脸屈辱,双手紧抓裤头。
武奎挑眉:“这可是一千两,靠他一个人可不行,怎么,不帮帮他?”说着便往竹楼外面走去。
那官员庶弟突然意识到什么,但回头就被练家子狠狠按在地上。
月黑风高,水面上传来隐约的惨叫声。
“这梅大人还真是...启发老头子我了。”武奎拎着着竹竿,往码头走去。他从兜里摸出半个发硬的馒头,一路走,一路碾碎扔进圈出来的鱼塘中。
各种鱼儿浮上水面抢食,其中夹杂着几分艳色,几尾锦鲤沉浮。
==================
第二日,刑部门口挤挤挨挨围着一群人。
梅瑛走进人群,竹席包裹着尸体,没人知道谁放在这里,仿佛凭空出现。有人掀开竹席,不是别人,正是那贪污官员的庶弟。他面色惊恐,身上遍布淤痕,未着寸缕,显然死前受到莫大的酷刑。
人群中有人恨恨道:“匪帮手法,他们好大的胆子。”
仵作细细验尸,尸体的谷道撕裂,脱垂的肠子里找到一百两银子。
梅瑛皱了皱眉,这是威慑。
线索已断,此事就此结案。
(1)都是江湖黑话,混了丐帮和洪帮的,时代对不太上。只是理论知识,没实际应用作者只有照猫画虎:
“这个人打哪儿来的”
“不认识,怕是要走漏消息出去的。”
“走漏消息出去的人?没用!这哪里是圈内人,明儿自个儿找到那间谍把双眼挖了。”
(2)清·《子不语》——“此名花魄,凡树经三次人缢死者,其冤苦之气结成此物,沃以水,犹可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