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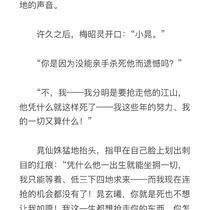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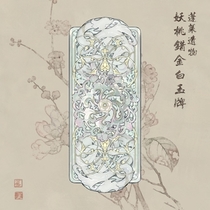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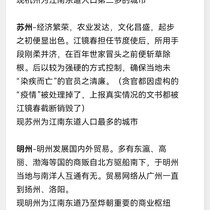

石征服,持卡人:文则野
陛下复生那日,肆意生长的桃花几乎毁掉了半个长安城,就连六部衙门也不例外。工部的人理应负责长安城重建的事务,又有临时迁都的需求,应渡干脆暂时宿在临时的办公点,只是这薄木拼合的门板挡不住来往的车马人声,即使睡梦中也是浑浑噩噩,似有人在耳边窃窃私语。
应渡艰难地从桌案上爬起来,这样别扭的姿势入睡的后果就是他半个身子都是麻木的,一直到酥麻感褪去之后,才揉了两把晴明穴让酸涩的眼眸稍微缓解一下,随后推开窗子,看那模模糊糊的光影透过木棂。
如今夏末初秋,天气逐渐凉了起来,清晨时的空气都是冷的,深吸一口冰凉的触感直通肺腑,几乎让人瑟瑟发抖。应渡把从椅背上滑落的外衫捡起,迟钝的脑子恍惚想起,如若陛下在长安的话,这就是该上朝的时间了。
豫王暂理国政一切从简,大半的朝廷官员如今已经慢慢转移到了洛阳,长安剩下的这些官员,索性就凑在一起。如今开个会都只用拐两道门槛,就连用餐都能凑在一张桌上,什么尊卑规矩都能暂时放一放了,可谓是高效又便捷啊。应渡坐在豫王对头,觉得他似乎瘦了一些,朝服好像空荡了不少,眼底青黑,倒是人看起来成熟了几分……这也是难免的事情吧?应渡暗自思忖,这一堆的烂摊子压下来,如今还在长安的,哪个不是把人当驴子使,恨不得眼前拿个萝卜吊着就能拉上一天的磨,可惜现下的人也是比驴子还不如,连个吊在跟前的萝卜都没有。
应渡撕下包子暄软的皮,看里头露出肉汁饱满的馅料,热气蒸腾着冒出白雾,感觉又找回了些生活的趣味。他慢条斯理地吃着手上的包子,看豫王大约是回过神来了,才施施然开口,“虽说这肉包滋味不错,不过我想豫王殿下应当不是特意来吃饭的吧?”
豫王大概是还年轻,被说中了心事就有些拘谨起来了,他如今也算是半个皇帝,这些情绪都是很不必要的,但这些话不应当应渡来说,所以他只是静默着等待年轻人整理措辞。
“往年夏末多是降雨频繁,本王近日翻阅之前呈上的奏折,见应大人此前上书,河南今夏多雨,恐有泛滥之险。我知晓应大人已是派了人治水,只是不知如今是否仍有水患之忧?”
应渡不假思索便给出了答案,“豫王殿下的忧心亦是「有梁」*的忧心,臣此前已然派了人到河南去,如今河堤修缮已是快要完成了,只是……陛下挥兵赤梁,征调了不少农夫民兵负责运输粮草辎重,此前我曾问过自洛阳来的转运使言大人,便是听闻迁都洛阳亦是因着如今大烨赤梁战事为重,原本该从洛阳转运至长安的盐粮也运输不便,何况那不过「未雨绸缪」的河堤呢?”
他接着说道,“然而臣万万不敢欺瞒殿下,今夏雨水丰沛,陛下挥兵赤梁,陇右的工匠或许也会被征召入军,若无上游疏导水流,下游的河南堤坝又修筑不成……若是秋日雨水未减,便是有河水泛滥的险境了。
豫王听着这一番话,也是不得不叹了口气,这便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只是他忽然心思一动,连忙追问,“若是堤坝能筑成呢?需要多久才能筑成?可需要旁的抛费?”
应渡略一思忖:“秋日雨水渐少,若是按照往年的雨水,只要不是遇到什么百年一遇的暴雨,是万万不可能叫黄河泛滥成灾。如今工事已经做了九成的功夫,再要赶工月余便可当用。至于旁的,只需役工的米粮罢了,若是再从田中招徕农人,便可再减工期,在处暑前完工也并非不可能。”
豫王眼睛一亮,矜持地抿唇微笑,原本疲倦的脸都精神了不少,“此行甚好!我记得秋收还有一段时日,便先紧着河堤的事情,待到堤坝筑成,便叫他们一齐去田里收秋粮,再给当地农人减几分赋税,或许是可行之策……而且,我倒是想起来,我们确实有一伙得闲的匠人。”
虽然豫王并没有指名道姓,但毕竟应渡是工部尚书,他眉心一跳,很快想起了这所谓的匠人是从哪里来的,不由得感叹还是年轻人胆子比较大,“……便是如今在邙山的那些匠人么?”
豫王轻轻点头,邙山便是大烨历代帝王墓葬所在,那所谓的匠人——自然也是给烨灵帝修坟墓的工匠了。
应渡远眺城中那遮天蔽日的桃树,抚掌大笑,“陛下如今成仙在望,这等凡人贪恋的身后事,于陛下来说自是无用武之地了。有梁斗胆请求豫王殿下,将这些工匠交付于我,臣愿亲赴河南主持工事,这洛阳……我便不去了。”
豫王便是为此而来,自无不可,只是他心知肚明,如今应渡开口点破了这点,若是之后皇帝问责起来,便无回转的余地了。
应渡注意到豫王的表情,却无半分怯意,而是掷地有声:“有梁全因治水之能侥幸做得丞相之位,但凡有几分力,便当为陛下尽几分力,若因畏惧陛下未曾出口的责难便推脱起来,岂不是欺君罔上,有负陛下信重。”
·多年前太极殿上
应渡俯身贴地,发白的手指温度并不比殿上的汉白玉要暖多少,紧绷的情绪让他整个人尤为恍惚,几乎对时间失去了感知能力。不知过了多久,皇帝的声音远远地传来,模糊地灌入应渡耳中,“应渡……这个名字倒是好,你是应尚书的孩子罢?”
应渡用力吞咽下口水,想清下嗓子让自己声音听起来更为成熟稳重。可惜为了避免御前失仪,今晨饮食都颇为克制,干涩的喉咙徒劳地蠕动着,几乎有刺痛的感觉。于是只得懊恼地听着自己的声音像是香炉里的烟雾一般飘着向上,没有半分沉稳,倒像是被掐住了嗓子的黄鹂,“回禀陛下,家父确实曾任工部尚书。”
“哦……应尚书是哪一年走的,好似是过了许久了。”晁玄曦自言自语般低声说道,他坐得那么高那么远,以至于应渡都有些不敢确定,这是自己真切听到的话吗?还是在哪个梦中呢。他记得听闻父亲去世的那一日,距今已经四年零三个月又十六天了,只是,陛下竟然也记得吗?原本他以为,父亲就如同黄河淹没的土地一般,此后再无一丝痕迹留存世间了,可如今方才知晓,竟然是有人也曾记得他的。
“我见应卿未曾取字,”晁玄曦并不等他答话,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年轻的帝王声音里还带着几分少年意气,显然颇为自得,“应卿既然以「渡」为名,那我便为你起「有梁」二字吧,「水虽无梁,不渡由我」,如今「有梁」,可愿为朕渡一渡那黄河呢?”
应渡几乎要忘却不可窥见天颜的规矩,却又在最后深深地将头埋在手背之上,他声音微颤,却斩钉截铁,“有梁必不负陛下期望,愿效吾父以身报国。”
“既然你要效仿父亲,朕又怎么能阻拦呢?便点你为水部郎中罢,只是这「以身报国」未免太重,有梁可要多多爱惜自己,多为朕分忧几年才是。”
————————————————————
应渡当了几年臣子,便治了几年的黄河。此前下官已经将这几里河堤修筑得差不多了,如今从长安赶赴而来的工匠正是最后一块补丁。
此前估计并没有出错,秋收前的最后几场雨势凶且急,但如今工部调用了造皇陵的熟手匠人,又临时征了当地的农人出力,由王都尉那借来的几支兵将负责督建工作,终究是在河水泛滥之前将河堤修筑完成了。
冥虚子虽非善类,但高空之下所见山河形势叫此次治水成功扼住了黄河几处关隘,或许近几年都不必担忧此地河泛之事了。
众人抢筑完河堤,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抢收,好保住这一茬秋粮,又能安抚民心。当最后一粒麦子被从田地中拾起,应渡站在秸梗堆上颁布了豫王监国的临时政令,今年粮税折半,以犒慰此地百姓协力修堤的义举。
秋日的太阳或许仍然刺目,以至于当百姓为之欢欣鼓舞之时,应渡却觉得眼前模糊不清……多年前少年皇帝的影子似乎已经淡去了,如今挥师西进的圣人,是否仍记得,水有覆舟之能?
*有梁:应渡的字,烨灵帝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