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y care is like my shadow
Laid bare beneath the sun
It follows me At All times
And flies when I pursue it
I love And yet Am forced to hate
I seem stark mute inside I prate
========================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魔女歌唱之时,化为人形。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在机械轰鸣的爵士年代,魔法与巫术在此暗中汇聚。
器物与人类,是否能找到与之结缘的彼此。
两者的缘分与命运,无论善恶,就从踏入徒然堂的一刻开始。
欢迎来到TURANDOT•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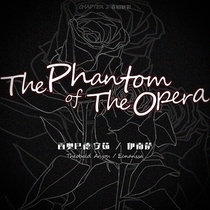



ff14 真是 太好玩啦!
*
*
*
推窗而入(一)
========================
阿尔文凝视窗外。
时值1925年的春季,今日阳光明媚,然并非有游行活动的节日。而示威集会即使在声潮最热的两年前也未打扰过这片街区,遑论如今。
可外头有个戴着鸟嘴面具、在这平凡一日裹着全黑的兜帽长袍、从指尖到发丝都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人。
即使现在是初春,他穿得也太过厚实了,且与潮流完全脱了节……在这儿住的人不该这样。
他和阿尔文隔窗相望,站定了久到像在审视镜中自己的时间。
阿尔文很肯定对方确实是在看他。尽管那位先生——就身高来看如此——的面具将双眼部分藏在以茶褐色镜片封起的小小孔洞中,可这个方向……除了他也实在是没别人了。
“……您好。”阿尔文说。
他想继续和这位奇怪的绅士说点什么,可隔着没打开的窗户说话实在奇怪,所以他卡在那儿,礼貌地颔首,接着又低下头去看病历。
“Tang”
尖尖的喙部敲在玻璃上,发出令人不安的声响。
阿贝尔只觉得有些失望。
啊,好吧,他没法穿墙,就和徒然堂那些看起来像是巫师,却普通地在用美元付账的人一样。
“Tang!”
对方又敲了一下窗,这次音量更响。尽管街上男女对此保持视而不见,但阿尔文毫不怀疑,如果这位先生因反震作用摔倒,一定会有热心民众将“阿尔文诊所”与“求诊者昏迷”两事联系起来,添油加醋地通知给附近的小报。
他伸手开窗。
面具人的手也向上探。向上,向后,被手套紧密贴合的十指探进礼帽,束缚带从脑后垂落,黑色的鸦羽中,阿尔文看见对方缺乏白得像没有血管分布的双耳。
在他完全看清它们的形状(据说妖精血统的人有尖耳朵)前,更多层坠下的发丝将之遮住,帘幔般衬出对方的五官。其中唯一有血色的是薄薄嘴唇,它对着玻璃张开,哈出稀薄的雾气。
面具人的指头一笔一划。
【A l v I n】
“阿尔文·帕特尔”他,或许是她?以有些拗口的音调陈述,“我来,找你。”
阿尔文没听见。
他听不见。
他所有的注意力给了视觉。他看着对方的面容,看着他平滑的前额,浅浅的眼窝,柔和的颧骨,与深黑色的发,还有醒目的古旧着装。他不可能对陌生人一见钟情,所以,一定是这个人身上有什么在让他本能地注意。
是什么?
国别?法国人?
是了,他肯定不是美国人,他说英语很奇怪,着装也非常奇异。但我为什么会在意他的国籍?
说来没有人在偷瞄这里,他是不是……法师?他施了能让人忽略的法术?他特意来找我,我需要一名翻译……我买的那些古董里头是不是终于有一件魔法物品了?他是来要走它的?
他胡思乱想着,放任自己的视线越过镜片钉在这人身上,直到对方把窗户拉得更开,随着满溢的薄荷芳香一下子勾走他的眼镜。
“先生?”阿尔文愕然地站起,模模糊糊看见对方把它戴到自己脸上。没等他想好要怎么反应,这位不礼貌的陌生人又做出了更奇怪的行径——他试图从阿尔文颇为满意的大扇拱形窗爬进诊所里来。
阿尔文退后几步,抄起他的病历夹准备夺门而去。可惜的是,往日里他既有关门的习惯,又没有放声大叫的经历,错失了呼救的最好机会,被迅速提着长袍钻进来的对方挡在了门与办公桌间。
美人、寻觅、突然而至的邂逅。多么香艳的开头啊!可在这种突发情况下,对方那副人畜无害的柔美相貌没能起到任何安抚作用,阿尔文几乎要贴上背后的文件柜。
“找到你了,阿尔文·帕特尔,”对方又用那种奇怪的音调重复一遍他的名字,逼近过来。
他的尾音轻飘飘地扬起,柔和,却像是命令“我要待在这里。苏拉说,我可以这么做。”
“可,先生,这位“苏拉”是谁?”阿尔文盯着他,缓慢地将双手举起。
“手术钳。”那个人说。
“抱歉……手术钳?”
“是的,手术钳。他是、手术钳,我是Schnabel(鸟嘴面具)。”这怪人,施纳贝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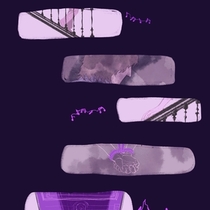
是卡。
甚至没写完第二章,只能先放一段出来打个卡,五一再补全。
日常疑惑,为什么我总是在写NPC,为什么,为什么。气死了,等推进到女朋友出场我一定大写特写补偿自己(?
害,写到现在人都没死,丢人,我自闭了。
这次依然抓了一些朋友参演,关联打扰了!
————————
科尔·道寇森舀起一勺汤,他平日里手一向很稳,这次汤汁却不慎泼在胡子上,于是他只好又将其放下。
银汤勺落在汤碗里,发出不合时宜的一声响,索性并未惊动这张餐桌上的其他宾客。
但科尔·道寇森已经没有胃口再享用餐桌上的任何一道佳肴了。
英格拉姆夫人的晚宴开始已经有一段时间,宅邸富有的女主人因身体抱恙,在简短的招呼之后,再度被女佣服侍着回到她位于二楼的寝床,只留下她的侄女,亚麻卷发的玛丽亚·英格拉姆小姐代为招待众人。
英格拉姆小姐乐于接下这份差事,席间表现得大方得体,招人喜爱极了。至少道寇森是这样认为的,他着实喜爱这个女孩儿,看她那双蓝眼睛,看你的时候就像升腾起渺渺云雾的海,多么迷人。
“听说今天的晚宴是您来拟定的单子?完美的选择,小姐。”
坐在英格拉姆小姐右手边的男人用餐巾碰了碰唇角,同主人家搭话,“请容许我这样说,小姐,我同英格拉姆夫人也有一段时间的交情了,竟还不知到她什么时候有了您这样出色的侄女。”
“不怪您不知道,因为我是不久前,才从南边的乡下赶来纽约。”
英格拉姆小姐笑着回答。
道寇森又捏着汤匙搅了搅汤,竖起耳朵,悄悄关注着两人的对话。
正在说话的那个男人,穿着最笔挺昂贵的西装来显示富有,他身材修长,竟然还年轻英俊。道寇森这辈子就没喜欢过这个小他将近二十岁的金发混球,他知道帕特里克·埃德温在一些领域混得风生水起,但他就是没办法看这个人顺眼哪怕那么一点点。
“南方,啊,我记得那块地方,炎热且干燥,不,不,我是说,那是个好地方。”
一个神情紧绷的年轻人冷不丁也加入了对话,道寇森不认识这张面孔,对方生一头铁锈一样颜色的暗沉短发,坐在距离主位较远的地方。
今夜在这间房间之中,有一些道寇森熟悉的人,如埃德温和他最近总带着去各种宴会的棕发女郎,还有那个漂亮的萨曼莎,从进房间起就高傲得没给任何人丁点眼神。
但也有道寇森说不上来的人。铁锈发色的年轻人身上的西装还带着点霉味,害道寇森有些想打喷嚏,另一边的红发修女自始至终没有和任何人交谈,神职者的目光在平静中总像是带有某种奇特的意味,像是审视着房间内的所有人。
对了,这个奇怪的组合里还要加上那个女人,那个不知廉耻,白色衣裙紧贴在身体上,黑发润湿滑腻的女人……
科尔·道寇森的思绪被一些杂音拦腰折断。
似乎是对于自己不得体的表现感到了一些羞耻,年轻人涨红了脸,连声道歉,这让道寇森的注意力得以被重新拉回到现实。
但年轻人这副滑稽的模样,非但不叫主人家生气,反而惹得英格拉姆小姐含笑瞥了他一眼。
道寇森对此有些气恼,他不确定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人,这个人,再加上电影演员、暴发户和女伴、修女,还有身为金融家的自己,英格拉姆夫人今夜邀请这些人到这里来的用意,也着实令人难以捉摸。
他忍不住又看了一眼红发修女,对方正巧也望向他,道寇森赶忙低下头,装作若无其事地喝起汤来。
“哦?是这样。”埃德温看起来倒是并不介意年轻人的语无伦次,金发青年屈起的食指在桌上敲了两下,只是随意地继续追问,“英格拉姆小姐原来是远道而来。从那样远的地方赶来,一定有什么理由吧?”
亚麻发色的小姐点点头:
“因为姑妈给家里写了信,说她身体近来总不太好,需要照料。”
道寇森在心中点头,他早就看出这位小姐就是这样温柔善良的姑娘,照料英格拉姆夫人这样挑剔的姑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有钱的老女人脾气有多坏,他知道得非常清楚。
想到这里,他的心情不免又焦躁起来,不论如何,今夜他必须要见到英格拉姆夫人,这将决定他的命运,这说法毫不夸张。
如果有必要,如果,如果她一定坚持要那样做……
道寇森在心中暗想,如果英格拉姆夫人过真那样绝情,那么,他绝不能坐以待毙,绝不能。
隐约中,金融家仿佛看到黑暗中浮现出动人的丝缕,滚落的水珠摔碎在女人青白色裸露的双足上,润进细腻圆润的脚趾间隙。
黑发女人朝他露出微笑,再一眨眼,却又自记忆中被抹去,仿佛从未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