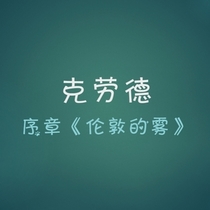故事的舞台位于1888年的欧洲。
由农业改革拉响了工业革命的第一篇章,此后的数十年,文明的曙光敲响了民智的门。
灯火点亮了伦敦的长夜,铁路如血管般布满大地,在蒸气轰鸣的城市里——
魔女与人类间隐秘的战争开始了。
本企为参考了现实国家、历史、人物的半架空企划,存在对真实事件的轻微魔改,可当做现实世界的平行时空看待,考据党切莫较真,介意勿参,感谢理解。
感谢大家半年以来的陪伴与付出,红月之下企划至此顺利完结!感谢每一位参与了红月之下企划的玩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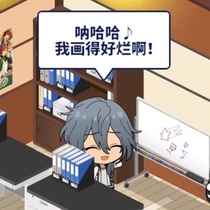
没有互动就要自己制造灵异事件×
奇迹赫莉环游世界√
先把卡打了,撕掉自己的请假条!!!
阴雨天,赫莉站在廊下看着逐渐漫过自己鞋底的水,草地被浸泡地湿润而柔软,踩下去还会啪嗒啪嗒作响,这实在是称不上舒心,至少赫莉不想出门,她不想弄脏自己的裙子,也不想让自己的翅膀沉得飞不起来。
“还不如找些羊来把草吃了。”
“那要去找羊吗?”彼特站在门口,举着那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一本书看,虽然他也没有眼睑让他眨,“街上有很多。”他顿了一顿,又翻过一页书,“书上讲羊太多了不好,土地会被吃地荒芜,所以我们还要找一头狼,这样才能达到自然的平衡。”
他似乎对自己能够记得这么多事情感到快乐,于是乎十分愉悦地摇头晃脑起来,断断续续地念着一首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诗歌,“青青河边草,应是绿肥红瘦。”
连字数都没能对上。赫莉想着,没有开口打断,她觉得找头羊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如果要去找羊,势必要出门,要出门,就一定会弄脏自己。
“我们应该先去找一辆车或者轿子。”赫莉转过头,甩掉了自己发梢上沾上的一点点水珠,晶莹剔透的,她无视了彼特试图询问什么是轿子又什么是车的眼神,指了指墙上挂着的帽子,“我们出门。”
“去找羊吗?”
“不。”赫莉说,“去找面包。”
魔女要不要吃东西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很多人眼里都显得不太一样,愚昧的人觉得魔女一定是要吃小孩的,隔三差五就要来上一个,不管是吊起来晾干,还是放在火上烧烤,亦或者是和童话书上画的那般,把人捆起来放进颜色诡异的锅子里煮上一顿。
“我想吃芝士。”
赫莉戴上那顶帽子,把史莱姆挤干了水分,又或者是魔力,弄成一个一拳大的黑团子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不行。”
对于自己主人的拒绝使魔并没有多大的想法,只是又一次提出了别的要求,“那我可以读书吗?”
赫莉看了看他最近正在读的书,又看了看自己口袋里眨巴着单眼的小球,一双眼睛滴溜溜转了半天,开口骂他,“不自量力。”恶狠狠地把书塞进了史莱姆嘴里。
而确实,史莱姆没办法在那个小口袋里展开书册,那样会把书页撕坏又或者自己会从赫莉的口袋里掉出去,啪嗒一声落进水坑。
那样不体面。不雅观。
彼特用着书上学来的,还没来得及忘记的词汇在口袋里滚了一圈,随即被赫莉一巴掌拍扁。
“别晃。”
好凶啊。
史莱姆想,但是他觉得这似乎也没什么不对,赫莉收留自己,是个好人,自己又不怎么记事,不灵活,书上说被厌恶的人大多都这样,总会落得一个孤家寡人,呃….分……分尸八马的结局,所以现在有赫莉,有眼睛,自己很快乐!
赫莉不管口袋里那个安逸地仿佛入土为安了的家伙在想什么,她撑着一把伞,穿着一双鞋,只觉得自己是在泳池里走路。步步艰难,还不如在家里和史莱姆拌嘴。
她住在这个森林里已经多久了?她不记得,魔女们似乎是淡出了世界,又像是在做世界阴影里的眼睛,蠢蠢欲动地试图吞并能吞并的东西。
她不介意,与她无关,人类就像是蛆虫,从腐烂的树木里,从新鲜断肢里长出,只要有一个,就会有无穷无尽个,它们不知从哪来,却一定要找一个自己的去处,于是遍布了世界各地。
那是消耗不尽的,不用管束也不会被用竭,放着不管也会自己消耗。
所以,她为什么要去管蛆虫的死活和去处?
赫莉走着,听着背后被惊起的鸟雀声,又听见噗通的脚步声,她没有回头,只是自顾自地往前走。
史莱姆像是睡着了,又像是在思考,总之无声无息地,赫莉伸手去碰也没有多大反应。
她的伞被风吹飞了,她的帽子被雨水打湿了,整个湿淋淋的罩在脑袋上,如同一朵乌云,就差轰隆隆地打雷。
噗通、噗通、噗通。
“赫莉?”史莱姆从口袋里爬出来,耷拉着两只细长的小手,“那是什么声音?”
“心跳。”赫莉说,摘下帽子来塞进了彼特的嘴里,又强行掏出一把伞,那把伞面是红色的,上面画着层叠的漂亮刺绣,赫莉转了转,一时间没能认出那是什么图案,乌木的手柄有些沉,但是很有质感,她很喜欢。
这把伞很大,很漂亮,也很没用。
赫莉转了两圈,又转了两圈。
“怎么了?”史莱姆想不起自己在书上看到过的形容词了,顾影自怜还是自作多情?矫揉造作还是搔首弄姿?他用细长的小手臂敲了敲脑袋瓜,终于糊涂了。
赫莉没有说,这其实是跃跃欲试。
她直觉这把伞不简单,或许可以称为自己从森林里走出去之后的第一个消遣。
史莱姆困了,乏了,于是缩了回去,安静地躺在女孩的口袋里,身体里包裹着那颗眼球,让自己看见一片黑暗。
书上说这就是睡觉。
赫莉走了很久,她没有钟表,也没有计时器,不介意日升日落,雨停了就飞,下雨了就走,累了就停在动物的头上,身上,角上。饿了就落在花上,草上,或者尸体上。
她没有叫醒彼特,不愿意听那个史莱姆啰啰嗦嗦,词不达意地聊天,也不想解释周围有什么,是什么,和无穷无尽的为什么。
那把伞被她拿在手里,渐渐地不再那么鲜艳华丽,变得有些旧。
森林里本就湿润,伞面会坏实在不是什么怪事。所以当她终于走出森林,看见街道和袅袅炊烟的时候,整个魔女都有种换个地方定居的想法了。
街道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活脱脱是个热闹街区,她回望自己走来的地方,那是一座巨大的山林,郁郁葱葱地,十分神秘。
有人看见赫莉这个生面孔,明明是晴天手里还拎着一把伞,好奇地问她是不是走丢了,或者离家出走的小女孩。
赫莉扯扯裙摆,想着自己应该装作是孩子,还是装作生来就这么高。
她的犹豫和迟钝似乎是让人感觉到了无措与迷茫,那位先生好心地牵起了她的手,让她在一家朴素的饭馆里坐下,给她点了一份烤香肠和焗饭。
彼特闻见香味动了动。
“小姑娘你走丢了吗?怎么会一个人在那里?”那位先生长得很是普通,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只是伸出来的手有些粗糙。赫莉盯着看了半晌,先是吃了一口饭,差点没被咸得吐出来,好不容易咽下去了才听那个人问,“你这把伞是哪里来的?”
赫莉清了清嗓子,试图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嘶哑,“是母亲给我的。”
那位先生很是犹豫了一会,又问她,“那我可以撑开看一眼吗?”
赫莉叉起烤香肠,“我不介意的,先生,谢谢您请我吃饭,如果您喜欢,我可以把伞送给您。”
那名先生没有推脱,在店里撑开了伞。
刺绣层层叠叠,即便被树枝刮破过几处线头,被雨水浸污了颜色也毫不影响它的贵重。
赫莉清楚看见了那位先生眼睛里闪过的光。
她捏了一口饭塞进了口袋里,彼特被咸地吐了本书出来。
完了,都还给作家了,白学了。
彼特没头没脑地想,捂着眼睛再不动弹了。
那位先生自称威廉,将赫莉领回了家。
他一手拿着乌木伞,一手拎着买来的几条裙子和日用品打开了一栋小洋房的门。
他的家里很干净,没有人,但是桌面上摆放着一张合影的相片,墙上也挂着一幅油画。从窗户里看出去还能瞧见院子里晾着几件衣服和一套工装裤。
都是金发碧眼的美人和这位威廉先生,赫莉实在是不怎么认脸,从昏暗的室内也看不清更多了,她有模有样地站在原地问道,“这位是您的夫人吗?”
威廉先生把伞收好,却依旧拿在手里,“是的,是我已故的妻子。”
赫莉点头,“她很漂亮。”
威廉先生笑答,“她会很开心的。”
魔女的眼睛转了转,没有问威廉先生为什么要把自己带回来而不是带去别的,或许是叫做警署一类的地方,她戳了戳口袋里的彼特,拿出一小袋金币来,“先生,很感谢您给的午饭,我想我的家人一定已经在找我的路上了,可否请您收留我一阵呢?”
不论是小女孩因为不愿意一个人住,还是因为小姐脾气不想住那脏兮兮的旅店,威廉都显得十分诧异而开怀。
他先是犹豫了好一会,才接过那袋金子,“这…我只是举手之劳,不能收下,我先帮您收着,待您的家人哪天找到你了,我再把这代金币还给您。”
赫莉得到了一间阁楼的房间。
木楼梯吱呀一声关上之后彼特从她的口袋里跳出来啪叽一声拍在地上,依旧是一个小圆球的样子。
赫莉把手指伸给他。
“赫莉,赫莉,威廉先生是个好人。”
“……”赫莉没说话,但是彼特直觉觉得那种神色不对。赫莉从来没有这么对自己笑过。
“赫莉,你喜欢威廉先生吗?”
“为什么这么问?”赫莉说。
“因为你说他是个好人啊。”彼特攀着赫莉的手指,“但是你为什么说谎呢?”
赫莉:“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蠢猪是好人了。”
彼特:“你谢谢他了啊?”
赫莉:“那我也谢谢你。”
彼特没心没肺地笑起来。
之后的一段时间一主一仆都住在阁楼里,他们没有再下过楼。
威廉先生每天都会按时地送来一日三餐,芝士、面包、煮豆子、咖啡或者是牛排。
赫莉不多做过问,只是每天就这样过着,既不问有没有家人的消息也不探听威廉先生的事情,她不急不躁,只是在阁楼里当一只小鸟。
赫莉划开自己的手指,给彼特喂了两滴血。
彼特藏在靠垫后面,把自己装成一个阴影,“赫莉,我想出去玩。”
赫莉把手上沾到的汤汁擦在彼特身上,又笑起来。
彼特怕她这样的笑,这应该叫怕吧?总之每每如此,彼特就闭上嘴什么都不说,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阴影。
“你今天在屋子里玩的不开心吗?”赫莉问他。
史莱姆使劲回忆了一下,除了那个很大的书房,他还看到了漂亮的卧室和一个地下室。
“你下去看了吗?”
史莱姆摇晃着身体,表达着没有。
又三天过去了,威廉先生放下楼梯,温柔地询问赫莉要不要下楼来。
“很抱歉,但是,您的家人始终没有消息。”
“没关系的威廉先生,是我自己不好偷跑出来,他们肯定是在生气,毕竟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女孩。”
威廉先生的面孔扭曲了一下,在烛光的噼啪声中缓慢地笑起来,“怎么会呢,您这么有教养,又淑女,您的家人一定很担心您。”
史莱姆躲在缝隙里,不敢说话。
“可是近期又没有什么危险的事,母亲怎么会还不来找我。”赫莉低着头,看着地板缝隙。
“最近外面确实危险。”威廉先生像是找到了什么可以自圆其说的故事,语调都高昂起来,“森林里发现了三具尸体,都是猎魔人。”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等赫莉的反应,“可能有魔女出没。”他状似温柔地摸着赫莉的脑袋,手心里的茧子将她一头短发摸得有些乱。
隔天,史莱姆从缝隙里看见了有人敲响了威廉先生的门。
那是一群穿着统一又奇怪的人,其中一个绿头发的人类手里似乎捏着怀表似的东西,好奇地四处张望。
赫莉把他从缝隙里抠了起来。
“那是谁?”
“那是猎魔人。”赫莉说,“你看到了几个人?”
彼特没有手指没办法掰着数,但他回忆了一下说:“我看到了四个人。他们来和我们交朋友吗?”
“他们来杀我。”
彼特一时间不能理解,问道:“什么是杀。”他转而又问,“为什么要杀你。”
猎魔人的来访似乎打乱了威廉的计划,他说了好一会话,从对面人手里接下了一张传单。
当夜赫莉只是坐在餐桌前,就着烛光,一口一口地吃着饭。
血色从肌肉的纹理中透出,银色的刀光缓慢滑过视网膜。
威廉吞咽着口水,恍惚间分不清赫莉切开的是牛排还是别的什么。那把红色的雨伞立在墙角,和油画与照片一起,静悄悄地。
“您不吃饭吗威廉先生。”赫莉叉起那块牛排,滴着汁水,“您这两天都瘦了。”
“难免的,您不必介怀。”
赫莉一边说着是吗,一边嚼着不怎么鲜嫩的晚餐。
赫莉没能出门,她被允许在房间里走动,但是更多的时间还是在阁楼里,只有威廉先生回家的时候才被允许在客厅或者书房呆着。
彼特有时候会被赫莉揣在口袋里,有时候就藏在阴影里。
他依旧每天都在探险,有时候去翻看书架上的书本,有时候看卧室里成排的空盒子,有时候看看衣柜里一整排的男装。
彼特每天都把看到的东西和赫莉说,活像是个小孩子在说自己的经历,翻来覆去,颠来倒去。
“为什么不去地下室看看呢?”
彼特义正言辞地说道:“那是威廉先生的隐私,我不该去看。”
赫莉似乎不怎么开心,指了指天花板的缝隙,“去看看。”
威廉先生每天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早,他询问着是否有人丢了孩子,却总是一无所获地回来。
可当他看着门口放着的伞和那个一天天瘪下去的空袋子时又觉得自己一定没错。
威廉喘着粗气,拎着酒瓶又一次在太阳落山前就回到了家里。
昏暗的室内他看不清周围,桌面上的相框里那个女人正披散着长发与他对视,而当他瘫坐在油画前的时候,那名女子也在对他笑。
窗外晾着的衣服随风晃动,他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今晚吃什么?”“水煮鱼。”
“今晚吃什么?”“牛排。”
“今晚吃什么?”“煮青豆。”
……
当他看见赫莉坐在楼梯上看书,手边是瓷花瓶的时候视线有一瞬间的恍惚。
“我家在很远的地方。”赫莉捧着书甚至没有抬头,“或需要很多时间才能找到我。今晚吃什么呢威廉先生?”
啪的一声。威廉看见无数白色碎光在眼前浮现。
彼特滑进了地板的缝隙里,看见了地下室的全貌。赫莉说的没有错,他应该来地下室看一看的。这里有他熟悉的东西。
两具雪白漂亮的骨架躺在那里,和他记忆中的某个场景渐渐融合,喷洒的血液和晃动的烛光,尖锐刀刃穿过身体时的迷茫。
彼特不知道那痛不痛,因为那个人没有发出声音,只是倒在了原地。
“这是哪里啊。”
“这里哪都不是。”赫莉将那张相片扣好,又把油画费劲地拿了下来。
“她们是谁呢?”史莱姆搭了把手,绿色的眼睛漂浮在领口的液面上。
随后彼特又指了指坐在椅子上的威廉。
“他为什么不动了。”
赫莉拿走了那把红色的雨伞,时隔半个月走在了街道上,她看见了张贴在餐馆里的公告,写着一位撑着红伞的小姐走失,希望家人尽快来接走她。
彼特探头探脑,问道,“为什么没有你的画像呢?”
“因为威廉没想要把我交出去。”
彼特又问道,“那他为什么天天往外跑?”
“因为想找到我的家人。”
彼特不明白其中缘由,他觉得‘威廉’很奇怪,把他们关在阁楼里,一边寻找赫莉撒谎说的家人,一边又不肯让赫莉见人。
赫莉撑起伞,在人群骚乱和议论中走出了小镇。
彼特听见有人在说死人了,有人说出了疫病,也有人说是魔女作祟。
——TBC


*祝我cp七夕快乐!
*狗狗早餐会·一些无人知道的故事
时间是上午九点一刻,房门刚刚关闭,一串轻快的脚步声渐行渐远。法斯特与布瑞克趴在地上,耳朵紧贴着地面,彼此交换着眼神。
她走了吗?
已经走远了。
于是法斯特直起身子,但并未像一条狗一样用四条腿站着。它缓缓抬起前爪,只靠两条后腿站了起来,为了保持平衡,它的一只爪子扒在门把手上。它脸上的表情可以用严肃来形容,与它平常的样子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天差地别。紧接着它做了个极为人性化的举动——它清了清嗓子,然后发出一连串的呜咽:
布瑞克,我们得开个会了。
这并不是人类能听懂的语言,但法斯特也并未说给人类听。布瑞克歪了歪头,它嫌站着太累,已经把肚皮安安稳稳地贴在地面上了。但法斯特居高临下,它又嫌仰头太麻烦,干脆打了个滚,四脚朝天地看向头顶的法斯特:搞得这么正式做什么?这里就我们俩。
法斯特对布瑞克的态度很不满意:你好歹站起来听我讲!它抬起一只脚,去踩布瑞克的肚子,后者灵活地一滚,完美躲开,顺便伸出爪子拨了一下法斯特仍踩在地上的那条后腿,其结果就是一阵响声过后大金毛狗委委屈屈倒在地上流眼泪,短腿的柯基托着下巴看戏,闻声赶来的小土狗满脸懵懂地看着两条同类,不知道它们在干什么。
去去,大人谈话,没有小孩插嘴的余地!法斯特看到萨拉米跑过来,冲它吠了两声,把小狗崽子赶跑了。萨拉米还听不懂两条使魔使用的语言,只是本能地觉得自己不受欢迎,于是迈开步子跑了。房门口又再度只剩下两条狗。
所以到底是什么事?布瑞克懒洋洋地问。还能有什么事?法斯特反问,那个人!除了那个人,还能有什么别的事吗?
听了这话布瑞克稍微动了动耳朵。它让自己稍微趴得端正一点,显示出对这件事的重视。法斯特继续说:关于今后如何应对那个人,我们应当制定一个统一方针。我有种预感,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的话,他可能很快要成为这里的一员。
这样不好吗?家庭成员的增加是好事情。布瑞克说。法斯特猛烈地摇头:别忘了,他可是猎魔人!猎魔人是魔女的敌人,也是使魔的敌人?我们绝对不可能让敌人来到这个家里!
那就让他变成使魔呗。布瑞克懒洋洋地说。给他也发一个项圈,拴在家里,不听话就打一顿,看他还敢不敢猎魔女。法斯特眼前一亮:是个好主意!到时候,我们把他的饭全都抢走,他就不敢再做坏事了!
但是,布瑞克又慢条斯理地说,最要紧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猎魔人,而是如果那家伙真的到这个家里来,诺玛还会继续宠爱我们两个吗?
肯定会的!法斯特斩钉截铁,但下一秒就露出泫然欲泣的表情,诺玛还会宠爱它们吗?她要有新的使魔,新的狗了!布瑞克继续火上浇油:想想看,那家伙变成了诺玛的使魔,他虽然不像我们,但他会说人话,还会陪她喝酒,陪她散步,还会帮忙洗衣做饭,那她还会养我们吗?我们好不容易跟着诺玛到这里,难道你还想回布兰达那里去吗?
法斯特想到自己同胞的遭遇,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呜呜,我不要回去!我不要变成狗肉香肠!
所以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将那个人从这个家里驱逐出去!布瑞克高声吠叫,法斯特也激动地附和起来:驱逐出去!驱逐出去!但是,大金毛脑袋一歪,看向布瑞克:该怎么做才好呢?
我们要变得比他还有用,布瑞克说。那个人会说人的语言,我们也要会。你现在会说几句人话了?
法斯特清了清嗓子,用标准的伦敦腔开口说话:“你好,我叫法斯特,我是一条狗。”
柯基犬用手捂住了脸:还会别的吗?
“我饿了,我困了,我想拉屎。你是狗吗?诺曼不在家,明天再来吧。”法斯特想了想,得意洋洋地又补充了最后一句:“Fuck you。”
布瑞克欲言又止,止言又欲:你还是别说人话了。
法斯特纳闷:怎么了?我学的不都挺实用的?它对布瑞克的反应很不满意:那你呢?你学会了什么人话?
布瑞克轻蔑地哼了一声,用充满感情的声音朗诵起来:“你以为我贫穷、相貌平平就没有感情吗?我向你起誓:如果上帝赐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让你难于离开我,就象我现在难于离开你一样。上帝没有这样安排。但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如同你我走过坟墓,平等的站在上帝面前。”
法斯特听糊涂了,它不得不承认布瑞克比自己更胜一筹。它又听布瑞克说,今后行动的主要方向就是学会说人话,最好学会直立行走,才能让诺玛更加重视它们两个。法斯特觉得很有道理,不住地点头,最后布瑞克用力挥了挥手:散会!然后它就一溜烟地跑去阳台午睡了,留下法斯特在原地迷茫,明明是它说要开会,最后怎么全都是布瑞克在说?
但无论如何,今后的方针倒是定下来了。说人话,办人事!法斯特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殊不知布瑞克在阳台上摇着尾巴懒洋洋地笑:诺玛接受会狗叫的人,却不需要会说人话的狗!它就等着法斯特弄巧成拙,被赶回老家,自己就能成为诺玛最喜欢的狗了!
使魔们的会议暂且落下帷幕。在主人看不到的地方,这样乱七八糟,不知所云的会议还会一次又一次地上演,而这对于魔女与猎魔人来说,只是另一个世界里发生的故事罢了。
*雪夜狂奔·一些未发生过的故事
伽利略提着油灯,神色匆匆地走在树林中。也许是下过一场大雪的缘故,深夜的树林并不显得太过黑暗,但却格外安静,鞋底踩在积雪上咯吱作响的声音仿佛被放大了数倍,让人听得心烦。他加快了脚步,心中满是不安,连远处积雪簌簌落下的声音都让他有点心惊肉跳。
他不知道自己的确切位置,只能靠北极星确认方向。在这空无一人的寂静森林,他感到恐惧渐渐爬上脊背——他知道,这片森林人迹罕至,常有野兽出没,没准儿现在就悄无声息地跟在他身后,等待着饱餐一顿……不,再这么胡思乱想下去,他还没被野兽吃掉,就要被自己吓死了。他强打精神继续赶路,却听到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咆哮。
伽利略顿时汗毛倒竖,他试图辨认声音的来源,那声音一声接着一声,像是嗜血的野兽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吼叫,伴随着身躯掠过树林时的沙沙响声,一步又一步地向他飞快靠近。他害怕极了,拼命地向前奔跑,跑到肺叶里的空气都快要被抽干,但那野兽的声音如影随形,他甚至能听到令人恐惧的鼻息,仿佛它就在他身后,冷静地等待着狩猎的好时机。
伽利略脚下一个趔趄,他跑得太快,又太慌乱,被一条裸露的树根绊倒在地。他绝望地想,完蛋了,他没有成为魔女的刀下亡魂,反而成为了野兽的盘中餐。他看到月夜下丛林中模糊的影子一闪而过,灼热的野蛮气息向他袭来。只是瞬息之间,他就被这猛兽结结实实地压在身下,胸口被脚掌牢牢按住,脖颈边划过一道温热的鼻息,伽利略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心脏在胸腔里砰砰直跳,等待着利齿割开他的喉咙,喷涌而出的鲜血成为野兽的美食,但想象中的剧痛并没有袭来——的确有什么东西触到了他的脖子,却只是象征性地轻咬了一下,像是猫狗嬉戏时的力道,轻微的一点痛感消失后,留下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痒。
伽利略心生疑虑,悄悄把眼睛睁开一条缝,正好对上眼前凶狠野兽金色的瞳孔。他几乎要怀疑那是错觉,那眼神并不像他想像中凶狠,反而带着一丝有些玩味的笑意,他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但借着洒下的月光,他终于看清了它的模样——这是一头母狮。
还没等他意识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眼前的野兽前腿踩着他的胸膛,露出了一个极具人性化的笑容。它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里尽是嘲弄,伽利略一动也不敢动,做出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狮子用脚掌在他的脸上拨弄两下,像是在玩弄猎物,又像是在与人玩耍,见伽利略一点反应都没有,一副被吓傻了的模样,它才停下动作,在月光下渐渐变化身形,变成了伽利略熟悉的样子。
魔女诺玛冷笑两声,拍了拍伽利略的脸,与刚刚狮子的动作如出一辙:“就你这胆量,还当猎魔人呢?”
伽利略活像个霜打了的茄子,他趁夜晚出逃,就是想逃离魔女的魔爪,结果还是未能如愿。他抬起头,越过诺玛的头顶,看向头上的皎洁月光,又想起那夜色下的金色瞳孔,突然有一种心脏在胸腔里横冲直撞的感觉。
肯定是吓的,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