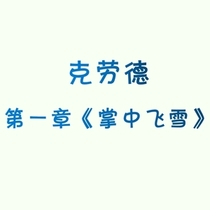故事的舞台位于1888年的欧洲。
由农业改革拉响了工业革命的第一篇章,此后的数十年,文明的曙光敲响了民智的门。
灯火点亮了伦敦的长夜,铁路如血管般布满大地,在蒸气轰鸣的城市里——
魔女与人类间隐秘的战争开始了。
本企为参考了现实国家、历史、人物的半架空企划,存在对真实事件的轻微魔改,可当做现实世界的平行时空看待,考据党切莫较真,介意勿参,感谢理解。
感谢大家半年以来的陪伴与付出,红月之下企划至此顺利完结!感谢每一位参与了红月之下企划的玩家。



这天刚下过雨,窗外的叶上还沾着些水珠,云一层一层的叠在天上,太阳只从里露了个半面,勉强算个好天气。缕缕热气交互捆成透明的烟往半开的窗外挤着出去,满屋都充斥着清雅又甜腻的药味香气。普拉维斯坐在沙发正中间,皱着眉头,手抵在下巴上,另一只轻轻地晃着奥萝拉之前递来的小瓶中的红色液体,仍摆出一副很认真地在思考的模样。
“既然那位魔女只能跟小动物相处的话,那奥萝拉必须'喵喵喵'地,跟她交流才行吗?”
“你可真会开玩笑。”
“啊,不是,我没在开玩笑。”
他话刚说完,门就被另一头的窗外吹进来的风啪地关上,二人条件反射地抖了抖耳朵,这句话过后空气便沉默了。不过她的眼神里写满了“不要再继续说了不然就把你沉进药锅里”的字,他也只得把那句“可你的药锅很小”给硬生生憋了回去。
巴掌大的猫坐在木地板上,身体上环绕的黑色条纹在被门阻拦了光线的屋内就跟被抹去了似的。奥萝拉“啧”了一声,但也还是先在地上弓起身子伸了个很标准的猫的懒腰,然后才甩着尾巴,懒洋洋地往窗户那边走去。
药效发作变成了狗的普拉维斯索性就坐在地上等。他看向禁闭的门,又看向半开的窗,至今也想不通为什么这间木屋要把窗户开在树边又把门迎着太阳,在没有点灯的情况下关上门,这屋内就好像比外面多流走了六小时以上的时间一样。
毕竟,虽然妹妹每天都用阴暗又凶恶的眼神拒绝与他一起出去散步,但她经常变成猫去门口的那片空地上,在那块吩咐他每天都要拿毛巾擦一遍的树桩上横躺着,把肚子露给太阳。
按奥萝拉本人的话来说,常年坐在家里就算是魔女也会腰酸背痛,所以要经常变成猫去放松一下。
看着身体柔软到可以在树桩上扭成一个人类绝对无法达到的麻花形状的只有巴掌大的猫,普拉维斯的眼里偶尔会投去羡慕的目光。
那些森林里的麻雀就叽叽喳喳地往附近的树上飞,偶尔也有几只会飞到有很小只的猫的树桩上,盯着毛有些长的条纹猫歪几下头,甚至还有些时候会啄上几口。
然而每当普拉维斯跨出家门一步,这些鸟就会四散逃离一次。
小动物之间的惺惺相惜,似乎不作用于他身上。又或者,奥萝拉肯定又在之前的炼药里偷吃了那些甜一点的小果子,其中定然有这些鸟的主食。然后她被药锅里的香气熏制,现在应该全身都是那种果子的味道。
奥萝拉究竟被这些鸟当做食物还是被当作同类,不论哪种都有些让他难以理解。何况话又说回来,虽说奥萝拉喜欢变成猫去晒太阳,但从来都不会发出猫应有的叫声,就算是偶尔睡糊涂、在木桩上躺着伸懒腰的时候也一样。作为魔女来说尚不作评价,但作为猫,她已经被野生动物看得非常轻了。
“喂,傻狗。”在他回忆的时候,跳上去并且坐在了窗台上的猫转过头来喊道,“我先去森林逛几圈习惯一下,好好看家。”
由魔女变成的猫说完就从窗户轻盈地跳了出去。普拉维斯回过神来,望了眼禁闭的门和自己很难爬出去的窗。
“呼姆。”
奥萝拉从窗户跃出去后,肉垫踩到的青草仍然有带来些许湿润感。视线点的变化导致了她看这个世界的角度也变化了,显得高了许多的青草和近乎高耸入云的树木,一切都再次变得新鲜,她一路上望望这里望望那里,竖着尾巴轻声地往森林的更深处里走。
之前跟普拉维斯交流意见的时候,她唯独在“搞不懂领袖在想什么”这一点上跟普拉维斯达成一致,分歧点在于“搞不懂过世的母亲在想什么”。普拉维斯认为母亲生前作为激进派的一员,应该理所当然地仇视人类或其他种族,但奥萝拉否认。
在那间她和母亲一起度过几十年的偏僻的小木屋里,母亲从来没有展现出过针对任何事物的恶意。她只是像对待她一样温柔地跟动物交流、亲手种下各种草药,然后调配出一些酸的甜的不知道到底能用来干些什么的药来。
然而对于跟父亲居住在原本的家里,不被允许踏入那间木屋一步的普拉维斯来说,那扇门的里面黑暗又压迫,从窗户的缝隙中流出的气味总是酸到苦涩,他没办法把魔女跟小时候见过的那位带着草与花香气的母亲的笑容重叠在一起。
父亲的解释无外乎“这是魔女必要的修行”一句罢了。如此,度过了截然不同的童年的奥萝拉无法想象的事物,普拉维斯也一样,不再有能依靠的人或事物后,她们两人方才惊醒。
不论彼此的分歧有多少,讨论都只需要达到岔路最后都通往一条大道的程度。为了之后的目标她需要完成现在的目标,就像炼药必须把药物分批次、类别和顺序,然后所有的最后一步,把普拉维斯掉的毛丢进去就好。
一只巴掌大小的猫在树木之间踩着些枯叶往不知尽头的方向飞奔而去,深色的穴兔好奇又胆怯地在洞穴的边缘往外望,低枝上的麻雀歪着脑袋,时不时地鸣叫上几声清脆。这种景象既和谐又带着违和感,只不过大地不会在意这只本不属于这里的小小过客,她灵敏地一跃而起,跳过那坑坑洼洼的由兽类爪印形成的,足以让她跌落进去的水洼,爪子在接触到水洼旁边的树木躯干上的那一瞬用了力,于潮湿的接近根部的部分上留下些攀爬的印。然后,稳稳地落了地。
猫的柔软和灵敏一旦习惯了就很难忘却。在以前她对这句话不屑一顾,这只不过属于反对的一种理由。正因为看到过许多次连普拉维斯这种家伙都能捕到兔子,她才抗拒跟母亲一样变成那种只有听力敏锐的被动的生物。
直到她学会跟猫一样往高的地方爬,在木质的桌腿上磨爪子,把那些堆放在架子上、桌子上的事物一点一点地推下去,“噼啪”的一声,母亲就惊醒了过来,在一片漆黑中点了光,捏住她的后颈把她提起来。
“奥萝拉,不能沉浸于猫的本能。”她头一次从母亲困倦的声音中听出几分严肃的意味,“你会忘记自己原本是什么。”
她怯生生地点了头,尽管每一个字都还不能理解得太明白,但她开始惧于使用与生俱来的力量,亦在与力量的疏远时期中忘记了普通的猫理应最喜欢做的事。戒掉猫的习惯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每次看见小动物她都会想些有的没的事。自小就不再能见到同龄人的她,在思考这些事的时候总是充满猫般的好奇与不敢踏足的恐惧。
至于现在,爪子应该在什么时候伸出去,四足应该如何交互地飞奔出去,身体究竟能扭到什么样的程度,经过长时间的晒太阳,在家里散步(主要是在普拉维斯出门的时间里),以及此时此刻地在森林里奔跑,她逐渐想起来那些习惯与一些隐隐约约的冲动。当年母亲想传达过来的事,想表达的事,忽然便了然于心了。
在肚子饿的时候不顾一切地去寻找食物是活下去的本能,在受伤的时候不应示弱,反而警惕地焦躁起来也是生存的本能。穴兔为了躲避天敌会在许多地方留下洞穴,鹿为了逃离狼群亦会全力奔跑,哪怕是位于食物链顶端的森林中的老虎,捕猎的时候也大多依赖于潜伏,他们伏低身子,踩着悄无声息的步,从掩体中一跃而出。
她一跃而出。
只因恰巧现在肚子有些饿,然后眼前出现了肉干这种恰好在她捕食范围内的事物。猫的牙并不像草食动物那样易于嚼碎,它只能撕下血肉,挑开血管,面对没有这些东西然后还硬邦邦的食物,她只得全力地歪着脑袋用里面的尖牙去咀嚼,面部用力的同时耳朵也狠狠地往斜后方拉成飞机耳,让这小猫的模样看起来有些许的狰狞。
“呃、为什么陷阱没有触发?!”
忽然听见了人类的问句,奥萝拉不由得地心里惊了一下,她瞬间警觉地把啃到一小口的肉干吐回地上,抬了头睁大眼睛看向声音的源头,灌木丛里面应邀发出一阵唰唰的声音。
高大的人类从里面钻了出来——不对,只是在现在的自己眼中看起来过于高大罢了,何况对方背着光,因此整个正面的阴影都从身为巨物的存在中勾出别样的压迫感。直到猫为此条件反射地连连后退,视野得以被解放后,看见对方头上沾着些与其发色相近的嫩芽树叶为止,她方才停下退却的脚步。
“森林里面原来会有猫吗…嗯?”
那人类自说自话地蹲了下来,也不管地上那堆刚刚被猫踩过的叶子与草尚还湿润,她用手把肉干下边的那堆形形色色的遮掩物拍开来,露出了埋于其中的精密器械。首先是几片铝片与铁片焊在一起形成的平整的测重板,又链接上那些敏感的铜丝铜线,另一段牵引至测重板的一端与其下方的更深处,以及以几个扁平的连上干电池的小型但有力的启动器与活塞作为推动测重板的力;按照预想,有活物停留在测重板上的时候,就会触发一系列精密的连锁反应,最后活塞会将测重板给推走,然后让活物的其中一只爪子落在其下的坑洞里,完成剥夺其行动力的功效!
本来设计图阶段的预想应该是这样才对。
“嗯……”
她收回手用那沾了些新泥的手抵在自己下巴上,浑然不觉地上下动着食指磨挲着思索着,期间她盯着不远处的大尾巴幼猫盯了好会儿。随后她又从身上的某个口袋里摸出一条手帕很随便地象征性地擦了擦右手,然后拿起地上那根已经被猫咬过一口的肉干,朝那只警惕地向后竖着耳朵、炸着尾巴毛的幼猫的方向递。
而那只体型极小的猫仅仅不满地甩了甩尾巴,没有理会白食的诱惑。亦或说,内心在毅然决然地不断地跟本能争斗。
这片森林即使在接近镇子的边缘地带也会有猎人啊小孩啊什么的来这里做各种各样的事吧。因此人类一视同仁地不被自然信任,野生动物像这样子警惕她倒也不是什么少见的事。她释然地收回肉干,张了嘴准备把原本作为自己的午餐而存在的东西一口吞掉,在那之前先闻见了土与雨混在一起的新泥与青草特有的气息,随后余光看见面前那猫似乎在把脖子往前探,跟这只猫对上视线后她再仔细一看方才发现,猫本来就属于眼睛在脸上占比更大的类型,而体型娇小的幼猫更是如此,那本应是一双淡些的红色瞳中,有一只呈现出带着点极浅蓝色的灰白就显得格外显眼。而且它总是习惯性地将红色瞳的那一半面稍微侧到前方,就好像仅仅在用一边的眼睛看东西一样。
她又闭了嘴,皱了眉头,神情为难地看看手里的肉干,又面色复杂地看看就坐在自己面前不远处,虽然显得警惕但是一步未离的可怜的小猫。她又试着把肉干往前递,那只猫虽然很明显地把脖子往前伸了伸表达出兴趣了,但仍然留在原地寸步不离。
无奈之下,她只得把手里的肉干朝自己前方稍远处丢去。野生动物也果然吃这一套,它们警惕着的往往是人类的那双手。那只猫一步步地靠过来了,迎着面前的庞然巨物的阴影带来的压力,奥萝拉也头一次觉得,平日里见惯的事物,在被放大的时候会看见一些本来看不清的东西,由此而显得新奇又可怕。
人类所腌制的肉干的味道也算新奇。说起来自小就跟着母亲吃这种果子那种果子,又或者跟着父亲吃那种肉和这种肉,缺少调味料的一成不变的腥味只在父亲和那只笨狗的眼里不让人恶心,老实说就算单纯地用水煮过或者用火烤过也难以下咽。她的记忆中,母亲的草园里本该应有尽有,却唯独没有香料。
在她认真地、狰狞地咀嚼着地上那块肉干的时候,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视野变高,变得能从正前方看见那人类的脸,又在她的眼镜中看见了反着映射出的自己狰狞的模样,她把自己惊了一下——然后条件反射般地从喉间发出些威胁或者说受到威胁时的凶恶的呜呜喉音,她又把自己惊了一下。
至于那位像对待普通的猫一样捏着她后颈提起来的人类,正惊叹于此猫的体重之轻,也难怪不会触发以重压为触发条件的陷阱。同时也像是被那幼小的喉音给威胁到一般,把猫给提到了离自己的脸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还顺便随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用手背把那几抹现在已经差不多快干掉的泥巴抹得更花。
如果屈于动物的本能,你就会忘记自己原本是魔女。母亲的话一遍遍如同警钟一样在她心中发出巨响,她在人类手中拼命地挣扎了几遍,又拼命地把嘴里的肉干嚼烂试图吞下。不对,不对,究竟哪边才是我的本能?
视野又发生变化了。被捏住的后颈的部分感受不到疼痛反而成为了不安的源泉,她被人拎到手心里去,然而后颈还是没有被放开,被压制的同时被掌控,一些被尘封起来的记忆瞬间险些被撬动,她狠狠地呲着牙,咬着嘴里的肉干,竖着毛竖着耳朵,但一切都因为彼此体型的差距,对方显然没有在意这些,甚至于放心地松开了捏着她后颈部分的那只手,默了片刻后,又伸出来拽她嘴里的肉干。
她下意识地把肉干咬得死死的,喉间发出“呜呜”的威胁喉音。
“……”戴眼镜的人类有些无语地看着这种护食的行为,眨了眨眼,疑惑道:“果然只是普通的猫吗?”
话罢,她把猫放回了地上。那猫也一点都不客气,一转身便跑了个没影。她低了头,拍了拍地上那组金属器械表面上粘上的干掉的泥土,将之一一折叠收起,而后站起身来。
“安妮!”
“嗯?”
背后的呼声叫她转过头去,手里也不忘再次拍了拍器械铺上地上的那面背面上,象征性的可能会沾染上的森林的尘。猎魔人打扮的人戒备地拿着武器靠了过来,他先环顾了此处的森林环境一眼,而后又看到她手里的器械,愣了半秒,方才继续说道:
“指魔针有反应了,大约就在这边的附近。”
“这附近?”
她略微有些觉得疑惑地抬起头来。
“没错。有什么发现吗?”
“不,只有一只普通的小猫。而且陷阱实验又失败了,啊哈哈哈…。”
“……你不是战斗人员,快回去避难吧。”
“明白!”
在跟着另一位猎魔人离开这里之前,她忍不住转头往森林的深处望了一眼。
雨后的太阳现在已经从云中慢慢地移了出来,映照出枝与叶投在地上的斑斓光点,那被茂盛的树木遮挡笼罩出的更深处的阴影,迎着面灌来一阵把树叶都扫得唰啦作响的轻风。
她抬手把被风吹得有些乱的耳边的些许发丝按住,朝耳后撩了一撩,然后在猎魔人同伴的催促下,抱着金属制的陷阱器械一路小跑着离开了森林。
另一方面,奥萝拉一路狂奔到自己家的附近。沉浸于本能忘记自己之前走了多远是她的大意,就这么中了最基础的食物陷阱亦是她的不堪,她警惕地朝自己身后望去,竖着耳朵试图分辨自己身后是否有什么别的生物的脚步跟过来,嘴里还不忘再咀嚼了几下肉干,然后她甩了甩脑袋,在原地追着自己的尾巴转了三圈,通过这样规定好的暗示来让自己忘却野性、得以变回魔女。
嘴里叼着的肉干倒也还剩下不少,她索性将剩下的那小半截用力扯开。
“走了,蠢狗。顺便。” 她拉开家门,随手把那小半截肉干硬塞进被放置在家中许久的狗的嘴里,“差不多又该搬家了。”
“嗷呜呜?”而那笨狗疑惑地歪着脑袋应了一句,嘴里的肉干也就自然没含稳,理所当然地落在地上、他便又低头去闻肉干掉在了哪里。
奥萝拉没理会普拉维斯,她只把一些必需品,诸如那口小小的药锅,母亲留下的草药的笔记,还有那件专为集会准备、不可或缺的礼服,以及一根刺猬身上的小刺,姑且用魔法暂时将这些东西收纳在了帽子里面,至于在这片森林里住下的几年来,家里累积起的剩下的其他东西,也许只能日后再来取——不,会被猎魔人找到、拿回去研究然后销毁也说不定。
虽然一些生长期久远又难以栽培的草药无法带走有些可惜,但相比起因为身上带着这些特殊的味道而被怀疑的情况来说要好太多了。这一点她跟普拉维斯可不一样,毕竟后者再怎么用水洗那个尾巴,没过几日就肯定又会开始掉毛、开始散发出独属于犬类的特殊气味。
好了。总之忽视掉普拉维斯带来的各种问题,准备就绪之后,便该戴上帽子骑上扫把,去完成现在应该做的事了。
在临走之前,她最后一次环视了一遍这个简单的家,视线最终落在了桌上的那封未拆开的信上。她沉吟不语地在原地顿了几秒,随后叹了气,在半空中用指尖向上勾了勾,让那封本就带点魔力的信浮空而起,随后又虚划了几笔,信件顿时从封标处开始燃烧起来,露出其中的信的内容,其中的几个预想之内的字眼,看来是不难理解的内容,即是说除了这几个关键词以外便不再具有作用——待整封信都烧成灰烬,一点一点地全部堆到桌上后,她才叹了气,随手拿起门边柜子上的空酒瓶,然后带上门走了出去。
“汪呜呜?”
听见身后那条狗的疑惑的呜呜声,这次她反应得很快,语气平淡地应道:“那封信大概是什么内容我已经猜到了。反正,接下来必须要先做的事,暂时跟那件事没有关系。”
话罢,她拿着扫把站在门前的空地上,将之前用来招待过别人的,已经空了的红酒瓶啪地一下摔得粉碎,然后蹲下去,在碎掉的瓶玻璃中挑选出最小最尖锐的那块,之后她再站起来把那枚小的碎玻璃片丢到空中,紧接着一道火焰覆盖着玻璃片的瞬间之后,它化作一道红色的光往某个方向直直地飞远。她见状便娴熟地抓着狗乘上了扫把,追着那道红光而去。
尽管之前因为各种各样的事耽搁了些,但所幸以直线距离飞往法国并不会花那么多时间,现在太阳在往山后落,那道引路的红光开始变淡便说明这里离法国已经非常的近,时间上也正是黄昏。
诚然,对派别不同的魔女的打扰容易引起某种问题,她也只得用上那种最庄重的送信魔法——在信封上耗费大量的没有意义的魔力,因此信件在被魔力推动、往目的地行进时能够变成更加华丽的“生物”。然而她的理性在被猫的野性压制的时候,那片森林开始变得堆魔女而言不安全,在寄出信件的几小时后根本来不及等待回信,她只得带着狗匆匆地往那边赶,寄希望于那位收到信的魔女不会恰巧在今日的黄昏时分出门。
这时引路的红光彻底地消失了,意味着接下来的这段路程必须自己来搞定。她便飞低了些,在其中的一片森林中探知着可能存在的那份作为信件的,属于自己的魔力。
在路过某一个掩藏在森林里的屋子的时候,她忽然顿了一下,此时的太阳已经近乎完全淹没,光线变得暗淡,视野愈来愈受到限制,如果再找不到那位魔女的居住地的话说不定就糟糕了——正这么想着的时候,她看见那座屋子里走出位与这暗淡的黄昏环境相融、有如落日余晖般的魔女,方才条件反射般地降落,抬了些音调大声喊道:
“——夫人!”
——那位被喊停脚步的魔女正要从帽下抬起头。
奥萝拉忽然想起那些传闻与记录,这瞬间她反应极快地摘了帽子、减了速,然后在降落的刹那,对方定住眼的前一秒,以巴掌大的猫的状态从扫帚上跃下,稳稳地落在了魔女的正前方的那块空地。然后不再被控制的扫帚失了力,顿时带着虽然起跳时机差不多,但没能真的跳起来的普拉维斯一起,几乎是硬摔在了地上,发出阵噼里啪啦的乱七八糟的声音,还因之前的惯性擦着地面向前再行进了十来厘米。些许尘土飞扬而起,普拉维斯亦摔在地上滚了一圈,把那身雪白的狗毛给染成了半灰。
最后,那顶魔女的帽子才悠悠地落了地,正好盖在普拉维斯身上。
“……哎呀。”被喊作夫人的那位魔女的目光在猫跟狗之前交互地看了几眼,面色愉悦地轻轻笑道:“真是难得一见的小客人。”
“有些事想拜托你…黄昏夫人。”
得以自下而上地拜见这位魔女容貌的此时此刻,诸如“一旦见到了就绝对不会认错”的不太可靠的言论与勉勉强强的情报倒也难得地被揉到了一起。看见那头显眼的发色,再加之已是黄昏之后,临近夜晚的时间段里,在那些逐渐沉默的小动物与昏暗的环境的村托下,她带着一种令人敬而远之又正因如此而高贵神秘的气质,而之后无论谁都能瞬间理解这一切。
“汪呜、汪!”
此时普拉维斯也终于从地上挣扎着爬了起来,在奥萝拉之后插了句谁也没听懂的话,然后叼起奥萝拉的帽子,小跑着也来到了魔女的正面。
“先不论你们要做什么。”她说着抬手打了个响指,身后的门便应声而开。尽管她并没有遮挡住进入屋内的直线路线,亦是象征性地往旁边退了一步,“欢迎。肮脏的小客人们。”
她所邀请进入的屋内,呈现出一种在其他地方绝对见不到的别样的景象。奥萝拉被好奇心驱使,普拉维斯被担忧推动,他们一前一后地踏入了屋内,也正在此时,太阳已经完全沉没。黄昏夫人最后回了屋,然后轻轻地,“吱呀——啪”地关上了门。
身着执事服的男性看到了先没声地走进来的猫,然后又看见了跟前面这只猫对比起来体格相差巨大的,嘴里叼着个帽子走路走得啪啦啪啦的狗,以及它们身后留下的那串明显带点尘与泥的肉垫留下的脚印,眉头忍不住动了一动,最后看见了回屋的黄昏夫人,便是先朝她鞠了一躬。
“贝洛,准备茶和点心。”
“是。”
他应声而去。黄昏夫人则站在沙发与茶几附近,看了茶几上的拆过封的信件一眼,然后稍微躬下了些身子,用手指叩了叩茶几的面。
“真是不好意思,没办法准备像你这种没断奶的猫能坐的沙发呢。”尽管她的语气中稍微带了些显而易见的歉意、再结合上具体的内容时却听不出她藏在话里的原本意味。仅能从对方的话语中听出一部分本意是交涉即将落于下风的预警,奥萝拉坐在地上,甩了一下尾巴,等着她把话说完。
“便请你坐在茶几上吧?”她说着,看向由奥萝拉变化而成的体型极其小的猫。
“……”奥萝拉跃到茶几上,在有点冰凉的茶几上坐下,四爪聚得很拢,尾巴绕着一圈摆到了前面,盖在了两只前爪之上。普拉维斯则留在了茶几后面,顺便把那顶帽子就盖在奥萝拉的旁边。她倒也不怎么在意有没有被真的被当成客人来对待这种事,猫的好奇心在这种时候驱使着她往四处望,她看见这个然后又看见那个,尽是些以前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一时间变得稍微有些情绪高涨,她忍不住像个孩子一样问道:“那些是什么?”
“很好奇吗?那些是尸体,也是人偶。”
“………”
奥萝拉缩了缩脖子,显然是心里惊了一下,尾巴上的毛隐约有些炸开,变得瞬间安分起来,不再好奇了。
“呵呵……好了,现在。”
她见猫跟狗都已经坐下,便也在沙发里入了座,然后抬手将帽子稍微往下按了一下,由帽檐带出一抹恰到好处的阴影。从那阴影下的锐利瞳孔中,投来仿佛有些叫人觉得刺痛的目光,她仍然保持着那一贯的可以称之为温和的笑容,用着柔和但又处处透着尖锐的语气。
“让我听听,你到底想找我这个亡灵魔女、做些什么呢?”
她的笑容里确实有着包容与怜惜,却亦藏着一丝只有小动物基于生存压力而得来的天生的敏感才能察觉到的,掩盖在层层笑容与温柔之下的,危险的偏执与疯狂。
这时那位执事打扮的男性走来上了茶与点心,其中不乏环境丝毫不搭的精美茶点。
在被尸体包围的诡异茶会里,也正因为她露骨地把危险的部分展露了出来,才反而显得真诚。
奥萝拉望着面前冒着丝丝热气的红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想请你…教我亡灵的魔法。”
黄昏夫人微微地挑了下眉,随后又恢复到那幅不动声色的表情中去。她自茶几上端起红茶,靠近杯缘,不紧不慢地抿了一口。然后她又拿起一块方格图案的曲奇饼,送入嘴里缓慢地咀嚼、咽下。
直到做完这一切,她方才重新投来审视的目光。
“你想用亡灵魔法做什么?”她语气平淡地问道。
“我想召唤一个灵魂,从那灵魂口中了解一些事……”她答着忽然开始忍不住舔起自己的爪,然后低了点头,用舔过的爪自耳朵背后往脸上滑。反应过来后她先愣了几秒,随后就像放弃再跟本能挣抗一般,开始当着别的魔女的面洗起脸来,边洗还边说道:“那个灵魂、是我以前的使魔。”
面前那魔女忽然用指尖抵在唇上,忍不住轻轻地笑了几声:“呵呵……呵呵呵……真是抱歉,无意冒犯。”她说着,把红茶“噔”地放回茶几上,“你也知道,只有我这样的魔女才会为此感到高兴。”
奥萝拉点了点脑袋,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你对'生命'还有留恋的话,我可没办法让你接触到亡灵魔法呢……你呀,没有这个'天分'。”
“……天分?”
黄昏夫人又笑了笑,重复道:“天分。”
“……”奥萝拉稍微压低了些身子,转而把两只前爪揣着压在胸前的毛下,仍然有些不死心地问着:“那、如果拜托你使用亡灵魔法的话?”
她没有第一时间答话,而是在注视了猫改变姿势的一系列动作之后,视线移至奥萝拉旁边的那顶魔女帽上,应道:“那就得付出些什么代价才行呢。”
“……代价。我有必须要做的事,等那件事结束之后,想让我付出什么都可以。”奥萝拉话是这么说着,但她仍是竖了些耳朵,显得稍微有些警觉了起来。
“别紧张,不请自来的小猫。”
在她那副看不出复杂想法的面容之下,无法确认她究竟隐藏着些什么扭曲在根部的本质。她仍然用着那种听起来较为柔和,情绪却没有起伏、显得有些平淡的语气。
“有的魔女在被完全当作动物对待的时候、会认为这是冒犯。”
话间她笑容不减地稍微调整了一下坐姿,亦用右手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双腿。
“我要你的尊严。奥萝拉。”她说这句话的语气尽管平淡依然,听起来却让人觉得没有妥协、不容拒绝。
“……。”
奥萝拉沉默了大约十来秒,她先转过头去看了眼张着嘴,震惊得连舌头都忘记收回去的普拉维斯,然后将之判定为派不上用场,也只得起了身,在茶几上把前爪往前拉着,伸了个猫的懒腰。
紧接着,她不情不愿地跳到黄昏夫人的膝上,在其双腿上绕着尾巴转了个圈,然后老老实实地蜷着睡在了上面,把脑袋抵在自己的前爪上。
她作为猫本来就仅有巴掌大小,在成年女性手中更是如此。
老实说,她不太明白魔女被当作动物对待时的屈辱是指什么。但是,她看见普拉维斯那投过来的震撼的目光的时候,从内心深处中升起一股不知由来的愤怒。也不对,应该还有些别的感情也交织其中,但是比起这个那些都不重要,她现在满脑子都只想着等找到了新的家,就把普拉维斯的尾巴毛给拔秃掉拿去炼成很苦很苦的药。
“这片森林里很少能见到猫呢。”黄昏夫人满意地伸了手,轻轻地抚摸着睡在腿上的体型偏小的猫的脑袋,然后她转过头去,对着那位执事服的男性喊道:“贝洛,去准备一下那个房间。今晚便先借给这些小客人用吧。”
男性鞠了一躬,先转头看了某个方向一眼,半犹豫道:“可是夫人,那个房间是……”
“没关系。”她头也不抬地轻轻摇了摇头。
“我明白了。”他点头应道,转身向某个房间的门走去。
奥萝拉一直在恶狠狠地盯着普拉维斯看,至于普拉维斯,此刻已经被震惊得思考都停止了。
今夜窗外的月光不知怎么的显得非常黯淡。兴许是因为拉着半边窗帘,又或者是未完全散去的雨云。不过它藏于云间也好,被窗帘阻拦也罢,总有那么一些让她隐隐约约中觉得不安的事物,在深处,在暗处就像积雨云一样悄无声息地堆积。。她不再理会傻眼的普拉维斯,亦顶着来自头上的温暖的手的压力,转头向窗外看去。
也许又要下雨了吧。